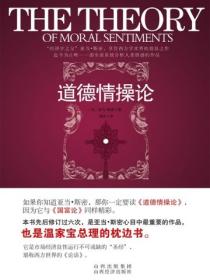第三章 论在行为的优点或缺点的判断上,命运对人类情感所产生的影响
引言
人在赞扬或责备某一个行为的时候,通常依据的都是以下三点:首先是发起这一行为的人的内心意图或情绪;其次是因为这种情绪所产生的身体外部的行为动作;最后是行为实际上产生的或好或坏的结果。一个行为的全部性质和状况都是由这三个不同的方面构成的,当我们根据行为来判断一个人的任何品质时,所依据的也只有这些。
这三种情况中,后两种是不能作为评价一个行为是该得到赞扬还是责备的根据的,没有人持反对意见。再清白无辜或再罪该万死的行为,都有可能在身体上出现相同的举止。就向鸟和向人射击这两种行为而言,都有一个同样的外部动作——扣动扳机。与身体的动作相比,行为的实际后果更无关于褒贬。所以,后果不能成为对行为者的品质和行动进行评判的合宜根据,因为后果并不取决于行为而是取决于命运。
只有那些可以用不同方式预期的,或者至少反映出行为人内心意图善恶的后果,才可以当做行为人该负的责任,或者换句话说,是该承受褒贬的。所以,某一行为应该得到的赞扬或责备、同意或反对,最终都取决于其内心的意图或感情,行为是否适当,是善的动机还是恶的动机。
这一高度抽象凝练的原则,没有人会反对,其正确性是为世人所公认的,没什么可非议的。人们都认为,不同的行为由于种种偶然、以外、无法预料的因素,其结果可能有天壤之别;但是,只要行为的意图或动机是同样的合情合理、慷慨仁慈,那就是好的,应该对行为人表示感激;反过来,如果是同样的不近人情、邪恶歹毒,那就是坏的,应该报以愤怒。
但是,我们的理性尽管完全服从于这种正确的原则,但在面对具体情况的时候,我们对于行善恶的感情还是会受其实际后果的巨大影响,我们的感受几乎总是随之波动。虽然我们很希望将情感放在这一原则的控制之下,但仔细研究一番,会发现,这种愿望在具体情况下却很少会实现。
下面,我们要继续讨论这种人人都能感觉到,却很少有人能充分认识且没有人愿意承认的感情上的矛盾。首先要关注它产生的原因,为什么人类的天性会产生这样的矛盾;其次是考察它的影响,最后是它的结果,或者上帝希望通过它来做什么。
第一节论命运产生影响的原因
不论痛苦和快乐是怎么产生的,其根源有无生命,都会在所有的动物身上迅速激起愤恨或感激。比如我们会对石头碰疼自己而发怒。小孩会敲打它,狗会对它咆哮,性情暴躁的人会咒骂它。但是,稍微一想就会意识到没有感觉的东西不是一个合宜的报复对象。然而,我们会因为这个引起伤害的对象感到不愉快并毁灭它。如果我们忘了对偶然造成朋友死亡的器械发泄的话,会被看做是不通人性的人。
同样,我们也会感激那些给自己带来巨大或频繁快乐的无生命之物。一个刚靠着一块木板逃生的海员,一上岸就用这木板添火,看似不合人情。我们希望他能小心而满怀深情地保存木板。一个人会对他长期使用过的东西怀有爱意,类似某种真正的热爱和深情。如果他损坏或失去它们,那么由此引起的烦恼同所损失的价值相比将会极不相称。我们对于长期居住的房屋,长期享受绿荫的树木,都怀有某种敬意,仿佛它们是我们的恩人。我们会对前者的腐朽,后者的腐败忧郁不快。古代的林中仙女和护家神,即树木和房屋之神,可能就是由那些对此类对象怀有敬畏之情的作者首先提出来的。如果此类对象没有生命,这种感情就似乎是不合情理的。
但是,某一事物要想成为合宜的感激对象或愤恨对象,不仅要能够带来快乐或痛苦,而且还要有能力去感知。如果缺乏这样一种性质,那些**就不可能尽情发泄出来。因为这些**是快乐和痛苦激发出来的,所以我们只有对这个对象报以感谢才能得到情感上的满足;至于没有感觉能力的对象是不可能接受我们的回报的。因此,把动物作为感激和愤恨的对象比较合宜。如果咬人的狗和以触角抵人的牛成为某人致死的原因,那么它们都要受到惩罚。只有杀死它们,公众和亲人才会满意。这不仅是为了生者的安全也是为了报仇。相反,主人会对有用的动物充满感激。我们对《土耳其侦探》中提到的那个官员的行为感到震惊,他刺杀了曾驮着他横越海峡的马,只是害怕它再一次做到使别人出名。
动物不足以成为感激和愤恨的完美对象,虽然它们能带来人们快乐和痛苦,也能感觉到那些情感,但它们仍然不能满足人类的感激和愤怒。我们感激一个人,不仅要让他知道自己是由于过去的行为才得到这一报答,并让他为作出这种行为而感到愉快,感到某人是值得他为之行善的。我们和我们的恩人在情感上是一致的,我们希望自己对自我评价的认定得到他们的认定和尊敬。别人对我们自我评价的认定,令我们很高兴,而我们也希望别人能另眼看待我们。那种通过不断地纠缠恩人要表示感激以强求新的恩惠的做法,常被那些心胸宽阔的人瞧不起。但是保持和增加恩人对我们的尊重,也是大公无私的人颇为认同的事情。如果我们不能理解恩人的动机,他的行为和品质显得就不配得到我们的赞同,那么,即使先前他给过我们很大的帮助,感激之情也会消弱,我们也会不高兴。他的青睐无法取悦我们,我们也不值得努力去对这样一个无足称道的恩人保持尊敬。
相反,愤恨之情主要达到的目的,是使他们意识到自己的痛苦来自他过去的行为,使他因为这而感到悔佷,使他知道他所伤害的人不应该遭受那样的待遇。我们对伤害和侮辱我们的人生气的原因是:他对我们抱有轻视的态度,他只顾自己这种荒谬的自私,他仿佛觉得,别人随时可以为了他的便利而做出牺牲。这种行为是不合宜的,夹杂着粗野无理和非正义性,这比我们所遭受的全部不幸更令人愤慨和恼怒。让他知道他应该怎样对待他人才是正确的,让他感觉他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和做的错事,这常常是我们报复的主要目的。当我们的敌人没有给我们造成伤害,在他的处境我们也会做这样的事,在那种场合,我们不会产生任何愤恨之情,如果我们存有一点起码的正义之心。
所以,任何事物要想合情合理、无可挑剔地得到感激或愤恨,都必须具备三个方面的条件。首先,它在某一场合是快乐的,而在另一场合是痛苦的。其次,它必须有感知那些情感的能力。最后,必须通过有意识的行为产生这些情感,这种意识一方面为他人所赞同,一方面为他人所反对。第一个条件,任何事物能都激起那些感情;第二个条件,使这些感情在各个方面都能得到满足;第三个条件,不仅能完全满足那些情感,而且其能带来强烈而特殊的快乐或痛苦,所以它同样能激起更多的情感。
因此,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给别人带来快乐或痛苦,是激起感激和愤恨的惟一原因。一个人的意愿可能非常地合情合理、仁慈大方,或者非常不近人情、邪恶狠毒,但结果若没能达到他所希望的或善或恶的目的,也没有让人可以激动的理由,由此也很难得到其他人的感激或怨恨。反之,一个人一方面没有值得赞美的仁慈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没有值得谴责的恶意,如果他的行为引发重大的善果或恶果,那么他就能容易得到人们的感激或愤怒之情。在前者,他的优点隐约可见,而后者,缺点油然而生。再者,行为的结果是完全掌控在命运的手中的,所以命运就会对优点和缺点产生影响。
第二节论命运影响的程度
假如最值得称赞或责备的行为,在命运的影响下没有引起预期应有的效果,会使我们对优点或缺点的感觉减弱。反过来,如果那些行为因为偶然的机遇引起了极度的快乐或痛苦,我们对其优点和缺点的感觉就会增强,甚至会超过我们队动机最初的感觉。
1.首先,我认为,某人的意愿有非常善良或非常恶毒的一面,如果还没有产生实际的作用,那其优点和缺点都不能算完整无缺。这种缺乏规律的感情变化,直接受行为影响的人能感觉到,公正的旁观者也能或多或少地有所察觉。一个人为他的朋友谋求一官半职却没能成功,她这种行为会让人觉得他是一个很够意思的朋友,而且应该受到人们的爱戴和尊敬。那么,如果这个人不仅尽力帮忙而且成功地达到了目的,就应该被当做恩人来看待,受到人们的尊敬和感激。但是,假如他感到自己比后者强,我们就不能体谅他。确实,通常情况下,对帮助我们的人和事,我们会抱以感激之情。若一个人对慷慨的帮助过他却未取得成功的朋友的感情与对那个成功帮助了他的朋友所持态度几近相同,那他是宽宏大量的,这两种情感就越接近于精确无误。较之他们所能期待那些情感带来的全部好处会产生更多的快乐,由于这种真诚的宽宏大量为那些他们自己认为值得尊敬的人所爱戴和尊重,从而也会激起更多的感激之情。因此,若失掉了那些好处,不仅仅只是失去了一点微不足道的东西,而是失去了一些东西。所以她们的快乐和随之产生的感激之情当然不是十分完美的。因此,若其他一切情况都一样,只是在助人失败的朋友和助人成功的朋友、最高尚和最优秀的心灵之中,偏爱助人成功的朋友的某些感情会存在细微的偏差。不仅如此,且在这一点上,人类是不公平的,导致人们即使会得到希望的利益但不是靠某个特定的恩人得到,就会对这个具有世上最善良的意图而未能进一步提供帮助的人毋须多加感激。这种场合,对他们影响不同的人分享着她们的感激之情,所以她们只须略表感激。人们常说,我们确信想帮助我们的人会竭尽全力。然而,我们并不因此而感激他,因为他人并不同意,他所做的也并非会有利益。如果公正的旁观者考虑到这一点,也会认为他们比比对行为者抱有太多感谢。如果一个人尽力给被人帮忙而没有取得成功,他自己也不会指望受帮助的人会对他有多少感激,也绝不会像帮忙成功的人那样感觉到自己有助于他人的优点。
即使是对于那些充分相信自己有能力造福于人类人来说,一旦他们的才干和能力的优点由于某些偶然事件的妨害而未能产生效果,这种优点似乎也多少会变成不完美的。那个遭到朝廷大臣的妒忌而未能在和祖国的敌人作战中获得巨大胜利的将军,后来一直悔恨战机的丧失和延误。他的悔恨并不仅仅是为了民众,而是痛惜没能完成一个不仅在他看来,而且在其他人看来都将使自己声名大增的行动。这些想法不能使他满意,同时也不能使别人满意:计划或谋略全部有仰仗于他的才能;完成它并不需要具备比创造它所需要的更多的能力;而且只要容许他以各种可能采用的方法去完成它,并且准许他继续干下去,那么成功是毫无疑问的。他毕竟没有能够完成自己的计划和谋略;尽管他也许会因为拟定了一个宽仁而又伟大的作战计划而得到各种嘉许,但是他仍想表现只有完成一个伟大行动时才能真正表现出来的优点。在一个人几乎要把公众所关心的一件事情办成的时候,削弱他办事的权限绝对是最可恨的不义行为。我们觉得,因为他已经做出了那么多的努力,就应该由于这件事情的完成给他记大功。庞培在卢库卢斯取得胜利时当选为执政官,并把那些应属他人的幸运和勇敢的荣誉集于己身,而遭人反对和质疑。据说,当卢库卢斯未获准完成那一征服战争的时候,甚至连他的朋友也认为他的荣誉似乎是不完美的。卢库卢斯的勇气和行动早已把这个战争推进到几乎任何人都能将它结束的地步。如果一个建筑师的设计根本没有被付诸实施,或者这些设计被稍许改动导致了建筑物效果的减弱,他必然会感到羞辱。然而,设计完全是建筑师的事。对于行家来说,和在实际施工中一样,在设计中也能充分展现出他的天才。不过即使对最富有才智的人来说,设计也并不一定能给他带来与建成一座辉煌壮丽的建筑物媲美的快乐。在这两种情况中,他们都可以表现出相同的天才和鉴赏力。但是,效果却大相径庭:从前者得到的乐趣有时根本比不上后者带来的惊奇和赞美。我们相信许多人的才能要高于凯撒和亚历山大;相信他们处于同样的环境中能够作出更伟大的行动。但是,我们并不会以惊奇和赞美的眼光来看待他们。在所有的时代和国家里,人们都会以同样的眼光来看待上述两位英雄,发自内心的冷静的评价还可能使我们更加赞赏他们,但是他们却缺少伟大行动的光辉带来的这种赞赏。卓越的品德和才干并不能也不可能产生同卓越的业绩一样的效果,就算是对承认这种卓越品德和才干的人也不能产生同样效果。
就像在忘恩负义的人看来。如果有人愿意行善却未能成功,其优点好像会因失败而缩小;企图作恶而未能成功的嗯,其缺点也一样会缩小。犯罪是唯一的例外。这种罪行直接影响政权本身的存在与否,当局对它的态度当然要比对其他任何罪行都更加小心地加以提防。在处治叛逆罪时,君主所愤恨的是它直接危害于他本人;而在判处其它罪行时,君主所愤恨的则是它危害于别人。在前一种场合,他所发泄的是来自于自己的愤恨;在后一场合,他的愤恨只是由于对自己的臣民的同情和体谅。所以,在前一场合,因为他是为了自己而处罚罪犯,所以他所作的判决很容易比公正的旁观者所能同意的更加严厉和残忍。而且,在叛逆罪较轻的情况下,他也会勃然大怒,而且跟在其他情况下不同,他不能等到罪行发生,甚至不能等到作出犯罪尝试就勃然大怒。一次图谋叛逆的商议,甚至仅仅只是一种叛逆的企图,只是一次叛逆的谈话,虽然没有采取什么行动,但是在许多国家都是要受到同犯下实际叛逆罪一样的惩戒。至于只是有所图谋而未予尝试的其他任何罪行,根本不会得到什么惩罚,更谈不上什么重刑。可以这样说,确实没有必要将设想犯罪的图谋和犯罪的行为归为同样的邪恶行为,因此不应使它们遭到同样的惩戒。也可以这样讲,当事态发展到紧要关头时,我们能够做出许多自己感到全然不可能完成的事情,还能够采取各种措施来完成它们。然而,当叛逆的图谋已经发展到进行最后尝试的程度时,这个理由就不能够成立了。虽然几乎没有一个国家的法律,会将一个用手枪射向他的仇人但未击中的人判处死刑;但是根据苏格兰古老的法律,即使那个人击伤了对方,如果后者没有在随后一定时期内死亡,前者也不应被判处死刑。但是,人们对这种罪行的愤恨之情是那么地强烈,以至于对那个表明自己会犯这种罪行的人的恐惧是如此之大,导致在所有国家里只是企图犯这种罪行的人也会被判处死刑。可对那些企图犯较小罪行的人的判处,却往往很轻。那个小偷在把手伸进邻人的口袋行窃之前被人当场抓住,对他的惩罚仅仅是使他丢脸而已。如果他有时间偷走一块手帕,那么面临他的就是死刑了。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人,在邻人的窗前置放梯子、尚未进去就被人发觉,也不会被处死;企图强奸妇女的人不会受到像强奸犯同样的惩戒。虽然诱奸妇女要受到严厉的惩罚,但是企图诱奸一个已婚妇女的人却根本不会受到惩罚。我们对仅仅是企图造成危害的人所产生的愤恨,很少会强烈到让我们为使他受到跟实际造成危害的人相同的惩戒而出庭作证。假如他真的做了那件坏事,我们就自然地认为他应该受到那种惩罚。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随着判决而来的高兴减轻了对他残暴行为的愤恨;在后一种情况下,我们对有人遭到不幸感到的痛苦增强了对他的残暴行为的憎恶。然而,在两种情况下,因为他的意图同样都是相当罪恶的,所以他实际存在的缺点都是一样的。所以在这一方面,所有人的情感中都存在着一种不那么规律的东西,并且,我认为,所有最文明的国家的法律都和最野蛮的国家的法律一样,有一种必然的用来减刑的条例。无论在什么地方,文明人自然的愤怒不会因罪行的后果而增强,而他们从仁爱出发总是会有意免除或减轻惩罚。相反的是,当某种行为并未发生实际后果时,野蛮人对它的动机往往不怎么敏感或追根究底。
如果一个天良未泯的人由于一时冲动,或者受坏人**,曾经打算犯罪甚至有过实际行动,但幸运地因为一些无法阻止的偶然事件或人而尚未完成,如果他良心尚存,就一定会在今后的生活中把这个偶然事件看做是对他自己的一个明显而重大的解救。他会非常感激地想到,神曾经如此仁慈为怀地把他从正要深陷下去的罪恶之中挽救了出来,并使他在有生之年不致于满怀恐惧、自责和悔恨。虽然他并没有真的犯罪,但是感受到了同犯罪一样的内疚,就像他实际上犯下了曾下很大决心去干的那桩罪。虽然他知道并不是因为自己善良阻止了犯罪,但是想到罪行并未发生,就能给他带来很大的安慰。他依然认为自己不应该受到多大惩罚,招致多大的愤恨和责难。这种幸运或者减弱了、或者消除了他的一切负罪感。回想起自己曾对这一罪行下了多么大的决心,他感到再也没有其它结果能比这使他把免于犯罪看作更重大而更不平凡的奇迹。因为他仍然可以想象自己已经免于犯罪,并且抱着那种惶恐的心理(处在安全之中的人有时可能抱着这种心理回想起自己曾处于灾难边缘这种危险境地)回顾他那平静的心灵所面临过的危险,一想到这一点,他就会觉得胆战心惊。
2.这种命运影响的第二种后果是:当行动者的行动偶然引起我们过多的快乐或痛苦时,除了由引起行动的动机或感情造成的后果之外,还会促进我们对行动优缺点的感情。然而,那种行动让人感到快或不快的结果虽然在行为者的意图中并没有什么值得称赞或责备的东西,起码至少没有达到值得我们加以称赞或责备的程度,它还是经常会给行为者的优缺点投上某种影像。所以,就连带来坏消息的报信者也会使我们感到不快;相反,我们对带来好消息的人会产生自然而然的感激之情。在某个瞬间,我们把这两者看成是我们命运好坏的根本,多多少少会带着这样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就像他们真的造成了这一结果,实际上他们只是报告了这个结果而已。最早给我们带来愉快消息的人自然变成了暂时的感激对象:我们热烈而满怀深情地拥抱他,在感受到幸运的瞬间,就像得到了某些重大的帮助一样,高兴地给予报答。根据所有朝廷的习惯,带来胜利消息的官员都是有资格得到引人注目的晋升,因而在外作战的将军总是挑选一个他最看好的人去完成这一美差。相反,最初为我们带来悲伤消息的人自然地成了暂时的愤恨发泄对象。我们不可避免地带着烦恼和不安的神情看他;粗暴无礼和不讲道理的人往往会向他发泄他的消息所引起的愤怒。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砍掉了那个最早向他报告令人生畏的敌人已经逼近消息的人的脑袋。当然,用这种方式来处罚带来坏消息的人,看来绝对是野蛮残忍和毫无人性的;但是,报答带来好消息的人却并不会引起我们的不快;我们认为这对于国王的恩典来说是非常合适的。可是,既然前者没有什么过失,后者也没有什么优点,为什么我们的做法会这么不同呢?这是因为,任何一种理智好像都足以使我们允许别人流露友好仁慈的感情;但是要我们对别人发泄不友好的、狠毒的感情产生同情,却都需要具有极其坚强的、丰富的理性。
除非那个邪恶和不义的个人意图企图直接针对它们的合宜对象,虽然我们一般不愿意去谅解一些不友好的、甚至是狠毒的感情,主张规定决不允许这些感情发泄,但是在某种情况下,我们终究还是会放宽这种严酷的要求。当一个人因疏忽而对别人造成某些无心的伤害时,我们通常但凡谅解受害者的愤恨,就会赞成他对冒犯者所施加的惩罚,远远超过那个没有因此带来这种不幸后果的冒犯者应当得到的惩罚。
一定程度的疏忽,即使没有对任何人造成任何损害,好像也应该受到惩罚。这样,如果某人事先没有警告可能通过的路人,就把一块大石头抛过墙头落在马路上,而自己还并不在意那块石头可能落在的地方,他无疑是要受到惩罚的。就算它没有造成什么危害,一个忠于职守的警察也处罚这种荒唐的行径。那个干出这种坏事的人对别人的幸福和安全表现出一种蛮横无理的蔑视态度。他的行为绝对是一种对别人的侵害。他肆无忌惮地使旁人面临着一个正常人所不愿面临的危险,显而易见,他缺少那种应当正确地对待同伴的意识——这恰恰是正义和社会的基础。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讲,严重的疏忽和恶毒的图谋几乎是相同的。当这种粗心大意产生某种不幸的后果时,干了这种坏事的人经常要受到严厉惩罚,就像他真的有意造成那些后果一样;他那轻率和无礼的、应该受到某种惩戒的行为,被当作了残暴的、应该严加惩处的行为。所以,如果他因为上述轻率行为而意外地砸死了人,那么,按照许多国家的法律,尤其是苏格兰的古老法律,他就会被处死。虽然这种处置无疑是太过严厉了,但是它并不完全是违背我们情感的。对不幸的受难者产生的同情激起了我们对他那愚蠢而缺乏人性的行为的正当的愤慨,但是把只是不小心地把石块丢到马路上且未伤人的人送上断头台,我们天赋的正义感对此并不赞同。考虑到这种不同,我们认为,人的义愤(甚至包括旁观者)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行为的实际后果。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在差不多所有国家的法律中都可以看到对此严加惩处的规定;如前所述,反之,则按照法律,一般可以从宽处罚。
还存在另一种疏忽,它只存在于对我们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各种后果缺乏使人深深为之不安的疑虑和谨慎之中。在坏结果没有出现之前,人们绝不认为缺乏这种高度的谨慎是应该受到责备的,而相反的认为这种品质倒是应该受到谴责的。对什么事情都胆小谨慎,从来就不被认为是一种美德,而被看成是一种比其他东西更不利于行动和事业的懦弱的品质。但是,当某人由于缺乏这种过分的小心,碰巧对别人造成损害的时候,法律通常是要强制他赔偿损失。比如,根据阿奎利亚的法律,因不能驾驭一匹突然受惊的奔马而恰好踩到了邻居的奴隶的人,需要支付损失。当此类偶然事件发生的时候,我们通常认为他不应该骑这样一匹马,并且认为他试图骑这匹马也是非常轻率的、欠考虑的举动。虽然没有这一偶然事故,我们不仅不会作出这样的反应,甚至会认为他拒绝骑这匹马是胆怯懦弱的表现,是对某种只是可能发生但没有必要多加小心的事情心存疑虑的表现。那个因这类意外事件而偶然伤害了别人的人,他自己似乎也觉得自己的过失应该受到责罚。他自然地奔向受难者,向他表示自己对所发生的事件的歉意,并试图用各种方式表示谢罪。如果他有理性,就必然会想赔偿这个损失,并且尽其所能来缓解受害者的愤怒和不满。他意识到受害者心中容易产生这种愤恨,不道歉、不做赔偿则会被认为是一种极为野蛮和无理的行径。可是,为什么要他道歉而其他的人却大可不必了呢?既然他和别的旁观者一样清白无辜,为什么就是要他对别人的不幸负责呢?这件难事看起来确实不应该强加于他,因为在最公正的旁观者看来,另一个人出格的愤怒并没有什么不妥,所以把重担强加给他确实有些不合适。
第三节 论情感变化无常的根本原因
行为结果的好坏,对行为者和旁观者的情感造成的影响正是如此。正因如此,虽然我们极不情愿,左右世人的命运却在某种程度上掌控着人们对自己和他人品行的看法。根据结果而非动机对事情作出判断,是从古到今,人们从未停止抱怨的、使美德受到巨大伤害的行为。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事情的结果从不由行为者决定,所以它不应影响我们对于行为者的优点与合宜性的判断——这是人们都同意的普通格言。但是,当我们被卷入其中,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我们都会发现自己的情感很难与这句公正的格言相符。无论行为的结果令人愉快与否,我们都会因此对其谨慎性给予或好或坏的评价,而且几乎总是能够极其强烈地感觉到感激或愤恨,以及动机的优缺点。
然而,当上帝在人们心中播撒这种变化无常的种子时,他似乎也像通常那样已经考虑到了人类的幸福和完美。如果仅仅具备危险的动机,恶毒的感情便足以激起我们愤恨,那么,只要我们怀疑某人具有这种动机和感情,即使他根本没有将其付诸行动,他也会成为我们不共戴天的仇人。这样一来,情感、思想和打算都可能会成为惩罚的对象;而且,如果人类对它们的愤恨与对实际行为的愤恨达到同等强烈的程度,如果没有产生任何行为的卑鄙念头,也像卑鄙的行为一样能够唤起复仇之心,那么每个法庭都将成为真正的宗教审判庭。最清白无辜和小心谨慎的行为也仍然会被猜疑为出自邪恶的意愿、目的和动机的举动,无法得到安全的保障;并且,当邪恶的意图和邪恶的行为一样遭人愤恨时,人们同样会面临惩罚和愤怒。因此,上帝将实际犯罪的行为与犯罪的企图,以及直接使我们产生恐惧的行为,都理所当然地变成了人们惩罚和愤恨的对象。虽然情绪、动机和感情都是根据人们冷静而理性的行为来进行全部优点或缺点的判断,但是人们内心中伟大的仲裁者还是置之于各种法律限制之外,并将其留给自己那从不会误判的法庭来进行审理。因此,人类这种关于优点或缺点的情感所具有的不规律性,虽然初看起来有些荒谬可笑、不可理喻,但却是有益和有用的,在其基础上产生了具有重大意义的法则,即在这个世界上,人们只应为他们的行为受到惩罚,而不应为他们的动机和想法受到惩罚。但是,如果留心观察,我们就很容易发现,任何一种人性都在证实上帝的深谋远虑;即便是人类的缺陷与愚钝,也会使我们对上帝的智慧与仁慈钦佩不已。
人类变化无常的情感并非百无一用。正是由于这种无规律的变化,那些有帮助别人的企图而并未成功的行为,以及纯粹善良而慈悲的意愿才显得并不完美。人是需要有所行动的,人们总是愿意竭尽所能地改善自己和他人所处的外部环境,让更多的人得到幸福。消极的慈悲之心,或仅仅将自己想象成人类的朋友必定无法使他满足,因为他在内心深处更希望自己能够为世界的繁荣尽自己的一份力。上帝教导他:为了达到目的,必须要全力以赴,除非他实际上已经达到了这些目的,否则无论是他自己还是别人都不会对他的行为感到十分满意,也不会给予他最高的赞美。上帝使他知晓:赞扬缺乏善行优点的好意,是不可能激起世人最大的、甚至是他自己的最高度的赞扬声。那个除了他全部谈吐举止表现出最正直、最高尚和最慷慨的感情以外,没有完成一次重要行为的人,即使他的无用仅仅是因为缺少帮助别人的一个机会,也很可能没有资格得到什么大的报答。我们还可以拒绝给他这种报答而根本无需受到谴责。我们还可以质问他:你都干了些什么呢?你干了些什么实实在在的好事才使得你有资格获得这么大的回报呢?我们尊敬你,爱戴你;但是并不是对你欠下了什么。真正去报答具有只是由于缺少助人机会而没有发挥作用的那种潜在美德的人,并给予其荣誉和晋升,虽然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应该的,但不能说一定是合乎适宜的,因为荣誉和晋升是非凡善行的结果。相反,在没有犯罪的情况下,仅仅因为内心的感情波动而施加惩罚,这绝对是最粗野和残忍的暴行。如果仁慈的感情在几乎成为罪过之前就被付诸行动,那似乎应该得到最高度的赞扬。但是,狠毒的感情化为行动基本上不会过分迟缓或多加考虑。
其实值得注意的是:对肇事者或者受害者来说,无意之中干下的坏事都应当被当作是一种不幸。所以,上帝教导人类:一定要尊重自己同胞的幸福,要唯恐自己会做出任何可能伤害他们的事情,哪怕全然是无意的;如果谁无意中不幸地给自己的同胞带来了灾难,他就必须担心自己所感到的那种强烈愤恨会冲自己突然爆发出来。在古代未开化的人的家教中,献奉给某神的圣地,只能在一些庄重或者必要的场合才可以踩踏。而且,即便是出于无知而违反上述规定的人,从践踏圣地那一刻起就成了一个赎罪者,在他完成合适的赎罪行为之前,他将遭到执行这一规定的法力无边而肉眼看不见的神的无情报复。同样,上帝以其智慧将每个清白无辜者的幸福化为圣地,将其保护起来防止他人的窥视;既不允许任意的践踏,也不允许任何不知情和无意的侵犯,这样也就不需要赎罪,不需要做出与这种无心的伤害相应的补偿。充满人性的人在无可责备的疏忽中意外地造成了别人的死亡,虽然没有犯罪,他仍旧感到自己是一个赎罪者。于是在其一生中,他把这一事故看成是落到自己身上的最大不幸。如果受害者的家境贫困而他自己尚过得去,他就会把赡养受害者家属的责任毫不犹豫地承担起来,并真诚地认为他们无需什么优点就应当得到一切恩惠和良好的待遇。如果受害者的家境尚可,他就会通过各种认过之举和各种悲伤的表示,做自己所能想到的或他们所接受的各种好事,试图补偿他所造成的损失并尽可能地安抚那些家属。对因他的过错而产生的愤恨之情来说,这种过错虽然是偶然的,但确实是巨大的;这种愤恨或许是自然的,却又是极不公正的。
一个清白无辜者因为一个偶然事件造成了一些过失,如果这是他自觉地和有意地造成的,他必然就会受到最严厉的公正的指责。此人所感到的痛苦曾成为了古代和当代戏剧中最精采和最吸引人的几幕。正是这种虚构的罪行场面——如果允许我这样称呼的话——构成了希腊戏剧中的俄狄浦斯和裘卡斯塔的所有不幸,也构成了英国戏剧中的蒙尼米亚和伊莎贝拉的所有不幸。虽然他们之中并没有人犯下甚至极轻微的罪行,却统统成了最大的赎罪者。
但是,尽管这一切看来都是情感的不规则变化,如果一个人不幸地犯下了那些他并非有意犯下的罪行,或没有能够成功地实现他有意做的好事,上帝自然也不会让他的清白无辜得不到些许安慰,也不会让他的美德全然得不到些许回报。那时,他应该会求助于那正确而又公平的格言:那些不依我们的行为而定的结果,不应减少我们该得到的尊敬。他唤醒了心中全部的坚定意志和高尚的感情,尽量避免自己以现在的面貌而是以应有的样子出现在人们的面前,他希望人们看到的是他那慷慨的意愿最后得到的成功,哪怕人们的感情都很正直和公正,甚至和自己全然一致。一部分很正直而又富于人性的人,完全赞成他如此这般按自己的观点来激励自己所作的努力。他们以心灵中的全部伟大而高尚的情感去纠正自己心中的人性的不规则变化,并努力以相同的眼光去看待自己那些没有获得应有成功的高尚行为,就算在没有作出任何大的努力的情况下获得成功,他们也会自然而然地倾向于用这种眼光去考虑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