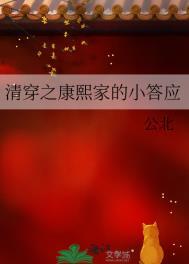第37章
她这段时间虽掌管后宫, 可处处不得意,处处不顺心,表面上人人都对她很恭敬顺从,背地里阳奉阴违, 如今一个常在都敢当众违抗她, 这几日盘查十四阿哥落水之事受到的阻碍让她心里憋着一股火,此时这股无名火燃到最盛, 她亲自起身, 朝着常常在走过去。
啪啪啪!
她朝着常常在的脸狠狠扇了三巴掌,长长的护甲划过常常在的脸, 划出三道红痕。
“她打不得,本宫可打得了你?”宜妃语气森冷。
对上宜妃凶狠凌厉的目光,常常在退缩了一下,刚才反驳的气焰顿时消失殆尽,她的确不敢反抗宜妃,她只是常在, 方才是怒极才口不择言冲撞宜妃,此时理智回笼, 她捂着自己传来火辣疼意的脸, 低头没有说话。
捕捉到常常在眼底的害怕后, 宜妃嘴角微扬,出了一口气, 目光一转看向更得宠的徐答应, 皇上近半年来对这个徐答应是恩宠有加,宫里传言徐答应的恩宠已经盛过她, 她剜了徐答应一眼。
“本宫并非无凭无据,有十四阿哥的证词在, 本宫可是有凭有据,是不是你们指使,待会一审便知,你们这会嘴硬,只会让你们吃尽苦头,本宫是给你们机会坦白而已,本宫不会冤枉你们的,来人,把人通通都带上来。”
徐香宁回头一看,只见她跟常常在身边伺候的人全部被带进来,同时还有十几个她瞧着面生的人,其中有三人全身伤痕累累,都走不成路,脸色灰败,一看就是被用刑了。
顿时大堂内跪满了人,宜妃已回她的座位上坐着。
“徐答应,常常在,你们可听好了。”
宜妃开始审问,挑着几个人问过去,徐香宁跪在最前面,其实看不到谁在回话,只是稍微听明白了一些。
十四阿哥落水是因被人从背后踢了一脚,但十四阿哥没看到凶手,十四阿哥身边伺候的人赶来时看到了凶手的侧脸,指认了一个叫赵树炳的小太监是推十四阿哥下去的人,是在御茶房干活的小太监,赵树炳一开始没有说出是谁指使,后被慎刑司用刑才肯说出“实情”,他是被人指使,对方给了五十两银子与一根金藕莲花簪子,他一时财迷心窍答应对方的要求。
“那你说这个人是谁?可在现场?”
赵树炳被打得已经快跪不住,用颤颤巍巍的手指向小邓子,徐香宁回头便是看到这一幕,被指认的小邓子眼底露出震惊,立即否认:“奴才没有,奴才没有,奴才并未给过他五十两银子,奴才没做过此事。”
“可有不少人看到你跟他接触,有谁看到他们私下接触?”
宜妃一开口,有两个太监加上一名宫女出来指认他们曾见过小邓子与赵树炳私下接触,两人在隐蔽处互相传递着什么,因被宽大的袖子遮住,他们都没看清互传的是什么。
指认的宫女与两个太监均在御茶房干活。
那五十两银子跟那根金藕莲花簪子被当成物证呈上来。
“翠玉,你把那根金藕莲花簪子拿给徐答应看看,是不是她的簪子?”
翠玉端着盘子拿近给她看,徐香宁拿起那根金藕莲花簪子细看,其实她也不知道是不是她的簪子,那些首饰平日里都是张嬷嬷在管理,她一点都不上心,她拿起时只是为了给后头的张嬷嬷看几眼,她看到张嬷嬷以极小幅度点头,她便知道这是她的簪子,只是为何被别人拿到就不得而知。
“徐答应,这是你的簪子吗?”宜妃再问。
恵妃倒是先回答了,“这簪子,本宫瞧着眼熟,这簪子是本宫在徐答应初次侍寝后赏给徐答应的,为何会出现在这?”
恵妃的话让宜妃更加得意,仿佛经过她缜密的盘查,已找到推十四阿哥下水的真凶,她呵斥,旗头上步摇的珠子都晃动两下,怒不可遏:“徐答应,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有什么话可说的,还说不是你在背后指使他人谋害皇嗣?”
“徐答应,本宫与你无冤无仇,你为何要害本宫的孩子?我的孩儿因落水可是刚从鬼门关走一趟,你为何如此狠心?”德妃哽咽,目光中含着对她的不解与复杂。
徐香宁不理会德妃的话,而是定定地看着宜妃,“这是我的簪子,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妹妹我也不得而知,不过既是我的簪子,是不是十四阿哥落水一事与常常在无关,那宜妃娘娘为何在刚开始指责我跟常常在,因常常在无辜,为自己辩解竟招来宜妃娘娘的毒打,宜妃娘娘可承认刚才是不是指责错了人,让常常在蒙受不白之冤?”
宜妃一愣,一时不知如何回话,过了须臾才反应过来回道:“常常在刚才以下犯上,冲撞了本宫,本宫打她是治她以下犯上的罪。”
“宜妃娘娘刚才可不是这么说的,宜妃娘娘可是指责我们两人到御花园勘察地形意图谋害皇嗣,这里明明只有我的簪子,为何宜妃娘娘要指责常常在?”
“所以你是承认是你在幕后指使下人谋害十四阿哥的性命?”
“我没有承认,我没谋害过皇嗣,更没有让人推十四阿哥下水,既然娘娘已经审问完了,是不是该轮到我问这些人了?”
“宜妃,这事还没定论,诸多蹊跷,是非曲直,不能只听一方之言,徐答应,你问吧。”荣妃开口,点头同意她问话。
宜妃想说什么又忍下去。
徐香宁站起来,将跪着这群人扫视一圈,向刚才指认小邓子跟赵树炳互传东西的三个人问道:“你们说你亲眼看到我宫里的太监小邓子与这个人互传东西,可是千真万确?”
“奴才不敢说谎。”
“是奴才亲眼所见。”
“是真的。”
三人回答的话不一样,但都承认是亲眼所见。
“你们见到小邓子与这个人……”徐香宁看向十分虚弱的人,“你叫什么来着?”
“奴才赵树炳。”
“好,赵树炳,你们见到小邓子跟赵树炳传过几次东西,一次,两次还是三次?”
几人两两对视,没有立即作答,略显迟疑。
“到底是几次?你们不是亲眼所见吗?”
“奴婢见过两次。”
“你叫什么?”
“回答应,奴婢是迎蓉。”
“你们呢?几次?”
一个穿紫色布袍的太监,身形微胖的太监说他只见过一次,另外一个身形瘦削一点的太监说他也只见过一次。
“好,那请问赵树炳,你跟小邓子传过几次东西?”
“奴才也不记得了,奴才跟小邓子关系熟稔,他常常给一些碎银给奴才,让奴才办事,小到要一杯姜茶,大到要奴才推十四阿哥下水,所以奴才也记不清。”
“小主,他说谎,奴才从来没有让他谋害十四阿哥,奴才有时的确给过他一些碎银求他办事,但奴才没有让他谋害十四阿哥。”小邓子哭喊,吓得眼泪直流。
徐香宁是知道一些的,她一个小答应先前无宠时,要一杯姜茶都是要给点碎银给御茶房的人,更别说偶尔她嘴馋,想要一点份例之外的东西,自然要花点银子,目前是这个赵树炳咬死是小邓子给银两给他,让他推十四阿哥下人,关键是在这个赵树炳身上。
“那赵公公,这五十两跟这根簪子是否是小邓子一次□□到你手上?”
“是。”
“哪一日,小邓子那日穿的是什么颜色的衣裳,你又穿何种颜色?”
“七月三日,小邓子穿的是紫色,奴才穿的也是紫色。”
七月三日是十四阿哥落水的五天前,紫色是小太监穿得比较多的颜色,太监只能穿紫色与深蓝色,徐香宁又看向另外三个人,“你们见到小邓子与赵公公互传东西是几月几日,又是穿什么颜色的衣裳,我要你们同时说。”
三人说的都不一样,迎蓉说的是六月二十日,穿的蓝色布袍,而那个身形微胖的奴才说的是七月三日,紫色布袍,另外一个瘦削的太监说是六月二十五日,紫色布袍。
“马公公是吧,你跟赵公公说的都是七月三日,紫色布袍,那些银两跟簪子又是一次交到赵公公手上,是不是你看到的那次便是小邓子把银两簪子交给赵公公那次?”
马公公犹豫,还是点点头。
“那既然这样,你跟赵公公同时说出小邓子跟赵公公□□的地点是在哪里,你是哪里看到他们互传东西的,我要你们同时回答!我倒数完三二一,你们便开始回答,三、二、一……”
“奴才……奴才好像……”马公公开始额间冒汗,犹犹豫豫,一时说不上来,而赵树炳同样没立即回答,虚弱地伏在地上,吐出一口血,整个人晕过去了。
明眼人已经能瞧出里面的端倪,而宜妃不是愚笨之人,只是她先前的审问已经架在那儿,若这会她承认她错了,不仅给了徐答应等人硬生生的把柄,更给了荣妃恵妃两人把柄,这个赵树炳之前怎样都不肯开口,她让人把他关进慎刑司,严加拷问之下他才开的口,指认徐答应身边的小太监,都这样了,赵树炳还会说谎吗?
他为什么要说这个谎?他被慎刑司拷问,是性命不保,实在撑不住才说出一个邓公公,分明是要保护徐答应之人,不然早就一开始他就说出邓公公,何必遮遮掩掩,非要上刑才说出他是收受邓公公的贿赂,替人办事。
只是眼下赵公公昏了,证据不实,徐答应再追问下去,怕是更加没有定徐答应的罪,没法定徐答应的罪就等于承认她先前一连好几天的盘查审问都错了。
宜妃不想承认她错了就更要定徐答应的罪,她心一横,怒道:“徐答应,你刚才是不是逼迫赵公公不敢说实话了,人证物证俱在,你还想抵赖不成,来人,把徐答应宫里的人通通给本宫压住,尤其是那个邓公公,他竟然明目张胆地谋害皇嗣,把他拖下去先打十大板子,看他说不说实话,还有徐答应,此事你抵赖不得,十四阿哥落水前明明见过你,十四阿哥身边伺候的人也亲口说过见到你跟十四阿哥说话,你竟然还想抵赖?”
“小主,救我。”
眼看着小邓子要被拖下去,十大板子下手重一点能把人打残废,徐香宁不知谁要诬陷她,眼下顾不得那么多,她护在小邓子面前,对上坐在上面的宜妃,“宜妃,事情还没查明,娘娘不能屈打成招,德妃,你真的相信我会害十四阿哥吗?我可是没有子嗣之人,我为何要害十四阿哥,德妃,真正害十四阿哥的人还没找到,娘娘,找不到凶手,娘娘便一直要担心十四阿哥的安危,这是娘娘想要的吗?”
“伶牙俐齿,来人,给本宫塞住她的嘴,人证物证俱在,不容她狡辩,把邓公公拖下去,徐答应若拦着,连徐答应一起拖下去!”
宜妃一声令下,有好几个人围住他们。
常常在也出来护人,常常在站出来,她身边伺候的人自然也护着自己的主子,场面瞬间乱成一团,十几个人纠缠在一起,互相拉扯殴打,有人被打得嗷嗷大叫。
康熙过来时便是见到这样一幕。
“这是在干什么?”
康熙一身蓝芝麻地单纱袍常服,青缎鞋袜出现在大殿里,一脸沉色,周身散发着冰冷的气息,让人如坠冰窖,闹哄哄的众人一下子静下来,纷纷跪下来行礼。
“参见皇上,皇上圣安。”
“这是在干什么?”
康熙再问一遍,已经到盛怒的边缘,他环扫一眼众人,目光锐利,气势威压,“谁来告诉朕,这是在干什么,在闹什么?”
康熙第一眼先看到头发凌乱,旗头都歪了的徐氏,挽系在脖颈处的白色领子亦已扯出来,衣裳不整,脸上还有一道红痕,整个人凌乱落魄中带有一种雄赳赳气昂昂的诡异感,别人急着整理衣裳,徐氏硬挺挺地跪在那,没有动作,只是撇着嘴,昂着脖子,仿佛受了天大的冤屈,他是看出来了,她是在与别人打架,她刚才发狠扯别人头发,他倒是瞧见了。
一群人都在打架,把这皇宫当什么了,不成体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