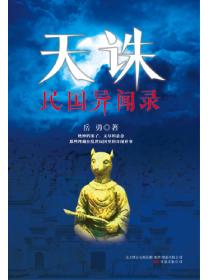渔杀
民国二十九年的冬天,似乎比往年来得更早些,立冬未至,天地间便冷雨霏霏,酷寒逼人。我的七爷爷,仍然披着蓑衣,每天到绣林河上捕鱼。
我的七爷爷学名叫岳满仓,住在绣林城北门外的太平村。村旁流过一条小河,叫作绣林河。绣林河是长江的一条支流,河面不宽,自北向南一路蜿蜒,从绣林城中穿城而过。七爷爷是绣林河上的一名渔夫。
七爷爷捕鱼,既不用渔网,也不用渔叉,他用的是滚钩。滚钩亦叫粘钩,它有一条近百米长的粗大结实的主纲线,主纲线上每隔三四公分拴有一条一米多长的脑线,每条脑线末端系着一把钢丝铁钩。近百米长的主纲线上,总共挂着两千多把铁钩。使用的时候,选定河底平坦鱼儿众多的河段,在河两岸各立一个木桩,把成排的滚钩横拦江河,设于水中,把主纲线两端系紧在河岸两边的木桩上。通常情况下,一个河段要布置两三套这样的滚钩,形成两三道密密的“钩帘”。大鱼自水中游来,遇到帘子似的成排铁钩拦阻,当它掉头摆尾转变方向或企图穿越时,身体碰到铁钩,锋利的钩尖钩进了鱼体,鱼儿疼痛挣扎,碰到的铁钩越多,钩住鱼体的滚钩也就越多,最后只能是在劫难逃。因为铁钩有倒刺,就像强力胶水一样,一旦粘上就绝难甩掉,所以民间也把它叫作“粘钩”。
七爷爷每天傍晚划着小船到绣林河上放钩,第二天清早出来起钩,粘钩上挂着的多是鲤鱼、青鱼、鲇鱼之类体形较大的鱼,偶尔也能捕到一二十斤重的大家伙。趁早挑到绣林城里卖了,换些柴米油盐回来,乐呵呵过上一天。
一进腊月,天就越发地冷,更冷的,是人的心。轰隆隆的枪炮声越来越近,日军一个联队越过绣林河上游的横山县城,直扑绣林城。绣林乃三国古城,两省通衢,扼荆楚之要冲,实为湘鄂边界的一个军事重镇。驻防绣林城的,是国军第77师辖下的一个步兵团,团长叫包国安,虽然脾气暴躁,但打起仗来却是一把好手。日军从绣林城东南西北四门发动数次进攻,硬是教他给打了回去。日军联队长吉井一雄只好将部队驻扎在城外,相机行事。如此一来,可就苦了城外的老百姓,鬼子兵天天在村庄里扫**,村民们再也没过过一天安宁日子。
这一天傍晚,七爷爷照例像往常一样,划着小船到绣林河上放钩。在距离绣林城河道口不远的一个拐弯处,他忽然看见朔风劲吹的水面上漂着一条乌篷船,船上站着四五个人,有人拿着长长的竹篙在河里探着深浅,有人负手立在船头看着两岸风景。七爷爷把小船从后面靠上去,这才看清那几个人的身形相貌,甚是陌生,不像是附近村庄的人。他顿时心生警惕,用力咳嗽一声,冲着那几人一抱拳,呵呵笑道:“几位可真有雅兴,大冷天的,居然还到这绣林河上看风景。”
乌篷船上的几个人吃了一惊,侧脸一瞧,这才惊觉有人驾船悄然靠近。站在乌篷船尾的两名大汉顿时紧张起来,手下意识地往腰间摸去。负手站在船头看风景的那个瘦高个儿望了二人一眼,用眼神制止了他们,冲着七爷爷一抱拳说:“这大冷天的,您不也在这河上漂着吗?”
七爷爷咧嘴一笑,说:“我是这绣林河上的渔夫,不管寒暑,一年四季都在这河里讨生活。”他上下打量对方一眼,“听口音,几位不像是本地人吧?”
瘦高个儿从船头走下来,说:“咱们几个,是从北方来的。”他目放精光,盯着七爷爷问,“您是……”
七爷爷说:“我姓岳,在家里排行老七,大伙都叫我岳老七。”
“原来是岳七爷,失敬。”那人冲着他略一拱手,说,“其实我们冒着寒风来到这绣林河上,并不是为了看风景。我们是来寻找绣林银鱼的。家母患病在床,医生说要寻一条两斤重的银鱼,晒干后制成银鱼干做药引子。银鱼可是少见的鱼种,我们打听了好久,才知道这绣林河里有一种绣林银鱼,正适合做药引,所以就过来碰碰运气。”
“您还真没说错。咱们这绣林河里,的确有一种银鱼,乡下人叫它面条鱼,此鱼身形细长,通体透明,在淡水鱼中十分罕见,不但味道鲜美,而且药用价值极高。因其色泽如银,且为绣林特产,故称绣林银鱼。这种鱼生长极其缓慢,一般都不足一斤,两斤多重的银鱼,已是极其罕见。而且这种鱼一般在春季繁殖生长,夏秋季节才能捕到,现在已经到了隆冬时节,想要捕到绣林银鱼,可不是件容易的事。”
“就是,我们也深感为难。”那人想了一下,忽然眼睛一亮,抬头瞧着他,“听您的口气,似乎您有办法?”
七爷爷是个古道热肠之人,当下点点头说:“既然是要拿银鱼做药引子救令堂,就冲您这份孝心,我也不能不管呀。”
“真的?”那人眉头一展,道,“有您这位行家出手,在下可就不用发愁了。您放心,只要您能帮我们捕到银鱼,我一定出市价十倍的价钱收购,绝不让您吃亏。”
七爷爷说:“救命要紧,价钱好说。只是我若捕到银鱼,如何给你?”
那人说:“在下姓江名悦诚,住在绣林城北门外十里铺鸿运旅馆。你如果捕到银鱼,就请去那里找旅馆的张掌柜。他自然会带你去见我。”
七爷爷呵呵一乐,说:“行,这单生意我就接下了。”
那人再次抱拳致谢:“那就拜托您了。”又给七爷爷付了三个大洋作为定金,这才划着乌篷船,缓缓离去。
第二天一早,七爷爷从滚钩上取了十几条大鱼,用一个竹篓装了,提到绣林城去卖。因为日军逼近,为防止奸细混进城,城门关口盘查极严,且四面城门只在早上和傍晚打开一小时,平时不允许有人进出。七爷爷早上在城里卖了鱼,并没有像往常一样赶着出城,而是在城里转悠了一整天,直到下午,才到集市上买些红虫和沙蚕作诱捕银鱼的饵料,等到城门打开,才出城回家。
七爷爷之所以信心满满地答应帮助江悦诚捕捉银鱼,是有原因的。他常年在绣林河上捕鱼,早已熟知银鱼习性,更知道绣林河天鹅洲一带水底土层肥沃,水质清澈微流,是银鱼繁殖生长和聚集觅食的绝佳位置。如果从天鹅洲下手,即便是在这天寒地冻的隆冬时节,想要捕到银鱼,也非难事。
当天晚上,他趁着月色,将三道滚钩在天鹅洲布置好,并且往水里投下不少银鱼极爱争食的红虫和沙蚕。三天后,果然捕到一条筷子长的大银鱼,拿秤一称,足足二斤,正适合拿去给江悦诚做药引子。
七爷爷提着银鱼,来到十里铺,找到鸿运旅社。走进去时,发现旅馆里空****的并无顾客,只有一个戴眼镜的白须老者坐在柜台后面噼里啪啦地打着算盘。七爷爷走近柜台,轻轻咳嗽一声,冲着对方一抱拳,大声问:“敢问您可是张掌柜?”
白须老者听到声音抬起头,目光从镜框上方望过来:“您是要住店,还是……”
七爷爷忙道:“我是来找人的。我找住在这里的江悦诚江先生?”
张掌柜忙从柜台后边站起身,上下打量他一眼:“您是岳七爷?”
七爷爷慌忙拱手:“不敢,您叫我岳老七就可以了。”
张掌柜问:“可是给江先生送银鱼来的?”
七爷爷说:“正是。”
张掌柜忙从柜台后边走出来,一面将他迎进里面一间客房,请他坐了,一面说:“江先生跟我交代过了,您一来,就让我去叫他。不巧他今天正好出门办事去了,不过去得不远,我这就出去请他回来。请您稍待。”又叫伙计看茶,这才急匆匆去了。
七爷爷就坐在屋里喝茶。屋子里烧着一炉炭火,很是暖和。一盏茶还没喝完,就听门外传来一阵杂沓的脚步声。七爷爷心中一个念头还没转过来,就看见一队荷枪实弹的鬼子兵气势汹汹闯进来,将他围在中间,枪栓拉得哗哗作响,黑洞洞的枪口一齐对准了他。七爷爷手一晃,一盏热茶全都泼在棉衣上。
一位足蹬皮靴手提战刀的日军军官缓缓踱了进来。七爷爷定睛一看,只见此人身形高瘦,长着一张瓦刀脸,双目中精光闪烁,认得他正是当初在绣林河上遇见的外地人江悦诚。七爷爷一下就蒙了,拎着手里的银鱼,瞧着他讷讷地道:“江、江先生,您、您要的银鱼……”
日军军官手中的军刀连鞘挥出,“叭”的一声,将他手里的银鱼打落在地,哈哈一笑,用标准的汉语道:“老东西,实话告诉你,我不姓江,我叫吉井一雄,是日军联队长。前几天,我们在靠近绣林城的河面上视察地形水势,不巧被你撞见,我手下的人当时就想一枪崩了你,但是那里距离绣林城太近,我怕突然响起的枪声会引起城里驻军的警觉,所以才放你一条生路。你问我们在那里干什么,为了不引人怀疑,我随口敷衍你说我们是外地人,来到绣林河上是为了捕捉银鱼作药引。想不到你还真给我捕来了一条这么大的银鱼。”
七爷爷可不是个蠢笨之人,愣了一下,忽然一拍脑壳,恍然大悟似的道:“你们在绣林河上又是探水深,又是看地形,难道是想从水路突袭绣林城?”
吉井一雄说:“不错,我们正有这个打算。老家伙,你就别装了,其实你早就猜测到我们的身份和目的了,是不是?要不然你在遇见我们的第二天进城卖鱼时,怎么会去国军驻地找他们团长包国安呢?你去找他,就是想告诉他皇军可能会从水路进攻,提醒他要在水路加强防守,对不对?”
七爷爷又是一愣,脱口问道:“你怎么知道?”
他那天在绣林河上遇见“江悦诚”一伙,见他们每个人腰间都鼓鼓的,显然是在腰里别着手枪,说起中国话来拿腔捏调,显得很吃力,就已隐隐猜测到了他们的身份和目的。他第二天进城卖鱼时,顺道去国军驻地求见包团长,想把自己的怀疑告诉他,叫他提防日军从水路进攻绣林城。谁知人家包团长根本没把他这个小老百姓放在眼里,只派了个勤务兵出来应付他。勤务兵听了他提供的“军情”,根本就不屑一顾,说:“咱们团长早就算计好了,日军根本就不可能从水路进攻。第一,在绣林河流经绣林城的入口和出口,国军早已在东西两岸布置好机枪火力,如果两边同时开火,将在河面交织起一道密不透风的火力网,不要说日军人员和船只,就连一只水鸟,也无法飞进城来。第二,现在已是隆冬时节,天气越来越冷,估计再过几天,河水就要结冰,河面根本无法行船,日军绝对没有办法从水路靠近绣林城。”七爷爷见国军不听他的意见,很是气馁。捕到银鱼后,明知“江悦诚”不是善茬,但为了进一步探听日军信息,为国军提供令人信服的准确的情报,他还是硬着头皮,拎着银鱼来找“江悦诚”。
吉井一雄扬扬得意地道:“我当然知道。我不但知道你去找过包国安,还知道他压根儿就没见你,只派了个小勤务兵敷衍你。你的意见,他们根本就没听进去,是不是?”
七爷爷惊道:“你、你怎么会知道得这么详细?难道国军队伍里,有你们的奸细?”
“不错,绣林城的守军里,确实有咱们的耳目,要不然你的一举一动,咱们怎么能了如指掌呢?”吉井一雄哈哈一笑,“不怕老实告诉,你的推断十分准确,我们的确打算从水路突袭绣林城。”
“可是河水马上就要结冰,你们怎么渡河?”
“我们等的就是河水结冰之日,绣林城守军麻痹之时。我早已训练好一百名敢死队士兵,只等河面一结冰,守军一松弛,我们的敢死队就将兵分两路,从绣林河流经绣林城的入口和出口处破冰潜入水中,悄无声息地自冰下水底潜入绣林城。我在城外四门率兵佯攻,吸引守军注意力,只等敢死队自水下潜入城中,放出信号弹,咱们再里应外合,打他个内外开花。绣林城这弹丸之地,还不是咱们掌中之物?”
七爷爷痛心疾首,跺脚大骂:“果然被我猜中,国军这帮蠢材,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啊!不行,我得去给他们报个信儿!”他突然用肩膀撞开一名日军,夺路而逃。
“八嘎呀噜!”吉井一雄大叫一声,凶相毕露,赶上一步,拔出军刀,猛然刺出。七爷爷后背中刀,被刺个透心凉,“哎哟”一声,痛苦地倒在血泊中。可怜我的七爷爷,一个绣林河上的渔夫,一辈子与世无争与人为善,最后竟死得如此惨烈。
三日后,气温陡降,天空中飘起雪花,绣林河上果然结起厚厚的冰层。一眼望去,河里河外,都是白茫茫一片。人们都缩在家里,不敢出门。吉井一雄见时机已到,当即命令实施他的水下突袭计划。
一百名经过水下耐寒训练的日军敢死队员,分作两拨,分别来到绣林河流经绣林城的入口和出口处,在距离河道口国军哨兵数百米外的隐秘地方凿冰入水,从南北两个方向同时向绣林城中潜行。
敢死队一入水,吉井一雄便立即率领日军对绣林城四面城门发起佯攻,以吸引守军注意力。一时间,绣林城外枪炮轰隆,杀声震天。
但是时间过去近两个小时,绣林城上空,并未升起吉井一雄期待的信号弹。他不住地看着表,又耐着性子等了半个小时,外面佯攻的日军不知浪费了多少枪炮子弹,城里仍然没有动静。吉井一雄知道,距离绣林城不足百里的荆州城里驻扎着国民党军一个精锐步兵旅。如果绣林守军向荆州求援,援兵三四个小时之内即可赶到。援兵一到,日军将陷入腹背受敌的不利局面。敢死队迟迟没有发出进攻信号,他情知有变,虽然心有不甘,却也只能下令撤退。
日军刚刚转身退却,城中国军团长包国安却忽然打开北面城门,带领一队人马杀将出来。日军措手不及,待要回头应战,国军的子弹已如狂风暴雨般席卷而至。日军丢下两百多具尸体,逃窜到数里之外,方才与进攻绣林城其他三面的部队会合。
吉井一雄得知此讯,气得暴跳如雷,立即组织火力反扑。包国安一战而退,早已退回城中,城门紧闭。吉井一雄命令炮兵全力轰击,霎时间,数不清的炮弹像冰雹一样倾泻在绣林城的城墙上。
吉井一雄挥舞战刀高声咆哮:“今天就算拿不下绣林城,也要把他轰成一片焦土。”话音未落,忽然呼啸一声,一颗子弹从背后飞来,正打在他屁股上。回头看时,但见身后数百米开外,国军援兵早已像洪水般不可阻挡地漫延过来。城中守军一见援兵已至,士气高涨,打开城门,猛虎下山一般杀将出来。日军顿时陷入腹背受敌进退维谷的险境。激战半日,日军大败,丢下无数尸体,仅剩吉井一雄带领二百余人冒死突围,往北方逃窜而去。
只是让吉井一雄大惑不解的是,他亲手训练的一百名敢死队员,怎么会在下水之后毫无动静?他的水下奇袭计划原本万无一失,怎么会功败垂成?
数日之后,太阳出来,天晴雪化,国军在水上巡逻时,在绣林河流经绣林城的入口和出口附近的河面上发现了一些异样,派人下水后竟捞起数道滚钩,滚钩上挂着不少日军血肉模糊的尸体。细细一数,整整有一百名日军挂在滚钩上。
国军团长包国安想了好几天,也没弄明白这到底是怎么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