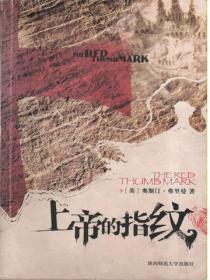在穿过市中心时,我的眼前一片混浊———雾气变得更浓了。我小心翼翼地摸索在雾气重重的街道上,路边的标示都已模糊不清,我不得不停下脚步,辨别方向。
当我到爱簦森公园的时候,吉伯尔小姐正好在家,而霍比太太外出了,这让我不自觉地放松下来。我承认那位女士具有高尚的道德贞操,可她那滔滔不绝的言论简直都快把人逼疯了,恨不得结果了她的性命!
“谢谢你能来看我,”吉伯尔小姐感激地说,“你是个赋于同情心的人,就像宋戴克医生一样,一点没有专家的架子。我伯母刚刚收到华科的电报,就马上去找鲁克先生了。”
“对霍比太太的不幸遭遇,我深表同情。”我差点儿连“也同情鲁克先生”这句也吐出来,幸好理智及时捆住了我的舌头,“可他却是个枯燥无趣的人。”
“没错,我也是这么想的。你知道吗,他竟然劝诺柏承认有罪!真是个无耻之徒!”
“他也对我们提过这事,结果被宋戴克骂得狗血喷头。”
“真让人解气。”她愤愤地提高了嗓门。“快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华科不肯告诉我,只说案子‘转到了高等法院’,我知道这意味着‘等候判决’。难道辩护失败了吗?诺柏到底在哪儿?”
“辩护被延期了。宋戴克医生觉得案子势必被送上高等法院,所以认为没必要在这个时候暴露辩护线索———你知道,一旦控方掌握了我们的动作,他们势必会相机而动。”
“我当然知道,”她回答道,脸上显出沮丧的神情,“但我仍然很失望。我原来以为宋戴克医生会提出足够的证据,使法院不受理此案。告诉我,诺柏到底怎么了?”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也是我最难以回答的问题。我清了清嗓子,眼睛紧盯着地板,不敢迎向她的目光。
“法院拒绝保释。”一阵难耐的沉默后,我还是说了。
“什么?”
“诺柏他……被羁押了。”
“你是说诺柏被关了在监狱里?”她瞪大了眼睛,呼吸急促。
“并不像你想的那样,他只是被暂时羁押,等待着最终的审判。”
“可还是一样被关在监狱里?”
“的确,”我不得不承认,“在赫维监狱里。”
她顿时面无血色,呆呆地看着我。不久她清醒过来,突然回身靠在铁架上,把头埋进臂膀里,小声地啜泣着。
我不是那种易于激动的男人,可也不是铁石心肠、对任何事情都无动于衷,看到眼前这位坚强而忠贞的女子如此悲戚,我顿时心生爱怜,轻轻地走到她的身边,将她那冰冷无力的双手紧紧地握在我的掌心,尽管显得有些笨拙,我还是以沙哑的声音,说出了几句安慰话。
她勉强打起精神,从我的手中抽回了她的手,转身拭去眼泪,对我说道:
“对不起,害你担心了。我真为我和诺柏有你这样的朋友感到高兴。”
“我们当然是朋友了,亲爱的吉伯尔小姐,”我答道,“不仅有我,宋戴克同样也是你们的朋友。”
“我相信你,”她点点头,可又不安地说道,“但这个消息对我来说实在太突然了———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也许从一开始,我就十分信赖宋戴克医生……可结果让我感到如此恐惧,这不禁使我对将来的庭审感到万分忧虑。整件事情给我的感觉就像是一场梦魇,恐怖而虚幻,好像永远都逃不出去。如今却噩梦成真,这实在太可怕了———他竟然被送进了监狱!啊!可怜的诺柏!他会怎么样?请你告诉我,他到底会怎么样?”
我该怎么办呢?我知道宋戴克对诺柏说了什么话,也知道他不会无缘无故说这些。我当然应该守口如瓶,编些别的话来敷衍吉伯尔小姐。可我不能那么做,她是我们值得信赖的人。
“没什么好担心的,你不必对将来的事心生恐慌,”我安慰道,“宋戴克医生已确信诺柏是无辜的,他会有办法还诺柏清白的。不过请不要把这些话告诉其他人。”在我说最后面的一句话时,我感到有些忐忑不安。
“我明白,”她柔声说道,“真是太感谢你了。”
“虽然目前的状况让人感到很痛苦,但也不必过分担心,这就像生病动手术一样,尽管很可怕,可为了解除病痛,这也是必须的。”
“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会控制好自己的情绪的,”她顺从地说道,“可一想到像诺柏这么有教养的人,竟然要被关在兽笼似的牢房里,而且和一群邪恶的抢匪、盗贼、杀人犯呆在一起,我就感到不寒而栗。这真是奇耻大辱!”
“遭受错误的指控并不是可耻的,”话一出口,宋戴克曾对我说过的那些话就在我脑子里轰然盖过来,虽然感到心虚,我还是继续说道,“只要被判定无罪,他还是可以和原来一样是清白的,这段不愉快的经历很快就会过去的。”
她再一次拭去泪水,便绝然地将手帕丢到一边。
“是你给了我力量和勇气,”她坚定地说道,“使我摆脱这场恶梦。真不知道该怎样表达我现在的心情。我向你保证,我一定会坚强起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我都不会动摇的。”
盈盈的笑颜重又回到她红润的脸庞,看起来是那么舒心甜美,风姿绰约。我的心也随之**漾,有股想将她揽入怀中的冲动,但这毕竟只是想想而已。恍惚间,我对她说道:
“很高兴能看到你现在这个样子。但我只是充当了代言人的角色,真正有能力使诺柏重获新生的人是宋戴克医生。”
“我明白宋戴克医生对诺柏的意义,可现在使我振作起来的人是你,因而你们各有功劳,但在我心中的分量却不一样———或许因为女人天生只凭直觉来作判断———无疑是你使我明白了这点。唔———好像是伯母回来了,我想你还是先避避为好,免得又被她缠上。不过在你离开之前请先告诉我———什么时候我才能见到诺柏?我决不让他有被朋友遗弃的想法。”
“明天就可以———假如你想的话。”我迫不及待地说道,同时不自觉地又加上一句:“我也要去的,宋戴克医生可能也会过去看望他。”
“我也可以和你们一同过去吗?会不会觉得我去那里会显得多余?可要是我独自一人去的话,我实在感到可怕。”
“你当然可以和我们一道去,而且一点也不多余,”我笑着说,“如果你能顺路到法学院来,我们就可以一起坐马车到那里。怎么样?不过说实话,待在那种地方可不怎么好受,我想你也应该明白。”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什么时候在法学院会合?”
“如果可以的话,下午两点左右。”
“当然,我会按时到的;现在你必须得走了,否则就走不掉了。”她轻轻地把我推向门外,然后跟我道别:“你对我的帮助我永远都不会忘记的。明天见!”
她静静地走了,只留下我一个人孤独的身影矗立在街头,傍晚的薄雾渐渐升起。当我走进那间小屋的时候,外面还是一片清朗,而此刻夕阳西下,天边飘过几朵灰云。那间小屋也渐渐被阴沉的暮色所笼罩,依稀只辨得出淡淡的轮廓。而此刻,我像是个真正的年轻人一样,心中热情如火,步履轻快地走在大街上。确实,我的心总被许多纷乱的事由所困扰;而一如常人般,最先笼上心头的,却是与个人联系最为紧密的事情。
我们之间的关系到底会有怎样的发展呢?我在她的心里,会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她看来,我们的关系是再单纯不过的,她的心完全为诺柏所独有,我只是她的好朋友,因为我是诺柏的朋友,仅此而已。而我的感受呢?我无法再为自己找任何理由了———对她的感情已使我坐卧不安。
在我过去的人生中,我从未遇到过如她这般美妙的女子,竟是我对女性理想的完美化身。她的美丽与高贵,她的坚强与柔情———我已被她彻底地征服。是的,彻彻底底地———这没什么不能承认的。可即使是这样,我仍然感到痛彻心扉———当她不再需要我的时候,我只能独自一人转身离去———别无选择,并试着痛苦地将她遗忘。
我是否选对了方向?我认为自己这么做并无可指责之处,目前与她所有的接触都限于公事需要,无可避免。除此之外,我只是一厢情愿地经历着情感冒险,并没有伤害到任何人———除了我自己,而我也有权这样对待自己———即便是宋戴克,也无法指控我的行为不正当。
我的思绪带着无尽的伤感终于绕回到了正事上,我忽然想到华科提到的有关霍比先生的事。这真是个意外的发现,但我并不认为这会影响到宋戴克的假设———对此我也还未得到机会一窥究竟,可走在这被浓雾包裹着街道上,我还是不自觉地将这一新发现与已有的材料联系到一起,思索着其中的意义。
在一番苦思冥想之后,我承认自己还是失败了。那枚血红的拇指印占据着我所有的思维,似乎它足以说明一切。除了我和宋戴克之外,所有人都认为这件事早已水落石出,毫无悬念。可当我将整个事件重新想过之后,突然灵光一闪,生发出一个全新的想法。
霍比先生自己会不会就是那个贼呢?在外界看来,他事业上的失利似乎完全是一场意外,可他自己实际早已料到会如此,而且留有拇指印的那张纸毕竟是他备忘录上的。没错,一定是这样的!可谁又能证明那张纸是他撕下来的呢?这件事完全是他自己说出来的。
而那枚指印又该如何解释呢?尽管看起来不太可能,可也不能完全否定,指印也可能是以前诺柏偶然间留下的,只是他自己没有注意到,也不记得了而已。而霍比先生发现了拇指印,而且他自己的指纹也留在了上面。他知道指纹鉴定对指控罪犯的重要性,所以就保留着那张纸以备将来用得上。在盗取钻石时,就用铅笔在那张纸上写上日期,然后放入保险柜里,以此来嫁祸于人。尽管这种情况发生的可能性很小,但其他案件又何尝不是这般匪夷所思?或许也有人会觉得不可能有如此龌龊的小人,可当一个人被逼上绝境时,什么事不可能发生呢?
我不禁为自己如此丰富的想象力开始手舞足蹈起来,恨不能即刻飞回家,把这个想法告诉宋戴克,看看他会怎么说。在穿过市中心时,我的眼前一片混浊———雾气变得更浓了。我小心翼翼地摸索在雾气重重的街道上,路边的标识都已模糊不清,我不得不停下脚步,辨别方向。直到过了六点钟,我才摸索出了市中心,到了中殿大道,穿过王厅街,回到家中。
刚到门口,我就看见彼得站在那儿急切地四处张望着。
“先生,医师外出还没回来呢,”他开口道,“也许是雾太浓的缘故。”
在此我必须说明一下:在彼得看来,宋戴克就是医师,医师就是宋戴克,这个名词为宋戴克所独有;至于其他那些带着“医师”名号的低等生物,他根本就不放在眼里,认为叫他们“先生”已足矣。
“啊,是啊,”我答道,“今天的雾可真大。”
我走上阶梯,在饱受湿雾所引起的那份窒息后,想到有一间明亮温暖的房间正等着我,我就感到十分舒服。彼得站在街头望了又望,最终带着十分不情愿的神色跟上了楼。
“要喝点茶吗,先生?”他一边问我,一边替我打开门,尽管我也带着钥匙。
我告诉他我的确想喝茶,在为我准备好茶点之后,他仍旧是一副魂不守舍的样子,这种情况令人感到惊奇。
“医师说五点钟之前会赶回来的。”当他将茶壶放回托盘上时,对我说道。
“这家伙真是不守信用。”我答道,“为了给他提个醒,我们应该把他的茶冲得淡些。”
“医师可是个守时的人,先生。”彼得积极地为医师辩护道,“分秒不差。”
“但在伦敦这种地方,几乎不可能做到这点。”我感到有点不耐烦。
我回来是希望自己能够单独待一会儿,从头到尾把事情好好想一遍。可彼得这家伙唠叨个不停,让我无法安静下来。他简直就像个罗嗦的女管家一样。
这矮小的男人最终还是觉悟了,默默地退到一旁,留下我一个人独自在那儿自艾自怨。直到他看到我往窗外张望,才又回到门口等待。不久,他上来收拾茶具,此时外面已是黑雾重重了,可我知道他仍旧在心神不宁地跑上跑下,一会儿心情郁闷地踱进屋内,一会儿又跑到大门口张望一番。最后连我也被他的举动搞得神经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