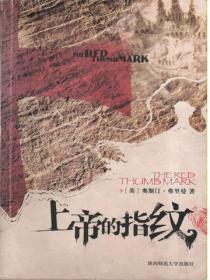“对金钱的过分追求,”吉伯尔小姐少年老成地说,“容易使年轻人误入歧途———噢,李维森医师,请不要笑话我引用格言;我说的是真的。事实上,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感到华科总有一天会走这样的道路。”
在我们回家的路上,宋戴克陷入一种不寻常的沉思之中,他的神情十分专注,虽然表面上看带着一丝冷静,但是我可以察觉到其中还隐藏着被压抑的兴奋。我强忍住自己不去打扰他,因为我知道他的个性,这个人会认为独立思考就是自己的本分,哪怕是对我,也无须做任何吐露。
回到住处,宋戴克立刻将照相机交给彼得,嘱咐了几句。这时午餐已经准备好了,我们二话没说就坐到餐桌前开始就餐了。
吃饭时我俩一句话都没说。突然,宋戴克将手上的刀叉放下,兴味盎然地看着我,说:
“里维斯,我突然感觉,你是世界上最适合给人做伙伴的人,因为你拥有一种天赋———沉默。”
“假如沉默被验证是做伙伴的试金石,”我咧嘴笑道,“那么你更应该受到恭维啊。”
宋戴克大笑着说:
“好家伙,没看出来你还是个牙尖嘴利的人啊。但是我的想法仍旧不变,我认为保持适当的沉默是极为珍贵的社交成就。好比今天这种情况,通常情况下一定会有很多人问我无数个问题,会把我烦死,要不就是滔滔不绝地发表意见、看法,让我听着就恶心;但是你和他们不同,你没有来打扰我,而是让我一个人在印象犹新的情况下,好好地在大脑里整理今天所搜集到的证据。顺便说一句,今天我犯了一个低级的错误。”
“噢?什么错误?”我问道。
“关于那个指纹模的下落,我忘了问它现在是在警察局里,还是在霍比太太那儿了。”
“这个很重要吗?”
“也不是很重要,但是我得看一看它。或许这为你提供了一个与吉伯尔小姐见面的好借口。今天下午我还要去一趟医院,彼得手上也有一堆事情要做,大概只有你去爱簦森公园那里拜访一下———我记得是这个地址。当你见到吉伯尔小姐后,尽可能地多和她聊些私事,尤其要从她那了解到三位霍比先生的生活习性。将你临床观察的能力充分地发挥出来吧,保持你最敏锐的洞察力,所有与那三位绅士有关的东西,你都不可掉以轻心。因为他们的每一件事都对我们很重要,哪怕仅仅知道裁缝师的名字也是很有用的。”
“那么,那个指纹模呢?”
“弄清楚它现在在谁的手上。如果还在霍比太太那,你就想办法把它借来,或者请她允许我们拍几张它的照片,这样是最好的。”
“好的,我会尽量完成任务的,”我肯定地说,“我想我要先装饰一下我的外表,今天下午得闪亮登场,扮演一个打破沙锅问到底的角色。”
一小时之后,我已经达到了宋戴克说的那个公园了———霍比先生的家就位于爱簦森公园。我按了一下门铃。
“找吉伯尔小姐?”一个女仆重复着我的话。“小姐好像出去了,可是我不确定她是否真的走了,请您先进来吧,我去找找看。”
我跟着这名女仆来到客厅,穿梭在一些小桌子和各式家具之间。这年头,女士们总喜欢将自己的空间装扮成旧物店,好不容易我才在火炉边找到了一处栖身地,等着女仆回报。
没过多久,吉伯尔小姐便在我面前出现了。此时她戴着帽子和手套,很明显她要出门。我真是庆幸自己没有错过时机。
“没想到这么快就见到你了,里维斯医师,”吉伯尔小姐温柔地说,然后友善地伸出一只手,“欢迎你的光临。有什么消息要告诉我吗?”
“噢,不,恰恰相反,”我说,“我是有事向你请教来了。”
“唔,是这样。那总比什么都没有要好,”她虽然这样说,但是脸上掩饰不住一抹失望的神色,“请坐吧。”
我小心翼翼地坐在了一张摇摇欲坠的小椅子上,然后直截了当地说:
“你还记得上次你说的那个叫指纹模的东西吗?”
“当然记得,”吉伯尔小姐的精神又提起了,“就是它引来的麻烦。”
“你知道那东西现在在哪吗?”
“当时探长把它带到苏格兰场去了,说是让指纹专家作鉴定;后来他们想把它留下,当做控诉证据,这令霍比太太感到十分苦恼,所以警方就把它还给了霍比太太。其实警方并不需要那个东西,只要把诺柏抓住,他们自己就可以取得他的指纹;事实上他们逮捕诺柏时,诺柏很主动地让警方采指纹,他们也真的取到了。”
“这么说那个指纹模现在在霍比太太手上?”
“是的,除非她把它毁了。我好像听到霍比太太说要这么做。”
“上帝保佑,愿她没有这样做,”我突然感到不安,“因为宋戴克医师现在急着想看看它。”
“唔,霍比太太几分钟后就会下楼,你可以问问她。我已经告诉她你在这儿了。你知道宋戴克医师为什么要看这个东西吗?”
“一点都不知道,”我回答道,“这个宋戴克对我可是和对别人一样———守口如瓶。他从不漏丝毫口风。”
“听你这么说,他好像是一个不太容易亲近的人啊,”吉伯尔小姐喃喃地说,“可是我知道他是个好人,而且很有同情心。”
“他的为人没得说,而且极富有同情心,”我强调着说,“但他从不因为逢迎他人而泄漏客户的秘密。”
“我想也是,他对我就不爱逢迎。”吉伯尔小姐微笑地说。显然,她因为我不够圆滑的措辞而表现得有些恼怒。
正当我犹豫着要不要自责加道歉地对这位小姐弥补过失的时候,门来了,走进来一位年纪稍大一些的女士。她身材健壮,神态安详沉稳,但看上去却有一些愚蠢。
“我来介绍,这位是霍比太太,”吉伯尔小姐说,“这位是里维斯医师,他来问指纹模的事。你应该还没有把它毁掉吧?”
“当然没有,亲爱的,”霍比太太回答道,“它在桌子上。不知道这位里维斯医师想知道什么呢?”
霍比太太的脸上浮现出一副惊恐的样子,我真不知道该怎样安抚她。
“我的同事宋戴克医师急着要检查它,我想你是知道,他目前正负责你的侄子诺柏的辩护工作。”
“是的,我知道,”霍比太太说,“朱丽叶跟我提过他。她说那位宋戴克医师是个可爱的人,是吗?”
这时我看了一眼吉伯尔小姐,恰巧与她的目光相接;她的眼神里有一种顽皮的感觉,不久她的双颊便红了起来。
“唔,”我模糊地说,“我倒没感觉到他可爱的地方,但是我对他的评价的确很高。”
“我想这无疑是男性的用词,意思应该是一样的。”吉伯尔小姐说,刚才霍比太太将她的形容直接转述出来,不禁使她感到困窘,不过很快她就恢复正常。“我认为女性在遣词造句方面就比较能一针见血且完整。但是话说回来了,你愿意把指纹模借给他,让他带回去给宋戴克医师看吗?”
“噢,亲爱的,”霍比太太诚恳地说,“只要是能帮助我那可怜的诺柏,什么事我都愿意做。我怎么也不相信他会做这种事情。我深信这里面一定有问题,当然我也是这么告诉探长的。我愿以人格向他们保证,诺柏决不会偷东西,可是他们并不相信我。我是看着诺柏长大的,所以我最有资格对他进行评价;还有,那些钻石,想想看,诺柏要那么多钻石干什么?它们还是没有切割的。”
霍比太太一边说一边流眼泪,于是拿出一条蕾丝手帕擦眼泪。
“我相信宋戴克医师能够从你那本小册子里找到什么。”为了阻止她继续哭下去,我赶紧转移话题。
“噢,那个指纹模啊,”她说,“我十分愿意把它借给宋戴克医师。他对这个小册子感兴趣我很高兴,这说明他对诺柏这起案子很用心,使我看到了希望。你相信吗?里维斯医师,那些愚蠢的警察竟然想把它留下来,作为指控我可怜的孩子的证据。那是我的指纹模呀,你想想看!我怎么能同意呢,所以他们只好还给了我。我已经下定决心了,如果这帮人还想对我的侄子落并下石,那我将拒绝帮助他们!”
“就是啊,”吉伯尔小姐说,“所以你最好还是把指纹模交给里维斯先生,让他带给去。”
“当然,”霍比太太爽快地说,“马上就给你,而且你还不用还,如果里维斯医师用完了,就把它丢进火里烧掉吧,我是不想再看到它了。”
看到霍比太太这番爽快,我却有一些顾虑,觉得就这样把东西从人家手里拿走好像有些不妥,于是我向她解释道:
“我并不知道,”我说,“宋戴克医师要检验这个指纹模的目的,但是我猜他好像要拿它作证据。如果是这样,这东西最好还是由你亲自监管。他只是交待让我得到你的准许,把它拍下来。”
“哦,是这样,如果他要照片,”霍比太太说,“那我很容易帮他拍一张。我的另一个侄子华科就可以帮忙,只要我说一句,他肯定答应。他是个很聪明的人,是不是,亲爱的姑娘?”
“您说得没错,伯母,”吉伯尔小姐微笑着说,“但我想宋戴克医师希望自己拍。”
“我确定宋戴克也是这样想的,”我补充道,“其实别人拍的照片对他而言,大概毫无使用价值。”
“哎,”霍比太太叹了口气说,“你们一定都以为华科只是个普通的业余玩家,可是如果我把他拍的照片拿给你们看,你们一定会对他的照相水准感到吃惊的。这个人可是绝顶聪明,我敢保证。”
“你需要我们把那个小册子送到宋戴克医师的住所吗?”吉伯尔小姐又把话题拉了回来,“这样可以省掉一些时间和麻烦。”
“你们实在是大好人啊。”我说。
“不用客气。你认为我们什么时候送去合适?今天傍晚?”
“好哇,”我说,“这样我那位同事就可以立刻检查了,这样他就可以决定该下一步改怎么做。只是给你们带来很多麻烦。”
“一点也不麻烦。”吉伯尔小姐说。“伯母你愿意和我一起去吗?”
“当然愿意,亲爱的。”
霍比太太回答道,而且好像就这个题目展开申论。这时吉伯尔小姐突然站了起来,看了一眼钟,然后说自己现在有事要出门。于是我也起身向她表示告辞。她说:“里维斯医师,不知道你是否和我顺路,我们可以在路上就拜访的时间做一个商定。”
我没有思考立即答应了这个提议,几秒钟过后,我们便一同离开了。霍比太太站在门口微笑着目送我们远去。“你认为8点钟合适吗?”当我们走到街道上时,吉伯尔小姐开口问道。
“很好,”我说,“如果中途有什么变化,我会送电报通知你的。还有一点我想说,今晚我希望你能够独自前来,因为我们要谈一件正事。”
吉伯尔小姐轻轻地笑了笑,发出如音乐般轻盈悦耳的声音。
“好的,我会的”她同意道,“那位亲爱的霍比太太说话有时的确不着边际,总不会专注在一个话题上与别人交谈,但希望你能够原谅她这个小缺点,如果你和我一样接受过了她的慈爱和慷慨,那么你就不会在意这个了。”
“我并没有在意,正相反,我完全同意你的说法,”我回答道,“其实我也是这么想的。哪个上了年纪的女士讲话都是啰嗦的,思绪都是模糊的,这算不上是什么缺点。”
吉伯尔小姐又一次露出淡淡的笑,以表示对我刚才这段高昂公正的说法的赞同。我们继续往前走着,我们沉默了一会儿,突然吉伯尔小姐转向我,用一种急切的表情对我说:
“里维斯医师,我想问你一个问题,请先原谅我的冒犯,我希望你能松松口告诉我一些情况,你认为宋戴克医师有什么把握或希望拯救诺柏吗?”
吉伯尔小姐提出了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我沉思了一段时间后,说:
“我也很想,”我无奈地说,“在我职责范围内将一些情形告诉你,可是我能说的很有限。不管怎样,在没有泄漏机密的前提下,我可以告诉你的是:宋戴克医师已经接下了这起案子,而且他对工作是相当认真的。如果他对这起案子没有信心的话,那么他就不会做那些无用功了。”
“听到你这样说,我真是感到振奋,”她微笑着说,“对此我是明白了。但是我还想问一件事,你们到苏格兰场有什么新发现吗?请不要认为我在越权,我只是太担心、心急这起案子了。”
“对不起,我能说的真的很有限,因为我自己知道的也不多。但我能察觉出来,宋戴克医师对于他今天早上在苏格兰场的工作表示非常满意。我想他一定搜集到了一些线索———只是目前我还不明白它们是什么———反正回到家,他就突然要检查这个指纹模了。”
“感谢你告诉我这些,里维斯医师,”她感激地说,“你让我感到振奋。请放心,我不再问你什么问题了。你确定你也走这个方向吗?”
“噢,没关系,”我急忙回答,“事实上我本来希望在谈完指纹模后,能够和你私下聊一聊。所以如果你容许我再陪你走一段路的话,那将是我的荣幸。”
吉伯尔小姐羞答答地向我鞠了个躬,问道:“唔,这么说接下来我要接受盘问了?”
“哎呀,”我回应道,“你也盘问了我不少啊。但是我并不是故意要盘问你的。想想看,在这起案子里,我们和你们都互不相识,这虽然可以让我们公正地对每个人作出估量,但是真正的了解要比这种公正有用。例如我们的当事人,当我第一次看到他时,他给我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但有可能他是一个前科累累的恶棍,只是从表面上看不出来而已;后来你告诉我们,他是一个纯洁无瑕的绅士,从而我们才对他有了信心。”
“这个我了解,”吉伯尔小姐若有所思地说,“这样说来,我或者其他人所提出的一些事,从一个方面可以体现他的人格特征,那会影响你们对他的看法吗?”
“所以说,”我回答道,“我们有责任查明对方所说的话是否属实,以及其背后是否有什么原因。”
“是的,我想换了谁都会这么做的。”
吉伯尔小姐开始陷入一种沉思,她那种神情让我决意继续问下去:
“我想知道,据你观察,你知道有谁说过不利于诺柏先生的话吗?”
吉伯尔小姐又开始思考了,她一直盯着地上,好像有什么难言之隐。过了一阵,她终于略带迟疑地说出了下面这段话:
“我想这是一件小事,而且与这起案子没有什么关系,但是它在我和诺柏之间造成了矛盾,使我一直感到烦恼,毕竟我们俩曾经是十分亲近的好朋友;而我也常常责怪自己,为什么因为这件事使我对诺柏的看法发生改变呢,这对他来说是不公平的。我现在就把整件事情告诉你,即便你认为我蠢。
“六个月以前,我和诺柏一直都是最要好的朋友,就像你知道的那样,仅止于朋友而已。诺柏对古代和中世纪艺术很有研究,我对这方面也很感兴趣,所以我们常常约好去看艺术展或博物馆,彼此讨论和交换意见,感到很快乐。
也是在六个月以前的一天,华科把我带到一旁,表情严肃地问我和诺柏之间到底是什么关系。当时我认为这与他无关,可还是将实情告诉了他,说我和诺柏只是很谈得来的朋友,没有别的。
‘如果真是这样,’华科很郑重其事地说,‘我建议你以后不要常常和他出去。’
‘为什么?’我很自然地这样问。
‘为什么?因为,’华科说,‘诺柏是一个该死的傻瓜。他在俱乐部里和其他人闲扯,说现在有一位年轻而富有的女士正对他穷追不舍,但是他是一个灵魂高尚的哲人,并不会被物质所**,因此他将这位女士的爱无情地拒绝了。我只是看不过去才告诉你的,’他继续说道,‘我觉得这件事并不会就此停止,我真的是为你好才告诉你这些的。但是你也不要生气,男人一般都喜欢炫耀,而且那些听到这种话的家伙一定会把他的话再添油加醋地告诉给别人,所以才弄成这样。我想你最好还是谨慎一些吧。’
你一定猜到了,当我听到这番话时我大为震惊,马上就要找诺柏说个清楚,但是华科阻止了我。‘即使你大闹一场又有什么用呢。’他这样说道,而且他还警告我这件事要保密。所以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设法忘掉它,一如既往地和诺柏来往,但是我认为诺柏不会这样做的,虽然我的自尊已经大受伤害,但同时,我又觉得应该给他一个解释的机会。虽然华科说的并不像诺柏这个正人君子的行为,但从某种角度来说,这又不是不可能的,因为他最看不起吃软饭的男人,所以从那时起,我就深深地陷在这种为难之中。你认为我该怎么办呢?”
我困窘地摸着下巴。毫无疑问,我最瞧不起像华科这种搬弄是非的小人了,但我又不忍心谴责眼前这位美丽的朋友耳根子软,当然我的立场也不适宜做出什么批评。
“我想是这样的,”我想了一会儿说,“若不是诺柏说了那些有损于你尊严的话,就是华科在造谣中伤他。”
“是的,你说得没错,”吉伯尔小姐同意道,“我也是这么想的,你认为应该是哪一种情形呢?”
“这个很难说,”我回答道,“我承认,有一种下流痞子喜欢对自己爱情的战利品大肆吹嘘,摆出一副洋洋得意的样子。这种人通常一眼就能看出来。但是说句心里话,在我眼中,诺柏并不是这种人;另外,如果华科真的听到一些流言的话,他最合理的做法是提醒诺柏,而不是向你打小报告。吉伯尔小姐,这只是我的感觉,并不可信。但是我想他们两个人大概不是那种亲密无间的好朋友,是吗?”
“哦不,他们是很要好的朋友,你不知道,他们只是有着不同的人生观和兴趣。虽然诺柏在工作上的表现极为优秀,但是他总像一个学生,或者说是学者。相反,华科在对待事情上就比较实际———他是一个精明干练,果断而有远见的人,就像霍比太太所说的那样。”
“就像他在拍照方面的能力?”我提出这个话题来。
“在这方面,他不仅是业余玩家,他的作品颇具专业技术水准。例如,他曾制作了一系列十分美丽的金属矿断层显微照片,而且在珂罗版上制作出版。他甚至还会自己冲照片呢。”
“这么说他真是一个能干的人。”
“的确,”吉伯尔小姐赞同地说,“他对名利也是很感兴趣的,只是我认为他太惟利是图了,这对年轻人来说不是什么好事,是吗?”
我表示同意地点点头。
“对金钱的过分追求,”吉伯尔小姐少年老成地说,“容易使年轻人误入歧途———噢,里维斯医师,请不要笑话我引用格言;我说的是真的。事实上,我有一种不祥的预感,我感到华科总有一天会走这样的道路。他有一个叫哈顿先生的朋友,他是证券公司交易人员,而且‘操作’得很大———‘操作’是他们的行话,可是我的理解就是赌博———我常常怀疑,华科有和那位哈顿先生的‘小玩一下’。”
“对于一个深谋远虑的人来说,玩股票是不会令人感到惊讶的。”
我这样说,完全出自我对贫穷的体验和理解,是十分公正的。
“你说得太对了,”她同意道,“是不值得大惊小怪的,可是赌徒却总是认为自己会赢。但是,你也不要因为我的话就把华科看作是一个赌徒。前面就是我要去的地方了,感觉你送我一程,希望你现在对霍比家族有一定的了解了。我们今晚8点会准时到的。”
她带着诚恳的微笑和我握手道别。当我走到路口回头看一眼的时候,吉伯尔小姐正友善地对我颔首致意,然后才走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