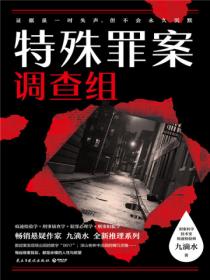“莫士亮不具备作案时间,他雇用陈浩山作案的可能也被排除了。”上了车,司徒蓝嫣说,“既然莫士亮还在,那么陈浩山绝对不会跑远。站在他的角度考虑,莫士亮虽口口声声说放下了,可他并没有完全相信对方的说辞。否则他也不会千里迢迢去作那三起案子。”
“陈浩山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牺牲自己保全弟弟。莫士亮的存在,对他来说始终是个威胁。如果莫士亮反悔,那么陈浩山必须要保证,在关键时刻出现在陈星面前。”嬴亮说,“他多半就在附近。”
“他应该就在修平区。”展峰道,“不管陈浩山如何隐姓埋名,他必须要有最基本的生活保障。”
嬴亮迅速整理几点核心。“想在一个地方这么长时间不用身份证,他首先要有固定住所,工作地和居住地也要离得很近,这样不需要乘坐交通工具,也就不会被巡逻民警发现。再就是生活区域的视频监控不密集。”
“陈浩山还存在伪装成流浪者的可能。”展峰补充说。
永元市十三个行政区里,修平属经济欠发达地区,城中村不在少数,大街小巷,蓬头垢面的流浪者也比比皆是。根据这种泛泛的推测,想找到陈浩山,无异于大海捞针。
嬴亮再次研究了陈浩山的话单,发现在为数不多的通话中,有一个固定电话,他曾经拨打过两次,第一次通话时长为8分24秒,第二次为57秒。
通过电信部门的反馈,该号曾被多家公司使用过,其中有汽车租赁公司、房地产公司、担保公司以及传媒公司。换公司不换电话的情况,说明几家公司可能使用了同一个办公地点。
“陈浩山为何会得知这个号?答案只有一个,他可能看到了招聘广告。那么是什么心理,驱使他拨打的电话?只有一种可能,为了获取经济来源。”司徒蓝嫣如此分析道。
“永元市那么大,招聘广告多如牛毛,在陈浩山为数不多的通话记录中,他为什么要单单拨打这个电话?而且还拨了两次?”嬴亮犹有不解。
司徒蓝嫣道:“人作为生活中的个体,在试图重新融入社会群体时,需要一种归属感。它是个体与所属群体间的一种内在联系,没有归属感的人,会对从事的任何事情缺乏**。只有归属感得到满足,人才会对其他事情提起兴趣。这就好比一个人到陌生的城市出差,第一个念头,就是要找宾馆落脚。此时的宾馆,就成了这个人与城市建立归属感的纽带。”
司徒蓝嫣看向不发一言的展峰,“展队,陈浩山能有心思去找工作,说明他找到了落脚点,而这个落脚点一定距离招聘广告不远。”
“他的两次通话:第一次时长为8分24秒,第二次为57秒,两次通话间隔二十二小时。看来,他第一通电话应该是在咨询岗位,考虑了一天后,拨打的第二个电话,就是答应了对方的条件。拒绝的话,完全没有必要再次拨打。”嬴亮的思路跟得很紧,看到展峰微微颔首,嬴亮顿时觉得心情松快了一些。
展峰的确能耐不凡,或许一时之间难以望其项背,可嬴亮也不想老落在师姐后头。
“陈浩山身背命案,不会频繁更换工作,如此一来,只要查到他进了哪家公司,那么之后的事情就会有迹可循。”展峰对嬴亮说,“查一下电信部门,调取几家公司的开户时间。”
嬴亮动作迅速,最终确定,陈浩山呼入时,该号码是一家名为“国洋地产”的公司在使用。当年地产公司刚刚成立,急需招聘劳务人员,提供的岗位主要有:保洁、物业安保、水电维修。
根据规定,安保人员必须至派出所备案,水电维修要掌握一定的技术,需要考取证件,那么,不需要身份证的工作就只剩下保洁了。
保洁员的工作地,主要在该公司开发的小区内,这个工种又细分为:楼道清洁、小区地面清洁及垃圾倾倒。前两个工种多为女性从业者,而垃圾倾倒这种又脏又累的活,只能由男性从事。
陈浩山要是从事垃圾倾倒,可谓好处多多。首先工作环境恶劣,平时不会有人靠近;其次不管春夏秋冬、黑夜白昼,任何时间戴口罩都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非常便于隐藏身份。
国洋地产在永元市有多个楼盘,而在修平区只建了一个成规模的小区,名叫“金融祥和苑”。该小区面积不大,负责垃圾倾倒的有三人,其中名为胡浩的48岁男子,立即进入了专案组的视线。
物业经理当然不敢怠慢,一见到专案组就把胡浩的事交代了个底儿。
胡浩从小区建成之初就在这里负责垃圾清理,从业时间足足十四年。他性格古怪不健谈,不管什么时候都戴着一副厚厚的黑色口罩,平时也不跟人来往。
眼下他本人租住在小区对面的塔楼里。塔楼前身是修平职业学院的学生宿舍,楼高33层,因造型如同塔,由此得名。
2002年,学院停止招生。在塔楼建造时,学校拖欠了大量工程款,为了偿还欠款,塔楼的产权被分割成多份用来抵账。塔楼内原本的学生宿舍,被林林总总的业主改得面目全非,楼内的住户,也是鱼龙混杂。
吕瀚海沿着楼层大致数了一下,每一层分为南北两排,每排有十二个房间,也就是说整栋塔楼可供居住的房间有七百多个,如果没有明确的地址,要想在这里找到胡浩只怕也并非易事。
虽说胡浩已是瓮中之鳖,但只抓到他这个人,却并没有什么用。
因为案件发生太久,能够直接定案的证据并不多,最好的结局,就是在他的住处将他抓获,这样说不定还有可能在他销毁证据前,找到一些线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