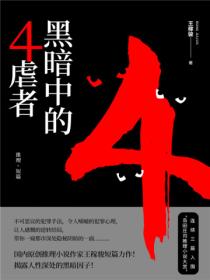我家座落在一片废墟之中,不要以为我的家园在伊拉克,而是因为我家正巧在高架公路规划的线路上,被列入了市政动迁的范畴之中,由于在动迁补偿上无法达成一致的情况下,我成为了令动迁组最为头疼的“钉子户”。
所以我把杨荪的尸体搬到出租车上,自始至终没有一个人看见。我用被单将尸体裹了个结实,在门前小道的瓦砾堆上拖行了一段路,在没有路灯的情况下,几次脚下拌蒜差点跌倒,不过这个矮小男人的尸体我还是应付得过来。
我的搭档守时的将出租车停在了老地方,那是周围唯一的一片平地,仅仅距离我家不到一百米。我手、脚、肩并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尸体塞进了汽车的后备箱,由于裹了厚厚的被单,尸体应该不会受到丝毫的损伤。
室外热浪滚滚,一出门粘乎乎的汗就冒了出来,可我却前所未有的异常冷静,清脆的蟋蟀声听来格外清凉,寂静的世界上似乎只剩下了我一个人。
放开手刹,转动钥匙,我自如的发动了出租车,按部就班的实施着我的计划,在这个我反复研究的计划下一步,是要把尸体运回他的家。
车里比外面凉爽多了,打开无聊的收音机,让音乐麻痹我紧绷的神经,使自己尽量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希望能一路顺利的到达目的地。
可我无法集中注意力开车,脑海中尽是一些奇怪的念头。我幻想着后面的尸体爬到后座,用那双死人的手卡住我的脖子,冒着水泡的喉咙向我索命。抑或是担心,跟在我后面的汽车能否看得到那具尸体?路边闪烁的警灯难道就是阻截我的?尽管知道这是多余的担忧,但我一路上总是提心吊胆的。
突然,车前灯闪过路旁的一个人影,似乎在挥手示意我停车。
一个后备箱藏着尸体的司机,在这个时候是无论如何都不愿意载客的,虽然车上没有乘客,但我早已将“空车”的翻牌盖下,任凭车外呼天抢地,我自岿然不动,只当作没有看见。
但一个意外打乱了我整个计划,我被一个红灯堵在了路口。从反光镜中上演了我最不愿意见到的一幕,刚才那个扬手的人,一路小跑到了我的车旁,来人笨拙的拉了好几下车门,终于坐了进来。
“谢谢,麻烦到太平街2号。”他自顾自的报着目的地。
我斜眼打量着副驾驶座上的男人,他一头乱发,身上是价值不菲的阿玛尼黑色西装,领口还别了一朵艳丽的鲜花,双手握着一包长方形的东西,他悠然自若直视前方,刚才的奔跑使得他的胸膛上下起伏着,额头布满了汗珠。
“可以开了。”身旁的男人伸出一根细长的手指冲着前面指了指。
我这才缓过神来,路口的指示灯已经由红转绿,可以通行了。我连忙踩下油门,车划出了白线向前方驶去。
“太平街应该是那边吧!”男人再次说道,“好象刚才的路口应该左转。”
“没事,走这条路不堵。”我急中生智的回答道。
一位突然上车的乘客,我强行将他赶下车的话,就构成了拒载,在这样一个特殊的夜晚被人投诉,我的杀人计划就等于是泡汤了。眼下要摆脱乘客的唯一途径就是安稳的将他送回家。
“咦?”男人惺忪的双眼睁得圆圆的。
我被吓了一大跳,一颗心如同装上了电动马达般在身体里跳动着。
“你的工号居然和我的生日一样,真是巧了。”男人饶有兴趣的看着插在计价器上的工作牌,笑眯眯的说。
原来是这事,我还以为尸体被发现了呢,虽然这几乎是不可能的,看来我的神经绷的太紧了。
不知道是他故意寻找的话题,还是真的凑巧,反正我保持冷淡的态度,轻描淡写的回答了一句:“是嘛?”
“你居然还是先进工作者啊!”男人如孩子般高兴的问我。
“评上那个完全就依靠运气。”我谦虚的说。其实那是我最在意的成绩,是我三十多年以来第一次被认可。
“你们做出租车司机的天天长时间驾驶,很久以来我一直对你们的工作精神十分敬佩。”他的语气很诚恳,不像是虚情假意的拍马屁。
“为了生计而已,没办法。”我边回答边打着方向盘,车子终于绕回到了通向太平街的马路上来,对此,男人似乎没有注意到。
“对了,我有一个疑问想要请教你一下,”男人抓了抓他的干枯的头发,这个动作令我联想到自己刚才抓着尸体头发的手,具备着死亡的意味。
他继续着问题:“你们空车出门的时候,你这样的先进工作者减少空车的诀窍是什么?”
“通常我都是在送完乘客后,固定朝一个热闹的地区开。”这的确是我往日的基本行车路线,但主要还是因为调度室的全力“支持”,所以我的业绩才会如此彪炳。
“真是不错的办法。呵呵!”男人随和的笑着说。这个略显颓废的男人或许看到了我的黑眼圈,语气中夹杂着几分关切说,“你的样子有些疲惫,难怪方才没看到我招手,努力工作也要注意身体。”
一瞬间,我对他有种难以言语的好感在心头涌动,是感动。
很久没有人在意我了,特别是男人。一个人老珠黄的女人,下场只有是被抛弃。
在他下车前的这段时间里,我们聊得很投机,在亲手杀死世上唯一亲密的男人不到一个小时,我被儒雅男人的气质所吸引。
在这几分钟内,我连后备箱里的尸体都忘得一干二净了。
车子安稳的停在了太平街2号的门口,乱发男人从西装的内侧袋中掏出车费,不等我找钱就开门下了车,礼貌的向我挥手道别。
他一下车,就在闷热的空气逼迫下,脱去黑色西装,信步走向太平街2号,此时门口站着一位圆脸的中年人,看起来正等着他。一见面,两个人有说有笑的走上了楼梯。
我在车里低身抬头看向二楼,一块破旧残缺的招牌上写着“事务所”之类的字,我猜不到他的职业,即便是我拥有一双阅人无数的锐眼。
我用力的晃了晃脑袋,将这场无疾而终的邂逅对象甩出了大脑,在这个连名字都不知道的乘客身上,我已经浪费了十五分钟,现在该办正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