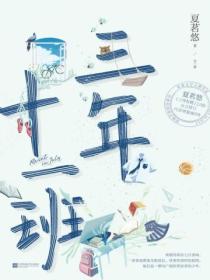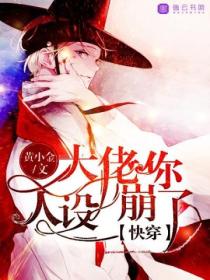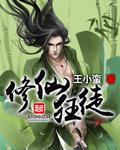大家好,我是猪妞。
这是我出版的第16部长篇单行本,但又是我的第1部作品。
14年前我动笔写下《三年K班》(出版名《三年十一班》),当时年纪还没赶上书里的京芷卉。因为刚经历高考,对高考有一些强烈的情绪,所以就这么无知无畏、毫无章法地写了长篇。长大后再回头看,很惭愧,它不能算一个完整的作品,只是一些点状的情绪爆发。
生活中遇到了作文竞赛被顶替的事情,看见身边有同学花钱上大学,就很愤怒地记录下来,但这些事与我的人物成长弧有什么联系?好像都根本没融合起来。
人物塑造也做得比较随意,就连谢井原是个不爱说话的男生,也是作者强行给读者硬塞的概念,小说里他话这么多又这么会撩,为什么前两年没有追到京芷卉,非要等一个车祸呢?对不起大家,作者也百思不得其解。
这本书因为我小时候笔力不济,留下了很多遗憾。它其实是个悲剧,到结局京芷卉并没有任何成长,她心里所有的噪音直接因为得到一个男生的爱就自然消失了,可如果人生路上得不到男生的爱呢?而这个男生为什么爱她,解释不了。
所以4年前我开始重写这本书,追更新的读者说新版本增加了很多细节,其实有误解。我增加的不是细节,是骨架和血肉,用来穿以前这件散落着细节的衣服。
扎实地做了人物的成长弧和人物关系弧,这本书不会再依赖读者自发的想象,读者们终于可以很清晰地了解谢井原为什么喜欢京芷卉,什么时候因为什么开始喜欢,他们的关系遇到过什么阻力,又是怎么克服困难的。反之亦然。
读者们喜欢京芷卉,也不会再只因为她是女主人公。我们的公主这次要自己走出来,相信自己,去追求梦想。王子跟在她身后走,看着她做每一个决定。她是谁,要成为谁,不再由别人的爱来定义。
高考是我迄今所见最激烈又最光明的战场,让我们在高考考场上相遇吧,经历过高考和走了捷径的一定是两种人生。
这些年我又有了一些别的经历,我读研时高中教过我的一位老师去世了,小时候我在他家补课,他女儿是低我一年级的学妹,和我玩得很好。他去世的消息是他当时教的一个小学妹告诉我的,葬礼我去了,很遗憾没看见学生。回来我问学妹为什么没来,她说班主任不准假。
我藏了一些私心让整个K班去送别老刘,现实中留下的遗憾,我们用美好的故事来弥补。我想这就是小说存在的意义吧。
感谢我的老师David Howard对我最重要的这本书提出的宝贵意见,尽管因为文化差异,对他解释中国高考为什么压力这么大,非常难。老师给结局建议了解散,对这本书是支柱性的概念,他说芷卉光是把大家聚集起来,那只能证明她是社交皇后,只有把大家解散了才能完成所有人的成长。
感谢我的读者过去对我的包容,难为大家抱着这样一本逻辑混乱的小书,想象出一个精彩的世界。一些读者有雏鸟情结,觉得旧版本更好,也可以理解,大家家里的旧书是不会消失的,也许它不是一个好故事,但可能代表了你的一段好时光。
更感谢连载期间一路留下评论的读者们。你们不仅给了我很多实用的反馈,而且增加了文本的趣味性。像“考前填志愿”“平行志愿不录”,我一直以为全国范围任何时候都如此,是大家告诉我,我才知道原来地狱模式只是我那几届的独家限定。比我更早几届的一个哥哥是上海中学名列前茅的优等生,就是高考差了两分没进交大,直接进了上大。当时身边所有人也都没有怀疑过,以为这是天经地义的,不知道其他省市、后面高考改革过的几届竟还有简单模式。
关于这本书的时代背景,和以前每本书一样,是当下。我不喜欢怀旧,觉得一部作品的共鸣感不应该建立在“怀旧时代物品”“怀旧社会事件”“怀旧流行歌曲”的基础上,相信文字本身的力量。所以这本书只有高考填志愿和录取模式用了我们当年那种,因为上海三五年一次高考改革,随时在变。不管怎么变,我们当年这种都是最难的地狱模式,选择这个是为了给学生更大压力,让他们获得更多成长。
有读者问,会不会随着《三年K班》的故事再重写《陪你到世界终结》?
可能会,可能不会。因为重写一本书是事倍功半的一件事,当初我表达要重写《三年K班》的愿望时,所有编辑都是反对的。现在大家看到了,这本书重写率百分之九十九,得把个别场面留下又得贴合主线,比写一本新书工作量更大,版税收入却是新书的一半,完全是用爱发电。只有自己最珍视、留下最大遗憾的作品才值得重写一次。《陪你到世界终结》因为写作年份晚,本身就是一本完成度较高的书。而且我自2017年以来存了完本还没有修改出版的新书已经有6本了,当务之急是这些。将来有时间会不会为了恢复故事连贯性去修改《陪你到世界终结》呢?我们等等看吧。
这本书的纸质版比网络版多了一封芷卉写给溪川的信,其中提到的一些情节在其他书中出现过,最重要的是后来大家还是朋友。还有一个番外《愒日惜时》过一阵可以随缘上网找找。
人的初心是一颗种子,这也是我对自己、对这本书说的话。
14年了,我还在写作,和我的初心在一起,耐心等着它,总会长出些什么。
再见,《天蓝海蓝》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