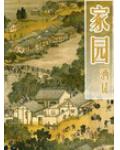第七章 盛世 (六 上)阳光一点点变强,变烈,长槊的影子从丈余变成了短短的数寸。
厮杀声却一点儿也没有变弱,无数壮年男子前仆后继,使天地间的血色愈发鲜艳。
仗打到这种地步,敌我双方将士都杀红了眼。
防御者踩在同伴的遗体上死战不退,狼骑也如闻到蜂蜜味道的蚂蚁般,剥掉一层又爬上来一层。
谢映登、刘季真等远道而来的豪杰起初还能尊重守将的命令,站在临近黄花豁子的一处烽火台上观战。
没过多久便被惨烈的战斗烧得血脉贲张,抓起各自的兵器冲到了第一线。
他们这些人身手矫健,投入战斗后,立刻将突厥人的攻势压了下去。
但部族武士刚刚离开城头,车轮大的石块便接二连三地砸了过来。
有些石块没等到达目的地便于中途坠落,将长城脚下的狼骑砸得血肉横飞,指挥着投石车的波斯人却仿佛什么都没看到般,平平淡淡地调整射程,将下一轮石弹再度发射到半空中。
每轮巨石只有两块,却令守军防不胜防。
时德方想尽各种手段,试图用床子弩将远处的投石车破坏掉。
但呼啸的山风却总是令弩箭失去准头。
突厥人见投石车攻击见效,也愈发乖觉起来,派了几百仆从举着大盾团团围在其周围,宁可仆从们被高速飞来的弩箭活活射成肉串,也不肯让投石车受到半点损害。
“***,还叫不叫人活了!”刘季真在城头上躲得郁闷,拄着血淋淋的长槊嘟囔。
还没等他话音落下,一块磨盘大的石头带着风声飞来,直接将其面前的城垛击飞了出去。
两旁的护卫舍命扑上,将刘大可汗压于身底。
片刻尘烟落尽,刘季真从泥浆中爬起,抹了把脸上的血块,指着城下破口大骂。
转眼又一块巨石砸来,他就地一骨碌,远远地滚了开去。
口中污言秽语不绝,气焰却被打丢了八分,整个人看上去都颓丧起来。
韩建纮在江湖上打滚多年,早有一些用兵心得。
见到这种情况,赶紧跑到时德睿的身边,忧心忡忡地说道:“怕是得主动杀出去,将那投石车毁了。
再这样砸几下,弟兄们的士气就被砸光了!”时德睿何尝不知道一味地消极防御不是个办法。
但自家弟兄都奉命在营里休息,一时半会儿叫不过来。
想提醒胞弟时德方下令主动出击,又怕建议不当,反而乱了守军阵脚。
正迟疑间,又听见谢映登低声叫道:“出不得。
那些突厥人还留着后手。
你看着山谷里还有两侧的山坡上,狼骑聚了不下万人。
主动出击,即便能毁了投石车,也难活着杀回来!”“那也不能在这干挨砸!”韩建纮憋得七窍生烟,心里好后悔没带自家弟兄前来观战。
眼下四周除了河东兵就是博陵兵,他自己想豁出去与敌人拼命,其他人也未必肯追随。
好不容易盼到投石车休息,狼骑又蜂拥着爬上城墙。
黄花豁子这段长城是临时赶工建成的,本来就不甚齐整。
被投石车三番五次地招呼,表面早已变得凹凸不平。
部族武士们则充分利用了那些凹凸点,竖起云梯,推动龟盾,争先恐后,不死不休。
众豪杰丢掉各种乱七八糟的想法,举刀迎战。
双方又是一场硬碰硬,数十名率先登上城头的狼骑尽数被剁翻,豪杰们自己的亲信也倒下了十余个。
得到喘息的弓箭手们拉开角弓,瞄准云梯附近的武士攒射,力气大的士卒举起滚木礌石,雨点般地下砸,在城墙下残缺不全的尸体当中添上新的碎肉。
有名武士刚刚探出半个身体,被刘季真干净利落地扫掉了脑袋。
喷着血的脖颈盘旋下坠。
一根狼牙快速从血瀑中探出来,直刺刘季真胸口。
刘季真跟跄着后退,避开狼牙棒的尖齿。
没等狼牙棒的主人翻上城墙,他又合身扑了上去,一刀砍中了对方肩膀。
云梯上的其他武士抛出套马索,缠上刘季真的大腿。
一边用力拉紧,一边借着刘季真挣脱的力量登上城墙。
上官碧跑过来帮忙,挥刀割断套马索。
刚刚站稳的武士失去了助力,身体向后歪斜,两腿交错着在城墙边缘打转儿。
女马贼毫不客气地推了他一把,然后拧身挥刀,隔开斜向刺来的钢叉。
“啊!”持索武士惨叫着跌落。
钢叉的主人心里打了个突,手上力道稍软。
上官碧侧身跨步,将钢叉引偏,紧跟着提膝盖抬腿,一记膝锤,重重地顶在对方**。
持叉武士没想到眼前的女人看似弱不禁风,手段却如此狠辣,躲避不及,疼得厉声长嚎。
缓过气来的刘季真冲到他身边,狠狠地一刀剁下,彻底解决了他的痛苦。
两个马贼头相视而笑,并肩扑向新的敌人。
手起刀落,在城头清理出一片空间。
几名刚刚从马道上赶来支援的河东士卒看到空隙,举着挠钩沿城墙拉扯,三下两下,将一座攻城梯连同梯子上的敌人一并扯翻于地。
“快躲,小心突厥人向这里扔石头!”刘季真挨砸挨出了经验,发觉城墙上的敌军开始变稀少,立刻向弟兄们出言提醒。
掀翻了云梯的河东士卒闻言赶紧后退,避开城墙外沿,以免让控制投石车的波斯人得到机会。
这次,令人闻声色变的石块却迟迟没有落下来。
相反,城墙下响起了一阵激越的战鼓声。
众豪杰与守军合力杀光眼前剩余的狼骑,俯身下望。
只见狭长的山谷中不知何时多了数百铁甲壮士,挥舞着陌刀将城墙附近的敌军像割麦子一样割翻。
气焰正盛的部族武士受到迎头重击,一时间做不出任何调整。
顺着打开的城门,更多的铁甲壮士鱼贯杀了出去,压得狼骑节节后退。
这伙人都是军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好手,个个以一当十。
由一名身材高大的武将率领着,片刻之间便在狼骑中硬切出一道缝隙来。
山谷中的狼骑再顾不上攻城,左右齐向中间压,试图将出击的守军分割包围,趁机夺取城门。
陌刀甲士们却连绵不绝,队伍被冲断后很快又连接上,如一条雪地上的溪流般,从城门一直连续到阵前,顺着固定的方向继续前进。
投石车、羽箭、床弩,攻守双方的远程武器再次失去作用。
谁也不敢胡乱发射,以免射不中目标,反而帮了敌人的大忙。
山谷中的部族武士虽然人数众多,能和重装甲士们相接触的却只有几百个。
而这几百个幸运者,却远非重装甲士的对手。
往往一个照面就被砍翻,连人带兵器一并做了甲士们的垫脚布。
踏着狼骑的尸体,重装甲士缓缓向前推进。
无论哪个试图阻挡,都被雪亮的陌刀砍成数段。
不仅突厥人和他的仆从们被杀得晕头转向,即便是城墙上观战的豪杰们也从没见过如此凶悍的打法,一个个惊得合不拢嘴巴。
半晌,才有人愕然地追问道:“那是谁,谁带人杀出去了?”“去年第一个登上京师城墙者!”几名来自河东的将领傲然回答。
不用直接说出名姓,提起率先攻入长安的战绩,大伙便知道此子是谁。
乱世中武将最容易扬名,但在层出不穷的将星中,若论勇悍,河东雷永吉甘居第二,无人敢吹嘘说自己是第一。
“好汉子!”无论先前服气不服气,众豪杰此时都不得不佩服雷永吉的勇猛。
只见他双手挥舞着一杆丈许长的陌刀,带队冲杀,手下根本没有一合之将。
突厥人数次试图结起阵来,挡住他的锋芒。
往往弹指的功夫都无法坚持住,防线便被他冲得四分五裂。
挡在投石车前的奴隶们吓呆了,丢下手中盾牌,四散奔逃。
周围督战的突厥士卒接连砍翻数名奴隶,却根本无法阻拦众人的脚步。
眼看着中原甲士就要靠近投石车,组织进攻的突厥将领大急,吹响号角,将正在攻城的以及山坡上观战的狼骑全部调了回来。
层层迭迭挡在甲士队伍前,双方在狭窄的山谷中激战,每前进或者后退一步都要付出无数条生命。
“向前,向前!”出击的甲士之中有人高呼。
无数弟兄昂首响应。
虽然人数不及对方十分之一,气势确如下山猛虎,咆哮冲杀,杀得敌军心惊胆战。
转瞬之间,两道仓促组织的防线又被大伙冲开,雷永吉双脚所踏之处,已经接近了祭台边缘。
指挥作战的突厥将领无奈,只好带着自己的亲兵迎了上来。
山谷两翼的狼骑也发了疯,一波接一波,舍命向甲士们的队列猛扑。
狼骑毕竟人多,僵持了片刻后,逐渐挽回了劣势。
两侧山坡上的武士奋力前挤,数度涌到了城门附近,又数度被守军砍了回去。
众豪杰猜出了雷永吉的想法,赶紧冲到城门旁给他助威。
敌我双方贴着城墙跟又一阵乱杀,直杀得尸横遍地,血流成河。
“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呜”关键时刻,四野里响起一片悠长凄厉的角声,凄厉苍凉宛若鬼哭。
山谷里的部族武士们闻听此音,个个如喝了药般,舍生忘死。
伴着角声,有杆绘着金色狼头的大纛旗挑了起来,五匹毛驴大的白狼跃入人群,冲着中原甲士们张开血盆大口。
“长生天保佑大汗!”领军的伯克振臂欢呼。
“大汗!大汗!大汗!”数万部族武士齐声呐喊。
“当苍狼重现世间,地面上长出红色的野草!喝狼奶长大孩子们,可曾记得你祖先的荣耀…”先前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的萨满们又钻了出来,一边摇着骨铃,一边以古怪的语调吟唱。
“我们是苍狼的子孙,骏马是我们的翅膀……”部族武士们痴迷地吟唱着,忘记了恐惧,也忘记了疼痛。
山谷里的形势对出击者越来越不利,雷永吉等人与投石车之间只剩下的三、五步距离,可就是这数步之遥,却如天堑般,大伙无论如何也冲不过去。
猛将军手中的陌刀已经砍出了无数缺口,脚下的包铁战靴也越来越沉,身后的弟兄们相继倒下,渐渐地,出击的队伍也裂成了数段,彼此不能相接。
“杀!”他怒喝着挥刀,将靠近自己的两名敌人劈成四段,然后回头看了看,扯开嗓子命令:“关城门——”“关城门———!”陷入敌群中的重装甲士们机械地重复。
好像根本不知道这个命令对大伙来说意味着什么。
喊罢,他们不再回头,不再管两侧蜂拥而来的敌人,大步向前。
一名小伯克挡在了雷永吉面前,弯刀力劈。
雷永吉连躲避的动作都没做,手中陌刀对着敌人的脑门砍去。
小伯克没想到自己遇见了一个不怕死的,气得大声咆哮,将砍到半途的弯刀撤回来,挡在自己身前。
雷永吉狞笑着加力,锯齿般的刀锋砸飞了小伯克的兵器,砸扁小伯克的头盔,将小伯克的脑袋硬生生砸进了铠甲中。
还有两步。
他在心里默默告诉自己。
踏过对方的尸体,陌刀横扫。
两名突厥武士被刀锋扫中,身体凹进去数寸。
雷永吉奋力前推,以两名垂死的突厥武士为盾牌,推得其他武士连连后退。
他身边的护卫狂奔向前,借着自家主将劈开的血路扑到山谷左侧的攻城车旁。
举起陌刀,力劈华山。
白花花的木渣四下纷飞,投石车被砍得吱吱咯咯乱响。
周围的突厥武士和奴隶仆从叫嚷着围拢过来,试图将陌刀甲士逼开。
更多的长城守御者奋不顾身冲上,将突厥武士与仆从们挡在***外。
“呯!”“呯!”砍砸声沉闷得令人窒息。
刹那间,几乎所有人的目光都投向此处,带着期盼、恼怒或者憎恨,看着雷永吉与他的弟兄们将投石车一点点肢解。
远处的狼骑们无法靠前,将手中兵器乱纷纷丢向投石车附近。
长城守御者们一边阻挡武士的进攻,一边拨打从天而降的兵器,浑身浴血,两腿却坚若磐石。
左侧的投石车接连遭受了二十几下劈砍,终于支撑不住,轰然而倒。
狼骑、仆从、围在投石车附近掩护同伴的中原壮士们全部被砸在了碎裂的木架之下。
幸存的壮士们哈哈大笑,抹去脸上的血迹,转身再奔右侧投石车。
突厥武士们无力也无胆阻拦,节节后退。
他们号称是苍狼的子孙,自幼以胆大凶悍为荣。
今天,他们却看到了比自己还胆大,还凶悍者。
投石车高逾丈半,支架底部的长度与宽度也超过了九尺。
左侧那辆投石车倒下后,砍砸它的人几乎无一幸免。
而来自中原的壮士们却对危险视而不见,笑着上前,笑着厮杀,笑着迎接下一波死亡。
这是一群疯子。
狼骑们绝望地得出结论。
只有疯子才会这样,把血当酒,把死亡当成一场盛宴。
他们不愿也不想与疯子拼命,倒退着避开对方的锋芒。
他们眼睁睁地看着对方接近第二辆投石车,高高地举起锯齿嶙峋的陌刀。
“当苍狼重现世间,地面上将长出红色的野草!喝狼奶长大孩子们,可曾记得你祖先的荣耀…”萨满们的声音再度响起,就像魔鬼在地狱中召唤自己的同伴。
几道白光迅速从狼骑头顶飞过,咆哮着扑向铁甲壮士。
雷永吉挥刀阻挡,刀锋却劈了个空,他惊诧地侧头,看到一张血盆大口向自己的脖颈咬来。
五头白色巨狼,在萨满们的驱使下扑入了人群。
雷永吉躲开了第一只巨狼的扑击,用战靴踢翻了第二只。
第三只巨狼试图咬住他的横刀,被他用刀刃逼退。
掉过已经不再锋利的刀头,他准备用尖锐的刀纂刺死扑过来的下一头巨狼。
后腰间却突然一麻,半截带血的利刃从胸前露了出来。
“苍狼的子孙,你们还等什么?”尼度设阿史那耶玄狞笑着命令。
从雷永吉后腰上拔出铁矛,他骄傲地前指,将染血的矛尖指向了投石车附近的十几名中原壮士。
五头白狼张开血盆大口,发出厉声长嚎。
“嗷——嗷—嗷!”伴着嚎叫声,一滴滴人血顺着它们的尖牙滴落。
“嗷—嗷——嗷嗷!”突厥将士与巨狼同时厉声长嚎,挥动兵器,扑向曾经吓得他们不敢上前接战的长城守卫者。
六名长城守卫者背靠着投石车,围成了一个小***。
他们相互配合,掩护身后的同伴们继续劈砍投石车支架。
四下里扑上来的“狼群”犹如海浪,他们却如礁石般将海浪撞碎,撞飞一团团血色浪花。
“呯”“呯!”“呯!”群狼环伺之下,砍砸的节律有条不紊。
巨大的投石车开始摇晃,倾斜,捆绑横梁的皮索与支架摩擦,发出刺耳的吱吱咯咯声。
五匹巨狼惊恐万状,晃着尾巴逃开。
狼骑们也唯恐再次遭受池鱼之殃,乱纷纷后退。
浑身是血的长城守卫们笑着放下陌刀,用刀柄支撑住身体。
这一刻,他们眼中满是轻蔑。
一名还有力气走动的长城守护者趔趄着挪到雷永吉将军的遗体旁,将其拖向摇摇欲垮的投石车,距离他最近的突厥武士明明只要伸出兵器便可将其留下,却惊恐地向后退了半步,不敢做任何阻拦。
“轰!”投石车倒地,烟尘腾空,遮断所有人的视线。
“风萧萧兮易水寒!”当烟尘落下后,山谷中依稀响起一声吟唱。
无悲,无惧,只有凛冽的决然。
什么意思,狼骑们听不懂,这首仅有两句,却传唱千年的中原古韵,他们永远不会懂。
跳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