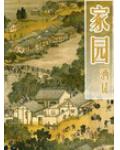第七章 盛世 (九 上)|| 有风,很大,这种大风的天气里羽箭根本无法射准。
但两军交战时弓箭手无需瞄准,他们只需要按照将领的口令将雕翎射向某一个大致区域,便能依靠羽箭的密度给予敌军最大的杀伤。
突厥狼骑最擅长的便是射术,阿史那骨托鲁甚至可以确信手中只有长槊的博陵军会在自己精心准备的弓箭大餐前狼狈逃窜。
不,他们即便逃窜也无法保住性命,如此近的距离,如此密的羽箭,根本没有人能幸运地逃过!然而,事实却正和骨托鲁预料中相反。
浓密的箭雨非但没能让博陵军大阵分崩离析,腾空而起的黄色烟雾反倒给本来就杀气腾腾的军阵平添了几分神秘和威严。
在羽箭攒射中,那条初醒的巨龙向前一步,又向前一步,转眼之间已经将阿史那骨托鲁牺牲了上千弟兄才制造出来的空隙跨过了一半。
“怎么回事?元庆这头蠢驴!”阿史那骨托鲁大惊,气急败坏地骂道。
一万五千名弓箭手的攒射却未能阻挡博陵军的分毫,不是指挥者阿史那元庆故意捣乱还能有什么原因?“抛射,传我的命令,抛射。
快!”他大喊大叫,唯恐传令兵无法正确转述自己的命令。
但很快,骨托鲁明白自己错了,左前统军阿史那元庆没有犯丝毫错误,从一开始,他就采用了抛射战术。
让羽箭斜向升空,避开博陵军前排的巨盾和侧翼的皮盾,径直打击对方军阵中央。
但是,所有突厥人都低估了博陵军大阵对于羽箭的抗击力。
第一排巨盾和江湖豪杰手中的皮盾只是为了防御流矢和羽箭直射,对于凌空飞来的箭雨,他们居然异想天开,依靠竖起的槊杆拨打格挡。
而偏偏这种看似愚蠢至极的方法,在此刻收到了无法想象的效果。
高速掠过的大风已经让羽箭的发飘,力道大为减弱。
修长的箭杆被一排排有节奏来回摆动的长槊拨打,梳理,过筛,能连续飞跃三重槊杆却不被拨落的羽箭已经不足一半。
而博陵军高举的长槊何止三重,当羽箭勉强到达预定位置,还能有杀伤力的只剩下了不足两成。
这两成能造成杀伤的羽箭,面对博陵士卒人与人间隔一步半稀疏队列,也只能有四分之一勉强能击中正确目标!(注1)两成羽箭的四分之一,也就是说,承载了骨托鲁大汗全部希望的羽箭,真正能对博陵军造成杀伤的只有半成不到。
即便这区区半成羽箭,依旧要面对铠甲的防护力和是否命中士卒要害等考验。
如此轻微的战损对一支身经百战的队伍已经够不成任何打击。
受了轻伤的博陵士卒随手将羽箭拔出向地上一丢,便又跟上了袍泽的步伐。
间或有不幸的博陵弟兄被流矢击中要害,后排正对着他的袍泽立刻迅速上前两步,填补牺牲者留下的空白。
下一排士卒填补第二排,再下一排弟兄依次补位,整个大阵的完整性丝毫不受影响。
天!居然有这种步兵战术?待看清楚了博陵军的对抗羽箭方法,习惯了骑射制敌的突厥贵胄们一个个目瞪口呆。
如果中原的军队都采用这种战术?突厥人如何可能与之为敌。
阿史那达曼,阿史那贺鲁,阿史那湖色罗等突厥贵胄同时将目光转向阿史那骨托鲁,这一刻,他们对夺取中原的信心彻底动摇。
他们当然不知道,此军阵是由北周、大隋两代王朝中的优秀将领,经过数十年的实战总结、改进才创造出来的。
其中凝聚了大将军王杨爽,楚公杨素、上柱国张须陀和敌将李旭无数将领的心血。
就在昨天,此阵还经历了老长史陈演寿的一番补充,从而达到绚丽的顶点。
这样的军阵,士卒非经历极其严格的训练根本不能掌握,将领非具备极其坚强的心志不敢实施。
可以说,整个中原,除了骨托鲁等人眼前这支脱胎于汾阳边军的博陵军,其他诸侯麾下的兵马根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学会,也根本不可能施展得出来。
就在突厥贵胄们无法从震惊中缓过神来的当口,博陵军大阵已经将骨托鲁精心布置的死亡地带跨了过去。
双方再度接触,博陵军三角形的阵锋插入突厥狼骑中间,然后迅速被巨大的阻力压成了一道弧线。
前排的巨盾手没有其他兵器,快速将手中巨盾转竖为横。
盾盾边缘相接,凌空加起一道木栅栏。
在这沉重的木栅栏之后,第二排士卒上前跨步,口中大喝一声“杀!”三尺槊锋掠过盾牌上缘,径直地刺入了狼骑的胸口。
说时迟,那时快,第三排博陵士卒看到两军接触,迅速将斜举的长槊放平,双脚发力前冲,顺着第二排士卒六留出的空隙向前补位,口中大喝一声“杀!”,又将数十根长槊刺入了突厥狼骑中间。
没等被打懵了的狼骑做出反应,第四排博陵士卒又至,还是一声大喝,干净利落地将手中长槊刺了出去。
敌我双方在军阵变形之后的接触面不过二十余人,三排长槊连刺,最大杀伤不过六十名名狼骑。
但随着这六十名狼骑的倒下,挡在博陵军面前的武士们顿时变得稀疏起来。
他们不畏惧战斗。
可只能被杀,却无法还手的战斗,谁也承受不了!屋漏偏逢连夜雨。
就在此时,博陵军大阵中又传来一声激越的号角。
大半数人马已经走出山谷河东弓箭手们,在陈演寿的指挥下斜斜地举起了角弓,将羽箭对准还在向博陵军骚扰的突厥同行射了过去。
论对射术的掌握程度,河东弓箭手远不及他们的塞上同行。
但论手中的兵器,狼骑所持木弓却永远无法与中原工匠精心制作的角弓相提并论。
组合了六种材料的反弯角弓射出的羽箭初速度大,力道足,受风的影响小,虽然有近三分之一被吹偏,仍然剩下了一万余支砸进了突厥弓箭手队伍内。
刹那间,正在引弓攒射的突厥弓箭手队伍便腾起了一股血雾,无数人倒地,无数受伤者在血泊中翻滚哀号。
身为中原军队阵腰的老长史陈演寿却丝毫不给敌人喘息机会,奋力吹角,随着高亢的角声,又一排箭雨凌空射了过去。
“嘭!”弓弦响处,一片羽箭组成的乌云遮断本来就十分柔弱的日光。
被阴影覆盖的突厥弓箭手转过身体,仓皇后逃。
人的双腿怎可能跑得过羽箭,随着一点点白光落下,上千人的身体被羽箭射穿。
锐利的箭簇撕开皮甲,撕开血肉与筋骨,将奔走不及的狼骑直接钉在了地上。
“转身,右前方,八十步,射!”老长史陈演寿再度举起号角,用角声引导着上万支羽箭向挡在自家右侧的突厥弓箭手还击。
雕翎腾空,从列队前进的博陵弓箭手上方掠过,然后苍鹰般疾扑而落,啄瞎突厥人的眼睛,撕碎突厥人的喉咙。
连番受到打击了突厥弓箭手哪里还顾得上再阻杀博陵军将士,或者手忙脚乱的逃避,或者在个别英勇的将领指挥下,匆忙向河东同行还击。
以密集阵列跟随在博陵军身后前行的河东弓箭手立刻出现了伤亡,血光四下飞溅。
但前方的博陵军弟兄与敌军舍命搏杀,河东将士不敢也不愿意在友军面前示弱。
他们冒着突厥人的箭雨,将手中雕翎一波波向草原同行射去。
自己这边倒下一名弟兄,至少也要让突厥人以同样的代价来偿还。
白羽在空中飞来飞去,两支雕翎正面相撞,闪着火星落地的情况屡见不鲜。
每一波弓箭落下,必然有一股血雾腾起。
但河东士卒却根本不为身边的伤亡所动。
这些仓促被征入军中,没经历过几次恶战的新兵终于成熟了起来,宁可正面被射穿身体,也不愿意自己或者袍泽的后背卖给敌人。
他们在箭雨中边走边战,从容不迫。
他们跟在博陵军的身后,亦步亦趋,不离不弃。
有了河东弓箭手的掩护,博陵将士无需再顾及来自头顶的威胁。
他们潮水般向前推进,将长槊如海浪般捅进突厥人的队伍。
在一连串的迭刺之下,突厥狼骑就像过了季的无根竹笋,一层层被剥了一下,一层层变为博陵军脚下的尸体。
看到自家弟兄当不住博陵军锋樱,几名领军的突厥伯克冒险调整战术,尽力让麾下狼骑避开槊阵正前,试图迂回到两侧,从侧翼打开槊阵缺口。
作为大阵两翼的江湖豪杰和塞上马贼们怎肯让突厥人的图谋得逞,拎着朴刀皮盾便迎了上去。
有博陵军为依靠,大伙无需担心自家军阵出现破绽,因此冲杀起来格外得心应手。
试图取巧的狼骑和部族武士很快就发现两翼的长城守护者一点不比大阵正前的长城守护者容易对付。
虽然他们手里所持的不是那种长得可怕的步槊,但出招比正前方的长城守护者更狠辣,杀人技巧也更娴熟。
弓箭手疲于自保,狼骑和部族武士在中原守护者的逼迫下节节败退。
如果不是仗着人数远远多余对方,他们几乎就要溃不成军。
见到这种情况,骨托鲁再也无法冷静下去了。
从身边的大梅碌阿史那候斤手里夺过令旗,拼命急挥,“原地,原地接战。
各守本位。
后退者格杀勿论。
杀敌一人,勿论出身,皆赏羊十头,马三匹!”嚷嚷完了,骨托鲁又回过头,瞪着赤红的眼睛对自己的亲弟弟阿史那达曼命令,“达曼,你带本部兵马上去。
顶住博陵军,不得让他们继续前进。”
“大哥?!!”阿史那达曼没想到一向宠爱自己的哥哥居然要第一个派自己去上前送死,瞪圆了眼睛抗议。
“速去。
候斤,你带领我的亲卫督战。
无论是谁,后退超过五步者,立刻斩首。
萎缩不前者,与通敌等罪。
部众剥夺,草场充公!”阿史那骨托鲁仿佛没压根儿听见达曼的抗议,解下自己的佩刀,直接塞到候斤之手。
“是!大汗!”阿史那候斤抱住骨托鲁的佩刀,转身去调兵遣将。
听哥哥已经下了如此狠心的命令,阿史那达曼知道再无回旋余地,跺了跺脚,举刀跑向自家部曲。
“弟兄们,跟我上,让他们看看突厥男人的血!”他大声呐喊,带队逆着败军向前。
不再抱怨,也不再看自己的哥哥一眼。
“贺鲁,你带领本部兵马跟在达曼身后。
组成第二垒,不得放任何人通过你面前。
包括达曼!”骨托鲁目送弟弟离开,然后命令亲信大将阿史那贺鲁去组建第二道防御阵地。
大汗的亲弟弟都压到第一线去了,阿史那贺鲁当然不敢再多废话。
闷闷地答应一声,转身而去。
骨托鲁继续分发令箭,将阿史那奚,阿史那玄,阿史那保柱等突厥贵胄全部派了上去,一层层在博陵军前方设立阵地。
然后又命人吹响号角,将麒麟谷,黄花豁子两处参与佯攻的士卒全部调向葫芦涧,集中兵力。
待得到两处的角声回应之后,喘了口气,将头转向心腹大将阿史那湖色罗低声命令道,“你,骑着我的马,去把军营和附近能参战的弟兄全调过来,不用等待我的将令,到达位置后,直接发动攻击!”“大汗?”阿史那湖色罗接过令箭,脚步却无法挪动分毫。
受长城附近地形所限制,骨托鲁每次出战带领的人都不足全营兵马的二分之一。
手中这支令箭,相当于近二十万大军的调动权利。
而眼前这些出战的弟兄锐气已失,万一在自己回来之前,达曼与贺鲁等人的兵马坚持不住,骨托鲁身边便无兵可用,十有八九会死在李旭手里!“快去!”阿史那骨托鲁知道爱将想表达什么意思,用手指了指不远处仍然在继续败退的大军,苦笑着道:“如果此战败了,我还能活下去么?你能早到一步,便是救了我一步。
否则,便等着赎回我的尸体吧!”“末将定然不辜负大汗所托!”阿史那湖色罗手按右胸,深深俯首。
他知道敌我双方已经到了必分胜负时刻,不敢再多说什么。
跳上骨托鲁的坐骑,在马背上狠抽了两鞭子,如飞般远去。
也只能如此了!派出了身边最后一员将领。
骨托鲁内心反而变得安宁。
他从贴身亲兵手里抢过一把横刀,紧握着站在了自己的羊毛大纛之下。
几名溃散的部族武士从他身边不远处跑过,骨托鲁刀尖一直,立刻有亲兵冲上去,不由分说将逃兵砍倒,割下脑袋,扔到了骨托鲁脚边。
负责督战的大梅碌阿史那候斤也不再手软,带着清一色的黑甲侍卫,在骨托鲁附近横成一道人墙。
无论任何人以任何理由试图穿墙而过,侍卫们立刻手起刀落,干净利索地割下他的脑袋,血淋淋地扔到自己的脚下。
有大汗地弟弟亲自领兵战斗在最前方,身后还有一群督战的凶神恶煞。
狼骑和部族武士们的士气稍稍提高的数分。
在低级将领们的指挥下,他们结成小队,负隅顽抗。
中原联军毕竟人少,在敌人舍死忘生的阻拦下,前进脚步大幅度放慢。
李旭见敌军死战不退,立即改变战术,命令隐藏于博陵军方阵部位的弓箭手们引弓向前攒射。
顷刻间,狼骑又倒下了数百人。
阿史那达曼也不示弱,带领亲信弯弓搭箭,对准前排的博陵军将士奋勇还击。
很多狼骑和部族武士都误伤在了阿史那达曼的箭下,但这种不分敌我的杀伤毕竟给博陵军造成了一定困扰。
转眼之间,刚刚被弓箭手射开的阵脚又被新的部族武士填满。
在财富的**与死亡威胁的双重作用下,牧人们一层层被杀死,一层层拥挤上来,居然短时间内,让博陵军止步不前。
双方的弓箭大战此时也陷入了胶着状态。
虽然河东弓箭手在陈演寿的指挥下打了突厥同行一个出其不意,给敌人造成了极大的杀伤。
但当突厥弓箭手将注意力从博陵军槊手身上全部集中到河东弓箭手这边,又补充了大量援军之后,竟凭借着高出河东将士不止一筹的射术,渐渐挽回了颓势。
担任两翼护卫的刘季真和时德睿二将多次分出兵来,试图冲进突厥弓箭手队伍,予敌以重创,都被苏啜附离带领亲信死死地挡在了阵地之外。
好在此时天空中的风力变得更大,羽箭的杀伤力骤减。
否则河东兵马肯定因损失巨大而丧失战斗力。
战斗到了此时已经进行到白热状态,敌我双方都使上了浑身解数,只要能杀伤对方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
几名突厥伯克看出陈演寿为弓箭兵之胆,立刻仗着射技高超,集中几柄强弓向他攒射。
羽箭多数被风力吹歪了,但数轮之后,终究有一箭命中目标。
老长史闷哼一声,手中号角落地,身边弓箭手立刻队形混乱。
突厥人看到目标达成,赶紧抓紧机会展开反扑。
但没等他们第二次拉开弓弦,一阵激昂的角声从敌阵中响起。
老长史陈演寿手握号角,身体半蹲半跪,布袍被血染透,角声却连绵不绝,宛若虎啸龙吟。
听到角声,河东将士重新抖手精神,挽弓回射。
双方弓箭手又开始较量起射术,每一刻都有人倒在箭下,却再无人言退。
就在此时,随着一阵闷雷般的鼓声响过,山谷中又杀出一哨兵马。
快速向左右一分,直接扑向突厥弓箭手。
负责护卫弓箭手的苏啜附离赶紧领兵迎战,却不料这次出来的河东兵马甚多。
分出了四分之一缠住了他麾下部属,另外四分之三中的一分护在自家弓箭手阵外,两分冲入了突厥弓箭手阵内大肆砍杀。
“以多欺少,不算英雄!”苏啜附离气得大叫,举着粗大的横刀,在长城守护者当中往来冲杀,势若疯狗。
他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部落和族群,如果再完不成骨托鲁交付的任务,回到草原上将永无立足之地。
长城守护者们却丝毫不理解他的苦衷,在底层军官的带领下动一转,西一转,不到半柱香时间,已经将苏啜附离身边的亲兵杀了个干干净净。
“我跟你们拼了!”红了眼的苏啜附离高举横刀,径直冲向陈演寿的座驾。
他想用自己的生命证明自己存在的价值,对方却不肯再给他机会。
还没等他靠近弓箭手阵列外围,一名大将举槊冲上,槊锋一挑一引,将苏啜附离绊倒于地,紧跟着一槊刺出,正中其哽嗓咽喉。
“河东姜宝宜在此,贼子速速束手!”挑起苏啜附离的头颅,姜宝宜大声喝令。
他是此阵的阵尾,关键时刻奉李旭之命杀出,一下子便发挥出了巨大作用。
苏啜附离战死,追随他的霫族武士立刻散去。
没人保护的突厥弓箭手转眼成了待宰羔羊,被河东弟兄杀了个七零八落。
掌管整个大阵的李旭见到机会,立刻调兵遣将,将完成任务的阵尾调到相对平坦的左翼,沿左翼斜向前压,以神龙摆尾之势予敌军以重创。
这伙生力军的投入立刻使得场上局面大变。
抵挡博陵军攻击的突厥人本来就已经非常吃力,又不得不分出兵来去抵挡姜宝宜,立刻首尾不能兼顾。
第一道阻拦眼看就要崩溃。
气红了眼睛的阿史那达曼带领亲兵冲到博陵军大阵前,挥斧猛劈,劈裂一面盾牌,直插阵核。
李旭在阵中看得真切,挥动令旗,命盾牌手们闪出空隙,放数百突厥人入阵。
然后敲响战鼓,大阵迅速闭上缺口,阵内一团团七蕊梅花擦着阿史那达曼等人快速旋转,花蕊乱吐,三下两下将入阵的突厥人杀了精光。
阿史那达曼见势不妙,转身欲走。
周大牛和张江带着亲兵夹了过去,两朵梅花交汇,然后快速分开。
阿史那达曼身上登时多出了数个透明窟窿,哼都没哼,轰然而倒。
主将身死,突厥人的第一道防线立刻告破。
博陵军加快脚步,冲向敌军第二垒。
阿史那贺鲁赶紧领兵顶上,用自己本部兵马携裹着阿史那达曼麾下残兵死战不退。
怎奈博陵军越杀越勇,数息之间便将他精心构筑的防线捅了个千疮百孔,摇摇欲坠。
站在羊毛大纛下,阿史那骨托鲁心如刀割。
他自幼丧父,年少时屡屡遭受始必兄弟的欺负,全靠亲弟弟达曼这个精神寄托才不至于郁闷至死。
因此,于他心中,达曼就像自己儿子般重要,绝对不允许任人伤害。
但今天为了稳定军心,他却不得不将达曼派到了第一线去,然后眼睁睁地看着他被人捅死。
想到自己今天可能也会与弟弟“团聚”,骨托鲁心里更加凄凉。
偷偷抹了一把泪,回过头来,对着身边一个亲卫打扮的人问道,“如果我今天战死了。
你可怎么办?是不是立刻去投奔他?”那名亲兵闻听此言,立刻从腰间拔出刀,二话不说便向脖子上抹去。
骨托鲁吓得手忙脚乱,上前一把将亲兵死死抱住,一边偷偷流泪,一边哽咽着道:“我不过问问而已!你又何必去死?”“自从嫁给了你。
我什么时候想过别人。
骨托鲁,你尽管放心。
如果你今天战死了,陶阔脱丝没本事为你报仇,跟你一道走勇气还是有的!”扮作亲卫的陶阔脱丝丢下刀,呜咽着回答。
她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才导致今天两个她曾经最放不下的人自相残杀。
但经历了那么多事情,她已经相信命运。
是长生天安排了眼前这一切,作为长生天的孩子,她没法抱怨,没法抵抗,只能默默承受。
“大汗何出此言!”另一名亲兵打扮的女人低声喝问。
“为将者乃三军之胆,岂可轻易言败。
我军人数是敌人三倍,援军马上便到。
此处地形已经可以供骑兵展开,难道大汗不相信自己,还不相信狼骑的英勇么?”“滚!”虽然对方所说全是金玉良言,骨托鲁依旧破口大骂。
“你这个女人。
葬送了苏啜附离一个人还不够么?如果不是你,我岂会这么着急南下?”挨了骂的陈晚晴不敢还嘴,躬了一下身子,默默地闪到一边。
骨托鲁却不依不饶,走上前继续数落道:“你这个该受诅咒的女人。
苏啜附离为你连命都搭上去了。
你居然连眼泪都不肯为他掉一滴。
你的心肠真的比月牙湖底的冰还冷。
我知道了,在你眼里,他不过是把刀。
我们,我们这几十万人,在你眼里全是刀,对不对?江南大陈,恐怕在你眼里,除了陈家外,其他人全是牛羊草木吧?”陈晚晴被他骂得面色苍白,浑身发抖。
嘴唇嘟囔了好半天,才冷笑了一声,昂首回敬道:“大汗后悔了么?后悔了尽管杀我,拎着我的头去给李旭赔罪。
看他是否会放过你,放过你的部落?”阿史那骨托鲁虽然奸诈,毕竟是个突厥人,嘴巴远没对方灵巧。
被质问得无言以对,顿了顿脚,悻然道:“我何必杀你。
你这辈子无论毁了多少人,也无法看到好梦实现。
江南不会属于你们陈家。
江北也不会。
那里从来就没属于过你们陈家。”
说罢,不再理会陈晚晴,拥着陶阔脱丝继续观战。
看到李旭手持鼓槌,指挥千军万马如手使臂,心中暗道:“输给如此英雄,也不算委屈。
可惜我一时糊涂,让这么多突厥男儿为我殉葬!”正沮丧间,忽然听到山谷左侧一阵喧嚣。
正在扩大战果的河东兵马突然放弃对手,转身原地结阵。
紧跟着,数杆大纛挑过山梁,从黄花豁子附近赶来的一部分突厥兵马终于到达的战场。
没等骨托鲁抹额相庆,又一哨兵马呼啸而来。
竟是距离此地最近的一部突厥狼骑,听到葫芦涧的角鼓之声,在阿史那步真的带领下主动赶来援救。
两支新锐聚集到一处,立刻顶住了姜宝宜的攻势。
李旭见到这种情况,不得不重新调整队列,命令河东兵马向博陵军侧后收缩。
阿史那贺鲁也借此机会重新调整部属,居然和援军一道将劣势又搬回了几分。
时间拖延越久,对长城守卫者们肯定越不利。
刚才陈晚晴的话说得虽然刺耳,但突厥人在大营里休息的那部分兵马很快便能赶来却是事实。
此外,骨托鲁战前对形势估计不足,为了尽快破城,将狼骑徒步带上了战场。
而赶来援救他的狼骑作战目的不是为了破城,自然也会策马而至,充分发挥自家的特长。
在山谷中会战,无论突厥人是步兵还是骑兵,博陵军都有必胜把握。
在山谷外相对开阔的地方以步对骑,人数又远少于对方的情况下,李旭却真的未必能力挽天河。
想到最后胜利可能在一点点向自己倾斜,骨托鲁的心情渐渐好转。
手臂用力揽了揽陶阔脱丝的腰,动情地解释道:“刚才我的话并非完全是胡说。
如果我不幸战败,你带着咱们的孩子去投奔李旭,以他的为人,绝不会让你们母子受人欺凌。
而去投奔我那些族兄,恐怕不到一个月时间,咱家的部众和财产便全被他们吞了。
你们母子能留下三头活命的小羊都得感谢长生天!”陶阔脱丝轻轻点头,珠泪滚滚而落。
骨托鲁用大手在她脸上抹了抹,继续道:“如果此战我侥幸胜了。
攻破长城后,我也不会伤害李旭的妻儿。
你去出面收留她们。
附离是个英雄,值得我尊敬。
不像某些中原贵族,只想着自家,眼里从没有别人!”陈晚晴知道骨托鲁在拐着弯骂自己,心中百般滋味交织,脸上的表情却装作什么也没听见。
想到苏啜西尔当年的夫妻之恩,又想到苏啜附离为自己做得诸多事情,暗自思量道:“我真是把他们兄弟只当复仇的工具么?我真的有那么冷酷无情?兄终弟及,在草原上本来就合情合理,我又做错过什么?如果没有我,突厥人便不会南下,这话有谁会信?”转而想到刚才骨托鲁说话的神态,她心中愈发凄凉。
大陈国复国是空,昔日王谢两家的水榭歌台,终究要变成瓦砾场。
自己原来坚持复国,只是不愿意面对现实罢了。
眼下即便塞上诸部打到江南,会真的扶持一个中原王朝起来么?恐怕,这些永远是梦罢了。
如果这些是梦,那自己此生抓住了些什么?月牙湖畔与苏啜西尔兄弟刚刚相识的那段日子又涌入她的心头。
虽然年代已经非常久远,却历历在目,宛若昨日。
正沉沉想着心事,耳畔又有角声传来。
陈晚晴举头望去,看到就在来援的突厥人身后,一面红旗耀眼夺目。
旗面上写着斗大三个字,“河间?王”。
正是奉李旭之命埋伏在山间多日的王伏宝,接到烽火台上的信号,率领部众杀来。
这一下,局势愈发扑朔迷离。
几波突厥军队和中原军队你隔着我,我隔着你,往来厮杀,各不相让。
没等双方主帅根据新的形势调整战术,远远地又是一声号角,河东窦琮率领部众从骨托鲁的侧面杀来。
麒麟谷撤下来的各部联军也于阿史那陌米带领下急匆匆赶到。
如此混乱的局面,双方主帅当中若是谁能一眼看出胜负,那简直就是神仙下凡了。
骨托鲁这边人多势众,但王、窦两支兵马赶到后,李旭一方人数也不能算少。
李旭麾下将士骁勇善战,可几哨兵马实力差异巨大,综合起来,未必比狼骑好上多少。
士卒们也都明白,能不能压倒对方,取得决定性胜利就在今天,因此人人奋勇,个个争先,百死而不旋踵。
窦琮所部人数最少,却都是轻甲骑兵,正好适应山谷外围的相对平缓的地形。
带领麾下弟兄快速甩开哭笑不得的部族武士,占据一个山坡,然后他马刀奋力向前一挥。
轰隆隆,马蹄声令风云变色,数千骑箭一样刺到阿史那步真面前。
阿史那步真麾下原来都是骑兵,此刻却要站在地上接受骏马的践踏,甭提心里有多别扭了。
可别扭归别扭,仗打到了这个地步,谁也不敢怠慢。
抖擞精神,聚集成团,拼死缠住窦琮所部,坚决不放其向战场核心靠近。
最后赶来的阿史那陌米见自家兵马被窦琮所部骑兵踩得血肉横飞,心中大怒。
带着身边数千亲卫直扑窦琮侧翼。
他这边刚刚做出调整,与突厥人纠缠厮杀的王伏宝也立刻改变战术。
分出一部分人来缠住自家对手,派遣军中精锐一口咬住阿史那陌米所部的咽喉。
虽然是军中精锐,窦家军的战斗力依然不如对方。
与敌军接触后,队伍居然迅速被冲散。
将士们各自为战,彼此互不相顾。
好在这些人都是流寇出身,悍不畏死。
因此队形虽然乱了,士气却没有丝毫降低。
很多弟兄宁可凭着挨上突厥狼骑一刀,也要一刀捅进对方身体里边,与敌人同归于尽。
正所谓狭路相逢,勇者胜。
短时间内,阿史那陌米还真拿王伏宝的麾下将士没什么办法。
他这里一耽搁,阿史那步真那边立刻险象环生,大将窦琮三番五次带着亲兵从阿史那步真身边冲过,每次都能将步真麾下的弟兄卷走几百个。
阿史那思摸见不得自己弟兄吃亏,也立刻带了几千人赶过来,与阿史那步真二人合兵抵挡窦琮。
他们这厢用了近万将士,才勉强把三千河东轻骑挡住。
战场中央,阿史那贺鲁那里却又发成了变故。
一支不知道从何出飞来的短矛正中阿史那贺鲁的胸口,将其和身后的护卫直接穿成了葫芦串。
阿史那贺鲁战死,塞上联军的第二垒告破。
骨托鲁毫不犹豫,立刻将第三垒的阿史那奚,第四垒的阿史那玄,和第五垒的阿史那保柱等人全部派上去迎战。
自己带领侍卫和阿史那候斤紧随几名大将身后,转守为攻,誓与博陵军死拼到底。
骨托鲁心里很明白,眼前这仗既然已经打成了滚雪球,胜负便不再取决于自己和李旭谁的指挥更高明一些。
敌我双方谁能坚持时间更长,谁能投入更多的援军,谁便能取得最后胜利。
李旭所部兵马1/2|跳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