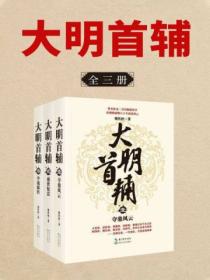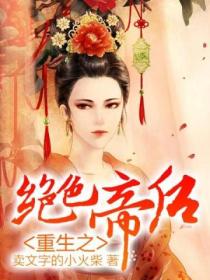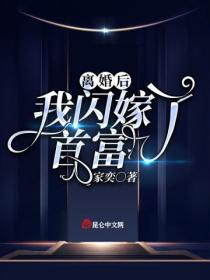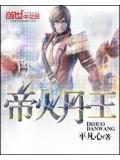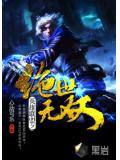第二十二回 行重贿徐晞买尚书 张后崩王振方用事
平定麓川的捷报传到京师的时候,正好是正统七年的元宵佳节期间,北京城一片欢腾。张太皇太后尽管卧病在床,还特意召见内阁大臣杨溥和英国公张辅,署理兵部事务、兵部右侍郎邝埜进宫,详细禀报情况,叮嘱正统皇帝要重重封赏平定麓川的有功之臣。正统皇帝新年伊始即闻佳音,更是喜之不胜,高高兴兴和文武百官一道欢度元宵,着实快乐了好几天,直到正月二十元宵节结束方才上朝。二月九日,正统皇帝根据内阁提议,任命礼部侍郎王英、翰林院侍读学士苗衷为壬戌科考试官,会试天下举子,取会元姚夔等一百四十九名。二月二十九日,又摆驾天寿山扫墓祭陵。三月十五日举行廷试,三月十七日,取刘俨为状元,赐进士及第、进士出身、同进士出身共一百四十九人,还取了若干副榜。接着,又根据内阁票拟,正统皇帝又下诏命户部免除陕西屯粮十分之五。等忙完这些事,已是四月上旬。这一段,内阁忙是忙了些,但事情办得倒还顺利,杨溥还带着马愉和曹鼐抽空去西杨府第看望了正在养病的杨士奇。不过,过了不久,一件麻烦事儿终于来了。
这一天,华盖殿早朝散罢——三殿重建后,早朝改在华盖殿了——正统皇帝在西角门召见几位大臣,内阁大臣杨溥、马愉、曹鼐,英国公张辅,礼部尚书胡滢,右都御史王文——前任右都御史陈智因事被御史于去年六月劾免,王文由大理寺卿迁右都御史署理都察院事,吏部尚书郭琎等人都来了,只有那内阁大臣杨士奇因病未能应召出席。
见大臣都到齐了,站在一旁的司礼监太监王振命人斟了一杯新茶递给正统皇帝,附在他耳旁嘀咕了一句,只见那正统皇帝呷了一口茶,对坐在末位的王文说道:“王爱卿,你把御史孙毓参劾本章念一遍,并把都察院监察情况说说吧。”
这是正统皇帝在张太皇太后染病后第一次单独召集大臣议事。这皇帝今年已经虚十六岁了,经过七八年的读书和历练,朱祈镇逐渐成长起来,可以单独上朝了,虽说国家大事他还是拿不定主意,仍然需要禀告张太皇太后,但怎么处理朝政也渐渐有了一些经验。他知道太皇太后的主意也是内阁杨溥的主意——杨士奇虽说仍然还是首辅,但一连数月病养,让他无力理政,内阁事务、国家大事都是杨溥裁决——这杨溥成了太皇太后和他自己的依靠,所以朝中无论大小事情,他都非要杨溥到场不可。
遵照谕旨,右都御史王文从王振手中接过御史孙毓参劾本章,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原来那孙毓本章参劾的是吏部尚书郭琎,说郭琎的儿子郭亮收受他家乡北直隶保定府新安县知县布正贿赂白银三千两,为布正求得安州知州一官,不料事后布正炫耀自己有本事,酒后吐真言说出了贿赂求官的内情,这事恰巧被巡按北直隶的御史孙毓察得真实,于是参了郭琎一本。
王文刚刚念罢参本,在座的杨溥等人不禁大吃一惊。王文尚未说出监察情况,只见郭琎吓得额头冒汗,“扑通”一声跪在地下,连连叩首道:“陛下,臣罪该万死,不该听信犬子吹捧布正的虚假之辞,违规举荐擢拔布正当了安州知州,臣知罪了,听凭陛下处置绝无怨言。不过,臣要说明的是,犬子收受布正贿赂,臣实实在在不知情,请陛下明察!”
听郭琎说儿子郭亮收受贿赂他不知情,一旁站着的王振立时变了脸色,他张了几次口想插话,因杨溥在座,他只好忍住不出声,只把嘴巴朝地上努了努,示意正统皇帝责问郭琎。正统皇帝会意,立刻沉下脸向郭琎问道:“你儿子郭亮为布正求官,收受贿赂你能不知道么?王爱卿,你把都察院查办的情况说说看!”
“是,陛下。”王文应了一声,说道,“接到孙毓的参本后,臣于近日奉旨调查了布正和郭亮,二人均供认不讳,一个说贡了三千两银子,一个说收了三千两银子,布正行贿,郭亮受贿已经坐实,现有布正和郭亮供词以及证人证言在此,请陛下过目。不过,据臣调查郭亮受贿,郭琎大人确实不知,那郭亮受贿后即到保定府嫖娼,三千两赃银全部丢进销金炉了!”
一听王文的调查结果证实儿子受贿,老子确实不知情,郭琎连忙叩首谢罪道:“陛下,臣教子无方,辱没祖宗,败坏风气,臣知罪了。”
听罢王文说的查办情况和郭琎的谢罪言语,正统皇帝很不高兴,他板着脸对郭琎说道:“儿子收受巨额贿赂,就算你不知情,但儿子为人求官你也不知情么?”
正统皇帝这话说得郭琎无话可说,他满面羞惭地说道:“臣一时糊涂,溺爱不肖儿子铸成大错,举荐失察,举荐失察!”
“不光是举荐失察!”正统皇帝严厉地斥责道,“郭琎你避重就轻,该当何罪?诸位爱卿,大家议议,郭琎如何处置?”
说到如何处置,当然是专管纠劾百官的风宪官都察院掌院右都御史王文拿处理意见了,王文忖了忖说道:“陛下,郭琎身为吏部尚书,不思清正廉洁为国选贤,却收受贿赂,任用贪墨之徒,按《大明律》应下狱论罪,交三法司会审;其子郭亮收受贿赂,以其父之权谋私,且纨绔不端,依律当徒;布正公然行贿谋官,影响极其恶劣,依法当夺官戍边。臣以为郭琎三人应即刻押送刑部大牢,待三法司会审后依律惩处,以正朝纲。”
“臣附议。”张辅一生雄毅方严,治军整肃,最恨那些贪官污吏,见王文说罢处置意见,便立即表态赞成,“吏治腐败最是国家祸害,也最为百姓痛恨,郭琎受贿授人以官,不啻买官卖官,理应严惩,以儆效尤!”
“臣也附议。”坐在一旁的礼部尚书胡滢见正统皇帝对郭琎很不满意,料想皇上极欲树威,治臣一定会用重典,便顺着正统皇帝的意思说道,“郭大人触犯律条,依律论罪那是理所当然。”
张辅、胡滢都表态了,在座的还有内阁的杨溥、马愉、曹鼐三位大臣没有说话。正统皇帝朝他们三人望了过来,马愉为人端重简默,论事宽厚,又是宣德二年丁未科的状元,杨溥的门生,恩师不说话,他怎能先开口?曹鼐出身较晚,宣德八年,杨溥奉旨选拔庶吉士,那当科状元曹鼐和榜眼刘哲在选之列,也与杨溥有师生之谊,杨溥德高望重不表态,他怎好先发言?这么一想,马愉、曹鼐二人望了望杨溥,沉默不语。
见三人都不说话,正统皇帝急了,他对杨溥说道:“南杨阁老,您说说看,这事怎么处置好?”
“陛下容禀。”杨溥躬身拱手说道,“郭亮受贿为人求官,实在太不应该,有损吏部清誉,影响极坏,令人愤慨。郭琎平常厚重勤敏,为人称道,不想一时糊涂,晚节不保,令人惋惜。现在都察院已经查清此案,行贿受贿、买官卖官业已坐实,依律论处,整肃朝纲,理所当然,臣等也不敢徇情枉法,坏毁官纪。纵观此案,臣以为郭琎事涉三罪:一是举荐失察,仅凭儿子片面之词便滥举贪赎之徒,按《举主连坐法》应受连坐之罪;二是擢拔不公,布正本是新安县一个平庸知县,虽九年考满但并无卓异政绩,即使擢拔也只能按部就班,从正七品升为从六品,到安州当一个同知为宜,可是郭琎竟违规将布正一下子从七品超迁为从五品的安州知州,连升三级,这是典型的以权谋私,令人愤慨;三是收受贿赂,尽管郭琎对郭亮收受布正白银三千两确实不知,但官员家属子女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不正当利益,而且经郭琎利用手中权力已使他人得逞,已经构成受贿罪,郭琎难逃罪责,不容置疑。怎么处置?臣赞成王大人关于郭亮和布正的处置办法,立即下狱,交三法司会审依律惩处。至于郭琎,臣以为他儿子受贿可以认定是他收受贿赂,但毕竟郭琎确实不知情,尚有可原之处,而且事发之后认罪态度尚好,也有从轻之节。出了这案件,郭琎再在吏部为长已经不适宜了。念郭琎三十余年来勤勤恳恳忠于国事,从未犯过,今日之罪宜从轻发落,臣以为可以罢免郭琎官职,令他居家思过,到时致仕归田的好。”
杨溥这番话说得十分中肯,既严肃了纲纪,又考虑了从轻情节,合情合理,令人折服。杨溥说罢,马愉、曹鼐立即躬身拱手说道:“臣等附议,让郭琎面壁思过吧。”
“好,”听杨溥这么一说,虽然杨溥令郭琎罢官的意见,与王振事先教的将郭琎下狱的主张不合,但正统皇帝心里明白,这事只能听杨溥的,因为杨溥是托孤重臣,一生忠诚恭谨,不会有错,所以他连连点头。说完,他又对郭琎问道,“郭琎,你心服么?”
“臣心服,谢陛下宽宥之恩。”郭琎连忙磕头说道,“臣身为吏部尚书,不能清慎持正,竟然以权谋私,晚节不保,愧对陛下,愧对诸位大人,臣惶恐无地,甘愿回家思过谢罪天下。”
听郭琎说罢,正统皇帝点了点头,说道:“既是如此,那你就回家去吧!”
郭琎叩首谢恩,站了起来又向杨溥等人拱手道谢,然后主动摘下乌纱帽,低着脑袋,满面羞惭地回去了。
望着郭琎蹒跚的背影,杨溥不胜叹息。一个人一时清廉并不难,一辈子清廉可就难了。这郭琎仕宦三十余年,最后竟栽在以权谋私上,晚节不保,可惜可惜。
待郭琎离去,正统皇帝向杨溥问道:“南杨阁老,吏部可是六部之首,尚书不可或缺,您看谁可当此大任?”
“谁可当此大任?”郭琎罢官事出突然,杨溥一点心理准备都没有。他仔细思索了一会,说道,“臣举荐现任礼部侍郎王直当此大任。王直举永乐二年进士,寻改庶吉士,与曾棨、王英等二十八人同读书文渊阁,旋为翰林修撰,历事太宗、仁宗、宣宗三朝,累迁少詹事兼侍读学士,正统三年进礼部侍郎,出莅部事已有四五年,资历声望俱佳,且为人端重,不苟言笑,担任吏部尚书为国选才最是合适。”
杨溥说罢,正统皇帝又向张辅、胡滢、马愉、曹鼐、王文等人问道:“你们几位爱卿以为如何?”
王直在朝中口碑极好,众人一齐说道:“南杨阁老举荐极当,臣等附议。”
见大家都赞成王直担任吏部尚书,正统皇帝也觉得那老头学问渊博,与礼部侍郎王英齐名,人称“二王”,是一个极好的人选。想罢,正统皇帝点头说道:“好,那就擢拔王直为吏部尚书吧。”
五月十二日,麓川平叛的兵部尚书王骥和主帅蒋贵等人从云南回来了。正统皇帝派户部侍郎王质带着羊、酒到卢沟桥迎接慰劳。
第二天中午,正统皇帝在奉天门举行盛大宴会,为王骥、蒋贵等人庆功。酒宴开始前,由杨溥、张辅、胡滢等人陪同,正统皇帝在西角门召见了王骥和蒋贵——杨士奇因病未能出席。
一进西角门,王骥和蒋贵便山呼万岁,行了朝参大礼。正统皇帝赐座,还特意命内侍赐茶。
“二位爱卿辛苦了!”待王骥和蒋贵二人品茶之后,正统皇帝说道,“麓川一役,平定了思任发叛乱,安定了西南边陲二三十个州县,二位爱卿为国家立下了汗马功劳,可喜可贺!麓川那地方偏远蛮荒,打起仗来肯定十分艰苦吧?”
“的确十分艰苦。”王骥躬身拱手回道,“臣和蒋将军率领将士兵分三路进剿,托太皇太后和陛下的洪福,官军经过上江寨战役、木笼山战役、马鞍山战役,一举歼灭了叛军,安定了西南边疆。”
说罢,王骥把如何火焚上江寨、如何遣参将宫聚和副将刘聚分左右两翼缘岭而上大破木笼山、如何在马鞍山诱败大象阵等等战斗故事绘声绘色地讲了一遍,听得正统皇帝眉飞色舞,杨溥等人啧啧称奇。
待王骥讲完,正统皇帝好奇地问道:“麓川叛贼叫思任发,他的父亲叫思伦发,他的儿子叫思机发,据说其孙叫思命发,怎么他们四代名字中都同用一个‘发’字?”
“陛下有所不知,那‘发’字并不是他们的名字。”王骥笑道,“思任发本来叫思任,他所居本是麓川之地,与缅甸接境,皆在大金沙江之南,在元代的时候属平缅宣慰司。其父思伦元末乘乱占据了缅甸之地,自称滇王,那滇王号在傣语中称为‘法’,于是人称思伦法,中国内地讹为思伦发,其后思任发以滇王自居,遂儿孙名字中都有一个‘发’字,这是内地人不知其详,以讹传讹而已。”
“原来如此。”听罢王骥的解释,正统皇帝恍然大悟,“那思伦发以滇王自居,时刻都想独立为王,分疆裂土之心必然不死,这次他只身败走孟养,不会东山再起继续为患么?”
“陛下所虑极是。”一旁的平蛮将军、定西伯蒋贵回道,“思任发逃窜孟养,那里山高林密,地势险峻,实在不易擒获,他日一定会再度为患。臣与王尚书思量,若要根治思任发叛乱,除非将其擒获,但此事一时难以奏效。为今之计一是强兵固边,严阵以待,防止叛贼再次兴风作乱;二是请陛下敕谕缅甸、孟养等地宣慰司,擒拿思任发献来京师。臣等班师之前,已部署李安、宫聚、刘聚、方瑛、蒋雄等将据兵镇守金齿、麓川、孟定等地,如若思任发胆敢再次叛乱,臣等再去剿灭。”
听罢,正统皇帝向张辅、杨溥、胡滢问道:“这样安排行么?”
“行,”张辅点头道,“如果思任发再次叛乱,一定要穷追猛打,务求全歼才是。”
“对叛乱之徒一是要严打,二是要严防,不给叛贼以可乘之机。”杨溥说道,“此外还要对边民做好安抚,晓以利害,劝阻盲从。边民思安,思任发便无法兴风作浪了。”
一旁的胡滢想了想,说道:“还有一条,如果捉不到思任发,可否悬赏捉拿,谁献来思任发,即分其麓川之地给他!”
一听胡滢这话,杨溥连连摇头道:“不可!朝廷捉拿思任发,为的是平定叛乱,保靖边疆,并非硬要斩杀思氏方休,那样做毫无意义。思任发逃窜之地只有缅甸和木邦,能够擒捉思任发的也只有缅甸和木邦。如果依胡大人之议,则缅甸和木邦必将执思氏而要挟朝廷,以求共分麓川之地。朝廷不给吧,言而无信必生怨恨;给吧,而缅甸、木邦二司坐大,是减一麓川而生二麓川也,不妥!还是依前之计,一严打,二严防,三安抚的好!”
见杨溥反对分地悬赏的做法,正统皇帝连忙摇头道:“朕思量也是分地悬赏不妥,还是按南杨阁老的意见办。王爱卿和蒋爱卿回朝歇息几日,思任发不乱则罢,如若再次作乱,还是劳烦二位爱卿再次出征。”
王骥和蒋贵立即躬身拱手说道:“臣遵命!”
正在这时,只见内侍张环前来报告道:“陛下,吉时已到,礼部侍郎王大人请您起驾奉天门呢!”
正统皇帝一听,立即兴冲冲地说道:“好,众位爱卿随朕到奉天门赴宴吧!”
不一会,正统皇帝来到了奉天门,数百名文武官员早已依序就座。正统皇帝款步登上宝座,环顾了一下殿内殿外的百十桌宴席,高声说道:“诸位爱卿,兵部尚书王骥和定西伯蒋贵等将士肩负王命,不辞辛劳,远征叛贼,浴血奋战,平定了麓川、绥靖了边陲,为国立了大功,朕奉太皇太后懿旨,今日要重赏有功将士,以彰勋劳。王公公,你宣读谕旨吧!”
“是,陛下!”立在一旁的王振应了一声,上前一步,立在丹阶边,捧着圣旨,尖着嗓子大声宣读道,“……兹加封兵部尚书王骥为推诚宣力武臣、特荣禄大夫、上柱国、靖远伯,岁禄一千二百石,世袭指挥同知,赐貂蝉冠、玉带;加封平西伯蒋贵为平西侯,增禄至一千五百石;从征军将李安、刘聚、宫聚、冉保、马让、方瑛、柳英、蒋雄等各升一秩;兵部右侍郎徐晞进位左侍郎;从征少卿李贲,郎中侯琎、杨宁,皆擢侍郎;主事蒋琳晋员外郎。其他将士皆升赏有加。云南沐昂此次有功,着即恢复右都督原职。钦此!”
王振宣读完毕,王骥、蒋贵等人一齐谢恩。文武百官纷纷道贺,大殿上喜气洋洋,一片欢腾,那人群中更是喜坏了刚刚进位为左侍郎的徐晞。
这天晚上,兵部左侍郎徐晞顾不得旅途劳累,揣着礼物,连夜到朝阳门南侧不远的王府拜谒王振。
王振正在喝茶,听说府外有兵部左侍郎徐晞求见,他漫不经心地吩咐道:“叫他进来吧!”
少顷,徐晞来到了大堂,见王振坐在中堂上津津有味地品茶,他连忙紧走几步,双膝一跪伏地便拜,口里说道:“下官徐晞拜见王公公!”
“你是哪个徐晞?”王振把玩着那精制的景德镇茶盅的盖碗,头也没抬地问道,“本公公好像不认识你?”
那徐晞本是个心术不正的奸邪小人,当年阿台朵儿只伯寇犯庄浪,都指挥江源战死,明明是当时身为兵部右侍郎他的责任,他却一股脑儿全推到了刚刚选兵甘州的蒋贵身上。就是这次麓川平叛,他徐晞不过是一名协助沐昂督运粮草的角色而已,却极力钻营企图谋取要职,所以他见了王振,不顾兵部左侍郎的堂堂身份,竟然卑躬屈膝地跪拜王振,极尽谄媚之态,令人不齿。
见王振不在乎,徐晞心里明白,连忙跪行几步,从衣袍中掏出一个一尺来长的紫檀木匣,揭开匣盖双手托起献了上去,口里说道:“些许薄礼不成敬意,望公公笑纳。”
内侍长随毛丛接过来呈到王振桌上。王振瞟了一眼,忽然眼前一亮,只见那紫檀木匣内放着一座高约尺许的象牙雕佛像,那女菩萨雕刻精致,通体晶莹,雍容华贵,仪态万方,真是一件稀世珍宝!
王振平常好佛,看见这件宝物,他心里一喜,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他放下茶杯,抬起头来含笑问道:“你就是今日朝会上嘉奖的平麓川大臣兵部左侍郎徐晞徐大人么?”
徐晞连忙答道:“公公好眼力,正是下官。”
“起来,起来。”王振不紧不慢地说道,“这象雕菩萨是从哪里弄来的?”
“下官仰慕公公已久,特地登门看望您。”徐晞从地上爬了起来,王振没说看座,他也不好坐下,只好站着低头笑眯眯地说道,“下官这次在麓川平叛,到缅甸宣慰司宣慰使那里偶然发现了这件宝像,听宣慰使说,那是从西洋榜葛剌弄来的呢。下官想您平日虔诚信佛,便把它买来孝敬您,还不知您喜欢不喜欢呢!”
“还算可以,”现在的王振可不是几年前的王少监了,那年教场阅武,王振矫旨骤升纪广,得了一百两银子,便大喜不已;去年矫拔王佑,得了一千两银子,更是喜之不胜。可是,今日见着这尊象牙雕像——这雕像少说也值个四五千两银子——他却觉得并不稀罕了。他从匣中拿出那尊佛像仔细端详了好一会,皱着眉头问道:“这尊菩萨我好像在哪儿见过,怎么这么眼熟啊?”
站在一旁的内侍长随毛丛凑上来看了看,笑道:“我的爷,您怎么忘了,这不是前几年奴才随您到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看到的那尊最大卢舍那大佛的像么?”
“是了,是了!”王振一听,立刻想了起来,“那尊佛像传说是唐高宗命人按照武则天的容貌雕刻而成,这尊佛像不过是整体缩小了,模样儿还真和卢舍那大佛一模一样。如此说来,这菩萨就是武则天的真容了,宝像,宝像!”
“就是武则天的模样儿!”徐晞见王振爱不释手,便凑上去指着那菩萨说道,“您看她面相丰满圆润,眉若新月,双目含蓄,嘴角内陷,略作微笑,神态庄严又不失慈祥。除了武则天,谁还有这么漂亮?”
看着这尊佛像,王振高兴了。他对站在一旁的内侍长随王谋吩咐道:“给徐大人看座,奉茶!”
待徐晞坐下,接了茶杯,王振问道:“徐大人有事么?”
“启禀王公公,下官也没什么大事,只是想请公公帮个忙。”说到这里,徐晞看了看站在一旁的内侍毛丛和王谋,缄口不言了。
“没事,没事。”见徐晞欲言又止,王振笑道,“他们都是我的贴身内侍,有事但说无妨!”
“那下官就放肆了。”徐晞放下心来,拱手说道,“现在兵部尚书王骥大人不是已经加封为靖远伯了么?那么王大人就不能再任现官,尚书一职就出缺了。下官想请您在皇上面前美言几句,不知王公公肯不肯帮忙?”
“原来徐大人是想当兵部尚书,那可是个权势熏天的要职呢。”听罢徐晞的要求,王振忖了忖,面有难色地摇头说道,“朝廷规定,知府以上官员出缺,应由三品以上京官保举,这兵部尚书可是正二品,那要由内阁大臣们荐举才行呢。徐大人求别的事倒好说,提这么个要求,本公公恐怕办不到呢。”
见王振不肯帮忙,徐晞十分乖觉,连忙改口道:“没关系,没关系,下官也只是这么说说。这次麓川平叛,下官在木邦宣慰司还得到了一件东西,下官孤陋寡闻不知叫什么名字,有何用处,特带来府上,请王公公帮下官鉴定鉴定,您见多识广,一定知道那东西的来历,不知公公答不答应?”
听说又是一个宝物,王振眼睛一亮,睁大双眼问道:“什么东西?拿来瞧瞧!”
徐晞连忙起来对府外喊道;“徐甲、徐二,把那宝物抬上来吧!”
只听外面有人应了一声,不一会,徐晞的两个家丁抬着一个一二尺宽、七八尺长的大木箱进来了。
打开木箱,只见那箱子里放着一株千枝百桠、桃色鲜艳的东西。王振看了又看,脸上洋溢着笑容,说道:“这东西叫桃红珊瑚树,产自西洋海中,一般的只有一二尺来高,你这株高达六七尺,真是件稀罕宝物,哪里弄来的?”
“听木邦宣慰使说,这东西是从西洋天方国弄来的。”徐晞媚笑道,“您看下官这没见过世面的连这桃红珊瑚树的名字都不知道,真是委屈了这宝物!要是公公不嫌弃,下官就送给您了,望乞笑纳。”
“那我就不客气了。”王振端起茶杯呷了一口,对毛丛、王谋二人说道,“把这株珊瑚树抬进去吧。”
毛丛、王谋二人将宝物抬进去了,王振抬头对徐晞笑道:“徐大人刚才所求兵部尚书一事,可急不得,待本公公从容向皇上进言,为你求求吧。”
一听王振答应为他谋官,徐晞先是一喜,但接着听王振说要“从容向皇上进言”,徐晞又不禁急了。这兵部尚书的职位只有一个,能够担任此职的人可不少,比如仅说兵部,现在兵部侍郎邝埜就署理着兵部的日常事务,排位就排在他徐晞的前面,要说接任兵部尚书,那首先应该是邝埜,怎么也轮不到他徐晞。夜长梦多,假使南杨阁老动议由邝埜接任兵部尚书,那不就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了么?不行,这事儿得趁热打铁!想到这里,徐晞又从怀中掏出一包东西,打开来捧给王振,谄笑着说道:“王公公,这点好东西,是下官特意谋来孝敬您的。”
王振接过来看了看,闻了闻,原来这是一支棕红色长约四五寸的鹿角,他问道:“这不是鹿茸么?你是哪里弄来的?”
“这可不是普通的鹿茸。”徐晞神秘地笑道,“这是产自湖广荆州府石首县的麋鹿制成的麋茸。这麋茸是用麋鹿初生的麋角制成的。《本草纲目》载‘麋茸功力胜茸,角煮胶亦胜白胶’,乃强壮激性之药,功能补髓生精,红颜乌发,尤其是能重生根本,紧挺阳道,那功效神奇得很,据说前代有几个内宫公公服用之后,张本复元,还生了儿子呢!”
一听徐晞这话,王振不禁精神大振。为了图个荣华富贵,十岁时他不惜自残除了根本随姑姑王杏进了皇宫当了阉人,那时只想有个安逸,倒未曾想到其他,而现在自己已经一步一步走向成功,距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仅差一步之遥,而且家室财富已非昔日可比,富贵思**乐,那男女之情和传宗接代的欲望便日盛一日地强烈起来,可惜自己成了个无根废人,无缘**,无法生儿育女,每想及此,便懊恼不已。今日忽听徐晞说眼前这东西便是“只见经传,难见实物”的麋茸,立刻兴奋起来。不过,此时他也特恨杨溥,杨溥是石首人,但从来没听他说起过他的家乡有这样的魔宝!想罢,王振喜笑颜开,说道:“徐大人会办事,这兵部尚书非你莫属!这样吧,本公公立即去向皇上说说,你回去静候佳音吧!”
“谢公公,倘若事情成功,下官定当厚报!”徐晞大喜不已,告辞出来,乐颠颠地回去了。
第二天早朝,王振宣布了正统皇帝的一条谕旨:根据本朝兵部尚书由文官担任的规定,原兵部尚书王骥已加封为武官靖远伯,已不适宜再任兵部,着即免除部事。鉴于兵部侍郎徐晞麓川平叛有功,特擢拔为兵部尚书。钦此。
此事一宣布,立刻引起了满朝文武的议论,照往日的惯例,像擢拔尚书这正二品的六部九卿,从仁宗、宣宗皇帝以来一直是皇上与内阁大臣面议然后再下达谕旨,就是正统皇帝登基以来的这几年,擢拔三品以上大臣,也是由张太皇太后和正统皇帝与内阁三杨、张辅、胡滢等五名顾命大臣面议后确定的,怎么这次擢拔徐晞,内阁大臣与张辅、胡滢等人竟事先丝毫不知,这是怎么了?杨溥心里明白,这肯定又是王振从中捣鬼,怂恿正统皇帝下的谕旨,这皇上怎么这么听信王振,把握不住自己呢?擢拔兵部尚书,理应先由现已署理部务五年的兵部侍郎邝埜担任,那徐晞人品不端,功劳不大,竟然越过邝埜成了兵部尚书,怎么服人?但是,这谕旨已经宣布了,还能怎么着?怎不能当庭抗旨指责皇帝擢拔不公吧?何况擢拔徐晞的理由一是徐晞先邝埜一年任兵部右侍郎,二是麓川平叛有功,那理由还冠冕堂皇呢。想到这里,杨溥只好不出声了。
就这样,徐晞靠着依附王振,爬到了兵部尚书的高位上。虽然徐晞缺德少才,兵部尚书只当了三年便被免职致仕,正统十年九月杨溥还是秉公用贤举荐邝埜当了兵部尚书,可是徐晞和前王佑二人,首辟趋媚之路,百计效勤,极尽谄媚之态,为朝廷上下开了个极其恶劣的行贿买官的先例!
正统七年的五月十九日,在张太皇太后的主持下,大明朝廷为正统皇帝举行了大婚典礼,虚十六岁的正统皇帝朱祈镇与刚封为皇后的海州美女钱氏成婚了。按照年龄,正统皇帝本可以再待个一二年成婚也不迟,但张太皇太后日渐消瘦,病疾渐重,她担心自己来日无多,急于想在自己有生之年把孙儿的大婚办了,就是朝夕西归,也好瞑目远行,于是她为孙儿从各地选美送来的女孩中选中了南直隶淮安府海州的钱氏为皇后,择吉为正统皇帝大婚。
正统皇帝大婚不到二十天,年已七十的工部尚书吴中病逝了。这吴中从永乐五年正月任工部尚书至今已有三十六年,其中八年任刑部尚书,又复任工部尚书,先后在工部二十八年。吴中死后的一天,朝廷的诰敕来了。中使宣读毕,其妻叫来儿子问道:“这诰词是皇上亲自拟写的呢,还是翰林代草的呢?”
其子回答道:“听宣旨的公公说,诰敕是内阁大臣杨溥写的呢。”
其妻叹道:“南杨阁老果不虚妄,秉笔直书,吴中一篇诰文,只说他平生为人,何尝有‘清廉’二字!”
张太皇太后的担心果然不是多余,正统皇帝大婚五个月后的正统七年十月,她的病突然沉重了!
十月十八日这天一早,张太皇太后挣扎着命内侍太监传旨,请皇太后孙氏、正统皇帝、皇后钱氏到清宁宫,召内阁大臣杨士奇、杨溥、马愉、曹鼐和顾命大臣张辅、胡滢等人速赴禁内。听说张太皇太后病危,杨士奇也扶病来了。
张太皇太后躺在病榻上,脸色蜡黄,两眼浮肿,只有出气没有进气,已是临崩状态。众人一见,不禁热泪滚滚而下。过了好一会,张太皇太后才悠悠醒来。她极力睁开双眼,缓缓地巡视了一遍床前的众人,眼光最后落在杨士奇的身上,有气无力地问道;“朝廷尚有何大事未办么?”
一听张太皇太后这话,杨士奇明白这是她的临终遗言了。杨士奇对杨溥看了看,只见杨溥点了点头,意思是叫杨士奇抓紧时间奏事,不要错过机会。杨士奇会意,即忙上前一步喘着气,拱手说道:“臣等尚有三事未办,恭请太皇太后懿旨。一是建文皇帝虽然已灭,但曾经临御四年,当命史官修其一朝实录,仍用建文年号。”
听到这里,张太皇太后挣扎着拼力说道:“建文时的历日已经革除,改称洪武年号,能复用么?”
“能用,能用。”杨士奇连忙回答道,“历日行于一时,实录万世信史,岂可蒙洪武之年以混淆历史真实?”
听杨士奇这么一说,张太皇太后沉默不语了。她思索片刻,点了点头,说道:“这事就照你们说的办,那第二件呢?”
“第二件事是方孝孺之书。”杨士奇赶紧说道:“建文时方孝孺已诛,太宗皇帝曾经下诏,严禁其著作诗文刊行,说如有人收藏其片言只字者论死,臣等请求解除禁令,其文辞不关系国事者,听令存之。”
听罢此事,张太皇太后默然未答,似乎已经无力说话,默认了。
“第三件事……”杨士奇的第三件事尚未说出,只见张太皇太后眼一闭,头一歪,溘然长逝了!
见张太皇太后与世长辞,杨士奇、杨溥、张辅、胡滢等人赶忙跪地叩首,俯伏恭送。一旁的孙太后、正统皇帝、钱皇后一齐扑向前来大放悲声。张太皇太后平日对宫中内侍、宫女宽厚慈善,内侍、宫女都十分敬爱,今日永诀,宫内的中官宫女们都哀哀地哭泣起来,顷刻之间,整个清宁宫一片悲戚,人们沉浸在悲痛之中。不过,只有王振一人狂喜不已。这下好了,最为畏惧的最后一人已去,今后我王振就是唯我独尊了!
张太皇太后驾崩后,内阁大臣杨士奇、杨溥同礼部尚书胡滢会商,定下大行太皇太后丧礼:自次日起辍朝七日,不鸣钟鼓,驾崩后越三日的二十二日正统皇帝成服,成服三日后皇帝听政视事,诸王以下百官素服哭临皆如仪制,素服二十七日而除,军民男女素服十三日,诸王勿会葬,外官勿进香,臣民勿禁音乐嫁娶,十二月葬献陵。整个外朝内宫都为大行太皇太后的丧礼忙碌起来。
大行太皇太后驾崩后的第七天,也就是辍朝的最后一天晚上,正统皇帝带着王振来到皇宫东北部的仁寿宫,去拜见太后孙玉儿。虽说这朱祈镇已经做了近八年的皇帝,但从未单独决定过国家大事,每次都是内阁三杨草拟阁票,由张太皇太后亲自审定后交正统皇帝当庭宣读的,可以说这八年来他依赖的是张太皇太后,从来没有亲过政。现在,张太皇太后大行了,他失去了依靠,一时没了主心骨,想到明日要亲政视朝了,不免心怵胆怯,他要到母后那儿去讨教讨教,壮胆雄心呢。
孙玉儿太后自幼由张太皇太后抚养成人,又得太皇太后恩惠,得为宣宗贵妃,所以她平日以生身母亲一样孝敬太皇太后,再加上她秉性谨慎,这几年张太皇太后幕后主持国政,她一直谨守宫规,安享荣华,从不过问政事,很少露面,是宫中有名的安分守己之人。现在,太皇太后虽然大行了,偌大的皇宫就算她是最大人物了,但她不想干预朝政,她陶醉于已得的荣华富贵,不愿劳心费神了。
见正统皇帝夤夜来此,孙太后不禁疑惑地问道:“皇上有事么?”
正统皇帝上前一步行礼请安,说道:“皇儿明日就要上朝亲政了,有些事儿拿不准,特来向母后请教呢。”
孙太后笑道:“皇上已经大婚了,正该早日亲政,乾纲独断才是,有哪些事儿拿不准,说来听听。”
“是,母后。”朱祈镇望着母亲,说道,“国家大事以前都是由内阁三杨票拟,再由皇祖母审定,然后由皇儿当庭宣布。杨荣殁后由杨士奇、杨溥提出意见,现在杨士奇疾病缠身,养疾在家,内阁政务处理均由杨溥主持,他们对国家大事提出的处置方案,现在没了皇祖母,皇儿该怎么办才是呢?”
“这事好办。”孙太后一听,笑道,“大行太皇太后在生时经常向哀家提起,说内阁三杨忠心耿耿,不愧为皇帝股肱大臣,大行太皇太后临终时还留有遗诏,勉励二杨佐帝惇行仁政,语甚谆笃,对二杨十分信赖。这七八年来,二杨是谨守臣德,勤劳国事,并无丝毫越分弄权之失,满朝文武有目共睹。哀家看皇上大可放心,国事依靠二杨就行!”
“那是当然。”正统皇帝点头道,“这些年三杨柄政,劳苦功高,但并无震主之嫌,这点皇儿可以做证。但杨荣已经殁了,看样子杨士奇也不久人世,那又该如何呢?”
“杨士奇殁了,就依靠杨溥!”孙太后果断地说道,“杨溥在朝为官数十年,入阁一二十年,人品官德值得信赖,这是大行太皇太后的遗言,皇上不必犹疑。至于杨溥身后又该如何,哀家想那杨溥不会不虑事长远,为国储才,现在内阁的好几位年轻人不是都由杨溥带着么?皇上放心好了。”
说到这里,孙太后对站在一旁的王振一指,笑道:“万一遇到难题,皇上身边还有这位足智多谋的先生呢。”
说到王振,正统皇帝也不禁笑了起来,连连点头道:“对对对,还有这位王公公呢!”
“陛下,您叫王公公,奴才觉得好生分呢。”一旁的王振暗藏心计,见眼前这种情况,他一边苦着脸,一边抓住时机说话了,“陛下自降生的那一刻起,奴才就一直服侍陛下,襁褓之中是奴才抱着您,孩提时候是奴才背着您,启蒙年代是奴才教着您,读书时期是奴才伴着您。您一口一个王公公,奴才听着心寒呢!”
听王振这么一诉苦,正统皇帝还真的动了感情。他想了想,不解地问道:“不叫你王公公,那叫啥呢?”
孙太后当然明白王振的用意,他是想借皇帝之口抬高自己的地位。不过,母子俩能有今天的荣华富贵,还真是得亏这个王振,何况还不能把他怎么样,他可是掌握着本朝天大的机密呢!想到这里,孙太后微笑着说道:“皇上自小就在王公公的教导之下,那就叫先生吧。”
“好,就叫先生。”正统皇帝点头答应道,“先生,朕明日上朝亲政,你说说看,朕该怎么办?”
一听正统皇帝果真叫他先生,王振不由心下大喜——虽说正统皇帝小时候启蒙读书哪会儿也称过王振为先生,但那是偶尔呼之,不足为尊,现在可不同了,这“先生”成了皇上对自己的正式称呼,那是何等的荣耀——他忖了忖,说道:“上朝的礼仪,陛下均已娴熟,不必担心;国家大事自有杨溥他们料理,也不必担心。现在要紧的还是如何治理文武大臣,防止文武大臣欺蒙陛下。”
正统皇帝虽然宠信王振,但毕竟已是十五六岁的青年,多少有了一些主见,听了王振这话,他惊疑地问道:“现在满朝文武大臣不都是忠心耿耿为国效劳么,为什么还要防备他们?”
“别看他们表面服服帖帖,骨子里还不知是怎么想的呢。”王振阴森森地说道,“陛下年轻,别让他们给蒙蔽了。依奴才看,还是三句话:一是重典治臣,二是派中官监督,三是撤换一批大臣。尤其是像杨士奇、杨溥、张辅、胡滢那些年老昏聩的老臣,动不动就是‘礼制’、‘祖训’,让陛下处处掣肘,什么事也办不成,早就该让他们致仕赋闲去,把朝中内阁和六部九卿都换上陛下的人,那事情就好办了!”
“不行!”好在孙太后也不是糊涂人,她明白王振这家伙工于心计,野心大得很,虽然他已经宫了成了废人,做不成皇帝,但他想做个幕后操手,代替皇上发号施令,做个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人。什么全部换上皇上的人?还不是全部换上他王振的人么?不能上当,必须保住皇上,保住皇上就是保住自己,照王振的话把杨士奇、杨溥、张辅、胡滢他们都撤换了,皇上依靠谁去治理国家?他王振能耐再大,也不过是一个内宦,总不能到内阁去处理朝政吧?想到这里,孙太后连连摇头道:“杨士奇、杨溥、张辅和胡滢都是先皇托孤重臣,且久经考验,忠心耿耿,正是皇上股肱,不可猜疑,还要依靠才是。至于治臣用重典,监督用中官倒是可行,皇上你看如何?”
“母后说得是,皇儿记下了。”正统皇帝还算是宅心仁厚,听孙太后这么一说,连忙点头道,“先生也不必说了,朕今后小心就是。”
见孙太后和正统皇帝都说要依靠杨士奇、杨溥等几位老臣,王振也不再坚持。他知道二杨在太后和皇帝心目中的地位不可动摇,一时难以撼动,好在他们都已到了古稀之年,时日无多,伺机而行吧!
第二天,正统皇帝在奉天门上朝,正式亲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