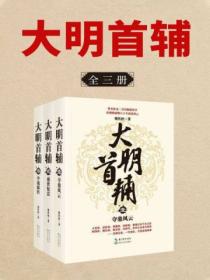第二十回 兀良哈抢掠刺军情 喜峰口奇袭平贼寇
宣德三年八月十五日,宣德皇帝命太监袁琦急召三杨、金幼孜等紧急议事,等杨士奇、杨荣、杨溥和金幼孜急急忙忙赶到西角门的时候,张辅、张本、蹇义和夏原吉等人早已到了。
“张爱卿,你把情况向大家说说。”一见几位主要大臣到齐了,宣德皇帝向兵部尚书张本说道,“你们兵部是什么主张也一并讲讲。”
“是,陛下。”张本答应一声便说了起来,“今日早间接到开平卫报告,说兀良哈那里的朵颜、福余、泰宁三卫头目率万余众南犯,大肆抢掠我永平府边民,观其势将有继续南寇之意,特向朝廷告急。臣兵部众人商议,认为这是兀良哈朵颜三卫人众,因冬天来临,无以为生,特南下抢掠,并无攻城略地之意,不过是抢些粮食、布匹、草料以备冬需而已,不必大惊小怪,只是紧守边塞即可。”
“此议不妥!”一听张本主张紧守边关,任由兀良哈抢劫,张辅就火了,他立即反驳道,“兀良哈人万余南下抢劫边民,谁能保证他们不攻城略地?即使他们不以占地为目的,他们大肆抢劫边民,我们听之任之,那边境尚有宁日么?陛下,臣主张即刻发兵征讨,免其势张难制!”
“这事还是慎重点的好。”夏原吉老气横秋,他望了望宣德皇帝慢慢地说道,“发兵征讨说是容易,但做起来却难。兀良哈来犯人众万余,我朝发兵少说也得三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三万人马出征,得耗费多少粮草?恐怕至少也得七八十万,甚至上百万斤!现在虽说国库尚足,但转运起来也是困难,不可小觑。陛下,臣看还是派人安抚吧。”
“臣觉得夏大人主张安抚较为妥当。”蹇义点头附和着。在座的几位大臣中,他年纪最大,今年已经六十六岁了。他从燕王即位起就任吏部尚书,历时已经二十七年,如今他只想过个安逸日子,不想再有什么大的动作了,现在见夏原吉主张安抚,他便随声附和。看了看宣德皇帝没有作声,蹇义便接着说道,“洪熙元年,仁宗皇帝许朵颜卫头目哈剌哈孙、泰宁卫头目脱火赤和福余卫头目安出自新,宽宥其阴附鞑靼之罪,还分别授以都指挥佥事之职,至今已有四年。这次三卫头目带人南犯是不是嫌职久未升,有要挟朝廷擢职授官的企图?如果是这样的话,臣主张安抚时把他们都晋升一级为都指挥同知,由正四品擢升为从三品,或许能让他们安定几年。”
“下策,下下策!”听了蹇义和夏原吉的主张,坐在一旁的杨荣不禁激愤起来。他是内阁中负责军伍边关之事的大臣,对边塞的情况最为了解。蹇义和夏原吉都是五朝老臣,杨荣不留丝毫情面,头一扬,慨然说道,“朵颜三卫自归顺我朝以来,先后三次叛附鞑靼阿鲁台,反复无常,实在可恼!而且他们贪得无厌,岂是一次两次安抚,赏给粮钞物资,擢升官职爵位所能安定的么?陛下,此事无须犹疑,发兵征讨方是上策!”
在座参加议事的七位大臣,已有张本、张辅、夏原吉、蹇义和杨荣五人先后发表了自己的主张,只有杨士奇和杨溥二人没有说话。杨士奇正琢磨着如何是好的时候,只见宣德皇帝把目光投了过来,探询地问道:“西杨爱卿,你认为征讨的好,还是安抚的好?”
“臣以为此事还须从长计议。”杨士奇不说也不行了,他沉吟了一下,谨慎地说道,“据开平卫的报告,只说朵颜三卫头目哈剌哈孙等率众抢掠我永平府边民,至于是否继续南犯,尚不得而知。如果在这等情况之下,我即发兵征讨,似乎有擅开边衅之忧,不可不慎。陛下,臣觉得是否再等一等看一看再说,如果朵颜卫确实南犯攻我城池略我土地,我再发兵不迟。”
杨士奇的这番话不说倒也罢了,一说出来,立时惹起了宣德皇帝的一丝不快。这模棱两可的话说了不是等于没说么?朵颜三卫已经骚扰到了永平府,打到了山海关,还能再等一等看一看么?但杨士奇毕竟是五朝老臣,当众也不好驳他面子。宣德皇帝沉住气,对杨士奇的话含糊地“嗯”了一声,转而向杨溥问道:“南杨爱卿,说说你的看法?”
“臣以为尚须弄清朵颜三卫南犯的原因,方好抉择。”见宣德皇帝点名,杨溥习惯地搓了搓手说道,“比如医生看病,需要先望闻问切弄清是何疾病,方能对症下药,如此自然药到病除。”
“这个比方恰当。”宣德皇帝不禁笑了起来,“那你就说说,这朵颜三卫害的是什么病?”
“臣看朵颜三卫害的是伤寒症,时冷时热。”杨溥回答道,“此次朵颜三卫南犯,臣看事出有因。元亡之时,朵颜、泰宁、福余人众远蹿东北,居于黑龙江,后来耐不住北方苦寒逐渐南下,至永乐初设置三卫,其人众基本游牧于我开平卫、大宁卫一带,其地已与我永平府相邻,距北京也不甚远,按理说生活所需粮草、布帛已与内地相差无几,不存在因饥寒所迫而南下抢掠之事,况且现今还是八月。因此,臣以为朵颜三卫此次南犯,抢掠财物不是主要原因。”
此言一出,宣德皇帝和在座的几位大臣都感觉新奇,大家睁大眼睛望着杨溥,等待下文。宣德皇帝欠身问道:“那他们南犯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杨溥不假思索地说道:“臣看他们南犯的主要原因是刺探军情。”
“刺探军情?”杨溥这话说得满座皆惊,宣德皇帝连忙说道,“爱卿请道其详。”
杨溥继续说道:“自从永乐二十二年太宗皇帝第五次北征,将鞑靼阿鲁台驱赶至答蘭纳木儿河之后,阿鲁台部就日见衰弱,而西部的瓦剌脱欢乘机掩杀,把阿鲁台驱赶到母纳山、察罕脑剌之间,从而侵占了阿鲁台的大部土地,朵颜三卫见势不妙,便暗中依附于瓦剌脱欢。瓦剌脱欢势力渐强,时刻窥伺中原,无日不思南侵,甘肃、宁夏、大同等西部要塞都有我重兵镇守,且距北京较远,瓦剌从西部南侵,不易得手。而朵颜三卫靠近北京,正是大举南犯的绝好位置,只要突破喜峰口等处要塞,仅四五百里路,三四日便可攻到北京。所以臣料想朵颜三卫此次南犯的主要原因,定是受瓦剌脱欢的指使,前来刺探军情,试探我边塞有无准备,他们企图趁边塞无备,大举南侵呢。”
“有道理。”宣德皇帝一听,立刻对杨溥的说法进行了肯定。他继续问道:“如此说来,爱卿以为如何处置方好?”
“御驾巡边。”杨溥脱口而出,“朵颜三卫此次南犯既是前来刺探虚实,那就无须发兵征讨。陛下只要带上数千御林军,亲自出喜峰口将边塞巡视一番,如果朵颜三卫闻风而退便罢,如果胆敢拒敌,陛下则挥轻骑突袭,打他个措手不及,定能将朵颜三卫降服。但要朵颜三卫长久不叛,必须采用武服恩定的方针,即恩威并施,武力降服,恩抚安定。”
“好一个武服恩定,说得好。”听了杨溥的主张,宣德皇帝不禁击掌叫起好来。他环视了一下在座的几位大臣,说道,“朕即位已经三年,主要精力都放在处理重大朝政上,还一直未曾巡视边关。目前守成大业诸事已有条理,正要去北方诸卫巡视巡视,现在朵颜三卫南犯,朕正要去会会他们,让他们知道朕和皇祖爷爷一样,不仅勤于文治,而且喜欢武备呢!”
说到这里,宣德皇帝把话打住了,他看了看几位大臣,等待着大家的反应。
宣德皇帝的观点已经再明确不过了,他赞成杨溥的主张,御驾巡边。一旁的内阁首辅杨士奇立刻明白,这宣德皇帝年轻气盛,决意北行了。这次不同于交阯用兵。交阯用兵那是路途遥远,旷日持久,年轻皇帝厌战,那时自己和杨荣二人一反对,宣德皇帝便采纳了,结果丢弃了交阯,遭到国人的普遍反对,宣德皇帝后来也颇有悔意。但是这朵颜三卫不同,他们距离北京仅有四五百里路,如果兀良哈作乱,他们一迈腿便打到了北京,所以宣德皇帝也不敢大意,此次巡边,看来皇上是铁了心了。想到这里,杨士奇躬身说道:“陛下,刚才南杨大人分析得颇有见地,臣以为就目前形势而论,也只有御驾巡边的好。”
见宣德皇帝态度已经明朗,主张安抚的张本、蹇义和夏原吉也就不再坚持,他们一齐说道:“臣等唯圣命是从。”
张辅和杨荣当然喜之不胜,二人朗声说道:“陛下,您就下旨吧。”
“好,御驾北巡,这事就这么定了。”见几位大臣意见已经统一,宣德皇帝决断了,“朕决定即日开始准备,发京军三大营五千将士随朕北行巡边,由蓟州经遵化出喜峰口。西杨、东杨、南杨、蹇、夏五位爱卿扈驾随行,英国公张辅、阳武侯薛禄、兵部尚书张本、驸马都尉宋琥、都指挥同知任礼各领前后左右中将兵前行,锦衣卫指挥使钟法保随行护驾,朝中就请金爱卿留守。今日晚间的中秋赏月取消,大家从速准备,不日出征吧!”
“是,陛下!”众人答应一声匆匆地走了。
宣德三年八月二十八日,宣德皇帝由杨士奇、杨荣、杨溥等大臣为扈驾,率领精兵五千,出北京城,经通州,过三河,越蓟州,九月二日黄昏时分来到遵化县西南四十五里的石门驿,前方飞马来报,朵颜三卫人马已经过了会州,正在慢慢地向宽河掠来。听说朵颜人马已过会州,宣德皇帝并不着急,命令部队依然原速前进,八月五日晚间到达了遵化以北一百余里的喜峰口。部队安营扎寨,锦衣卫将士布好行幄,司礼监太监金英、御用监太监袁琦、御马监太监王敏等人服侍宣德皇帝用过晚膳,便洗漱完毕,遵命将几位扈驾大臣请来,与宣德皇帝边品茶边商议军情。
宣德皇帝正待说话,忽见袁琦进来奏道:“陛下,喜峰口参将、指挥同知费广前来,有紧急军情奏报,现在行幄外候旨。”
听说费广前来奏报紧急军情,宣德皇帝手一挥说道:“叫他进来吧。”
“启奏陛下,朵颜三卫头目哈剌哈孙等已逼近宽城。”费广一进来便跪下奏道,“臣刚刚接到宽城守备指挥佥事康茂紧急军报,说朵颜三卫军队已经在宽河城北不到二十里的龙须门扎营,有消息说他们准备明日攻城。康茂说宽城守军仅有两个千户所二千四百余人,实难抵挡朵颜,恳请陛下速速发兵救援!”
费广说完,宣德皇帝沉思片刻问道:“朵颜究竟来了多少人马?何人率军?”
“据探马报告,朵颜三卫此次军丁不少于一万八千人。”费广回答道,“带队头目是朵颜卫的哈剌哈孙,泰宁卫的头目脱火赤和福余卫的头目安出也在军中。不过他们行军速度不快,似乎十分谨慎。”
听罢费广的报告,兵部尚书张本顿时紧张起来,他着急地说道:“陛下,朵颜人马将近两万,而我方仅有五千,敌众我寡,力量悬殊,一旦交战,胜算不大,还是速速增兵的好!”
见张本提出增兵,杨士奇、蹇义和夏原吉也一齐说道:“陛下,再增兵三万,双倍于敌,就有决胜把握了。”
宣德皇帝看了看张辅、杨荣和杨溥三人,见张辅和杨荣凝神静思不说话,显然他们二人也多少有些担心兵少,唯有杨溥正望着自己微微摇头。宣德皇帝略一沉吟,便对杨溥问道:“南杨爱卿意下如何?”
“现在的情势是一急一难。”杨溥搓了搓手回答道,“这一急是兵临城下,宽河告警,战机难得,稍纵即逝,克敌制胜,刻不容缓;这一难是喜峰口地处燕山山脉红石砬子山麓,山路崎岖,险峻难行,仅容单骑,若待诸军从他路并进,恐宽城已陷朵颜了!”
“南杨爱卿所言喜峰口地势十分准确。”宣德皇帝一听杨溥的说法十分惊讶,“朕年轻时随皇祖爷爷巡边,曾数次出过喜峰口,那里的道路确实险狭难行。朕不明白,南杨爱卿未曾到过此地,你是怎么知道此地地形的?”
“启奏陛下,臣是刚刚才知道的。”杨溥笑着说道,“不瞒陛下,臣有个习惯,走到生疏的地方总是喜欢打听地形地貌和风土人情,这次行军巡边,臣更是留心山水道路,以备急需。昨日在遵化东北三屯营宿夜时,臣就找当地土人详细询问了前方地形道路,所以才知道喜峰口不适宜大部队行军,仅容单骑通过。”
“原来如此。”听到这里,杨荣不禁笑道,“难怪昨日一宿营,南杨大人就来找我要地图,原来是要摸清前方地形道路呢。可惜你是一位文官,如果是一名武将,那定是一名会打仗的常胜将军了。”
“这还不是向你东杨大人学的。”杨溥也笑道,“谁不知你东杨大人永乐五年奉命往甘肃经画军务,所过之地览山川形势,察军民,阅城堡,竟成了我朝熟晓边塞军务的专家呢!我也想知己知彼,百战不殆,行军途中,学些军事,有朝一日陛下命我经画边塞的时候,也好备用。”
“有你们这些细心的股肱大臣,朕的边务就放心了。”宣德皇帝也笑了起来,“不过闲话少说,南杨爱卿还是继续说说你的看法吧。”
“是,陛下。”杨溥应了一声,继续说道,“鉴如上述一急一险的情况,臣以为不宜用大部队齐头并进,最好是奇兵奔袭,可以选取精兵三千,连夜突出喜峰口,拂晓时赶到宽城,一鼓作气奔袭龙须门,打他个措手不及,定可大获全胜。”
“此计甚妙。”听罢杨溥主张,宣德皇帝心下大喜,这正合他此刻豪气干云意欲大显武备的心情。他再也不征求其他大臣的意见,断然吩咐道,“这事就这么定了。兵在精不在多,英国公张辅与阳武侯薛禄、都指挥同知任礼速到军营挑选精兵三千,带上神机铳,再到喜峰口兵塞挑选一些良马,一兵两马,各带十日粮食,人噤声,马衔枚,连夜奔袭朵颜营寨,务求全胜!兵部尚书张本与喜峰口参将费广率领喜峰口兵塞人马随后跟进。中官袁琦随前队先进,到宽城后命守备康茂见机策应。西杨与蹇、夏三人留守大营,东杨、南杨扈驾,随朕与三千铁骑出喜峰口,随军参谋。大家明白没有?”
众人一齐回道:“臣等明白了!”
宣德皇帝起身把手一挥,命令道:“大家从速准备,尽快进军吧!”
众人应了一声,快速走了。不一会,薛禄为前队,任礼为后队,张辅扈驾为中队,各自带领一千精兵迅速消失在夜幕之中。
喜峰口是座著名的要塞。北京的正北面两百余里,横亘着巨大的燕山山脉,崇山峻岭,绵延起伏,逶迤一千余里,一直到宽城东面一百余里与辽东的黑山相邻。不过,燕山山脉到了宽城,山势逐渐减弱,山岭之间出现了一些大致南北走向的狭长的平川,宽城就筑在这其中的一条平川上,但从遵化北上到宽城,还有一条山梁挡着,只有一条山口可以通过,这个山口就是喜峰口。从喜峰口进山向西北行进,大约十里便出了山,再往北走,经桲罗台、孟子岭、小岭、东水窖,仅四十里便到了宽城,所以这段路最为艰难的便是喜峰口这十里。走过这十里,不说是一马平川,但地平路宽可以放马了。
宣德皇帝挥师从戌时末起驾,不久便进入了喜峰口。那道路只有五尺来宽,一人骑着马手里还牵着一匹马,刚好容身通过,而且那通道两旁怪石嶙峋,稍有不慎,便会头破血流,实在险峻,山口满是石头子儿,疙疙瘩瘩,十分难走。宣德皇帝骑着白龙驹,两旁由中官金英和王敏护持着一步靠一步慢慢前行,走得极为缓慢。
宣德皇帝虽然走得慢,但他年轻力壮,精力旺盛,倒也并不在乎。可是,那扈驾的杨荣和杨溥二位大臣可就苦了。他们二人都是五十六七岁的人了,平素又不善骑马,再加上天色漆黑山路不平,骑在马上摇摇晃晃,随时都有可能掉下来,他们只好双手紧紧抓住马鞍,两腿夹住马腹,跌跌撞撞地往前挨着,一路走来浑身上下都汗湿透了。
足足走了一个多时辰,才走完了那艰难的十里山路,走出了喜峰口。三千兵马松了一口气,稍事休息,便继续向宽城前进。好在道路较为宽阔平坦,行军的速度明显加快了。
卯时初刻拂晓时分,宣德皇帝率领的三千精兵赶到了宽城。早有先期赶到的中官袁琦和守备康茂等在道旁迎接。一见袁琦和康茂,不等他们说话,宣德皇帝便问道:“康茂,朵颜人马现在何处?”
“启禀陛下,朵颜人马现在还驻扎在距此二十里的龙须门。”康茂回答道,“臣派了四五路探马监视敌情,每隔一个时辰便有一路探马来报,如有异动随时来报,至今未发现朵颜有何动静。”
宣德皇帝朝袁琦望了望,问道:“最近的一次探马来,是怎么说的?”
“回陛下的话。”袁琦连忙躬身答道,“探马刚刚来报,说朵颜人马这时候还在营帐中睡觉,尚未起床呢。”
听罢袁琦和康茂的回答,宣德皇帝望着晨曦中的北方思索起来。这时,站在一旁的杨溥拱了拱手,说道:“陛下,这是天赐良机,不可错过。我军宜正面进攻,两面包抄,出其不意,突袭敌营,破敌在此一举。”
“陛下,南杨大人说得对。”紧跟着杨荣也进言道,“趁朵颜尚未明了我军底细之际,突然发起攻击,必然一击即溃。”
“我们还可来个先声夺人。”在一旁的张辅也立即补充道,“臣带的神机营将士带来了三十几门铁铳,叫他们来个一阵连发,首先打他个下马威,让他们军心涣散四处逃窜,我军便可乘势踏平他们的营寨。”
“好,抓住战机,一鼓作气!”宣德皇帝下了决心,“命薛禄和任礼各带所部人马分成左、右两路包抄敌军,张国公带领中军正面攻击,袁琦和康茂率兵掩杀,其余各人随朕行动。不过,大家不要忘了朕的方针是‘武服恩定’,目的是要降服他们,交代将士们不要杀戮太过,只要朵颜投降,便可不杀!”
“臣等遵旨!”众人说罢,迅速走了。
很快,宣德皇帝率领的三千精兵,换了马匹,吃了几口炒粉,精神抖擞地跨上了战马。宣德皇帝一声令下,三千铁骑分成三路,风驰电掣般向龙须门的朵颜营寨杀去!
这时天已大明。九月初的塞北,天气晴好,万里无云,朵颜营寨内缕缕炊烟袅袅升起,兵士们正在埋锅造饭。果然不出杨溥所料,已经安定了多年的朵颜三卫,如果不受人差遣,他们是不敢轻举妄动的,此前的数次骚扰盗边,都是受瓦剌马哈木和鞑靼阿鲁台的指使。这次率众南犯,正是奉瓦剌脱欢之命,前来试探朝廷边塞有无准备,再伺机行动。
朵颜卫头目哈剌哈孙清早命人把泰宁卫头目脱火赤、福余卫头目安出一并请了过来,正准备商议今日如何攻打宽城,只见有人慌慌张张地骑马跑来报告道:“不好了,不好了,明军来了!”
“慌什么!”朵颜哈剌哈孙大喝一声问道,“什么明军来了?把事情说清楚!”
“确实是明军来了!”那小卒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小的正在南边巡哨,忽见大批明军从宽城方向来了,小的便慌忙跑回来报告。”
“大约有多少人?”哈剌哈孙问道,“都打着什么旗号?”
“天刚刚亮,看不太清楚。”那小卒回答道,“反正人马很多,一大片一大片的,五色旗帜都有,小的一时慌张,具体的情况也说不上来。”
听罢小卒这模糊的报告,哈剌哈孙不胜恼怒,他大声喝骂道:“不中用的东西,滚一边去!”
说罢,他带着脱火赤和安出,走上高处向南方眺望起来,只见远处确实有一队骑军正向营寨奔来。哈剌哈孙想了想,向脱火赤和安出说道:“昨日探马报说宽城周围平静如常,未见朝廷一兵一卒。这奔杀的一队明军,大概是宽城守军想趁我清晨不备偷袭我营寨,我们正好将他们作为早餐一口吃掉。你们二位意下如何?”
“将军所见极是。”脱火赤和安出两部势力都比较弱小,一向是唯朵颜之命是从,见哈剌哈孙说是宽城守军前来偷袭,便齐声说道,“该怎么迎敌,将军你就下令吧。”
“好。”一见脱火赤和安出并无异议,哈剌哈孙便下令道,“你们二人立即率领各部,从两面包抄上去,我率部从正面冲击,先将他们团团围住,再一口一口吃掉。”
“好,我们这就去办。”脱火赤和安出答应一声,正要离去,忽然轰隆一声,一颗炮弹落在不远处爆炸了,一阵热浪和烟雾迅速地向哈剌哈孙所在的高地扑来,一阵爆炸掀起的泥土溅了哈剌哈孙三人一身,营寨中的兵士们立刻惊惧地喊叫起来。
哈剌哈孙三人一下子惊呆了。还没等他们反应过来,轰隆隆!轰隆隆!一阵密集的铁铳发出的炮弹,在朵颜三卫的营寨中炸开了。不少的士卒被炸得抛向天空,血肉模糊地落了下来;许多帐篷被掀翻,营寨中燃起了熊熊大火;一万余名兵卒来不及披挂上阵,丢盔卸甲哭爹喊娘,向北没命地奔逃;那一万余匹战马,被那轰隆轰隆爆炸声吓蒙了,惊慌地嘶叫着四下狂奔,一时间烈焰冲天,灰尘蔽日,人践马踏,惊叫哀号,朵颜三卫营中大乱。
距离朵颜营寨仅一箭之遥的一处高地上,宣德皇帝和杨荣、杨溥正在观战。眼见得张辅带领的一千精兵发射的一阵铁铳炮弹,把朵颜打得军中大乱,他不禁一阵欣喜。他立即叫中官袁琦摇动黄龙旗,发出两翼军同时进攻的命令,薛禄率领的一千名左队军和任礼率领的一千名右队军,扬鞭跃马,飞也似的向朵颜军包抄过去。忽见明军骑兵从天而降,朵颜军吓得潮水般向北溃逃,还有少数朵颜士卒吓得昏头昏脑,慌慌张张地竟朝宣德皇帝所站的高地逃来。
一见那伙朵颜士卒向高地逃来,宣德皇帝豪情勃发,他从身上摘下弓箭,从箭袋中掏出鸣镝,拈弓搭箭向那逃在最前面的朵颜士卒射去,只听“呜”的一声鸣叫,一道白光飞向敌卒,那朵颜士卒惨叫一声,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第二声鸣镝响起,朵颜的又一个士卒倒下了。还没等奔逃的朵颜兵士们弄清是怎么回事,第三声鸣镝又响了,又一个朵颜士卒应声而倒!
宣德皇帝三箭射倒了三名朵颜士卒,周围的明军发出一阵“万岁!万岁”的欢呼声;袁琦将手持的黄龙大旗拼命地摇动,三千精兵精神大振,一齐纵马挥刀,排山倒海般地向朵颜军杀了过去!
正在慌乱得不知所措的哈剌哈孙、脱火赤和安出,一见黄龙旗不停地挥动,才知道前来攻营的根本不是什么宽城守备军,而是当今圣上宣德皇帝御驾亲征了!哈剌哈孙等人不禁大惊失色,原来这即位不久的年轻皇帝确实是睿智英武,乾纲独断,不仅文治卓异,而且武备强雄,名不虚传,这大明朝廷岂是我等所能撼动?这下糟了!想到这里,哈剌哈孙胆战心惊地对脱火赤、安出二人说道:“看来宣德皇帝十分英武,朝廷也比永乐时更加强大,那瓦剌比起大明朝来不值一谈,我们还是趁早投降,归附朝廷的好。”
“将军说得对。”脱火赤和安出早已吓得魂不附体,见哈剌哈孙愿意投降,二人连忙说道,“我们哪是朝廷的对手,早早投降,免得身首异处。”
说罢,哈剌哈孙、脱火赤、安出三人走出营寨,望着前面的黄龙旗,双膝一跪,投降了!那朵颜三卫的兵士们看见三个头目都已投降,他们也不逃了,纷纷就地跪下,俯伏在地,大声喊道:“皇帝饶命,皇帝饶命!”
战事已经结束,宣德皇帝带着杨荣和杨溥,由锦衣卫队护卫着,意气风发地策马向哈剌哈孙等人走来。
一见黄龙旗下的宣德皇帝这么年轻英武,哈剌哈孙等三人赶忙膝行几步,伏地叩首大声请罪道:“臣等罪该万死,伏望皇帝殿下恕罪!”
“你们叫什么名字?什么职务?”骑在马上的宣德皇帝威严地问道,“你们在兀良哈生活得好好的,为何要兴师南下侵扰他地?”
哈剌哈孙、脱火赤和安出分别报告了自己的姓名和职务,哈剌哈孙叩头说道:“陛下,臣等愚昧无知,千不该万不该听信瓦剌脱欢的胡言,兴众骚扰内地,犯下死罪。尚望陛下念臣等一向守边辛苦,饶恕臣等吧!”
“原来是你们三位都指挥佥事。”宣德皇帝语气缓和了许多,他用马鞭指着跪在地上的哈剌哈孙等三人道,“都起来说话吧!”
“谢陛下!”哈剌哈孙等三人又重重地磕了一个头,才站了起来。哈剌哈孙这时才放胆看了看周围,只见宣德皇帝明盔亮甲,一身黄色戎装,好生威武;站在两旁的几位大臣,也都是身着戎服,气宇轩昂;那周围的锦衣卫,个个都是虎背熊腰,威风凛凛,好一支雄武之师!看罢,哈剌哈孙不由心里十分佩服,他整了整衣冠,拉着脱火赤和安出重新跪拜行礼:“臣等参见陛下,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见朵颜三卫的三个头目行礼参见,俯首称臣,宣德皇帝心下不由一阵高兴。他翻身下马,把手象征性地一托,说道:“荒郊野外不必多礼,你们都平身吧!”
待三人站起,宣德皇帝好言教训道:“你们都是朕的爱将,都是朝廷命官,理应识大体,顾大局,怎么能阴附瓦剌,受其蛊惑,兴师动众,公然与朝廷为敌呢?这不是糊涂至极,以卵击石,自取灭亡么?”
“陛下教训得是!”哈剌哈孙等三人连忙低头谢罪,“臣等愚昧,罪该万死!”
“只要你们明白就好。”宣德皇帝继续说道,“所幸你们此次驱众南犯,为害不烈,罪孽尚不至深,且能迷途知返,朕念你等长居漠北,艰辛苦寒,守御边陲,有功有劳,就饶你们一次,赦你等无罪吧。”
哈剌哈孙、脱火赤和安出三人喜出望外,连连磕头谢道:“谢陛下不杀之恩,谢陛下不罪之恩!”
“都起来吧。”宣德皇帝伸手拉了哈剌哈孙等三人一下,那哈剌哈孙等人受宠若惊,连忙感激涕零地站了起来。宣德皇帝温和地说道:“自今而后,朕望你等牢记你们是大明朝的边疆守备将军,时刻要以国家朝廷为重。要带领你们的百姓,安居乐业,着力发展畜牧,允许你等以马匹、皮革与内地互市贸易,以兴边塞。你等要切记朕的话,不要与他部互相勾结,阴谋作乱,那样绝无好下场!”
“臣等记下了。”哈剌哈孙等三人连忙点头,“臣等再也不敢违抗朝廷律令了。”
见哈剌哈孙、脱火赤和安出已经慑服了,宣德皇帝指了指近处的几匹马对哈剌哈孙等三人说道:“好了,那里有马,你们各自回去吧。”
“谢陛下隆恩!”哈剌哈孙、脱火赤和安出三人谢了一声,各自跨上马,带着自己的部落回兀良哈去了。自此而后,兀良哈三部安定了二十余年。
望着哈剌哈孙等朵颜三卫的人马渐渐远去,宣德皇帝异常兴奋!这是他即位以来的第一次北巡,仅仅几个时辰,便降服了强悍的朵颜三卫,解决了心腹之患,安定了边塞,真是旌旗所指,所向披靡,这还不值得得意么?他踌躇满志地对身旁的杨荣、杨溥和张辅说道:“众位爱卿,朵颜三卫虽定,但边务事大,朕与诸卿再把边塞城堡巡视一番然后班师还朝吧!”
“臣等遵命!”众人答应一声,簇拥着宣德皇帝向宽城守御千户所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