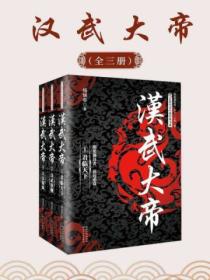第二十章 落叶萧萧长安树 阴霾重重汉宫秋
转眼间刘彻离开京都三个多月了,时序已到了八月。
自送走父皇后,刘据一直处在心绪不宁的彷徨中。
那天,看着浩**的车队驶上咸阳北原,他才收回忧郁的目光。他想说的话太多了,可父皇却没给他机会。
在刘彻离开京城的日子里,尽管讲述《春秋》的活动仍在博望苑按部就班地继续,尽管每日都有大臣前来请示朝事,可刘据的精神却无论如何也集中不起来,他挥不去父子相别时的冰冷。他感觉许久以来所担心的事似乎在日益临近。因此,在石德讲书时,他常常走神。
石德任太子太傅较晚,面对的是而立之年的刘据。刘据对军国大事不仅关注,而且总是与史载前事比较,形成自己的见解,这给他留下了博学慎思的印象。这使他不得不调整教授方法,更趋向于从微言切入,从一时一事引发议论。
刘据对这种方法很喜欢,他们的议论常常碰出智慧的火花。这比之过去更实事求是,更心地默契,两人的关系渐渐地超越了君臣和师生,而带了挚友的意味。
可这超乎师生的关系发展下来,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石德的情感在不知不觉间向刘据一边倾斜,他也顺着太子的思路而对皇上的朝事颇有微词。
他们今天讲的是“鲁隐公十一年冬十一月”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位羽父先想说服鲁隐公杀了自己的弟弟,让自己当宰相,当他的请求被拒绝后,竟然背叛了鲁隐公,转而去煽动桓公弑兄自立。
石德讲到这里,借题发挥道:“殿下,一部《春秋》言尽兴废之理。而朝之兴废,在于用人。依臣看来,这鲁隐公兄弟都算不上明君,像羽父这样的乱臣贼子,朝三暮四,无非图私利耳。然他们却不能识其面目,难免不祸起萧墙啊?”
可他却没有从刘据那儿得到满意的回应,等来的确是沉默。
石德很不满足,站起来施了一礼再问道:“殿下以为然否?”
刘据这才从沉思中醒过来,不禁赧然一笑道:“刚才本宫想起一件事,故而失态,请太傅见谅。”
“哦!殿下想起何事?”
“太傅以为江充其人如何?”
石德顿觉吃惊,原来太子并未走神,而是由史想到了当前。
石德掩上门,小声道:“藏而不露,口蜜腹剑。去年公孙贺那桩案,就是他一手酿成的。”
刘据站了起来,临窗而立,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窗外白云悠悠,黄门和宫娥来来往往,鸟儿在老绿的槐林、松柏的枝头歌唱。他想,父皇此刻在甘泉宫一定过得很惬意吧?他忘不了少年时父子相亲的情景。
那时候,母后正值青春,每年一到六月,都是他和父皇、母后一起在甘泉宫中度过的。
在记忆中,父皇是威严的,也是慈祥的。他不能忘记十岁夏天的那晚,父皇和他沿着甘泉宫旁的一条小径散步,坦率地说着年轻时的一些孟浪行为。
阳光西斜,在山间投下浓密的树影,刘彻偕刘据缓缓地走在山道上。坡很缓,天气也不那么热,时间很充裕,他们完全不用着急赶路,而将自己散淡地置于斜阳碧树间。
警跸们在身后跟着,父子似乎都可以听到彼此的心跳。
话题很分散,先是说到了为君者的道德,进而又说到了七国之乱,连刘彻自己都不知道,他们是怎样说到自己早年孟浪的行为上去的。
“人在年轻时,往往虑事不足,朕在年轻时,也曾多有狂悖。”
刘据很吃惊,父皇竟是如此坦率。
当年,父皇刚刚把母后接过来时,两人感情甚笃,常常结伴到终南山下打猎。有一天,当他们踏着月光赶到长安城下时,城门已经关了。守门的司直在城头喊话:“皇上有旨,私自开城门者,斩无赦,小吏岂敢违背皇命!”
父皇无奈地看了看母后,唉!他怎么会想到,有一天会被自己的诏命堵在城外呢?他没有理由违背自己颁布的法令,于是两人回头来到沣河岸边,寻一农家借宿。
父皇轻叩柴扉,开门的是一老者,他见是一身着锦袍的官员,气就不打一处来:“你们只知游猎,从来就不知百姓死活,现在想来借宿,除了猪圈,没有地方给你们住!”
年轻的父皇何曾受到如此奚落,一道诏书就将阿城以南,周至以东,宜春以西的农人籍没迁徙,广袤的关中平原被扩充为上林苑。
刘彻说起这段往事,笑着摇摇头道:“现在想来,那实是一个误农伤民之举。你既为太子,万不可步朕的后尘啊!”
父皇曾当着自己的面悔过,那曾强烈地感染了刘据。
往事不堪回首,留下的只是依稀梦影。
自他进入而立之年后,就逐渐感受到父皇的固执和偏狭,听不进忠言,惧怕老去;多疑和孤僻。这一次,他带着刘弗陵和钩弋夫人去了甘泉宫,却把母后冷落在长安……
一想到母后,他的心就益发苦涩。昨日,在母后处当差的黄门王谦来报,说江充率人手持皇上诏命,从御花园到寝宫,一块砖一块砖地挖掘搜索人偶,已有几位夫人因忍受不了这种侮辱,香消玉殒。
母后最后也难幸免,江充派人把母后的寝宫折腾得凹凸不平,连放一张榻床的地方都没有了。
他到底要干什么?他要将母后怎么样?这万里河山到底还姓不姓刘?……
刘据再也没有心情听石德讲授那些遥远的宫廷血腥,将手中的《春秋》抛在一边道:“这书本宫不读了,治史与治国相去远矣!”
石德于是无言。给太子当老师,他就是在刀刃上过日子,唯一的选择就是悄然退出去,掩上书堂的门。
世上最折磨人的就是有话无处倾诉,有情无处宣泄,郁闷中的刘据下意识地拨动了身旁的琴弦,他说不清是什么力量驱使一曲《无衣》从他的指尖流出: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
琴声伴着歌声,如大海奔流,万马低吟,时而慷慨激昂,时而纤弱婉转……
这时候,常融拿着一把拂尘,貌似悠然地踱着步子,时不时地注视着假山后的一丛月季,看看没有什么破绽,才又向前踱去。
转过假山就是一座小桥,他装作拾履,慢慢地蹲下去,用袍裾将身后的一块地方盖住,从地上掀起一块方砖,看看所埋之物安然无恙,这才放心地站起来。
迈过小桥,迎面走来一群玉面桃花的宫娥,她们见了黄门,纷纷上前施礼。常融与宫娥搭讪之后,就急着往前殿去了。
在通往前殿的路上走着,他的心一刻也轻松不了。想起十几天前与江充的会面,他仍然走不出那场噩梦的阴影。
当府令要他在宫中埋人偶时,他就知道自己再也回不了头。
平心而论,自他到太子府以来,刘据待他十分宽容。可那一纸留下他指印的“供词”,就把枷锁套在了他身上。
江充毫不掩饰地告诉他,此事乃苏公公的安排。
而一提到苏文,他便没有话说。他本来是一个孤儿,那年到京城行乞,流落街头,因向店家讨要残羹而遭殴打。恰巧苏文从那里经过,为他买了饭菜,并且带他回了家。从此,他的人生就进入一个新的境界。
苏文教他宫廷礼仪,让他学习怎样待人接物。一天,苏文说要送他去宫中做黄门。他虽然年少,却也知道受阉割的痛苦。可对迫切需要改变命运的他来说,这一切都不重要了,何况苏文把黄门每日不离皇上左右,随时可以向皇上进言的情景描绘得非常诱人呢?
常融虽然极不情愿,可又不得不埋人偶。他在心里暗下决定: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幼稚的他哪里知道,他已经没有第二次了。他的手,将在长安制造一场风声鹤唳的血案。
他路过博望苑书堂,从里面传出苍凉的琴音和低沉的吟唱: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
岂曰无衣?与子同泽。
王于兴师,修我矛戟,与子偕作!
岂曰无衣?与子同裳。
王于兴师,修我甲兵,与子偕行!
……
那凄婉、那沉郁,让常融为之动容,他不敢久停,怕自己在一瞬间动摇了决心,便急急忙忙向前殿奔去。
这首《无衣》是刘据最喜欢的一首,那铿锵有力的节奏,那同仇敌忾,气壮山河的威势,都让他血脉贲张。两位大司马曾传令在军中传唱,以壮军威。可自他们去世后,他便弦断少知音,许久不曾动过琴了。现在,这歌声就在他的指尖流淌,可有谁能解其中的情怀呢?
他悲愤交集,泪如雨下,琴弦“当”的一声就断了。刘据大惊,朝外面喊道:“太傅!太傅……”
石德闻声赶来,见太子双手捂脸,伏在琴上。他还没有来得及问话,侯勇便进来奏道:“外面人声嘈杂,好像是江充带人来搜查了。”
“哦!该来的还是来了。”难怪琴弦断了,它是提醒本宫大祸已经临门了啊!
刘据将断了弦的琴推到一边,令侯勇出去察看动静,要石德回避。
石德似有预感,眼含热泪道:“殿下,此时此刻,老臣无论如何也不会离开的。”
刘据强打精神劝慰道:“太傅放心,清查巫蛊,乃父皇诏命,本宫身为太子,岂能违抗,太傅在反而不便,请您暂时回避。”
“殿下,那老臣就先行告退了。”走出殿门,他还是不放心,又折回来叮嘱道,“殿下须当从容,才不致授人以柄。”
石德刚进入小憩的侧室,江充的人马就呼啦啦地冲进太子府。
羽林卫玄甲被身,执戈持戟,一个个杀气腾腾;与此同时,博望苑的两厢中冲出一群禁卫,列队整齐,剑拔弩张。
侯勇手持宝剑,大喝一声:“光天化日之下,何人如此大胆,竟然闯入太子府中,难道你们不怕死么?”
一位队史上前回道:“我等奉御史大夫之命,搜查巫蛊,实是有命在身,还请詹事见谅。”
“搜查巫蛊,与太子何干?”
“这个末将就不知道了,末将只是奉命行事。”队史虽然话音柔和,却仍示意兵卒朝内拥来。
侯勇凛然而立,对禁卫喝道:“谁敢近前一步,杀无赦!”
两边刀光闪闪,空气骤然紧张起来,大有一触即发之势。
就在这时,从书堂内传出太子的声音:“詹事少安毋躁,让他们进来!”
禁卫“哗”的一步,让开一条道,这时候,江充匆匆赶来了。
江充并没任何逾越的狂悖,而是文质彬彬地上前施礼道:“微臣叩见太子殿下,臣奉皇上旨意,清查巫蛊一案,惊动太子,臣深感惶恐。”
“难道御史大夫怀疑本宫诅咒父皇不成?”
江充拱手道:“微臣不敢。微臣只是奉旨行事,还请殿下体谅臣的难处。”
“御史大夫倘若从府中搜不出人偶,该当如何?”
江充依旧笑容可掬:“微臣亦愿殿下清白,臣也好向皇上复旨。”
话说得如此冠冕堂皇而又滴水不漏,刘据自然没有阻挡的理由。
羽林卫在队史指挥下,在博望苑出出进进了大约一个时辰,却没有搜出任何证据。
刘据心中愈益坦**:“本宫素来严谨,江大人既是奉旨而来,不妨验看仔细,也好了却大人心中疑窦,还本宫一个清白。”
此举正中了江充下怀,他暗中看了看跟在太子身边的常融,他的手微微向后指了指。
“谢殿下宽容,微臣也是出于无奈。”言罢,他带着一干人向后花园散去。
石德和侯勇急忙来到太子身边,不约而同道:“殿下受惊了。江充借诏书之威,实在是欺人太甚。”
侯勇圆睁两眼道:“若非殿下约束,臣早就一刀结果了他。”
刘据摇头叹道:“他也是奉旨行事。”
石德知道,如果太子事发,他也脱不得干系。刚才他分明看见江充出苑时,面带杀机。他顿然感到了危机的逼近。
“殿下素来宽仁,可防人之心不可无啊!”
“他又能把本宫怎样?”
“殿下之言差矣!我朝多少人因巫蛊冤死刀下?今日江充来者不善,殿下可矫节捕他入狱,治其罪。”
“唉!本宫乃太子,怎可擅自做主?倒不如辞去太子之位,也许还可以保公主和母后平安。”
侯勇急忙接道:“太子此言又差矣!臣闻皇上离京时,对巫蛊一案查意甚坚,倘小人先一步诬告于圣前,殿下就是辞去太子之位也于事无补。臣以为,太傅所言极是,先捕江充入狱为好。皇上远在甘泉宫,只要殿下封锁消息,皇上回京,就说江充欲劫持太子、丞相,意图谋反,故而治罪。”
石德亦劝道:“事急矣!詹事速去调集禁卫,须臾江充返回,一切都晚了。”
侯勇闻此转身就朝门外走去。
刘据惊道:“太傅这不是要陷本宫于不忠不孝么?”
石德近前一步劝慰道:“殿下放心,臣誓死追随殿下。”
“早知宫廷如此险恶,倒不如做个寻常百姓,也少了许多事端。”刘据话音刚落,江充便带着一干人从门外进来了,他一副茫然困惑的样子。
等到了刘据面前,他拱手道:“微臣有要事奏。”
太子扭过头来。
“臣在太子御座下面、后花园牡丹下面和双拱桥上共掘得人偶六个,请问这……”
这时羽林卫已将六个人偶一字排在太子面前。
“这……你看该如何处置?”刘据先是一惊,旋即平静了下来。
“臣当如实禀奏皇上!”
“本宫胸襟坦**,岂会干这等下作之事,分明你蓄意陷害。”
太子话音刚落,就见一宫娥泪流满面地跑进来了,她断断续续地道:“娘娘……和小王子投湖了!”这消息如晴空霹雳,刘据只觉眼前一黑,险些倒下。
前天夜里,夫妻俩还为近来宫廷动**不安,人心惶惶而相坐良久。当时史良娣还安慰说他是皇长子,又是太子,就是有事,也绝对与他无涉。她还反复叮嘱身边宫娥,近来凡事小心谨慎,不要给奸人留下把柄。可刚过了一天,他们就死于非命。
“想我堂堂太子,竟无力保护自己的妻儿,我何为太子?何为男人啊!父皇!您在哪里?孩儿何罪之有?竟要遭此浩劫?父皇!父皇……”
跟随太子多年的石德和侯勇,顾不上征得太子同意,怀抱汉节,手指江充,疾言厉色道:“江充奸臣,祸国殃民,皇上早知你素存异心,令你查处巫蛊,不过欲擒故纵而已。皇上临行时,早授太子以节,还不跪下受缚。”
这一出江充着实还没想到,顿时他目光迷离,犹疑彷徨。这时听见身后有人喊道:“御史大夫,谨防汉节有诈!”
一言未了,石德挥动汉节,侯勇从侧室冲出,一剑结果了那人性命。
江充大惊,忙向身后的羽林卫喊道:“还不将这反贼拿下!”
羽林卫中有人正欲动手,侯勇一把将血刃横在手中,大吼一声:“休得妄动,一切听令于太子。”
江充惊慌中回头看去,两厢廊庑下、墙头上,禁卫军容整齐,早有所备,一张张弓弩直对着天井,他顿时慌了。
悲愤交加的刘据,在众人的扶持下,从台阶上一步一步地走下来,目光含着愤怒:“你这乱臣贼子,手无寸功,凭阴险狡诈,下欺文武阁僚,上蒙皇上视听,今日若不杀你,国无宁日,来人,快将这贼子首级取下!”
江充这才觉得事态的严重,忙求饶道:“微臣素知殿下与皇上情感笃重,巫蛊之案,臣只是奉诏行事,实出于无奈,殿下若是饶了臣,臣一定在皇上面前澄清是非……”
见太子毫不动容,他“扑通”一声跪倒在地,头在砖上磕得“砰砰”直响。
刘据“嘿嘿”冷笑道:“逆贼,没有想到你还会有今天吧?”说着他夺过侯勇手中的利剑,向跪在地上的江充刺去,顿时,江充血流如注,喷在博望苑的柱子上。
侯勇扯下一片战袍,擦了血迹,骂道:“不要让这贼子之血污了神圣之地。”
随来的羽林卫见大势已去,纷纷跪倒在地,表示愿听太子之命。
侯勇让人将那些蛊惑人心的人偶烧掉,而石德则在一旁提醒太子,让常融去禀明皇后此事。可待他们回身寻找时,却发现常融早已不见了……
“皇儿!你闯下大祸了!”卫子夫听说刘据杀了江充,愁容顿时就上了眉头,“他是钦命的御史大夫,位列三公不说,他还肩负着清查巫蛊的皇命,你杀了他……”
从清查巫蛊以来,天天就守在卫子夫身边的卫长公主,对母后的忧虑表示了有度的不屑:“母后总是忍让,结果都让那些乱臣贼子欺负到头上来了。”
卫子夫狠狠地瞪了一眼卫长公主道:“你懂得什么?你们只图一时泄愤,若你父皇得知消息,看你们怎么收场?”
从建元二年进宫至今,卫子夫目睹了无数腥风血雨,却从来没有把它们同自己的命运联系起来,可如今,她也不得不面对这一情况了。
刘据望着卫子夫蹙郁的眉头,心底一下子沉重了:“孩儿也是出于对江充的义愤,孩儿若不杀了他,到头来还是要危及母后的。”
卫子夫落泪了:“儿啊!为今之计,要先得到丞相襄助。若是丞相与你站在一起,也许还有回旋余地。你速遣人到丞相处,通报江充谋反罪行,丞相若是个明白人,一定会临危受命,同舟共济的。”
卫子夫更清楚,在这个生死关头,无论是她还是刘据,都不能乱了方寸。以江充的作为,也真是死有余辜。想到这点,卫子夫昂然抬起头来,一改往日的和颜悦色,对春香和詹事严厉地道:“皇上如此信任江充,然彼不思图报,反而趁皇上离京之际,密谋造反。本宫依照大汉律令,剪除国贼,以正朝纲。从现时起,两宫禁卫,严阵以待,有违令者斩无赦!”
她又对石德道:“烦劳太傅速到丞相府通报事变缘由。”
“诺!”
卫子夫又对侯勇道:“本宫素知你忠直,你须臾不可离太子身边,要选派最亲近的士卒护卫。椒房殿詹事何在?”
“臣在!”
“本宫平日待你不薄,现今国逢危难,命你率领宫中禁卫,守卫宫门,以保皇宫安全。”
“诺!”
卫子夫又叮嘱春香道:“你不可离开本宫半步,派出练过武功的宫娥打探城内消息,随时回奏本宫。”
“诺!”
卫子夫安排完这一切,才对刘据道:“你速去传本宫的懿旨,告令百官,言明江充谋反之事;并部署兵力,以确保京城安定。”
卫子夫的镇定,使刘据忐忑不安的心平静了下来。回到太子府,他立即以皇后的名义发中厩车载射士,打开武库,分发兵器。
傍晚,天色又阴沉下来,从南山传来沉闷的雷声,风掠过长安城头,吹得旌旗“哗啦啦”直响。
刘据焦急不安地等待着丞相府的消息。他不断地派人前去瞭望,可是,直到天黑下来,仍不见太傅的踪影。
宫娥捧上晚膳,被刘据喝令撤下。直到京城亮起灯火的时候,石德终于出现在太子府。
刘据迫不及待地问道:“丞相如何说?”
可口干舌燥的石德张着大口,却说不出一句话来。侯勇忙要宫娥捧了茶水,石德润了润喉咙,才挤出一句令人沮丧的话来:“丞相说尚未见皇上虎符,北军无由发兵。”
“还有呢?”
“丞相说,事已至此,要太子少安毋躁,他连夜派人到甘泉宫奏明皇上,请求定夺。”
这不等于把实情都告诉了皇上么?这样一来,还能造成既定局面么?刘据沮丧地坐在地上,一时没了主意。
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无论是石德还是侯勇都清楚没有退路了,侯勇道:“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我们既然可以矫节杀了江充,也可以劫持丞相,逼他承认江充谋反。”
“眼下兵力不足,怎么劫持丞相?”
“倒是有两处有兵。”
“快快讲来。”
“为今之计,殿下不妨矫诏放出牢中刑徒,由臣率领捉拿丞相;另外,据臣所知,当年浑邪王降汉后,皇上曾将余部分屯各处,长水一带就有一部。这些人平日对汉军状况知之甚少,殿下亦不妨矫诏,招其进京。”
刘据搓着手来回踱步,举棋不定:“矫诏!矫诏!此乃欺君大罪也!”
石德看刘据失魂落魄的样子,不免失望:“殿下不可犹豫,保住了殿下,就是保住了汉家江山。殿下可一面令禁卫加强戒备,一面于长安城内广贴檄文,言明殿下是奉节除奸,皇上临行托朝事于殿下,臣下焉有不信之理?”
刘据蓦然颔首,待侯勇离去后,他登上宫墙,望着灯光黯然的长安城,心中阵阵绞痛。
不久前,他还秉承母后旨意,祈求父皇万寿无疆,孰料残酷的现实竟将他推向父子相残的地步。要命的是,一旦自己举兵不成,血洒长安的就不止他一人了。
“上苍啊!刘据何负于你,却要遭此天谴啊?”
第二天,长安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太子的檄文:“帝在甘泉病重,疑江充谋反,诏发三辅之兵……”可城内的百姓却有种异样的感觉,檄文虽然言事变之烈,历数江充谋反罪状,却未见巡逻的兵卒增加。
酒肆茶舍的商贾们在大惑不解的同时,暗祈罢兵息戈,好让他们一如既往地安心做生意。
……
刘据的估计没错,当侯勇率禁卫来到丞相府时,府令说丞相在太傅离开时,就匆匆坐上车驾走了,至今未归,也不知去向……
“此事关系重大,本相未见皇上兵符,实在不敢贸然行事。”昨晚,刘屈髦在详细听了太傅的述说后,用一句很谨慎地回答婉拒了太子的请求。
可石德竟猜不透刘屈髦那迷离目光后深藏的心机,还是抱着一线希望而不愿离去:“丞相!江充谋反之心已昭然若揭,太子剪除国贼上合天意,下顺民心。”
“太傅勿复再言,本相恕难从命。”
“不!太子护驾之心天日可鉴,丞相若能助一臂之力,日后……”
刘屈髦挥了挥手道:“太傅请回吧,请先容本相奏明皇上。”
“丞相……”
“送客!”刘屈髦毫不犹豫地下了逐客令,石德便踉踉跄跄出了丞相府。
的确,事情来得太突然了,让他有些措手不及,可诛杀江充却为他排除了一个障碍——这个令人生厌的小人,一心想着攀附刘弗陵,迟早会成为国贼。
面对突如其来的事变,他需要做出慎重的抉择。
早在钩弋宫的御前会议上,他就摸清了皇上的心思,因此他断定,不管太子出于何种目的,皇上都不会原谅他。他发现,上天就这样把消除太子的机遇降在他面前。
在与石德说话的那一刻,他的思绪一直在高速运转,他对自己在这场事变中的角色已有了清醒的认识。太傅一走,他就立即传来了长史,要他连夜奔往甘泉宫,向皇上禀奏京城的事变。
酉时三刻刚过,刘屈髦的车驾就已停在了北军大营的门口。
积了后半天的雨云终于在震天响的雷声中将大水泼洒在天地间。
刚刚从益州刺史任上调任北军使者护军的任安听说丞相来访,急忙到营门口迎接。看见站在大雨中的刘屈髦,他很吃惊地问道:“夜色漆漆,大雨滂沱,丞相何故匆匆来此?”
“事急矣!容本相进营详叙。”
安顿丞相坐下,任安问道:“发生了什么事?”
刘屈髦喝了一口茶,才开口道:“太子杀了清查巫蛊案的御史大夫江充。”
“哦!有这等事?”
“太子以江充谋反、维护京城安定为由,要老夫征发北军,被老夫拒绝。案件是非曲直一时分辨不清,老夫岂可轻信传言。而且,大汉律令——见虎符才可发兵,老夫没有见到皇上虎符,贸然发兵,也有违律令。考虑到太子会持节要将军发兵,老夫才连夜冒雨赶来,怕将军不慎,殃及家人。”
任安十分感谢刘屈髦在这个关头对自己的提醒:“请丞相放心,末将一定严守营寨,不见虎符,绝不发兵……”
“在没有接到皇上诏命之前,老夫也不准备再见太子,今夜老夫就暂借将军大营歇息了。”
现在已是凌晨子时,在距中军帐不远的地方,刘屈髦已经进入梦乡,可任安却毫无睡意了。
虽然长期在外,但太子的为人他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不相信太子会无故把宝剑刺向一个位列三公的御史大夫。皇上对司马迁处以腐刑的事使他断定,江充的死一定与皇上有关。
他应该如何处置?
他多么需要一位智者为他指点迷津,假如司马迁在身边,他一定能为他找到一个合理的途径。可作为中书令,他现在就在甘泉宫,在皇上的身边。
要是大司马活着也好。早年,他在卫青府上做舍人,后来被推荐到军中任郎中,直至将军长史。他亲身感受到卫青的儒将风度,每临大事的冷静和沉着。
唉!今后不会再有这样的砥柱了,在这个雷声大作的夜晚,任安觉得自己有些进退维谷。
唉!京城如此混乱,皇上为何还要到甘泉宫去避暑呢?
帐外传来脚步声,他抬头看去,原来从事中郎进来了。
“将军还没睡么?”
“睡不着啊!”
“一定是为京城的事吧?”
“中郎相信江充谋反么?”
“依下官看来,江充羽翼未丰,还没有这个胆量。”
“那就是太子试图借巫蛊案取代皇上?”
“太子为人宽仁,也不可能生出此等妄举。一定是江充意图陷害太子,才遭此毙命之灾。”
“那依中郎之见……”
“下官以为,在事态未明之前,北军还是不要介入为好。”
“倘若太子持节前来发兵呢?”
“我朝除皇上曾命严助持节前往会稽发兵外,就严令,不见兵符绝不可发兵。将军没有理由冒违大汉律令之险呀!”
“感谢中郎提醒。”任安终于心安下来,随即命令道,“传令北军将士,紧闭营门,一律不得外出,违令者斩!”
今晚,刘彻破例没有批阅奏章。午后,他同司马迁连下了五盘棋,以连胜四局而结束。接着,他又在苏文的陪同下登上通天台,焚香叩首,诚邀仙人降临。他不免有些累——毕竟是上了年岁的人了。
用过晚膳,刘彻便早早地睡了,很快就进入梦乡。
他晃晃悠悠来到通天台前,举首望去,台上站着一位鹤发童颜的仙人。
那仙人一看见刘彻,就轻摇拂尘道:“刘彻,到贫道身边来。”
惊异的是,他不用拾级而上,就到了仙翁身边。
仙人捋着美髯道:“难得你诚心筑了通天台,贫道才得以降临人间。果然是大汉兴盛,帝业辉煌……哈哈……”
“弟子盼仙翁若久旱之盼望甘霖,今日得见,实乃三生有幸,未及远迎,还祈大仙恕罪。”
仙翁摆了摆手道:“你有何求,尽可道来。”
刘彻又虔诚地施过一礼道:“弟子为帝嗣一事困惑,还请仙翁指点迷津。”
仙翁北望甘泉,道出一番玄妙密语:“一阴一阳,一长一短;一大一小,一兴一亡。”
刘彻越发如坠五里云雾,急忙跪倒在通天台上道:“请仙翁明示。”
“天机不可泄露。”仙翁将手中的拂尘一甩,便隐入五彩祥云中,只有洪钟般的笑声留在通天台上,久久不绝……
刘彻正待要喊,那仙翁却已不知去向,而自己却似单骑在山中行走。
枯树遮道,雾霭重重,他呼唤钩弋夫人,回答他的却是风声;他呼唤刘弗陵,看见的却是迎面扑来数千木人,手持木棍,直将他追至悬崖边上。他身下的坐骑惊恐中飞越山崖,不料却跌入深谷。刘彻大叫:“吾命休矣!”
一个激灵,刘彻醒了,他摸了摸,浑身都是冷汗。再看看窗外,除了朦胧的夜色外,哪里有什么仙翁、木人?
从殿外传来格斗声和喊声:“大胆狂徒,还不快快受死!”
刘彻跳下皇榻,“嗖”的从鞘中拔出宝剑,就冲出殿了。
透过雨雾,朦胧的夜色中,三个黑影杀作一团,那一高一矮身穿夜行衣者,一个如蛟龙出水,一个如猛虎下山,把手中的短刀舞个密不透风。迎战他们的那位彪形大汉,从鼻翼间发出哼哼声,听得出是金日磾。
虽然是面对两人,可金日磾却毫无惧色。他挥动手中的宝剑,招招紧逼,将一个黑影逼向绝地。如此酣战,令刘彻眼花缭乱,他欲上前助战,然毕竟年事已高;再看看大殿四周,弓弩手张弓搭箭,欲引待发。
刘彻大声疾呼:“不要伤了金将军!”
那黑影经这一喊,顿时分了神,被金日磾回身一剑,刺在咽喉,便重重地倒了下去。
高个一看矮个已成亡魂,自知非金日磾对手,再也无心恋战,卖出一个破绽,便回身要走。金日磾哪会给刺客机会,飞身而起,便截住了高个的去路。夜色中寒光一闪,高个应声毙命。
金日磾擦了擦血迹道:“让皇上受惊了!”
刘彻把剑插入鞘中问道:“何人如此大胆?竟敢黑夜行刺?”
羽林卫早有人将二人首级奉上,刘彻借着灯光一看,顿时惊呆了:“怎么会是马河罗、马通兄弟,他们是受何人差遣呢?”
是金日磾首先发现了刺客的踪迹。
自从随驾移到甘泉宫后,金日磾因水土不服,一日腹泻数次。皇上酣睡的时候,他腹中隐隐作痛,便急忙地向羽林卫叮嘱一番,三步并作两步朝厕房跑去……
蹲在厕中,多年养成的习惯让他注意着外面的动静。
金日磾一生最大的欣慰和幸运莫过于皇上对他的知遇之恩。在他的记忆中,自古贵中华,轻夷狄。可英明的皇上却不以种族论亲疏,对他信任有加,他相信上苍有意要他终生陪伴皇上。虽然他父亲死在霍去病的刀下,可他从未有非分之想。为了皇上,他就是舍去自己的生命也在所不惜。
就在他步出茅厕的时候,忽然看见黑影一闪,他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刺客,他没有任何犹豫,就迎了上去……
听着金日磾的奏报,刘彻唏嘘道:“板**识忠臣,朕风云一世,却不能理好宫中之事,真是愧对列祖列宗啊!”
恰在这时,苏文从暗处走来,一边喊着“奴才救驾来迟,乞皇上恕罪”,一边从怀中扯出一道锦囊,呈于刘彻面前:“此乃御史大夫自京城发来,请皇上御览。”
汉时的锦囊,类似于今日的信封,用一丝织袋子密封。
这锦囊在苏文怀中揣了多日,直到今夜见人,才煞有介事地拿了出来。
刘彻拆开锦囊,将绢书由右至左仔细看了一遍后,一双眼睛先自直了,胸中如有一块大石堵着,气喘吁吁。
从建元初年登基至今,刘彻征讨匈奴、平定西南,凿空西域、扫平大宛,早已对流血抛尸、刀光剑影司空见惯了,只是眼前这场事变来得太突然。这几个月,在钩弋夫人劝导下,他本来已经打算待十月回京后,要和太子做一次坦率谈话,谁知此刻却发生了太子派遣刺客的事件,他的精神被重重击倒了。
他虽与太子在巫蛊案上存有分歧,但是自己却是看着他长大的。他认为太子柔弱,因而无法把太子与刺客联系在一起,从情感上也无法接受太子谋反的现实。
可这密札字字如刃,直刺他饱经沧桑的心。他只觉喉咙中有一股热血朝外涌,未已,血已喷出口,长呼一声,昏厥过去了。
众人见皇上如此情景,急忙将他扶进大殿。刘彻躺在皇榻上,双目紧闭,也不说话,两道浊泪默默地顺着眼角淌了下来。
钩弋夫人自进宫以来,何曾见过皇上如此失魂落魄。她也不管周围站满了黄门、宫娥和大臣,一头扑在刘彻身上,放声大哭道:“皇上!您这是怎么了?皇上……”
“不关你的事。你暂且到偏殿休息,朕有事同众卿商议。”
“皇上,您要保重啊……”钩弋夫人泪水盈盈,一步三顾地出殿去了。
“朕自信有一双识人慧眼,却不料事出太子,朕情何以堪?宫中生此事变,朕能不忧思么?”
刘彻遂问苏文道:“长安生乱,丞相何在?”
“昨夜接到丞相飞报的奏章,言太子谋反,丞相已暂避北军大营了。”
“国有大事,他竟然回避,朕要他只是摆设么?”刘彻从榻上坐起来,要一直没有说话的司马迁草诏,命刘屈髦持虎符前往北军大营调遣人马,平定叛乱。
“传朕旨意,皇后纵容太子诛杀御史大夫,命宗正刘长乐、执金吾刘敢奉诏前往椒房殿,收其玺绶,令其闭门思过。”
“皇上!”司马迁迟疑了片刻。
刘彻不耐烦地看了看司马迁:“还迟疑什么?难道要朕亲自拟诏不成?”
司马迁退下后,苏文顺势把第二条消息告诉刘彻:“从长安来的使者说,太子在京城广贴檄文,声言皇上在甘泉宫患病,奸臣欲作乱,因此奉节发兵讨逆。”
“逆子!竟敢诅咒朕,这哪里还有骨肉之情?”
这个意外的消息,让刘彻意识到事情的严重,他不能再在此滞留。
想到这一层,他就再也在榻上躺不住了,他果断地站起来,对金日磾道:“传朕口谕,即日移驾长安,朕要亲自平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