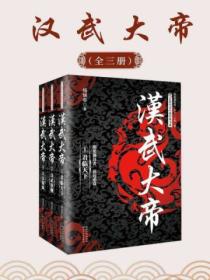第十四章 两年受降成梦影 三载远征千马回
左大都尉耶律雅汗紧紧追着前面逃跑的一只黄羊,一跑就是十几里。有几次,那猎物明明早已在射程之内,他都拦住了卫士举起的弓箭,喝令继续追赶。
跟在他后面的几位当户都不解,但还是急忙策马跟了上去。
“大人这是要干什么?他是在怜悯黄羊么?”巴尔呼当户迷茫地问着身边的乌云其当户。
乌云其摇了摇头:“我也觉得奇怪,难道大人要玩猫捉老鼠的游戏吗?”
查尔奴当户的黑马老了,总比这两位当户慢了许多,当他好不容易追上前面的马尾,就迫不及待地问道:“两位大人刚才说什么呢?”
巴尔呼笑道:“好狼从不吃陈肉,好话从不说二遍。”
查尔奴喘着气:“那好啊!我就告诉左大都尉,说你们背后妄议他。”
乌云其忙打圆场道:“我们在说大人今天不知是怎么了,眼看到手的肥羊硬是不让属下狩猎。”
查尔奴不说话了,他在心里嘲笑他们比牛还蠢,一点也不懂大人的心思。他明白,左大都尉是借狩猎的机会躲开乌师卢单于的眼线,以便商议如何归降大汉。昨夜,他只对查尔奴坦白了自己的心事。举事的日期越近,他的心就绷得越紧。
马队飞驰而过的地方,蓑草一片片倒下。
那只黄羊几度摔倒,又几度挣扎着爬起来,拼命向前奔去。它发现前面有一块突起的石头,就绝望地撞了过去。石头上飞溅出血花,黄羊**了一会儿,就慢慢平静了。
这情景,强烈震撼着耶律雅汗的心,走兽都知道宁可粉身碎骨,也不愿为人掳的道理,何况人呢?他跳下马,用马鞭拨拉了一下羊头,竟发现除了羊头顶有细小的血渍外,黄羊整个身体都干干净净的。
不知为什么,他的心头霎时有一种说不出的悲凉。
耶律雅汗命卫士抬了黄羊,他便登上高坡,眼前就呈现出一片洼地,虽然已是秋天,草色泛黄却依旧十分厚实。他很满意这地方,如果没有人泄密,谁能想到密草丛中聚集着一群密谋起事的人呢?
几位当户已跟了上来,耶律雅汗要卫队长布置好岗哨,然后就牵马下了坡。
此刻,在烈火的炙烤下,黄羊发出浓浓的肉香。烤肉的卫士每翻一次,都会向冒着油脂的羊肉上洒下各种佐料。
耶律雅汗回望了一眼四面的高地,确信安然无恙时,才对面前的三位当户道:“本官今天以打猎之名邀各位前来,是要告诉大家一件天大的事情……”
查尔奴突然打断道:“大人没发现少了一个人吗?”
原来是昨晚相约的封都尉乌尔禾吉没有来。
耶律雅汗道:“他也许是母羊下了崽,也许是猎狗生了小狗。不用等他,我们继续吧。”对乌尔禾吉他还是放心的,他看着乌尔禾吉长大,平日里乌尔禾吉也拿他当父亲看。
“大家也看到了,自乌师卢即位后,对非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的部族大肆杀伐,现在是人人自危。如此下去,匈奴会自取其灭啊!”
“谁说不是呢?昨天一次就杀了三百多人,刽子手的刀刃都卷了。”巴尔呼附和道。
乌云其从地上揪起一把蓑草,扔进火堆:“他们简直是一群野兽,不但杀了自己的兄弟,还把他们的心掏出来烤了吃。”
查尔奴听着听着,就愤恨出声来:“我的兄弟也是当户,就因为为被关起来的族人说了几句话,就被杀了……”
卫士把烤好的黄羊抬了上来,耶律雅汗从腰间拔出尖刀,狠狠地插在黄羊的腹部道:“为使匈奴百姓少受血光之灾,本官决计生擒乌师卢,然后归降汉朝。”
其实,这件大事耶律雅汗早已与他们谈了多次,因此大家并不感到意外。只是乌云其还是担心,左大都尉势单力薄,难以对呼衍氏、兰氏和须卜氏形成围剿。
“这个各位不用担心,汉皇十分看重本官举事,他于去年派遣公孙敖在漠南筑城,迎接我军,前不久又派遣赵破奴率部到浚稽山接应,如果没有差错,我的使者此时正在前往汉营途中。”
耶律雅汗对成功充满了信心,他要查尔奴将具体部署通报给大家。
查尔奴俯下身体,在羊皮上画线部署,从怎样麻痹左右屠耆王,到怎样擒拿左右大将军;从怎样争取左骨都侯,到如何包围乌师卢的穹庐,几乎都涉及了。
查尔奴道:“汉皇最嫉恨的就是伊稚斜单于杀了他的姐姐隆虑阏氏,所以我们一定要活捉乌师卢。”
耶律雅汗举起马奶酒,高声道:“为了部族,为了各位的前程,干!”
四只碗刚碰在一起,还没有来得及喝下马奶酒,突然一支飞箭过来,不偏不倚,穿过查尔奴的脖子。
耶律雅汗一个虎扑,紧紧地抱住查尔奴:“查尔奴!你怎么了……”
查尔奴睁开眼睛,艰难地说道:“大人!乌尔……乌尔……叛徒……”
巴尔呼和乌云其“嗖”地拔出腰刀,背靠背站着。他们朝四周看了看,顿时惊呆了,那里哪还有左大都尉的哨兵呢?现在全都是乌师卢的卫队,在洼地周围形成一道人墙。
从坡上传来右骨都侯耶律孤涂老迈的笑声:“哈哈哈!本侯身历三位大单于,还没有见到哪家部族举事会成功的,你们想没有想过会有今天呢?”他转过脸,要乌尔禾吉站到前边来。
耶律孤涂很鄙夷这位出卖主子的年轻人,不无讽刺地说道:“朝他们喊话,要他们上来,跟本侯回去受审。”
因为距离太远,一切都有些影影绰绰,可耶律雅汗仍能在密集的人群中,分辨出那熟悉的身影。
乌尔禾吉被两个士卒押着,看上去很狼狈,也许是心中有愧,也许是生命受到威胁,他被风吹来的喊声显得十分苍白:“义父,放下刀吧!单于已知道了你们的全部罪行,早点投降,也许还能落个活命。”
接下来是耶律孤涂的话:“给你们半个时辰,再不回头,休怪本侯无情!”
耶律雅汗没有回应,他只是觉得自己和乌尔禾吉都很可悲。
乌尔禾吉的母亲是汉人,曾在汉匈交战中被裹挟到匈奴。她不甘背井离乡,就在一个深夜,将乌尔禾吉托付给她的牧羊犬,然后自己骑马逃到塞内。
乌尔禾吉被左大都尉的夫人抱回家时,几乎没有了体温,是夫人用自己的身体救活了他。
现在回想起来,他不该给这个汉族弃婴那么多关爱,更不该将他视作亲生,而把许多举事的细节告诉他,并让他做各个当户之间的联络人。
而乌尔禾吉的可悲在于,他并不知道乌师卢单于最恨的就是背叛主子的软骨头,现在还对未来抱着幻想。
耶律雅汗狠狠地摇了摇头,把乌尔禾吉从自己情感中彻底扫了出去,他向身边的两位当户问道:“二位后悔了么?”
“草原上只有兔子才后悔,什么时候见过雄鹰后悔过呢?”
“是雄鹰就该撞死在崖壁上,而不能做了猎人的俘虏。”
耶律雅汗又向身边的卫兵问道:“你害怕么?”
“属下的父母都被乌师卢杀了,属下孤身一人,死而无憾。”
“好!拿火把来!”
耶律雅汗从卫兵手中接过火焰熊熊的衰草,先点燃了自己的皮袍,接着又把火引向两位当户,最后才点着了卫兵。
耶律雅汗借着灼热和疼痛,一把将两位当户和卫兵紧紧抱住。
他用尽最后的力气,朝着南方高喊道:“汉皇啊,请你拯救匈奴百姓吧!”
“太阳神啊!我们来了……”
他们倒地后四溅的火星,很快将洼地变成一片火海。
……
浚稽山矗立在郅居水南岸。
赵破奴的军队,在这山林中驻扎已经六个月了。
可左大都尉的军队在哪里呢?自上个月送走前来联络的匈奴使者之后,就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秋日短暂,刚刚过了申时一刻,天就渐渐昏暗了,赵破奴看了一眼血色的残阳,刚刚在中军大帐坐下,就见从事中郎带着一位浑身是血的匈奴人进来,原来就是上次来联络的使者。
他一下子扑倒在赵破奴面前道:“赵将军!大事不好了!”
从事中郎命人送来茶水,使者一饮而尽后,遂将自己的遭遇一股脑道出:“卑职奉左大都尉之命,前来报告会合地点,不料中途被单于抓住。乌尔禾吉向单于告了密,左大都尉等人被围自焚身亡。卑职在射杀乌尔禾吉之后奋力逃出,现在,左屠耆王的大军已向浚稽山而来。”
安顿好使者歇息,赵破奴的情绪顿时沉重了,他埋怨左大都尉不谨慎,不仅害了自己,也将汉军置于被动之地。
第一次独当一面,赵破奴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与过去是多么的不同,没有人为你拿主意,一切都得靠自己。
时间紧迫,已不容他召集各路司马议事。赵破奴焦虑地对从事中郎道:“传令下去,命左路司马向北,造成向单于庭进军之势,使匈奴军不敢轻易南下;右路司马向受降城方向突进;中路军跟随本官直击左屠耆王军。”
赵破奴摆出这样的阵势,就是要给左屠耆王造成汉军早已洞悉其目的、张网以待的错觉。果然,当晚左屠耆王没有大规模进攻,而只派了前锋做试探性进攻。
黎明时分,匈奴军前锋行进到郅居水南岸的时候,与赵破奴遭遇,双方在河谷地带展开厮杀。养精蓄锐的汉军士气分外高涨,中军司马与匈奴当户接战,双方大战十数个回合不分胜负。
赵破奴见匈奴当户力猛,大吼一声:“司马退下,待我取其首级!”
匈奴当户听到身后有人怒吼,一时分心,就被赵破奴挑下马去,立时毙命。
赵破奴收回长枪,观望了一下河谷地带,只见汉军已将匈奴军团团围住,喊杀声激得郅居水发出一阵阵呜咽。到了巳时,匈奴军大势已去,纷纷投降。
到这时候,赵破奴的脸上才有了活色,他对从事中郎和中路司马下令道:“事已至此,接应已成泡影,我军当务之急是向受降城撤退,与公孙将军会师拒敌。传令左路司马迅速南撤;右路司马在距受降城二百里处接应我军。”
可他没有想到,在他与匈奴军前锋激战之时,乌师卢率领的八万骑兵已将他的左路军歼灭在东撤途中,并在距受降城四百里处的丘陵地带设伏,等着他的到来。
他也没有想到,看破他计策的不是别人,而是已故匈奴骁将呼韩浑琊的三弟呼韩昆丁。他断定赵破奴一定不会北进,而必然会向受降城突进。
这是第三天的午后,草原在干旱了几个月后,天空中终于铺开了厚厚的黑云,似要下雨的样子。赵破奴率领七千余人离开郅居水岸,向东南方撤退。
秋风吹着天上的云团,自西向东涌动。赵破奴觉得那云低得伸手就可以抓下来,他的心十分沉重,眉头也挤得很紧。
在这样的天气行军,一旦下起雨来,就会面临意想不到的危险。赵破奴勒住马头,问道:“距受降城还有多远?”
从事中郎在风中展开地图,瞅了一眼回道:“照图上看,现在至少还有四百里。”
赵破奴一摔马鞭,有些急了:“严令各部加快进军,务必于明日中午前与公孙将军会师。”
在从事中郎即将离去之时,赵破奴又喊道:“命令将士提高警觉,谨防埋伏!”
傍晚时分,风越刮越大,天空飘起了小雨。从事中郎来报:“大军已疾行数百里,将士疲惫,可否休整一下?”
赵破奴立即正色道:“你是想让大军陷入匈奴军重围么?赶快加速行军,违令者斩!”
从事中郎正要转身传令,就听见雨中传来“喔嗬嗬”的声音,一阵接一阵地朝汉军涌来。
赵破奴飞身上马,朝远处眺望,只见成千上万的匈奴骑兵从四面飞驰而来,马刀汇成的丛林,搅动着雨雾。
“不好!我们中了埋伏!”
从事中郎看着滚滚而来的敌军,惊道:“将军!我们该怎么办?”
“速令中路司马率军朝南突围,能出去多少就出去多少!”赵破奴挥动着手中的长枪,一马当先地冲进了敌阵。
以八万之众对七千人马,匈奴军胜券在握,呼韩昆丁建议乌师卢单于不急于阵前肉搏,要他发挥强弩优势,轮番射杀敌人。
汉军远途而来,弓箭有限,不到半个时辰,就有一千多将士死于箭下。
敌军的用意赵破奴看得很明白。他率领数百骑,拨开箭雨,舞动长枪,把一个个匈奴弓弩手挑在地上。身后的将士被将军的气概所感染,一个个奋力拼杀,匈奴弓弩手在留下一批尸体后,纷纷后撤。
赵破奴令从事中郎挥动战旗,召唤部属朝余吾河北岸退却。
天完全黑了下来,匈奴军停止了进攻。赵破奴拖着疲累的身体靠着一棵树。他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吩咐从事中郎到河边弄些水来解渴。他喊了数声却不见回应,凭着直觉,他知道从事中郎已殒命疆场。
他又喊卫兵,只听见暗夜中传来微弱的呻吟:“赵将军!我在这里。”
赵破奴顺着声音上前抚着卫兵,天哪,他的双腿从膝盖以下被匈奴军砍掉了。
“我本农人,如今没了双腿,以后也无法苟活了。请将军给我一刀,也少了许多痛苦。”
赵破奴的心在滴血,他所带出来的将士,大部分都是农家子弟,每个人都被一大家人盼望归去。
他摸着卫兵的脸颊道:“你还是个孩子啊……你先躺着,我去弄些水来。”
可他这一去,就再也没有回来。
他刚刚把头盔伸到水里,就被从身后落下的网给罩住了……
那一刻,他的脑海里只闪过一句话:“皇上!一切都完了!”
“完了?怎么可能就这样完了呢?”刘彻反复看着右路司马的上书,似乎不相信这一切。
公孙贺道:“公孙将军从受降城送来奏章,请皇上圣览。”
刘彻看了包桑呈上来的奏章,终于相信左大都尉举义失败,赵破奴的中路军和左路军全军覆没。
“那赵破奴呢?”
“赵将军为乌师卢单于所掳。”
“公孙敖呢?”
“公孙将军坚守受降城,乌师卢见久攻不下,又怕中我军埋伏,遂向北撤退了。”
刘彻将奏章摔在案头,朝公孙贺怒吼道:“此建元以来最大耻辱,赵破奴误国。”
公孙贺闻此,便不敢此时再把来自大宛的消息禀奏给刘彻了。
其实,公孙贺压根儿就不想做这个丞相。
太初二年正月,窝囊的石庆在丞相位上度过了八年之后去世了——这是公孙弘之后唯一善终的首辅。大臣中竟没有一个人愿接任丞相的,他们不是称病请皇上赐告,就是以年迈体衰而请致仕回乡。
公孙贺在接到皇上的诏命时,跪在宣室殿里,以“鞍马骑射为官,材诚不任丞相”为由而拒受印绶,惹得刘彻拂袖大怒而去。
平心而论,公孙贺觉得赵破奴的遭遇完全是因为左大都尉举事失败所致。可现在说这些皇上会听么?他正踯躅间,刘彻又问话了。
“西边怎么样?贰师将军现在何处?”
“这……”
“这什么?莫非他也让朕在一个弹丸之国面前颜面扫尽。”
公孙贺呈上自敦煌发来的奏章,他没有说任何话,只是打量着刘彻的情绪。果然,刘彻看了没一半,就已是脸色铁青了,他对包桑喊道:“传御史大夫児宽、搜粟都尉上官桀等前来议事。”
包桑道:“御史大夫正在病中,已请告多日了。”
“难道你没有听懂朕的话么?”
包桑不敢怠慢,急忙出殿去了。
公孙贺问道:“皇上,此事要不要宣太子一同商议?”
刘彻坚决地摆了摆手道:“罢了!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朕眼不见心不烦。”
公孙贺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收住了话头,但内心已打定主意,要见一见皇后卫子夫。
半个时辰后,上官桀、児宽进了未央宫。
脸色蜡黄的児宽在两位黄门的搀扶下进了宣室殿,挣扎着要向皇上跪拜。
君臣直接进入正题,几位大臣就浚稽山和大宛之战开始商议对策。
公孙贺反复掂量之后说道:“浞野侯被俘,受降城已成为一座孤城。依臣之见,不如命公孙敖将军撤回塞内,命朔方太守和北地太守屯垦漠北,以作长久御敌之计。”
刘彻沉吟良久,不得不承认眼前这个现实:“我军新败,一时很难再图北进。传朕旨意,命公孙敖班师回京!此事一了,那么大宛之事怎么办呢?”
児宽支撑着病体,说话的声音虽然衰微,可表达出来的意思却是思虑很久的。
“皇上,臣以为……”児宽咳嗽了一阵后,继续道,“眼下……匈奴新胜,必生南下之意,臣以为……此时不如且罢了击宛之兵,专力攻胡。”
说罢,児宽就觉得胸口堵得慌。
包桑见状,忙传黄门上来捶背,半天児宽才缓过气来。可此刻,刘彻却是一脸的不悦。
“御史大夫之言差矣!大宛弹丸小国犹不能下,则大夏等国必渐渐轻汉,乌孙、轮台等则会轻慢汉使,岂不为外国所笑?”刘彻将目光投向上官桀,“爱卿以为如何?”
上官桀毕竟年轻,他很快就理解了皇上的意思,忙道:“皇上圣明!微臣以为大宛之战不仅是取马,而在于震慑西域各国。若我军中途撤回,则西域诸国必畏于匈奴,叛汉而去。”
“丞相也这样看么?”
公孙贺忙道:“上官大人所言,臣深以为然。”
“好!”刘彻的情绪,因为各位大臣与自己意见相似而好转了不少,“朕绝不容许西域各国轻慢大汉。”
刘彻的声音在宣室殿内回**,公孙贺许久没有这种感觉了:“所谓木叶将落,震而坠之。拟诏给贰师将军,朕在明年将发士卒六万,牛马无数,不拿下大宛决不罢休!”
上官桀深为皇上的磅礴气势所震动,那建功的热血顿时涌上心头,请缨道:“臣愿奉诏前往敦煌,助贰师将军降服大宛。”
“如此甚好!爱卿不日即奔赴敦煌,朕等着大捷的消息!”刘彻情之所至,言犹未尽,来到公孙贺和児宽面前道,“朕早年曾说过,兴大汉者,非少壮有力者不能为之。自卫青甥舅去后,朕许久不闻将军请战之声了。”
这话让公孙贺很惭愧。自卫青去后,中朝之首长期空缺,他实际是以将军之身而总揽中、外朝事务,却不能在关键时刻为皇上分忧。他正要说话,却听见包桑一声惊叫,大家急忙上前,只见児宽脸色发青,昏厥过去了。
“速传太医!”刘彻大声喊道。
……
敦煌在长安阳气暖渭水的日子里,还像一座冰雕,没有生机地雄踞在大漠腹地。
李广利昨夜喝了太多酒,一直睡到很晚才醒来,他简单地用了一些早膳,就坐在帐中理事:“朝廷还没有消息么?”
从事中郎摇了摇头。
他的眉头就紧蹙了:“年前就去了奏章,想来也该到了啊!”说着,他就收拾起案头的文书。
两人打马出城,在大漠上缓缓而行。他们展眼望去,南面是气势雄伟的祁连山,西面是浩瀚无垠的大沙漠,北面是嶙峋蛇曲的北塞山,东面是峰岩陡峭的三危山。
巡逻兵手持武器,瑟缩着身体在营区穿梭。
天气很冷,李广利拉了拉头上的风帽,忽然觉得自己很孤独,就像一个被抛弃在天涯的弃儿,离家是那么的遥远。
当年他是多么羡慕和嫉妒卫青、霍去病的高车巨辇,爵禄皇皇,还因此对妹妹拒绝在皇上面前举荐耿耿于怀。如今,当他跻身近臣之列,并做了讨伐大宛国的主帅后,却发现这是一爵苦酒。
当初接过主帅印绶时,他原以为大宛弹丸之地,唾手可得,可不料几个月过去了,战事却进行得如此艰难。
恳请班师的奏章去了很久,却杳无音讯?是皇上出巡不在京城,还是朝廷生变,无暇西顾……
李广利苦思冥想,不得要领。
他很羡慕他的兄长李延年,靠着乐技,就可终日陪伴在皇上身边,而自己却要吃这份苦。
唉!妹妹!你害苦为兄了。
他越是心烦,不顺心的事情就总往眼里钻。刚刚登上一面坡,他就看见一位伍长正用皮鞭抽打士卒。从事中郎上前询问,原来是这位士兵拒绝操练。
“你是王公还是贵胄,竟敢不操练?”李广利怒问道。
其实,以他的身份是没有必要去过问的,只是他心里憋得难受,要寻找一个发泄的对象。
“那么多将士为国捐躯,为何独你活着?你是贪生怕死之徒么?”
那士兵害怕了,“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祈求饶命。可李广利却越骂越生气,骂到激动处,从腰间拔出宝剑,手起剑落,那士兵血淋淋的头就在手上了。
他使劲将头扔向很远的沙堆,冷哼道:“如此贪生怕死之徒,只配喂野狗。”
他这样的发泄已不止一次了,以致后来士兵看见他,就有大难临头的感觉。
“扫兴!”
一大早就遇到这样的事情,太不吉利。他再也没有心思转下去了,便拨转马头朝大营走去。远远地他就看见军正在中军帐外等候,他刚刚下马,军正就迫不及待地上前告诉他,皇上的敕令到了。
“哦!皇上怎么说的?”
“下官还没有看。”
“哦?”李广利对从事中郎道,“快去传李哆来,就说皇上的敕令到了。”
正午的时候,李哆从十里外的军营赶来了,大家很严肃地开启了皇上的敕令。但是,李广利仅看了几行,就觉得大事不好。皇上对他久久攻不下大宛给予了严厉的斥责:“朕念及夫人,委卿重任,然卿之所为,甚失朕望。夫大宛者,西域弹丸小国,竟敢蔑视大汉,不贡汗血马,倘若其谋得逞,则车师、康居、乌孙、轮台、大夏诸国必轻汉矣……”
皇上的敕令根本没有退兵的意思,反而要继续发兵攻打大宛,大有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之势:“望卿不负朕望,攻下大宛,使西域震恐,彰大汉国威!”
看来,在攻下贰师城之前,长安是回不去了。
李广利收起敕令,对从事中郎道:“传令下去,各营加紧操练,等待援军。”
晚上,敦煌太守前来拜访,李广利又一次喝得酩酊大醉。
四月,敦煌周围的骆驼草刚露出一点绿芽,援军就相继抵达敦煌。
让李广利吃惊的是,皇上虽然人在长安,却对此次战役运筹帷幄。除主力军向西进击外,又发十八万大军进驻酒泉、张掖,还派李陵在居延、休屠两地屯兵数万,与酒泉形成夹击之势,摆出一副打大仗的阵势。
皇上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告诉西域各国——顺我者昌,逆我者亡。
皇上不仅派来上官桀助他攻打大宛,而且还派了一名执马校尉和一名驱马校尉,专事挑选良马。
军前会议由李广利主持,上官桀宣读了皇上的敕令。
李广利道:“皇上严令我军西进,现在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但西进途中,最大的障碍莫过于郁城。如何攻打郁城,不知众位有何高见?”
李哆去年就攻打过郁城,知道此城易守难攻,可一时也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因此也拿不出什么意见。
李广利遂将目光转向上官桀,问道:“大人为何一言不发呢?”
上官桀喝了一口茶水,觉得水中有一股咸味,远不如长安的水甜,但还是闭着眼睛咽进腹中:“下官初到,不明情势,因此不敢妄言。不过,下官离开长安时,皇上曾叮嘱过,用兵之道,在于因时而变。我军上次失利,是因为大宛人有备,这次就不同了,郁城守敌新胜,骄兵必然轻敌。因此,下官愿率部攻打郁城,以牵制救援之敌。”
“这样行么?”李广利犹豫道。
“下官相信皇上。”上官桀很自信。
军前会议一直开到深夜,众人商定在敦煌西分军。上官桀率领所部人马直奔郁城而去。
大军浩浩****向西进击,一路上,旌旗招展,军伍塞道,转输车马相望。果然,这次情形与上次大不一样了。所到之处,各国纷纷开城迎接,箪食壶浆。那些试图顽抗者,都遭到灭顶之灾。大军到贰师城下的时候,正是五月上旬。
安营扎寨,稍事休整后,李广利就和军正、李哆和从事中郎去看地形。
李广利勒住马头,举目望去,午后的阳光照着坐落在河谷里的贰师城,呈现出一种凝重。城不算高,全用戈壁石砌成,不要说与硕大的长安城相比,就是在敦煌这样普通的边城面前,都显得十分简陋。可它却让大汉失去了多少男儿!
对他来说,如果这次再失利,那结果就不仅仅是受到皇上的斥责了。
李广利收回目光,向身边的众人问道:“各位认为,我军该如何克敌制胜呢?”
“我军乃远征之师,不可久战。”李哆分析道。
“大人言之有理。”军正手指前方,对李广利说道,“将军请看,贰师城之所以选在河谷地带,是因为瀚海缺水。据当地百姓说,此城用水皆赖于东南方葱岭之融雪。若是我军一面从正面佯攻,另一面在城外开挖渠道,断其水源。不用数日,城中则会人心大乱,城必破之。”
“妙!我军此行目的,在夺取大宛宝马。如此蛮荒之地,我军占之无益。何况中间隔着许多小国,节制多有不便。若是他们愿意献出宝马,我军即可班师。”李哆又道。
众人各抒己见,这让李广利的思路逐渐清晰。
“好!明日一早便攻打贰师城!”他下定决心。
他们回到大营时,看见上官桀和他的军侯也来了。
上官桀看见李广利一行人,急忙迎了上去道:“下官前来听候将军调遣。”
“大人一路辛苦了。”
李广利下马步行,与上官桀一同向中军大帐走去。
路上,上官桀说道:“果然不出所料,郁城王兴桀毫无防备,在遭我军突袭后,逃往康居,而康居王闻我大军一路西指,兵锋正锐,因此不敢收留他,命人缚了送至我营。孰料,当夜他伺机逃离,被下官的军侯一剑结果了性命。”
李广利闻言大喜,连道:“郁城已破,贰师城指日可待矣。”
当晚,李广利在大营宴请各位将军,大家商定由李哆攻城,上官桀率部挖渠断水。
夜深人散之后,上官桀留了下来。卫士上了茶,两人相向而坐,李广利问道:“自大人来敦煌后,一直忙于公务,没有时间叙话,不知皇上近来可好?”
上官桀放下茶杯,话中充满忧郁:“皇上精神尚好,只是十分思念夫人。”
“唉!本将的这个妹妹,也太让皇上伤心了。”
“其实,让皇上揪心的事情还多着呢!将军不知,自大司马去后,匈奴又复南侵,为接应匈奴左大都尉降汉,皇上派遣浞野侯赵破奴率军北去浚稽山。后来,匈奴左大都尉事泄,赵将军回师时,在受降城东南遭匈奴军埋伏,赵将军被俘,除先归的右路军外,全军覆没。消息传来,皇上震怒,赵将军一世英名也毁于一旦。唉!”
上官桀平静了一下心情,接着说道:“下官的意思,想必将军已经明白。此仗我军只能胜,不能败。否则,你我必成罪臣。”
“多谢大人指点。”李广利谢道。
送走上官桀,李广利传来从事中郎:“今晚让全军提高警觉!我们一定要拿下贰师城!”
第二天辰时,李哆率部在贰师城下与大宛军展开了一场大战,双方骑兵在河谷里厮杀了半日,突然汉军骑兵撤出战斗,埋伏在高坡后的弓弩手顿时箭雨倾泻,大宛军毫无防备,死伤惨重。在城头观战的大宛国王忙鸣金收兵,从此坚守不出。
汉军每日都纵横戈壁,杀声震天,摆出一副决战的架势。不管敌军是否应战,直至日落方回营。
如此盘桓月余。这一天,上官桀风尘仆仆地来到大营。一下马,他就迅速奔向中军大帐,对正趴在案头观看地图的李广利道:“禀将军,改道之渠已经开成了。”
李广利抬起头来,来不及寒暄,就朝着帐外喊道:“拿酒来!”
“下官料定,用不了几日,大宛人必来献马。”上官桀接过卫士呈上的酒酿,一饮而尽,“下官已派重兵沿渠巡守,大宛军必不敢来取水。将军可令士卒带着水和干粮,在城下食用。城内大宛士卒见此眼馋,必然厌战。”
“大人如此妙算,此乃天助我也!如果此次大胜,也不负皇上封本官贰师将军之名了。”李广利握着上官桀的手道。让他没有料到的是,眼前这个搜粟都尉,多年后却成了皇上的托孤重臣之一。
以后的日子里,汉军对贰师城便围而不攻。每日晨曦初露之际,戈壁上马蹄如涛,旌旗映日,各路校尉在城周围轮番演阵。待到正午酷热之时,汉军只留弓弩手防敌,步军则集结在胡杨树下,喝水吃干粮。
这样的等待,对求胜心切的李广利来说,是段难熬的时光。在细作没有带回消息的时候,他甚至对继续围城失去了耐心。
他明白,军正随时都会将这里的情况报告给朝廷。他找来上官桀,将自己的担心告诉了他。
“大人说,大宛国会投降献马么?”
上官桀看着李广利,很肯定地说道:“将军请放心!下官料定两日之内必有消息。”
“军中无戏言,这可是用本将的项上人头当赌注呀!”
“呵呵!下官心中有数。”
大军西行的这些日子,上官桀就觉得这个李广利眼光短浅,患得患失,绝非统兵之才。只是以他现在的地位,不便言明罢了。
事情的发展果然不出上官桀所料。这天午后,李哆就来了,他带来了一个让李广利十分震惊的消息。
“潜入贰师城的细作回报,大宛国内发生变故,相国昧蔡与人合谋围了王宫,杀了大宛国王毋寡,现在正酝酿着献马投降呢!”
“这个上官桀,果然是料事如神啊!”李广利心头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他对从事中郎道,“吩咐下去,让执马校尉和驱马校尉做好准备。”
不过李哆建议道:“事虽如此,但为防有诈,今夜我军还应攻打外城,给敌人造成压力,促其速降!”
“有这个必要么?”
“有备无患。”从帐外传来上官桀的声音,他在听到消息后也赶来向主将祝贺。
“我军攻城,不仅要促其速降,目的还在于震慑西域诸国。我军所到之处,战未尝不胜,攻未尝不取也。”
李广利暗暗惊异,上官桀总是比自己先看一步。他心里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究竟是什么,他也不知道。可眼下他来不及多想,此刻最重要的是宝马尽快到手。他觉得,今天是决定他命运的关键时刻。
“如此则可保万无一失。今夜子时造饭,亥时攻城。本将在大营静候佳音。”
太阳将它的光芒洒到戈壁的各个角落,贰师城周围一片沉寂,远去了人喊马嘶、烽烟火光和兵戈的撞击。一夜无眠的李广利伸了伸酸困的胳膊,仓促地擦了擦脸,就见从事中郎进来了。
他喜形于色道:“李将军趁夜攻破外城,俘获大宛国大将煎靡,消息传进城中,满城震恐。这不,一大早,大宛国相国昧蔡就捧着大宛国王的人头,在营外等候了。
“真的?”
“军中无戏言。”
李广利眼里多日来第一次有了自信的光彩,情绪也亢奋起来:“快传各位大人到中军大帐来。”
做完这一切,他忽然陷入一种仓皇,好像这一切都在梦中。他似乎看见,皇上已经跨上宝马,驰骋在咸阳原上了……
走过队伍组成的长廊,走过战刀架起的拱门,坐在右首的上官桀却没有从来人眼中发现些许惊恐。这昧蔡不是等闲之辈,他立即暗示李广利以国宾之礼迎接来客。
李广利会意,率领众人迎了上去,热情地邀他进入帐中。昧蔡先将毋寡的人头献上,然后才落座开口说道:“天兵远途而来,鄙国未能远迎,请将军恕罪。”
李广利道:“本将率军前来,皆因贵国君王言而无信,实非得已,还请相国原谅。”
“本相今日前来,正为此事。尚有不敬之言,还望将军海涵。”
“相国有话但说无妨。”
昧蔡站了起来,向在场的将领们施了一礼,语调骤然严肃道:“鄙国素来敬仰大汉文明,然新王不尊盟约,致使贵国劳师远征,鄙国百姓生灵涂炭。今我等顺应民心,杀了毋寡,献上宝马,以表重修睦好之意。将军如果答应,那当然是鄙国百姓之福。如果将军不答应,鄙国将尽杀宝马,拼死一战。这样一来,恐怕西域各国都要群起而与大汉为敌了。”
李广利沉吟片刻,神情肃然道:“两国交战,原为宝马。既然毋寡已死,宝马可得,大汉自然不会再战。请相国转告贵国百姓,大汉不日将撤军。”
“如此,本相在此代鄙国百姓谢过大汉皇上!”昧蔡上前面朝大家,高声道,“诸位!从此以后,汉与大宛永结睦好,永不再战。”
昧蔡的话赢得经久不息的欢呼,大家纷纷起身,走向对方执手言和,长达三年的战争在笑声中化解。趁着这个气氛,昧蔡适时提出了要求:“为两国永久和睦,本相以为两国立个誓约为好,不知将军以为如何?”
上官桀忙在一旁道:“相国此议甚好。”
李广利也深以为然,当下就派出以上官桀与昧蔡议定誓约条款。经过半日斟酌谈判,誓约乃成,昧蔡与李广利分别代表两国盖了银印。
当晚,李广利在营中设盛宴招待大宛国众人,又回赠了玉器、布帛,直到黎明,大宛国众官才相继离去,只有昧蔡与马监留下帮助汉朝挑选宝马。
选马的仪式在城外戈壁上进行,五千多匹宝马聚集在茫茫戈壁上,远远望去,黑压压一片。李哆带着执马校尉和驱马校尉,与大宛国的马监在马群中穿梭察看。
选马一直进行了十多天,最终,一匹匹千里良驹从中选出,被送往长安,送给翘首以盼的皇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