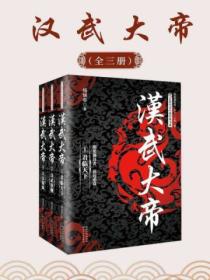第十一章 绝爱失爱各自痛 君情臣魂天地分
知春莫如鸟儿。
一轮残月还在西天挂着,太白星俯瞰大地的时候,它们已经耐不得寂寞,在合欢树的枝头“啾啾”的歌唱。那歌声清脆悦耳,传递着绵绵的深情和爱意。
鸟儿不知道人的惆怅与伤情。
李妍再也无法躺在榻上了,朝外面喊道:“紫云!紫云!”
女御长紫云闻声急忙过来,掀开帷帐,轻声道:“夫人醒了。”
李妍叹了一口气:“这恼人的鸟儿叫个不停,本宫岂能安卧?”
“奴婢这就把它们赶走。”
紫云正要朝外走,李妍却叫住了她:“还是算了!听它们恩恩爱爱的,本宫也不忍棒打鸳鸯。对了,皇上还没回来么?”
“皇上昨日就回京了,说不定一会儿早朝完了就会来看夫人。”
“哦!本宫身体为何就不见好呢?”
“夫人不必过于伤感,时逢新春,万木争荣,阳气升腾,夫人玉体必会日渐康复的。”
李妍凄然一笑道:“但愿吧!”
话虽如此,可李妍心里明白,自己这病恐怕是回春无望了。前年皇上到泰山封禅时,她的病已见端倪,她多么希望皇上留在京城,让她能感觉到他的呼吸。可皇上还是不断地出游,寻找长生不老之药。
皇上四处巡游,不要说她,即便是皇后又如之奈何?
前日卫子夫来探视时说,皇上到了零陵郡,在九嶷山上祭祀虞舜。接着又到了江都郡,登上了天柱山,并且乘船游了浔阳江,并亲自射死了江中的恶蛟,然后又折转北上,到了琅琊海边。最后,又到了泰山。要不是卫青病重,皇上大概会在甘泉宫过夏了。
李妍看着窗外那一对依偎在合欢树上的鸟儿,想起与皇上在一起的那些缠绵悱恻的日日夜夜,竟不由自主地流泪了。
她只觉得上天太残酷了。她的病是在生皇子刘髆时落下的,几年了,人也日渐消瘦,脸上的春色也日渐退去,乌黑的头发日渐粗糙,一丝丝地往下掉。
在这个妃嫔成群的深宫,女人活的是什么呢?就是春驻颜面,没有了姿色,就如敝帚一样,迟早是要情绝爱弛的。
而更让李妍伤心的是,刘髆自生下来之后,就身体衰弱,病恙不断。
开春以来,她冥冥中有一种黄泉路近的感觉。似乎有一个声音在呼唤她,催她上路。
有时候,她从梦中惊醒,就是一身冷汗。这情景,紫云看在眼里却痛在心头。
而皇上在何处呢?晨昏旦暮,日落月升,皇上只在李妍的期盼中。
紫云进宫的时候,还是个孩子。太后驾崩后,她就跟着皇后,李妍被皇上宠幸后,紫云就被任命为女御长到她的身边来了。
唉!这世间注定红颜薄命么?果真如此,那这世间也太不公平了。
看着时候已经不早了,紫云对李妍道:“皇上既然已回到京城,不定何时会驾到,奴婢这就去唤宫娥为夫人梳妆。”
李妍摇了摇头道:“不必了,病恹恹的,脂粉遮不住红颜衰去,何须枉费心力?”
其实她心里打不开的是一个结。
那是元鼎四年的事情,皇上闻听当年黄帝铸鼎于荆山,后得与神仙相通,乘龙而去,只把衣履留在了人间。他当即对跟在身旁的方士公孙卿说:“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
这话出自皇上之口,让她想起来就伤心。
紫云还想劝说李妍,但看到她坚决地摆了摆头,并顺势歪倒在榻上,就把后半截话咽了回去。
她刚刚躺下,黄门就传进话来,他的两位哥哥——李延年和李广利来了。
他们来干什么?李妍厌烦地皱了皱眉头道:“命他们来见。”
李延年、李广利带来了皇上将要驾临丹景台的消息。他们要妹妹赶快梳妆打扮,要她光彩照人地出现在皇上面前,并要她借机为他们多多美言。
听着听着,李妍就禁不住来气了:“二位兄长为何而来?是传皇上口谕,还是寻觅你等升迁之机?该如何打扮,本宫焉能不晓,何劳兄长多舌?本宫累了,想歇一会儿。”
李延年、李广利分外尴尬,他们对妹妹这样绝情很是不满,心想,早知今日,当初就不该千方百计把她送到皇上身边来。
两人刚刚转身,就听见殿外传来包桑的嗓音:“皇上驾到!”
李延年有些慌了手脚,又转身来到殿内对紫云道:“快请夫人梳妆,皇上都进殿了。”
紫云无奈地朝里面努了努嘴。李妍不但躺下了,而且还用被子蒙了脸。
李广利没有经历过这样的场面,一时间抓耳挠腮,乱了手脚:“这可如何是好!”
着急中他们听见皇上落轿的声音,接着,包桑喊道:“皇上驾到,请夫人接驾!”
李延年和李广利随着包桑的声音跪倒了:“臣李延年、臣李广利迎接圣驾。”
刘彻并不在意他们的恭谨,问道:“夫人呢?”
两人相互看了看,双双屏住呼吸,不敢说话。
紫云主动上前答道:“启奏皇上,夫人玉体欠安,还请皇上到前厅用茶,待奴婢禀明夫人,前来迎驾。”
刘彻“哦”了一声,似乎明白了什么,遂对众人道:“你等先退下,朕要探视夫人病症。”
紫云见状,忙上前轻声说道:“夫人!皇上探望夫人来了。”
李妍没有回应,紫云又唤道:“夫人,夫人……”
如此接连呼唤几次,李妍始终没有露面,却从被里传出微弱的声音:“臣妾久病在床,形容毁坏,无颜见皇上。臣妾惟愿皇上照顾好髆儿和兄弟。”
这声音让刘彻心头一酸,手抚着夫人的被角道:“朕知道,夫人久病,身上倦怠,不起来就不起来吧,夫人要托付髆儿和兄弟,那也该让朕看看你,当面托付,岂不善哉?”
李妍在被里道:“礼曰:妇人貌不修饰,不见君父,妾身实不敢蓬头垢面以见皇上,请皇上回去吧!”
隔着锦被,紫云也能感觉到李妍的痛彻心扉,不过这有什么呢?皇上既然宠爱夫人,还会计较她的病态么?
果然,刘彻又俯下身体,对着锦被里的夫人道:“夫人这又是为何呢?夫人不妨见一见朕,朕不仅加赐千金,还要封夫人兄弟官职。”
“唉!封不封官职,全在皇上,不一定要见臣妾。”
“不!朕今天就要看看夫人。”刘彻说着,上前拉开被角,可还没有等他看清李妍的面容,夫人就把头转向另一边,只是嘤嘤地涕泣,不再说话。
映入刘彻眼帘的是什么呢?
是没有梳理,已经不见当年风采的头发。
可他的性格固执而又倔强,越被拒绝,他越是要看。
可他没有想到,外表娇花弱柳的李妍竟然比他还固执,她始终只给刘彻一个背影。
让他吃惊的是,伴随着夫人的哭泣,她脖颈间的青筋清晰可见,当初的丰柔早已**然无存。
刘彻轻轻呼唤道:“夫人只要转过脸来让朕看一眼,朕也好命太医为夫人治病啊?”
李妍没有回答,泪珠儿顺着脸颊直流。
刘彻的自尊心受到了强烈的冲击,他对李妍的哭声也由刚来时心痛转为不悦:“朕自远方归来看你,你使使小性子也就罢了,可没有休止,恐怕就太不知趣了吧!朕就是再宠爱你,也不能不要面子吧?”
刘彻愤然起身,对着殿外喊道:“包桑!起驾回宫!”
随着黄门的喊声,李延年和李广利仓皇地跪倒在地:“臣恭送圣驾!”
刘彻拂袖而去,宽大的衮袖,扫在李延年脸上,热辣辣地疼。他回看丹景台时,愤怒的目光冰霜一样地拂过李氏族人的心头,让他们有一种大祸临头的感觉。
直到皇上的轿舆走出好远了,他们都没敢抬起头来。
紫云对李妍的两位兄长在心里表示了有度的鄙夷,她像是对他们,又像是对黄门、宫娥们,不冷不热地喊道:“皇上都走远了,各位是不是该起来了?”
李延年和李广利当然听得出紫云话里的意思,只是不敢发作,自我解嘲地笑了笑,跟着紫云进了殿。只见李妍躺在榻上,泪眼矇眬地朝外面看着,他们一肚子的埋怨霎时涌上了心头。
“夫人这到底是怎么了?刚才皇上要见夫人,你只给他背影。现在皇上走了,你反而转过脸来,这不是故意让为兄难堪么?”李延年气道。
“岂止是难堪,简直是目无尊长,目无皇上!妹妹见一见皇上又如何?”李广利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自己对妹妹的愤懑,说起话来也结结巴巴的,“为兄就是不明白,妹妹为什么那么怨恨皇上呢?”
紫云听着这些让夫人伤心的话,忙道:“二位大人就不要说了,究竟是夫人的病要紧,还是大人的前程重要……”
李妍欠了欠身体,那呼吸就急促了,但她还是强撑着拦住了紫云:“本宫听着呢!让他们把话说完。”可两兄弟却缄口不言了,只是暗地打量着妹妹。
“你们让本宫如何说呢?”李妍咳嗽了一阵,又沉默了一会儿,才接着用那低得只有倾耳才能听到的声音说道,“兄长焉知本宫所思啊!”
李妍说着,眼圈又红了,那积攒了多日的委屈,那在心中掂量了多日的话和割舍不下的情感,都在看着家人的这一刻奔涌而出了:“非我不见皇上,之所以如此,正是要把二位兄长的前程托付给皇上啊!兄长应知,妹妹因容貌姣好,才得以宠幸于皇上。然自古以来,以色事人者,色衰而爱弛,爱弛则恩绝。皇上之所以眷顾于我,乃在昔日妹妹之姿容。然今妹妹病重容毁,今非昔比,若贸然见之,皇上必因厌恶而弃之。如此,皇上还肯怜悯兄长么?”
李延年和李广利面对妹妹忧伤的目光,一脸的愧色。直到走出丹景台,他们都没有勇气回头再看一看病中的李妍。
“夫人!二位大人走远了。”紫云提醒道。
“哦!走远了……皇上走远了。”李妍情感的堤坝终于被悲哀冲毁,她伏在紫云的肩头放声大哭起来——她病得太久,哭声也只是细细的音律,宛若秋蝉。
跟着皇上的轿舆出了丹景台,包桑一路都在纳闷。李夫人今天这是怎么了,为何坚决不见皇上呢?而皇上愤而离去,却也不传太医来为夫人诊病。这两人怎么了?
包桑正想着,就听见皇上的口谕:“移驾椒房殿。”
包桑又摸不着头脑了。皇上已有近十个多月没有去皇后那里了,难道今天忽发恻隐之情,动了去看皇后的念头?不管怎么说,这对日渐老去的皇后来说,是件幸事。
包桑的心情顿时好了起来,朝着后面的黄门、宫娥喊道:“皇上口谕,移驾椒房殿。”
于是,轿舆转而朝椒房殿的方向去了。
包桑哪里知道,这会儿卫子夫也正在对着窗外暮春的景物而垂泪呢!
这一年来,卫子夫心力交瘁,人又老了许多。
两个公主:一个因栾大的案子至今寡居不嫁;一个因为失去了心爱的儿子一直疯疯癫癫,神志不清。这让她一想起来就泪水沾襟。
四年的时间倏忽即逝。皇上那年离京时带走了一个活蹦乱跳的霍嬗,回来却是一套空空衣冠,这成了她永远抹不去的记忆。
那次从泰山回来后,霍光不敢去见日夜思念儿子的阳石公主,只有先来拜见卫子夫。
其实,霍嬗遭遇不幸的消息,早在霍光进宫前卫子夫就知道了,只是当那一件皇上御赐的小朝服摆在面前的时候,她还是忍不住泣不成声,悲痛欲绝地呼唤道:“嬗儿!我的嬗儿!”
她几度哭昏过去,醒来时,就看见坐在榻前的霍光和秦素娟。她向霍光问道:“皇上对这件事情怎么处置?”
霍光直到秦素娟退出后才禀告道:“皇上相信方士的话,认为霍嬗去了仙界,要太常祭祀天地时,在‘五帝’旁边竖起霍嬗的神位。”
卫子夫不再说话,只是默默地流泪。她知道皇上沉醉太深,不再指望他会就霍嬗之死,给女儿一个理由。
她明白自己的身份,她必须站在皇上一边,去说服女儿相信,霍嬗遭遇不测绝非皇上的本意,皇上是嬗儿的外祖父,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因为太怀念霍去病了。
她要霍光与椒房殿詹事一起接阳石公主到她的身边,她要用母爱去抚慰她的创伤。
可是,当女儿出现在她的面前时,她却不知该如何说了。想来想去,话题还是绕不过霍去病。她回忆起霍去病少时的轶事,不厌其烦地重复那些阳石公主早已耳熟能详的故事,她越是说得详细,阳石公主就越断定母后召她来绝不仅仅是为了说这些。
“母后召孩儿来,一定另有话说。”
卫子夫凄然一笑道:“就是想和你说说话。”
“不!一定有什么事,请母后不要绕弯子,就直接告诉女儿吧!”
卫子夫明白迟痛不如早痛的道理,事情拖得越久,对女儿的伤害就越重。她从春香手里接过霍嬗的衣冠,颤颤巍巍地递到阳石公主手里:“嬗儿他……嬗儿他……嬗儿他……追随上仙去了。”
“嬗儿……嬗儿!”阳石公主一把夺过霍嬗的衣冠,一声撕心裂肺的长叫,就昏过去了……
她从此就没有再清醒过,终日生活在幻境里。
阳石公主身边的丫鬟说——她会在夜里对着窗外问,你们看见大司马和奉车都尉了么?他们就在窗外骑着马舞剑呢?他们要本宫陪他们习武呢?呵呵!你们看不见的。
她从此就没有再痛苦过,有时候睡到半夜,她会忽然地要丫鬟为她穿甲戴盔,去牵战马,说是大司马在泰山等她去救嬗儿。
她从此就忘记了公主的威仪,常常会披头散发地抱着霍嬗的衣冠,大骂府令耽误了奉车都尉上朝的时辰。
“惹恼了本宫,一刀杀了你!”公主登上车驾,看着战战兢兢的府令莫名其妙地大笑。
那笑声让大家毛骨悚然。
让卫子夫最为难堪的是,有几次在宫中遇见皇上,阳石公主竟然“去病!表兄!夫君”地乱叫,惹得皇上十分不快,把愤懑都发在了皇后身上:“堂堂宫苑,如此胡言乱语,成何体统?封了大司马府,从此不让她出门。”
卫子夫哭拜在刘彻面前,请他饶恕蕊儿的无知,怎么说她也是皇上的亲骨肉啊!
有谁能说得清楚,一个神智昏迷的公主心底的那一份酸楚;又有谁能说得清楚,妻子儿女与江山社稷,在刘彻心中的分量呢?
可怜的蕊儿。
这不!殿外又传来她憨憨的笑声:“嘿嘿!嬗儿!娘的嬗儿。嘿嘿……娘这就带你去见皇上。”
卫子夫听见这声音,禁不住又泪流不止,急忙要春香到院子里去看看。
春香跑出殿门,看见阳石公主蓬头乱发,衣衫不整,语无伦次地在那自说自话。她换上一副笑脸,软语细声地劝道:“公主呀!您让我抱抱孩子,皇后在殿内等着呢!”
“嘿嘿!皇后,谁是皇后?嬗儿才是皇后呢!嘿嘿……嘿嘿……”阳石公主傻傻地笑着,抱着枕头旋转了一圈,又低下头去亲意念中的孩子,“嘿嘿!皇后,嬗儿是皇后了!嬗儿是皇后了!嘿嘿……”
春香小心地走上前,顺着公主说道:“小少爷何其威武,来日必是大汉栋梁!”
公主笑了:“是么?他可是去病的孩子,皇上的奉车都尉,还要去早朝呢!”
春香讪讪地笑道:“公主忘记了?皇上巡视去了,尚未归来呢?公主不妨暂且回府,等皇上回来,奴婢立即禀报公主如何?”
阳石公主亢奋的情绪低落了,吻着枕头道:“嬗儿呀,皇上不在宫中,就随了娘回去吧,嘿嘿……”
公主上了车,朝驭手喊道:“送都尉大人回府。”随即,大家呼啦啦地走了。
春香进了椒房殿大殿,看见卫子夫还在那儿流泪,于是便上前道:“皇后,公主走了。”
卫子夫擦了擦眼角的泪水:“整日疯疯癫癫的,何日才好哦?”
春香劝道:“皇后何不让她进来坐坐,开导开导?”
“唉!”卫子夫长叹一声,“不是本宫无情,实在是因为皇上已回京,说不定何时驾到,看见她这个样子……”
皇后没有再说下去,但春香已猜出来了。她是怕皇上看见,万一封了大司马的府门,那不等于杀了她么?
春香想法子排解皇后的抑郁:“哪能那么巧呢?皇上来之前,总要知会皇后的。”
可这一次,皇上就是没有打一声招呼,听听!从宫门外传来包桑的叫声:“皇上驾到!”
椒房殿许久没有听到这样的声音了,以致大家一时都反应不过来,直到包桑第二次高声传话进来,卫子夫才意识到皇上真的来了。
“臣妾恭迎圣驾。”只这一句,卫子夫就忍不住泪眼婆娑,可抬起头的时候,嘴角还是溢出了愉悦的笑容。
刘彻显然还没有从对李妍的怨气中转换过来,说话的声音很重:“平身!”
卫子夫心中就打起鼓来,这又是怎么了?十个月未来,来了就怒气冲冲的。
刘彻见卫子夫在自己的对面坐下,便对包桑道:“你们先退下。”
刘彻呷了一口热茶,忍不住话就出了口:“真是气杀朕了。”
卫子夫莞尔一笑,给刘彻的盏里续上了茶水:“何人如此不知深浅,惹皇上生气了?”
“还会有谁呢?朕去看她,她竟然拒而不见!”
卫子夫明白了,皇上说的是李妍。
“李夫人一定是觉得沉疴日重,不忍皇上瞧见衰颜。”
刘彻瞪了一眼卫子夫道:“这是什么话?朕何时嫌弃过她?朕对她说,如果让朕看上一眼,就让他的兄弟为官,可她到朕走时都未转过脸来。好了,她不愿意见朕,朕从此就不再见她!”
这话放在过去,也许卫子夫会责怪李妍,可是那一天两人在病榻前谈了许久,她就知道了李妍的心思。
卫子夫看了看皇上道:“皇上能容臣妾说两句么?”
刘彻虽然没有说话,可他也没有阻止。
“依臣妾看来,皇上还是不懂李夫人的心。”
刘彻很诧异:“你说朕不懂她?”
卫子夫不紧不慢地说道:“夫人不愿见皇上,是替皇上着想。想昔日夫人姿容如花,皇上宠爱有加,如今病了,皇上看见一脸的病态,未免伤心,她是想着让皇上记住她往日的容颜呢!”
“就算是这样,可她又为何不理解朕的良苦用心呢?”
卫子夫向前挪了挪,目光充满真诚和理智:“这正是李夫人的可贵之处,她同臣妾一样,不愿意李氏族人借她的关系谋取官位。皇上想想,李夫人不干政,可是社稷之福,江山之幸啊!”
卫子夫悄悄打量着皇上神色的细小变化,眼见他脸上活泛了,就知道他听进了自己的话。
果然,刘彻低头捻须思忖了一会儿,抬头说道:“听皇后如此一说,朕也觉得委屈了李夫人。”
“臣妾不敢做如此想,臣妾只是觉得,李夫人也不容易,她可是日日夜夜盼着皇上回来呢!”
刘彻看着卫子夫,感叹岁月是那么无情,给她涂上了秋的色调,而惟一不变的是她对自己的情感。
两人眸子相撞的一瞬间,刘彻忽然生出一缕无以言说的愧意。
“那依皇后之见,眼下朕该如何处置呢?”
“李夫人这病,虽然现今日益沉重,可只要有一线生机,就该尽力救治,还请皇上能听一听秦素娟关于夫人病情的禀奏。”
“还有呢?”
“自李夫人进宫以来,虽蒙皇上宠幸,却从未为兄弟族人请官。皇上若是体恤一二,给予其兄为国建功立业的机会,这也许有益于她的康复。”
话说到这儿,刘彻的臂膀不自觉地伸过案几,握住了卫子夫的手。
“难得皇后如此宽仁,朕立即遣人处置。来人!”
包桑应声进来,刘彻要他立即知会秦素娟,午后到宣室殿禀奏夫人病情,同时要丞相和大司马到宫中议事。哦!他想起来了,大司马病了:“朕早说要去探大司马的!这一回来……”
卫子夫道:“他毕竟是长公主夫君,于此于彼都能体察圣恩的。”
“唉!朕的两位大司马……”卫青的病让刘彻又想起了霍去病。
天地尊神啊!朕一趟趟地祭祀,您为何不能赐阳寿于朕的臣下呢?
刘彻的目光暗淡了,只要思念霍去病,霍嬗之死就总是缠绕他。
“蕊儿近来好么?”
卫子夫沉默了一会儿,便按着事先准备好的话说道:“好多了,还经常念叨皇上呢!”
“哦!如此就好。都几年了,可霍光还是不相信嬗儿仙去的事实,怀疑其中有诈。”
卫子夫便不再说话,而对春香使了个眼色。
春香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奏道:“午膳已经备好,请皇上用膳。”
“呵呵!”当刘彻把目光转向卫子夫时,他被她温柔的眼神融化了。
“好!朕今日就与皇后一起进膳。”
这久违的声音,在卫子夫听来是多么的温暖。
元封五年(公元前106年)清明那天,卫青从茂陵返回京城后,就病倒了。
与其说是受了风寒,倒不如说他像一颗燃烧的星,终于在元封五年的春天渐渐冷却,甚至有了熄灭的预感。
从元狩六年到元封五年,整整十一个年头,卫青一直没有踏进茂陵邑一步。
这不仅因为他是霍去病的长辈,以长者悼念少者,于礼制有违。还因为他的心承受不了那种生命易碎的压力。
可这一次,他却不顾皇后和长公主的劝阻在清明的前两天,约了赵破奴、公孙贺和公孙敖,驱车去了茂陵。
坐落在茂陵司马道东侧的霍去病墓,自东南向西北逶迤起伏,俨然一座小祁连。
那一次,皇上没有恩准卫青的请求,而是把大战河西的机会给了霍去病。而现在,那里已设立了酒泉、张掖、武威、天水四郡。
站在霍去病墓前,卫青忽然想,假如当初是他率军西去,将会是怎样的结局呢?
卫青看见赵破奴的眼里含着泪水,他一定是想起了与霍去病一起风餐露宿的那些日子。
唉!他身上去病的影子太多了。元封三年,他奉诏进击车师国,一举俘虏楼兰王,而后又发兵围困乌孙、大宛边境城池达数月之久。他还在从酒泉到玉门的数百里边陲上修筑亭障,这是何等巨大的业绩啊!
朝廷像这样的将军不多了!
茂陵县令听说大司马来谒陵,急忙带着属下前来迎接。
皇上的陵寝,已经修了三十六年了。当年栽下的松柏树苗,如今都长成了大树。高大的松枝从高筑的墙头伸出,十分挺拔。
茂陵县令道:“少府寺依照皇上的口谕不断改进,陵高和陵体都大大地扩充了,现在茂陵已成了诸陵之最。”
这些让卫青有些迷茫,皇上一方面到处寻求长生不老药,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扩充陵墓的面积,这二者在皇上心里,究竟是怎样相处的呢?
这一天晚膳后,茂陵县令准备了美酒和佳肴招待各位。酒至半酣,大家的话就多了起来。
公孙贺问道:“请教大司马,朝鲜一仗是如何打的?”
他说的是元封三年的事情,刘彻派驻扎在山东的楼船将军与来自燕、代的左将军组成联军与朝鲜大战于湨水之上。朝鲜右渠王坚守不出,数月不下,两位将军围绕战和发生争执。刘彻见久攻不下,又派济南太守公孙遂前去节制,孰料这个公孙遂竟然取缔了楼船军。
此事上报到朝廷,卫青觉得此事事关社稷安危,奏报之后,刘彻一怒之下便斩了公孙遂。
“可惜!骠骑将军若在,定当饮马辽东,横刀朝鲜。”赵破奴遗憾道。
公孙敖将一口酒灌进肚里,长叹一声:“将军所言,亦我之感。霍将军之后,朝廷再无如此将领了。”
公孙贺接着道:“虽说两越平定,可那焉能与两位大司马相比呢?数来数去,也就只有路博德还算是从骠骑将军军中出来的,那个杨么,竟然罔视朝廷,待价而沽,实在可恨!”
卫青一直没有说话,可将军们的话引起了他强烈的共鸣。
这两年皇上起用孔瑾、桑弘羊推行盐铁官营,日见其效。大农令呈送给皇上的奏章说:“一岁之中,太仓、甘泉仓满,边余谷;诸物均输,帛五百万匹,民不益赋而天下用饶。”
可相反的是,将才却渐渐不济,作为中朝之首,他自觉责任甚大。此次皇上回京,他一定要陈奏朝廷,希望皇上下诏命各郡推举贤才。
“各位所言,也是本官所虑。皇上定会广纳贤才,我等皆皇上股肱之臣,推举良将,责无旁贷。”卫青道。
赵破奴闻此建议道:“依末将看来,侍中霍光,相貌奇伟,心胸大度,喜武知兵,颇有景桓侯之风,大司马何不向皇上举荐,令其担当重任呢?”
“大人又不是不知道,他与本官……”
卫青的话还没有说完,公孙敖就接上了话道:“自古外举不避仇,内举不避亲。大人如觉得不方便,就由下官直接面奏皇上。”
卫青点了点头。
公孙敖早已是朝廷老臣,如果由他来出面,自然少了许多是非。
夜已经深了,卫青举杯站起来对大家道:“难得闲暇相聚,喝完这爵中之酒,大家都歇了吧。”
第二天,下起了蒙蒙细雨,卫青忽然起了雨中踏青的意念。他邀集几位同行,换车乘马,披着雨丝,朝着邑外去了。
赵破奴道:“桃花雨最是入骨,大司马不比当年,还是待雨住后再外出不迟。”
公孙敖也劝卫青还是谨慎为好。
“本官自任军职以来,风雨数十年过去了,还怕这蒙蒙细雨么?”卫青说着话就出了门。
正是麦子出穗的时节,被雨水洗涤一新的田禾,显得更加碧绿葱茏。麦垄间,分布着星星点点金黄菜花,倒也有些情趣。
路过司马相如的墓时,他忽然忆起解东瓯之围时与他相处的日子,像这样的雨天,他若是同行,定会诗兴大发的。
过了司马相如的坟茔,是一田间小径,众位将军下马步行,朝着霍去病墓东南方向的一处高地走去。
登上高坡,转目西望,施工中的茂陵气势磅礴,回眸霍去病墓,与高坡遥遥相对。卫青凝视良久,忽然冒出一句话来:“此处甚佳。”
公孙敖不解道:“大司马此话何意?”
“诸位看看,这高坡西伏茂陵,北与去病墓相对,倘若本官百年之后葬于此地,岂不与去病对茂陵形成拱卫之势,也不枉与皇上君臣一场了。”
一句话说得在场的人沉默不语。
许久,公孙贺故意怪道:“大人也是,好好的踏青,却说出如此令我等寒心的话来。”
卫青很豁然地笑了笑道:“人活百岁,终有一老,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么。”
可没有想到,一回到京城,他就一病不起了。
对长公主来说,卫青的病是她彻骨的痛。那早年的爱如海潮,那天各一方的魂牵梦绕,那久别之后的绵绵依偎,甚至为儿子的前程,为与皇后之间的疙疙瘩瘩,夫妻之间发生的争吵,如今都成了温馨的回忆。
她有时候一个人坐着,看卫青昏迷地睡去,就自责自己之前太任性,太好面子,没有很好珍惜眼前这个男人。
这些日子,她几乎把所有的精力都用来照顾卫青。隔两天就传太医来诊脉问病,调整处方,然后看着翡翠煎好药,自己亲自伺候卫青服下。她多希望自己的爱能创造奇迹,重新看到夫君能出现在朝会上。
即使不能,只要他能早晚与自己一起叙话,排解寂寞,就够了。
可卫青病疴日沉,她的心事也就愈来愈重,常常彷徨地对翡翠道:“愁煞本宫了。”
她还有许多事情要办。
大儿子曹襄早早地去了。下面三个儿子因为牵涉矫制和酎金案先后被削掉了爵位,而卫伉一度还被罚修城池,她不能不为儿子的前程考虑。
儿子们再不争气,可毕竟是自己生的,又是皇上的外甥,她要趁卫青还在的时候,了却这事。
皇上一回到京城,她就进宫去了。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诉说心中的烦恼,说卫氏家族两代人为大汉江山出生入死,一个累死了,一个病倒了,若是没有他们,皇上还能率领十八万大军扬威于漠北么?她说到伤心处,声声呼唤着母后……
刘彻对这位秉性随了窦太主的姐姐,只有忍让和抚慰:“皇姐稍待,明日早朝后朕即去探视大司马。”
现在日已上三竿,长公主要府令在门口探看皇上有没有驾到。
府令刚刚走到门口,却不意撞在进府来的霍光身上,顿时灵魂都飞了,忙道罪该万死。
霍光明白,他定是受了长公主的训斥,于是宽容地笑了笑,就径直来到前厅拜见长公主。
长公主立即换了笑脸,以舅母的身份迎接霍光。眼睛却跳过霍光的肩头,朝身后打量:“皇上呢?不是要来么?”
“皇上正和丞相商议采纳舅父奏章,以解人才匮乏之急。皇上命我前来禀告公主,他随后就到。”
“看看!自己都病成这样了,还惦念着朝事。”长公主撇了撇嘴。
霍光了解长公主,也不与她计较。他来到内室,见卫青面色灰暗,形容憔悴,人已瘦得不成样子,心里霎时沉重了:“太医来过了?”
“别提这些庸医了,药吃一剂又一剂,可就是不见起色。一会儿皇上来了,一定要奏请治他们的罪。”
等翡翠退下去后,卫青无奈地看了看长公主,轻叹一声道:“你呀!就不要给皇上添乱了。太医们尽了心,是上苍不予我阳寿罢了。”
“哼!为军惜将,为病怜医,满朝惟有夫君如此柔肠。”长公主愤愤不平。
卫青摇了摇头,不再与长公主理论,却道:“为夫有几句话想与光儿单独说说,可以么?”
“好!他是你的亲外甥,有话说吧。”长公主说着,就喊翡翠扶自己到前厅迎驾。
内室只剩下卫青和霍光,他挣扎着要坐起来,霍光忙拉了锦被在他身后垫好,呼吸才均匀了些。
霍光的手扶过卫青的肩膀,他十分惊异,这还是那个决胜千里的大将军么?经历过丧兄之痛的霍光预感到,舅父也将不久于人世了。
他第一次撇开官职而用了最亲的称呼与卫青说话。
“舅父!舅父有话尽管说,甥儿一定转奏皇上。大汉不能没有舅父啊!”霍光眼里噙着泪水道。
“唉!你都做了侍中了,还如此脆弱。保护太子的重任还要你来承担呢!”卫青示意霍光在案头坐下,“舅父自知阳寿已尽,然有事托于皇上,惜哉无力,还是请光儿代笔吧。”说着话,卫青就喘了起来。
霍光忙递热茶过去,卫青喝了一口,才又说话——
大司马臣卫青上疏皇帝陛下:
臣本平阳骑奴,蒙陛下不弃,拔于末尘,臣屡沐圣恩,每思及此,感激涕零。臣子无尺寸之功,襁褓之中而得以封侯。然臣教子不严,三子纨绔,触犯律令,有负圣望,臣不胜惭愧之至。臣自知沉疴难愈,臣去之后,三子未可复爵。公主与陛下同胞情深,早年丧夫,今又孀居,还请陛下相怜,悉心关顾,臣于九泉亦含笑矣。臣生为大汉之臣,死亦魂归汉土,恳请陛下准葬臣于茂陵……
听着卫青啼血溅泪的奏章,霍光才知道这些年,他不仅活得很累,而且活得很苦。尤其是三位表弟触犯律令,成了他的一块心病。
写着写着,霍光就不由得泪水涌流,写完后,卫青看了看,盖上大司马的印玺。
“你一定要转呈皇上,我累了,休息一会。”
“如此,甥儿告退了。”
帮着卫青躺好,霍光来到前厅,却见皇上坐在那里,正和长公主说话。他急忙上前参见,并呈上了卫青的奏章,刘彻浏览了一遍,长叹一声问道:“大司马这会儿怎么样了?”
“舅父说有些累,睡了!”
“好!朕就在这儿等他醒来。”
趁着这个机会,长公主把在心中盘桓许久的请求说了出来:“臣妾不敢再提不疑和登儿的事情,只是伉儿当年矫制,乃是年幼无知,现在大司马又病疴不愈,皇上看……”
刘彻捧起卫青的奏章道:“大司马在奏章中写得明白,朕现今想来,当年要是听了他的谏言,也不至于后来……”
“当年的事已经过去了,皇上不必自责。如今卫青病成这样,皇上难道……”长公主说着话,声音就哽咽了,随口喊了一句,“母后啊!孩儿……”
刘彻最怕听的就是这句话了,忙道:“皇姐就不必再提旧事了吧,朕怎么会忘记母后的临终遗嘱呢?这样吧,待大将军醒来,朕当面与他商议之后再定吧。”
“如此!臣妾先谢过皇上了。”长公主说着,眉头一皱,又想起一件事情来,“乐坊近来又进来几位歌伎,皇上要不要看看?”
自李妍病后,宫中确没有刘彻可心的女人,他不免有些寂寞。可现在是什么时候,大司马病着,他会有此心思么?只见时候不早了,他便要霍光去看看卫青醒来没有。
霍光去了片刻,就踉踉跄跄地回来了,他声泪俱下地跪倒在了刘彻和长公主面前:“皇……皇上,舅父他……去了。”
“夫君……”这消息如晴天霹雳,长公主一声惨叫,朝内室奔去。
刘彻对惊在一旁的包桑吼道:“还不快去照看公主?”
他随之也站了起来,却有些昏厥。霍光急忙上前与黄门一起扶着皇上来到内室,只见长公主伏在卫青胸前,放声恸哭,口里声声呼唤道:“夫君呀,你好狠心啊!你怎么可以撇下我而去了呢……”
卫青面色苍白,静静地躺在榻上。
仿佛经过一场漫长的远征,他沉沉地睡去了,没有遗憾,没有痛苦,一任长公主如泣如诉的念叨。
刘彻忽然觉得很疲惫,他坐在榻上,想站起来,却使不上力。十一年前,霍去病走了;十一年后,卫青也走了。他们仿佛两座山峰,在他的眼前崩塌。
他想说什么,嘴张了张却说不出来。这可把包桑吓坏了,他上前摸了摸刘彻的手,冰凉冰凉的,他急忙喊道:“皇上!皇上!”
半晌,刘彻才缓过气来。他走近卫青,亲手为卫青蒙上了洁白的丝绢。
“大司马,朕的爱卿,朕来迟了。”
霍光看见泪珠挂在刘彻的眼角,颤巍巍的,很心酸……
两天后,刘彻下诏,谥号烈侯,葬于茂陵,起冢像卢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