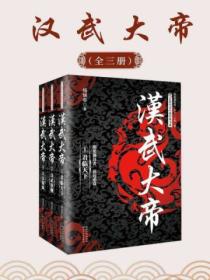第十五章 暮霭深秋残阳落 风雨关河看英杰
一年一度,春去春回。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四月间,正是长安万千芳菲的季节,但是从咸阳北原却传来了不好的消息,说是长陵的寝殿遭遇了火灾,这让刚刚重掌朝政的刘彻十分震惊。
往日大都是百官在塾门等候皇上的到来,但是今天,刘彻却先于大臣们到达大殿,并派人传太史令司马谈到宫中问话。
司马谈匆匆走进大殿,还没有等他行礼,刘彻就拿上宗室录浏览起来,眉宇顿时紧蹙在一起。司马谈记得很详细,建元元年以来的所有重大天象都没有遗漏,刘彻的目光在建元四年以来的记录上反复扫过:
建元四年夏,有风赤如血。
六月,大旱。
秋九月,有星孛于东北。
建元五年夏五月,大蝗。
建元六年二月,辽东高庙遭遇火灾。
刘彻记得,这高庙是父皇在平定七国之乱后诏令各诸侯国修建的,其意在唤起诸王渐渐淡忘的血缘和亲情。他觉得这火烧得太蹊跷,按说辽东这时正是冰封雪飘的季节,为何就忽然起了漫天大火呢?
据宗正寺和太仆寺的官员说,大火烧得很猛,供奉太祖高皇帝的大殿一夜之间化为灰烬,其他附设建筑也已成为残垣断壁。而眼前,长陵高园的寝殿又被焚毁。
“这到底是为什么?”刘彻将目光投向面前的司马谈。
司马谈很惶恐,作为史官,他明白自己的职责不仅是忠实地记录皇上的起居、朝廷的大事,还负有解释天象的责任。但如回答不慎,往往要担着身家性命,他不免慎之又慎了。
“依微臣看来,天象与人道相分而又相应。记得当年五星逆行于空时,皇上曾借用荀子的话来解释,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高园失火,臣认为纯属偶然,皇上大可不必在意。”
“是这样吗?”刘彻对司马谈的回答显然不够满意,他指着实录上的记载道,“朕之所以忧虑,是因为前年有星孛于东北后,辽东的高庙就毁于火灾。今年刚刚开春,高园又再度毁于大火。不知道是天意还是人为?‘相分而又相应’,这让朕想起了董仲舒当年在策对中的话,这是不是皇祖的在天之灵在警示朕呢?”
司马谈犹豫再三,觉得还是把天象和人事分开来说比较稳妥,他整理一下思路道:“董公之言,过于玄秘。臣记得周昭公十八年,宋国发生天灾,郑国亦惧,史官欲以宝物祭灶,祷于上天,子产闻之,言于王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臣又闻,宋襄公在位,陨石落入境,鸟退而翔,国人皆惧之,内史叔兴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由是观之,臣认为高园大火,乃天行之常,非上天谴告。建元四年以来,虽天灾频仍,然闽越臣服,东瓯围解,农桑兴国,万民安乐,皇上无须忧虑。”
话虽这样说,但刘彻的心情却没有因为司马谈的分析而有丝毫轻松。正待要再问下去,包桑进来说众位大臣已在塾门等候多时了。刘彻才收住话头,传旨上朝。
刘彻将灾变提到朝会上,固然有反躬自省的意思,但他更有一个内心深处的目的,那就是以此为据,向许昌、石建等人问罪。当大臣们站定在大殿时,刘彻的目光环顾了一下,语气重重地问道:“丞相到了吗?”其实,许昌就在面前站着,他之所以明知故问,意在强调今日早朝的不同寻常。
“启奏陛下,臣在……”昨晚,许昌即获知高园失火的消息,因此当皇上问到他时,他心里就格外紧张。近来皇上总是对他的行为多加指责,以致他一上朝,就从心底发慌。
“高园失火,是何原因?”
“这个?臣……”
“朕一问话,你就支吾其词。”
刘彻又问了石庆和石建,这兄弟俩也摇了摇头。刘彻的脸顿时拉了下来,不满道:“身为朝廷重臣,碌碌无为。高园毁于火灾,你等竟不知原因,这是何道理?这都是你等尸位素餐,惹恼了太祖高皇帝的在天之灵,以灾异谴告于朕!”
在刘彻发脾气的时候,许昌等人都耷拉着脑袋不说话,这是他们多年来养成的习惯。他们知道,任何辩解都会招来更严厉的斥责,甚至会激怒皇上而招来杀身之祸。
在将大臣们一一数落过后,刘彻宣布道:“高园遭灾,是朕之过,朕自今日起,素服五日。内史石庆,着即免职,闭门思过。”
朝堂上的风雨,有时候就是如此莫测。表面上的处罚和被处罚,隐藏在背后的往往却是智谋和权力的较量,关键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理由。如若四年前,赵绾不丢失那份要命的奏章,太皇太后就算对皇上有多少愤怨,也不会公开阻挠新政。同理,高园火灾也成了石庆被逐出朝堂的缘由。
相比之下,经过四年磨砺的刘彻,处置这些事情来,却比太皇太后高明多了。他并没有将许昌和庄青翟的职务也免掉。这样,既表明他整肃纲纪的决心,又不至于让躺在病榻上的太皇太后受太大的刺激。而他素服五日,又一次将大汉以孝立国的宗旨昭示天下。
散朝以后,司马谈又被刘彻留下,但却再没有谈灾变的话题。刘彻指着实录上的文字问道:“这是怎么回事?”
司马谈捧起竹简,见刘彻在记载他外出狩猎、踩踏百姓稼禾一处点了记号:“你这不是给朕难堪么?后人看了这些记载,将会怎样评价朕呢?”
司马谈对刘彻的问话并不感到意外。他早已从父亲口中得知,历来的国君或帝王总是希望在历史上留下自己最辉煌的、最神圣的形象,而不愿把哪怕一点污渍留给后人。但是,史家世代因袭的传统又不容许他去按照个人好恶编纂历史。
司马谈跪在刘彻面前,将《宗室录》举过头顶说道:“陛下,此乃史官之责,臣记得《礼记》说,‘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皇上一言一行,臣都要记录在案。如此,臣留给后人的才是一部信史。”
“朕自登基以来,做了那么多大事,你能保证都记录在案了吗?”
“皇上圣明,臣斗胆,倘有一件遗漏,臣甘愿领罪。”
“这么说,朕不早朝的事你也记下了?”
“皇上圣明。”
看着一脸严肃的司马谈,刘彻又问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就不怕朕罢了你的职么?”
“启奏皇上,微臣不过是六百石的小官,不要说皇上罢微臣的官,就是将臣诛灭九族,也易如反掌。然臣宁可身死族灭,也不能因文过饰非,而遭万世唾骂。臣记得圣人有云:‘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焉,过也,人皆见之;更也,人皆仰之。’历史不仅在微臣笔下,更在百姓的心中。就是微臣不书,百姓也会传扬的。”
刘彻望着跪在地上司马谈,侃侃而谈,毫无惧色,一时倒不知怎样描述自己的心情了。司马谈说得是否有理,他需要时间思考,但现在他明白了一个现实,就是对史官来说,信史如同他们生命一样重要。纵然杀了司马谈,他的儿子也会秉笔直书的。
“难得爱卿如此忠直,这本《宗实录》,暂且留在朕这里。你先下去吧!”
出了未央宫前殿,司马谈才发觉刚才与皇上一番对话,自己早已大汗淋漓了,如今冷风一吹,浑身透凉。他正要回府,却远远地望见了田蚡,看样子是刚从宫中出来。
最近不断传言,说田蚡倚仗与太后的关系,不断向皇上提出要求,甚至他推荐的人也都得到了安排。于是,很多人都纷纷投到田氏门下。司马谈一想起这些作为,就从心底鄙夷这样的追名逐利之徒,急忙转向走上去官署的道路。
“太史公!太史公!”田蚡隔着数十步远就和司马谈打起了招呼。
“呀!是侯爷呀,在下眼拙,请侯爷恕罪。”
“说哪里话?本侯现是赋闲之人,大人何罪之有?”说话间,田蚡已来到司马谈面前,语气急促地问道,“大人知道么?长陵高园失火了!”
“在下知道了,今日早朝皇上还为此素服五日!”
“皇上为什么要这样呢?这事是因为……”田蚡压低了声音说道,“这是先帝在天之灵告诉皇上,太皇太后就要寿终了。”
司马谈心里顿时“咯噔”一下,惊道:“侯爷!这话可不能乱说。太皇太后乃我朝支柱,国不可一日无她。”司马谈说着就要离去,却被田蚡拉住了。
“太史公不要走,老夫还有话说。”田蚡挤了挤小眼睛悄悄问道,“这件事太史公记录在案了吗?”
“在下的职责就是记录朝廷大事,这件事情当然也不能例外。”
“太史公说得好。不是老夫夸口,不出一个月,这事就可见分晓。”田蚡捻着胡须笑了笑,“到那时候,皇上就可以大刀阔斧地推行新制了。”说完,他就摇头晃脑地走了。
这尘世的人从来就是形形色色的。有时候,两个看似极不相容的东西就偏偏奇怪地融合在一起。田蚡就是这样,论起治学,他不可谓不精。虽不能与公孙弘、董仲舒这些“内不自以诬,外不自以欺,以是尊贤畏法而不敢怠傲”的雅儒相比,却也是说起儒家的经典就滔滔不绝。但他自己明白,要内修为“虽隐于穷阎漏屋,无置锥之地,而王公不能与之争名”、“言有类,其行有礼,其举事无悔,其持险应变曲当”的大儒是一个很痛苦的过程。故而,他更看重的是眼前利益。
不管窦婴当面贬斥他为人俗气也好,还是有人背地里骂他“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也罢,他依然按照自己的处世原则去看待身边发生的一切。现在,田蚡坐在车驾上,对高园火灾的发生表示了难以言表的暗喜。
他虽然没有到过火灾现场,但却透过那联想中的熊熊火苗,依稀看到了那扇紧闭了四年多的仕宦之门已被烧开了。他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如何通过太后阻止窦婴复出。
“回府!”田蚡向驭手挥了挥手。
而此时司马谈望着田蚡的车驾远去,直觉得一股凉气直朝脊梁袭来。田蚡的话语,他不敢多想,也不能多想,只能匆匆打道回府了。
按照父亲的安排,司马迁已经将《诗经》中的有关部分读完,刚刚伸了伸酸困的胳膊,丫鬟就来告诉他,说老爷回府了。他不敢有丝毫的懈怠,匆忙来到书房。
司马迁是最近才来到京城的。在他出生以后,父亲就将他送回家乡龙门,在祖父身边长大,他随后读完了《小学》《大学》等经书。
司马谈之所以现在将他带在身边,是想从小就培养他史官的使命和品格。因此,现在司马迁正在读的书是《中庸》,等到有了一定的积累,他就要开始读《春秋》。
“父亲回来了!”
“嗯!书都读完了么?”
“读完了!”司马迁答道。
近来他在读《诗经》的同时,也先看了一部分《春秋》的内容,他将自己不懂的问题提到父亲面前:“父亲,孩儿不大明白,按儒家为尊者讳的传统,《春秋》中有许多记载就不大合情理。”
“都有哪些方面呢?说给为父听听。”
“《春秋》中有不少臣弑君、子弑父的故事,这不是暴露国君的隐私么?如果真是这样,那么为尊者讳的传统又体现在哪里呢?”
“哦?你先坐下,为父正要和你说这个呢!”司马谈随手翻开手头的一卷竹简,沉吟片刻后道,“这是为父草就的一部分手稿,你可以拿去看看。这里面不仅记载了三代的盛世,也记载了他们的缺点甚至污点,不仅如此,我朝历代皇上的一言一行,为父都真实地记录着。你长大后是要继承这史官之职的,为父最担心的就是你不能秉笔直书,现在让你看这书稿,就是要让你记住史官的职责,你知道么?”
“孩儿明白了。”
“仅有这点还不够。再过几年,你还要到各地去游历,要实地考证史实的来龙去脉,才能承担起撰写信史的重任。”司马谈说到这里,拢了拢灰白的鬓发,“天将降大任于你,你一定要上不负苍天重托,下不负祖宗期冀,身不负太史的使命,更不能辜负了为父的一片苦心啊!”
司马迁撩了撩宽大的衣袖,那充满稚气的脸上顷刻间充满了庄严:“请父亲放心,孩儿一定记住父亲的教诲,将来写一部流传万世的信史!”
司马谈会心地笑了,上前抚摸着司马迁乌黑的头发,心头涌起说不尽的欣慰,可是这种欣慰很快就飘逝了,他想起了眼前这个孩子出生的那天,正是未央宫东阙被大火烧毁的日子,而现在他十岁的时候,高园又毁于火灾,于是心中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沉重——莫非这预示着迁儿今后的命运会十分坎坷?
司马谈抚着的手久久不愿意拿开,他向来不相信这些,可这两次灾象也太巧了!
五月,太皇太后的精神忽然好了起来。当她坐在永寿殿的病榻上追忆渺如烟海的往事时,思路分外的清晰——她想起当年与文帝邂逅在代国、一见钟情的幸福时光,蜡黄的两颊泛起难得的潮红。
宫娥们都十分惊异老人家顽强的生命力,可有人也明白这不过是回光返照,但谁也没有胆量敢将这个事实说穿。当着太皇太后的面,她们总是拣好听的说。
丁亥日早朝后,许昌到永寿殿来探望太皇太后了。对许昌太皇太后自信还是比较了解的,他虽然在任上没有多少建树,可他对黄老学说的精到,对自己的毕恭毕敬,都使得他们一见面就总有共同的话题。她相信,有许昌做丞相,完全不用担心刘彻会重启新制。
“丞相有好些日子没来看哀家了。外面都有哪些新鲜事,说来给哀家听听。”
“启奏太皇太后,皇上近来十分勤勉,只是微臣……”
“怎么了?”
“只是微臣愈来愈老迈,不能为皇上分忧,总觉惭愧。”
“又发生了什么事情么?又是那些儒生兴风作浪了?”
“这倒没有。”许昌嗫嚅了几次,都不知道该不该将高园火灾的消息告知眼前这个病中的女人。
太皇太后听出了许昌欲言又止,身体便情不自禁地成了前倾的姿势,急道:“快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看着太皇太后着急的样子,许昌便觉得她的心一刻也没有离开未央宫前殿——那座作为王朝权力象征的建筑。许昌被深深地感动了,面对这位虽然苍老却坚韧的老人,似乎任何隐瞒都是一种不可饶恕的罪过,于是他说道:“太皇太后,一个月前,长陵高园的寝殿忽然起火,皇上为此而素服五日。”许昌刚一说完,就老泪纵横,“都是微臣无能,让太祖高皇帝在天之灵不能安宁。”
不过耳边的呼唤声打断了许昌的哭声。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
太皇太后的昏厥让永寿殿内一片混乱,大家一时不知所措。许昌明白是自己的不慎加重了太皇太后的病情,他几乎声嘶力竭地喊道:“还不速传太医!速去禀奏皇上和太后。”
……
消息传到长信殿时,田蚡正与太后说话。
看着日渐衰老的太后,田蚡深为这些年姐姐生活在太皇太后的阴影下而打抱不平。
“那边……”田蚡指着永寿殿,“时间不会太久了。”
王娡看了一眼四周,低声道:“这话兄弟也只能在哀家这里说,万不可在外信口张扬。”
“那是自然。”田蚡呷了一口茶,嗓子利索多了,话也更加清晰,“臣弟此话绝非妄言。去年九月,她之所以声明不再过问朝政,非是不愿,而是力不从心了。今年四月高园起火,臣弟就断定,她将不久于人世。其实,这个朝廷也早该有气象更新的样子了,总让一个将去的人指手画脚,太后的位子往哪里放呢?”
王娡却没有顺着田蚡的意思说下去,而是感叹道:“哀家这里倒没什么,只是皇上被掣肘,委屈他了。”
“谁说不是呢?尤其是太皇太后安排的那个许昌,整日浑浑噩噩。前些日子,为了高园起火的事,他就受到皇上的严厉申斥。”田蚡不失时机地把话题转移,“那边一去,皇上肯定要对官职重新考虑的。”
这话一出口,王娡就摸清了田蚡的心思,故意淡然道:“怎么安排,那是皇上的事。”
话虽这样说,但王娡不是没有想到。而且她对田蚡的复出也有一些预先的打算,只是不便言明罢了。
“哀家要劝你,近日你的举止要谨慎些,你的所为不但皇上看不过去,哀家也是略有所闻。”
田蚡点了点头,太后的话他已经听出了八九分,进一步探道:“臣弟所忧虑的,就是那个窦婴。”
王娡正要说话,就听见紫薇慌慌张张的声音:“太后!太后!大事不好了!”
王娡皱了皱眉头,不快道:“何事如此惊慌?”
“永寿殿那边来人了,说太皇太后病危,传太后过去呢!”
王娡顾不得和田蚡说话,就向殿外疾步走去。
当王娡赶到永寿殿时,刘彻、阿娇、窦太主已先到了。黄门、宫娥把宫院挤得满满的;门外警跸全副武装,严阵以待;新任长乐宫卫尉程不识按照安排,在宫外的大街上布满了岗哨。自建元二年以来,京城的气氛从来没有这样紧张过。
太皇太后已被移往内室的卧榻,刘彻等人就在大厅等候。看见太医走出内室,刘彻便急不可待地上前询问病情。太医犹豫再三,只是叹息。
刘彻分外不悦,怒道:“到底如何?或吉或凶,都应奏明才是,你吞吞吐吐是何道理?”
太医“扑通”一声跪倒在殿前,浑身颤抖道:“皇上,微臣无能,微臣无能啊!”
刘彻见此情景就明白了,太皇太后的生命已到了最后时刻。他把目光投向内室,隔着一层幔帐,他已看不清太皇太后的面容,一时间,这些年的风风雨雨全都涌上心头。忽然,他的眼睛就潮湿了,缓缓说道:“生死有命,你不必过于自责。先站到一边去吧!”
太医刚刚站起来,许昌就对着太后和皇上跪下了,哭道:“老臣许昌,请皇上恕罪,如不是老臣将高园起火的消息禀奏给太皇太后,也不至于……臣万死而难辞其咎啊!”
刘彻闻言大怒道:“你真是老糊涂了,如此大事你怎能告诉太皇太后呢?朕恨不得……”下面的话没有来得及出口,太皇太后的女御长就出来传话让皇上和太后进去。
“朕回头再追究你的失职!”刘彻狠狠地瞪了许昌一眼,与王娡匆匆进了内室。
“祖母!孙儿来了!孙儿看您来了!”
“母后!彻儿看您来了!”
太皇太后的声音很微弱,只见她布满皱褶的嘴唇轻轻地蠕动,她握着刘彻的手已经没有了力量。王娡望着这一切,泪水骤然涌出了眼眶。她轻轻俯下身体,对太皇太后说道:“母后,您有什么话就说吧,彻儿就在您身边。”
“哀家刚才看见你祖父了,他正在灞上等着哀家呢!哀家这一生,跟随先皇文帝、辅佐你的父皇,做了不少的好事,也犯了不少的过错。现在好了,哀家就要到你祖父那里去了。”太皇太后说着说着,就觉得痰涌胸口,神志模糊,恍惚间整个身体升上了长安的空中,回头望去,那万里锦绣江山,那富丽堂皇的宫殿,那滔滔东去的渭水,那莽莽绵延的终南山,渐渐地在她的视线中模糊起来。
她深情地望着这方曾经浸透着情感、心血,倾尽了她整个生命的土地,用尽最后的力气道:“彻儿!哀家身后,就葬在灞陵,哀家要陪伴你的祖父。”
这就是一个曾经掌握着王朝命运的女人留在这个世间最后的嘱托。
“祖母!祖母!”刘彻拉着太皇太后的双手急切地喊着,“祖母!您醒醒啊!”
王娡轻轻地拍了拍刘彻的肩膀,悲怆地说道:“太皇太后已经去了。从此,一切的风雨雷电,一切的沧海桑田,都只有我们去面对了。”
在大厅里等候消息的窦太主和阿娇听见刘彻的呼喊声,一下子奔进内室,扑到太皇太后身上放声大哭:“母后!您怎么就这样走了呢?”
窦太主凄婉的倾诉从内室传到每一个宫娥与黄门的耳里。
“母后!您走了,留下妾身该如何是好啊!母后!您睁开眼睛,看看女儿和外孙女吧!”而阿娇不知道该说些什么才好,只是掩面嘤嘤的哭泣。她们的情绪很快感染了大殿内外的人们,于是永寿殿哭声一片。
王娡这时候倒冷静了,她近乎无情地听着窦太主母女撕心裂肺的诉说,她怎会听不出这哭诉的弦外之音呢?与其说她们是为太皇太后的驾崩而哭泣,不如说是在为自己今后的命运而伤情。
这哭声让王娡心中颇为不快。哭什么呢?似乎我们母子要把你们怎样似的。说到底,你不还是皇上的岳母么?你不还是当今的皇后么?王娡决不容许这种情绪再蔓延下去,她几乎是狂怒地朝着窦太主母女喊道:“不要哭了!”
永寿殿的哭声戛然而止,窦太主有些愠怒的目光与王娡对峙了片刻,就移向一边。王娡趁着大家静下来的机会说道:“如果眼泪可以唤回太皇太后,哀家情愿哭瞎一双眼睛。哀家蒙太皇太后垂爱,方有今日,哀家与太主一样悲痛。国母驾崩,天崩地裂,眼下最要紧的是,莫过于安排好老人家的身后事。”
王娡以她丰富的经验表示了对儿子的支持。刘彻发现在一片哭声中,许昌一直跪在那里没有起来,只是面前的地面被泪水打湿了一大片。
“你还跪在这里干什么?还不考虑怎样张罗丧事?传朕旨意,自今日起,诏令天下,举国致哀。宗正寺、太仆寺择定吉日,为太皇太后举行国葬。”
但刘彻这一决定,却遭到了许昌等人的阻拦。其实,他们内心也有一个恐慌,就是太皇太后这棵大树倒了,他们必须寻找与皇上亲近的机会。他们以为皇上所做的一切只不过是为了试探朝臣们的反应,而内心仍对这个曾经将新制斩断的女人有着不尽的怨恨。
许昌忽然不顾太皇太后刚刚驾崩,诸事未定的混乱局面而变得严肃执拗起来,慨然劝阻道:“皇上,国葬万万不可!”
“你意欲何为?”
“我朝自开国以来,太后的葬礼从来没有高过先帝的,如今皇上却要为太皇太后举行国丧,臣以为不妥。”
许昌的话立即得到庄青翟和石建的支持。
“丞相之言,臣等深表赞同。如此铺张,有违祖制,臣等请皇上三思。”
可是他们猜错了,他们根本不会明白刘彻和王娡提高葬礼规格的真正意图。他们是想借太皇太后的葬礼去堵刘姓诸王的嘴,去平息窦氏家族的愤懑,去淡化朝廷新派与旧派之间的裂痕。他们要借此机会,在一片哀声中营造一个和谐的氛围。
而许昌等人的行为更是引起王娡极大的厌恶,她用冰冷的目光看着老迈的许昌,怒道:“听听!你都说了些什么?太皇太后生前视你等为社稷股肱。现在她老人家的尸骨未寒,你等就如此做派,岂不让老人家在天之灵寒心么?”
“微臣不敢!”
“你们究竟要干什么?传朕口谕,速传太宗正、太仆正入宫,总领国葬事宜。”刘彻走到永寿殿门口,回过头来,望着仍然跪在地上的许昌,大声斥责道,“太皇太后葬礼由宗正寺和太仆寺直接奏朕定夺!回头再追究你等不治丧事的罪行!”
……
而此刻,一场应对战争的紧急御前会议正在南越国都番禺的王宫中举行。南越国王赵胡,刚刚举行了登基大典,就接到了闽越国大军压境的急报。
“寡人新服未满,闽越国就来进攻,众位以为如何才能退兵?”一脸愁容的赵胡将目光投向丞相。
“目前军情紧急,不容迟疑。要解这场危机,非得求助于汉廷不可。况且我国与汉廷有约,不得天子诏令,不可妄动兵戈。请王上派快马飞报,请求援兵。”
大将军上前一步说道:“丞相所言极是,不过,长安距番禺千山万水,只怕远水解不了近渴啊!依臣愚见,可一面派使者驰往汉廷求援;另一面修书给淮南王以求近援。论国力,我们虽不及闽越,但我国倚山临海,北控五岭,近扼三江,闽越要攻下我国,也不是那么容易。”
“如此看来,也只能这样了。”
第二天,晨曦刚在五岭山露出白色的时候,一队使团离开了番禺,向长安的方向疾驰而去;而另一支队伍,则沿着长江向淮南进发了。
朝廷的丧报星夜送往各地,使者在淮南相的陪同下来到寿春城东的王府街。
来自南越国的求救信让刘安一夜都没睡好,黎明时分,他终于做出决定,要上书朝廷阻止出兵。只要朝廷对南越和闽越的战争作壁上观,那朝廷就必然失信于属国,那时候……
刘安再也无法在榻上泰然安寝了,他迅速来到书房,铺开竹简,洋洋洒洒地写到:“陛下君临天下,布德施恩,天下慑然,人安其生,自以为没身不见兵革……”
太阳跃上寿春城头的时候,刘安已写完了他的谏书。他对自己这篇上书的措辞很是满意,不仅展现了绮丽的辞采和飘逸的书法,而且字里行间还潜藏着一股无形的压力。他很得意地传来刘迁和伍被,正要念给他们听,却听见王府外传来门丞悠长的声音。
“朝廷使者到……”
刘安第一个反应就是太皇太后驾崩了。他没有任何的迟疑,就带着刘迁和伍被到王府大厅迎接使者。
刘安做事向来是滴水不漏的,他面对诏书,如同朝觐皇上一样一丝不苟,诚惶诚恐。
刘迁在旁见了,心里想到:有这个必要么?又不是在京城。
更令刘迁不能理解的是,刘安在接过诏书后,竟然声泪俱下,痛哭失声:“呜呼!贤哉太皇太后,待我有如亲生,萦萦系念于怀,瀚海之恩,海枯石烂,何以忘之;慧哉太皇太后,固我刘氏社稷,辅佐三代君王,功可比天,冬雷夏雪,何以忘之;圣哉太皇太后,持黄老以立国,倡《鸿烈》以天下,相坐赐酒,教诲谆谆,天涯海角,何以忘之。呜呼!国失天柱,吾失至亲,天丧我也。昊昊上苍,何不让安代母一死……”
刘安哭着哭着,竟然昏厥在地,不省人事了。刘迁和淮南相都慌了手脚,急忙传来医者,仓皇救治。半晌,刘安才缓过气来。他躺在榻上,仍然流泪不止,对淮南相和刘迁道:“寡人心痛如绞,恐不能赴京城为太皇太后奔丧,就让世子代本王尽孝吧!”
接着,他要刘迁从案头拿起一卷竹简,说道:“这是本王为皇上新写的《颂德》和《长安都颂》,还有《谏不出兵闽越国书》,都一并呈送。国葬事急,你等速速准备去吧!”说罢闭了双眼,又是两行热泪。
朝廷使者被刘安的悲痛神情深深感动了,不免对淮南王欲步吴楚后尘的传言心生疑窦,心想:像这样一个温文尔雅、文采泱泱的王爷,怎么可能心怀叵测呢?看来是有奸人诬陷了。
使者正这样想着,刘安又说话了:“使者大人远道而来,不胜辛苦,寡人本来略备薄酒,想为大人洗尘。然太皇太后驾崩,寡人心痛难忍,就不奉陪大人了。就请国相奉陪吧!”
使者安慰道:“王爷如此,太皇太后在天之灵必然安宁,还请王爷节哀。”
不几日,刘迁到达长安。各诸侯国奔丧的藩王或使者一时云集京城,人数之众不亚于十月的朝觐。刘迁秉承刘安的吩咐,并没有立即进宫去朝见皇上,而是暗地先回了淮南王在京城的府邸。
刘迁十分吃惊,当他在王府里看到妹妹刘陵时,怎么也不能将之与四年前那个小姑娘联系在一起。她不仅出脱得如芙蓉般俏丽,目光中也多了京城女人的风情,言语举止都俨然京城皇家公主的做派了。
在这里,兄妹间说话便不像在刘安面前那样拘谨,提起父王接到朝廷丧报时的情景,刘迁便觉得好笑,打趣道:“不就是一个老女人么?又是顿足,又是捶胸的。”
“兄长知道什么?此正是父王谨慎缜密之处。父王对世事洞若观火,岂能动辄怒形于色。你以为父王真的在哭太皇太后么?呵呵,那一切都是做给当今皇上看的。”
“妹妹不提倒罢了,一提这皇帝,为兄就更加大惑不解了,难道他真如此令父王害怕么?”刘迁问道。
谈起京都的职官,刘陵了如指掌,谙熟在胸,尤其是对当今皇上的印象,竟然与父王的判断如出一辙。
“父王是对的,这个刘彻万不可小视。太皇太后专权那几年,他能忍别人所不能忍,又能及时抓住机遇,逼太皇太后退却,就足以证明他不好对付。你不要看刘彻对父王很是看重,依我观察,他对淮南国十分警惕,连睡觉都是睁着一只眼睛看着的。兄长敢说,你进京不会被朝廷监视?”
“照小妹这样说,父王只能寄人篱下了?”
“目前只能取悦于上而暗流于下。国葬结束,你得速速离京,不可久留!”刘陵的果断让刘迁不知所从,半天说不出话来。
不日,刘迁向皇上呈送了《谏不出兵闽越国书》等几篇奏书,特别是他的《哭祭太皇太后》,听得守灵的诸王和大臣们泪如雨下,哀声一片。连刘彻一时都无法判断那些断肠的话语究竟几分是假,几分是真了……
一个权倾一时的女人永远地躺在了孝文皇帝身边。
国葬的规模十分盛大,京城和各国的诸王、官员数千人出席了葬礼,这是宗正寺和太仆寺按照刘彻的旨意精心安排的。送葬的队伍从灞陵一直排到长安近郊,白色的荆幡和旗帜搅得周天寒彻,似乎这个六月蒙上了隆冬的惨淡。刘彻借此不但对王朝的承前启后有了一个交代,而且还从内心深处抹去了那段曾经让他郁闷、压抑的岁月。葬礼结束的时候,他回望坐落在白鹿原畔的灞陵,心中忽然有了一种解脱的轻松。
许昌、石建和石庆因阻拦国葬的行为为刘彻整顿朝纲创造了一个契机,他以“丧事不办”的罪名免去了许昌、庄青翟和石建的职务。
又是秋风飒飒的九月。
刘彻要考虑的是,谁来接替丞相和御史大夫的职务。可是一涉及这些,他很快又与王娡之间发生了冲突。这一天,王娡召刘彻到长信殿,就丞相一职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哀家以为,眼下丞相的最佳人选莫过于田蚡。”
“舅父?”刘彻坚决地摇了摇头,“他不合适。无论是能力还是品格,他都不能胜任。”
“许昌昏庸,窦婴老迈。皇上看看朝野,还有谁比田蚡更合适的呢?田蚡再不好,他也是哀家的兄弟,你的舅父。他总不会与皇上离心离德吧?皇上推行新制不就是要以儒立国,以儒治国么?田蚡精通儒术,正合皇上的意图,不用他又用谁呢?”
“论起儒学,他远不及严助精通。”
“严助只是一介书生,难当宰辅重任。”
“论起人品,他远不及韩安国忠直刚正。”
“可韩安国资历尚浅,还需历练。”
“照母后说来,朝廷内外便只有田蚡一人当之无愧了?”刘彻站起来,在大殿里走起来,脚步带起的风吹动了殿内的纱帐。
“虽说历来有‘内举不避亲’的常理,可母后总该推举那些德才兼备者才是,像田蚡这样……”
“这些哀家都知道。”王娡制止了刘彻的发泄,她的语气也缓和了许多。
“皇上说的这些都对。可田蚡还有哀家,还有皇上管着呢,他再怎么样,也不敢拂逆皇上的旨意吧!”
“当年他做太尉时,母后也是这样说的。”刘彻反驳道。
王娡知道,今天他们怎么说也不会出结果了。于是她婉转地说道:“哀家有些累了,话就说到这儿吧,孰轻孰重,皇上细细想想,自然不难明白。”
刘彻心里当然明白,他首先还是把丞相的人选定在窦婴身上。这一天早朝后,他留下韩安国,要他登门请窦婴再度出山,辅佐自己重启新政,共谋大汉中兴。他认为只有韩安国才能出于公心,准确地转达他的意思。
果然第二天,韩安国就带来了窦婴的上疏。窦婴在疏里对皇上重启新政满怀希望,对皇上再度召唤他出任丞相百般感激。不过涉及丞相一职时,窦婴却是这样说的——
臣闻天子三公,诸侯一相,大夫擅官,士保职,莫不法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论德而定次,量能而授官,皆使其人载其事而各得其所宜。上贤使之为三公,次贤使之为诸侯,下贤使之为士大夫,是所以显设之也。故明主有私人以金石珠玉,无私人以官职事业。《书》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择。”新政以待重启,百废以待重兴,必赖才俊新秀,良骥少壮。陛下不以臣愚钝而厚遇之,臣铭感皇上隆恩。然臣以衰朽残念,羸弱之躯,而居于阁僚之首,立于陛下左右,于国无益。让贤荐才,论德任官,乃尧禹大治之故。燕相灌夫,中直刚勇,主三军必胜任;中大夫严助,贵名而不比周,求实而不夸诞,积德而遵道,乃丞相之才;大司农韩安国,虽治申韩,然则内足使以益民,外足使以拒难,民亲之,士信之,上忠乎君,下爱百姓而不倦,乃御史大夫之用也。臣祈皇上隆礼至法,尚贤使能,才技官能,使德厚者进而佞说者止,贪利者退而廉节者起,公道达而私门闭矣……
这一番至诚之词,让刘彻十分感动,他默然良久,问道:“韩爱卿如何看待窦婴的奏章?”
“魏其侯之言,至忠至诚。三公之任,不可不慎。”
“爱卿以为田蚡做丞相如何?”
皇上这样一说,韩安国立即悟到此事定非皇上所愿,皇上向来不待见自己的这位舅父,多次当着大臣们的面责备他,这是朝野尽知的。这必是太后的意思,这下就难了。帝后不和,受损失的将是新政,而南越国事急,不容久拖不决。
他当然不会忘记,当初自己复出时田蚡百般刁难,然国是惟大,岂可以私废公。想到这里,韩安国道:“臣以为,目前武安侯出任丞相,未尝不可。臣闻术者,因任而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故校之以礼,而观其能安敬也;与之举措迁移,而观其能应变也;与之安燕,而观其能无流慆也;接之以声色、权力、愤怒、患险,而观其能无离守也。彼诚有之者,与诚无之者,若白黑然,皆在皇上。”
是啊!用人之掣肘在太后,而驭人之术在朕啊!这个韩安国何其聪颖,他不点破帝后之间的龃龉,却把一切都看得明明白白。好!若是田蚡出任丞相,那是非让韩安国任御史大夫不可。
大臣们期待许久的职官任事,在建元六年六月终于尘埃落定了。田蚡任了丞相,而刚刚入朝两年,因在兴农务本方面显露出过人才华的韩安国也拟任御史大夫。
之后,刘彻顺理成章地把出兵闽越的议题提上了朝会。早朝时,刘彻面对群臣,把刘安呈送的《谏不出兵闽越国书》弄得哗啦啦响,犀利的目光掠过每一个大臣的额头,洪亮的声音在未央宫墙壁间**起阵阵回音。
“闽越国屡次违背誓约,前几年发兵东瓯,现在又入侵南越。此乃目无朝廷,以强凌弱之举,朕欲遣王恢出豫章、韩安国出会稽以讨伐之。然朕的这位皇叔却上书朝廷,说‘越,方外之地,被发文身之民也,不可以冠带之国法度理也。’说‘三代之盛,胡越不受正朔,非强勿能服,威弗能治也’。说‘不居之地,不牧之民,不足以烦中国也。’这都是些什么话?难道南越不是我大汉的国土么?南越之民不是我大汉的子民么?众卿说说,难道朕不该发兵?”
刘彻将奏折掷之案头,将目光聚在田蚡身上,问道:“丞相以为如何呢?”
田蚡没有想到刘彻会让自己首先说话。昨夜,妩媚而又**的刘陵又一次约他到淮南王府邸。虽然说这已不是第一次,但当他面对灯下刘陵的胴体时,还是不由得血脉贲张,而她却在他最兴奋的时候提出了要他设法阻止皇上出兵的要求。
“父王已向皇上上疏,建议不要出兵闽越,大人还要多在皇上面前进言劝阻。”
“皇上的性格你又不是不知道,他恐怕……”
“妾身不管,妾身就要大人说话。”刘陵扭动着身躯,把一种滑腻的感觉传给田蚡。
“要是皇上不答应呢?”
“那我……那我就把大人的胡子一根根拔下来,给院中的蟋蟀挽个笼儿。”刘陵睨斜着田蚡,就揪下一根发黄的胡须,疼得他直咧嘴。
“哎呀!小乖乖,你轻点,疼死老夫了。”
可刘陵却不管这些,自顾自道:“还有,就是把大人与妾身的事情告诉皇上,那时候……”
“好!好!好!别闹了,老夫答应你就是。”田蚡精疲力竭地趴在刘陵身上。
但现在看皇上的态度,他作为丞相还能唱反调么?他早已从王娡那里获知,他这个丞相做的不容易,他不能拿着头上的冠冕当儿戏。想起建元三年就因为反对皇上出兵救援东瓯遭到了批评,他觉得这一回再不能模棱两可了。他眨了眨小眼睛,很快就做出了支持皇上出兵的选择。
“皇上圣明!闽越多行不义,天怒人怨,我军师出有名,必将震慑南疆,安抚黎民,振我国威。”
田蚡一表态,朝臣们也都纷纷跟上来了表示,皇上出兵乃是张正义之举,行济弱扶困之道,上顺天意,下合民心。
韩安国顺势道:“皇上出兵讨伐闽越,其意不仅在匡扶正义,而对岭南诸国更是一个警示,在我大汉统治之下,决不容许有以强凌弱,逆天乱国之举。”
严助也出列道:“韩大人言之有理。待战事平息后,臣愿作为使者,出使南越,传达皇上圣意,使他们各自守土安邦,效忠朝廷。”
王恢慨然道:“臣愿率军出豫章、越五岭,南下驱敌。”
韩嫣此刻也道:“臣以为,皇上出兵的深意还在于给那些心怀叵测的诸侯王一个警告。因此,微臣奏请皇上,在二位将军离京之际,应举行盛大的出师仪式,宣读讨伐檄文,以示大汉一统,乃朝廷国策。”
“韩大夫所奏正合朕意。”刘彻环顾了一下丹墀内的大臣们,语气雄浑地说道,“朕那位皇叔不是说对胡越威不能治么?朕就是要天下人都知道,大汉之威无所不及;他不是说文身之民不可以冠带之法度理么?朕就是要让我中国的文明如日月之光,照耀大汉的每一寸土地。”
接着,他话锋一转:“不过淮南王有一点说对了,就是天子之兵,有征无战。讨伐不是目的,目的是要宣我大汉国威,让世人都知道,四海之民,皆为汉臣;大汉之恩,泽被万世!”
“司马相如呢?”刘彻的目光在朝臣中搜寻着司马相如的身影,“这个檄文就由你来拟就吧。”
“臣遵旨。”
在司马相如入列后,刘彻情绪高昂地站了起来,他目光炯炯,脸上洋溢着踌躇满志的气息,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高声道:“众位爱卿!出兵闽越,不过是一个序曲。内正朝纲,外御匈奴,革故鼎新,百业待举。大汉正处在治国兴邦的紧要关头。朕决意从明年起,改元元光,再举贤良,广纳人才,重启新制……”
刘彻洪钟般声音振**着每一个人的耳膜,大臣们因此而倍感振奋。九月的阳光,透过淡淡的云彩,洒在宽阔的司马道上,清爽的秋风吹动着宫阙上的旗帜,而宫外安门大街上的金菊,正以它炫目的金色和浓郁的芬芳为王朝新纪元的到来献上如意和吉祥。
而此刻,距太皇太后还政正好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