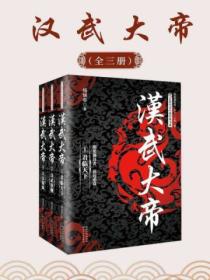第十四章 龃龉始觉心隔远 佳气天赋麒麟情
第二天,卫青举行军前会议,商议对苏建的处理。令他没有想到的是,要求严办苏建的,不是朱闳,倒是议郎周霸。
“大将军自领军以来,未曾斩过裨将,以致有赵信投降匈奴之举。而今苏建单骑而归,依律当斩,请大将军不要姑息,这样才能树立军威。”
朱闳立即反驳:“议郎之言差矣!兵法云: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战之,敌则能分之,少则能守之,不若则能避之。胜负不仅取决于士气,还取决于敌我力量的对比。苏将军以数千之众当数万之敌,已属罕见,单骑归来,更见忠心。因此,下官认为不当斩。”
“军正大人所言甚是。如果对苏将军处以极刑,势必冷了将士们的心,将来处于危机之中的将军们谁还敢回来呢?”身为长史,任安在军中的地位仅次于卫青,他的话无疑对苏建的命运有举足轻重的作用。
但卫青想得更多的是,作为三军主帅,自己应该对这场失利负什么责任。如果不是自己轻易答应了赵信的请求,也不会将这三千将士交与他。斩了苏建,无异诿过于人,这不是他的秉性。
想到这里,他站起来向大家拱手道:“各位对朝廷的忠诚让本将感激不已。议郎劝本将斩将明威,此意离本将初衷甚远。虽然‘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然本将之意,还是等回京面呈皇上,由皇上定夺为妥,不知众位大人以为如何?”
卫青的一番坦诚直言,在众人心中引起了不同回响。周霸虽以为他过于谨慎,却也没有再提出异议。至于朱闳与任安,更是为卫青的慎微和慎行而赞赏。
看大家没有不同意见,卫青遂做出决定,待班师回京请皇上定夺。
虽然卫青派公孙敖沿着赵信、苏建的路线追寻匈奴主力,但他内心十分清楚,因为赵信的投降,汉军已失去战机。他之所以摆出这种架势,也是为了迷惑敌人,稳定军心。
现在让他唯一牵挂的就是从云中出击的霍去病,每天坐帐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向李晔询问他的归程。
军前会议后的第三天早上,任安兴冲冲地来到中军大帐禀告:“霍去病所部大胜而归,估计今日可以到达,李晔已经率大营卫士前去迎接了。”
“回来就回来了,还迎接什么?”
“大将军为何如此?少将军以八百骑斩首两千二百余人,我军伤亡甚微,下官以为应当摆宴庆功才是。”
“年纪轻轻,正当建功立业之时,不可纵容他。”
“论功行赏,乃汉军之规,也是皇上一贯的主张。大将军为何因噎废食,顾虑重重呢?”
卫青放下手中的战报,站起来望着帐外,对任安道:“长史所言,本将不是没有考虑过。然为臣之道,在于有自知者明。本将自任将军以来,虽事事小心,处处谨慎,可在朝野不少人眼中,仍然以为本将之所以有今日,乃因皇后之故。倘若再不谨慎,大肆铺张,宣功邀赏,难免授人以柄。长史与本将相知有年,此种苦衷,想是不难理解的。”
“下官明白了!”任安向卫青拱手致意,一时无言以对。但他还是以为,像霍去病这样的将才若是冷落了总是不妥,于是提出由他出面,稍事庆贺。
卫青很感谢任安的热心,谢道:“不必了。霍去病是本将外甥,还是由本将为他操办吧,费用从本将的俸禄中支取,长史若是没有其他的公务,也过来一起开怀畅饮吧!”
“大将军戎马倥偬,你们甥舅见面也不容易,下官就不打扰了。”
可就是这样的甥舅小聚,也延宕了数日,直到公孙敖的人马归来才得以实现。
公孙敖很沮丧,他一路追击到颓当一带,也没有见到伊稚斜和赵信的影子,无奈只有退兵而还。
这本在预料之中,卫青丝毫没有责怪公孙敖的意思,他能将一万汉军全部带回,这就是功劳。
时序进入七月,边境出现了数年来少有的平静。于是卫青召集云中、定襄、雁门三郡太守和中部都尉、东部都尉参加军前会议,决定大军择日起程,班师回京。
各路将领散去后,卫青留下公孙敖和霍去病小聚,他吩咐下面备了小菜和酒酿,就在大帐内小酌。
公孙敖举杯向霍去病庆贺:“少将军风华正茂,英才初显,一战而斩匈奴首虏过当,可喜可贺!”
霍去病忙起身答谢:“末将受皇上垂爱,舅父栽培,才得有小胜,何足挂齿?请将军共饮此爵!”
随后他又斟满一爵酒,面向卫青说道:“甥儿能有今天,舅父恩泽如海,请舅父饮了此爵!”
卫青举起酒爵,蓄积多日的话都化为舅父对外甥的慈爱,但话一出口,还是有些含蓄。
“制胜之道,在于天时、地利、人和。你之所以能够以少胜多,首先得益于长期在侍中供职,耳濡目染皇上雄才大略,才有所长进;其次,胜在天时,虽说东线战事,出师不利,损失了三千人马,但他们以三千之众牵制了数万敌军,为你赢得了战机;其三,胜在地利,你出兵之地乃匈奴老者居住之地,兵力薄弱。加上张骞随军,知水草处,军得以不乏。故而此役之胜,非你一人之功。本将且饮你一爵,但你不可骄矜自恃。”
霍去病没有想到,卫青接下来的话却含着尖锐的批评:“兵法云:故兵贵胜,不贵久。可你孤军深入敌境两千里,此兵家大忌,你年轻气盛,于为将之道还远矣。”
“这……甥儿倒没有……”霍去病咽下了后面的话。
要真正理解卫青的话,还需要时间。年轻的霍去病知道,云中之役拉开了他军事生涯的序幕,他将从这里开始,用他的青春,用他的战刀去刻画大汉的锦绣江山。
……
大军回到长安,已是八月了,朝廷的封赏很快就下来了。
霍去病以斩首虏过当,俘获甚多而取了头功,敕封为冠军侯。
张骞因熟悉匈奴环境,为霍去病速胜创造了机会,被封为博望侯。
上谷太守郝贤,先后四次跟随卫青出击匈奴,又在这次定襄大战中再立新功,被封为众利侯。
卫青因赵信投降、苏建获罪而没有加封,但刘彻还是赏赐了千金。
对个人的荣辱,卫青看得很淡,但他却十分关心苏建的命运,他多次向皇上陈奏原委,终于使他开了天恩,免去了苏建的死罪,使之得以赎为庶人。
从宣室殿出来,卫青直接乘车回了大将军府,他为自己没有得到封赐而庆幸,这样一来,他不用再为三个儿子而背上太多的压力。
现在,他可以卸去盔甲,陪长公主很休闲地度过这段平静的日子了。
卫青的车驾缓缓行驶在尚冠街上,他远远地瞧见大将军府的门楼,心中就满怀回家的温暖。
自从被授予大将军印信后,皇上就指派少府寺扩充了府第,现在这里已是修竹茂林、花木扶疏、曲径通幽的住所。他期待自己在京城的这段日子,谁也不要打扰,让他有时间与妻儿尽享天伦之乐。他也好借这个时间读一读兵法,好好总结一下出征以来的经验。
还好,门前没有车马的影子,卫青舒了一口气。他进了府门,就看见长公主带了丫鬟们正在院内赏菊。
长公主抬起头就看见了一身朝服的卫青,她脸上立时笑意盈盈,忙对翡翠道:“快为大将军沏茶。”
“他们呢?”
“夫君是说不疑他们几个?这不!今日秋高气爽,他们闹着要去郊游,本宫让府令和骑奴们护着他们出城去了。”
卫青的眉头一皱:“不疑已经不小了,皇上像他这样大的时候,早已在思贤苑中读书了。”
“他们都还是孩子嘛!看看朝廷那些王公子孙,哪个在这样的年龄不是在玩耍呢?”长公主不以为然地笑了笑。
卫青与长公主席地而坐,他接过翡翠递过来的茶水,喝了一口道:“将门之后,如果成了纨绔子弟,如何对得起皇上的恩典啊?”
“大将军还记着那件事啊?”
因为给儿子求封,他们夫妻之间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冲突,直到出征定襄也没有云开雾散,中途长公主虽然托霍去病带了信,可现在看来,那横在他们之间的心结依旧没有打开。
长公主就是不明白,作为父亲,卫青为什么就不能替儿子们着想呢?但现在,她只想千方百计淡化这些,她珍惜的是他们之间难得的相聚。
“本宫往后对他们多加教诲就是。”
长公主的柔情在卫青的脸上停留了许久,说话时眼圈就红了:“看看!一仗下来,人又瘦了许多。司马相如常说,久别胜新婚。你这是怎么了,刚刚回来,就批评儿子……”
“好了!过去了就不说了。”卫青的表情开朗了很多。
其实,女人是很容易满足的,就是长公主这样的皇家贵胄,也一样对男人的爱有着期盼甘霖一样的焦渴。她要翡翠准备酒菜,她要把几个月来的每滴思念都注进浓浓的酒酿里……
夫妻间的叙话,没有任何禁忌,从府中的大小变故,到前方战事的惊心动魄;从霍去病脱颖而出,到朝廷对有功将士的封赏,无拘无束,话随心走。
说到没有加封爵禄,只赏赐千金,长公主就为卫青打抱不平,声言改日要进宫面见皇上,讨个说法。
卫青用淡然抚平了长公主的愤懑:“倘若如此计较,那长眠在边塞的三千士卒又该如何呢?不管怎么说,皇上没有追究用兵的失误,已属万幸。想想那些失去亲人的百姓,我就非常不安。”
“夫君总是这样小心谨慎。”长公主嗔怪道。
卫青除了报以宽容的憨笑,没有再说什么。她毕竟是皇家的长公主,当今皇上的姐姐,他不能不顾及她的这个身份……
卫青斟满一爵酒谢道:“我不在的这些日子,夫人为府上诸事操劳,请夫人饮了此爵。”
长公主急忙举爵应道:“夫君劳苦功高,应当本宫先敬才是。”
两人相互推让,晶莹的酒酿顿时洒到了衣襟上。长公主投给丈夫的目光,星星点点间都**漾着柔和,生怕一不小心,眼前这个男人就丢了。
“夫君,你我永远就这样该多好啊!”
“呵呵!那哪能呢?我还是皇上的人啊!”
太阳的金线拉着婆娑的竹影淡淡地涂在织锦的幔帐上,长公主望着西斜的太阳,多希望上苍赐予她一条纤绳,系住这流逝的光阴,把这卿卿我我永久地留在身旁。
卫青怎能读不透长公主的心思呢?他当下就道:“我今日已谢绝一切应酬,一心一意地陪着夫人。”
长公主闻言不能自持,不由得越过案几,依偎在卫青的怀抱里。
可他们谁也没有想到,一个偶然的话题,就让这缠绵的气氛从身边流走了。
长公主借着酒意说给一个让卫青十分不解的消息:“夫君知道么?皇上最近要为王夫人庆寿,大臣们都纷纷张罗着送礼呢!”
“朝廷财力不是很紧么,皇上还不得不诏令郡国买武功爵和令民赎禁锢呢!是谁又在皇上耳边吹风呢?”
“国家财力再紧,难道还没有给心爱女人庆祝寿诞的钱么?”
“王夫人春秋尚富,年不过二十一二,过什么寿诞?”
“那是皇上的事了,做臣子的只要顺从就行了。”
长公主隐瞒了一个环节——那就是她向皇上谏言要为王夫人过寿诞的。她当然不会告诉卫青,这不过是她向卫子夫一连串报复和示威的筹谋之一。
长公主从卫青的怀抱中坐了起来道:“皇上不是赏赐了夫君千金么?本宫的意思,不如从中拿出五百金作为贺礼。”
“这是什么话!”卫青推开长公主,吃惊的目光反复地打量着这个刚才还温情脉脉的女人。
“怎么了?有什么不妥的?”
“不行!它是皇上的赏赐!每一钱都浸透着边关将士的血,岂可用做后宫夫人的贺礼呢?用将士的血去为一位夫人庆寿,我做不到。”卫青紧紧抓住长公主的胳膊。
“放手!”
长公主挣脱卫青,那种带着讥讽的冷漠和傲岸,自内向外从每一个句子中散发出来。
“什么将士的血?那是皇上的恩典!王夫人寿诞,朝臣们还怕送不进去贺礼呢?夫君倒好……左一个将士,右一个将士……难道大将军有今天,仅仅是因为将士么?”
“别人怎么说我并不在乎,夫人你总该知道我为大汉江山,出生入死……”
长公主转过身来,话语益发尖酸刻薄:“大汉将军如雨,谋臣如云,哪一个不是提着脑袋走上疆场的?若没有了本宫,没有了皇后,夫君就是用十颗脑袋也挣不下这个大将军的地位。夫君不要以为有了皇后就有了靠山。有道是花无百日红,以色事君,色老而爱尽。古往今来,哪个皇后不是这样呢?”
卫青终于明白了,他不仅是公主的丈夫,而且还是她的臣子;他不仅是大汉的将军,更是她恩赐的对象;他头上的冠冕不仅染着将士们的鲜血,更闪耀着皇后的光环;他在战场上号令三军,却对一个皇家女人无可奈何。他找不到排泄愤懑的方式,胸口憋得难受。
“来人!”
“大将军有何吩咐?”卫士应声而到。
“备马!”
“诺!”卫士被卫青铁青色的脸吓坏了,不敢怠慢,匆匆地向马厩跑去。
战马载着卫青,出了横门,在广袤的咸阳原上飞驰。
马蹄**起阵阵黄土,淹没了跟在他身后的卫士,马群过处,田垄上的农人们都惊恐地望着。
为什么到这里来?他说不清楚,只是觉得很疲倦。他翻身下马,躺在距长陵不远的松树林中。
一只苍鹰在卫青头顶盘旋,卫青望着它大叫道:“非功莫侯……非功莫侯啊……”
“什么事情,让大将军如此烦恼呢?”一个声音从秋风中飘来。
卫青坐起来看去,只见汲黯散散淡淡地朝着这边走来了。
他急忙站起身来行礼:“大人为何也到这里来了?”
汲黯挥手在面前画了一个半圆道:“皇上让下官作了右内史,这京畿之地都是下官的辖内,出来兜兜风,赏赏秋,那总可以吧?”
“那是!那是!”
“看大将军脸色,有什么心事吗?”
“这……在下也是在府上待烦了,出来透透气。”
听卫青这样说话,汲黯只是微笑。卫青有些不解道:“大人为何用这样的眼光看着在下?”
“大将军熟读兵法,运筹帷幄,但有一样不行,就是没有学会说假话。如果下官没有猜错,大将军一定是为给王夫人送礼的事上与长公主意见相左吧?”
卫青惊道:“大人怎么知道的?”
“给王夫人祝寿,是满朝文武皆知的事啊!”
卫青知道这事没法瞒下去,便将对王夫人祝寿的看法直接说与汲黯听。
其实,汲黯早知道这事是长公主一手促成的,他更明白长公主不是一个好惹的人。再说对卫青来讲,他也不缺那几百金。倒是刚才遇见的一件事情让他揪心:“不就是几百金么,公主有意送去就是了。倒是令公子应该引起大将军的注意啊!”
卫青忙问道:“大人听说什么了?”
汲黯顿时严肃起来:“是下官亲眼所见。就在一个时辰前,令公子带着骑奴们撵兔,从百姓刚成熟的糜谷地里跑过,弄得农夫们怨声载道。骑奴们一顿皮鞭,把一个老者打得鲜血淋淋,若不是下官及时赶到,恐怕就要出人命了。”
卫青听着,脸色便阴沉了,他转身就要上马,口中怒道:“在下这就去杀了这个逆子。”
汲黯见状,忙上前拉住马头道:“一个号令千军的大将军,怎么能如此沉不住气呢?他不过是一个孩子,知道什么?要紧的是做父母的要担起责任。”
卫青长长叹了一口气道:“谁说不是呢?都是他母亲溺爱的。”
太阳在咸阳原畔西沉,遥远的天际升起了乳白色的烟雾,两人牵着马缰,一路缓缓地朝原下走去。
正是秋色渐深的日子,回望身后的长陵、安陵,寂寞地矗立在千里暮云下。再看看眼前,是当年始皇帝倾举国财力兴建的宫室,如今只剩下风雨剥蚀的残垣断壁。
这情景让汲黯的眼睛有些湿润,他对眼下皇室贵胄的作为充满了忧虑。走在身旁的卫青见汲黯沉默不语,便问道:“大人在想什么?”
汲黯叹了一口气道:“下官是在想秦朝兴亡的教训。”
卫青点了点头道:“是啊!不想大秦一统天下,竟然亡于陈胜、吴广。”
汲黯摇摇头道:“亡秦者,非陈胜、吴广,乃秦也。若非秦二世沉湎于声色犬马,岂有亡秦之祸?”
“大人真知灼见,在下受教矣。物必自腐,而后虫生。可是当朝如大人这样居安思危的智者也不多了。”
来到横桥桥头,卫青站住了,他深深向汲黯作了一揖,道:“在下今日回去,定要严责逆子。小小年纪,就染上了这种恶习,以后还怎么了得……”
“好在公子年幼。人云,玉之不凿,难以成器。公子天资聪颖,只要好生**,将来一定会大有作为的。”
两匹马载着主人上了横桥,渭河的水声,夹杂着马蹄声,杂沓地传向远方……
第二天一早,卫青进宫拜见皇后。
卫子夫正在询问刘据的学业,刘据看见卫青,就跑上前来亲昵地问候:“舅父在上,甥儿有礼了。”
这不是普通百姓家的外甥,他自出生就打上了皇家烙印。卫青赶忙匍匐在地,口中讷讷道:“臣卫青拜见皇后、皇子殿下。”
“平身!”
行过大礼,姐弟就开始叙话了。春香知道大将军进宫一定有事,于是忙带刘据出去玩了。
“公主怎么没有一起来呢?”
“这……”
看见卫青为难的样子,卫子夫不再问下去。她知道长公主的脾气,但她说出的话却是充满着对长公主的宽谅:“这几个月你在边关,也真难为她了。”
姐弟俩都尽量回避那些不愉快的事情。
“虽然臣弟身在疆场,可没有一刻不思念皇后的。好在将士们奋勇争先,终于大胜回朝。”
卫子夫说,尽管她也知道卫青身经百战,可每一次出征,她的心就要悬几个月,晚上总是做噩梦。而后他们又说到母亲的身体,卫子夫告诉他母亲身体康健,不要他分心。
真是岁月催人老。
椒房殿的春秋带走了卫子夫的年华,她看上去再也没有当年在平阳公主府中那样润泽了。
卫青透过姐姐淡淡的笑意,看到她内心深处的惆怅。一切都是因为自己儿子引起的,因为得罪了长公主,她就把王夫人引荐给了皇上。
在这个幽深的皇宫里,皇上的情感是不断转移的,而留给女人的只有承受,有谁能理解皇后呼风唤雨背后的寂寞呢?这一年,姐姐受了不少委屈,却又无法对人诉说。
一想到王夫人,卫青就不由自主地谈起了因为要给王夫人送礼,他与长公主之间发生的不快。
卫子夫只是静静地听,偶尔眉毛微微颤动,但很快就回归淡然了。直到卫青刹住话头时,她波澜不惊地说道:“公主是对的,你按公主吩咐去办即可。”
“这是为何?”
“不必多问,寿诞都由本宫张罗,这可是皇上的旨意。”
“皇上经常与皇后见面么?”
卫子夫眉头皱了皱道:“你问这些干什么?这是你该问的么?”
卫青发现,姐姐这话一出口眼圈就红了,他就在心里埋怨自己太莽撞了,不该触动姐姐的忧伤。
卫子夫爱怜地看着卫青道:“本宫老了,可据儿还小,去病也还要你关照,大将军可是重任在肩啊!本宫累了,你就快回去吧。”
卫子夫显然不想将这个话题继续下去,徒生烦恼。
“诺!臣弟告退了。”
就在卫青刚刚迈出殿门时,身后又传来卫子夫的声音:“回去后向公主道歉,不要太任性了。”
“臣弟记住了。”
但是,在他即将走出宫门的时候,却又被春香叫了回去,其实皇后要说的也就只有一句话:“记住!你现在是大将军了,凡事要学会忍耐。”
“臣弟记住了。”
“好!你现在可以走了。”卫子夫挥了挥手,转过身去。
卫青仿佛看见皇后的肩膀在颤动。
唉!她心中一定不好受。卫青捶打着自己的胸膛,自问道:“你这是干什么啊!”
……
由皇后为王夫人安排的寿诞,场面气派而又繁华。
丞相公孙弘、御史大夫李蔡等中外朝在京两千石以上官员,都送了丰厚的礼品,各个郡国也都借机表达了对朝廷的敬意。
卫青将皇上赏赐的千金分出五百作为贺礼,由长公主亲自送到宫中,夫妻间的这场风波终于以卫青的妥协而平息。
长公主在酒席宴上频频举杯向王夫人致意,以此来表示了对皇后的冷落,可卫子夫毕竟是母仪天下的后宫主人,她的端庄和娴静,忍耐和宽容,使得寿诞自始至终都洋溢着祥和福瑞的气氛。
不过明眼人都看出来了,长公主才是真正的幕后主宰。
也许是考虑到皇后的感受,刘彻没有出席寿诞筵席,而是让包桑送了一块和田玉,上面刻了“嘉气始降”四字。
当天晚上,王夫人就留在了温室殿。她不断用娇喘刺激着刘彻的神经,扭动的身体就像一条玉色的鱼,在情感的激浪里穿梭,她多么希望皇上的“嘉气”能在这个不平常的日子在她的体内凝结成一颗皇家的种子。她明白,只有如此她的命运才有转机。
可上苍的嘉气没有在她身上降临,却于秋冬交替的时节在雍城应验了。
十月,刘彻照例地移居雍城橐泉宫,在那里举行一年一度的祭祀五帝的仪式。除公孙弘留守京城外,卫青、李蔡等人都陪同皇上一起到了那里。
刘彻毫不掩饰对霍去病的偏爱,特地点名他以“骖乘”的身份坐在自己的车驾上。
车队一出长安城,刘彻就按捺不住对战场的好奇,他要霍去病把战场上的形势讲给他听。
因为在侍中待过一年多时间,在霍去病眼里,皇上并不神秘,他与皇上说话的时候没有一点拘束。他虽然读书不多,但却对那些克敌制胜的经历有着直接的感受,讲起来绘声绘色。
“臣的骑兵挥剑驰骋的时候,匈奴的士卒简直不敢相信汉军会以如此迅疾的速度来到他们面前,他们以为是神兵天降,来不及应战就一个个做了刀下之鬼。”
刘彻沉浸在这绘声绘色的战争传奇中,他侧目打量着身边的霍去病,觉得那一对鹰目,还有刚刚从唇边冒出的胡须,现在都变得十分可爱。
“假如朕给你十万大军与匈奴决战,你可有胜算?”
“赖陛下神威,没有什么不可以。”
“二十万呢?”
“臣一定不负圣望。”
接下来,霍去病把这些日子对如何打仗的思考,直接说给了刘彻听。
“我军以往与匈奴作战,从不离塞,因此也不能永绝边患。臣以为只有将匈奴人驱出漠北,使长城内外,均为我大汉疆土,才会永绝边患。”
“爱卿所言,正合朕意。朕已决计,倾全国之力,不扫灭匈奴,决不罢兵。”
驾车的公孙贺听着他们君臣的对话,很吃惊于霍去病的胆识。显然,他的雄心已远远地超过了卫青。他不敢想象,这个平阳县吏的儿子在将来会创造出怎样惊天动地的伟绩。而这一切,又将会给自己带来怎样的影响!
他扬起马鞭,打在六匹御马的身上,行进的速度加快了……
祭祀的程序一如往年,在雍城逗留的日子,卫青和霍去病一直陪伴在皇上身边。
大臣们只能随在后面,看着他们驱车莽原,驰马高畤,将八百里锦绣秦川尽收眼底;感受他们纵论周秦兴废,勾画扫灭匈奴宏图的畅想;倾听他们说到高兴处,留在雍水河畔的笑声。
刘彻不是那种怠于朝政的君主,不论是在长安还是出巡,他都一如既往地保持从前的习惯。不过这回陪同他练剑的不是未央宫卫尉,而是两个从疆场归来的将军。
刘彻感兴趣的是匈奴人的刀法,他要卫青扮作匈奴将军,以匈奴的刀技向他发起攻击。这让卫青很为难,生怕不慎伤了皇上,每每对阵,总是以守为主,展不开手脚。这让刘彻觉得很不过瘾,于是干脆让霍去病出刀。
霍去病就没有那么多忌讳,一上来就步步紧逼,几个回合下来,刘彻便有些气喘不匀了,头上也冒出蒸蒸热气。
刘彻边招架边思索,渐渐就发现了匈奴刀法的破绽,很快由守转攻。一把宝剑缠住霍去病,无论他怎样周旋就是不能脱身。并趁霍去病一大意,就直取他的脖颈,霍去病的战刀“当”的一声便落地了。
这一阵厮杀,看得卫青和众位大臣眼花缭乱。霍去病从地上拾起战刀,却是不服道:“皇上乘虚而入,臣输得不甘心。”
刘彻收起宝剑,哈哈大笑道:“爱卿可知输在哪里?”
“还请皇上明示。”
“爱卿不输在力上,而是输在心上。”
“臣还是不明白。”
“还记得爱卿在侍中时,朕要你熟读兵法的事吧。须知读书可以明智,可使做事达到事半功倍之效。”
卫青在一旁听着,不由得感叹皇上的有心,他这是在借机教导霍去病。他急忙上前道:“皇上一席话,使微臣茅塞顿开。”
刘彻边走边意味深长地说道:“为帅者,不习兵法,可以随机成小胜,终不能成大器也。”
霍去病紧紧跟着刘彻,虽然没有再说话,可皇上的训诫如同重锤,让他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皇上与卫青、霍去病如此亲近,这让李蔡心里感到很不舒服。说起来,做过代相的他也曾随卫青打过几仗,可……这些埋藏在心底的嫉妒和不平,他无法说出口,他只有等待机会。
这一天,刘彻很早地就起来了,在卫青和霍去病的陪同下,他们来到雍水河边。
淡淡的晨雾中,雍水自北向南地流入渭河。勒马瞩目不远处的秦穆公墓,刘彻心中顿然地生出了敬意。这时候,霍去病突然叫道:“皇上请看!”
顺着霍去病手指的方向看去,刘彻不禁惊呆了。这是何等绮丽的景象啊!被晨曦染作五彩的岚雾中,一只从来不曾见过的生灵就站在那里。
这东西头上长着一只角,鹿身、牛尾,蹄胼五瓣,毛色洁白,声如钟吕。刘彻似在梦中见过,却又是这样的陌生。
霍去病不假思索道:“此等非牛非马之兽,一定不是吉物,待臣射杀它就是了。”说罢,就从箭囊中抽出一支银羽。正要发箭,忽然晴空雷声轰鸣,电光闪闪。
天空无云而雷声大作,这令卫青大惑不解,他忙抽出腰中宝剑,号令禁卫保护皇上。只听见一个低沉的声音喊道:“大将军且慢!”
刘彻回头去看,却是李蔡匆忙地赶来了。
“皇上!此乃嘉气始降矣!嘉气始降矣!”李蔡气喘吁吁道。
刘彻闻言,益发奇怪,前些日子他为王夫人祝寿时,曾赐她一块和田玉,上面就刻有这四个字,他忙要李蔡平身回话。
“爱卿不必惊恐,快与朕详细奏来。”
李蔡拍了拍袍子上的尘露,就带着几分神秘道:“皇上肃祇郊祀,上帝报享,赐一角兽,此乃麒麟是也。”
经李蔡这么一说,卫青倒想起来了,在边关时他也听任安说过,天有神兽,名曰麒麟,于是忙对刘彻道:“既是天帝所赐,臣不妨令禁卫捕之,养在宫中,以祈社稷之福。”
禁卫从四面包围,向雍水河边收拢。可那麒麟似乎是受命于上苍,早就在这期待这次嘉会,它轻盈地撒开四蹄,越过卫青、霍去病和李蔡,来到刘彻面前,温顺地匍匐在他脚下,润泽的白唇吻着刘彻的衮袖。刘彻俯下身体,手指缓缓抚过麒麟角上的肉瘤,似乎是对一位久违的朋友说话。
“惠哉昊天,赐我神兽,大汉社稷,悠悠万世。随朕回宫,大祀五畤,牲加一牛。君臣大宴,喜庆三日。”
一路上,麒麟在卫青、霍去病与皇上之间,紧紧地追着刘彻的脚步。那种忠诚和驯服,让随行的大臣们无不称奇。
郊祀结束,回到长安,李蔡先是到宗正寺查阅了高皇帝以来像天法地的记载,又到太常寺咨询了改元的记录,然后协同太常向刘彻提出了改元的奏章。
“元宜以天瑞命,不宜以一二数。皇上登基,乃元之首,曰建元;二元因有白光出现,曰元光;三元因收回河南地,筑朔方城,曰元朔;今皇上于郊祀得一角兽,此乃祥瑞之兆,臣等启奏皇上,以改元为狩。”
这项奏议几乎没有什么异议,就在廷议时得到了三公九卿的赞成。
时序就这样地进入到了元狩元年。
朝廷大赦天下,诸侯纷纷朝贺,王朝沉浸在一片祥和的气氛中。
先是济北王刘胡献上泰山及其周围的县邑,以作封禅之用。接着,各个郡国纷纷上表,呈报购买武功爵和赎禁锢的表册,同时将所得源源不断地解往京城,一度空虚的府库又渐渐地丰盈起来。其中,以淮南王刘安申报的数量最多。
严助从寿春回来后说,淮南境内民安其居,商安其业,夜不闭户,山无盗贼。淮南王还对皇上削去二县毫无怨言,并斥责了王太子。
作为侍中,严助系建元以来老臣,刘彻虽然对其所奏提不出多少质疑,可依他对这位皇叔的了解,心中总有些不安。
危机就在一片歌舞升平中一天天临近了。
这是十一月的一个傍晚,公孙弘刚刚回到府上,还没有来得及喝上一口茶水,府令便送来两封上书,声称送信的人称情况紧急,请丞相立即禀明皇上。
公孙弘拆开信札,只粗粗地浏览了一番,就脸色苍白,冷汗淋漓了。
“夫君!这是怎么了?”
“休得多问,老夫要进宫。”
“就是进宫,也得用了晚膳吧!”
“你懂什么?”公孙弘不耐烦地盯了夫人一眼,就出了相府,径直奔未央宫而去了……
“皇上在里面么?”公孙弘心急火燎地向殿外的包桑问道。
“正和司马相如、东方朔谈诗论文呢!”
“请公公奏明皇上,就说老臣有要事求见。”
过了一会儿,包桑就出来领他进殿回话。公孙弘捧着上书,刚进宣室殿门,就听见刘彻在殿中央来回踱着步子,高声朗诵道:
朝陇首,览西垠。
雷电燎,获白麟。
爰五止,现黄德。
图匈虐,熏鬻殛。
辟流离,抑不详。
宾百僚,山河飨。
掩回辕,鬗长驰。
腾雨师,洒路陂。
流星雨,感惟风。
鬗归云,抚怀心。
一首歌罢,刘彻就面向司马相如和东方朔问道:“朕的这首《白麟歌》如何?”
东方朔连道:“好诗,好诗!皇上的诗,起首不凡,落语尤好,‘鬗归云,抚怀心’,长发如云,飘飘若仙。”
刘彻捻须微笑,并不纠正东方朔的理解。这是他心中的秘密,那飘洒如云长发的只有王夫人,而领受这长发摩挲的男人,还会有谁呢?
有过风流体验的司马相如领会了皇上的诗意,却又不便明说。当刘彻要他发表见解的时候,他换了欣赏的角度道:“皇上这首《白麟歌》借物起兴,意象纷纭,尤以气势夺人。”
刘彻放声大笑道:“还是二位爱卿解得好!”于是令黄门奉上御酒,以示褒奖。
他转过身来,就看见一脸焦急的公孙弘,笑问道:“丞相平日里处事稳健,今日何以如此慌张?”
公孙弘将两封上书呈送给刘彻道:“皇上看了就明白了。”
刘彻接过上书,大致浏览了一遍,似乎一切都在预料之中。遂对司马相如和东方朔道:“时间不早了,丞相又有事禀奏,看来朕只有另择他日与卿等谈诗论赋了。”
等他们告退后,刘彻把两封上书扔在案头,嘴角露出讥讽:“终于来了!”
这两道上书来自淮南国和衡山国,上书的不是别人,一个是刘安的孙子刘建,密告他的祖父私刻皇帝玺,制作御史大夫、大将军至两千石官员印,密谋造反;一个是衡山王的废太子刘爽,状告新立衡山王太子刘孝私做輣车、打造弓箭,密议与淮南王策应起事。
“龟蛇欲动,风必兴焉。朕倒要看看,他们能奈朕何!速宣李蔡、张汤、公孙敖到宣室殿议事!”
大臣们在时近戌时接到皇上召见的口谕,心头都捏了一把汗,急匆匆地赶到宣室殿。
公孙弘向大家简述了两道上书的内容,刘彻就要大家发表看法。
李蔡道:“上书的一为淮南王长孙刘建,一为衡山国废太子刘爽。据严大人说,刘建对淮南王立刘迁为太子一直耿耿于怀,今番上书,所陈事实的真伪尚需甄别;至于衡山国废太子刘爽,大概也是报复,还请皇上明察。”
张汤看了看李蔡道:“大人所虑,不无道理。不过元朔五年臣审理雷被一案时,获得大量证言,足以表明淮南王图谋不轨已非一日,因此臣请皇上当机立断,缉拿淮南、衡山王父子归案。”
在李蔡和张汤说话的时候,公孙弘一直在对两人的陈奏做着比较和分析。
他很快发现,无论是李蔡还是张汤,都忽视了一个与此案有着密切关联的人物——严助。
许多被忽视的现象,让公孙弘越来越感到蹊跷。他发现在以前严助不止一次向皇上陈奏要警惕淮南王,可自从出使回来后,说话的语气就全变了。有几次在塾门等待皇上召见时,严助还极言淮南国对朝廷的忠诚。后来,他还听人说,这位侍中常常出入于淮南王在京城的府第,与刘陵过从甚密。
公孙弘之所以没有太在意,也是因为严助是建元以来的老臣,饱经风霜,屡经历练,不相信他会与皇上离心离德。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不是空穴来风。
他一旦发现了这个细节,就对思路做了迅速的整理,他充分肯定了李蔡顾虑的合理,又对张汤的主张表示了明确的支持,最后,他清楚而明晰地将严助牵进了案情。
“臣以为,两道上书所陈事实与严大人向皇上复旨时所言相去甚远。要么就是刘迁、刘爽诬告两位大王,要么就是严助欺君罔上。因此臣请皇上立即将严助下廷尉府审理。”
刘彻重新拿起案头的上书,指着其中所列“刻皇帝玺、打造弓箭、制官印”等罪状道,“这些蛛丝马迹,朕平日里屡有所闻,只是没有证据,去年朕削去淮南二县,意在摇枝惊鸟。临行前,朕曾叮嘱严助,一定不要放过每一个细节。孰料他回来却送给朕一幅淮南太平图。”
他的目光掠过大臣们的额头,立时让人感觉到一股威严的杀气。
“公孙敖听旨,命你连夜秘捕严助,送廷尉府严加审问。”
“诺!”
在公孙敖转身朝殿外走的时候,刘彻又加了一句:“还有那个长期盘桓在京的刘陵,也一并捉拿归案。”
命令一下,刘彻就把思绪转到平定淮南、衡山事变上来。他对张汤道:“可将严助一案交与廷尉长史审理,由李蔡监审。爱卿带治狱使者即日起程,前往淮南、衡山缉拿逆贼。”
刘彻又对公孙弘道:“丞相要做的事情就是,明晨起,督促宗正寺、太常寺整理淮南王、衡山王的作为,他们皆刘姓诸侯王,一定要持之有据,不可臆断。”
为了保证张汤能将叛逆缉拿归案,刘彻又下令发庐江、临淮、汝南三郡兵马,对寿春围而不攻。
“这是为什么呢?”公孙弘问道。
“唉!同宗血脉,兵戈相见,若非万不得已,朕又如何忍心呢?”
夜色沉沉,天空很黑。宫墙外宽阔的大街旁,亮起两排灯火,一直绵延到城门口,从巷闾街市的酒肆中传来文人骚客们的笑声,和着浓浓的酒香在夜色中飘散。
而一场平叛战争,就在这夜色中悄悄地拉开了帷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