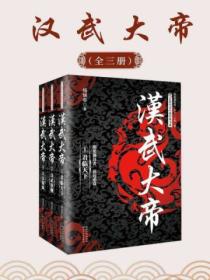第二十三章 霍光观画体君意 汉皇一怒斥红颜
夜风呼呼地掠过长空,李广利勒马站在风中,一脸茫然。
“我军伤亡如何?”他向跟在身边的从事中郎问道。
从事中郎的声音有些沙哑:“开始的时候,我军依靠精弓良弩,射杀匈奴人无数,可由于弓矢越来越少,匈奴骑兵已突破了我军防线。日落时分,各路司马报来的死亡人数总计在两千人。”
事情怎么会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呢?这是入朝以来,李广利最投入的一场战役啊!
这动力的源头就是他与刘屈髦咸阳原头的盟约,一切都是为了让刘髆登上太子之位。战事一开始很顺利,匈奴人节节败退。左路军和右路军几乎没有遇到匈奴的抵抗就全胜而归。
两军派使者前来提醒李广利班师,可他当时一心想为自己的外甥挣足做太子的资本,就婉言谢绝了他们的劝告,然后率领大军越过居延泽,一直打到范夫人城。
可就在这时,他忽然接到了好友送来的密信,说刘屈髦夫妇已卷入了巫蛊案,并阴谋欲立昌邑王刘髆为帝。皇上知道后龙颜大怒,已于去年十二月,将刘屈髦腰斩于东市,将其妻枭首于华阳街,将军夫人因受到牵连也被下狱。
那一夜,他传来从事中郎,借酒浇愁道:“你说说,本官该如何应对?有亲不能见,有家不能归?这仗打下去还有何益?”
“眼下还不是将军气馁的时候。将军可曾想过,夫人、家室都在狱中,如果回去,稍不留意,皇上也会将将军下狱的。”
“依中郎看,本官只有客死异国了?”
“将军眼下只有一条路可走。”
“快说!”
“继续北上,寻机与匈奴决战。倘能大胜,皇上必念及将军殊勋,宽恕将军及家室。”
李广利长叹一声:“看来也只有如此了。”
那是一场冒险的厮杀!在左右两路大军回撤的形势下,他率部长驱千里,孤军深入,随时都可能遭遇匈奴的埋伏。可他顾不了这些,他要的是皇上的信任和宽容。在歼灭右大将所部后,他迅速地将大营向前转移,并在军前会议上与长史发生了大战以来的第一次冲突。
“不妥!”长史在李广利话音刚落的时候,便站起来说话了。他详细分析了敌我的态势,一针见血地指出,“汉军现在距离后方已很远了,如果没有援军策应,是很难取胜的。”
他的话立即得到了决眭都尉和各路司马的响应,大家纷纷建议李广利撤军,到酒泉与霍光会合,然后再从长计议。当十几双眼睛一齐投向李广利的时候,他们从那里得到的却是冰冷,是恼怒。
“本官心意已决!传令下去,明日卯时出兵,直驱北上。有取右贤王首级者,本官自当奏明朝廷,以求皇上封赏!有动摇军心者,斩!”
然求胜心切的李广利不知道,狐鹿姑单于闻知汉军意欲北上,已亲率五万大军张网以待了。果然,汉军还没有来得及扎营,狐鹿姑单于率领的五万精兵就席卷而来了。一场厮杀下来,又有两千多名将士抛尸郅居河畔。
李广利眼中满是匈奴人用刀剑织成的囹圄,有几次,他将剑抹向自己的脖颈时,都被匈奴人用枪隔开了——显然,匈奴人是要活捉他。
夜幕降临,双方厮杀暂停,李广利来到半山坡上撑起的一顶帐篷里,向从事中郎求助:“现在我军该怎么办?”
“为今之计,我军应趁夜撤到酒泉,与霍将军会合。”
“将士太疲劳了,明日再撤退吧?”
“不可!等到天明,就是想走都走不了了。”
“我军疲劳,匈奴军亦疲劳,本官估计今夜他们不会进攻的。明日黎明便出发,等到他们醒来时,我军已离开数十里了。”
“将军……”从事中郎还有话说,却被李广利制止了。他眼中充满了失望,认为将军患得患失,会给他们带来灾难的。
果然,匈奴人没有给他们机会,就在他倚着一块石头、想休息一会时,却忽然听见一股声音从夜色中传来,好像是山坳里刮起的风声。
不好!匈奴人进攻了!从事中郎顾不得多想,一边大喊着匈奴人来了,一边跨上坐骑来到李广利面前。
各路司马这时也都赶来了,李广利立刻下令道:“各自率部朝南撤退,先到范夫人城集结,然后退入酒泉。”
“伤兵呢?”
“轻者带上,重者就地处置。”
“他们可是家乡子弟啊!”
“带上他们,我们都得死!无须多言,速去集结队伍,迟则晚矣!”李广利下了狠心。
司马们刚刚离去,喊杀声就四起。李广利惊慌中上了马,率领从事中郎和近身卫士朝南奔去。可刚走出不远,他就遭遇了一个匈奴当户。他无心恋战,应付了几个回合就逃了,那当户也不追赶,只是命令他的部属在后面喊道:“李将军,你抵抗无益,快下马投降吧!”
他刚跑过一道沙坡,只听见“扑通”一声,就连人带马跌入匈奴人挖的陷阱中去了。
时年正是征和三年八月。
……
半个月后,狐鹿姑单于在郅居水南岸,为李广利举行了盛大的婚礼。
曾与他对阵的卫律、左贤王以及左右骨都侯和右大将都按单于的旨意赶来赴宴。
李陵没有参加,他选择在这个日子和妻子阿维娅到北海边看苏武去了,他不愿意在这种场合与李广利相见。
狐鹿姑单于同意了右校王的请求。
自元狩二年置郡以来,酒泉郡的禄福城先后迁来中原数十万人到这里定居,现在城池的规模已很可观了。
中原百姓与羌族、戎族和睦相处,使它成为大汉在河西一带的军事重镇,也是大汉的屯兵前沿。霍光率部撤到兄长霍去病当年鏖战的旧地,不禁生出许多感叹。
匈奴军与汉军刚刚接触,就匆匆撤退了。与他对阵的将军不是别人,就是曾经的汉骑都尉、现在的匈奴右校王李陵。
两军在蒲奴水流域展开九天的拉锯战,霍光一直在寻找与李陵正面接触的机会,但直到匈奴军撤退,他都没有能够与李陵见面。李陵为什么不与他打照面呢?可能是出于心中的愧疚吧?
从事中郎赶上来,与霍光并马而行。霍光问道:“近来营中军纪如何?”
“唉!怎么说呢?”从事中郎叹了一口气,“李广利投降后,他的部分属下辗转到了酒泉,常常到酒肆借酒浇愁,长此下去,军心必然涣散。”
霍光勒住马头,脸色严肃起来:“治军不严,必受其乱,怎么可以如此放纵呢?朝廷有制,非节庆之日,严禁军中饮酒。传令给各路司马,校尉醉酒者,杖击五十;什长醉酒者,鞭笞三十;伍长醉酒者,鞭笞二十。”
“诺!不过还有些士卒经常与民争水,还打伤百姓。”
进入酒泉时,霍光就命令军士不能与老百姓争水。可还是有些士卒违反军纪,这让他十分恼火:“自古以来,凡伤害百姓者,没有不身败名裂的。凡糟践百姓者,斩!”
太阳已近正午,两人驱马回城。霍光松了马缰,让速度慢下来,为的是不打扰正在市易的百姓。
酒泉不同于京城,长安的店铺都是分门别类地被设置在不同的街区,边城的店铺却都是混杂在一起。交易的物品也是琳琅满目,内地的布帛织锦、西域的玉器宝剑、羌人的羊毛制品、匈奴的银器宝马,一应俱全。
前面簇拥着一堆人,这引起了霍光的注意,他对从事中郎道:“你去看看,那是怎么回事?”
从事中郎挤进人群一看,就明白了,又是士卒与百姓为水起了纷争,几个年轻的士卒把一个当地人打倒在地。
“光天化日之下,殴打手无寸铁百姓,成何体统?”霍光的脸色顿时阴沉了,向卫队挥了挥手喊道,“将那几个士卒押过来!”
士卒们低着头,就知道今天闯了大祸。
霍光用鞭子挑着为首士卒的下巴,冷笑道:“没有仗打,筋骨不舒服了?这泉是你家的么?”
士卒战战兢兢地摇了摇头。
霍光厉声道:“这酒泉流着皇上的浩浩恩德,可你们目无法纪,与百姓争水,今天本官倘不让你们长点记性,说不定哪天就会干出杀人越货的勾当。来人,给我打!”
顷刻间,卫队的皮鞭就在士卒的脊梁上开了花。
几个士卒开始还本能地躲避着,到了后来,连躲避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直呻吟。
在场的百姓都看呆了。他们想起霍去病当年将御酒倒在泉中的情景,又见霍光严厉责罚部属,顿生由衷的敬仰,几位长者纷纷上前求情:“乡人亦有越礼之处,还请将军息怒,宽恕了他们。”
霍光把马缰交给身边的卫士,双手扶起长者道:“今日之事,都是本官治军不严。大军驻扎酒泉,对父老乡亲多有叨扰,本官已很不安。今日部属又做出此等伤民之举,还请乡亲们原谅。”
他回身对几个躺在地上呻吟的士卒道:“看在父老的分上,且饶了你们。如再有此类举止,定要你们项上人头!”
人群中爆发出呼声,霍光连连向长者作揖。
走了好长一段路,身后还传来百姓的欢呼:“吾皇万岁!万岁!万万岁!”
回到行辕,酒泉太守已等候多时了。一见霍光进来,急忙站起来作了一揖:“朝廷来人了。”
“哦!不知是哪位大人?”
“桑弘羊大人。”
“哦!是桑大人来了,是不是皇上又催促进兵了?”
“不像!桑大人只是说,皇上有口谕要当面传给将军。”
当晚,霍光在行辕设宴迎接桑弘羊。席间,霍光不时谈到对长安的思念和对皇上的牵挂。
“李广利已投降匈奴,本官担心皇上春秋已高,身心承受不了如此变故。”
桑弘羊只是喝酒,夜深席散之后,桑弘羊才告诉霍光,皇上听到李广利投降匈奴的消息后,昏倒在钩弋宫。
“李广利所部七万余人,回来者不过十之一二。”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桑弘羊问道。
“唉!说起来与刘屈髦一案有关。李广利闻听夫人入狱,皇上要缉拿他,心中生惧。有人建议他若能斩匈奴左大将,也许皇上会宽恕他。他在取其首级后,本该撤军,孰料他拒听忠言,贪功冒进,遭匈单于大军的伏击,最终被俘。”
桑弘羊沉默良久后想:李广利之失,不在战局,而在品节。
桑弘羊告诉霍光,先期回朝的商丘成做了御史大夫,曾在长陵高庙守陵的执戟郎田千秋,做了大鸿胪。
霍光凝视着手中的酒爵问道:“太子一案查清楚了么?”
“事实证明,太子一案完全是江充等制造的冤案。真相大白后,皇上思念皇后和太子心切,日渐消瘦了。”
霍光饮干酒酿,重重的呼吸代替了千言万语。
长安兵乱时,他正与李陵大战,是断断续续听到一些只言片语。可因为与皇后的关系,使得他对太子与皇后的安危十分关心。他相信,太子绝不会僭越犯上。
现在,是非终于清白,霍光除了欣慰外,更为这场杀戮伤了大汉的元气而痛惜。
“从京城来的人纷纷传说,长安屠城五日,死伤数万人。”
桑弘羊道:“这不是传说,是真情,驰道两边的阳沟都淌着血水。”
一轮明月透过营帐,静静地照着两人,掌灯案头,霍光对桑弘羊道:“大人此行应还有其他的事吧!”
桑弘羊点了点头,从囊中取出《周公辅成王图》,摊在案头道:“下官此行,就是奉了皇上诏命,将这个转交给大人。”
霍光借着灯火,看了一下之后,就向桑弘羊问道:“皇上没有别的什么‘谕意’么?”
“皇上说,该说的话都在画中,将军看了就自然明白了。”
霍光于是埋头看画,很快就入神了。
他不仅在画上看到了金日磾的影子,也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并且还看到了皇上忧郁、沉重、期盼的目光。
那谁是成王呢?那是皇上将要立的新嗣啊!
往事如烟,所有的痛,所有的伤,所有的忧郁都散去了。
“大人!您说……”霍光谨慎地把目光投向桑弘羊。
“皇上要立新嗣了!”桑弘羊并没有拐弯抹角,“皇上的意思将军难道还不明白么?这幅画在您去年赴前方后,就由上官桀监工开笔了。画工连画了多幅,都因为不谙皇上深意而被下狱,可见皇上用意之深啊!”
“当然明白!只是本官还不知道……”
“还能有谁呢?”
“莫非……”
桑弘羊笑道:“你我不妨用水书之案头,看可否不谋而合。”
两人蘸了茶水,在案头写了三个字,就把目光投向对方。胶东王——两人几乎同时写下这个称谓。
霍光很吃惊,心中疑问这是不是上苍有意安排了的。
五十多年前,当今皇上身为胶东王的时候,曾围绕废立有一场血腥的争斗,现在,又一个胶东王在废立的紧要关头进入朝野视线,这到底意味着什么?
皇上为什么要册封刘弗陵为胶东王呢?是要在这个王爷身上找回当年的梦么?他又为什么千里迢迢的送来一幅画呢?皇上的忧虑在哪里呢?霍光看了看桑弘羊,又在案头写下了四个字道:“皇上担心的是这个吧?”
“哎呀!大人果然才思过人。”桑弘羊用袖头抹去“钩弋夫人”四个字,一双精明的眼睛等待着答案。厅内一下子非常寂静,只有这时候,塞外的风声才进入他们的耳际。
“母壮而子弱,又是大汉一个关口啊!”良久,霍光讷讷自语道。
“大人明鉴!因此皇上才有了托孤的思虑。不过这只是下官的猜想,下官姑妄说之,大人也不妨姑妄听之。”
“本官知道此中利害,今夜之叙只在你我心中。”
可桑弘羊却突然换了话题,问道:“将军,此去轮台有多少路程?”
霍光不知道桑弘羊为什么忽然问起这个,随口答道:“大概两千里之远。”
“下官在想,自太初三年占领轮台以来,汉匈之间的战场已经移至天山南北,即使从陇西、天水、酒泉诸郡调运粮草,也是长途转输,不堪其力。倘若能在轮台屯田、筑亭,岂非戍边与省减两利?”
霍光惊异地打量着桑弘羊,心中叹道,桑弘羊真乃经国济世的良才,一趟西行,竟有这么多收获,那喜色就爬上了眉梢。
“倘能如此,当然再好不过了。”
“有将军这句话,下官就放心了,此次回京,下官就奏明皇上,力求早日实施此议。”
“好!”霍光站了起来,向桑弘羊作了一揖,“烦劳大人奏明皇上,就说皇上的意思臣明白了,臣虽愚钝,然为匡扶社稷,不惜此身。”
……
送走桑弘羊,踏着月色回来,子时三刻都过了。
一轮朗月西去,虽天上人间,可那玉兔、桂树都看得清清楚楚。
酒泉的月,总给人冰冷的感觉;加上已是十月,那月色携带的寒意,被风卷进心中。
走进帐内,一股暖气扑面而来。从事中郎一定来过了,霍光心里一阵感激。
烘了烘冰冷的手之后,霍光在案头坐下来。
往日在这样的冬夜,他很快就会进入梦乡,可今晚,他却全无睡意了。重新摊开《周公辅成王图》,看着看着,整个灵魂似乎都附在了周公身上了,那一颗心也飞到了皇上的身边。
卷起画轴,铺开绢帛,他庄重地写下了“光禄大夫臣霍光上疏皇帝陛下……”
可刚开了个头,他就停下了。他之所以没有直接委托桑弘羊把自己的奏章带给皇上,是因为事关重大,生怕自己的不慎给这位同僚带来不便。
其实,从情感上说,他对钩弋夫人并无恶感。她也不像宫中其他妃嫔那样争宠掠爱,若不是生了一个被皇上看中的儿子,她又怎么会成为王朝的障碍呢?
霍光不是没有心结。卫氏一族死的死,亡的亡,现在在朝堂上与之有亲缘的就只有他一个人了。他想向皇上陈奏,即便另立新嗣,也该给皇后恢复名分,哪怕是一座衣冠冢,也要安葬在茂陵,位于李夫人之上。
可这样一来,皇上又该怎么想呢?自己不是要背着逼主的罪名么?而且,这也违背了皇后生前的品格,更让已长眠在茂陵的卫青、霍去病泉下不安。
霍光将胶东王与其他皇子一一作了比较。刘弗陵年幼、娇弱,燕王与之相比,更具皇上的雄才大略。他不但与刘据一样喜欢读书,更喜欢结交贤士、习武弄兵。可自离开长安后,就不断听到他在封邑内大造宅邸的消息。而且他心理阴暗,这是为人主的大忌。再者,他和广陵王均乃李姬之子,并非嫡出……
李妍所生的刘髆,承继其母温厚的品格,又因皇后生前多加关照,倒是宽厚、温雅。只是早早地去了。
数来数去,也就只有一个胶东王了,可他偏偏有一个年轻的母亲。
霍光放下笔,来回踱着步子,反复思忖着奏章该怎样写,话该怎样说?
进入侍中以后,他遍阅春秋往事,因内宫干政而致乱者数不胜数。他觉得,一幅《周公辅成王图》就是大汉江山传续图,他站在了王朝的风口。
在关系到大汉前途命运的问题上,他没有选择,他必须要把该说的话说出来。可这些话又不能太具体,太具体了会伤及皇上的情感。
他掸了掸笔尖,俯下身体,把反复掂量斟酌的言辞落在洁白的绢帛上。
臣观画卷,感慨万千。陛下忧思,臣深会意。初,成王年少,周公乃摄行国政,兴礼乐,改度制,而民和睦,颂声兴。行政七年,夜以继日,坐以待旦,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及成王长,乃还政于朝,北就臣位。贵而愈恭,富而愈俭,胜而愈戒,乃人臣之极范也。
陛下不以臣愚钝,诚征立嗣大计,此大汉国脉之基,社稷永固所系。臣不可不慎思,亦未敢不慎言。然则,为人臣者,忠信而不谀,谏争而不谄,臣不敢以私抉择,不敢以私取与也。
诗曰:“温温恭人,维德之基。”胶东王虽少,而性宽仁,智敏慧,堪当国嗣。然夫人春秋尚富,臣不得不存诸吕之忧。自古子弱而母壮,未有不危国者也……陛下圣君,好同而尚贤,使能而飨盛,故臣不揣浅陋,直陈胸臆……
写完奏章,雄鸡便唱出了第一声啼晓。而从事中郎也进帐来了,他一看就知道霍光又是一夜未睡。
“将军……”
霍光站起来,封了奏章,对他说道:“速派可靠使者送往长安。”
“诺!”
从事中郎接过奏章,准备出帐,霍光又叮嘱道:“不必告知桑大人了。”
……
入冬以后,皇上就带着刘弗陵搬回未央宫去了,而将夫人留在钩弋宫中。
皇上没有说为什么这样做,而且临行时也没有向夫人提起,而只是让包桑转达了他的意思,说陵儿从现在起要独处了。
钩弋夫人虽然心里感到憋屈,可她很快就说服了自己。
皇上说得对,陵儿已五岁了,也该学习礼仪典籍了。可接下来发生的事,却让她的心境涂上了一层阴影。
皇上自离开后,就再也没有宣她到未央宫,也从来不让她传陵儿到钩弋宫。她说不清楚其中的原因。
是因为长安事变让太子遭受了不白之冤么?可她想来想去,这件事都与她没有关系。在甘泉宫时,她不止一次为太子辩白,劝皇上父子重归于好。可后来,怎么就发生了太子谋反的叛乱呢?
是因为那个入狱的苏文么?她对苏文的好感,仅仅是因为他对陵儿的呵护和关爱。她信守母亲传给她的做人规则,那就是知恩图报。因此,苏文的入狱她也觉得不理解,曾谏言皇上从轻发落。可即便是错了,也不应该如此啊!
她已有多日没有看见皇上了,她担心宫娥们不能照看好他的起居,黄门不能时刻守在他的身边。
她现在已把皇上看成生命的全部了。看不见他,她会寝食难安。
夜里躺在榻上,耳朵却不放过殿外任何一丝动静。她多么希望皇上传她到未央宫,可每次都等到月影西斜,换来的是满腔失望。
每次御膳房来问饭菜的搭配,她总是点几样皇上喜欢的菜肴。她多么期待皇上能不期而至,与她吃一顿饭。可直到檐下的**都凋落了,皇上还是没有来。
那种殇菊的凄婉笼罩着钩弋夫人的情绪,人也越来越消瘦了。每天卧榻的时间多,走动的时间少。在芸香眼里,生性活泼的钩弋夫人现在话越来越少,有时候一天都很难听她说一句话。
一天,芸香为钩弋夫人梳头,发现她的头发越来越燥,而且大量的脱落,她在心里断定夫人一定生了病,于是便问道:“夫人身体不舒服么?要不要传太医来?”
“不用了,本宫就是看那些**落了,心里有些不好受。”
说这话的时候,其实她心里已有了打算。她要亲绣一幅《菊祭》,为了远行的香魂,也为了抚平自己心头的忧伤。
听说夫人要绣花,宫娥们就收拾好绣架,准备好丝线。平日里,钩弋夫人在绣架前坐定,大家都不能远离,只能簇拥在一旁看着。可今天她发话了,要她们都退下,只留芸香一人在身边。
今天,钩弋夫人下针的动作有些迟滞,不像往日那样针走线飞。刚刚开始绣,眼睛又不由得潮湿了。虽然针是刺在洁白的绢帛上,可也是刺在她心底啊!
钩弋夫人被这种理不清的情绪,牵出了诸多的回忆。
从甘泉宫回到京城,长安那场战乱的枝节通过芸香和苏文的口,不断传到她的耳里,让她总是摆不脱卫皇后、卫长公主的影子。
她从来就没相信皇后会策动一场反叛,说起来,她与皇后相差了一辈,甚至比太子还要小几岁,可自打她进宫,皇后就视她如姐妹,从未有过严责和申斥。
刘弗陵出生时,皇后亲自上门探望。她曾担心,皇后看了寝宫门口的“尧母门”三字,会不会心生不快。可直到皇后离开,她也没有从皇后的脸上发现一丝愠怒。皇后倒是说,皇上多一个皇子,是大汉江山的福祉。
这样一位贤淑的女人,怎么会对皇上有异心呢?
之后的日子,她曾多方打听皇后的下落,却知之甚少。后来听说春香回到了宫中,从一个不为人知的地方找到了皇后的时候,已是白骨累累,香消玉殒了。
据苏文说,本来皇上是要把皇后葬在茂陵的,可皇后临终遗言,声明自己教子不严,无颜葬在茂陵,因此此事就作罢了。
苏文跟皇上回到京城后,说话办事都是小心翼翼的。但却屡次在她面前暗示,太子已埋骨青山,皇上有意立陵儿为太子。
她虽然从理智上告诫自己,立太子是皇上的事,但她从内心还是感谢这个跟在皇上左右的中人。
可有一天,皇上一道口谕,苏文也入狱了,据说罪名是陷害太子。她无法相信,如此一位和善的黄门,怎可能去陷害他人呢?
她忘不了苏文在被押上囚车时,留下“夫人保重,王爷保重”的声音。
从未央宫那边传来的消息说,朝野有不少人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种局面,是因为皇上太宠爱她和陵儿了。风言风语说得很难听,甚至把她比作褒姒和妲己。芸香曾谏言她将这些议论禀奏给皇上,但她拒绝了。
可她感到很委屈。她从来没有非分之想,只是想待在皇上身边,怎么就被卷进了一年前的事变了呢?
钩弋一想到这些,就分心了,手指被针刺出了血。她“哎哟”一声,忙放进嘴里吮吸。那咸咸的味道,把她的思绪带到了与皇上邂逅的岁月。
没有皇上,她这双手至今还会蜷在一起;没有皇上,就不会有她后来的欢愉和幸福。
半个时辰以后,第一朵**的轮廓越来越清晰。枝叶还没有展开,可钩弋的心已经碎了,竟伏在绣架上哭泣不止。
芸香吃惊地看着钩弋,呼唤道:“夫人!夫人!您怎么了?”
钩弋凄然一笑,便挺起身体,将绣针插在绢帛上道:“今日就先绣这一朵吧!本宫累了。”
“夫人如不想绣了,奴婢安排人来绣。”
“不!她们不了解本宫的心思。”
钩弋离开绣架,进了内室,芸香急忙落下帷帐,轻手轻脚地退了出来。
钩弋哪能入睡呢?
芸香刚刚出去了不一会儿,就回来了,并带给钩弋夫人两个消息。
“从未央宫那边过来的黄门说,昨日,刘屈髦游街示众后,被腰斩于长安东市。”
“哦!他诅咒皇上,罪有应得。”钩弋夫人不以为然。
“还有呢!黄门们说,今日廷尉府要在横桥北行刑,要火焚苏文,以祭太子亡灵。”
“什么?你说什么?”钩弋“呼”的从榻上坐起来问道,“现在是何时了?”
“辰时三刻。”
“詹事何在?”
钩弋宫詹事应声进殿道:“夫人有何吩咐?”
“你速去横桥,让他们刀下留人,本宫要进宫面奏皇上,对苏文从轻发落。”
“夫人!万万不可啊!”芸香劝道。
“苏文有罪,罪不至焚。”
“夫人三思,苏文焚刑,乃皇上御批,夫人贸然阻拦,违逆陛下……”
“本宫不为别的,就为他对陵儿的一片真心……”
人老就是一瞬间的事情。就好像喝得酩酊大醉,一觉醒来,就须发皆白了。
刘彻在梳洗时,常常对着铜镜中的自己发呆。
从钩弋宫搬回来后,他不再坐在案头批阅公文了,而是靠在榻上,让包桑把竹简递给自己。
从包桑手中接过竹简时,他忽然愣愣地看着眼前这位跟了自己许久的黄门总管,发出神秘的笑声。
包桑有些尴尬,不好意思问道:“皇上为何如此看着老奴?是老奴脸上不干净么?”
“呵呵!你说人也真怪啊!朕这一辈子,后宫有多少妃嫔,可临到老了,还是觉着与你在一起舒心啊!”
包桑很感动,也很惭愧。他也老了,论起来还比皇上要大,腿脚没有了早年方便。
“奴才老迈,还能伺候在皇上身边,乃是天大的荣幸。”包桑说着,就从案头拿起银钗,为皇上拨了拨灯花。
刘彻今天批阅的是田千秋关于太子一案真相的查验以及对几位涉案人的处置谏言。他就着灯火,眯着眼睛看了半天,只觉得那上面的字迹模模糊糊的。
“朕看不清了。”他收起竹简,对包桑道,“自今日起,令人来代读。”
“诺!”
包桑出去不一会儿,就引来一位年轻的黄门。他跪在刘彻面前,展开奏章,小心翼翼地读起来。
田千秋在长陵为郎的岁月里,读过不少春秋战国时期的典籍,长于叙述。特别是关于长安事变的每一个故事,都强烈地冲击着刘彻的情感。
那天从覆盎门逃出后,太子率领百名禁卫,一路来到弘农郡的新安县。新安县令李寿,乃元狩年间举荐的贤良,在京城候任时,曾由太子舍人张光引荐,得以在博望苑中拜见太子。太子的敦厚宽仁,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得知长安事变的消息后,他就认定太子必是被奸人陷害。于是他躲过北军和羽林卫的追击,将太子一干人藏于隐秘处,并放话说太子一干人往东去了。孰料追兵东去数十里,一无所获,便在新安县四门布置了岗哨,张贴了通缉榜文,严查进出之人。
是日,太子望着守在门外的禁卫和新安县令,心境十分烦乱。他觉得郡国遍贴通缉榜文,即使逃出新安,也还会在别处倾覆。与其这样东躲西藏,倒不如悬梁自尽,结束自己的生命。
登上石鼓,面对绢帛,他又生了许多的纠结和不舍。觉得自己愧对为了引开官军,与自己换了战马、如今还不知生死的太傅石德;愧对吉凶未卜的侯勇;愧对几十年来跟随在左右,如今正在长安城内抵抗的舍人和门客;他更舍不下的是,为了自己而遭受折磨的母后。那时,他还不知道皇后已经自杀的消息。
他将绢帛套进脖颈,用力蹬开脚底的石鼓,便觉得呼吸断绝,昏迷不醒了。
那石鼓倒地时的一声沉闷,重重地敲在李寿的心头。
“不好!太子有事。”李寿转身向门内冲去,却发现门关着。跟在他身后的从卒张富昌一脚踹开大门,就见太子悬在空中。张富昌一剑割断绢帛,李寿便从下面抱住了太子,连声呼唤:“殿下!您怎么了?殿下!您醒醒!”
太子的灵魂离开躯体后,在茫茫夜空中飘**,忽然听到有人呼唤,他睁开沉沉的眼睛,发现自己躺在李寿怀里,不禁潸然泪下:“你们为何要救我?本宫一死,一了百了。”
李寿一手抱着太子,一手接过张富昌递来的热水,一滴一滴地喂到太子口中。
“太子此言差矣。我们冒死护救殿下,所为者何?就是期盼有一日能真相大白于天下。殿下贸然一死,岂非自认有罪,也给奸佞提供口实?”
叙述完这段后,田千秋总结道:“臣闻疾风乃知秋草之坚劲,岁寒而晓松柏之不凋,板**乃识人臣之忠贞。李寿、张富昌者,忠信端悫,出死无私,致忠而公,是为功臣,然因太子罹难,至今隐匿皋泽,岂非圣朝之失乎?”
刘彻听到这里,摆手喊了一声“停”。年轻的黄门吃了一惊,还以为是自己念错了而惹恼了皇上。孰料,刘彻在感叹“又一个汲黯”之后,睁开眼睛道:“朕多年来,屡屡诏命两千石以上官吏举非常之人,于今方知,‘鹤鸣之九皋,声闻于天’,传朕旨意,封李寿为邘侯,张富昌为题侯。”
包桑急忙递过朱笔,刘彻思忖片刻,除了批示二人封侯之外,又加任李寿为未央宫卫尉。
刘彻放下笔,扬了扬手,示意黄门继续读下去。可接下来记述的事情,不仅让刘彻吃惊,而且几乎汗颜了。
陛下以太子谋反故,令郡国吏民以巫蛊相告言者,案验多不实。谗言罔极,交乱四国。然则,陛下不省察,深过太子,发盛怒,举大兵三百里而求之。三公自将,智者不敢言,辩士不敢说,更有甚矣,泉鸠里以兵刃围捕太子者,陛下封赏至厚,任以北地太守。其所谓亲痛仇快者欤。
这些事都是刘彻亲历的,听着听着,他就不觉心底颤栗,冷汗淋漓,拼尽力气大喊一声“罢了”。
包桑和年轻黄门立即跪倒在地,连道奴才罪该万死。
刘彻颓然地靠在榻上:“不关你们的事,朕是自愧不已啊!”
良久,刘彻从榻上挣扎着坐了起来,又在田千秋的奏章上加了一条:“北地太守追捕太子,罪在不赦。族其户。”
见刘彻有些累了,包桑问道:“皇上还要继续批奏章么?”
“还有要紧的么?”
“霍将军的上书到了。”
“哦!”刘彻沉吟一声,“你们先退下,朕自会观之。”
拆开信札,就着灯火看去,刘彻就感叹霍光的周详,他连皇上上了年纪都想到了,字写得很大,也很清晰。比起霍去病来,霍光不仅有将才,而且文墨通畅。一字一句,言辞恳切,胸臆坦**。
“哦!他真的读懂朕的谕意。”刘彻在心里对自己说。可读到后来,他的眉毛就紧锁住了,霍光所言之忧,竟与金日磾所虑、自己心头所系如此相通。
但是,毕竟他与钩弋夫人有长达八年的耳鬓厮磨,毕竟她是陵儿的母亲,毕竟她在李妍去后,给了自己情感和精神的抚慰。现在,因为立嗣而要将她……他一时无法面对这残酷的现实。
收起信札,刘彻觉得很累,人靠在榻上,心却不能归于宁静。眼前流过的,都是与她在钩弋宫中度过的情景。
包桑这时又进殿来了,他轻轻地唤道:“皇上!皇上!”
刘彻睁开眼睛,觉得有些昏花,问道:“有事么?”
“夫人求见,现在塾门候旨。”
“这个时候她来做什么?”
包桑摇了摇头:“夫人只说有要紧事求见皇上。”
“哦!宣她进来吧!”……
钩弋夫人清瘦的身影出现在温室殿门口,她看上去很憔悴,很疲倦,那双悲怆的眼中也流露出不掩的焦虑。
仅仅分开一个多月,现在出现在面前的钩弋对他就陌生多了,除了陵儿维系着两人的心,往年的那些临池观鱼,月下漫步,似乎都已经很遥远了。一如雾里看花,留在记忆里的都是些虚渺的影子。
刘彻说不清从什么时候有了这种感觉,也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对她有了一种莫名的疏远和厌倦。总之,她在这个时候到来,弄得他很不高兴。
“朕没有宣你,何事如此着急,非要亲自进宫禀奏?”刘彻折起霍光的上书,头也没有抬。
钩弋觉得皇上的话里没有温度,举止间早就丢了早年的烂漫和婀娜,而循了生分的宫廷礼节。
“臣妾叩见皇上。”
“有事你快说,说完就回宫去。”
“臣妾问皇上龙体安康。”
刘彻便显得有些不耐烦:“朕还没死呢?你有何事,快说!”
这冷冰冰的话,让钩弋打了一个寒战,说话的声音就显得颤悠悠了。
“臣妾听说皇上要火焚苏文,可有此事?”
“此廷尉所判,与夫人何干?”
“臣妾请皇上对苏文从轻发落。”钩弋也很吃惊,不知自己的勇气是从哪里来的,还没有等皇上回话,就喘着气将自己想说的话都说了出来。
“苏文触犯哪条刑律,被判火焚,臣妾不清楚。然臣妾记得,他在钩弋宫当差之时,一心一意伺候臣妾和陵儿;臣妾记得,陵儿三岁时,不小心绊倒在皇宫阶前,鼻孔流血不止。太医说用头发闷煅炮制的血余炭,才可止血。苏文二话没说,就剪下自己的头发,救了陵儿。没有苏文,焉有陵儿?因此臣妾恳求皇上,念在他一片赤诚,饶了他的死罪……”
“罢了!”刘彻打断了钩弋夫人的话,语气就重了,“夫人休要再说,苏文与江充合谋陷害太子,致大汉险些绝续,不用说火焚,就是死上千万次,犹不能平朝野之愤。”
“皇上,臣妾……”钩弋额头贴地,那长发都散在殿中央,“臣妾请皇上三思。”
“晚了!朕如果没有猜错,苏文现在早已成一堆灰烬,夫人还是回去吧!”
“臣妾已命人前去阻止。陛下一道谕意,即可保其性命。”
“放肆!”刘彻“嗖”的从榻上坐起来,手指钩弋怒吼道,“你好大的胆子,竟敢阻止朝廷行刑,难道你不知道后宫不可干政的训诫么?”
“皇上!臣妾……”
“休得再说!朕念及陵儿年幼,屡屡宽谅于你,孰料你不知深浅,竟敢阻止朝廷行刑,你项上到底有几颗人头?”刘彻怒气填膺,狠狠拍打榻床沿,“气杀朕了!来人!”
未央宫卫尉进殿道:“臣在!”
“送夫人回宫,闭门思过。”
“谢皇上隆恩。”钩弋夫人从地上站起来,凄婉地看一眼刘彻,一颗心就此碎了。她转过身时,流下了两行辛酸的泪水。
她脑子里一片空白,在自己的记忆中,她怎么也找不出两人独处时杀气腾腾的皇上,也无法将眼前的皇上与温柔乡里的男儿联系起来。
在即将走出温室殿的那一刻,她用力挣脱羽林卫,疾步跑到殿中央,那哭声中就多了许多幽怨。
“皇上!自皇上回到未央宫后,臣妾就没有再见到陵儿,臣妾恳请皇上,能让臣妾看看他……臣妾想他啊……”
刘彻愤怒地斥责着羽林卫,又对钩弋夫人吼道:“你目无朝廷法纪,愧为人母,永不可再见陵儿。还不退下!”
“皇上……”钩弋夫人被羽林卫簇拥着出了温室殿,很长时间,刘彻的耳际还回旋着她呼唤儿子的声音。
“夫人!休怪朕无情。悠悠万事,社稷为大!朕若再柔肠,只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