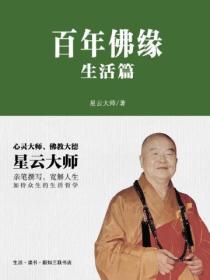与佛菩萨感应记
我一直相信:
“只要发心,佛菩萨不会辜负我们。”
这一句话看似简单,
实际上,在我一生信仰当中,
确实是这样体会:
发心,不是坐着等的,
不是光用要求来的。
发心,还是要流汗、辛苦、勤劳,
不然,哪里能成就呢?
经常有很多人祈求菩萨给予感应,
但菩萨也不一定来无影、去无踪,
他可能就是你身边帮助你的人。
有宗教信仰的人,都希望能有宗教的体验。宗教的体验不一定从外来的灵感,主要的是来自内心的升华,如果把自己一味地依赖给所信仰的教主,以他作为依靠,那就会失去自我的助力。佛教禅宗有云:“不着佛求,不着法求,不着僧求。”已经为我们做了说明,更重要的当务之事就是:“自己做自己的教主!自己做自己的贵人!”
我一生接触许多宗教人士,佛教徒、异教徒、神道信徒,都各自叙述他们的灵感。当然,像我在宗教七十多年的岁月里,也有许多超世俗人情的佛教感应,但是不好说。尤其,我倡导人间佛教,如同孔子所讲不语怪力乱神,但是灵感在宗教里,确实是平常、稀松见惯的事。
你很渴,吃一杯茶,不渴了,这不是感应吗?你很饿,吃一碗饭,不饿了,这不是感应吗?冷了,加一件衣服,就会暖和,这不是感应吗?别人一句赞美的话,引得我心花怒放;别人的一句批评,叫我灰心丧志,这不都是感应吗?感应,不一定从佛菩萨那边要求,生活里面到处都有感应。
所谓“灵感”,就是感应,你敲钟,钟就“当!”一响;你打鼓,鼓就会“咚!”一声。敲钟、打鼓,当、咚各响,这不就是灵感吗?
我勤于读书,以智慧抉择事物,智慧就是我的感应;我慈悲待人,别人也回报我友谊,慈悲就是我的感应。原来,感应不一定是向佛菩萨祈求,自己也可以创造自我的灵感。
我也常想,我们的感应究竟在哪里?我帮助别人,别人也会帮助我;我服务别人,别人也会为我服务,这种交流不就是感应吗?所以,灵感是有因果的,你有善因好缘,怎么会没有感应呢?
关于灵感,在《法华经·观世音菩萨普门品》中,有显益及冥益二说。所谓“显益”,就是观世音菩萨的三十二应化身,应以什么身得度,就现什么身而为说法,这就是显益;现在生气烦恼,自己的嗔恨之火正焚烧自己,假如称念“南无观世音菩萨”圣号的时候,嗔怒会消逝,这就叫冥益。
《普门品》中提到的三毒七难。比方:“若人多于**欲,称念观世音菩萨,便得离欲。”**欲心重的人,只要称念观世音菩萨,自然就会离欲。别人骂我们,如同刀剑一样刺激我们,心中称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我不感觉难堪,甚至顺着对方的话“你骂得好”,继续称念“观音菩萨、观音菩萨”,那么,责骂的刀剑,伤害不了我们,这就是冥益。
又例如,文中提到的“二求愿”也是冥益。经文中:“若有女人,设欲求男,礼拜供养观世音菩萨,便生福德智慧之男;设欲求女,便生端正有相之女”,说得实在巧妙,求男要具有“福德智慧”,因为对男生来说,福德智慧很重要;求女时要求“端正有相”,因为对女孩子而言,庄严漂亮是最重要的了。
其实,这也是一种胎教。因为母亲怀孕时,心怀慈悲、善意,情绪平和、理智,生下的儿女,性格会不一样。倘若母亲的情绪暴躁,胎儿也会受到影响,这也是老一辈的人为什么说怀孕的女孩子,要在家休养,不要做事。不过我想,重要的还是内心要培养慈蔼、和气、温柔才是。
有人问有没有观世音菩萨?何以证明有观音菩萨?具体来说,佛教里有五量:现量、比量、譬喻量、神通量及圣言量;唯识学家也有现量、比量、非量等三量可以说明。
“茶杯在哪里?”“茶杯在这里。”“卫生纸在哪里?”“在那里。”这很容易了解。因为看得到,我能证明存在,你不能说没有,这就是“现量”。
有人问:布有多长?你拿尺一量就知道了。这个东西有多重?你用秤一称,就晓得了,这叫“比量”。
什么是“譬喻量”?你说木头棍子很硬,到底有多硬呢?我找一支很硬的铁条给你看,就是这么硬。“盘子有多大?”“桌子有多大?”我告诉你就像什么东西一样大。什么叫“无我”、什么叫“舌灿莲花”,我用一些譬喻来说明,让你能明白懂得,这就叫“譬喻量”。
至于“神通量”,我不知道神通,也没有神通,不过,有神通的人会知道。例如,晋朝佛图澄大师为了感化石虎、石勒兄弟不要再杀人,他对着一盆水念念有词,盆里缓缓地长出一朵莲花来,石虎、石勒看了惊叹不已。从此,无论他们性格再怎么凶残,都相信佛图澄的话了。这就是神通量。
又例如吴国孙权,原本他也不相信佛教,康僧会对着铜瓶焚香礼敬,过了三七日,最后瓶子终于“咯!咯!”声响,生出了舍利子来。至此,孙权也不得不相信康僧会了。不过,神通也不是人人都相信,当场见到的人相信,没有见到的人就不一定相信。
最重要的是“圣言量”。这是指圣人的言语,没有一句是乱说,也没有一句话是不对。例如,释迦牟尼佛是圣者,他说有观世音菩萨,你能不相信吗?当然,有人会说:“念观音、拜观音,不如自己做个观世音。”观世音菩萨就是我们自己,反观自性,这就说明有观世音。
观世音菩萨有谓“三十二应遍尘刹”,到处随缘应化,这就是感应。但是,感应也要合乎因果。比方《阿含经》中有个例子,一块石头要沉下去,你祈求:“神明,神明!让这块石头浮起来吧!”这是不符合因果的,你祈求也没有用。油是浮在水面的,你祈求:“神明,神明!让油沉下去吧!”这不合乎物理,你祈求神明也没有用。因此,讲神通、灵感,都是要有一定的因果法则。
佛教讲五戒,你能持守五戒,用行动奉行,就会获得感应。有的人跪在佛菩萨、神明的前面,祈求自己能够长寿。其实不必,只要你受持五戒中的“不杀生”,不侵犯人的生命,甚至积极护生,不必佛菩萨帮忙,你自己就会帮自己长命百岁了。
也有的人跪在神明前面,祈求神明让自己发财、富贵荣华,你说,哪一位佛菩萨、神明来赏赐给你呢?你必须借助信仰的力量,不偷盗而喜舍布施,好比你在田地里播撒了种子,还怕不能生长?不能有收成吗?
经常有很多人祈求菩萨给予感应,但菩萨也不一定来无影、去无踪,他可能就是你身边帮助你的人。
好比国共战争发生时,这是国家的大事因缘,我没有办法抗拒,只能随着人潮来到台湾。过去,我并没有到台湾的念头,台湾在哪里我也不知道,但就是这样随着大时代环境来到这里。虽然我在台湾无亲无故,无处安身,但是因缘很好,感谢中坜圆光寺的妙果老和尚,当时大部分的人都离开了圆光寺,却有些少数的人得以留下来。你说这不是感应吗?他不是活菩萨的示现吗?
我在台湾留了下来,吃住都解决了,但实在不得穿。刚好有一位老太太给我一条她的长裤,乡下老太婆的裤子都是很宽大的,我也没觉得很“歹势”(不好意思)就接受了下来。后来,她又给我一件女众穿的海青,像条裙子一样,倘若现在拿出来看,一定会给人取笑,但我也就这样穿了。北台湾的冬天,天气还是很寒冷,妙果老和尚给我一件旧夹袄,我没有嫌弃,反而很高兴。衣、食、物,我不嫌弃它,这许多东西就会跟我很亲,便会自动出现。我少了什么,它们就自动跑来,这不是生活上的灵感吗?
后来,有人给我一块布料,我做了长衫、海青,着手缝制时,也有人自愿前来帮忙。那时候,有一位性定法师对外省人不是很好,但是奇怪的是,却肯帮我这个外省人做这许多事。这不都是因缘吗?
那时候心想,我无法一直寄居在圆光寺里,未来前途该怎么办?不久,就有台北广播电台找我写文章,随后又有《自由青年》找我编辑写文章。如果现在有人来找我做广播节目、要我写文章,这是很稀松平常的事;但在那个社会局势都还不是很稳定的时代,就有因缘来找我,这实在也很不可思议。
有一次,顾正秋女士在永乐戏院演出《火烧红莲寺》,内容涉及诋毁佛教,我在刊物上写了一篇《致顾正秋小姐一封公开信》表示抗议。当时,顾正秋是剧坛名伶,假如她不高兴,只要跟蒋经国先生讲一句,恐怕我的头就掉地了。但即使如此,为了护法,我也要勇敢地去做。其时,类似这样的事情发生过多件,也不及一一去叙述了。
建筑师姚仁喜(对面)汇报佛陀纪念馆设计方案(二〇〇四年三月十五日)
前几年,我和顾正秋女士还在佛光山台北道场见过面。她送我一本她的传记,我请她吃一顿素斋,席间相谈热络。她的女婿姚仁喜、女儿任祥也都支持我们,还帮忙我们建设佛陀纪念馆,因缘也是相当奇妙。
说来,妙果老和尚、顾正秋女士都是观世音菩萨给我的感应,他们一个以比丘身说法,一个以妇女身说法。因此我常说,从内心去体验,只要我心中有佛,看到的世界都是佛的世界;只要我心中有佛,耳朵听到的声音都是佛的声音;只要我心中有佛,我的语言都是佛的语言;只要我心中有佛,看到的这个世界,到处都是佛、都是菩萨,我的周遭都是与佛菩萨为邻。这就是我的灵感。
在我年轻时,心里有一股为教的热忱,应该是可以进到“中国佛教会”服务的,因为他们需要人,我也需要“中国佛教会”。但是,如果我进了“中国佛教会”,就会变得肤浅、世俗。那个时候,本来宜兰对我来说,也是没有来往的因缘。但是有一天,慈庄法师的父亲李决和居士,在佛教会见到我,于是邀请我去宜兰弘法。我真是把李居士看成真的菩萨,他流露的慈祥、爱语,给人感觉就是一个好人。我十分感动,决定要前往宜兰,从此展开我在台湾数十年的弘法历程。这能说不是灵感吗?
在此之前,初到台湾时,由于被密告是匪谍而被拘留起来,那许多在外面为我们奔走,想法子营救我们的人,由于他们的搭救,才有我后来的这种种弘法。说来,他们不都是佛菩萨?他们不都在救苦救难吗?
到了宜兰以后,实在讲,倘若今天给哪一个人去驻锡弘法,可能都住不下去。为什么?不管他有什么天大本领,第一个面临的问题就是:没有厕所。过去,我们在大丛林里面生活,设备、环境再怎么坏、乱、不好,必定都还有厕所。一个人内急之时,没有厕所可以使用,第一个条件就住不下去了。
第二,没有电灯。这对我而言倒还不要紧,因为我也不曾用过电灯,只有短期停留在南京华藏寺时曾经使用过。像我住过的栖霞山、焦山、宜兴大觉寺、中坜圆光寺、新竹青草湖灵隐寺等处,都没有电灯。
第三,没有住的地方,床也只有用几张桌子拼凑起来,简陋的床铺,让人一坐下来,声音就响亮得吓人;而书桌只能用裁缝机充当桌子来写文章。我在大陆做学生时,至少都还有张桌子可以写字。现在请我来讲经,连一张桌子都没有,这实在太没有条件了。
此外,我经常形容的,吃饭的时候,四方形饭桌是用二块木板钉起来的,中间还有一条五公分宽缝隙;汤匙则是用薄薄的铝片自己做成的,风一来,很容易就吹走了。
我是在刚过完年的农历正月到了雷音寺,那时候,一走出佛殿门口,就可以看见丹墀上挂着许多腊鱼、腊肉,大概是寺里的三户军眷人家,他们过节吃不完的腊货,准备晒干之后慢慢食用。甚至还有男男女女、小孩子的衣服、小裤,也通通都挂在一起,可以说,环境条件比过去的大杂院还不如。
台湾佛光山寺——大悲殿内白衣观音(佛光山馆藏,林艺斌摄)
大悲殿白衣观音
位于佛光山西山丛林学院女众学部区域,殿内供奉的白衣观音大士高约七公尺,四周供奉有万余尊观音圣像。当初名曰“万佛大悲殿”,在《觉世》旬刊刊登启事,欢迎大家捐献一尊观音。想不到号召力大,连台北的出租车司机都寄钱来响应。
一九七一年大悲殿落成前几天,我和慈庄、慈惠、慈容法师,以及当时还是学僧的心定和尚,每晚都听到悠扬的梵呗声,恢宏深广,遍于虚空之中,感受到好似万佛围绕。
别的不说,一般人光是看到这种情况,想必是不想留下,放弃走人了。当时,雷音寺确实没有生活上的条件,如果我不接受也是可以,因为也没有人强迫我一定要接受。但奇怪的是,我并没有被这个艰困的环境打倒,反而很自然地就接受了。想到地藏王菩萨“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誓愿,如果我不来宜兰度众生,谁来度呢?我想,这正好可以给我有个用武的机会。
后来,我在寺旁边加建了一个小型的讲堂,但是宜兰包括头城募善堂和罗东、苏澳等地的各个神庙,都是金碧辉煌。宜兰县议会开会时觉得很奇怪,怎么宜兰这么多的寺庙纷纷复兴要重新建设?
在当时,其实我还没有力量重建,但信徒他们有办法修建,只不过县议会不了解,寺院的重建,是我们弘法的效果。因为大家听经闻法,生起信心,不断发心做功德。我在台湾各处弘法,撒遍这许多菩提种子,才有这种发展的基础,但他们哪里会想得到这与我是有关系的呢?
宜兰,真是一块极乐净土,那里的歌声梵呗嘹亮,童男童女围绕,将军身、梵王身等各界的人士,我没有见过,并不认识,但他们全都来了。佛祖慈悲,以种种因缘方便,让那许多的善知识、善护法一起前来护持道场。
我在宜兰弘法来来去去前后二十多年,但世间无常,总要有离开的时候。当时没有人传灯,没有人出家,因此这盏灯也不晓得传给谁?宜兰的寺庙,在我初到时曾经算过,没有一家寺庙的出家人不是半路出家的。他们大多是在中年时期,带儿带女、携家带眷出家。
后来,我决定去发展佛光山,舍不得的,是宜兰一直跟随我的那许多老先生、老太太和年轻人,他们都是跟着我,经过许多苦难的岁月一起走过来的。我放下了他们就离开,正是大家道心坚固、已经形成一个道场的时候。这许多信徒学佛需要人领导,我只有告诉他们,依法不依人,学佛不在一时;我在台湾弘法也遇到一些挫折阻碍,不过总是一一克服化解。因为尽管这娑婆世间如污泥,只要我们自己做一朵莲花,污泥也会成为修道上的灵感。
在宜兰弘法的感应事迹,除了上述说的“显益”外,也有一些“冥益”的事情。
首先,一位姓曾的退伍军人,因患风湿症瘫痪了八年,两条腿瘦到仅存皮包骨而已。一九五八年我在宜兰念佛会主持佛七,每一天他都坐在旁边随众精进念佛。到了第七天,清晨早课念佛的时候,我坐在佛前领众共修,他竟然站了起来,走到我前面向我三拜。我吓一跳,心想,曾居士往生了吗?怎么这时候灵魂来跟我礼拜?不过,也不必害怕,有这么多人在这里念佛,就是鬼,也不值得我惊吓。他满面红光,就像喝过酒一样,三拜以后,我说:“好了,三拜就好。”
曾居士看着我,我想,他是想跪下来跟我讲话。但我那时候还不晓得怎么回应他,这太突然了,便说:“回去再念佛。”这时候,大众正在念诵《弥陀经》,念过之后,接下来就是绕佛,他也站起来跟着大家绕佛。
他瘫痪了八年,双腿早已没有知觉,完全要靠两张短小的竹凳子协助,先把二个小凳子摆到前面,再用双手撑起身子,整个人才能往前移动。他信佛虔诚,家就住在距离雷音寺不远,每次都会来参加共修。所以到了要念佛了,我都叫人去把他背到寺里来。这件奇妙的事情就这样传了出去,轰动整个宜兰。
后来我问他:“你怎么忽然会走路的?”
他说:“我也不知道,只是感觉到有一股热气冲上来,两腿突然觉得有力,我就试着站起来,然后很自然地就走去向你礼拜了。”
第二件事就是雷音寺的大佛开眼。
一九六四年雷音寺举行佛七,供奉在佛殿中央的是刚从香港塑造回来的佛像,非常庄严。一天清早,有一位名叫邢大军的退伍中校,他问我:“师父,这个佛像里面是不是有机关?”
“佛像怎么会有机关?没有啊。”我回答。
邢大军说:“可是,我看到他的眼睛睁开。”他是一个很正派、虔诚的佛教徒。我就说:“大概是你看到佛前的蜡烛光影在飘吧。”
过了一会儿,又有很多人谈说:“佛像开眼了!”一时之间,大家纷纷传述。
到了晚上,法会即将开始,我也在外面准备好即将上殿,等待司法器人员敲磬后,就进殿里拈香主法,但是隔了好久都没有动静。平常,法会都有一定的时间、程序,这么久了,怎么还不敲磬让大众礼佛三拜呢?原来,每个人都在大殿里争看大佛开眼。
就在这时候,有一位五六十岁左右的女众信徒,跑来一把抓住我:“师父,你来看,佛祖开眼了!佛祖开眼了!”这个当下,我怎么可以听她的话,让她抓着我进去看大佛开眼呢?
我说:“好啦,你去看就好了。”
她又说:“走不进去啊!”
我说:“你敲引磬,大众就会让路了。”于是,他们就敲引磬,让引礼师六人进去引导大众开始唱诵《香赞》。法会前的三拜,每一个人礼拜,都像是朝着天在拜似的,因为大家看到佛像开眼了,心情都很激动。他们三拜过后,就是轮到我要进殿了。我心想,佛像究竟有无开眼呢?
那尊佛像很高,一般我们都不会特意朝上看。我想,如果我看到开眼,当然就要照实说有,可是就会有人说你宣传,毁谤你。算了!不要看吧!我也就特意不去看佛像了。
但是,人心还是很矛盾的。我走到佛前拈香礼拜的时候,很自然的,往上看了佛像。“咦?没有开眼啊?”三支香拈过了,我回到主法的座位上,很安心地随着法会程序唱《香赞》、诵《弥陀经》、绕佛。
绕佛的时候,我走出大殿,同时也把念佛会的总干事林松年喊了出来。他是一位新潮的人,但是对佛教相当虔诚。我问他:“佛像有开眼吗?”
我只是想,等一下绕佛后的开示,一定会讲到这件事,我必须要求证一下。
林居士的性格冲动,马上大声地责备我:“怎么没有开眼!”
我也不多作解释,只是说:“好啦,我知道了,进去念佛。”
于是,绕佛结束后,大家坐定下来,我为大家开示说:“佛陀开眼不开眼,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开我们的心。我们的信心门要开,要找到自己内心的宝藏,这个才是重要。”
我不知道这件事对我有什么样的影响?但是事隔好多年,再回到宜兰念佛会的大雄宝殿,念佛的人数也没有减少,不管有没有法师领导念佛,都不要紧。为什么?在信徒心中:这尊佛像是开过眼的。
所以说,佛菩萨都在帮助我教化众生,让我可以代他到各方去弘传教法。直到现在,宜兰信徒的信心,仍然坚定不变。
我一直相信:“只要发心,佛菩萨不会辜负我们。”这一句话看似简单,实际上,在我一生信仰当中,确实是这样体会:发心,不是坐着等的,不是光用要求来的。发心,还是要流汗、辛苦、勤劳,不然,哪里能成就呢?
一九六七年我来到高雄佛光山开山,因为我有心想要办学。那个时候,凭我个人,哪里能办学?又无寺庙,又是外省人,也无任何基础,只可说是穷光蛋一个。但我是真心想要办学,虽然我们只是一个小小的寿山寺,我也要很认真。而且我办的佛学院,不要像别人办一期三年就不办了,是要一直办下去的。后来因为学生增多,寿山寺不得地方住,越南华侨褚柏思夫妻来找我,给我一块土地,就是现在的佛光山。
当时,我到山上来勘查,发现这是一块荒丘之地,水土都给雨水流失了,到处是深沟,我哪里有办法建设呢?虽然我也知道这块土地贫瘠,但是我也没有能力再去找更好的地方。土地虽不好,总是我的,当然也希望获得信徒的了解和支持,于是便带人一同前来察看。哪知道,他们看过之后,竟回应说:“这种地方,鬼都不来。”
我听了以后,一点都不伤心难过,心里头想:“鬼不来很好,只要佛祖来就好了。”后来我想,当时的这个念头,就是佛祖给我的灵感,不然,怎么说得出来呢?
那个时候,连现在大雄宝殿的那块地,都还没能力买下来,从朝山会馆往后的地界都是别人家的,虽有平地,但我不能动啊!而属于我们的地,仅仅只是从现在男众学部的水塔处到万寿园,形状就像一把刀一样。再从“大海之水”这个地方到朝山会馆前面,绕到大悲殿,往下到现在的香光亭、西来泉,这也都是长形的山沟地貌。你想想,这哪里有平地?没有办法可建啊!
就是现在不二门、灵山胜境这块平地,也是非常勉强,艰难地开发出来的。过去都是土丘,只有慢慢地把土推到两旁,整平而成。那时候也没有水土保持,就这样做起来了。
佛光山大悲殿落成开光,人潮行经宝桥盛况(一九七一年四月十一日)
看起来好像也没有什么了不起,但很奇妙的,在整地的过程中,我们发现现在大悲殿的所在,是一块平地。“有希望了!终于可以建一座佛殿了。”
于是,先从这块平地的下方建设东方佛教学院的院舍开始,建好之后,再建大悲殿。过去,院舍落成的时候,一般人说有十万人前来,我想五万人是少不了的。后来又过了两年,大悲殿落成了,也不只五万人以上参加,满山满谷的人潮,真是盛况空前。
经济上的困难,使得院舍还没有办法装修,不过总之盖了屋顶,也有了门窗。
佛光山刚开山的时候,我在高雄欠了很多的建筑材料费用,再加上举办第一届大专佛学夏令营(一九六九年),我也担心未来还债,恐怕会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想不到就在夏令营开营的第三天,从不平的土堆山丘工程中,不知从哪里走来一位打着赤脚、拿了一顶斗笠的老太太,竟然用报纸包了五万块给我。那时候的五万块,价值应该是现在的五百万以上;我才将款项收下转给负责会计的徒众,转身要找这位老太太,却怎么找都找不到了。你说,佛光山不是到处都有菩萨?到处都有这许多感应吗?
深刻的印象中还有这么一件事:一九七二年,有一天晚上,我在佛教学院慧明堂外的阳台上,朝向大佛城的方向欣赏夜色,大约是在九点半前,我看到一道光照在龙亭上。这道光,并不是一般的阳光或是电灯的光线,而是像鸡蛋黄一样,很柔和的金色光,把整个亭子都显现出来了。我心里想:“怎么那么亮呢?大概是卡车的光打到上面去了吧!”因为那时候,山下的道路上,会有很多卡车在夜间行驶。
佛光山大众在大悲殿兴建工地(一九六七年六月十八日)
“但是,卡车的车灯照映上来,应该打在下方,怎么连屋顶都是亮光呢?”我正在想着,一位郑宝秀同学跑来向我问事情。因为九点半正是接近佛学院打安板,学生准备熄灯要睡觉的时间了。我讲了二三分钟,交代以后,她就走了。我回头再朝龙亭一看,刚才的亮光没有了。
这一件事情,让我联想到栖霞山的无量寿佛。我就读的栖霞律学院后山,有一个地方叫千佛岩,是南齐明僧绍夜晚讲《无量寿经》时,忽见岩边放光,因此发愿在那里开凿了千佛岩,其中最大的一尊佛即名无量寿佛。我想,现在看到那一道光,是不是佛菩萨要我在那里建一尊大佛呢?可是,以我眼前的情况,哪里有这个能力建大佛?不可能的,我连买个茶杯都困难了,怎么有力量建大佛?
但心念一转,佛像艺术雕塑家翁松山不是在这里吗?不妨问他一问。我说:“翁松山,你能做尊大佛吗?”他回答说,“我先把佛陀的模型做出来给您看看吧!”就这样,后来果真用水泥塑灌成功。从此,佛光山接引大佛就站立在东山上,迎接着每日的第一道朝阳,也迎接着每一位有缘众生。我想这都是灵感所成,该你成就多少,就是成就多少,也不要妄求。
佛光山的开山建设,可以说就是在“日日难过日日过”中进行着,幸好有千千万万的信众人士共同护持成就。记得初创的时候,旅居美国的沈家桢居士托人带信说要捐我五千万。那时候的五千万,已不只现在的五亿元,至少也十亿以上了。他并且说:“我帮你建佛光山。”在这样的条件下,有谁会不要呢?但是我回复说:“谢谢,不用了。”
为什么我会有这一个念头呢?我想,我自己在台湾收人家十块、二十块的捐助,累积万千人的发心,慢慢地建佛光山。假如建成以后,人家说佛光山是美国沈家桢建的,只因为他钱出得多,那么,我会对不起台湾人。所以,不要这五千万,我宁可要五块、十块,因为佛光山是大家发心建起来的。现在想来,我认为这也是我的灵感。
台湾佛光山寺——大佛城(慧延法师摄)
大佛城
大佛城坐落于佛光山东山,居高临下,与大智殿相毗邻,是来山信众必到圣地。接引大佛高一百二十余公尺,面向东山日出,俯瞰高屏溪。我为此作偈:“取西来之泉水,采高屏之沙石,集全台之人力,建最高之大佛。”可见建设大佛城的工程及投注的人力。四周有四百八十尊阿弥陀佛围绕,入口回廊墙上,塑有大忏悔文、毗尼经三十五玉佛,四周为五方佛、无量寿佛等,飞天舞跃其间,护法金刚排列,神情生动,栩栩如生。另有毗卢遮那佛、文殊、普贤菩萨,迦叶、阿难二尊者,象征南北兼扬、显密融通,明镜高悬,光光相映。中央须弥座下,设有“大佛法语”,为参礼者开示,增长慧解。
率领弟子们至日本访问立正佼成会。前排左起:杨慈满、慈容法师、慈庄法师、慈惠法师、依严法师、心舫。后排左起:萧顶顺、翁松山、心定法师、心平法师、煮云法师、本人、圣严法师、宽裕法师
自从开创佛光山以来,从信徒的口中,就不断地传说大雄宝殿佛祖的灵感、接引大佛的灵感、观世音菩萨的灵感,那里有现世的因果、好心好报、恶心恶报等等许多灵感的例子。我们要知道,灵感的发生,不能只靠祈求,不能只想到助缘,一定有很多的因缘果报关系。在佛光山发生的灵感事迹不少,我也不方便叙述过多,仅举出几个例子,把这许多感应的故事略微记录下来。
早期,心定和尚也跟随着我参与开山建寺,他经历了两件事,都是在开山之初所发生的。一九七〇年,联邦德国有一位青年叫何吉理(GehardHerzog),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硕士,因为仰慕中国大乘佛教的教义与修持,特别申请来台,并且住在佛光山,研究寺院丛林所见。喜爱梵呗诵经音声的何吉理,为了让居住在联邦德国的母亲也能听一听中国佛教的梵呗,有一天晚上,他找到心定法师为他诵念一部《心经》,以便录起音来寄回去给母亲。
当他们诵完《心经》时,何吉理站起来,沿着大悲殿周围走来走去,好像在找什么东西似的。心定问他:“你在找什么?”
何吉理说:“刚才那三棒大磬的声音,是从哪里来的?”被他这么一问,心定也有点惊讶。“是啊,刚才那三棒大磬声是哪里来的呢?”在佛门,通常在唱诵赞子之前,要先敲三次大磬收摄身心,那么清脆幽远的磬声,确实不知从何而来。我想,菩萨或许是被何吉理先生的一片孝心、诚心所感应的吧!
另外一件事,是在一九七一年大悲殿落成的前几天。当天晚上八点左右,我在大悲殿瞻仰菩萨圣容,忽然听到钟、鼓、铛、铪等敲击的声音,清晰得仿佛就在耳边。但由于有空间的回音,那声响,仿佛有一种恢宏的气势,听起来特别的深广,似乎遍于一切虚空之中。
第二天,慈庄、慈惠、慈容法师等人随我到大悲殿,也同样听到梵呗的声音,当时在场的人感受到好似万佛围绕。惊讶之余,当时还是学僧的心定,刚好走了出来,我就问他是否有听到?他淡淡地说:“我每天晚上在大悲殿抄写信徒功德芳名,都会听到这悠扬的课诵声啊!”
还有佛光山的灵感事迹中,一直以来最令大众津津乐道的,应该就是大佛转身了,不少信众来山参加万缘水陆时,都曾亲眼见过。
一九九四年,慈嘉法师的弟弟郑秀雄老师上山来参加水陆法会。那一年,大佛很慈悲,在法会期间,几乎天天转身,大概是想增加信众的信心吧!
有一天晚上,郑秀雄老师与慈嘉法师走在一起,走着走着,大佛又转身了,当许多人不约而同就地礼拜的时候,郑老师身边有一位五十岁左右的女众信徒,一边缓步走上来,一边嘟囔着说:“奇怪?我怎么没看到大佛转身?”
“不是大家都有看到吗?只有她没看到,怎么这么奇啊?”虽然郑秀雄心里这么想着,但也没有多说什么。
佛事进行到圆满送圣的那一天,他因为有事迟到,便排在大雄宝殿前丹墀的最后一排。仪式开始,突然听到背后大佛城的方向,发出隆隆的声音。郑秀雄老师和大家回头一看,原本背对大雄宝殿的接引大佛,正缓缓地转过身来,佛颜含笑,金色的佛身,通体大放光明,连身上一条一条的袈裟褶痕,都清晰可见。不少人至今仍然啧啧称奇。
同样也是接引大佛的灵感,侨居香港的李志定居士,由于工作关系,经常往来香港、美国之间。一九七九年某一个晚上,睡梦中,见到一尊非常高大的佛像对他说:“我是从佛光山来的,衣服已经破损不堪了,你能发心为我修补吗?”
醒来后,梦境历历如绘,李志定居士不断思索:“佛光山在哪里?”因为他不曾听过佛光山。经过打听,得知在台湾高雄,于是千里迢迢前来一访。走上大佛城,赫然发现,大佛右下角的油漆已剥落,于是向知客法师表明来意,并且发心捐赠,让大佛重新粉刷。
刚刚述及大悲殿里的灵感事迹,而关于观世音菩萨灵感事迹,不得不在此一提。曾经听住在山下的居民说,他们看到大悲殿上空,出现了五彩伞盖,观世音菩萨从天而降;也听闻观世音菩萨经常到外面去度众,不少人都是因此仰慕而来山朝圣。甚至不少善男信女求子得子,求女得女,所求如愿,尤其观世音菩萨的现身,也是众人所乐于谈论。可以说,观音菩萨的感应,实令人敬仰。
一九八二年暑假,有不少的信众来山礼拜挂单。有一天晚上,我正在丛林学院圆门,为学生讲授“僧事百讲”,隐隐约约,听到背后宝桥的方向一片喧哗。
为参加佛光山万缘水陆法会的信众开示。把参加法会当作“六根”训练班,修好一颗心,让心能够作主,就是最好的感应(蔡荣丰摄,二〇一二年十二月一日至八日)
原来,大悲殿东侧的山壁上,出现似黄似红又带点白紫,说不出是什么色彩的光环,吸引了不少信徒、游客的驻足围观。当中,有人看到光环中有观世音菩萨的现身,有人只看到一闪一闪、柔和美丽,又呈辐射状的光环。这道光环的出现,大约是在晚上八点半至九点五十分左右,共历时一小时又二十分,所有见到的人,无不满心欢喜。
说到这里,我想,所谓“灵感”,也不全是好的事情才算感应。比方:财神爷送钱来了,意外获得奖金了,这才叫感应吗?不是的。其实,苦难、考验、艰辛,也是一种感应,一切感应都要经过考验,才能获得真正的感应。
佛光山很多不可思议的缘分,例如:佛光山没有人出去化缘,不要钱,也没有钱,但需要的时候,它就来了。像过去朝山团从台北到佛光山,一趟行程三天二宿,只酌收二百元。当时台北高雄的火车票价都还要三百块,可以说,连过路费都不够了。不过我想,只要有人来了,就有感应。
后来,佛光山外来的因缘促成开枝散叶,到处要求要建寺院,可以说,真是佛菩萨三十二应化身,无处不现身。所以我说,佛光山的别分院不是人要的,都是佛菩萨要建的。
因此,假如把感应用神通来解释,就可惜了,那只能叫神乎其技。而感应,应该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挚诚,才叫做感应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