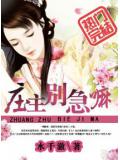新中国成立后,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制度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儿童文学工作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在党和政府的关心与积极引导下,儿童文学的发展在50年代中期出现了一个被后来称为“黄金时期”的繁荣局面,“一年比一年出版并发行了质量较高、数量较多的儿童文学书籍。特别是在量的方面发展得更加显著,仅以少年儿童出版社来说,1954年发行数字为上年的四倍半,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出版了2800多种,发行了6000多万册(发行数字不包括少年儿童阅读的连环画)的相当巨大的数字的儿童书籍”。这些读物,从思想内容方面来看,包括了各个方面,有关于革命英勇斗争的,较优秀的作品如《鸡毛信》等;有关于学习和纪律的,较优秀的作品如《罗文应的故事》;有关于集体主义、团结友爱的,较优秀的作品如《吕小钢和他的妹妹》等;有关于‘儿童生活’的,较优秀的作品如《小胖和小松》、《海滨的孩子》等;有关于科学知识的,较优秀的作品如《我们的土壤妈妈》、《森林的故事》等;此外还有关于英雄模范的,关于国际主义和和平与友谊的,关于爱国卫生的……所以在主题和题材的广度上看,已经逐渐远离了狭隘的窠臼,走向广阔的平原去。然而就这样,也仍然“不够广泛,不够少年儿童要求书籍来满足他们自己的好奇和求知的愿望”,因为“儿童读物有它的特点,在读者年龄的特征上不仅要有‘分类’,更有‘分年’的必要,在这样的规律之下,2800多种书就像汪洋大海中的几个岛屿,显得更加单薄而寥寥可数,远远地落后于客观的殷切的需求,与祖国在经济、文化建设各方面飞跃前进的形势,在比例上感觉到太不相称了”。数量是如此,质量上又如何呢?陈伯吹认为仍然存在着许多不如人意之处。
首先是“科学知识技术结合着劳动生产的科学文艺读物非常少,现有的一些,只是一般知识的硬绷绷的叙述,缺乏文学因素,不能很好地用艺术手段来传授知识技术和启发热爱对科学事物的兴趣。10岁左右的小学生爱看的‘科学童话’几乎没有”。
其次,“关于描写英雄模范人物的斗争事迹的书籍,也是比较弱的一个部分。一般地说,内容写得不丰富、不细腻,不能把英雄人物写得有血有肉,这样就不能使小读者获得深刻难忘的印象,起着典型示范的教育作用。又因为一般都只是罗列事迹,平铺直叙,写得干枯单薄,不但不能激动小读者的心灵,反而把英雄形象和卓越事迹‘贬值’了。于是他们只能超越年龄地去硬啃那些翻译的大部头的有关英雄人物的传记文学作品了”。
第三,“对少年儿童进行社会主义的劳动教育的作品又是一个较弱的部分”。
第四,“从艺术形式上来看,虽然文学的各种体裁已经具备,达到了多式多样的境地,可是10岁以下的儿童所心爱的‘童话’,却是连年歉收”。“诗歌的产量虽然较多,但还不是‘陌上青青,红杏出墙’的春天原野的景象,少年儿童还很少能从我们的诗歌里获得清新的诗意和审美的感觉,多半是一些押了韵的标语、口号式的‘诗的语言’,难怪小读者们不能琅琅上口,不能达到‘口而诵、心而维’的意境。我们写的诗歌没有把政治思想溶化在作家的优美的思想感情里,水乳交融地通过美丽的想像的具体形象,从笔端上表达出来。对于艺术加工也没有给予充分的应有的注意”。
第五,“还有讽刺小说、惊险小说、科学幻想小说,作品在这方面也是绝无仅有的”。
综合上述五个方面的明显不足,陈伯吹认为:“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初步的结论:解放后将近6年来,我们的儿童文学工作是肯定有成绩的,但是它的现状还是不能令人满意。为了全国不同年龄和不同程度的一亿二千万的少年儿童,对于精神食粮的‘嗷嗷待哺’的情况是必须就从今天起大力改善它,并且立即用切实的办法来推动工作。”为此,陈伯吹提出了4个方面的要求:
首先是繁荣创作。有成就的作家们必须把创作儿童文学的计划列入创作日程中去,当作一个严肃的政治任务来接受,要认真地保证质量,超额完成。儿童生活不理解,可以下去体验;儿童语言不熟悉,可以深入学习;……任何理由都不能成为推诿的理由。应该说没有一个作家是会在困难面前低头却步的。
其次是原来从事儿童文学工作的同志们,不论过去在搞创作、搞批评研究,或者在编辑书刊,甚至在学校担任教学儿童文学的,现在应该更加发挥潜力,群策群力地搞好这个工作。
再次,教师和辅导员无疑是最了解儿童心理、最富有儿童生活的人,如果有人(当然不限于教师和辅导员)爱好儿童文学、具有一定程度的文学修养和创作基础的,在提出了创作计划以后,通过一定的步骤,应该得到积极的帮助。
报纸、刊物对于繁荣儿童文学创作,起着巨大的推动作用,所以也就担负巨大的责任,要经常注意选刊有关儿童文学的作品、研究、评介等文章。那些与儿童文学有血缘关系的文学、教育刊物,在编辑和选题计划上,应该把关于儿童文学的稿件,考虑作为重点之一来组织、审读。
上述关于“儿童文学现状”的认识与分析,所引文字,均见陈伯吹写于1955年9月10日的《关于儿童文学的现状和进展》,发表于1955年第11期《新华月报》。此后,陈伯吹又陆续发表了《谈儿童文学创作上的几个问题》(1956)和《谈儿童文学工作中的几个问题》(1958)两篇长文,对如何“繁荣创作”作了进一步的研究。陈伯吹再一次指出发展中国儿童文学,“首先应该抓住‘繁荣创作’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因为没有儿童文学作品,就没有儿童文学,一切也就无从谈起”。所以,“繁荣创作的主要责任,落在作家和儿童文学作家的肩上,尤其是后者。所以培养和组织建立起一支儿童文学的创作队伍,是和提高作品的质量(当然也关系到扩大作品的数量,从量中求质)有着密切的关系”。一个儿童文学作家如何才能创作出高质量的作品呢?陈伯吹认为,首先是要能正确地、深刻地理解儿童文学的特殊性:
怎样正确地、深刻地理解儿童文学的特殊性,对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来说,是极端必要的,并且是有益的。
有一些同志,相反的,过于把儿童文学的特殊性看得深奥而神秘,认为这是一种专门知识,因此小心谨慎地在“专门”的前面,不敢“破除迷信”,怅然而去,这就使得儿童文学门前冷落,这情形是阻碍着儿童文学的发展和繁荣的。
其实,儿童文学在业务知识上除开特别要钻研“教育学”、“儿童心理学”等以外,也很难说再有其他特殊之点。它既然是文学领域中的一个部门,它的理论根据也就是一般的文学理论,也还同样要学习政治,使具有高度的思想水平;深入生活,求得丰富的积累;提高文学修养,掌握艺术技巧,才能创作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
一个有成就的作家,能够和儿童站在一起,善于从儿童的角度出发,以儿童的耳朵去听,以儿童的眼睛去看,特别是以儿童的心灵去体会,就必然会写出儿童所看得懂、喜欢看的作品来(着重号为引者所加)。作家既然是“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当然比儿童站得高、听得清、看得远、观察得精确,所以作品里必然还会带来那新鲜的和进步的东西,这就是儿童精神粮食中的美味和营养。正如前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所说:“它应该一直在这一综合(指一定年龄的心理综合)的前面,把儿童带向前进,到他还没有到达的那些目的。”专给儿童喝乳汁是不可能成长得正常健康的。
如果作家以为创作儿童文学,必须和儿童站得一样高,比如我们有这种情形,尽力在自己的作品中学小娃娃的话,装“老天真”,学“孩儿腔”,这对于作家来说,显然是一种“委屈”,也显然是对于儿童文学特殊性的一种误解。
在充分重视儿童作家在繁荣创作中所起的关键性作用的同时,陈伯吹还看到“繁荣创作的另一个原动力,是要由编辑,特别是少年儿童出版社和各地人民出版社儿童读物编辑室的编辑同志来担负,应该说,他们也支撑了儿童文学天下的‘半壁江山’。首先我们必须实事求是地赞扬他们在繁荣儿童文学创作这一工作上,几年来所做出的相当巨大的贡献。……要知道光有作家,没有编辑是不行的,他们是在向文艺进军中的两个相辅而行的轮子。而作家往往由编辑的发现、推荐、赏识并爱护,甚至于在培养提拔中起来的”。陈伯吹在肯定编辑工作所取得的成绩的同时,“为了改进工作”,“站在‘与人为善’的基础上,以‘乡人献曝’的诚意”,对他们“工作中的缺点”提出了6个方面的批评,或者说希望。其中第二个方面是:
儿童文学作品既然和成人文学作品同属于一个范畴的两个分野,尽管真正好的儿童文学作品成年人也喜爱读,并且世界上也不缺乏好的成人文学作品同样适用于儿童而列入儿童文学,然而由于它的特定的读者对象的关系,究竟具有它自己的特点。因此,编辑同志在审稿的时候,应该注意到它虽然也是文学作品,而在某些地方必须分别对待,甚至应该有另外一种尺度去衡量。可惜事实上并不能如此。一般来说,编辑同志在不知不觉间,有意无意地把它们等同起来看,这种主观主义的“一视同仁”式的看法,难保不错误地“割爱”了较好的作品。虽然这种错误是谁也难以完全避免的。然而如果能够“儿童本位”一些,可能发掘出来的作品会更加多一些。如果审读儿童文学作品不从“儿童观点”出发,不在“儿童情趣”上体会,不怀着一颗“童心”去欣赏鉴别,一定会有“沧海遗珠”的遗憾;而被发表和被出版的作品,很可能得到成年人的同声赞美,而真正的小读者未必感到有兴趣。这在目前小学校里的老师们颇多有这样的体会。这没有什么奇怪,因为它们是成人的儿童文学作品啊!(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细心的读者可能要问笔者为什么这样详尽地介绍陈伯吹对当时儿童文学现状的看法及其意见,并不厌其烦地做起“文抄公”,大段引录陈伯吹的文字呢?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说清楚陈伯吹为什么要写《关于儿童文学的现状和进展》等3篇论文,才能明白陈伯吹为什么要对儿童文学作家的创作和儿童读物的编辑提出那些建议与要求,才能理解为什么有笔者加了着重号的那两段文字——或者说,笔者如此铺叙,目的就是要讲清楚“那两段文字”的来龙去脉,因为正是这两段文字,陈伯吹提出了儿童文学创作与编辑过程中的“童心”问题,也正是因为提出了“童心”问题,后来被作为资产阶级的“童心论”,受到了批判,陈伯吹也因为“那两段文字”,成了资产阶级儿童文学理论的反动权威,遭到了迫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