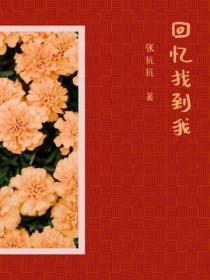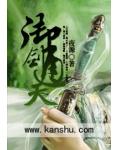这一日,好像天下所有的鸟都一齐飞回来了。飞回了这座曾经孵养哺育过他们的老巢。从远离着西湖的北方和南国、从海峡那边的宝岛、从太平洋的彼岸……急切切地赶回来。这是一个不能更改的佳期,若是错过了,一误就是百年。
这一日老巢突然变得喧闹和拥挤了。那座老巢从诞生之日起,已在中河边上静静地度过了第一个百年。至今那巢门依然肃立,仍能辨出老巢若干年前书香飘逸的形状。远方归来的老年鸟中年鸟和那一群群扇动者蓝白相间羽毛的当年少年鸟,翅膀挨着翅膀,羽冠贴着羽冠,密密匝匝熙熙攘攘挤挤踵踵,把偌大个校园,填塞得连空气都变得黏稠了。
这一日,回归的鸟们竞相发出**的呼唤,欢声笑语在养正园、鲁迅亭、科学馆上空穿梭盘旋,校园像一只巨大的蜂巢,被嗡嗡嘤嘤的声浪覆盖。甚至谁也听不清谁在说些什么,比说什么更重要的是声音本身。
这一日,1999年5月14日,这一日是属于杭高和杭高人的。
这一日,是杭高人的节日。这一日,在杭高聚集了100年的杭高人。这一日的杭高人没有年龄之别、没有界别之分,没有党派之异、没有长幼之序、没有学历高低、没有职务大小。杭高的百年庆典日,来者都是校友,都是杭高培育的杭高人。
这一日,在初夏炽热的阳光下,校园中心大道两侧签到处的字牌,如同大理石的碑文赫然入目:毕业于30年代、40年代、50年代;然后,依次是60届、61届、70届、71届、80届、81届、90届……直至98届。无数双老少学子之手,颤抖着签上了自己的名字,就像当年在老师点名时响亮地喊一声“到!”几千位不同届别的校友编织着母校的百年史,汇流成一条百年的长河,构筑成一座百道石阶的天梯。
恍然就生出一种幻觉,似乎那个即将逝去的百年,被这一日聚合的历届校友,活生生地浓缩在眼前了。它们在这一日的同一时刻里被重新清晰地展示并显现,整个校园是一所延伸和扩展的校史陈列馆,那些世纪初最早的师长和校友们,那些曾经披荆斩棘、窃盗天火的先知哲人文化先驱,那些艰辛的传承着科学自由民主精神之炬的后来者,如同一座座栩栩如生的雕塑,饱经沧桑地向我们走来……
往事常常是借助于光明而成为记忆并载人历史的。
因而历史常常会遗忘耻辱、掩饰错误、躲避沉重而变得虚妄。
与这灾难深重的20世纪同在的杭高,真的会是百年荣耀、百年辉煌么?
作为老三届的校友,在这一日灿烂的阳光和喜庆的鼓乐声中,无奈地想起33年前那个恐怖的初夏。这所具有悠久文化传统的学校,在“十年浩劫”中并未能幸免于难。杭高的百年史上,无法将“文革”中践踏师尊、摧残文明的种种恶行一笔抹去。那是杭高文化传统和人文精神的断裂期,是与共和国同龄的一代人之公耻。它为杭高的老三届校友留下了难以弥补的创痛和愧疚,也将向新世纪未来的杭高人,发出永远的提醒和警示。
这一日,在欢悦和沉重交织的复杂心情中,我始终在张望并寻找一棵树。那是30多年前离开杭一中前夕,我和我的语文老师、初三(6)班的班主任姜美琳老师,在校园东侧的一口水井边上,共同栽下的一棵柳树苗。但我已经无法辨认出那棵树了,因为校园已被太多高大粗壮的树木所覆盖。它们不是孤零零的一棵树,而是长长的一大排、一大片,是一片郁郁葱葱的树林。它们日日夜夜站在那里,似乎代替着我们留守在校园里,用绿叶和枝干,向那些曾经辛勤孵育了我们的老师,挥手传递着我们深深的感激之情。
这一日,离别母校之前,我看见了路边一棵大树上的鸟巢,有大鸟雀跃的翅翼从空中忙碌地掠过,巢边隐约传来幼雏欢乐的吵闹声。也许不久后那些幼雏就会飞离它们的老巢,在新世纪的蓝天阔野中展翅翱翔。但每年定有一个日子,它们会相约来寻找这棵大树,探望它们曾经的老窝,百年老巢已把它的血脉拴在老树下沃土的根系中,这一日任是矫健的还是疲倦的鸟们,都会在巢中重温或汲取新的养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