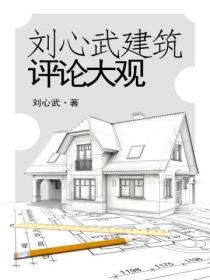§作为雕塑的建筑
本来我写下的题目是《建筑与雕塑》,但那样会让一些人以为我所要谈的仅仅是作为建筑物附属成分的装饰性雕塑。不妨先从这个角度谈谈。依我观察得来的体会,建筑物附属的装饰性雕塑大体上又分为两类,一类是连体的,另一类是离体的。所谓连体,就是雕塑与建筑物本身相连接,比如巴黎圣母院第一层与第二层之间,有二十八具以色列和犹太国王的雕像;再往上,在大玫瑰花窗前面,则是更加醒目的圣母以及护卫着她的圣子与天使的圆雕,等等。西方古典建筑物上的连体雕塑,无论是完整的圆雕、半圆雕还是浮雕,多半以装饰性为主,这些装饰品当然会含有某些宗教或世俗的意义,却并非建筑物本身必须具有的承重或切割空间区域的构件。中国古典建筑上的大型连体雕塑似较少,个别殿堂的立柱上或许会出现盘龙雕塑,但那有特别的使用规则,绝不普及;宫室、宗教建筑的顶部会有鸱吻檐兽之类的名堂,不过在比例上一般不会十分突出,而且往往还具有十分明确的功能;民居园林建筑会附属许多琐细的雕塑,如精美绝伦的砖雕,但如果是人物造型一般都不会超过三十厘米,绝少有西方那种类似真人甚至超过真人高度的圆雕出现。所谓离体雕塑,就是配合建筑物但离建筑物又有一定距离的雕塑。西方的这类古典式雕塑多注重与建筑物周遭的花草树木水域丘壑相配伍,中国的这类古典式雕塑则更专心于与建筑物本身呼应,如牌楼、华表、石狮等等,即使周遭没有花草树木,这些格外讲究对称、均衡意蕴的离体雕塑也能产生如花似树的美感。
随着全球一体化的进程,建筑科技、建筑工艺、建筑材料、建筑施工管理等方面日趋一致,建筑规划、建筑设计方面很难像古代那样东西方各自一套,势必也要趋同。现在的新建筑越来越讲究简洁,即使是新古典主义建筑,或者讲究拼贴效果的后现代建筑,在使用连体雕塑这种古典建筑语汇时都十分慎重;大多数建筑设计基本上完全杜绝了连体圆雕,半圆雕也很罕见,只偶尔搞一点浮雕,而且往往还是浅浮雕。至于离体雕塑,虽然现在使用得相当多,但一是很少采用对称、均衡的配伍方式,二是越来越趋向于抽象化,在当前的中国,最受欢迎的是介乎抽象与具象之间的那种,例如北京建国门内长安光华大厦前面的戏曲脸谱雕塑。
现在我要说到正题,就是我们应当确立这样一种建筑理念:建筑物本身就该是一种大型的雕塑品。法国雕塑家罗丹一般以石料搞雕塑,他有个说法常被人引用,就是在他看来,完成一件雕塑,只不过是把石料的多余部分去掉罢了。作为雕塑的建筑,是不是也可以作如是观呢?除了中国西北的窑洞那类很特别的建筑,一般来说,是不可以这样说的。罗丹的雕塑是“有中生有”,建筑师的设计则是“无中生有”。或许可以这样反过来说:在建筑师看来,完成一件建筑设计,只不过是在大地上把必须多出来的东西让它多出来罢了。低能的雕塑家总不能恰到好处地去掉石料的多余部分,常常该去掉的没能去掉,而不该去掉的却愣给削掉了。低能的建筑师总不能恰到好处地无中生有,现在的通病,似乎更多地出在生出来的东西过多,而不懂得节制。
有的建筑师本身就是雕塑家,比如法国的柯布西埃。他有许多可以放置在展览馆里供人当作单纯的造型艺术欣赏的雕塑作品,而他设计的位于小丘上的朗香教堂本身也就是一件完整的大型雕塑艺术品。柯布西埃的成功昭示了我们,想象力对于建筑师有多么重要。从前人的创造里获得启示是必修之课,但总是从老师那里偷艺,再聪明也不过是设计出一些可以获得高分的“作业”罢了。想象力的最高层次是“前不见古人”,甚至也不期望“后有来者”,从厚积的学识与经验中先达到“无”的境界,再“无中生有”出瑰丽诡奇的设计。悉尼歌剧院、巴黎蓬皮杜文化中心,或许还可以把上海的金茂大厦,都归纳为这种想象力的产物。安德鲁设计的中国国家大剧院,那“大水泡”的方案出来以后,一位朋友在我面前惊呼:“亏他想得出来!”他是愕然并且愤怒,因为他说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来国家大剧院可以是这种模样!”我却先是本能地叫好,然后才去细究其功能性是否有漏洞需要弥补——比如因为在天安门地区必须限高,所以整个剧院的使用空间是下陷的,那么观众的疏散会不会派生出多余的麻烦和隐患来?我的叫好也使用了同一句式——“亏他想得出来!”只是口气里充溢着狂喜与钦佩,我以为人类文明中最可宝贵的就是突破性的美好想象及其把想象勇敢地化为现实存在的作为。安德鲁的设计使建筑物本身构成了一件大地上的巨型水晶雕塑,只要他能把功能性方面的欠缺修正好,我以为北京市民可望在不久的将来从那座建筑里享受到一种特殊的快乐。
把建筑物本身作为一件大型雕塑品来想象,这是我对当今建筑师进入设计思维时的殷切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