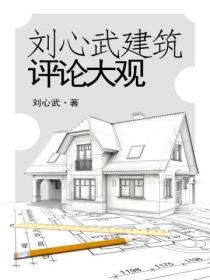§前门箭楼传奇
1996年是我国建筑界泰斗梁思成先生诞生九十五周年,1997年又逢其谢世二十五周年,故这两年纪念他的文字不少,这些文章里,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提及他关于保存北京城墙与城门的建议终被否定弃置的遭际;未及他撒手人寰,北京的城墙与城门除少数幸存的残段与孤门外,已被尽悉拆除,实在令人扼腕欷觑。由此人们又进一步生发出关于城市改造中如何尽量保护体现地域文化的古旧建筑的讨论,冯骥才就特别关注这一问题,并在天津的城市发展过程中参与了不少具体而微的“护旧”工作。
我1950年定居北京,是北京城墙与城门近乎“全军覆灭”的见证人,对此我也是痛心疾首的。但痛定之后,冷静思考,也就悟到,一座大城,在历史的进程中一味地想维护古风古貌,实在是很难很难的。
北京的城墙与城门,其实早在辛亥革命之后,就被动过一次“手术”。那便是前门(正阳门)及周遭城墙街区的改造。那改造的最主要的缘由,是其旧有的格局不仅完全不能适应新时代的交通需求,而且严重地妨碍了彼时人流与车流的通畅。我们都知道,当时北京火车站建在前门的东南侧,如今遗迹仍存(拱形顶的室内车站现改造为铁路工人俱乐部),这样前门一带便必须提供疏阔畅达的公众空间,以使从轿子骡车转换到蒸汽火车时代的人际交流,在数量与速度上都能得到充分的保证。
改造前的正阳门,在正门与箭楼之间,有封闭性的瓮城,巨大而富有神秘感的瓮城的设置,本是刻意要使进城的过程变得艰难而曲折,当然皇帝本人穿行时会成为一种例外,那时位于中轴线的所有门洞中那些布满巨大门钉的沉重门扇都会彻底敞开,但一般官绅平民出入这座界定内外城的大门时,麻烦就多了,即使恩准出入,也必得绕瓮城从侧面穿数个门洞迂缓而行;至于敌人,那瓮城与护城河的配置,特别是箭楼的巍然屹立,都是“固若金汤”这个成语的物质性体现,是“挡你没商量”的。20世纪初对正阳门的改造,其最主要的“手术”便是拆除了瓮城。瓮城一拆,正阳门的门楼便与其南面的箭楼分离开来,各成一景了。这景象一直延续到今天。
从瓮城上剥离下来的北京前门箭楼,一个世纪以来已成为了北京的三大代表性徽号之一(另两个是天安门城楼和天坛祈年殿),由于有一种跨越几个历史时期而至今依然存在的香烟牌子“大前门”,那烟盒上总是印着它的雄姿,所以前门箭楼的形象传播可说已十分地深入了人心。
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前门箭楼,其主体结构,是否是明正统四年(1439年)初建时的风貌?答案是否定的。这箭楼在乾隆和道光时代都曾因火毁而重建。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又一次毁于大火。清王室再次重建时,那建筑师并没有按原样来设计这座箭楼,幸好位于城西北的德胜门也还存有一个箭楼至今,我们可以两相比较,据载,1900年毁于大火的前门箭楼,与德胜门箭楼是基本相同的,但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前门箭楼,它的体量在改建时被增大了,齐平台处宽50米,最大进深24米,通高38米,建筑构件的强度与数量均有增加,是二重檐、歇山顶样式,北面凸出抱厦五间,东、西、南及两檐间开箭窗82洞。另外,其墙基的倾斜度大增,就视觉效果而言,更显得雍容儒雅。
这重建的前门箭楼好不好看?说不好看的,大约不多。拆除瓮城后面貌稳定下来,并在“大前门”烟盒上被世俗所熟知的这座箭楼,其实与清光绪年间火毁后重建的那形象,又有了变化,其一,是登楼的梯道,改成了“之”字形,并且台阶间有数层平台;其二,是梯道与城楼上的大平台周遭,增加了汉白玉栏杆;其三,是其下面两层箭窗上,增加了拱弧形护檐;其四,是在楼基的斜壁(月墙断面)上,增加了巨大的水泥浮雕。这些装饰性构件,不仅在影视照相中十分显眼,即使在用线条表达的烟盒画上,也凸现为其不可删却的细节。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到,光绪年间前门箭楼的重建,并非“恢复都门旧貌”,而民初拆除瓮城后改装的箭楼,更是改变了容颜。
对这改变了容颜的前门箭楼,从审美心理上予以排拒,尤其是以“未能保持古貌”的理由而加以排拒的,从那时到如今,究竟有几多人?恐怕其人数,是本来就未必多,而随着时间的增加,更以反比例而锐减吧!
民初的那次改建,具体而言,是1916年,当时的北洋政府,请了德国建筑师罗斯凯格尔(Rothkegel)来主持的,前门箭楼以上所述的四大装饰性配置,全是他的设计,特别是楼基侧壁上的巨大浮雕,真亏他苦运“匠心”,以至当我把这一点向一位看熟了前门箭楼的朋友指出后,他大吃一惊说:“怎么,那不是原来就有的,竟是一位洋人生给加添上去的?”可是他迟疑了一下也就表了态,“唔,看上去倒也天衣无缝……看惯了,抠下去也许倒会觉得不对劲了……”那浮雕其实说不清究竟像个什么,只是其配置于其位,使中国古典风韵中,糅进了一些西洋的趣味,既与附近的西洋式火车站有了一种必要的视觉与情调的呼应,又制衡了因拆除瓮城后楼体本身的单调感,增强了稳定效应。
古建筑作为文物弥足珍贵,尽量地加以保存,必要时投资修复,已成为绝大多数人的共识,但在公众生活方式及审美趣味不断发生巨大变革的历史进程中,某些古建筑也未必不能拆除,而修复重建时也未必不可以加以变通性更动,我在《祈年殿的启示》一文中,已表达过这一见解。但天坛祈年殿当年的改建,还并不牵扯到公众共享空间的配置,而随着世道的昌明、文明的推进,古旧建筑群如何在城市发展中适应公众共享空间的展拓,越来越成为一道难解的方程式。在梁思成先生出生前后直至他的少年时代,前门箭楼的改头换面、瓮城的拆除,以及前门箭楼楼基侧壁上巨型浮雕装饰件的出现,提供了前人的一次经验,激励着我们超越“旧物勿动”“整旧如旧”的简单化思路,去探索开辟出一条既尊重文明史的“旧链环”,又大胆创造“新环节”的蹊径来!
1997年8月2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