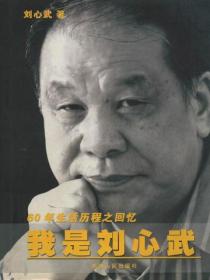当我还没有从事文学创作的时候,就喜欢阅读外国文学作品了。1956年的时候,我14岁,已经上中学,我一方面从学校图书馆借,一方面自己花钱买,间或也从哥哥姐姐那里弄到,读了大量的外国文学作品。从1956年到1965年那十年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全部外国文学作品,我大概都读过。这话并不怎样夸张,因为在那十年里,我国对外国文学作品的出版无论种类和速度,都远不能同近十年相比,对于一个热爱外国文学的阅读者来说,公开正式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是完全可以“读完”的。那十年里所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记忆中,粗分起来无非三类,占最大比重的一类,是俄国十月革命以后,特别是苏联卫国战争期间及那以后的文学作品。另外一类则是古典作品,所取的标准,除马、恩、列、斯直接肯定过的作家作品外,大体上是看苏联译介的走向,大凡在苏联被肯定的,我们这边就可以见到译本。例如伏尼契的《牛虻》,在西方一般不认为是怎样重要的作品,因为苏联大力肯定,且经《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作者用火热的语句加以推荐,所以那时在中国达到家喻户晓的程度。而例如蒲宁,虽在1932年获得诺贝尔奖,国际声誉很高,但因苏联当时视其为流亡国外的反动文人,所以我们中国当然也就不会出版他的小说,我那时就简直不知道世上还有这样一位作家。第三类则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一些作品,这类作品优秀的确实不少,但其出版却只带有明确而单纯的政治象征意义。1978年我在一家大图书馆中就发现了一本20世纪60年代初期所出版的这类译作,厚厚的一大册,在书架上一直静静地摆着,竟始终没有一个人借阅过,其印装过程中未及裁开的篇页仍旧连接在一起。
“**”前夕人民文学出版社(以作家出版社名义)曾办了一件事,就是出版了若干的“黄皮书”,全是一些供内部参阅批判的“修正主义”及“资产阶级”的“反面教材”,例如美国塞林格的《麦田守望者》、苏联冈察尔的《小铃铛》等。尽管印数很少,且规定只在当时有身份的文化人中发行,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这批“黄皮书”很快成为一些文学青年想方设法借到手的珍本。我那时人微力弱,远在当时那“黄皮书”的流布圈外,所以只偶然见到过两三本。但我也承认,那“黄皮书”的冲击力确是非常之大的。“文革”中,出版“黄皮书”一事自然成了有关部门和有关“黑线人物”的一大罪状,但据我所知,“黄皮书”大概并没有销毁多少,仍在暗中流传。一位比我小十岁的当年参与过“破四旧”的朋友告诉我,他就是从阅读被抄来的“黄皮书”开始,而萌发出文学创作冲动的。
1982年苏联莫斯科进步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集《一个人和他的影子》一书前面,有热罗霍夫采夫和索罗金合写的长篇序言,其中介绍到我的小说《班主任》和《我爱每一片绿叶》时,分析到我所受到的俄罗斯古典文学及苏联文学作品的影响,这在《班主任》里不仅体现在作品内涵中,也直接显示在情节的构成和若干细节描写上。我想他们是有道理的。
1990年香港中文大学翻译中心出版了我的英文小说集《黑墙——刘心武作品集》,内收我的六篇作品:中篇小说《如意》和短篇小说《黑墙》、《公共汽车咏叹调》、《她有一头披肩发》、《5·19长镜头》、《白牙》。澳大利亚汉学家杰瑞米·巴梅为该书写了一篇序。他说,《她有一头披肩发》的结尾使他想到欧·亨利的手法,《黑墙》有“黑色幽默”的味道,《白牙》中的“沉默试验”有某种超现实的气息,而《如意》则使他有一种恍如“中国的《金色池塘》”般的感觉。也许,他这是在从旁揭示我从外国文学作品中所获得的潜移默化的影响。《金色池塘》原是美国的一部舞台剧,剧作者为厄内斯特·汤普森,1981年据此拍成了大受行家青睐和观众欢迎的影片,由老资格的好莱坞大明星凯瑟林·赫本和亨利·方达联袂主演。亨利·方达的女儿简·方达出演他们所饰的片中老夫妇的女儿。我在几年后才在中国看到这部影片,当时我的中篇小说《如意》早已完成(它发表于1980年,并于1983年拍成影片,我于该年秋天还随该片去法国参加了“南特国际电影节”),所以,我写《如意》不可能是受到了《金色池塘》这部作品的影响。但我却乐于接受杰瑞米·巴梅那个“中国的《金色池塘》”的说法,根据《如意》改编拍摄的影片(导演黄建中)在法国“南特国际电影节”放映时,确实很受欢迎。后来此片又在法国和德国的电视中播出,《如意》除了被译为英文外,也被译为德文和俄文,在德国和苏联都得到了介绍。我想这除了因为他们可以通过《如意》了解当时中国普通人在中国社会变迁中的生活风貌以外,也确实可以从作品中一对老龄男女的黄昏恋中,感受到某种人性中相通的东西,这其实也正是中外古今大量文学作品里贯串始终、永不枯竭、永能出新的一脉文气。我写《如意》,首先自然是出于对中国社会生活和普通中国人心灵(尤其是北京这座古城的市民)的深切感受,但其次,就需谈到早已存在的文学(或扩而大之到整个文艺和文化)大河对我的沐浴与滋养,这当中除了本民族的文学传统外,外民族文学的影响,当然也融化在其中了。
鲁迅先生1925年2月21日在《京报副刊》上,应编者“青年必读书”之征,作答曰:“从来没有留心过,所以现在说不出。”又在“附注”中说:“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这是80年前的话了,因为系鲁夫子所说,总不会被认为过时吧。中国书(我认为他所指的是20世纪以前的书)是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我因没有深入研究过,以自己有限的读书心得,似也并不能如此概括,所以姑且勿论。但“读外国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外国书即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却深合我自身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经验——而且就我来说,即使印度如泰戈尔的作品,也并不例外。
我步入文坛,写了不少作品,主要是小说,自认贯串在这些小说中的,是一脉关注社会、拥抱生活、品味人生、探索人性的。不同时代、不同民族、不同流派、不同风格的外国文学作品对我的影响,系融于其中,如春光烂漫般显著,但要我说出个子丑寅卯,却又梳理不清,正所谓“无数杨花过无影”,是当局者迷吧。
我不能直接阅读任何一种原文的外国文学作品,因此,同许多与我情况类似的作家一样,就文体与文气方面而言,与其说是外国文学作品影响了我,不如说是成功的翻译家那笔下的中文影响了我。这里且不细说,同那些具有直接阅读原文能力的作家们相比,我总是十分惭愧,也往往非常困惑。近年来,我国在译介外国文学方面,不仅领域种类上有极大的拓展,数量上更是猛增。我以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现象是以往不曾有过的:一是出版了大量的外国通俗文学作品,二是出版了大量的非现实主义流派的作品,再有就是有种尊崇和追踪诺贝尔文学奖的倾向。不仅好几家出版社在出历届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作家作品选集和单本著作,而且,近年来每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揭晓,似乎都成为了我国文坛关注的一桩大事。一般宣颁不久,我国的译文类刊物上便有关于获奖作家作品的介绍,单本的书出得也颇快,有时还有两种版本同时推出的现象。在近十多年里,我想纵然是最热衷于阅读外国文学作品的人士(哪怕是以研究外国文学作品为职业的人士),也不可能把公开出版的译本都读遍了,我自己在这方面的阅读上,自然形成了大量的空白点。
西方文学中上世纪以来涌现的非现实主义文学作品,举凡现代主义、超现实主义的、后现代主义的……种种创作,越来越体现于其文学语言的创新乃至“文体”和“语体”的“颠覆”上,这样,不能阅读原文,不能直接感受其“文本”,只依靠翻译介绍,至少在我,就常常陷于困惑之中。尽管我认真而细心乃至虔诚地阅读译文,往往还是茫茫然而不能入其堂奥。例如福克纳的那部《喧哗与**》,我懂得译者呕心沥血地将其译出真是不容易,了不起,但说实在的,我读起来却只有啃酸果的感觉。
我想一个作家在广泛阅读他人作品的过程中,一定会或多或少、或强或弱、或隐或显地受到某些影响。但一个有创造力、有自尊心和自信心的作家,却不应有意去专门接受他人作品的影响,尤应如同逃避瘟疫般地戒惕自己不要堕入模仿、效法、追踪他人(又尤其是外国作家)作品的渊薮。
诺贝尔文学奖是世界上现有各类文学奖中影响最大的一种文学奖,排除掉评奖中所潜伏着或直露出的某些非文学性的动机与标准外,总体而言,这项文学奖也确实评出了一些很不错的作家和作品。因此,关注、重视诺贝尔文学奖的颁布,研究、借鉴每年的获奖作家和代表作,我以为都是必要的。不过,摆脱掉这项文学奖对我们作家进行创作的阴影,不要赶潮流、赶时髦地去主动接受它那历届得主特别是最新得主的影响,而是坚持自己的创作完全体现出自己的心灵意志和自择自创的符号系统,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
记得在1980年,当时西德驻华大使魏克特博士,曾请我们几位中国作家到大使馆去聚会。魏克特本人也是一位作家,他写的广播剧《德语课》不仅在德国电台播出,也由我国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译文也曾在我国《世界文学》上刊出过,他并著有以中国太平天国革命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他那次请中国作家去聚会,是因为德国名作家君特·格拉斯作为他私人的朋友,到中国旅游,住在大使馆中,他想让君特·格拉斯能有一个与中国作家接触的机会。我在此之前已经知道君特·格拉斯与伯尔同为当代德国最著名的作家,伯尔的写作风格比较写实,君特·格拉斯在《铁皮鼓》中已显示出不拘泥于写实的文风,而他那次到中国时,恰好正完成了以非写实手法写成的《鲽鱼》一书。记得那天聚会时他还举起一幅木刻画给我们看,所刻的正是两条变形的富于装饰趣味的鲽鱼。魏克特博士从旁介绍说,那是格拉斯自己所刻,他不仅能文,而且精于版画,那幅木刻便作为了他新著的封面。当时便问及《鲽鱼》的内容,他略作解释,而翻译已极感困难,我们都不得要领。两年多以后才在《外国文艺》上看到了一点摘译,译者在附言中也说那作品只有直接阅读原文方能品出其中滋味,简直没有办法通过翻译传达出作者的妙意。大家都知道伯尔已在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而君特·格拉斯多次进入该奖的提名角逐却至今与该奖无缘。作家有必要去争取诺贝尔文学奖吗?记得那回格拉斯微笑着说:提名,竞争,都是别人的事,作家写东西,简直不要去管那一套,他写《鲽鱼》,就颇有如入无人之境的气概,全凭自己的灵感一口气写下去。当然,他说,《鲽鱼》对许多读者来说,要比《铁皮鼓》难于接受,但他相信,《鲽鱼》是一部比《铁皮鼓》更精彩的作品,终会获得若干知音。格拉斯那天洒脱自信的音容笑貌,二十多年后仍宛在眼前。
1988年访问巴黎时,在法国文化部的一次招待会上,我又有机会同法国“新小说派”开山祖,也是有名的“午夜出版社”主持人罗伯·格里耶接触。我们站在宽敞的宫殿平台上,下面是气魄宏大的协和广场,广场中央竖立的楔形文字方尖碑,以及四角配有古典圆雕的喷泉,给人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不过罗伯·格里耶的某些谈吐,不再是当年以《嫉妒》、《去年在马利昂巴》等作品披荆斩棘开创新业的猛将风姿,他显得格外沉静、恬淡。“新小说派”的业绩通过头两年克洛德·西蒙的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已然算是获得了世界文坛的稳定评价。据说克洛德·西蒙获得1985年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到巴黎时,街头行人面面相觑、互相询问:“他是谁?”报刊舆论上也责问为何该奖不颁给罗伯·格里耶或其他几位远比克洛德·西蒙知名度高、业绩也大的“新小说派”主将。但当我们几位中国作家通过翻译问及此事时,罗伯·格里耶却称根本不存在一个什么“新小说派”,他说这个派那个派全是一些评论家捏合起来的。对于他来说,文学是一项无休止的试验,他现在所写的作品,就全然不同于以往所著,作家不仅要竭力摆脱他人的影响,摆脱评论界的影响,摆脱诸如诺贝尔文学奖之类的影响,而且,也要摆脱自己过去的影响。
同格拉斯、格里耶这样的外国作家的接触,给予我的影响,似乎比阅读译成中文的外国文学作品,还更触动我的创作神经。
我也许并不具有多高的才能,我的写作,也许仅仅出于一种对文学的执著爱好,甚至只出于一种生命本能,但我一定要使自己的每篇作品,不仅不是任何中国或外国作家写出的作品的影子或摹本,而且,也不是自己以往作品的重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