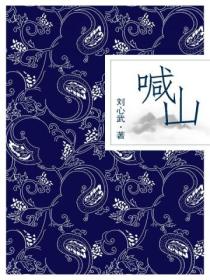冬天到了。谁说冬天花儿少?嘿,当天上往下撒雪花的时候,你摊开巴掌接吧。每朵花的形状都不一样,可都那么美丽!
又是一个星期日。早晨,天上灰蒙蒙的,下雪花儿了。等大地铺上厚厚的雪毯儿,我们就能团雪球儿,在胡同空地里打雪仗了!
“炒豆儿”戴着好大一顶狗皮帽子,脖子上围着好厚一条围脖,手上套着熊掌般的一对大棉手套,跑到我家,喷着白气,扬着大嗓门,向我宣布:“我发现了几个真格儿的侦察兵!搞不清是‘侵略军’还是‘友邻部队’!”
“嗨,”我不在意地说,“准是‘黑大力’、‘小绪子。’他们吧。”
“不是‘黑大力’他们!”“炒豆儿”顿着大棉窝,急得结巴起来,“是是是几几几个大人!不信你去看!”
我就抓起帽子、围脖,顾不得拿上手套,随他跑了出去。跑到胡同当中的空地边上,“炒豆儿”指给我看:“唷,可不是真格儿的侦察兵吗!”
也难怪“炒豆儿”那么认为。只见离我们五六步远的地方,有两个穿皮夹克、戴皮猎帽的叔叔,支着一个比我们小孩还高的三脚架。三角架底下吊着个用线拴着的小铜锤,那两个叔叔轮流把眼睛凑到三角架上好似望远镜的东西前头,看一阵,打开皮面本子记一阵。而对面一百多步远的地方,站着一个用大红拉毛围脖裹住头的阿姨,用戴着红毛线手套的手扶着一根带尖铁脚的木柱,看上去仿佛是根特大号的尺子……啊,我眨眼想了想就明白啦,这是搞测量呢!
十几分钟以后,我和“炒豆儿”就把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带回了院里——明年开春我们这条古老的胡同就要拆掉,将在这里盖又高又大又美的现代化大厦。那时候,我们各家都将搬到那新住宅区舒适的单元楼里去住。
雪下得越来越大了,院里的大人小孩们关于这件事的议论也越来越热烈。“炒豆儿”在院里得意地晃来晃去,活像发现了美洲新大陆的哥伦布一样。
方伯伯把我们几个小学生叫到他屋里,一边从取暖的花盆炉子里夹出烤白薯来请我们吃,一边打开了话匣子。方伯伯感慨地说:“咱们这个院子,还有‘炒豆儿’他们那个院子,再过去点程海岩她们那个院子……原来是连在一起的,是清朝一个王府的祠堂。我这间屋子,原来是搁祭器的——”
谭小波立即好奇地问:“我们家那两间呢?”
“是祭祖先的仪式开始以前,王爷他们休息的地方。”
“我们家的呢?”“我们家的呢?”“我们家的呢?”这一来大伙全询问上了。
方伯伯望着炉子里跳跃的火舌,缓缓地说:“后来,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这祠堂成了军阀作恶的地方;再后来,又成了国民党的衙门,日本的特务机关……抗日战争胜利以后,落到了几个国民党‘接收大员’手里,他们打着没收敌产的名义,把这几个院子贪污下来,隔开租出去捞钱……新中国成立后,这几个院子才回到劳动人民手里,成了居民院。一住,可就快三十年啦!”看上去,方伯伯有点舍不得这个院子似的。
我们的心情可不一样。
谭小波说:“快点拆了吧!我可不喜欢那么高的纸顶棚,一掉土沙拉沙拉响,挺怕人的。”
我也说:“住楼多好呀,我表哥立东他们就住楼,比这旧房子强多啦!”
另外几个小朋友也都说,宁愿工人叔叔早点来,把这些古老的院子拆掉。
“炒豆儿”吞完最后一口香喷喷的烤白薯,舔舔嘴唇,认认真真地说:“我喜欢这样的房子。”
“为什么呀?”我和谭小波抢着问他。
“因为,住楼就不生炉子了,不生炉子就烤不了白薯,我爱吃烤白薯呀!”
包括方伯伯在内,大伙“哗”地全笑了。
正笑着,立东表哥跑进来了,他已经知道了我们即将拆迁的消息,就建议说:“快到院里照几张相吧,留个纪念啊!我带着相机哩!”
我们欢呼着跑到了院子里。雪下得更大了,地上已经积了两寸厚的雪,几棵松柏树戴上了美丽的雪帽,密密的雪花织成了一面网。
我们请方伯伯一同来照,方伯伯问立东表哥:“这么个天,能照出来吗?”
立东表哥自豪地说:“没技术的照出来准砸锅,有经验的仔细点能照好!”
正说着,“黑大力”、“小绪子”跑来约我们出去打雪仗,我们就热情地邀他们一块照相。程海岩也恰好跑来找我们院的女孩子玩,方伯伯便把她叫到身边,约她照完相杀一盘象棋。刚拍了一张,立东表哥让我们别动,打算再拍一张,我们却又蹦又跳,拍着巴掌跑向了门口——原来是班主任吕老师和大队辅导员冯老师来了。大考临近,他们一块来串胡同进行家访,检查我们温习的情况。我们不由分说就把他们推到了正对镜头的位置。吕老师紧了紧咖啡色的花毛头巾,四面望了望说:“今天少一个人哇!”
我立刻猜出了她的念头,转念一想,便大声提出了一个建议:“相片上应该有高山菊——她没来,咱们堆个雪人代表她,好吗?”
嗬,赞成的声音差点没把雪花吓回天上去。不一会儿,一个瘦长的雪人就堆好了。谭小波拿来了两支笔,一支蘸黑墨水的用来画鼻、眼、耳,另一支蘸红墨水的用来画嘴,你别说,他画得还真有点像高山菊的神气。
“可这是个秃小子呀,哪是高山菊呀!”“炒豆儿”挑毛病说。
“脑袋上扣顶草帽,不就显不出秃啦?”“黑大力”动上了脑筋。
话音落下没多久,一顶草帽就扣上去了。
“高山菊得有辫子呀!”“炒豆儿”还挑毛病。
我想了想,便飞快地跑回家去。进了小厨房,我把墙上挂的蒜辫子摘下来,跑了出去。到了雪人前头,我把蒜辫子往草帽底下一搁,嘿,两只辫子就搭在雪人肩膀上了。谭小波跟着就用墨把那辫子涂黑,于是,一个眉开眼笑的高山菊就站在我们当中了。
立东表哥退后好几步,刚要按快门,“黑大力”陡然嚷了一嗓子:“等等!我请宋大哥去!”拔腿便跑出去了。
不一会儿,宋大哥随“黑大力”来了,他只穿着一身枣红的运动绒衣,没戴帽子,头上却冒着热气——原来他正在练举重呢。吕老师见了他便同他握手说:“谢谢你配合学校做了好多工作!”冯老师捶捶他肩膀说:“你真有两下子,把‘黑大力’的坏毛病都给扭过来了!”宋大哥只是乐呵呵的,也没说啥客气话。大家自自然然地站到了一起,立东表哥拿出浑身解数,拍成了这张特殊的“全家福”。
现在我给你看的,就是这么一张照片。希望你看到这张照片上的人物时,能想起有关的故事来。当然,都是些平平常常的事儿,你如果听着还有点滋味,那么以后也许我还会接茬儿往下讲,不过,那些故事将发生在另外的地方了。
1979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