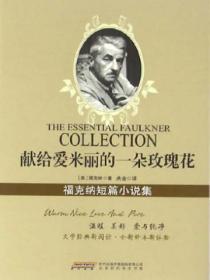§二
这件事是我刚开始记事的时候,赫尔曼·巴斯克特告诉我的。他说杜姆从新奥尔良回来时带来六个黑人,其中有个女人,尽管赫尔曼·巴斯克特说当时庄园中的黑人已经多得无法使唤。他们有时就会驱使黑人和猎犬赛跑,就像你们追捕狐、猫和浣熊一样,而杜姆又从新奥尔良带回六个。他声称是在汽船上赢来的,所以不能不要。赫尔曼·巴斯克特说,杜姆下汽船时,除了这六个黑人,还随带着一只装有活东西的大箱子和一只盛着新奥尔良盐末的、金表那么大的小金盒子。赫尔曼·巴斯克特随即叙述了杜姆如何从大箱子里抓出一条小狗,用面包和一撮金盒中的盐末搓成一粒药丸以及如何将药丸塞进小狗的嘴巴,小狗就立刻倒地毙命的事情。
赫尔曼·巴斯克特说杜姆就是那么一种人。他说那天夜晚杜姆下船时穿着一件缀满金饰的外衣,戴着三只金表。赫尔曼·巴斯克特还说,虽然事隔七年,但杜姆的眼睛却依然如故,与他出走之前的眼睛一模一样。那时他的名字还不叫杜姆,他与赫尔曼·巴斯克特以及我爸爸当时一如村童,常在夜晚在同一张草席上抵足而卧,娓娓长谈。
杜姆原来不叫杜姆,他的原名叫伊凯摩塔勃,当然,他并不是生来就配当头人的。杜姆的舅舅才是头人,他自己有儿子,还有一个兄弟。甚至在那时,在杜姆与你一样年幼时,头人有时就瞟着眼看杜姆说:“外甥啊,你眼露凶光,像匹劣马。”
赫尔曼·巴斯克特说,因而,杜姆长大成人,宣称自己要去新奥尔良时,头人并不惋惜。头人过去喜欢玩掷刀和掷蹄铁之类的游戏,随着年岁渐高,他现在只爱掷刀了。因而杜姆出走后,他虽然没忘掉他,却并不懊丧。赫尔曼·巴斯克特说,每年夏天威士忌酒贩来时,头人总要问起杜姆。“他现在把自己叫做戴维·卡利科特了。”头人会这么说,“但他的真名是伊凯摩塔勃。你们有没有听说过有一个叫戴维·伊凯摩塔勃的在大河中淹死,或者在新奥尔良白人厮杀时丧生呢?”
只是,赫尔曼·巴斯克特说,杜姆这一去就整整七年,七年中他杳无音信。后来有一天,赫尔曼·巴斯克特和我爸爸突然收到杜姆的一根写了字的棍子,要他俩到大河去接他,因为那时的汽船不再驶进我们这条河了。当时有一艘汽船一直搁浅在我们小河里,寸步难行。赫尔曼·巴斯克特告诉我,大概杜姆出走后的第三年汛期,有一天,这艘汽船溯流而上,窜上了沙洲,就“死”在那儿,动弹不了了。
这就是杜姆的第二个名字——杜姆之前的那个名字的由来。赫尔曼·巴斯克特告诉我,那以前,一年中汽船只有四次机会驶进我们的小河,溯流而上,每到汽船来时人们就会一起拥到河边露营,然后守候着观看汽船经过。他说给汽船导航的那个白人名叫戴维·卡利科特。所以当杜姆告诉赫尔曼·巴斯克特和我爸爸他要去新奥尔良时,他说:“我还要告诉你们另一件事,从现在起,我不叫伊凯摩塔勃了,叫戴维·卡利科特。总有一天,我也要拥有一艘汽船。”赫尔曼·巴斯克特说杜姆就是这么一种人。
七年后,他写信给赫尔曼·巴斯克特和我爸爸,之后他们便套车到大河接他去。杜姆带着六个黑人下了汽船。“他们是我在船上赢来的。”他说,“你和克劳·福特(其实我爸爸的全名叫克劳菲什·福特,但他们通常只叫他克劳·福特)两人分吧。”
“我不要。”赫尔曼·巴斯克特说我爸爸当时这么回答。
“那就统统归赫尔曼吧。”杜姆说。
“我也不要。”赫尔曼·巴斯克特回答。
“好吧。”杜姆说。随后,赫尔曼·巴斯克特问杜姆是否还叫戴维·卡利科特,杜姆没有搭腔,却对一个黑人叽咕了几句白人的话语,那黑人便点燃一枝松节。接着,赫尔曼·巴斯克特说他们愣着眼看杜姆从大箱中抓出一条小狗,又用面包和小金盒中的新奥尔良盐末搓了一粒药丸,就在这时,他说我爸爸突然叫道:“你说过要让赫尔曼与我分这些黑人吧?”
赫尔曼·巴斯克特说我爸爸这时看见黑人中有一个是女的。
“你和赫尔曼都不要啊。”杜姆说。
“我刚才说话明显没有经过考虑。”爸爸说,“我要包括那个女人在内的那一队,其他三个分给赫尔曼。”
“我不要。”赫尔曼·巴斯克特说。
“那分给你四个。”爸爸说,“我要这女人和另外一个男的。”
“我不要。”赫尔曼·巴斯克特说。
“那我只要这个女人。”爸爸说,“其他五个都归你。”
“我不要。”赫尔曼·巴斯克特依旧这么坚持着。
“你也是不要的。”杜姆对爸爸说,“你自己说过你不要。”
“你还没告诉我们你的新名字呢。”他对杜姆说。
“现在我叫杜姆。”杜姆说,“是新奥尔良的一位法国头人给我取的,法国话叫杜·昂姆,用我们的话讲就是杜姆。”
“‘杜姆’是什么意思?”赫尔曼·巴斯克特问。
杜姆直愣愣地对着他凝视了一阵,回答说:“这意思就是头人。”
赫尔曼·巴斯克特向我描述了他们听后对此所作出的感想。他说他们伫立在黑暗之中,大箱子里杜姆还没有用掉的其他小狗吠着、打闹着,而那松节的光亮照耀着那些黑人的眼珠、杜姆的金饰外衣以及那条已经丧命的小狗。
“你当不了头人,”赫尔曼·巴斯克特说,“你是头人的外甥,头人自己既有兄弟又有儿子。”
“不错。”杜姆说,“可我要是头人,我就把这些黑人送给克劳·福特,也要送赫尔曼一些东西。我要是头人,每给克劳·福特一个黑人就送赫尔曼一匹马。”
“克劳·福特只想要面前这个女人。”赫尔曼·巴斯克特说。
“我是头人的话,无论如何要送赫尔曼六匹马。”杜姆说,“不过,也许头人已经送给赫尔曼一匹了。”
“没有。”赫尔曼·巴斯克特说,“我至今连灵魂也还是靠两条腿走路。”
他们要走三天路程才能到达庄园,到了夜晚他们就在路边宿营。赫尔曼·巴斯克特说他们一路上紧闭嘴巴,一句话也不说。
第三天,他们来到了庄园。赫尔曼·巴斯克特说尽管杜姆拿糖果馈送头人的儿子,头人却并不是那么高兴见到他。杜姆对一切亲朋故友都各有所赠,甚至连头人的兄弟也不例外。头人的兄弟独自一人住在溪边小屋里,大名叫“难得睡醒”。人们只有在偶尔送些食物去时才能见到他。赫尔曼·巴斯克特讲了那天关于他、爸爸和杜姆去见他的情况。那是一个夜晚,杜姆先叫赫尔曼·巴斯克特关上大门,然后从爸爸手中接过小狗放在地上,接着就用面包和新奥尔良盐末捏好了药丸,以便让“难得睡醒”目睹药丸的功效。赫尔曼·巴斯克特说他们刚离开,他就点燃了一根树枝,然后用毯子把头蒙上了。
杜姆回家的第一个夜晚就是这么度过的。到了第二天,赫尔曼·巴斯克特告诉我,头人吃饭时动作突然失常,在医生还没有赶到和烧树枝之前就一命呜呼了。而当头人的遗孀把儿子叫来接替他时,人们发现头人的儿子也行动怪异,很快就死了。
“现在该由‘难得睡醒’当头人了。”爸爸说。
于是,头人的遗孀又去请“难得睡醒”,但没多大功夫就返回了。
“‘难得睡醒’不肯当头人。”她说,“他头上蒙着毯子就坐在小屋里。”
“那就只有伊凯摩塔勃当了。”爸爸说。
就这样杜姆当上了头人。但赫尔曼·巴斯克特说爸爸当时显然很是焦躁,他劝爸爸给杜姆一点时间。“我还是靠两条腿走着呢。”赫尔曼·巴斯克特说。
“可这件事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爸爸说。
他说爸爸最终还是在头人及其儿子入土之前,丧葬宴会和赛马还没有结束就去找杜姆了。
“什么女人?”杜姆问道。
“你说你当上头人时要给我的啊。”爸爸回答。赫尔曼·巴斯克特说那时杜姆两眼瞪着爸爸,而爸爸的一双眼睛却看也不看杜姆。
“我看出来了,你是不相信我。”杜姆说。赫尔曼·巴斯克特说爸爸始终没有朝杜姆瞥上一眼。“你好像以为那条小狗是生病死的。”杜姆说,“你还是再考虑考虑吧。”
赫尔曼·巴斯克特说爸爸当时考虑了一下。
“你现在怎么想啊?”杜姆问。
不过,赫尔曼·巴斯克特说爸爸仍然不瞧杜姆一眼。
“我看那条小狗本来是很健壮的。”爸爸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