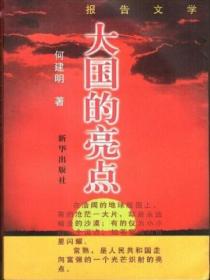(代后记)
中国曾经有个独特的年份,它被称之为“大跃进”年代。在这个年代前夕的一个初冬日子的早晨,在江南水乡的一个何氏宅院,突然传出一声婴儿的啼哭——一个生命就这样来到了这个世界。19年后,这个男性公民穿上绿色军装,挥泪告别母亲,去远方边塞履行神圣职责。后来辗转20余年,当他带着对母亲和故乡的一片赤子之心再度回到生他养他的那个江南水乡时,发现昔日印象中的家乡已经变得不认识了……于是那种强烈的无法抑制的情感顿时一泻而不可收,最终变成了这部二十余万字的书。
这个人就是本书作者,也就是我——一个十足的至今仍在语言和血脉里带着家乡泥腥土味的常熟人。
谁都说自己的家乡好。我的家乡地处江南腹地,又有近五千年的文明史,自然她比哪个地方都好、都美。想起碧水见底、鱼儿在草中嬉戏的阳澄湖,想起金黄色的油菜地和姑娘脸蛋般的成片桃花,想起小桥流水旁的茶馆内那浓浓的清香与老人们悠闲自得的逸情……你醉,我醉,谁都会醉。
然而,在我19岁那年离开故乡前,我记忆中的故乡只有那不尽的优苦和早日远远离她而去的心。
在我脑海中留存的对故乡的第一个记忆,是大人们没了没完地让我吃黄罗卜(北方人叫胡罗卜)。后来我实在不愿再到食堂里去吃这东西,母亲就只好给我开“小灶”,每天让吃大麦粥(六七十·年代的猪饲料,现在的猪都不吃那最次等饲料了)。吃长了,我又不要吃,整天闹,可看到母亲在一边无奈地流泪时,我又只好端起那碗无法咽入细嫩肠胃的饭……那年比我小三岁的弟弟在母亲的怀里饿死了(从此我再也没了弟弟)。弟弟出殡的那天,我见母亲哭得死去活来——这是我生命中对故乡最初和最深刻的印象。
后来是我读书后的事。有一天放学回家,母亲突然满脸泪水地把我和姐姐拉到身边,‘说让我们到好婆(外婆)家躲一躲。我问为啥?母亲含泪说你父亲被“打倒”了,造反派马上要来封我们家的门了。从小倔辈的我就是不愿离开家,我一直蹲在家的后面想看那些“坏人”是怎样封我家门的。在寒风中,我一小时一小时地等,直到手脚都是冰冷冰冷——这是我一生中渡过的最寒冷的一夜。
再后来,我就必须什么都得干,一边上学,一边和姐姐帮着父母干活挣工分。冬天下河挖泥,春天给麦地上粪,40多度高温下播秧争第一名、秋里拉纤到上海大街上收垃圾……凡是能说出的农活我没有没干过的。我最怕跟那些壮汉子们挑一二百斤重的河泥与湿稻;我最怕蚂蝗蛤蟆成群的水田;我最怕让我跟船老大到上海去收垃圾装下水……但这些又却是干得最多的。我不会摇船,总摇不好,于是拉纤入上海境地时那些上海嘉定人总找麻烦。有一次我们逆水而行,他们顺流直下,结果两船相撞,他们抢走了我们船上最重要的舵和竿。为了生存,我跳上了他们的船,想抢回属于我们的东西。那时我才16岁,面对的都是些三四十岁的大汉。他们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继续直流而下,并说干脆要把我扔进江里。我侧眼一看,那江里急流滚滚、旋涡迭旋涡……这是我少年时最惧怕的一次。
1975年初冬,又一个“农业学大寨”大会战。在又是雨又是风又是冰的长江堤坝上,几万人的筑堤大军中夹着我这个又瘦又细的“壮劳力”,肩挑一二百斤沉的担子,一步一哼地在风雨中摇晃着。入夜,在湿浸的草地铺上只听得阵阵的筋骨咯咯声……那一刻是我最想离开故乡而去寻求人生出路的时间。
后来我真的离开了故乡,带着某种对故乡和对亲人在内的复杂清感。虽然在这之后的20多年间,我也不止回过一次家,但都因为想念母亲和亲人而已,且这样的回乡都是匆匆而去,匆匆而归,并不怎么留意故乡已经或者正在发生的变化。然而在我突然感到自己一向认为年轻的生命走到40岁时的今天,我仿佛一下悟得古人常言的“叶落归根”真谛似的,是那样迫切地期待重新细看一眼久违了的故乡。于是在不久我携妻带女回到故乡常熟,并专心细细地留意我既熟悉又陌生的那城、那路、那水、’那地、那人。呢,我顿时发现我的故乡已经全变样了,变得我根本的生疏。
在我的眼前,今日故乡的那城、那路、那水、那地、那人,与我记忆中的概念已全然不同。那是一种崭新,是一种流畅,是一种激扬,是一种扑面而来叫人热血沸腾,呼之有情,按之能动的铿锵步履声。在我故乡的今天,其城市已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概念,因为由工厂、楼房,‘公路象征组成的城市在这片土地上无处不有;其乡村的概念也不再是过去意义上的乡村了,因为那种似乎只有现代城市人才能享受的卡拉OK厅、酒吧、别墅、游泳池与网球场,尽有我的父老乡亲们在里面纵情享受。故乡各种物质与精神文明进步的程度,与我记忆中的故乡胜似两个世纪的间隔。而正是这发生在历史瞬间的巨变,才使我这个生不逢时的游子,一改过去对故乡的厌烦感,重新唤起一种犹如情人般的激**。
常熟的变化,是中国改革的“个缩影。同时它又是中国改革取得辉煌成就的最具闪光的地域之一。.在那里,’·我们可以看到21世纪中国社会将出现的景象。看到那时中华民族作为一个真正大国而具有的实力与繁荣。我坚信自己的这一预感是正确的。这是因为邓小平同志生前所倡导的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目的,就是让占全国总面积与总人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广大农村和农民们能实现现代化,过上富庶日子。常熟人民依靠政策和智慧及干劲,走在了别人的前面,给全国的农民兄弟以激动人心之希望,而这个激动人心的过程,正是中国农民们自己建立起来的特有的社会主义农村市场经济大潮的催发与涌动过程。
常熟的变化是巨大的、瞬间的和充满魅力的。凡到过这儿的人,都会由衷地感叹。作为曾经是这块土地上的一员,我自然比别人更多一份热忱与赞美之心,并且更多一份深切的感受。其原因如前所言,在我童年和少年时,那个政治年代所留下的曾经使我对只有苦难的故土产生过强烈的厌烦与不快。然而,今天的故乡,当我再回到她身边时,我感到一种母亲般的无限亲近感、温暖感。在我幼小的时候,我曾为美丽的母亲自豪过。在我成年的今天,我更为美丽的故乡自豪。而正是这种胜似于对母亲的情感,使我格外看重在故乡这块热土上发生的历史性变迁,并为之深深动情。
我曾经以最真切的笔力为母亲抒情过。当我看到今天的故乡时,又无法掩饰我心中的真情。文学需要真情,没有真情的文学,将是乏力和虚伪的文字垒砌物。然而,作家的真情又常需付出沉重的代价。而沉重的代价又常常是唤起真情所必须的。
面对着蓬勃生机,一派繁荣的故乡时,我当然不能不奉献自己的那份最诚挚和炽热的真情。(大国的亮点》一书就是我对母亲和故乡所吐露的这番真情。当然,我不能不申明我十分富庶与繁盛的故乡,仍非十全十美,但谁都无法否认,常熟作为一个以农民占主导地位的县级小市,在改革开放后的短短时间内,由于全面的实行了农村市场经济而带来的巨大成就与实力,雄居全省乃至全国的最前列。市场经济的今天,衡量一个地方的实力已不能再用行政级别和地域大小来圈定了。市场占有率和综合实力已替代了传统的概念,所以常熟便成为共和国繁荣与发展进程中光彩耀目的巨人。《大国的亮点》虽然写的是我家乡的事,然而在写作的过程中,我一直是以一个局外人的目光,用审视的长镜头对它进行扫描与解剖的。如果不是这个后记和书帧上的作者小传,读者是不会从书中认出我是个“常熟人”的。我这样做的目的很清楚:常熟的经验与成就,不该仅我一个人感到自豪与骄傲,应当成为中国全体公民的自豪与骄傲。我愿意人们通过共和国的这个“亮点”,增强对社会主义祖国未来更多的信心。像常熟那样的富有与美丽,繁荣与生机,难道不值得全中国人向往吗?!
我们有理由对此肯定。
常熟的今天和今天的常熟人,是一个丰富的世界。本书所描述与涉及到的仅是她历史进程中的几个断面。包括书中没有写到的诸多干部、实业家,他们每个都是一个战线上的指挥者,拥有最精彩的乐章。还有数不清的群体形象与动人业绩,由于本部文学报告的局限无法得到展示,但无妨他们在常熟历史进程中闪耀光芒。
最后,我要由衷感谢为我完成此书采写而付出诸多辛劳的市委宣传部朱养刚、市文联袁文龙,及有关部门的王建康、吴建平、闻水昌、李文俊、陶振球、徐国良、吴建国、陆水根、陈培元、王敏玉、吴伟、崔广全、屈险峰等同志,他们的友情,是我对家乡永恒已忆中的美好景点。
1997年7月
常熟—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