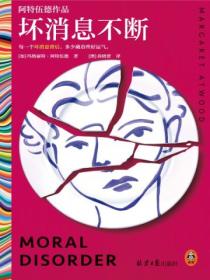2 烹饪与餐桌服务之道 The Art of Cooking and Serving
十一岁那年的夏天,我把很多时间用来编织。我以一种远非轻松的姿态蜷缩在羊毛线团、钢针和越来越长的织物中间,顽强而安静地织着。我学会编织时年纪太小,所以没能掌握用食指绕线的技巧——我的食指那时还太短——于是我只能先把右手的针插进线圈,用左手的两根手指捏住它,然后再抬起整个右手,把毛线绕在针尖上。我见过那些能够一边编织一边聊天的女人,她们几乎都不用低头看,但我做不到那样。我的编织风格需要全神贯注,这导致我双臂酸痛,并时常恼怒。
我正在织的是一组婴儿套装,就是给新生儿穿戴的一整套衣物,宝宝从医院回家时可以穿上保暖用。你至少要织两只连指的毛线手套,两只毛线短袜,一条紧身毛裤,一件毛衣,还有一顶软帽,如果你有耐心,还可以加上一条编织的线毯,以及一件叫作屁兜的东西。那个屁兜看起来就像一条有着南瓜形腿的短裤,就是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1]肖像里的那种。布尿片和橡胶制的宝宝裤很容易漏,所以才会用到屁兜。但我不打算织屁兜。我还没办法让自己想象出宝宝可能会尿出来那些喷泉、小溪与河流。
线毯让人跃跃欲试——我一直想织那款有小兔子图案的——但我知道自己得适可而止,因为我没有用之不竭的时间。要是我磨磨蹭蹭,宝宝可能在我准备好之前就出生,就只能穿旧衣服临时拼凑起来的不配套的套装了。我从紧身毛裤和手套开始织起,因为这两件相对简单——基本上就是正反针逐行交换着织,再织进去一些罗纹就好。然后我可以用同样的方法把更复杂一些的毛衣也织好。帽子我会留到最后:那会是我的点睛之作。我还会给帽子装饰上缎带,好系在宝宝的小下巴上——当时还没人考虑到这种系法有勒死宝宝的危险——还要有大朵的缎带花,像小卷心菜一样在宝宝脸庞的两侧盛开。我从《蜂巢编织图谱》的图片中了解到,穿着婴儿套装的宝宝们看起来应该像糖果一样——干净又甜美,撒着柔和的糖霜,如同一块美味可口的小蛋糕。
我选择的颜色是白色。这是传统的颜色,尽管蜂巢图谱里有些图案也用了精灵般的淡绿色或者实用的黄色。但白色是最好的:知道了宝宝的性别之后,我再加上蓝色或粉色的缎带就行了。我能想象到套装完成后会是什么样子——崭新,光彩,值得赞赏,彰显着我的善良与美意。我还没意识到的是,套装也可能是这些美好字句的替代品。
我要编织这套婴儿服是因为我的母亲有喜了。像其他人一样,我避免使用“怀孕”这个词:“怀孕”是一个生硬、臃肿、松垮的词,想起来都沉重不堪,而“有喜”则如同一只竖起耳朵的小狗,带着快乐的期待,活泼地聆听着越来越近的脚步声。我母亲已经过了适合生育的年龄:我得出这个结论是因为我偷听了她和她城里朋友们的对话,还有那些朋友额头上忧心忡忡的皱纹,她们紧闭双唇微微摇头的模样,她们说出“唉,天哪”的语气,以及我母亲说她只能尽力而为等迹象。据我所知,我母亲的年龄可能会导致宝宝出问题;但到底会出什么问题?我尽量去听,但还是没听出个所以然,也没人能让我去问。宝宝会不会缺胳膊少腿,会不会有点笨,会不会是个白痴?在学校里,白痴是个骂人的词。我并不确定这个词的意思,但是在大街上你不应该盯着看某些孩子,因为那并不是他们的错,他们只是天生就那样。
五月,父亲告诉我母亲有喜了,正在待产。这让我非常焦虑,部分是因为我同时得知,在我的弟弟或妹妹平安降生前,母亲一直有危险。她可能会遇到一些很可怕的情况——一些可能会让她病得很厉害的情况——而且,如果作为我而言不多加小心的话,这些情况就更有可能发生。父亲没说会有什么样的情况,但他的严肃与简洁意味着事关重大。
父亲说,母亲不能扫地或者搬重东西,比如拎水桶,也不能弯腰太深或者举起大件物品。父亲说,我们都得帮忙承担额外的家务。从现在开始到六月份我们去北方之前,由我哥哥负责修剪草坪。(北方没有草坪。而且无论如何我哥哥也不会去:他要参加一个男生夏令营,在森林里用斧头干活。)至于我,总体上能有帮助就可以了。我父亲用一种意在鼓励的语气补充说,要比平时多帮点忙。当然,他自己也会帮忙的。但他不会一直在。我们在那个被别人称为小别墅但是被我们叫作小岛的地方居住期间,他还有工作要做。(小别墅里通常会有冰箱、燃油发电机、划水橇,而这些我们都没有。)难办的是,他必须得离家一阵,他继续说道。但他不会离开太久,而且他确信我一定应付得来。
我自己就没那么确信了。他一直觉得我比实际上更懂事、更有力、更成熟、更坚强。被他误认为是冷静与才干的实际上是惊恐:那才是我默默望着他,不停点头的原因。若隐若现的危险因为太模糊,所以才更巨大——我连怎么为它做准备都不知道。我在心里把自己编织的壮举视为一种魔法,就像童话中的哑巴公主为了让她的天鹅兄弟变回人形而编织荨麻衣服一样。只要我能够把一整套宝宝的衣物织完,那么这套衣服的小主人就会随即离开我母亲的身体,被召唤到人间。只要宝宝出来了,让我看到了——只要宝宝露脸了——就都好办了。但目前来说,这小东西是个威胁。
于是我继续一心一意地专注于编织。我们北上之前,我织完了手套;除了个别笨拙的针脚,多少算是完美无瑕。到了岛上之后,我织完了紧身毛裤——一条裤腿略短,可以抻长些,我觉得。我马不停蹄地开始织毛衣,其中有几行要织出桂花针——有难度,但我下定决心要把它克服。
在此期间,我的母亲一点用处都没有。我的编织马拉松刚开始时,她答应负责织袜子。她会编织,以前也织过:我用的编织图谱曾经就是她的。她会织袜子的脚跟部分,这个技巧我还没完全掌握。但是,尽管能力超强,可她一直在偷懒:到目前为止她只织了半只袜子。她把织物丢在一边不管,而是倚着躺椅休息,双脚翘在木材堆上,读着有关骑马、下毒和剑术的古代浪漫小说——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我也读过那些小说——要不然就头靠枕头懒洋洋地打盹儿,她的面容苍白湿润,她细长的头发也潮乎乎的,她腹部隆起的样子让我感到眩晕,就像看到别人划破手指时的感觉一样。她喜欢穿着一件很久前曾被她束之高阁的旧罩衫;我记得某年万圣节我还穿上它扮演过一个拎着小包的胖女人。那衣服让她显得可怜。
她大白天睡觉的样子让人害怕。那不像她。通常情况下,她是那种散步时目标明确、步履迅速,冬天在冰场上能用相当惊人的速度滑大圈,游起泳来劈波斩浪,并且可以热热闹闹地鼓捣出一桌菜的人——她管那叫鼓捣。她总是知道在紧急情况下该怎么做,她有条理又乐观,她掌管大局。可现在她好像退位了一样。
不编织的时候,我勤奋地扫地。我用手压泵一桶接一桶地打水,然后拎上山,溅出来的水花洒在我**的两条腿上;我用镀锌的盆洗衣服,用阳光牌肥皂在洗衣板上搓,再把衣服装进篮子,拿到山脚下的河边去漂干净,然后再把它们拿上山,在绳子上晾晒。我给花园除草,我搬木头,这一切都在母亲令人担心的懈怠中进行着。
她每天都去游个泳,只不过游得无精打采,只是在随波逐流地漂,和从前的她大相径庭;我也会一起去,不管我愿不愿意:我得看着她别淹死。我很担心她会突然沉下去,沉入冰冷的褐色的水中,头发像海草一样朝四面八方漂散,双眼冷静地望向我。那样的话,我就必须跳进水里,用胳膊搂住她的脖子,把她拖到岸边,可我怎么做得到呢?她太沉了。但这种情况还没发生过,而且她很喜欢到水里去;那似乎能让她醒来。只有头露在水面上时,她看起来才更像她自己。在这种时候,她甚至会微笑,而我就会产生一种错觉,仿佛一切都回到了本来的模样。
但随后她会浑身滴着水走上岸来——她的双腿后侧有曲张的静脉血管,虽然我感到尴尬,但还是无法避免看到——她会迈着缓慢到令人揪心的步子回到小屋,为我们准备午餐。午餐是沙丁鱼,或者抹上花生酱的饼干,或者——如果我们有的话——奶酪,再加上菜园里种的番茄,还有我挖出来洗干净的胡萝卜。她似乎没什么胃口吃午餐,但是无论如何还是会嚼完咽下去。她会尽量聊几句,比如我的编织任务进展如何,但我不知道该跟她说什么。我不理解为什么她要选择这么做,为什么她要让自己变得这么有气无力,浑身臃肿,并让未来——我的未来——变得充满阴影和不确定性。我以为她是故意这样做的。我没想过她或许也被打了个措手不及。
那是八月中旬——又闷又热。蝉在枝头嘶叫,干燥的松针踩在脚下瑟瑟作响。湖面平静得可怕,仿佛在酝酿着一场即将发生的雷暴。我的母亲在打盹儿。我坐在码头上,拍着螫蝇,忧心忡忡。我想哭,但我不能让自己哭出来。我只能独当一面。如果危险情况——无论是什么——开始出现,我该怎么办?我觉得我已经知道了有可能发生的事情:宝宝马上要出生,比预产期提前很多。然后呢?我总不能把她塞回去吧。
我们在一座岛上,目力所及之处看不到其他人的踪影,没有电话,到最近的村子要开船七英里[2]。我得登上我们那艘笨重的旧船,发动舷外马达——我知道该怎么做,但是我必须使出全身的力气才能拉动马达线——并一直把船开到村子里,路上可能要花一个小时。到了那儿我就可以打电话求救了。可是如果马达发动不起来怎么办?之前有过这种情况。或者,如果船在半路上抛锚了怎么办?船上有个工具箱,但我只会最基本的修理。我能修好安全销,我会检查油路;如果这些都不管用,我就只能划桨,或者朝着路过的渔民挥手呼叫——如果有的话。
我也可以划独木舟——我学过,要在船尾处放上一块石头压住分量,在船头那端划桨。但是这个办法遇到风就没用了,哪怕是一点微风都不行:我没有足够的力气保持船行进的方向,我会被吹歪。
我想出了最后关头的计划。我可以划独木舟去往近岸的某个小岛——那个距离我无论如何都能划到。然后我会在岛上放一把火。护林员会看到烟雾,然后派出一架水上飞机过来,而我就可以站在码头上,挥舞着一个白色的枕头上蹿下跳,他们一定能看到。这个计划绝对不会失败。风险在于,我可能会一不小心把陆地那边也点着了。那么我就会成为纵火犯并被关进监狱。但无论如何我还是得这么干。不然的话,我的母亲就会……会怎样呢?
我的思绪在这里中断,我跑上山坡,从熟睡的母亲身边轻轻走过,走进小屋,拿出那个装满葡萄干的罐子,走向那棵大杨树,每当我因为有了莫名其妙的想法而抑制不住自己的时候,就总是会到那里去。我倚在大树下,往嘴里塞了一把葡萄干,开始投入地阅读我最喜欢的一本书。
这是一本烹饪书。书名叫《烹饪与餐桌服务之道》,我最近放弃了所有小说,甚至连《森林蘑菇指南》都不看了,开始全心全意地阅读这本书。书的作者是一位名叫莎拉·菲尔德·斯普林特的女士,这个名字就让我有信任感。莎拉老派而可靠,菲尔德[3]带着田园的芬芳,而斯普林特[4]——嗯,如果你身边有一位叫作斯普林特的女士,那就不会有胡言乱语、痛哭流涕、歇斯底里和对正确行动方针的怀疑。这本书年代久远,在我出生前十年已经面世;它是在大萧条初期由植物起酥油制造厂商科瑞公司出版的,据我母亲说,那个时候黄油开始变得昂贵,所以书中的所有食谱都用到了科瑞起酥油。我们总是在岛上储备很多科瑞起酥油,因为天气一热黄油就很容易坏。但科瑞起酥油基本上是永远不会坏的。很久前,母亲有喜之前,用它做过馅儿饼,这本书里也到处能看到她的批注,她写道“好!!”,或者“使用一半白糖一半红糖”。
然而,让我着迷的并不是书中的食谱,而是开头两章。第一章叫作“没有仆人的家庭”,第二章叫作“有仆人的家庭”。这两章都是进入另一个世界的窗口,让我迫不及待地透过它们窥探一番。我知道它们只是窗,不是门:我无法进去。然而,里面的生活多让人心驰神往啊!
莎拉·菲尔德·斯普林特对于正确的生活方式有着严格的要求。她有规矩,并强制实施。热菜必须趁热上桌,凉菜必须足够凉。“无论用什么方法,这是必须做到的。”她说。我需要的正是这类建议。在餐布的清洁度和餐具的光泽度方面,她的态度很坚决。“即使只是一餐的布置,就算只用一尘不染的镂花针织餐垫,也好过铺上一块有污渍的桌布。”她命令道。我们的桌子上铺着油布,餐具是不锈钢的。至于餐垫,那是超出我人生经验的东西,但我想,能够拥有几条应该会很优雅。
虽然对于基本原则非常坚持,莎拉·菲尔德·斯普林特也有着其他更为圆融的价值观。用餐时间一定要让人乐在其中,一定要有魅力。每张餐桌都应该有中心装饰,比如一些鲜花,或者摆好的水果。如果做不到,“一些小小的蕨类植物加上点鹧鸪藤,或者在矮边碗或者精美的柳条筐里放上一些色彩缤纷的植物”同样可以。
我多希望能拥有一个早餐托盘,上面放着一个小花瓶,里面插着几朵水仙,和图片上一样,或者在小茶桌旁边招待“几个最好的朋友”——这些朋友会是谁呢?——又或者,我最希望的,就是在看得见风景的边廊上,一边吃早餐,一边欣赏“蜿蜒的河流,还有白色教堂的尖顶从对岸郁郁葱葱的树木中舒展出来”的怡人景色。舒展——我喜欢这个词,它听上去是那么平静。
所有这些都是没有仆人的家庭能够实现的。然后,是有仆人的那一章。斯普林特夫人在这一章里也极为讲究,并提供了翔实的内容。(能看得出她是斯普林特夫人;她已婚,但没有其他马虎的后果,这一点和我的母亲不同。)“如果耐心、善良并且公平,就能把一个懒散并缺乏经验的女孩转变成一个干净整洁的专业仆人。”她这样告诉我。吸引我的是转变这个词。我想转变别人,还是想被别人转变?我要做那个和善的一家之主,还是那个曾经懒散的女仆?我不知道。
女仆有两张照片,一张是白天的服装,穿着白色的鞋和长袜,系着一条白色的平纹细布围裙——平纹细布是什么?另一张是下午茶和晚餐时的服装,穿着黑色的长袜,领子和袖口是蝉翼纱的。这两张照片中她的表情相同:脸上带着温柔的浅笑,一双眼睛坦率而矜持地凝视前方,仿佛正在听候吩咐。她的眼睛下面有若隐若现的黑眼圈。我无法判断她看起来是和蔼可亲,还是忍辱负重,抑或只是茫然。如果桌布上有一个污点或者一件银餐具不够亮,她就是被责骂的对象。无论如何,我还是嫉妒她。她已经被转变了,也不需要再做任何决定。
我吃完了葡萄干,合上了书,在短裤上抹了抹黏糊糊的双手。现在该继续编织了。有时候我忘了洗手,把褐色的葡萄干污渍沾到了白色毛线上,不过这可以晚点再补救。斯普林特夫人总是使用象牙皂,知道有这种东西存在真好。我先到菜园里摘了一些豌豆藤,又从红花菜豆藤上摘了一把红色的花朵,用来作为餐桌上的装饰,这项工作现在由我负责了。然而,我的装饰再有魅力,也无法抵消我们使用的纸餐巾的劣质感:母亲坚持要重复使用两次后才丢掉,以避免浪费,而且她还用铅笔在餐巾上写下了我们的姓名的缩写。我能想象,斯普林特夫人看到这种邋遢的做法会作何感想。
这一切持续了多久?似乎像永远那么漫长,但实际上可能只有一两个星期。我的父亲及时回到了家里;几片枫叶变成了橙红色,然后又是几片;潜鸟们开始聚集,每天夜里整装待发,准备着即将开始的秋季迁徙。很快我们就返回城市,我又可以照常上学了。
我织完了一整套婴儿服,除了母亲负责的一只小毛袜子之外——宝宝的小脚丫不会像天鹅那样吧?——我把那套小衣服用白色的棉纸包好,放进抽屉。它有些变形,也不太干净——葡萄干的污渍去不掉了——但是衣服叠起来的时候反正看不到。
我的小妹妹是十月出生的,在我十二岁生日之前几周。她的手指和脚趾数目都对。我把粉色的缎带穿进婴儿服的小扣眼里,还给小帽子缀上了花环,宝宝漂漂亮亮地从医院回到了家。母亲的朋友们过来看望,并且赞赏了我的编织技术,至少看起来是这样的。“这些全是你织的?”她们问。“几乎全都是。”我谦虚地回答。我没有提到母亲没完成她自己的小任务。
母亲说她连一根手指头都不用动,我就像一只小鼹鼠似的开始了编织。“多好的一个小童工啊!”那些朋友说。但我感觉她们认为这件事很滑稽。
宝宝很可爱,虽然转眼间她就穿不下我给她织的婴儿服了。但她不睡觉。你刚把她放下,她就会立刻醒来,号哭不止:她出生之前笼罩在她周围的焦虑情绪似乎侵入了她的身体,她每晚会醒来六或七或八或九次,哀怨地哭泣着。斯波克医生在《婴幼儿护理》一书中说这种情况会在几个月内消失,但在她身上非但没有消失,反而越发严重。
我曾经过于肥胖的母亲如今已经过于消瘦。缺乏睡眠让她憔悴,她的头发暗淡无光,黑眼圈像是淤青一样,肩膀向前佝偻。我躺着写作业时,就把双脚搭在宝宝的摇篮上不停地摇啊摇,让母亲能得空休息一下。有时我放学回家后会给宝宝换好尿布,把她包裹好,放在婴儿车里推出去,或者我会抱着她来回溜达,一只手把法兰绒里她那温暖的、香喷喷的、蠕动着的小小身体贴近我的肩膀,另一只手举着一本书看,或者我会把她抱回我的房间,用臂弯轻轻摇动着她,给她唱歌。唱歌尤其有效。哦,我亲爱的内莉·格雷,他们把你带走,我再也见不到我的宝贝,[5]我会唱这个;或者唱少年唱诗班的《考文垂颂歌》:
希律王,很愤怒,
这一天下达了命令,
让他的勇士,在他面前,
把所有的儿童,全部杀戮。
这首歌曲调很哀伤,但是能立刻让她入睡。
除此之外,我还要打扫洗手间或者洗碗。
妹妹一岁时,我十三岁,已经上中学了;她两岁时,我十四岁。我在学校的好姐妹们——她们有些人已经十五岁了——会在回家的路上磨磨蹭蹭,跟男生搭讪。有些人会去看电影,在那儿认识别的学校的男生;还有的人在溜冰场上干同样的事。她们互相交流哪些男生是帅哥,哪些很差劲,她们带着新欢到汽车电影院去赴四人约会,吃着爆米花,在汽车后座上滚来滚去,她们试穿没有肩带的礼服,她们参加各种舞会,在昏暗的体育馆里沉浸于暧昧的音乐和魅蓝的光线,她们紧贴着自己舞伴的身体四处扭动,或者到娱乐室里打开电视,然后在沙发上耳鬓厮磨。
这些描述都是我在午餐的时候听说的,但我没办法加入她们。我避开主动接近我的男生:我想办法拒绝了他们,我得回家照顾仍然不肯睡觉的宝宝。我的母亲在家里有气无力地走来走去,仿佛生病了,或者在挨饿。为了宝宝不睡觉的问题,她去找过医生,但医生也没办法。他只是说:“你刚好生了个有这种情况的孩子。”
我的担忧变成了暴躁。每天晚上我都尽快从餐桌边逃掉,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用只言片语敷衍地回答父母提出的问题。没有作业和家务,也不需要照看宝宝的时候,我就躺在**,把头悬在床边,举着一面镜子看自己头朝下是什么样子。
一天晚上,我正站在母亲身后。我一定是在等她走出浴室,好进去试试某件新品,很可能是一种不一样的洗发水。她正俯身把脏衣服从洗衣篮里拿出来。这时,宝宝哭了起来。“你能去把她哄睡吗?”她说,她经常这样。正常情况下,我会脚步沉重地离开,去安抚宝宝,给她唱歌,轻摇着她入睡。
“我为什么要去?”我说,“她不是我的孩子。我没生她。是你生的。”我从未对她说过这么粗鲁的话。甚至当这些话从我嘴里吐出来的同时,我就知道我太过分了,尽管我说的只不过是实话,至少是一部分实话。
我的母亲站直,转身,然后狠狠地打了我一个耳光,整套动作一气呵成。她以前从没做过这种事,或者任何类似的事。我什么都没说。她也什么都没说。我们都为自己感到震惊,也为对方感到震惊。
我应该感到受伤,我确实感觉到了。但我也感到自由,仿佛从某个魔咒中解脱了一样。我不用再被迫为她服务了。表面上,我仍然会帮忙——在这一点上我无法改变自己。但是另一种更为隐秘的生活如同一幅黑色的织物,在我面前展开。很快我也会到汽车影院去,我也会吃爆米花。我的灵魂已经开始奔跑——到电影院去,到溜冰场去,到令人神迷的蓝色光线中的舞池去,到我仍然无法想象的那些诱人的、俗丽的、可怕的快乐中去。
[1] 十六世纪英国航海家、政治家。
[2] 1英里约为1609.34米,7英里约为11.27千米。
[3] 菲尔德英文为Field,这个词也有“田园,田野”之意。
[4] 斯普林特英文为Splint,这个词也有骨科夹板的意思,以及修正混乱错位的引申含义。
[5] 歌曲《亲爱的内莉·格雷》中的歌词,这首歌是一首十九世纪的反奴隶制民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