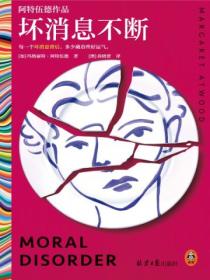10 拉布拉多[1]大溃败 The Labrador Fiasco
那是个十月。不过,是哪个十月?反正是某年的十月,日光倏然亮起又骤然暗淡的十月,有着红色和橙色叶子的十月。我的父亲坐在壁炉旁的扶手椅上。他穿着黑白格子的便袍,套在其他衣服外面,还穿着老式皮拖鞋,把脚架在一个脚垫上。所以那一定是个傍晚。
我的母亲正在读书给他听。她摆弄着眼镜,俯身于书页上;又或者只是看起来像是俯着身。实际上那就是她现在佝偻的体态。
我的父亲在笑,所以这部分一定是他喜欢听的。他左脸的笑容比右脸明显:六年前他中了风,我们都假装他已经康复;他也确实康复了——基本上。
“现在发生什么了?”我边脱外套边问。我知道这个故事,以前就听过。
“他们刚出发。”我的母亲说。
我父亲说:“他们带错了补给。”这让他开心,他自己肯定不会带错补给。实际上,他从一开始就不会展开这次不明智的旅程,或者说——尽管他以前更鲁莽,更急躁,更确信自己有能力对抗命运和超越危险——这是他现在的观点。“十足的傻瓜。”他说完又笑了。
但是,除了错误的补给之外,他们还能拿到什么补给呢?白糖、白面粉、大米,你当时能拿的就是这些。豌豆粉、脱水苹果、硬饼干、熏肉、猪油,都是重东西。那时还没有冻干技术,没有方便的汤料包;没有尼龙马甲,没有能收成口袋大小的睡袋,没有轻便的防水布。他们的帐篷是用气球绸做的,涂了油用来防水。他们的毯子是羊毛的。背包是帆布的,附有皮带和横过额头的扎带,以减轻腰部的负重。这些东西会有焦油的味道。此外,还有两支步枪、两把手枪、一千两百发子弹、一台照相机和一个六分仪;还有炊具和衣服。每一磅物资都必须由人工进行水陆搬运,或者用独木舟拖上岸,独木舟有十八英尺长,木质框架,覆盖着帆布。
然而,这一切都不会让探险者们望而却步,或者说起初不会。他们有两个人,两个年轻的美国人。他们以前也参加过露营探险,不过那是在纬度更低的温暖地区,他们可以在愉悦的篝火前抽着气味芬芳的傍晚的烟斗,当夕阳西下天色苍白的时候,锅里烤着的新鲜鳟鱼滋滋作响。关于荒野的魅力与挑战未知,每个人都能写出一两段吉卜林风格的清新散文。这是1903年,当时探险仍然是一种时尚,被视为对男子气概的一种考验,同时男子气概自身也仍然是一种时尚,并且会自然而然地与干净这个词一起出现。男子气概、干净、荒凉,让你能感觉自由的地方。当然,得带着枪和鱼竿。你要靠山吃山,靠水吃水。
探险队的领队名叫哈伯德,为一家专门介绍户外活动的杂志工作。他的想法是,他要跟他的表弟兼好哥们儿——这个人的名字叫华莱士——深入拉布拉多地区最后一片尚未开发的荒野,然后他会发表一系列的文章来讲述他们的探险经历,并借此扬名立万。(这是他的原话:“我会扬名立万。”)具体而言,他们会沿着纳斯科皮河上行,据说这条河的源头是传说中渔产丰富的密奇卡茂内陆湖;从那里他们可以抵达乔治河,印第安人每年夏天都在那里集中狩猎驯鹿,从那里再前往哈得孙湾的一个驻点,然后出去再次抵达海岸。哈伯德计划与印第安人相遇时做一点业余的人类学研究,他也会把这部分写进文章,并拍些照片——一个蓬头垢面的猎人手持一把老式步枪,脚下踩着一具动物尸体;一只被砍掉的鹿首,鹿角张牙舞爪。戴着珠子项链、眼睛炯炯有神的女人在咀嚼或缝制兽皮,或者做着任何事情。最后的野人,类似这种题材。人们对这类题材很感兴趣。他也会描述野人们的菜单。
(但那些印第安人是从北边过来的。从来不会从西边或者南边走水路。)
在这样的故事中,总会有——总应该有——一位印第安老人,在白人们计划出发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是来警告他们的,因为他心地善良,而他们却莽撞无知。“别去那里,”他说,“那个地方我们从来不去。”这些故事中的印第安人讲起话来都一本正经。
“为什么不去呢?”白人们问。
“恶灵住在那儿。”印第安老人说。白人微笑着感谢他,但没有理会他的忠告。本地迷信,他们想。所以他们去了曾被警告不要去的地方,然后,在经历了很多磨难之后,他们死了。印第安老人听说之后摇了摇头。愚蠢的白人,但你还能怎么跟他们说呢?他们不懂得尊重。
这本书里没有印第安老人——不知道为什么他被漏掉了——所以我父亲自己担任了这个角色。“他们不应该到那里去,”他说,“印第安人从来不走那条路。”不过,他并没有提到恶灵。他说的是:“没有东西吃。”对印第安人来说两者是一回事,因为如果食物不是来自灵魂,那还能来自哪里?食物不是本来就有的,而是被赐予的;但有时也会被扣留。
哈伯德和华莱士试图雇几个印第安人,至少在旅程的最初阶段和他们一起走,并帮他们扛行李。没人愿意去。他们说他们“太忙”。实际上是因为他们知道得太多了。他们知道的是在那里你不可能把你需要的所有食物都随身携带。如果你带不了那么多食物,你就只能打猎。但绝大多数时候,那里没有什么猎物。“太忙”意味着还不想去送死,也意味着拘于礼貌而无法直言问题。
这两位探险家做对了一件事。他们雇了个向导。他的名字叫乔治,是个克里族印第安人,或者有部分克里族血统。按照他们当时的叫法,是个“杂种”。他来自距离拉布拉多非常远的詹姆斯湾,所以他根本不知道拉布拉多的不幸的真相。乔治一路南下,到纽约市去见他的雇主,他以前从来没去过那里。他以前从来没去过美国,甚至从来没进过城。他保持镇定,他环顾四周;他弄清楚了什么是出租车,以及如何叫出租车,这充分显示出他的足智多谋。他的理智分析能力今后会派上大用场。
“乔治那小子很不一般。”我的父亲说。乔治是整个故事里他最喜欢的人。
家里的某个地方有一张我父亲的单人照——可能被夹在了某一本相册的后面,和一堆还没来得及整理的快照放在一起。照片上是三十年前正在某次独木舟旅行途中的他——如果你不把这些说明写在照片的背面,他们就会忘记。他显然正在经过某个渡口。他没有刮胡子,他的头上缠着一条头巾,为了防止黑蝇和蚊子,他背着一个沉重的背包,宽大的扎带勒住额头。他的头发乌黑,他那张闪着光的脸被晒成深深的古铜色,而且并不太干净。他看起来有点不怀好意;像个海盗,或者其实更像个北部山林的向导,那种半夜里狼群袭来的前一刻带着你最好的步枪溜之大吉的人。但也像一个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人。
“那个乔治知道他在做什么。”这时我父亲说道。
说的是他离开纽约之后;但是在纽约期间,乔治没什么帮助,因为他不知道去哪里买东西。那两个人正是在纽约购买了所有必需的补给,只差一张刺网,他们以为刺网在北边也能买到。他们也没买备用的软皮鞋。这可能是他们最严重的错误。
然后他们出发了,先坐火车,再坐船,然后坐更小的船。细节很枯燥,天气很差,饮食很糟糕,没有一种交通工具是准时的。他们花了很多个小时,甚至是好几天的时间在码头附近等待,不知道自己的行李还会不会出现。
“今晚就读到这儿吧。”我母亲说。
“我想他已经睡着了。”我说。
“他以前从来不会睡着,”我母亲说,“听这个故事的时候不会。他一般都会忙着列出他的清单。”
“他的清单?”
“他要带的补给的清单。”
我父亲睡觉的时候,我跳着读了故事后面的部分。那三个人终于从拉布拉多凄凉的东北海岸进入了内陆河,离开他们最后的起点,认真地开始航行。那是七月中旬,但短暂的夏天很快就会结束,他们还有五百英里的路程要走。
他们的任务是穿过又长又窄的格兰德湖。湖的最末端,就是纳斯卡皮河汇入之处,或者至少他们是这样听说的。他们见过的唯一一张地图是一位白人旅行者早在大约五十年前粗略绘制的,地图上显示只有一条河流汇入格兰德湖。就是所有印第安人都提到过的那条河:那条通向某处的河。为什么要提到其他的河流呢,因为怎么会有人想要知道它们的存在呢?很多植物没有名字就是因为它们不能吃也不能用。
但实际上还有四条其他河流。
在这第一个早晨,他们兴高采烈——反正华莱士是这样记录的。他们充满希冀,期待着探险。天空湛蓝,空气清新,阳光明媚,树梢似乎在向他们点头示意。他们并不明白看到树梢点头要小心。他们吃了配糖浆的薄饼作为午餐,充满幸福感。他们知道他们即将去往险境,但他们也知道他们是不朽的。在北方确实会产生这种心绪。他们用相机拍照,拍他们的独木舟,拍他们的背包,拍彼此的样子:胡子拉碴,满脸汗水,缠着绑腿,头上也缠着圆顶硬礼帽一样的头巾,轻快地靠在桨上——令人心碎,但只有当你知道了结局才会这样想。但此时他们正在享受着人生的高光时刻。
还有另一张我父亲的照片,也许也是在经过渡口的那次旅行中拍下的,不然就是他戴了同样的头巾。这一次,他对着相机镜头咧嘴笑着,假装在用手里的斧头刮胡子。这张照片说明了两件夸张的事情:一是他的斧头像剃刀一样锋利;二是他的胡子非常硬,只有斧头才能砍断它们。这都是胡扯,是独木舟旅行时的玩笑。当然他私下一度相信这两件事都是真的。
第二天,三个人错过了纳斯卡皮河口,这个河口隐藏在一座岛屿的后面,看起来像一条海岸线。他们甚至没有怀疑它有可能在那儿。他们继续朝着大湖的尽头航行,并进入了他们在那里找到的一条河流。他们走错了路。
我超过一周没有回到拉布拉多。再次回去的那天是个周日的晚上。壁炉里的火焰熊熊燃烧,我的父亲正坐在壁炉前,等着听接下去会发生什么。我母亲正在忙着准备发酵粉饼干和低咖啡因的茶。我在找曲奇饼吃。
“一切都还好吗?”我问。
“不错,”她说,“但他运动量不够。”在她看来,一切就是指我父亲。
“你应该让他出去走走。”我说。
“‘让他’。”她说。
“呃,建议他。”
“他觉得如果没有目的,纯为走路而走路没意义。”她说。
“你可以给他找点事去办办。”我说。对此她甚至懒得回答。
“他说他脚疼。”她说。我想到了柜子里那一大堆几乎全新的靴子和鞋以及最近数量激增的靴子和鞋。他还在不停地买。他一定觉得,只要他能找到合适的那双鞋,那么让他脚疼的原因无论是什么,都会消失。
我把茶杯拿进去,把盘子收拾好。“所以,哈伯德和华莱士进展如何了?”我说,“你们读到他们吃猫头鹰的那部分了吗?”
“无济于事,”他说,“他们找错了河。不过即使他们找对了,也一样来不及。”
哈伯德、华莱士和乔治辛苦地逆流而上。正午热浪逼人。苍蝇在折磨着他们,小苍蝇像针尖一样,大苍蝇有拇指那么大。这条河几乎无法航行:他们不得不拖着负载沉重的独木舟走过砾石的浅滩,或者从陆地上绕过急流,穿过条件恶劣、没有标记、错综复杂的森林。河流在他们面前延伸,在他们身后则像迷宫一样封闭起来。河岸越来越陡峭;一座又一座的山丘,看似平缓,实则艰难。这是一片稀疏的风景:破烂的云杉、桦树、杨树,都骨瘦如柴,在有些地方甚至都被烧毁了,前路被烧焦和倒下的树干挡住。
他们过了多长时间才意识到自己驶入了错误的河流?太长了。他们把一些食物藏了起来,这样就不必随身携带;他们把另外一些食物扔掉了。他们射杀了一头驯鹿,吃了,丢下了蹄子和鹿头。他们的脚很疼,他们的软皮鞋已经磨损了。
终于,哈伯德爬上了一座高山,从山顶看到了密奇卡茂湖,但他们航行的河流并不通向那里。那个湖太远了,他们不可能拖着独木舟走那么远的路穿过森林。他们只能折返。
他们傍晚时分的谈话内容不再是关于发现和探索,他们讨论的是准备吃什么。他们明天吃什么,他们回去之后吃什么。他们为伙食、筵席和盛大的宴会编写菜单。乔治能够猎取和抓到一些东西。这里一只鸭子,那里一只松鸡。还捕猎了一只灰燥鸦。他们抓了六十条鳟鱼,是费尽心思一条一条用钩子和线钓上来的,因为他们没有刺网。这些鳟鱼像冰水一样清澈、新鲜,但只有六英寸[2]长。什么都远远不够。旅行所消耗的能量超过了他们所能吸收的能量,他们正在缓慢地溶解,消耗。
与此同时,夜晚变得越来越长,越来越暗。河流的边缘开始结冰。蹚着冰冷刺骨的河水,拖着独木舟走过浅滩,让他们浑身发抖,喘不上气。第一场雪飘落下来。
“那是穷山恶水的地方,”我父亲说,“没有麋鹿,甚至连熊都没有。没有熊永远是个恶兆。”他去过那边,或者附近有着同样地形的地方。他带着向往和思念说起来,还有某种悲伤。“如今你当然可以坐飞机过去。几个小时内就可以走完他们的全程。”他不屑地挥了挥手指:飞机也不过如此。
“那猫头鹰呢?”我说。
“什么猫头鹰?”我父亲说。
“他们吃掉的那只,”我说,“我记得就是在独木舟翻覆的地方,他们还把火柴塞进耳朵,好保护它不会被打湿。”
“我觉得是别人,”我父亲说,“是后来又做了同样尝试的那些人。我认为这群人没吃猫头鹰。”
“如果他们真吃了,那应该是什么种类的猫头鹰?”我说。
“大角鸮或者鬼鸮,”他说,“如果他们幸运的话。它们的身上肉更多。但也可能是小东西。”他发出了一连串细小而阴森的叫声,就像远处的一只狗,然后他笑了。他能通过叫声判断出那里的每一种鸟类,现在也能。
“他下午睡得太多了。”我母亲说。
“也许他累了。”我说。
“他不应该累到那种程度,”她说,“累,但又不安分。他的食欲在减退。”
“也许他需要个兴趣爱好,”我说,“能占住他脑子的东西。”
“他以前的爱好可多了。”我母亲说。
我想知道它们都去哪儿了,那些爱好。属于它们的工具和材料还在:木工刨子和水平仪,用来绑拟饵的羽毛,放大版画的机器,制作弓箭的尖头。在我看来,这些零碎的东西就像是出土文物,它们从考古现场被挖掘出来,经过辨别和归类,作为推断昔日生活的凭证。
“他以前经常说要写回忆录,”我母亲说,“某种意义上的记录。他去过的所有地方。他确实开过几次头,但现在他已经没兴趣了。他的视力不太好。”
“他可以用录音机。”我说。
“哦,天啊,”我母亲说,“更多新玩意儿!”
狂风呼啸而过,雪落下又停止。三个人已经穿越陆地来到另一条河,期望着情况能够好转,但事与愿违。一天晚上,乔治做了一个梦:上帝出现在他面前,光芒四射,和蔼可亲,语气友好但坚决。“我不能再给你们鳟鱼了,”他说,“但如果你们坚持沿着这条河航行,就能顺利到达格兰德湖。只要你们不偏离这条河,我就会安全地把你们带出来。”
乔治把这个梦告诉了其他人。没有人当回事。他们放弃了独木舟,改走陆路,希望能回到他们以前的路。过了太久之后,他们确实找到了之前的路,并沿路跋涉着走下了他们之前逆流而上的河谷,他们在曾经的宿营地翻找着之前丢弃的食物。他们不再用英里计量距离,而是以天为单位:他们还剩下多少天,还需要多少天。但那取决于天气,也取决于他们自身的能力:他们能走多快。他们找到一坨发霉的面粉,一点猪油,几根骨头,一些驯鹿的蹄子,他们把这些东西煮了。还有一小罐干芥末,他们把它混进汤里,发现它令人鼓舞。
十月的第三个星期,情况是这样的:
哈伯德已经虚弱得不能继续走了。他被留了下来,待在帐篷里,裹着毯子,生着火。另外两个人接着走了。他们希望能走出去,然后派人回来救他。他把最后的一点豌豆粉给了他们。
雪不停地下着。他的晚餐是浓茶和骨头汤,他还把自己仅有的一双软皮鞋的生皮煮熟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味道真的很好。现在他没有鞋了。他把全部希望寄托在别人成功出去并回来救他,反正他是这样记录的。但他还是开始给妻子写遗书了。他写道自己还有一双牛皮手套,准备明天煮了吃掉。
然后他就睡着了,然后他就死了。
沿途走了几天之后,华莱士也不得不放弃。他和乔治兵分两路:华莱士倾向于带着他们设法找到的最新一批储藏物资——几把发霉的面粉——往回走。他会找到哈伯德,和他一起等待救援。但他遇到了一场暴风雪,并迷失了方向。此刻他正在一个树枝搭成的窝棚里,等着大雪逐渐停止。他非常虚弱,而且已经感觉不到饥饿了,他知道这是个不好的迹象。他做出的每一个动作都缓慢而谨慎,同时又很不真实,仿佛他已经离开了自己的身体,只是在一边看着它。在白天的日光下或者晚上的红色火光——因为他仍然可以生火——的闪烁中,他手指末端的涡纹在他眼中都显得神奇无比,如此清晰详细;他的眼神追踪着编织毯上的图案,像是在看一幅地图。
他的亡妻出现在他面前,并就他的睡眠安排提出了几条实用的建议:下面垫一层更厚的云杉树枝,她说,会更舒服。有时他只能听到她的声音,有时他还能看到她,她穿着一件蓝色的夏装,她的长发被一枚闪亮的发卡盘在头顶。她看起来非常自在。透过她的背影,可以看到窝棚的柱子。对此华莱士已经见怪不怪。
在更远的地方,乔治继续走着,继续往外走。他多少知道他要去哪里,他要找到救援并带着他们回来。但他还没出去,他还在里面。雪包围着他,灰白色的天空包围着他。他一度遇到了自己的脚印,才意识到自己一直在绕圈。他也瘦了很多,并且虚弱,但他成功地射中了一只豪猪。他停下来想了想:他可以转回头去,沿着他来时的脚印返回,把豪猪带回去与其他人分享;他也可以自己把豪猪全部吃掉,然后继续前进。他知道,如果他回去,那么很可能最后不会有人活着出来,但如果他继续前进,至少还有存活的可能,至少对他来说。他把豪猪的骨头囤好,继续前进。
“那个乔治做得对。”我父亲说。
一周后,父亲坐在桌边用餐时再次中风。这一次,他每只眼睛失去了一半视力,还失去了短期记忆,以及对自己身在何处的感知。仅仅一分钟之隔,他就会糊涂。他在客厅里摸索,仿佛以前从没到过这个地方。医生说这一次他不太可能恢复了。
时间流逝。窗外的丁香花此时正在盛开,他能看到它们,或者它们的一部分。尽管如此,他仍然觉得现在是十月。然而,他的精神还在。他坐在扶手椅上,想要把事情弄清楚。一个沙发垫看起来很像另一个沙发垫,除非你有别的判断标准。他看着阳光在硬木地板上闪耀。他最好的判断是:那是一条河。在极端情况下,你必须运用你的智慧。
“我来了。”我说着,亲吻他干燥的脸颊。他没有变秃,丝毫没有。他有一头银白色的头发,像一只被冻住的白鹭。
他用双眼左侧的余光看着我,只有那样他才能看到。
“你似乎突然老了不少。”他说。
据我们所知,他失去了之前四五年的记忆,还有再之前的几段时期。他对我感到失望: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而是因为我没能做什么。我没能保持年轻。如果我做到了,我就能拯救他,那他也可以保持以前的样子了。
我希望我能想出一些让他开心的办法。我试过录下鸟儿的歌声,但他不喜欢:它们让他想起他曾经知道但现在却想不起来的事情。故事也不好,连短篇故事都不行,因为当你读到第二页的时候,他已经忘记了开头。如果失去了情节,我们会去向哪里?
音乐好一些,因为它在一点一滴地发生。
我的母亲不知所措,所以她重新布置一切:杯子和盘子,文件,写字台的抽屉。现在她正在外面,带着一种茫然的愤怒拔除花园里的杂草。泥土和野草在空中飞舞:至少这件事总有完成的那天!一阵风吹来,她的头发被吹乱,在她的头顶像羽毛一样飞舞。
我已经告诉她我不能久留。“你不能吗?”她说,“但我们总可以喝个茶,我可以把壁炉点起来……”
“今天不行。”我坚决地说。
他多少能够看得见她在外面,他想让她回到屋里。他不喜欢她在玻璃的另一边。如果他让她溜走了,离开他的视线了,谁知道她会去哪儿呢?她可能会永远消失。
我握住他那只健康的手。“她马上就进来。”我说。但马上可能是一年。
“我想回家。”他说。我知道告诉他现在他就在家里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他指的是别的地方。他指的是他以前的样子。
“我们现在在哪儿?”我问。
他向我瞥来一个狡猾的眼神:我是想要挑他的错吗?“在一座森林里,”他说,“我们得回去了。”
“我们在这里也没事的。”我说。
他考虑了一下:“没太多吃的。”
“我们带了合适的补给。”我说。
他放心了。“但是木材不够。”他对此感到焦虑。他每天都这么说。他说他的脚冷。
“我们可以找来更多的木材,”我说,“我们可以去砍。”
他没那么确定。“我从没想过会发生这样的事。”他说。他不是指中风,因为他不知道自己中风了。他指的是迷路。
“我们知道该怎么做,”我说,“不管怎样,我们会没事的。”
“我们会没事的。”他说,但听上去半信半疑。他不相信我,他是对的。
[1]加拿大的一个地区,位于大西洋沿岸,与纽芬兰岛一海之隔,该地区30%的人口为原住民。
[2] 1英寸约为2.54厘米,6英寸约为15.24厘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