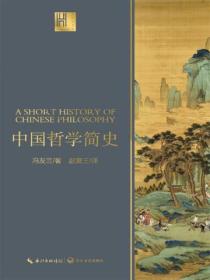第十九章 新道家:崇尚理性的玄学
公元三四世纪盛行的思潮,历来称为“玄学”;“玄”字原出自《老子》第一章,末句形容“道”是“玄之又玄,众妙之门”,意思是指它深远神秘,变化莫测。“玄学”的名字表明它是道家的继续,因此,我称它为“新道家”,这是我起的新名字。
名家再次引起人们的兴趣
在前面第八、九、十章里,我们已经看到,名家向道家提供了“超乎形象”这个概念。在公元三四世纪里,随着道家的再起,对名家的兴趣也再次抬头了。新道家对惠施和公孙龙的理论再次钻研,在“玄学”中提出了“辨名析理”观念。首创这个观念的是郭象,他在《庄子注》的《天下篇注》里,把“玄学”和“辨名析理”结合起来。在本书第八章里,我们看到公孙龙也曾这样做过。
在《世说新语》(下章里,我们还将更多参阅这本书)里,在《文学》篇中说到一个故事,“客问乐令‘指不至’者,乐亦不复剖析文句,直以麈尾柄触几曰:‘至不?’客曰:‘至。’乐因又举麈尾曰:‘若至者,那得去?’于是客乃悟。”乐令名乐广,是当时一位名士。“指不至”是说战国时名家公孙龙分析:一个名词的内涵就是概念,是不变的;名词的外延与其内涵是两回事,它是可以转化的。人指向一个事物时,不等于就已到达那里,这便是“指不至”所要争论之点,也就是“名”与“实”的道理。至魏晋时,还有人以这一点问乐广,乐广以一个拂麈来说明理论问题,当他用麈尾柄触茶几时问“至不”时,这个“至”是指“至”的共相,它是概念,是不变的,既“到”了就不能“不到”;但拂麈在拂拭几上时又至又去,乐广说:“若至者,那得去?”这时,他所用的“至”乃是指具体的“抵达”。名词的概念内涵是不能变的,“至”不能转化为“去”;但名词的外延是能转化的,一个具体的、“至”的东西,又可以转化为“去”。乐广的一系列表示,是辨“至”之名,析“至”之实,这就是“辨名析理”。
用手指指向一张桌子,通常就被认为是已经在概念上到了桌子,但是乐广认为,若以概念而论,到了桌子,就不能离开,这才是“至”;但拂麈却又至又去,因此他反问“若至者,那得去”,意思是说,拂麈表面上已到桌子,实际并未到。因此,乐广从“至”之名分析“至”之实,这是“辨名析理”的一个例子。
对孔子的重新诠释
新道家中,至少有大部分还以孔子为圣人,究其原因,一部分是因为到魏晋时,以孔子为国家崇奉的先师,这思想已经确立。还有一个原因是,新道家对儒家经书中的重要部分也趋于接受,只是在接受中又按老庄的精神予以重新诠释。
举例来说,《论语·先进》篇里,孔子曾说过:“回也其庶乎,屡空。”孔子的意思大概是说,颜回虽然很穷(“空”),但在精神上却是快乐的,由此表明他的道德已接近于完美。在《庄子·大宗师》篇里则衍生出一个颜回“坐忘”——在冥想中与大化合一,以至忘记自我存在——的故事。后来的太史叔明(公元四七四至五四六年)注释《论语》这一段时,心里还想到《庄子·大宗师》里的故事,因此他说:“颜子……遗仁义,忘礼乐,隳肢体,黜聪明,坐忘大通,此忘有之义也。忘有顿尽,非空如何?若以圣人验之,圣人忘忘,大贤不能忘忘。不能忘忘,心复为未尽。一未一空,故屡名生也焉。”(皇侃《论语义疏》卷六)这就是说,颜回还是未能全忘自己,因此才意识到自己的“坐忘”,否则,连“坐忘”也应忘记才是。颜回头脑里还未完全虚静,因此他才说自己“常”空。
另一位注释家顾欢(公元四五三年卒)在注释《论语》的同一段时说:“夫无欲于无欲者,圣人之常也;有欲于无欲者,贤人之分也。二欲同无,故全空以目圣;一有一无,故每虚以称贤。贤人自‘有’观之,则无欲于有欲;自‘无’观之,则有欲于无欲。虚而未尽,非屡如何?”
新道家尽管是道家,却认为孔子比老子、庄子更高明。他们认为,孔子不讲坐忘,因为他已经忘记了“坐忘”这桩事。孔子也不讲“无欲”,因为他已经修养到这地步,已经没有了“无欲”的欲望。正因此,《世说新语》中记载了裴徽和王弼的一段“清谈”。王弼(公元二二六至二四九年)是玄学大师,他对于《老子》和《易经》的注释都已成为经典著作。王弼和裴徽的对话是这样的:
“王辅嗣弱冠诣裴徽,徽问曰:‘夫无者,诚万物之所资,圣人莫肯致言,而老子申之无已,何邪?’弼曰:‘圣人体无,无又不可以训,故言必及有。老、庄未免于有,恒训其所不足。’”(《世说新语·文学》)这个解释正反映了《老子》第五十六章“知者不言,言者不知”的看法。
向秀和郭象
在这一时期里,郭象(死于约公元三一二年)所著《庄子注》即便不是其中最重要的哲学著述,也是最重要著作之一。这里有一个史实问题,即:《庄子注》这部书究竟是否郭象所著?郭象的同时代人曾经指控郭象的《庄子注》是剽窃了与他同时而稍早的另一学者向秀(约公元二二一至三〇〇年)的著作。看来,他们两人都著有《庄子注》,思想也十分接近。因此,随时间推移,他们的两部著作渐难分辨,而成为一部著作。《世说新语·文学》篇曾提到对《庄子·逍遥游》篇的向、郭注,以此和僧支遁的释义相对应。因此,现在流传的《庄子注》,虽然署名是郭象注,其实多半是向秀和郭象两人合著。《晋书·向秀传》中称,向秀著《庄子注》,郭象予以“增衍”,这看来较接近于事实。
据《晋书》记载,向秀和郭象都是河南人,都擅玄学,以清谈著称。在本章里,我把这两位哲学家作为新道学中主张理性的流派的代表,在征引《庄子注》一书时,援《世说新语》例,称“向—郭《注》”。
道是“无”
向—郭《注》对老庄的早期道家思想作了重要的修订。首先,它把“道”解释为“无”。老子和庄子也主张“道”是“无”,但他们所讲的“无”,意思是说:“无以名之”。这是说,他们认为:“道”不是一样东西,因此,无从为它命名。而向—郭《注》则以“道”为“无”。道“无所不在,而所在皆无也”。(《大宗师》“在太极之先而不为高……”注)
向—郭《注》中又说:“谁得先物者乎哉?吾以阴阳为先物,而阴阳者即所谓物耳。谁又先阴阳者乎?吾以自然为先之,而自然即物之自尔耳。吾以至道为先之矣,而至道乃至无也。既以无矣,又奚为先?然则先物者谁乎哉?而犹有物,无已,明物之自然,非有使然也。”(《知北游》“有先天地生者物耶……”注)
向—郭《注》还说:“世或谓罔两待景,景待形,形待造物者。请问:夫造物者,有耶无耶?无也?则胡能造物哉?有也?则不足以物众形。……故造物者无主,而物各自造,物各自造而无所待焉,此天地之正也。”(《齐物论》“恶识所以然……”注)
老庄否认有一位具有人格的造物主,而代之以没有人格的“道”。它是万物之所由生。向、郭两人更进一步,认为道即“无”。他们还把早期道家主张万物来自“道”解释为万物自然而在。因此,向—郭《注》写道:“道,无能也。此言‘得之于道’,乃所以明其自得耳。”(《大宗师》“傅说得之,以相武丁……”注)
同样,先秦道家说,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也只是说,有是自在的。向—郭《注》中有一处说:“非唯无不得化而为有也,有亦不得化而为无矣。是以夫有之为物,虽千变万化,而不得一为无也。不得一为无,故自古无未有之时而常存也。”(《知北游》“无古无今……”注)
万物的“独化”
万物自生,这是向—郭《注》里称之为“独化”的理论。按照这个理论,万物不是由一位造物主所造,但万物之间相互关联,这种种关联不仅存在,而且是必要的。向—郭《注》中说:“人之生也,形虽七尺而五常必具,故虽区区之身,乃举天地以奉之。故天地万物,凡所有者,不可一日而相无也。一物不具,则生者无由得生;一理不至,则天年无缘得终。”(《大宗师》“知人之所为者……”注)
每一物需要每一个“它物”。但每一物仍然是独立自为地存在的。向—郭《注》说:“天下莫不相与为彼我,而彼我皆欲自为,斯东西之相反也。然彼我相与为唇齿,唇齿未尝相为,而唇亡则齿寒。故彼之自为,济我之功弘矣,斯相反而不可以相无者也。”(《秋水》“以功观之……”注)照向—郭《注》的说法,事物之间的关联就像两支国际同盟军,每支军队都是为本国而战,但是两支军队互相支援;一支军队的胜负,必定对它的同盟军产生影响。
宇宙间存在的每一事物都需要整个宇宙作为它存在的必要条件,而它的存在又并不是由某一个特定事物所产生的。当某些条件具备,在某种情况下,某些事物就必然会发生。这并不意味着,万物是由一位创世主或某个人所创造。换句话说,事物是由一般性条件所产生,而不是由于其他某个特定的事物。举例来说,社会主义是一定经济条件的产物,而不是马克思或恩格斯所制造出来的,更不是马克思的《共产主义宣言》所造出来的。就这一层意义来看,我们可以说,事物是自己生出来,而不是由别的事物产生的。
正因为如此,每一事物只能是它自己。向—郭《注》中说:“故人之生也,非误生也;生之所有,非妄有也。天地虽大,万物虽多,然吾之所遇适在于是……故凡所不遇,弗能遇也,其所遇,弗能不遇也;凡所不为,弗能为也,其所为,弗能不为也。故付之而自当矣。”(《德充符》“死生存亡……”注)
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社会现象领域。向—郭《注》又说:“物无非天也。天也者,自然者也。……治乱成败……非人为也,皆自然耳。”(《大宗师》“庸讵知吾所谓天之非人乎?……”注)这里所说“皆自然耳”是指它们都是一定条件和情况下的产物。《庄子·天运》篇讲到圣人乱天下,向—郭《注》对此评论说:“承百代之流而会乎当今之变,其弊至于斯者,非禹也,故曰天下耳。言圣知之迹非乱天下,而天下必有斯乱。”(《天运》“人自为种而天下耳……”注)
典制与道德
向、郭认为,宇宙是在流动不居之中,在向—郭《注》中写道:“夫无力之力,莫大于变化者也。故乃揭天地以趋新,负山岳以舍故。故不暂停,忽已涉新,则天地万物无时而不移也。……今交一臂而失之,皆在冥中去矣。故向者之我,非复今我也。我与今俱往,岂常守故哉!”(《大宗师》“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注)
社会也是在不断变动之中,人的需要同样是在不断变化之中。典制和道德适应一时,不可能适用于永久。向—郭《注》中说:“夫先王典礼,所以适时用也。时过而不弃,即为民妖,所以兴矫效之端也。”(《天运》“围于陈蔡之间……”注)
向—郭《注》中还说:“法圣人者,法其迹耳。夫迹者,已去之物,非应变之具也,奚足尚而执之哉!执成迹以御乎无方,无方至而迹滞矣。”(《胠箧》“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注)
社会随情况而变化,情况变了,典制和道德也应作相应的改变。如果不随之而变,就将扞格不入(“即为民妖”),变成人为的桎梏。新的典制和道德应运而生是自然的事。新的与旧的扞格不入,因为他们所处的时代变了。两者都是应时而生,因此不能说,一个比另一个就一定高明或不如。向、郭并不像老子、庄子那样一般地反对典制和道德,他们所反对的是在现实世界中已经过时、已经背乎自然的典制和道德。
有为与无为
向、郭就是这样,对先秦道家思想中的天、人、有为、无为都赋予了新的诠释。在社会情况变动中,新的典制和道德自然应时而生,在这时候,顺应天、顺应自然就要顺应新的典制道德,这就是“天”,就是无为。反对新的典制道德,极力维护旧的典制道德,这便是“人”,便是有为。向—郭《注》中有一段话:“夫高下相受,不可逆之流也;小大相群,不得已之势也;旷然无情,群知之府也。承百流之会,居师人之极者,奚为哉?任时世之知,委必然之事,付之天下而已。”(《大宗师》“以知为时者……”注)
一个人,在他的活动中让天赋的才能发挥出来,这在他就是无为。反之,就是有为。向—郭《注》中说:“夫善御者,将以尽其能也。尽能在于自任……若乃任驽骥之力,适迟疾之分,虽则足迹接乎八荒之表,而众马之性全矣。而惑者闻任马之性,乃谓放而不乘;闻无为之风,遂云行不如卧;何其往而不返哉!斯失乎庄生之旨远矣。”(《马蹄》“饥之渴之……”注)尽管向、郭作出这样的批评,就这些人对庄子的理解来说,其实错误并不十分严重。而向、郭两人的见解则确是十分有创见的。
向、郭对先秦道家的“纯素之道”思想也作了新的诠释。向—郭《注》中说:“苟以不亏为纯,则虽百行同举,万变参备,乃至纯也;苟以不杂为素,则虽龙章凤姿,倩乎有非常之观,乃至素也。若不能保其自然之质而杂乎外饰,则虽犬羊之鞟,庸得谓之纯素哉!”(《刻意》“故素也者……”注)
知识与模仿
老、庄都反对通常被社会推崇为圣人的那种人。在先秦道家著述中,“圣人”这个词有两重含义,一重含义是道家推崇的真人,另一重含义是拥有各种知识的饱学之士。老子和庄子都蔑视知识,因此也蔑视那些饱学之士。但是,从下面所述,向、郭并不反对有些人成为圣人;他们所反对的是有些人力图模仿圣人。柏拉图就是柏拉图,庄子就是庄子。他们质朴纯真,他们的天才是龙章凤姿,天质自然。柏拉图写《理想国》,庄子写《逍遥游》,都是一片冰心,直道而行,只是顺乎自己的天性。
这个看法可以举向—郭《注》下列一段话为证:“故知之为名,生于失当而灭于冥极。冥极者,任其至分而无毫铢之加。是故虽负万钧,苟当其所能,则忽然不知重之在身。”(《养生主》“而知也无涯……”注)这是说,知识聪明的由来是由于人的欲求超过了人的才智所能。如果人在自己的才智范围之内行事,也就无需知识聪明了。人只要按自己的天生才智行事为人,志无盈求,事毋过用。如果能够力负万钧,他这样负重,也不会觉得力不能胜;一个人如果能日理万机,他这样做时也不会叫苦连天。如果这样来理解知识聪明,则柏拉图和庄子都不算是有任何知识聪明的人了。
照向、郭的看法,唯有东施效颦的人才需要知识聪明。向、郭把模仿看为谬误,大概有三个原因。其一是它无用,在向—郭《注》中他们写道:“当古之事,已灭于古矣,虽或传之,岂能使古在今哉!古不在今,今事已变,故绝学任性,与时变化而后至焉。”(《天道》“古之人与其不可传也死矣……”注)在道家看来,“学”就是模仿。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古代的事情已经不复存在,虽然载入了史籍,却不能使它们在今日再现。古今不同,今世已变,只能抛弃恋古、仿古的念头,按照人的本性,与时代同变,才能臻于完善。万物都流动,人们每天都遇到新问题、新情况,感到新需要。对付新情况、新问题和新需要,要采取新的方法。即使在同一个时候,不同人的处境、情况和问题也有所不同,解决问题的方法也不可能尽同。一个人如果只知一味模仿,那有什么用?
其次,模仿是徒劳的。向—郭《注》里有一段说:“有情于为离、旷而弗能也,然离、旷以无情而聪明矣;有情于为贤圣而弗能也,然贤圣以无情而贤圣矣。岂直贤圣绝远而离、旷难慕哉?虽下愚聋瞽及鸡鸣狗吠,岂有情于为之,亦终不能也。”(《德充符》“庄子曰:道与之貌……”注)离朱是古代传说中的“明目者”,师旷是春秋晋国的乐师。他们的特殊才能是天生的。其他人想成为离朱、师旷而不能,离朱、师旷并无心成为精工巧匠,却取得了成就。常人想当圣贤而不能,圣贤顺其本性而成为圣贤。如果说,模仿圣贤太远,模仿离、旷太难,常人想成为下愚聋瞽、成为鸡狗,也不可能。每个事物之成为它自己,是身不由己的,它想变为其他事物,是不可能的。
其三,模仿是有害的。向—郭《注》中还说:有些人“不能止乎本性,而求外无已。夫外不可求而求之,譬犹以圆学方,以鱼慕鸟耳。……此愈近彼,愈远实,学弥得而性弥失。”(《齐物论》“五者圆而几向方矣……”注)这是说,有些人不知足于自己的天赋,硬勉强自己做不可能达到的事情,如同一个圆形,要模仿成为方形,鱼要想成为飞鸟。他们的目标定得越高,自己走得越远;知识越多,戕贼本性也愈甚。
不仅如此,“爱生有分,而以所贵引之,则性命丧矣。若乃毁其所贵,弃彼任我,则聪明各全,人含其真也。”(《胠箧》“擢乱六律……”注)事物的本性都有它的局限性。人如果力图超越本性,结果就将丧失本性;只有不顾外面的引诱,顺乎自己的本性,才能保持自己内心的完整。一意模仿别人,不仅不可能成功,还陷入丧失自己的危险。这是刻意模仿带来的危险。
这表明,模仿不仅无用,毫无结果,还将戕贼自己。因此,人的唯一明智的生活方式是“弃彼任我”,这便是在生活中实践“无为”。
齐万物
如果一个人能够真正“任我”地生活,不顾外来的压力或引诱,这意味着他已经能够祛除向、郭在《齐物论》注中所说的“偏尚之累”,时刻苦于选此舍彼的烦恼。这也就是说,他已经能够从一个超越的观点,看到万物在本质上并无差别,已经登上“无差别”、“混沌一体”的康庄大道了。
在《齐物论》里,庄子强调事物本质上并无差别的理论观点,其中又特别强调:像儒墨两家那样是己非彼并无意义。向、郭在《庄子注》书中对此也特别着力。对庄子所说“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向—郭《注》说:“将明无是无非,莫若反复相喻。反复相喻,则彼之与我,既同于自是,又均于相非。均于相非,则天下无是;同于自是,则天下无非。”能够最好地表明事物的是非本无区别,便是把事物拿来比较。这样做时,人们就会发现:所有事物的共同之处就在于都以自己为是,而以别的事物为非。既然它们都确定地认为,一切其他事物都不对,那就是说,天下没有一样东西是对的;既然它们都确定地认为自己是对的,那就表明,世上没有错的东西。
向—郭《注》又说:“何以明其然邪?是若果是,则天下不得复有非之者也。非若果非,则天下亦不得复有是之者也。今是非无主,纷然淆乱,明此区区者各信其偏见而同于一致耳。仰视俯察,莫不皆然。是以至人知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故浩然大宁,而天地万物各当其分,同于自得,而无是无非也。”这是说,如果自认为“对”的果真绝对正确,则世上便没有“不对”的东西了;如果被指为“错”的东西果真都错,则世上也就没有能自认为“对”的东西了。事实是,在事物的是非上难以确定,分辨是非的界限陷于混乱,这表明,是非之分,无非是一种偏执之见,而在偏执这一点上,万物倒是一致的。仰观俯察,到处都如此。至人有鉴于此,从中知道天地如同一指,万物如同一马,因而得以心平气和。懂得齐万物,万物都顺性“任我”,就都怡然自得了。
终极的自由与快乐
如果人能够超越事物之间的差别,就能够享受像《庄子》第一篇《逍遥游》中提出的绝对自由和绝对快乐。在《逍遥游》里,庄子讲了许多故事,其中提到大鹏、小鸟、蝉等等。朝生暮死的朝菌只有“小知”,千年古树(“大椿”)则有“大知”;小官僚才德有限,而列子则“御风而行”。对此,向—郭《注》说:“苟足于其性,则虽大鹏无以自贵于小鸟,小鸟无羡于天池,而荣愿有余矣。故小大虽殊,逍遥一也。”(《逍遥游》“蜩与学鸠笑之曰……”注)
但这种快乐只是相对的快乐。如果万物只是在自身有限的领域中自得其乐,它们的乐也只是极其有限的。针对这一点,庄子在《逍遥游》的故事里提出了一个独立的人(大鹏),超越有限而融入无限,享受到无限所给予的绝对快乐。他因超越了有限、融入无限而“无我”。他顺乎万物本性,与万物一起得其所哉,因此,在世人眼中,他“一无所成”。他与道成为一体,道无名,依同样的道理,至人也无名。
向、郭在《庄子注》里,把这思想发挥得淋漓尽致:“物各有性,性各有极,皆如年知……历举年知之大小,各信其一方,未有足以相倾者也。”这是说,事物各有其性,事物本性又各有局限。事物之间的差别往往只是数量上的差别,例如大知和小知,长寿和短寿,改变不了人的知识有限、生命有限这个本质。庄子在列举这方面的许多例证之后,举出了他心目中的独立的人,既忘记了自己,又忘记了和自己对立的一方,因此达到了“无差别”境界。因此,万物在各自的范围内自得其乐。独立无待的人既无功,也无名,向—郭《注》中说:“是故统小大者,无小无大者也;苟有乎大小,则虽大鹏之与斥,宰官之与御风,同为累物耳。齐死生者,无死无生者也;苟有乎死生,则虽大椿之与蟪蛄,彭祖之与朝菌,均于短折耳。故游于无小无大者,无穷者也;冥乎不死不生者,无极者也。若夫逍遥而系于有方,则虽放之使游而有所穷矣,未能无待也。”(《逍遥游》“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注)
庄子在《逍遥游》中描写独立无待的人有如“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向—郭《注》说:“天地者,万物之总名也。天地以万物为体,而万物必以自然为正,自然者,不为而自然者也。故大鹏之能高,斥之能下,椿木之能长,朝菌之能短,凡此皆自然之所能,非为之所能也。不为而自能,所以为正也。故乘天地之正者,即是顺万物之性也;御六气之辩者,即是游变化之涂也;如斯以往,则何往而有穷哉!所遇斯乘,又将恶乎待哉!此乃至德之人玄同彼我者之逍遥也。苟有待焉,则虽列子之轻妙,犹不能以无风而行,故必得其所待,然后逍遥耳,而况大鹏乎!夫唯与物冥而循大变者,为能无待而常通,岂独自通而已哉!又顺有待者,使不失其所待,所待不失,则同于大通矣。”在这里,“通”就是自由。
在向、郭的思想里,“道”即是“无”,“天”或“天地”成为他们最重要的思想。“天”是万物的总称,因此也就是万物的整体,从“天”的观点看万物,把自身融入“天”,就是超越万物和万物的差别性,或如新道家所说:“超乎形象。”
因此,向秀和郭象不仅对先秦道家的思想作了重要的修正,还把庄子在思想上的暗示用具体透彻的语言表达出来。如果有人觉得,任何话语都不宜说得太透,暗示比明确更堪玩味,就会同意从前一个禅宗僧人所说:“曾见郭象注庄子,识者云:却是庄子注郭象。”(请参阅本书第一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