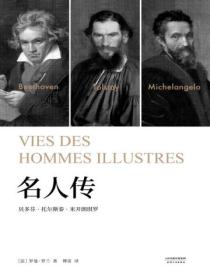注释03
[434]保尔·比鲁科夫最近在德译本中发表一部托尔斯泰与他的女儿玛丽亚的通信。
[435]见一九一〇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费加罗》日报,这封信,在他死后,由他们的女婿奥博连斯基亲王交给托尔斯泰伯爵夫人。这是数年之前,托氏把这封信付托给女婿的。这封信之外更附有另一封信,涉及他们夫妇生活的私事的。此信为托尔斯泰伯爵夫人阅后毁去。(见托尔斯泰的长女塔佳娜·苏霍京夫人的叙述)
[436]这种痛苦的情况自一八八一年,即在莫斯科所度的那个冬天起即已开始,那时候即托尔斯泰初次发现社会惨状。
[437]在托尔斯泰的最后几年,尤其在最后几个月中,他似乎受着弗拉季米尔-格雷戈里奇·切尔特科夫的影响。这是一个忠诚的朋友,久居英国,出资刊行并流通托尔斯泰的著作。他曾受到托尔斯泰一个儿子,名叫列夫的攻击。但即是他的思想的固执不无可议之处,可没有人能够怀疑他的绝对的忠诚。有人说托尔斯泰在遗嘱中丝毫没有把他的著作权赠给他的妻子的,这种无情的举动,是受着这位朋友的感应;但究竟我们无从证实,所能确实知道的,是他对于托尔斯泰的荣名比着托氏本人更为关心。自一九一〇年六月二十三日起到托氏逝世间的六个月中的情况,托尔斯泰的最后一个秘书瓦连京·布尔加科夫知道得最清楚,他的日记便是这时期托氏生活的最忠实的记录。
[438]一九一〇年十月二十八日的清晨五时许,托尔斯泰突然离开了亚斯纳亚·波利亚纳。他由马科维茨基医生陪随着;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为切尔特科夫称为“他的亲切的合作者”的,知道他动身的秘密。当日晚六时,他到达奥普塔修院,俄国最著名的修院之一,他以前曾经到过好几次。他在此宿了一晚,翌晨,他写了一篇论死刑的长文。在十月二十九日晚上,他到他的姊妹玛亚丽出家的沙莫尔金诺修院。他和她一同晚餐,他告诉她他欲在奥普塔修院中度他的余年,“可以做任何低下的工作,唯一的条件是人家不强迫他到教堂里去”。他留宿在沙莫尔金诺,翌日清晨,他在邻近的村落中散步了一回,他又想在那里租一个住处,下午再去看他的姊妹。五时,他的女儿亚历山德拉不凑巧地赶来了。无疑的,她是来通知他说他走后,人家已开始在寻访他了:他们在夜里立刻动身。托尔斯泰,亚历山德拉,马科维茨基向着克谢尔斯克车站出发,也许是要从此走入南方各省,再到巴尔干,布尔加列,塞尔别各地的斯拉夫民族居留地。途中,托尔斯泰在阿斯塔波沃站上病倒了,不得不在那里卧床休养。他便在那里去世了。——关于他最后几天的情景,在《托尔斯泰的出走与去世》(柏林,一九二五年版)中可以找到最完全的记载,作者勒内·菲洛埃普-米勒与弗里德里希·埃克施泰因搜集托尔斯泰的夫人,女儿,医生,及在场的友人的记载,和政府秘密文件中的记载。这最后一部分,一九一七年时被苏维埃政府发现,暴露了当时不少的阴谋,政府与教会包围着垂死的老人,想逼他取消他以前对于教会的攻击而表示翻悔。政府,尤其是俄皇个人,极力威逼神圣宗教会议要他办到这件事。但结果是完全失败。这批文件亦证明了政府的烦虑。列下省总督,奥博连斯基亲王,莫斯科宪兵总监洛夫将军间的警务通讯,对于在阿斯塔波沃发生的事故每小时都有报告,下了最严重的命令守护车站。使护丧的人完全与外间隔绝。这是因为最高的当局深恐托氏之死会引起俄罗斯政治大示威运动之故。——托尔斯泰与世长辞的那所屋子周围,拥满了警察,间谍,新闻记者,与电影摄影师,窥伺着托尔斯泰伯爵夫人对于垂死者所表示的爱情、痛苦与忏悔。
[439]见一八七九年十月二十八日《日记》。那一页是最美丽的一页,我们把它转录于下:“在这个世界上有没有翅翼的笨重的人。他们在下层,骚扰着。他们中间亦有极强的,如拿破仑。他们在人间留下可怕的痕迹,播下不和的种子。——有让他的翅翼推动的人,慢慢地向前,翱翔着,如僧侣。——有轻浮的人,极容易上升而下坠,如那些好心的理想家。——有具有强大的翅翼的人……——有天国的人,为了人间的爱,藏起翅翼而降到地上,教人飞翔。以后,当他们不再成为必要时,他们称为‘基督’。”
[440]“一个人只有在醉于生命的时候方能生活。”(《忏悔录》一八七九年)“我为了人生而癫狂……这是夏天,美妙的夏天。今年,我奋斗了长久;但自然的美把我征服了。我感着生的乐趣。”(一八八〇年七月致费特书)这几行正在他为了宗教而狂乱的时候写的。
[441]一八六五年十月《日记》:“死的念头……”“我愿,我爱永生。”
[442]“我对于愤怒感到陶醉,我爱它,当我感到时我且刺激它,因为它于我是一种镇静的方法,使我,至少在若干时内,具有非常的弹性、精力与火焰,使我在精神上肉体上都能有所作为。”(见《涅赫留多夫亲王日记》一八五七年)
[443]他为了一八九一年在伦敦举行的世界和平会议所写的关于战争的论文,是对于一般相信仲裁主义的和平主义者的一个尖锐的讥刺:“这无异于把一粒谷放在鸟的尾巴上而捕获它的故事。要捕获它是那么容易的事。和人们谈着什么仲裁与国家容许的裁军实在是开玩笑。这一切真是些无谓的空谈!当然,各国政府会承认:那些好使徒!他们明明知道这决不能阻止他们在欢喜的时候驱使千百万的生灵去相杀。”(见《天国在我们内心》第六章)
[444]自然一向是托尔斯泰的“最好的朋友”,好似他自己所说的一样:“一个朋友,这很好;但他将死,他要到什么地方去,我们不能跟随他。至于自然,我们和它的关系是那么密切,不啻是买来的,承继得来的,这当然更好。我的自然是冷酷的,累赘的;但这是一个终身的朋友;当一个人死后,他便进到自然中去。”(致费特书,一八六一年五月十九日)他参与自然的生命,他在春天再生,(“三月四日是我工作最好的月份,”——一八七七年三月二十三日致费特书,)他到了暮秋开始沉闷。(“这于我是死的一季,我不思想,不写,我舒服地感到自己蠢然。”——一八六九年十月二十一日致费特书)
[445]见和保尔·布瓦耶的谈话。(一九〇一年八月二十八日巴黎《时报》)实在,人们时常会分不清楚,例如卢梭的朱莉(译注:朱莉是卢梭著《新爱洛伊丝》小说中的女主人翁)在临终时的说话:“凡我所不能相信的,我不能说我相信,我永远说我所相信的。属于我的,唯此而已。”和托尔斯泰《答圣西诺德书》中的:“我的信仰使人厌恶或阻碍别人,这是可能的。但要更改它却不在我能力范围以内,好似我不能更变我的肉体一样。我除了我所相信的以外不能相信别的,尤其在这个我将回到我所从来的神那边去的时候。”或卢梭的《答特博蒙书》似乎完全出自托尔斯泰的手笔:“我是耶稣基督的信徒。我主告我凡是爱他的同胞的人已经完成了律令。”或如:星期日的全部祷文又以归纳在下列这几个字中:“愿你的意志实现!”(卢梭《山中杂书》第三)与下面一段相比:“我把主祷文代替了一切祷文。我所能向上帝祈求的在下列一句中表现得最完满了:‘愿你的意志实现!’”(一八五二——一八五三年间在高加索时代的《日记》)两人思想的肖似不独在宗教方面为然,即在艺术方面亦是如此。卢梭有言:“现代艺术的第一条规则,是说得明明白白,准确地表出他的思想。”托尔斯泰说:“你爱怎么想便怎么想罢,只要你的每一个字都能为大家懂得。在完全通畅明白的文字中决不会写出不好的东西。”此外我亦说过,卢梭在《新爱洛伊丝》中对于巴黎歌剧院的讽刺的描写,和托尔斯泰在《艺术论》中的批评极有关联。
[446]“真理……在我道德观念中唯一存留的东西,我将崇拜的唯一的对象。”(一八六〇年十月十七日)
[447]“纯粹的爱人类之情是心灵的天然状态,而我们竟没有注意到。”(当他在卡赞当学生时代的《日记》)
[448]“真理会导向爱情……”(《忏悔录》一八七九至一八八一年)“我把真理放在爱的一个单位上……”(同前)
[449]“你永远在提及力量?但力的基础是爱。”(见《安娜小史》第二卷安娜的话)
[450]“美与爱,生存的两大意义。”(《战争与和平》第二卷)
[451]“我信上帝,上帝于我即是‘爱’。”(一九〇一年《答圣西诺德书》)“是的,爱!……不是自私的爱,但是我生平第一次感到的爱,当我看到,在我身旁的垂死的敌人,我爱他……这是灵魂的原素。爱他的邻人,爱他的敌人,爱大家,爱每个,这是在各方面去爱上帝!……爱一个我们亲爱的人,这是人的爱,但爱他的敌人简直是神明的爱!……”(这是《战争与和平》中安德烈临终时所说的话)
[452]“艺术家对于他的作品的爱是艺术的心灵。没有爱,没有艺术品。”(一八八九年九月书)
[453]“我写了这些书,所以我知道它们所能产生的罪过……”(一八九七年十一月二十一日,托尔斯泰致杜霍博尔人的领袖韦里金书)。
[454]参看《一个绅士的早晨》,——或在《忏悔录》中理想的描写,那些人是多么质朴,多么善良,满足自己的命运,安分守己,博得人生的意义,——或在《复活》第二编末,当涅赫留多夫遇见放工回来的工人时,眼前显出“这人类,这新世界”。
[455]“一个基督徒在精神上决不会比别人高或低;但他能在完满的道上,活动得更快,这便使他成为更纯粹的基督徒。因此,那些伪善者的停滞不进的德行较之和基督同时钉死的强盗更少基督教意味,因为这些强盗的心魂,永远向着理想而活动,且他们在十字架上也已后悔了。”(见《残忍的乐趣》)
[456]托尔斯泰写道,“其中一部分是我亲历的。”
[457]这种精神上的健康,有他的朋友切尔特科夫与他最后病倒时的医生的叙述为证。差不多直到最后,他每天继续写或读出他的日记令人笔录。
[458]比鲁科夫在他的书末,把托尔斯泰浏览与参考的关于东方的书籍作了一张表。
[459]似乎一部分中国人也承认这类似性。往中国旅行的一个俄国人,于一九二二年时说中国的无政府主义充满了托氏的思想,而他们的共同的先驱者却是老子。
[460]经查此人为钱玄同(1887— 1939),原名钱夏,字德潜。中国现代思想家、文学家、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编注)
[461]在致辜鸿铭书中,托尔斯泰猛烈地批评中国的传统教训,服从君主这信念:他认为这和强力是神明的权利一语同样无根据。
[462]阿部畏三,《平民报》经理。在托尔斯泰的复信寄到之前,他们已下狱,报纸也被封了。
[463]一九〇六年十月三日,德富写信给他道:“你不是孤独的,大师,你可**了!你在此有许多思想上的孩子……”
[464]德富记得一九〇六年时托尔斯泰问他道:“你知道我的年纪么?”“七十八岁。”我回答。“不,二十八岁。”我思索了一会说道:“啊!是的,从你成为新人的那天算起。”他颔首称是。
[465]托尔斯泰极佩服穆罕默德关于贫穷的祈祷:“吾主,使我在贫穷中生存,在贫穷中死去!”
[466]此系印度的苦修士。(译注)
[467]除了极少的例外,如马克斯·缪勒那大思想家,心地宏伟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