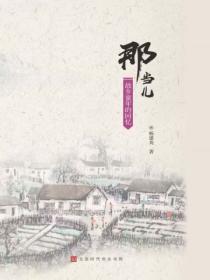序一 乡愁:游子的精神“容器” ——读杨建英散文集《那当儿》[1]
纪红建[2]
收到建英[3]从新疆阿勒泰发来的散文集《那当儿》电子稿时,我正准备前往地处祖国北疆的大兴安岭采访。于是,我带上《那当儿》出发了,白天在原始森林里穿梭采访,晚上在整理好采访笔记后,便是读建英的《那当儿》。很快,他的文字,他呈现出的记忆中的故乡场景,他所构建的精神世界,深深地吸引了我,打动着我的心灵,温暖着我的心灵。这种难以割舍、刻骨铭心的乡愁,是他,也是我们的精神“容器”。
因为新疆与湖南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并于十年前达成“加强文学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两地文学发展繁荣”的意向,湖南省作家协会在毛泽东文学院每年举办一期新疆作家班,也因为我在文学院工作的缘故,七年前的金秋时节,我与建英相识于岳麓山下。当时,建英在毛泽东文学院第三期新疆作家班学习。在随后的交往中,阳光帅气、温和内敛、宽容厚重的建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名优秀的散文家,我们聊得最多的是散文,但偶尔他也会聊到他的故乡北京。每当他说到故乡时,我总是洗耳恭听。那里也是我的第二故乡,我曾在那里当兵十多年,在我脑海中存下了许多挥之不去的记忆。虽然湖南到新疆相距数千公里,但这并没有隔断我们的深入交流。我们互相关注对方的创作动态,互相鼓励。偶尔他还会发来新近创作的散文,如《村上椿树》《拾荒者传奇》《听鬼故事长大》《暖冬》《湘西杂记》等,让我对他的散文创作、对他的乡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但还不够系统与深刻。无疑,《那当儿》让我对建英的散文创作,对他的乡愁,对他的精神世界,有了更加全面、立体、丰富的了解。
《那当儿》让我感受到了建英那颗纯粹的热爱文学的心。集子分“流年碎影”“柔软时光”“乡村浅唱”“树熟流芳”“金色流年”“岁月诗章”“乡村物语”七辑,无论何辑的内容,均无造作、刻意为之,感受到的全是他对乡愁,对生活自然、真情的表达。尽管文字中建英充当的不是政治和道德裁判者,不是伤痛的抚摸者与控诉者,只是一个记忆中的或者已经发生变化后故乡乡村的见证者与呈现者,但我总能深深感受到他内心自然汹涌的情感力量。他向我们呈现的大马村的乡村物语,包括《土炕》《小卖部》《村上椿树》《大马村纪事》《听鬼故事长大》《姥姥家唱大戏》《盗花生 盗白薯》《歇后语 俏皮话》《七月枣》《八月梨》《九月柿子红了皮》《肥年》《年夜饭》《致老师》《致同学》《乡村物语》等,见人见事见物,有动态也有静态,显然是一个北京西南城郊原生态的古朴村庄。透过纯粹而洁净的文字,我看到了一个游子内心深处对故乡的思念之情,也看到了他那颗纯粹的热爱文学的心,这颗心正如他笔下的大马村般原生态。正如他所说,“那年我从北京坐三天三夜火车到乌鲁木齐,又坐两天两夜汽车到阿勒泰,真有到天边儿的感觉”,于是这里成了安放他文学梦想的地方。从那一刻开始,故乡注定成为他文学表达的重要部分。
《那当儿》展现了建英朴素而精练的散文叙事能力。他的语言,他的叙事,他的故事,无一不将我深深吸引。尤其令人感叹的是他的语言,质朴得精致,精致得质朴,自然而洒脱,虽然离开故乡三十多年了,但文中依然散发着淡淡的京味儿。在《土炕》中他这样描述道:“这种炉子很低,离地只有两块砖高,俗称‘地蹦子’。它是在地下挖一个深坑把炉子砌进去的。这个坑俗称‘炉灰坑’。这种炉子炉膛很大,炉口极小,所谓‘里面蹲条狗,上面伸只手’。炉子与炕相连,形成炉洞。连接处用一块砖:抽出来,烧坑;推进去,做饭。炉内安放一个小瓦缸,放满水,借着炉火热力形成一个‘土过水热’。”这样朴实而凝练的描述在作品中无处不在,对事物的描述细致入微,不急不慢,舒缓自如,节奏把握得非常到位,既打动人心,又真实可信,还引人沉思。大马村的一切事物在他的笔下逐一登场,奶奶、母亲、老师、同学、石匠,麦田、大场、椿树、麻雀、碾子、磨子、麦秸垛、小卖部,枣儿、梨子、柿子、白薯、老咸菜、炸酱面、麻酱面、打卤面、年夜饭,丰收、肥年、守岁、打猎、劁猪、起名、像蛋、懈松、唱大戏、瞎晃**、盗花生、盗白薯、歇后语、俏皮话、听鬼故事、回家吃饭等,共同支撑起一个朴实而又鲜活的村庄。
《那当儿》构建了一个留下乡愁的精神“容器”。对于故乡一切事物的描写,建英都是那么信手拈来,自然而又真情地表达着。这种功夫,既得益于他良好的文学修养、语言叙事能力,也源于他对故乡的人及往事的无限眷念。正是他对故乡这种纯洁的情感,为我们呈现出故乡的淳朴和温暖。从文中也不难看出,故乡任何一个印记,都会引起他的种种心绪,泛起熟悉而特有的乡味儿。对于故乡,不是几篇文章或是一部作品能够表达清的,有说不完的话,道不尽的情。正如建英在文中所说:“有关大马村的话题还有很多很多,可越写越觉得许多重要的都没写,而写出来的又都不满意,这真把我折磨得心力交瘁,痛苦得像草一样不能自拔。”“我心里还是空落落的,觉得还远没有写出我心中的这个村庄的皮毛。就是说,根本没有触碰到筋骨,探索到精髓,心里还有一大堆东西没写。可糟糕的是,又根本写不出来了。”这是他自谦的表达,更是他对故乡的无限眷念。文中无处不表达着他对故乡的思念,同时也描述了他离乡后故乡所发生的巨大变化,这是对现实的深刻关照,更是对其精神“容器”的升华。对于这点,建英有深刻的认识:“我如果想不清楚当年老人老物老事在今天生活中的投影和影响,寻找不到这些过往在今天现实生活中的意义,就根本下不了笔。说句冠冕堂皇的话就是:历史照不进现实,那,写它何用?”我想,这便是建英创作《那当儿》的初衷吧。
总之,建英的散文集《那当儿》是一本内容丰富、情感饱满、朴实无华,散发着浓郁生活气息,对故乡深情回望的佳作。那充满温度的文字,让我们有更高更远的期望;那发自内心深切的情感,令我们回味无穷。
[1] 《那当儿》是本书《那当儿:故乡童年的回忆》的简称。
[2] 纪红建,著名作家,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
[3] 建英,即本书作者杨建英,下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