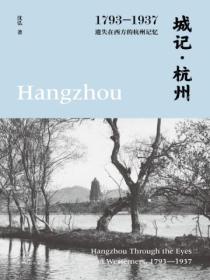1917—1919 甘博镜头中的杭州
在1949年以前,曾经有众多的外国人拍摄过杭州和西湖的照片。在这些对杭州情有独钟的外国人当中,有的长期在杭州城里居住,把这个拥有西湖美景的“人间天堂”视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如慕雅德(Arthur Evans Moule)、梅藤更(David Duncun Main)和费佩德(Robert Ferris Fitch)等人,有的则是萍水相逢,来杭州短期工作、考察、访问、旅游、报道和拍摄的外交家、学者、建筑师、记者、旅行家、摄影师和画家,如美国驻杭领事云飞得(Frederick D.Cloud)、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西德尼·甘博(Sidney Gamble)、德国建筑师柏石曼(Ernst Boerschmann)、美国旅行家盖洛(William Edgar Geil)、英国摄影师布列松(Robert Bresson)等人。在这些曾经给老杭州和西湖拍过照片的所有专业或业余的西方摄影师当中,西德尼·甘博可能是其中最具特色的一位。本文拟根据他于1917—1919年间在杭州拍摄的一组数量约为两百张左右的老照片,来讨论甘博根深蒂固的杭州-西湖情结,以及他在表现这个古老城市及其人文景观时所采用的别具一格的独特视角。
西德尼·甘博首次随父亲一起访问杭州是在1908年,当时他才刚刚18岁。他的家庭与这个古老的中国城市早就结下了不解之缘,因为他的父亲戴维·甘博(David Gamble),作为宝洁公司的创始人之一,是一位著名的美国实业家和慈善家,跟杭州的美国长老会传教使团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戴维带儿子西德尼首次前来杭州访问的那年,正逢美国北长老会创办的教会学校杭州育英书院酝酿在钱塘江边的秦望山山坡上购买地皮,以建立新校区,给学校升格和扩大办学规模。当时费佩德也是刚刚从宁波的一个美国北长老会学校调到杭州的育英书院任教,并被委任以监理新校区建设的重任。戴维·甘博出手不凡,毫不含糊地为育英书院计划中的新校区建设捐赠了一座大楼和修建浙江首个大型田径运动场。1918年,当费佩德去美国为之江学院的校园基础建设进行募捐时,戴维·甘博再次慷慨解囊,又捐出了在之江校区创建一个图书馆大楼及其配套藏书和设备的另一笔巨款。(1)
照片中的老人就是戴维·甘博
在首次访问杭州时,西德尼·甘博也跟之江大学未来的校长费佩德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虽然他俩之间存在着年龄的差距,出生于1873年的费佩德比甘博大了整整17岁,但是他俩具有共同的摄影爱好,都是对用照相机记录中国人文地理具有强烈兴趣的发烧友。西德尼于1917年6月和另一位名叫安尔吉(J.Hillcoat Arthur)的北长老会传教士摄影发烧友一起与费佩德在上海会合,共同参与了一个历时四个月之久的西藏摄影之行。这次极具冒险精神的摄影之旅虽然因为西藏边境发生僧侣暴乱被关闭而未能达到去拉萨的初衷,但是他们在沿途各地及川北地区的拍摄活动也留下了3500多张内容相当精彩的黑白照片。
由于家族与之江大学之间的渊源,以及自己与费佩德所结下的友谊,使得甘博数次来华旅居时曾经常来往于北京和杭州之间,尤其是1917和1919年这两次在杭州逗留期间,西德尼·甘博几乎走遍了杭州城的大街小巷和西湖的众多景点,拍下了数以百计表现杭州人文景观的照片。在如今收藏在美国杜克大学善本书、手稿和特藏图书馆中的近6000张西德尼·甘博中国老照片中,我们仍然能够看到他于1917—1919年间在杭州所拍摄的一组老照片,总数约有200多张。
西德尼·甘博夫妇,1919年。
甘博父亲捐赠的之江大学男生宿舍楼。戴维·甘博捐赠的这座楼最初是男生宿舍楼,因位于校园的东面,所以被称为东斋或“甘卜楼”。楼前不远的地方是一个悬崖,从那儿可以遥望下面的钱塘江和不远处的钱塘江大桥,以及对岸的风景。如今这座大楼依然存在,其外观也没有发生很大的变化,但是周围的环境已经完全改变。
甘博站在“甘卜楼”门前。这张照片是甘博本人站在“甘卜楼”大门前的留影。从照片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门的上方刻有“Gamble Hall”(甘卜楼)字样。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几个字早已在1950年代被抹去,门前的台阶也已经破旧不堪。饮水思源,今人应记得该楼捐赠人的姓名。
之江学院的主楼慎思堂
甘博父亲捐赠的之江大学运动场之二
从钱塘江上眺望之江大学的校园建筑。从六和塔再往西挪一下拍摄的角度,我们便清楚地看到了之江大学的校园及其校园建筑。校园内几个主要的建筑历历在目:前面三个大的建筑从左至右分别是西斋惠德堂(Wheeler and Dusenbury Hall)、主楼慎思堂(Severance Hall)和东斋甘卜堂(Gamble Hall)。第二排两个较小的建筑从左至右分别是中教习住宅楼(Chinese Teachers Residence)和西教习住宅楼(Converse Residence)。最上面那三个别墅从左至右分别是上红房(Southern Presbyterian Residence)、下红房(Rochester Residence)和灰房(North Pacific Residence)。
作为一名在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接受了正规学术训练的社会学家和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干事,甘博十分关注中国社会中普通老百姓的市井生活,曾经与北京基督教青年会和燕京大学的同事步济时(John Steward Burgess)合作,率先在北京城内开展过各种大型的社会调查,曾先后出版过《北京社会调查》(1921年)、《1900—1924年北京的物价、工资和生活标准》(1926年)、《两户中国家庭的家务账》(1931年)和《北京的中国家庭如何生活》(1933年)等多部社会学专著(2)。在利用照相机镜头来表现杭州这个古老城市上,甘博也具有自己独特的视角,跟他那位在杭州居住多年的挚友费佩德无论在内容,还是在表现手法上都有所不同。由于他们经常用不同的视觉来拍摄同一个事物或场所,所以他俩所拍摄的杭州和西湖老照片正好形成了有趣的对比。
就内容而言,甘博所拍摄1917—1919年间杭州和西湖老照片至少具有三个鲜明的特征。首先,他表现杭州之江大学和费佩德一家的老照片从当今的角度来看,已是弥足珍贵的历史文物。其次他对杭州古建筑,街道、运河、寺院、城门和学校等众多历史地标的兴趣和取景的手法在其照片中都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表现。第三,他对于各种中国传统手工业有着特别的兴趣,他的照片忠实地记录了如今可以被称之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许多手工业作坊和店铺的场景。
之江大学是中国近代史上传承最悠久的新式学校之一。从1845年美国北长老会传教士团在宁波创办崇实义塾开始,到1952年之江大学作为教会大学被强行解散,前后共经历了长达107年曲折复杂的发展过程。1867年,这个教会学校随北长老会差会一起从宁波迁到了杭州的上皮市巷,并改名为育英义塾。后来它又从皮市巷搬迁到了大塔儿巷,并于1893年改名为育英书院。接着,又于1910年,学校从位于城区中心的大塔儿巷搬迁到了钱塘江边秦望山麓的新校园,并改名为之江学院,直到1940年,又改名为之江大学。
长期以来,能反映之江学院早期校园景色和建筑的照片并不是很多,即使有一些,其清晰度都不高,而表现之江第四任校长费佩德及其家庭成员的老照片更是凤毛麟角。鉴于甘博跟之江大学和费佩德家庭的特殊关系,在他老照片收藏中出现这方面的照片并不令人惊奇,但是这些照片的数量之多,质量之好,仍令我们不禁眼睛为之一亮。根据统计,甘博所拍摄育英书院和之江学院校园的九张照片均属上乘,都是国内以前所没有见过的;二十余张表现费佩德及其家人的照片也非常罕见,尤其是费佩德拿着相机,正准备抓镜头拍照的那张快照使我们得知费佩德当时是使用什么样的相机,并且是以何种方式拍照的;而从费佩德位于杭州内城仁和路新居的三楼窗口遥拍西湖和湖滨风景的那五张照片则更是绝无仅有的摄影佳作。
甘博用照相机镜头来记录城市坐标的方式一般都比较独特。他善于选择那些具有鲜明特征的建筑物,而且由于他拍摄这些地方的时间相对较早,所以当我们如今来审视这些照片时,往往能够见到一些出乎我们想象的东西,即使是在那些现在依然能看到的景物上,也经常可以发现一些与现在已大相径庭的细节。
例如他所拍摄的一座城门的照片,其说明文字是“杭州西城门”,但是它的外观并不像英国女旅行家毕晓普夫人和美国驻杭州领事云飞得已经拍摄过的钱塘门,后者城楼底层只有三个方形的大窗,而甘博照片中的那个城楼底层却有八个圆拱形小窗;(3)从城门外的地形来看,它也不像民国初年一本名为《中国名胜》像册(4)中表现的涌金门,因为后者临湖,而且在甘博来杭州之前就应该已被拆毁,所以它几乎可以肯定是作为杭州三座西城门之一的清波门。
从费佩德家三楼眺望湖滨和葛岭之一。从甘博的照片来看,1919年的杭州西湖湖滨已经建起了一些西式洋房,但是它们并没有破坏城市的整体建筑风格,而且它们还是能够跟周边的中式建筑和谐相处,在树木的映衬下,跟西湖风景融为一体。但是如今湖滨有一些新建的高楼,不仅跟周边的环境极不协调,而且其本身的美观程度也很成问题。
从费佩德家三楼眺望湖滨和葛岭之二。甘博1919年访问杭州时,费佩德在杭州仁和路11号的新居刚刚落成。这是一座三层的中西合璧式的洋楼,从三楼朝西的窗户望出去,西湖风景一览无余。因为当时的湖滨并没有高房子,费佩德的三层楼就已经算是鹤立鸡群了。甘博在这个位置上拍摄了两张眺望西湖的照片,显然是用了望远镜头,因此把湖滨的那些房子距离拉得很近,可以看得比较清楚。这张照片跟下面那张的角度略有不同,如果用作图软件将它们拼接起来的话,可以组成一幅广角的湖滨写真图。
从费佩德家三楼眺望湖滨和葛岭之三。这是从杭州仁和路11号费佩德的寓所三楼朝西窗口拍摄的湖滨和西湖。在照片的下方可以看到费佩德寓所砖砌的坚固围墙,与附近一道用土夯成的土墙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湖滨目力所及的范围内有好几个大房子显然是旅馆,其中位于平海路上的一个屋顶有露台的西式洋房还挂着“清华旅馆”的招牌。湖滨一个白墙的大房子屋顶还飘扬着三色国旗。
从城隍山上鸟瞰杭州城。从照片上看,当时杭州城里的房屋建筑风格相对比较统一,均是白墙黑瓦的院落宅第。偶尔有一些西式的建筑,也没有破坏城市的整体建筑风格。这张照片是在城隍山上从南往北拍摄的,图中的建筑大多是大街清河坊一带的房屋。
他所拍摄的的拱宸桥外观大致上跟现在并无多大改变,其基本结构都已经保存下来了。但假如仔细观察的话,就可以看到1917年的拱宸桥与如今那座桥相比,还是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例如当时的桥上建有很高的扶手栏杆,以保证人们不会失足掉进河里;桥上还建有电线杆或电报线杆;在桥顶甚至还有一个岗亭,由此可见当时那儿还有警察看守。桥两端的建筑都很高,而且距离桥很近。所有这些细节都跟现在重修后的拱宸桥有较大的区别。
甘博对于中外文化交流的那段历史非常感兴趣,所以他在杭州期间曾专门前往留下镇的老东岳大方井,去拜谒和拍摄了那儿金尼阁、卫匡国等人的“天主圣教修士之墓”,从而为这个浙江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留下了十分珍贵的历史影像资料。从他拍摄的老照片来判断,这个早期耶稣会士的坟墓之中应该放置有十三位耶稣会士的骨灰瓮,但在“文革”之后重修的“卫匡国墓”中,我们现在只能够看到十二个骨灰瓮。(5)如果我们能够根据史料对此加以详细的考证,说不定就能够发掘出一段不为人所知的历史故事。不仅如此,现在的陵墓和骨灰瓮的形状跟以前的都不相同,估计重修这个陵墓的人并未见过相关的老照片。
毋容置疑,甘博杭州老照片对于杭州市园林和文物部门具有极为重要的参考价值。从他所拍摄的“碧血丹心”牌坊那张照片来看,当时这座古老的牌坊显然同时具有纪念表彰民族英雄岳飞和标示引导岳庙的功能。令人费解的是,杭州市园文局当时在重建这一牌坊时,完全无视上述功能,竟然在牌坊与岳庙之间建造了一个花坛,从而挡住了从牌坊处看岳庙的视线,把两者人为地割裂了开来。这一做法显然违背了当年修建牌坊和岳庙时的空间逻辑,以及保护历史文化遗产须“修旧如旧”的公认原则。
京杭大运河上的拱宸桥。这张照片中的桥估计大家都还能够辨认出来,它就是鼎鼎大名的拱宸桥。它的外观大致上并未改变,其基本结构现在都已经保存下来了。但假如仔细观察的话,就可以看到1917年的拱宸桥跟现在还有很多不同的地方,例如:当时的桥上建有很高的扶手栏杆,以保证人们不会失足掉进河里;桥上还建有电线杆或电报线杆;在桥顶甚至还有一个岗亭,由此可见当时那儿有警察看守。桥两端的建筑都很高,而且距离桥很近。所有这些细节都跟现在重修后的拱宸桥有较大的区别。
从西泠桥桥洞遥望保俶塔。西泠桥是从孤山去岳坟或北山街的必经之地,它的北端就是闻名遐迩的名妓苏小小之墓,而西泠桥本身也是西湖上一座著名的古桥。当年甘博在拍摄这座桥的时候,选择了一个绝佳的角度,使该桥半圆形的桥洞与它在湖面上的倒影形成了一个圆圈。而从这个圆圈望进去,则可以看见后面宝石山上的保俶塔和山脚的大佛寺。
杭州东河上的太平桥。太平桥连接双眼井巷,是杭州东河上最大的一座桥,它位于连接凤起路的凤起桥以南和连接庆春路的菜市桥以北。与东河上的其他绝大多数单孔桥不同,它是一座三孔桥,这主要是因为东河在这一段的河面最宽。从远处看,它的形状跟京杭大运河上的拱宸桥十分相似,只是桥的比例要小多了。令人可惜的是,这座风格古朴、具有文物价值的的石拱桥在“文革”期间的1971年竟被当时的革命委员会下令拆毁,改建成了一座以钢筋混凝土为桥基的廊桥。从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东河上一条客船的式样。桥南的河西边停泊着好几条船,而桥北的河东边有许多成捆的待运竹排。
杭州城内运河上的另一座石拱桥。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曾经宣称,在杭州城内的运河上共有12000座石拱桥,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但是旧时杭州城里水系纵横和桥梁密布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即使是在民国初年,城里的运河和石拱桥数量也要比现在多很多。照片中的这座桥便是当时众多石拱桥之一。虽然其所在位置和桥名现已难以考证,但从桥左端的民房、石栏杆上晾着的被子和桥上的电线杆来判断,它应该是城内运河上的一座桥。桥身坚固而美观,在桥洞的两边各有一根条石,上面刻有一副对联。石桥的南北两面各有一组石阶梯导向运河的水边,以供妇女到运河里洗衣、洗菜和淘米时行走。
杭州东河上的万安桥。民国初年杭州城里纵横交错的水道有不少,但主要的两条运河分别是中河和东河。由于位于城内,这两条运河上都有很多的桥。这张照片所表现的是东河上的万安桥。这是一座典型的江南石拱桥,桥上建有石栏杆。从桥洞下望过去,还能够看见不远处的另一座石拱桥,那就是淳佑桥,即现在的解放桥。笔者出生的大塔儿巷离这儿不算太远,小时候经常要走过这座万安桥,所以老照片中的场景能勾起许多儿时的回忆。
杭州“曲院风荷”南面的玉带桥。甘博照片中的这座玉带桥位于苏堤与曲院风荷之间的金沙堤上。这里原来只是一座小桥,清代时改为带有一座亭子的石桥。根据《湖山便览》中的描述,该桥“中设三洞酾水,上构飞亭,夹以朱栏,绕以花柳,晴波倒影,俨然长虹亘空,增修十八景目曰‘玉带晴虹’”。但是到了民国初年,桥上的亭子已经不复存在。1983年,玉带桥得以重建,恢复了往昔飞檐翘角、朱栏汉玉的原貌。
1919年的“天主圣教修士之墓”
2009年的“卫匡国墓”
1919年的“碧血丹心”牌坊
2009年的“碧血丹心”牌坊
老牌坊中段的细部
新牌坊中段的细部
从牌坊上的修饰图案来看,新修的“碧血丹心”牌坊也未能做到修旧如旧。从牌坊的中段部分来看,原来牌坊上雕刻着“二龙戏珠”“二凤戏麒麟”,以及二龙与三狮抢夺同一颗夜明珠等表示吉祥的典型中国民间传统图案;而在重修的牌坊上,我们再也看不到内涵如此丰富、形式如此多变的图案,取而代之的是相对比较单调的二龙戏珠和二麒麟戏珠的图案。同样的情形也可见于牌坊的顶部装饰图案。由于缺乏老照片作为客观比较和对照,重修的牌坊只能如鲁迅小说中九斤老太的口头禅那样,“一代不如一代”了。
除了上述对于修复文物的参考价值之外,甘博的杭州老照片对于我们了解民国初年杭州所发生的各种变化也有着珍贵的参考价值。例如费佩德和甘博这两位好朋友对于杭州的一些景点具有共同的爱好,他们曾经在不同的年代拍摄过同一景点的照片,如果我们把这些照片放在一起加以对比,就可以发现这期间所发生的一些变化。例如费佩德曾在《教务杂志》第45卷、1914年的10月号上撰写题为“对于道教地狱的研究”的文章,(6)详细记述了杭州东岳庙内“阴曹地府”的情况,并且附上了一组摄于1913年的照片,作为文章的插图。甘博在六年后也来到了同一个地方拍摄了另一组照片。从甘博1919年的照片来看,这座道观的香火依然旺盛,尽管已经发生了一些明显的变化,如1913年时,黑白无常的头上是没有头发的;1919年的照片里无常的头上加了头发,左边那位无常帽子上原来的字“财见勿来”改为“你来了”。在这六年期间,这个阎罗殿显然已经得到了修缮,原来“牛头”身上已经破损的盔甲在1919年已经得到了修补。1913年时,阴曹地府里的塑像较少,而且比较破旧,1919年时,已经增加了不少人物和厉鬼的塑像,而且整个地方都已经变得焕然一新,就连原来的血污池现在也改变了模样。甘博不仅拍摄了阎罗殿内部的情景,而且也拍摄了它外部的模样,这就为我们研究这座杭州庙宇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甘博1917—1919杭州老照片中最重要的一组照片当数他在杭州最繁华的一条商业老街,即御街(俗称大街)上拍摄的一组表现街景和手工艺老作坊和店铺的照片。这组照片反映出他作为一名社会学家和一向关注民生、民俗的摄影师所表现出来的独特艺术眼光,因为在清末民初,我们几乎找不到另一位摄影师曾经拍摄过同样内容的照片。这也就是为什么杭州市政府在重修中山路这条“宋朝御街”时深感老照片等图像资料匮乏,以至于准备于2009年9月30日正式开街的这个跟杭州市政府西湖申遗休戚相关的重大工程迄今仍留下了众多遗憾的关键所在。
从甘博所拍摄的这组御街老照片来看,清末民初的大街是杭州的商业中心,熙熙攘攘,店铺云集,其街景跟现在重修后的中山路的样子大相径庭。最大的差异就在于当时的街道十分狭窄,由于街道两边店铺的招牌和门面不断地蚕食街道,造成了用石板铺就的路面上最狭窄处就连两辆黄包车交会都有点困难。其次,当时的御街是按照“坊”来分段的,例如现在北起庆春路、南至鼓楼的中山中路这一段被划分为弻教坊、里仁坊、寿安坊、积善坊、三元坊、保佑坊、甘泽坊、太平坊、清河坊。每个坊之间都筑有一座砖砌圆拱门的高墙,拱门上方刻有坊名,门下则装有木栅门。每天深夜,木栅门会被关上,更夫则敲着梆子,在坊内来回巡逻,以确保社区的平安。1928年,御街上开修马路,街道随之被拓宽,各坊之间的所有公墙均被拆毁。如今重修的中山路不见了这些公用的坊墙,其标榜的“古色古香”自然是大打折扣。
杭州灵隐的冷泉亭。杭州灵隐的冷泉亭,因其历史悠久和跟众多的文人逸事相关,是人们争相拍摄的一个景点。甘博这张照片摄于1919年10月。
杭州福星观的道士。福星观的道士们崇尚天人合一的生活方式,每天清晨的卯时(5—7点),道士要诵读《功课经》的早课,此时正值东方日出,阳气上升,在玉皇山顶可以吸入清新的空气;傍晚的酉时(17—19点)还要念《功课经》的晚课,此时呼出浊气,既可消灾解厄,又有益于健康。道士们还要每天练习气功和太极拳,以修身养性。另外,琴棋书画也是道士们业余时间最常见的陶冶情操方式。
杭州灵隐回龙桥上的春淙亭
杭州灵隐寺领诵佛经的和尚之一。灵隐寺的和尚在念经或做水陆道场的时候,通常有住持或资深的僧人做领诵者。甘博拍摄的灵隐寺的照片中就有两张是专门表现领诵者的。这两位领诵者分别坐在大雄宝殿“三世如来”像左右两端搭起来的一个木制台上,他们的桌前有用绸缎装饰起来的一个门面,上面饰有龙凤、蝙蝠等表示吉祥的图案。这张照片所表现的是坐在右端的那位领诵者,他身穿袈裟,光着头,面前摆有已经展开的经卷,似乎正在念经。他的前面点着一支香,两边的玻璃灯罩里点着蜡烛,旁边有一只倒扣着的茶碗。
杭州灵隐寺领诵佛经的和尚之二。这张照片所表现的是坐在“三世如来”左端的那位领诵者。他也身穿袈裟,但是跟前面那位领诵者不同的是,他头上戴着风帽,捂得严严实实的,脸上还架着一副老式眼镜,似乎是近视眼。他的前面也点着一支香,左右分别点着一根蜡烛,桌上也倒扣着一只茶碗。
杭州福星观的香炉和前院。杭州的福星观是一个具有千年历史的道观,位于玉皇山的山顶,是人们每年正月初八给玉皇大帝祝寿的地方。它与葛岭南面山腰中的“抱朴道院”和葛岭北麓的“黄龙洞道院”并列为杭州西湖边最著名的三大道院。但就拥有道士人数而言,福星观也许可以被称作是民国初年杭州最大的一个道观。
杭州灵隐寺的和尚们。跟费佩德一样,甘博对于具有中国特色的佛寺和道观都具有浓厚的兴趣。他在杭州访问期间,拍摄了一组表现灵隐寺、天竺寺和玉皇山顶福星观的照片。在这张照片中,他拍摄到了灵隐寺三位服饰各异的和尚正匆匆赶往大殿。这三位和尚都身穿袈裟,第一个和尚带着一顶平天冠,第二个和尚带着风帽,第三个和尚光着头。
吴山东岳庙里的阴曹地府。位于杭州吴山顶上的新东岳庙颇负盛名。1913年,原之江大学校长费佩德就曾来这儿拍过一组照片。无独有偶,四年之后费佩德的朋友甘博在访问杭州时也拍下了一组东岳庙的照片。有趣的是,假如我们把这两组照片加以对比的话,就可以发现东岳庙在这四年中所发生的变化。在1913年的照片中,阴曹地府里的判官和小鬼的模样显得较为陈旧,而上面这幅照片里,那儿的塑像已经焕然一新,而且小鬼的数目也增加了不少。这说明东岳庙的经营者在这几年中收益不错。
吴山东岳庙里的阎罗殿。东岳庙阴曹地府的正殿是阎罗殿,其神龛上供奉的是分别代表五岳的五位阎罗王,它们是道教地狱中的最高统治者。神龛上方的横匾书有“位尊五岳”四个大字。在中国的传统观念里,东岳泰山、西岳华山、南岳衡山、北岳恒山和中岳嵩山这五大名山代表着天下的概念,这意味着堕入阴曹地府的鬼魂,无论到哪儿,也逃脱不了这五位阎罗王的管制。而在这五位阎罗王中,东岳大帝是老大,所以阎罗殿又称东岳庙。
吴山东岳庙里的血污池。按照中国民间宗教信仰的说法,所有因难产而死的妇女都会下地狱,在那儿的血污池里受尽煎熬。在费佩德的照片中,东岳庙血污池的容积很小,它的前面有一个真人大小的地母娘娘塑像,塑像前还有一个插蜡烛的木架子,血污池旁边有两个小鬼在等待着他们的牺牲者。在甘博的照片中,血污池的容积得以增大,池子里还坐着三位遭受血光之灾的妇女。池子旁边有一个很小的神龛,里面供奉着地母娘娘,比原来的塑像小了很多,前面的蜡烛架也变成了一个香灰炉。
吴山东岳庙里的牛头马面。
在1913年到1917年这四年当中,东岳庙的鬼门关也得到了修缮。例如原来牛头身上已经破损的盔甲在1917年时得到了修补。原来马面身上的盔甲比较陈旧,1917年时,这两个塑像盔甲上的图案都得以重新描绘,焕然一新。
吴山东岳庙里的黑白无常。1913年费佩德拍照的时候,鬼门关前黑白无常的头上是没有头发的;左边那位黑无常帽子上原来有“财见勿来”的字样,右面白无常的高帽子上则写着“一见生财”。到了1917年,黑白无常还是原来的模样,但是它们的头上都加了头发,而且左边那位黑无常帽子上的文字改成了“你来了”,但是右边白无常高帽子上的文字依然是“一见生财”。
吴山顶上包府的虎头铡。杭州吴山顶上有一个比较集中的寺庙群。除了供奉城隍爷的城隍庙之外,周围还有一些纪念其他名人的祠堂和寺庙。上面这张照片中间那个灯笼上写有“包府”二字,神龛右面的对联中也有“铁面无私”等字样,说明这个地方就是专门纪念包公的包公祠。院子里放着包公用以审铡美案的虎头铡。右面有一位留山羊胡子的老人悠闲地坐在条凳上,他显然就是包府的看门人。
杭州岳王庙内的万俟卨和张俊铁铸跪像。与秦桧夫妇并排跪着的另外两人分别是万俟卨和张俊。万俟卨(1083—1157)是秦桧属下的监察御史,曾秉承主子的意旨,将岳飞在死牢中迫害致死。秦桧死后,万俟卨继任宰相,因力主向金国求和投降,而被视为奸臣。张俊(1086—1154)是南宋的一名武将,曾与岳飞齐名。但他投靠秦桧,成为谋害岳飞的帮凶,因而也被人民所唾弃。
杭州岳王庙内的秦桧和王氏铁铸跪像。在岳飞墓阙的对面,有四个铁铸的人像**上身、双手反剪地跪在铁笼子里,其中还有个是女的。这就是当年诬陷和残害岳飞的四个奸凶。左面的那两个是秦桧和他的妻子王氏。他俩都**上身,跪在铁笼之中,引颈就戮。值得注意的是,1917年甘博所见到的那四个铁铸跪像跟现在岳王庙的跪像并不相同,旧跪像的“王氏”和“秦桧”等姓名是直接铸在肚子上的,而现在的两个姓名铁牌则是单独安置在这两个跪像后面的墙上。另外,铁栏杆的式样也不相同。
杭州城里的一个路边神龛。在中国民间宗教信仰中,有各种各样的土地神掌管着各种不同的地界,如住宅神君、墙土、灶土、栏前土地、牛土地、猪土地、沟土地、棉土地、布机土地、桥神土地、山神土地、树神土地等等。上面照片中这个路边神龛显然是为树神土地而建的,虽然有点简陋,但还是有模有样。神龛两边的对联分别是“万姓观瞻”和“千年香火”,横批为“神而明之”。
吴山顶上包府的看门人。包府的看门人是一位气质颇具吸引力的杭州老人。照片中的他坐在条凳上,正准备点燃自己的烟杆。这位老人身穿灰色的长袍、棉袄,头上戴着瓜皮帽,腿上用一块黑布条绑紧裤腿,脚上穿着中式的布棉鞋,瘦削的脸上留着山羊胡子,举止优雅而大方。
另外,原来御街两旁的店铺和手工艺作坊都具有浓郁的地方特色,一路看过去,几乎每一家都有自己的鲜明特色和看家本领,声情并茂、精彩纷呈,这是重修后的假古董店铺所难以比拟的,这也是以前在杭居住或来杭旅行的外国人能深深为御街所吸引的主要原因。美国旅行家盖洛在其于1911年出版的《中国的十八个省府》一书中用了大段充满深情的文字来描写他于1909年访问杭州时,在费佩德的亲自陪同下逛御街的难忘情景。在杭州出生并长大的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创始人鲍乃德(Eugene Epperson Barnett)的幼女鲍金美(Eugenia Barnett Schultheis),在其晚年所写的回忆录中也用了整整两个章节的篇幅来回忆她小时候坐着黄包车从御街上经过时的生动感受,(7)小时候在杭州御街的所见所闻使这位美国传教士的后代刻骨铭心,终生难以忘怀。
80年前,杭州“大街“(今中山路)上各种行当应有尽有,当一个洋人走过他们面前时,这些杭州人正各忙各的,做伞、制鼓、打剪刀、绷棕绷、弹棉花、敲洋铁皮……手艺有好有坏,生意有兴有衰,关键是做好手里的活计。
每天都是这样过来的,他们有的表情专注,有的神情快乐,有的技术娴熟,有的就是在看热闹——这是生活中平常的一天。他们并不知道,80年后的某一天,自己会重新从历史的尘埃里显影出来,与后人对视。相信现代读者在看完了甘博的这组老照片之后,也会感受到一种由杭州御街所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习俗给人们心灵带来的震撼。
杭州的一位算命先生
归根结底,甘博摄影的主要兴趣还是在于记录和表现人,无论男女老幼,苦力、文人,或者社会各阶层从事不同职业的人们。当他在拍摄杭州街头一位道士装束,白眉白须,颇有仙风道骨的算命先生时,甘博显然为后者超凡脱俗的气质所吸引。于是他便从不同的角度和距离给这同一位老人拍摄了多幅照片,甚至包括一张近景的特写镜头。应该承认,甘博这位美国的业余摄影师在这个人物形象中相当准确地把握住了传统中国文化和杭州地方特色的精髓,照片中的人物脸部饱受风霜,但其表情反映出了一种超然物外、与世无争、遗世独立和天人合一的生活理念。
上述甘博于1917-1919年间拍摄的所有这些杭州和西湖老照片加在一起,构成了一幅绚丽多彩、层次分明的全景图,充分而真实地展现了人间天堂的西湖美景,以及杭州这座古老城市民国初年的精神面貌。
清末民初的御街,是当时杭州最繁华的商业中心,手工业老作坊和店铺林立。当时御街以“坊”来分段,如清河坊、三元坊。每个坊之间都有砖砌拱门的高墙,拱门上刻有坊名。
茶馆里的大水壶
这是一把茶馆里烧开水用的大水壶。照片中这把大水壶被置于一口大缸和一口小缸之间,大缸里盛着尚未烧开的生水,小缸是用来接大茶壶满溢出的开水,壶顶那个烟囱般的装置,看上去像是安全阀,即开水沸腾之后出汽用的,有点类似于高压锅盖子上的安全阀门。不过用这样大的水壶来倒开水,的确需要有过人的臂力和高超的技巧。
白铁师傅
“洋白铁”(白铁皮)大致是在20世纪初从欧洲传入中国的,用它做成的桶、碗、瓢、盆等日常生活用品很快就进入了普通老百姓的家庭。白铁师傅也成了一种常见和受欢迎的手工行业。这张照片中的白铁师傅正在将一张洋铁皮敲成圆形的桶状。工作场所似乎就是他家的客堂间,揭开几块地板,放上模具,就成了他的工作坊,收工之后,把几块地板放回去,就可以摆放一家老小吃饭的桌子了。
制作灯笼
“大街”上有一家专门做灯笼的店铺。1909年来到来到杭州的美国旅行家盖洛对它留下了深刻印象:“最令我称羡的是用羊角来制作灯笼(的那家店铺),做这种灯笼需要五六个,工人,每人月薪在15到16元之间,再加上老板的米饭。工匠们从上海买来山羊角,加工磨光之后,用烧红的夹子把它们焊接成一体,整个制作过程中工匠表现了高超的技艺,令人目不暇接。”
盖洛在赞叹之余还专门拍了一张照片,附在他的书中作为插图。八年后甘博在同一个店铺拍下了这张照片。尽管照片中的主角已经换了一位工匠,但是制作灯笼的工艺和工匠干活儿的姿势依旧。
钻孔的小学徒
这张照片对于40岁以上的人而言,大概不会陌生,在电动和机械的打孔设备出现之前,人们就是用这样的工具来钻孔的。照片中,墙上挂着大大小小的各种十字形钻具。一位学徒正用这种古老的十字形工具在一块木头上钻孔,当他的手往下压的时候,横杠两端的绳索就会带动竖杆飞速旋转,于是钻头便可以在不同的材料上钻出一个洞来。过去人们甚至可以用它在破碗上钻孔,然后用金属钉子把碗补好。
脚踏车床
除了十字形钻机之外,木作坊里还有其他各种简单而巧妙的机械装置,例如这个脚踏车床。图中的小学徒用左脚不断地上下踩踏一根木棍,使得一个通过一根绳索与踏棍连接的圆形夹头飞速旋转,夹头上夹着一个小木件,这位学徒正在用锉刀在这个飞速旋转的小木件上刻出各种形状的环形花纹。注意到他脚下的那根踏棍了吗,已经被工人踩出了深深的凹印。
雨伞的制作
做伞是杭州一门古老的传统行业,西湖绸伞至今仍是杭州城市的金字招牌,笔者有幸在原杭州西湖伞厂当过几年工人,所以对于杭州的伞,有特殊感情。清代的杭州人已经使用桐油纸做成的雨伞。都锦生从日本引入阳伞,制作出西湖绸伞。民国时期出现的油布伞,因其坚固耐用,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仍然常销不衰。不过现在的80、90后已经难以想象使用油布伞的情形了。
这张照片展示了制作雨伞的工艺流程,先要制作伞骨,然后把伞的边缘缝住,再把伞面一块一块粘贴上去。当时的雨伞制作大多是家庭作坊,图中的父亲正在制作雨伞,儿子在一边观看,仰或是在做学徒打下手。
现场表演做鼓
鼓之所以能够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大声响,主要是因为敲击鼓皮所产生的空气振动,以及后者以声波形式扩散而造成的。而鼓的声响和音质则主要由鼓皮的大小和松紧,以及鼓桶本身共鸣的效果而决定的。所以蒙鼓皮是一个技术含量很高的活,工匠须具有丰富的经验,足够的技巧和体力。
照片中一位工匠正在现场表演做鼓,用八根粗大的麻绳,把鼓皮绷紧在一根木桩上,并用钉子固定住,然后通过调节麻绳缩紧的方法来消除鼓皮上的皱褶和其他不够平滑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使鼓皮跟鼓桶本身严丝密缝,从而确保有较好的音质。当经过处理变得光滑平整的鼓皮,被安装到鼓桶上后,还需要将它晾几天,再进行一些微调,然后才将鼓皮的松紧状态确定下来。蒙鼓皮一事,貌似简单,但里面的学问确实不小。
愉快的棕绷师傅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日子,两位面带笑容的棕绷师傅一边劳作,一边享受着灿烂阳光。棕绷床垫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千年前的宋代,据考证它的发源地就是临安(即杭州)。棕绷的制作工艺独特,用木头制成框架,然后用棕丝加工成的棕线密密地串编成床面。棕绷床具有极好的韧性,受力均匀,软硬适度,睡卧舒服,又防潮通气,是我国江南地区的传统卧具。
这种老式棕绷今天仍然可以见到,一些厂家甚至把它做在了席梦思床垫的反面,在濡湿的江南,夏季可以把席梦思反转来用,棕绷的通风凉爽远胜于新型席梦思,由此也可见床垫的转型。这门杭城千年老字号的民间手艺,完全可以申请非物质文化遗产。
新开张的张小泉店铺
1919年10月,甘博再次来到杭州时,正好碰上鼓楼的张小泉近记店开张。民国初年时,张小泉剪刀店店铺有炳记、近记、荣记之分。近记店铺的老板是张小泉的第八代孙子张祖盈,他发明了抛光镀镍的工艺,使得近记店铺生产的张小泉剪刀在市场上广受欢迎。
家庭木作坊
木匠这个行当有粗细之分。细木工匠,一般是指专门制作家具,尤其是能在木头上雕刻各种花纹图案的老师傅。浙江的东阳木雕闻名遐迩,杭州的木作坊也有其深厚的渊源和传统。这张照片向我们展示了细木工匠的三种基本手艺:左边那位年纪较轻的师傅直接用刻刀在木头上雕刻花纹;中间那位年纪最大的老木匠在用凿子和锤子将较大块的木头凿下来;右边这位中年师傅用钢丝锯在木板上直接拒出纹饰。这显然是一个家庭作坊,三位木匠很可能是一家祖孙三代。
杭州路边卖荸荠的小贩
90后的杭州年轻人可能认不出来这张老照片中的小贩在卖什么水果。但是上了年纪的老杭州们对此应该十分熟悉。它不是别的,正是江南水乡的一种特产,名叫荸荠。它有各种吃法,可以生吃,也可以煮熟了吃。由于荸荠里常常附有寄生虫,所以我们小时候都是要煮熟后才吃的。照片中的这位小贩向我们展示了另一种独特的吃法,即将荸荠削皮之后用细棍串起来吃,就像北京人吃糖葫芦那样。
杭州马路边的“门儿饭”
上了年纪的老杭州也许会对这张照片中的场景感到熟悉和亲切。在过去,杭州有不少沿街的小吃店常常因陋就简,用拆下来的店铺门板在街上支起一张桌子,招徕路人到小店里来用餐。在杭州方言中,到这样的小食铺来用餐被称作吃“门儿饭”。在这张照片中我们就可以看见一位路人在街上吃“门儿饭”。他就餐的桌子就是用门板搭在凳子上支起来的。
杭州御街上一家专织马带的店铺
马带的编织技术创始于湖北,从1894年起开始输入杭州,到了宣统年间达到鼎盛。当时杭州城里的马带店共有四十多家,主要集中在御街的众安桥至官巷口这一带。这张照片向我们展示了在民国初年的一家马带店铺内,人们是如何在织机上编织马带的。手工织机看上去比较简陋:织机不大,其框架是用木头做的,织工可以坐在上面。制作马带的原料是较粗的洋纱线,经过染色、浆洗、摇纱、牵经和上机等工艺程序,最后织成六寸、五寸和三寸等三种型号的马带。每个织工平均每天能织九条。从20世纪20年代起,因皮带、皮夹盛行,马带业逐渐衰落,销售对象也转向了金华、衢州、严州(建德)和杭嘉湖平原的农村地区。
杭州御街的街景
清末民初的杭州御街路面非常狭窄,最狭窄处就连两辆黄包车交会都有点困难。杭州基督教青年会创始人鲍乃德(Eugene Epperson Barnett)的女儿鲍金美(Eugenia Barnett Schultheis)回忆1920年前后在御街上坐黄包车的经历时写道:“当然,这是杭州市中心最长和最宽的一条街道,但仅有六至八英尺宽的路面并不能令人印象深刻,而且路上熙熙攘攘的行人更使这条街道显得狭窄。除了要躲避所有的人群之外,我们的黄包车还被从对面来的另一辆黄包车挡住了去路——那是我们在路上所看到的唯一一辆带轮子的车……”现在马路虽然拓宽了,但原有的韵味也随之尽失。
杭州城里的另一位算命先生
民国初年的杭州城里,算命先生们已经趋于专业化了。例如我们前面已经见过的那位老年算命先生在店铺门口挂出的招牌是“课命”,也就是以占卦的方式来预测顾客的命运。这张照片中的另一位算命老人则挂出了合婚择吉的招牌。显然,他的专长是测算待婚新人的生辰八字,以及选择适合于结婚的黄道吉日。他面前的那个箱子里装满了供人抽取的签,这既是用来算命的工具,也是向顾客宣布算命结果的一个凭证。
杭州人家养孩子所用的婴儿立桶这张照片反映的是早年杭州一个非常令人熟悉的场景。一个带着棉帽、穿着棉袄的婴儿站在一个位于住家门前的木制婴儿立桶里,正在晒太阳。这种特制的木桶在旧时的杭州颇为常见。由于它本身有一定重量,底盘较稳,所以将婴儿放在里面很安全,一方面可以让母亲腾出手来做其他家务,另一方面,让婴儿站立也算是一种锻炼。
杭州东河坝子桥附近的翻坝。沿着杭州城内的东河往北,到快接近艮山门水门的地方有一座桥称作坝子桥。顾名思义,在坝子桥的附近有一个运河上的翻坝。这是因为杭州城北的京杭大运河与杭州城内的东河和中河有一个水位的落差,船若想从京杭大运河进入杭州城内的运河,就必须要经过这个翻坝。翻坝处河道非常狭窄,只能供一条船通过,而且翻坝的两边都有木制的绞盘装置,即需要用人工通过绞盘把船从水位较低的京杭大运河河道拉上来,然后才能够进入东河。
货船沿着翻坝的斜坡滑入东河的河道。这张照片反映的是一艘满载货物的运输船在被人们用绞盘拉上翻坝之后,又沿着翻坝的斜坡徐徐滑入东河的情景。它与前后照片同为一组,完整地展现了民国初年的杭州人是如何用人工绞盘和翻坝来沟通京杭大运河与杭州城内运河之间交通的全过程。有趣的是,费佩德于1914年也拍摄过杭州坝子桥处翻坝的情景。
杭州人用绞盘把船拉上翻坝。这张照片以非常直观的方式向我们展示了民国初年人们是如何通过翻坝两边的木制绞盘将船从京杭大运河河道拉上来的。这个镜头非常难得,因为此前尽管在英国传教士慕雅德的回忆录中有反映19世纪末杭州人用牛把船从翻坝拉上来的照片,但是迄今为止,除了费佩德的一张老照片之外,笔者还没有看到过其他表现杭州人用绞盘把船拉上翻坝的老照片。
运往松木场的木材和毛竹。民国初年的杭州城与现在的一个重大区别就是除了延龄路等个别新建的街道之外,大多数的城市街道都很狭窄,但是城里水道纵横,运河水系比较发达,因此当时市内运河是一个重要的运输途径。从这张照片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的水路运输是多么的热闹和拥挤。这张照片拍摄于杭州松木场附近,照片中那么多的木材和毛竹都是运往松木场去的,因为那儿是杭州一个主要的木材交易市场。
杭州的凤山水门。清末时杭州城有一道城墙将其团团围住,城墙上共有十个城门,它们分别是凤山门、武林门、艮山门、清泰门、望江门、候潮门、清波门、涌金门、钱塘门和庆春门。其中凤山门、武林门、艮山门、候潮门和涌金门等五个城门的边上都附有水门。如今杭州的城墙和城门几乎已经全部消失,只有凤山水门还比较完整地保存了下来。这张照片所展示的正是1919年时的杭州凤山水门。
牛车将盐卤桶运到岸上。四轮牛车启动之后,水牛、牛车和装盐卤的大木桶实际上大部分还都沉没在水中。但随着车夫的大声吆喝,那两头水牛缓慢而坚定地将运载着盐卤桶的四轮牛车顺利地从浅水中拉到了江边的滩涂上。
运河杭州段有不少村民世代以船为家,这是一个船民的小男孩,面对甘博的镜头,没有丝毫惊慌。
杭州通江桥的九和染坊
杭州的染炼业主要是在民国初年迅速发展起来的。在民国之前,杭州的染炼作坊仅寥寥数家而已,如通江桥的九和染坊、仙桥的大章源、登云桥的恒瑞昌和石牌楼的公益染坊。民国之后,染炼作坊的数量迅速增加,1930年时便达到了214家。城里的运河沿岸随处可见染后晾晒的布料。开始杭州染坊里使用的主要是姜黄、苏木、花果、水靛等国产的颜料,自从外国颜料被引入中国之后,国产的颜料便逐渐被淘汰。照片中所表现的正是杭州的老字号九和染坊,背景中的石拱桥就是通江桥。正如店铺门口挂着的一块牌子所示,1919年时,九和染坊已经采用了西法洗染。
钱塘江上的一条住家船。
杭州西湖边的哈同花园。哈同花园曾经是杭州西湖边最美丽的私人花园之一。它位于孤山的南面湖畔的平湖秋月和中山公园之间,最早是由上海犹太富商哈同(Silas Aaron Hardoon)于1917年修建的,故称“哈同花园”,由于哈同的中国妻子罗迦陵经常在这儿住,亦称“罗苑”。从这张照片中,可以看到哈同花园那些亭台楼榭的精致豪华。在临湖的白墙上,可以看到三十五个形状各异的饰窗,每个饰窗内都有花鸟山水和各种人物的精美雕刻。可惜这些令人惊艳的造型艺术现在已经看不到了。从1927年起,民国政府就试图将西湖边那些被外国人占据的私人花园收归国有,但直到1956年,这件事才算最后尘埃落地。哈同花园的围墙早就已经被拆除,几座楼阁现归属于西泠书画院。
杭州文澜阁牌坊和圣因寺。康熙皇帝和乾隆皇帝曾经多次南巡来到杭州,当时就住在西湖孤山的圣因寺,因此孤山的圣因寺在清末民初又被称做皇帝行宫,里面的花园则叫御花园。御花园正门前面原来有一个牌坊,称文澜阁牌坊。这个牌坊1949年后曾经被毁,2005年杭州园文局又重新修复。对比老照片可以发现重建后的那块牌坊的许多问题。除了柱子和顶盖的比例有所失调,以及许多装饰细节的缺失影响到了牌坊的外形风格之外,更大的问题在于牌坊正面的匾额与原来的完全不同。原有的匾额跟牌坊的横梁融为一体,上书“光华复旦”,而新的牌坊匾额则向外倾斜,且上面的题词变成了“复旦光华”。自从本文2010年首发之后,这个错误已经纠正了过来。
杭州城内运河上的竹排。甘博的这张照片颇具视觉冲击力。在杭州城内本来就不太宽阔的运河里,一捆捆的毛竹整齐地堆积在一起,形成了一个规模浩大的竹排。这些毛竹都是用竹篾绳来捆扎的,捆扎的部位是在毛竹的顶端,这些毛竹被捆扎得如此之紧,以至于一捆捆毛竹的顶部都被挤扁了。由于堆放得十分整齐,那些笔直的毛竹和蝴蝶翅膀般的竹篾绳结组成了一幅漂亮的图案。
西湖小瀛洲上的树木在放生池里的倒影。小瀛洲的中间部分是放生池,池内又有一个小岛。围绕小瀛洲的环堤自东西走向有一条堤与中心小岛相接,自南北走向则有弯弯曲曲的九曲桥与小岛相连。从空中俯瞰,整个小岛就像是一个"田"字。这就形成了一个湖中有岛、岛中有湖的奇异景观。照片所表现的是生长在环堤上的各种树木在放生池水面上的倒影。远处群山的影子忽隐忽现,就像是一张水墨画。
泛舟西湖。来杭州游玩的外地旅客肯定会坐游船到西湖的小瀛洲和湖心亭上去看看。泛舟湖上,脸上吹拂着轻风,眼看着那西湖游船划破清波,慢悠悠地向湖中央的小岛划去,游客会感觉自己也融化在了这青山绿水之中,宋人徐元杰吟诵西湖的名句会不由自主地涌上心头:“花开红树乱莺啼,草长平湖白鹭飞。风日晴和人意好,夕阳箫鼓几船归。”
杭州运河上的一条客船。有不少船民的职业就是在运河上运送客人,这样的船被称作住家船,客人可以在船舱里坐下来喝茶和聊天,累了也可以躺下来休息。照片中的这条船有一个特殊之处是,在船尾有四个人同时在摇四条橹,这几乎可以肯定是在运送长途的旅客。当时从苏州到杭州的游客几乎都是坐船从运河上走的。
杭州城西的清波门。杭州城西城墙共有三个城门:钱塘门、涌金门和清波门。在1911年美国收藏家弗利尔(Charles L.Freer)拍摄杭州西湖的一张宽幅照片上,这三个城门清晰可见。通过比对,我们可以确定,甘博这张照片里的正是清波门。其特征就是在城门两侧突出部位的城墙上有两个小屋,其中左边那个小屋在1911年的照片中是完好的,但在甘博1917年的照片中就已经破败不堪了。清波门城楼是一个歇山顶的建筑,脊椿很高,两端分别有雷公柱连吻椿,脊椿的通花砖上刻有“风调雨顺”四个大字。城门内有一条石板路直通城里。
从小瀛洲上拍摄的雷峰塔。这是从小瀛洲的西湖游船停靠码头向东南方向拍摄雷峰塔的一张照片。从这个地方拍摄雷峰塔也是人们经常的选择,费佩德就曾经在这个地方拍过好几张雷峰塔的照片。甘博拍摄这张照片的时间大概是在上午,所以有点逆光,一道强光从右边进入画面,造成照片效果不太完美。
杭州西湖边的雷峰塔
杭州西湖十景中的“雷峰夕照”和“南屏晚钟”。南宋的西湖十景经过清代康熙皇帝的题字和乾隆皇帝的题诗早已是闻名遐迩,流传海外。其中第七景就是“雷峰夕照”,指的是矗立在西湖南岸,与北岸的保俶塔遥相呼应的雷峰塔在夕阳中熠熠生辉的风景。而作为西湖第八景的“南屏晚钟”就近在咫尺,两者堪称珠联璧合。
杭州净慈寺的一位和尚。
在雷峰塔的南面就是杭州的另一座江南名刹——净慈寺。它是由吴越王钱弘俶创建的,初名慧日永明院,后经宋高宗改名为净慈寺。1861年,太平军攻陷杭州城时,该寺院被毁。同治年间,在官府和当地乡绅的捐助下,净慈寺得以重建,并恢复了它往日的辉煌。在甘博的这张老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净慈寺院内相当整洁,就连和尚身上的衣服也显得比较干净。
从西往东眺望六和塔。照片是从山腰的之江大学学院校区从西向东拍摄的。从这张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当时钱塘江江边的情景跟现在有较大的不同。当时还没有钱塘江大桥,也没有建江堤,江边的滩涂很宽,而且连一条像样的道路也没有。江边的码头处建有一个仓库,仓库北面的山坡上,即如今蔡永祥英雄纪念馆的地方,原来有一座西洋式的高大筑。
从钱塘江中眺望六和塔。这也是一张拍摄六和塔的照片,但是拍摄的地点却转移到了钱塘江的江面上。从南向北看六和塔,可以更加完整地看清该塔的全貌。在江面上还可以看到一个从上游漂下来的木排,木排很长,上面有三个人在操纵它。木排上还竖了一块白帆,可以用它借助风力,增加木排漂流的速度。
送死者上路的谶语。在请人为死者念经超度的同时,人们还会在死者的房屋周围做一些专门的布置,以便能更加顺利地将死者送入天堂。在佛教的概念里,西天是可以永享极乐的天国,所以送人上西天原意为送人上天堂。在上面这张照片里,我们可以看到有人将一根竹枝插在墙砖的缝隙里,并在竹枝上挂了一张纸条,上书“引入西方”。这代表了一种祈愿,即希望死者能够进入天堂。
吴山顶上主日学校的三个小男孩。所谓主日学校,就是基督教会在星期天为信奉基督教的家庭的儿童们和其他平时上不起学的贫苦儿童所组织的非正规学校。照片上的三个小男孩,左面那个穿着白色的长棉袍;中间那个在深色棉长袍外面加了一件挽袖马褂,上面还缝了五颗闪亮的新式纽扣;右面那个则穿着典型的长袍坎肩,头戴瓜皮帽。他们的手上都提着一个铜火,这是一种颇有地方特色的杭州地区早年取暖用具。
正在上课的正则学校学生。
甘博的这张照片使我们有机会走进杭州教会学校的教室,去看一下当时的小学生是怎么上课的。六位男孩子围坐在用两张书桌拼起来的方桌周围,一个高年级的女生正在辅导他们朗读课文和写字。桌子的中央放着一份折叠起来的报纸,学生面前摆放着几本翻烂了的课本和几块用滑石笔来练习写字的石板。当甘博拍照的时候,站在女孩对面的那位小男孩正背课文和做听写练习。这显然是一堂早自习课。
一群代人念经超度的杭州老太太。
佛教说法认为,任何人去世之后,都必须超度,否则就会有下地狱的危险。有一些专门讲超度的佛经,如《救拔饿鬼陀罗尼经》和《地藏经》等,反复强调了超度的极端重要性。因此大户人家死了人之后,要专门花钱邀请和尚来家念经为死者超度;没钱做水陆道场的人家也得请一些信佛的老太太们来家里,代替自己念经。因此如这张照片所示,专门代人念经超度便成了这些老太太的职业。
(1) Janet Fitch.Foreign Devil:Reminiscence of a China Missionary Daughter,1909-1935.Taipei:China Materials Center,1981,p.135.
(2) Gamble,Sidney D.and John Stewart Burgess.Peking:A Social Survey.New York:George H.Doran Company,1921.Gamble,Sidney D.How Chinese Families Live in Peking.New York:Funk&Eagnalls Company,1933.
(3) Mrs.J.F.Bishop The Yangtze Valley and Beyond.London:John Murray,1899;Frederick D.Cloud.Hangchow:The“City of Heaven,”with a Brief Historical Sketch of Soochow.Shanghai:Presbyterian Mission Press,1906.
(4) 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这本相册,但是相册中没有出版单位和年月的信息,从相片的内容来判断,应该是1912-1915年间,因为相册中有袁世凯官邸“海晏堂”的照片。
(5) 在重修的天主圣教司铎公墓的前面,仍保留了两块石碑,上面刻有陵墓内所葬的九个半耶稣会士的姓名。他们分别是“罗儒望、金尼阁、黎宁石、徐日昇、郭居静、伏若望、阳玛诺、卫匡国、洪度贞”,以及一位叫“……玛”的意大利耶稣会士。
(6) Robert Fitch.“A Study of a Taoist Hell.”Chinese Recorder.Vol.XLV.October,1914.No.10,603-606,615.
(7) Eugene Barnett Schultheis.Hangchow,My Home-Groing up in“Heaven Below.”Fort Bragg,California:Lost Coast Press,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