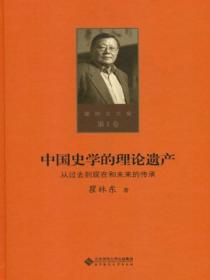《史学要义》的特点与价值
一、卜大有和《史学要义》
《史学要义》4卷,补卷1卷,凡5卷,明代卜大有辑,徐栻作叙,万历五年(1577年)刻本,距今已422年,后世未曾重刻。今仅存两部,分别收藏于国家图书馆和山东省图书馆。
《史学要义》卷1至卷4,卷首各有目录;补卷卷首无目录,其目,视所补内容分别列于上述各卷目录之后,并冠以“补集”二字,以示区分。
《史学要义》所辑之文,是历代学人讨论史学之作,上起西汉,下迄明代。诸文体例,有疏、表、事状、书、论、序、跋、传记等。其编次,卷1所辑之文,前一部分是关于史官、史官制度、作史义例、史馆修史、史法、正史、杂史等综论性质方面的议论,后一部分以及“补集”所列是关于《史记》《汉书》《后汉书》及其作者的评论。卷2所辑之文,是关于《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南史》《北史》《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及有关作者的评论,“补卷”所列大致同此。卷3所辑之文,是关于《资治通鉴》《资治通鉴纲目》《资治通鉴外纪》《续资治通鉴长编》《通鉴续编》《通鉴纪事本末》《通鉴前编》《大事记》《世史正纲》以及关于《史通》《古史》等书与有关作者的评论,“补卷”增列有关《稽古录》论正统的议论。卷4所辑之文,是关于《战国策》《汉纪》《后汉纪》《人物志》《续后汉书》《唐鉴》《唐史论断》《南唐书》《建隆编》《经世纪年》《宋元通鉴》《通典》《通志》《路史》《文献通考》等书及有关作者的评论,“补卷”所列仅限于《唐鉴》、唐论。通观全书所辑之文,凡200余篇,多是关于史家、史书的评论,或论得失、辨是非,或溯源流、探新途,都是关乎史学本身的认识,一言以蔽之曰“史学要义”,是名副其实的。书中所辑之文,也有几篇是讨论历史问题的,如卷4之论东、西周,补卷中之论唐八司马,《通鉴纲目》之论正统等文,虽与“史学要义”之本意不尽吻合,但寥寥数篇,不影响全书的性质和面貌。
辑者卜大有没有关于此书之编次的任何说明,根据各卷所辑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做这样的概括:卷1是关于史学的总的面貌和关于“三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的评论,卷2是关于《三国志》至《元史》历代正史的评论,卷3是关于《资治通鉴》及与之相关的多种历史撰述的评论并兼及对《史通》等书的评论,卷4诸文涉及的史书在内容上和体裁上广泛而驳杂,似乎是相对于“正史”以外的“杂史”。按照刘知幾《史通》的分类方法,纪传体、编年体的皇朝史均为“正史”,其他体裁的史书大多归于“杂述”之下。卜大有于卷1收入刘知幾论“史氏流别”、《隋书·经籍志二》的“正史”“杂史”小序,于卷3收入评论刘知幾和《史通》之文,或者包含了他关于本书的编次思想,即首先是综论,继之以“正史”,最后是“杂史”。
徐栻的叙文在揭示《史学要义》一书的内涵、价值以及表明他对于史学的期待等方面,都有明确而不俗的见解。他写道:
卜大夫究心史事,既得其旨趣,间尝采辑古今论著有切于史学者若干卷,题其端曰《史学要义》。予得而读之,见其陈叙事之义例,原载笔之职司,析编年、纪传之同异,以暨辨正杂,别良秽,罔弗备焉。乃叹曰:“勤哉,大夫之志乎!精哉,大夫之取裁乎!”[1]
这段话把《史学要义》的内涵,即“史学”的“要义”做了很好的概括:“陈叙事之义例”,是指作史的思想和体例、内容和形式;“原载笔之职司”,是指史官、史家的职责及其源流;“析编年、纪传之同异”,是指对有关史书体裁的认识和运用;“辨正杂,别良秽”,是指史学批评及其作用。文中所谓“究心史事”“切于史学”,是把“史事”“史学”区别看待的;所谓“精”于“取裁”,是强调了“切于史学”实为本书采辑之主旨。
至于《史学要义》的价值,徐叙开篇就这样指出:
载籍博矣,而义有要焉;得其要义,则会通有机。是学史者,要义尚矣。嗟夫!事以代殊,文缘人异,纷纭述作,迷目瞀心,自非博雅之士,恶足以与于斯。
这里讲的“博”与“义”的关系,本质上是知识与思想的关系;又讲到“要义”是“会通”的关键,表明作者重视会通并指出“要义”与“会通”的关系;还讲到只有“精明博雅之士”才有可能与之探讨“要义”。作者的这些见解,都是很有启发性的。“得其要义”的重要,是讲的一般原则,“精明博雅之士”的难得,自然就实指辑者卜大有了,二者都着眼于强调本书的价值。
徐栻从对于《史学要义》一书的介绍和推崇,进而谈到他对于史学的一种期待。他在叙文中说:
是书之作,真学海之舟楫、文艺之要旨也。当世贤豪励志“三长”者,固幸得指南……孔子以圣神之心而窃取鲁史之义,则心,其史学之尤要乎!是故公其心以定夺,明其心以辨正雅,大其心以尽人物之变,斯无负于《要义》之作也。[2]
徐栻认为,这书对有志于把“史才三长”,即史才、史学、史识作为努力目标的人来说,是有指导作用的。他举孔子为例,再次强调“义”的突出地位,指出“心”即思想是史学的核心。所谓“公其心”“明其心”“大其心”云云,就其本质而言,关系到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和气度。
从中国古代史学思想发展来看,徐栻叙文所论,一是中肯地阐述了《史学要义》的旨趣;二是提出了一些有意义的见解,如知识与思想的关系,“会通”与“要义”的关系,以及在思想上把握史学批评的标准、原则和气度的重要等,都是可以做进一步研究的。
徐叙末了有一句话,叫作“归诸心学,以为史学者勖焉”,同叙文讨论史学处多不协调,由此亦可见陆王心学唯心论在当时的影响。这是我们应当注意到的。
本书辑者卜大有是嘉兴府秀水县(今属浙江嘉兴)人。《明史》无传,其《艺文志一》诸经类著录“卜大有《经学要义》五卷”[3]、《艺文志二》史钞类著录“卜大有《史学要义》四卷”。这两部书,《四库全书总目》未著录,而《经学要义》已失传。[4]《万历秀水县志》卷五于“先达”一目中记卜大有兄弟三人行事,略述如下:
卜大同,字吉夫,嘉靖戊戌(1538年)进士,授刑部主事,迁湖广参议,再迁福建巡海副使,闽赖以安。弟大有、大顺,皆举进士。
卜大有,字谦夫,嘉靖丁未(1547年)进士,初知无锡县(今属江苏无锡),执法不挠,称“强项令”,中忌者调潜山县(在今安徽西南),莅政刚明,夙奸畏服;历南仪曹郎,以忤时宰,出为寻甸(在今云南中部偏东北)守,致仕。
卜大顺,字信夫,嘉靖癸丑(1553年)进士,初令当涂(今安徽当涂),治行称最,擢刑部主事,寻改吏部,历司勋郎。能留意人才,却问遗,不脂韦逐时好,卒于官,人共惜之。
据明人文集及焦竑《国朝献征录》所记,卜氏兄弟之父卜宗洛,生于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卒于嘉靖十七年(1538年),即大同进士及第之年,号长醉翁,曾为太学生。[5]卜大同生于正德四年(1509年),卒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是为大顺举进士后二年(见徐阶《经世堂集》卷一七《卜公墓志铭》)。卜大顺生于正德十五年(1520年),卒于嘉靖四十年(1561年),享年四十二岁(见《国朝献征录》卷26郑晓撰《卜君墓志铭》)。大有生卒年不详。今据大同二十九岁举进士,大顺三十三岁举进士,姑以大有三十一岁前后举进士推之,他当生于正德十一年(1516年)前后,而其卒年不会早于万历五年(1577年),是卜氏父子中年寿最长的人。这样一个进士屡出的官宦之家,同巡抚浙江的徐栻有所交往,是很自然的。
徐栻(1519—1581),字世寅,号凤竹,苏州府常熟县(今江苏常熟)人。《明史》卷220《刘应节传》、卷87《河渠志五》略记其行事。明人关于徐栻事迹的记载,主要见于王世贞《江右奏议序》《徐尚书传》[6]《徐公墓志铭》[7],以及《万历常熟县私志》《崇祯常熟县志》等。徐栻于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举进士,从宜春(在今江西西部)知县做起,“凡十五政”,曾先后巡抚江西、浙江,最后拜南京工部尚书,旋归里,里居二年而卒,终年六十三岁。徐栻先后为卜大有《经学要义》《史学要义》作叙,而他的《江右奏议》又是王世贞作的序,这都是他在浙江巡抚任上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