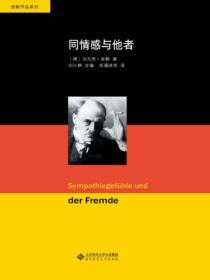三、对他者的感知02
可见,内在感知行为作为其本质者并不是只能针对感知者自身的心灵经历,似乎“内在感知”与“自我感知”同时发生。我们认为,从内在感知行为及其本质看,并联系到出现于内在感知中的事实领域,每个人对邻人的经历像对自己的经历一样都能够同样直接地(和间接地)加以把握。由于身体状态决定性地影响着对内在感知中出现的关于心灵生活的现象的选择——这些状态在这一功能中称为“内在觉知”——,所以,身体状态之不可消除的差别造成了下述情况:在实际发生相同经历的情况下呈现于B者,却是不同于呈现于A者的另一幅“图像”。[17]
人们曾试图(以不同的方式)证明,对心灵经历单元(Erlebniseinheiten)之每一可能的认识和规定之所以能够进行,只是由于一种“规定”是从外在的自然对象方面着手的。因此,纳托尔普认为——见他的《心理学引论》——在一切心理学之先,必须首先将所发生者“客体化”为外在的自然对象(借助“先验的整合”),由此一出发点方才可能通过一个重新架构的过程以“描写”的方式,尤其以“解释”的方式对一个心理经历“作出规定”,例如一种感觉是由于物理刺激引起的。持类似观点的是闵斯特伯格,他试图将自然对象规定为在多数个体的和个体间的主体行为中尚可确认的X,于是,“心理”概念便不啻为只可能“发生在”一个主体行为中、甚至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东西的化身。这些学说从定义上便排除了我们“感知”他人心理的可能性;甚至对自己心理的感知也只能间接地实现,即我们从外在的自然在(Natursein)的对象出发,进而规定我们的经历为其“相关物”。这些命题的逻辑结果是,根本不存在心灵世界之活的固有联系,既没有个体的,也没有个人间的固有联系;因为被确认为“心理”者只是未进入身体之自然对象和因果与法则联系结构的“发生者”之残余,自然不可能设想,它本身会在自身之内形成一种连绵不断的可理解的联系。这就是说,这些前提的自然结论便是伴生现象论(Epiphanomenalismus)和方法论上的目标,这一目标是,试图通过揭示神经系统中之生理的和物理—化学的相关过程建立心理经历之一切合理的联系。
这些理论所揭示给我们的基本上只有一点:我们所持的使自己“最先”完全被拖入外在世界之中的“自然的世界观”往往陷于迷误,即误将某种事实上只是作为躯体对象发生在我们之前的东西当成心理经历。柏格森(H.Bergson)的特殊功绩在于指出了一个事实:我们全都想将一种空间的多样性带进有着天壤之别的灵魂多样性之内。[18]可以说,凡是为一种特殊的、也许难以克服的内在感知的错误方向的东西,这些理论却将之当成“一般心理经验的条件”。这使这些理论不是将身体及其变化看成是对实在的心灵生活进行感知的有限制作用的条件,而是将之视为一条具有清楚限定性的和独立变化的因果链条。心灵事变自身便“依赖”这一链条的联系。这些后果产生于错误的假定:“凡是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者”,或者凡是通过多数主体行为无法认定者,便是“心理的”。假若心理的东西总是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那么,它便是不可传达的。在这里应指出,这种理论从一般意义上关于心理的言说事实上指的只是身体感觉和感性情感。[19]因此,它在其表述中总是陷入感觉论(Sensualismus),即徒然地试图将全部经历归结为“感觉”及其衍生物。[20]认为一种心理经历在多数行为中不可能保持同一,是完全错误的。难道我们不能在不同的时间时而“多些”,时而“少些”地感觉到“同一种”痛苦、同一种爱?不能多次回忆起同一次经历?不能现实地经历和重复感受——举例来说——同一种情感?我们心理学界不是普遍认为,同一种视觉上的感觉有时会成为视觉内容或者进入这种内容,有时则不会(如在神经症般的失明状态下),有时会“被察觉”,有时不被察觉,有时“受到关注”,有时则不受关注?谁如果认为属于心理之本质者是,心理不可能在多数的行为中保持其一致,他首先便混淆了心理现象领域与心理现实;其次混淆了一般现象的,即对于每一对象范围皆为直接给予者的领域与心理。冯特便是如此,他将心理等同于“直接经验”,而将躯体等同于“间接经验”,实际上,不论在外在感知和内在感知之内,还是与之相应地在自然之在和心灵之在中,既有直接对象阶段,也有间接对象阶段。[21]
但是,正是由于心理可能发生在多数行为中,同一心理也才有可能发生在不同的个体身上。正如我们在自己生命的不同时代能够“重复感觉”同一种苦难经历,“回忆到”它,时而多、时而少地为之“感到痛苦”,我们也能够“相互”将它作为同一种东西而为之“感到痛苦”。当然,我们绝不可能感觉到同一个(在身体某一部位之上的)感官快乐或者同一个疼痛。这些状态是每个人所独有的,它们只可能是“同样的”,但不可能是同一的。相反,两个人完全能够感受同一个痛苦,严格意义上的同一个,而不是“相同的”痛苦,尽管由于器官感觉的不同而带有不同的色调。凡是认为心理总是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人,永远不可能解释清楚下面一些句子究竟是什么意思,如“同一种**洋溢于士兵队列之中”;感染着人民的是一种欢乐、一种痛苦、一种狂热的喜悦等。习俗、语言、神话、宗教、童话与传说世界,——在心理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这一前提之下,人们怎样去理解这些东西呢?
以上所述表明:这些理论将通过每个人对于他的(以及其他一切人的)心理经历的内在知觉而呈现于他的东西与一般心理之此在和如此在混为一谈。不过,这个错误并不比另一错误更大,坚持另一错误的人认为,自然只是落入一切人的感官感知中的碎片之总和。事实上两者没有什么差别。我们即便以外在感知(作为独立的行为意向)也能够在“自然”之整体的背景之上把握住其如此在的每一细部;在每一个此类行为中都将确认作为领域的自然之存在,而无须“推论”或者“移情”。即便在这里,身体也切入根据合理和可能而针对自然整体的感知行为主体与感觉对象之间,同时切入其间的是身体的感觉,即“外在觉知”(?uβerer Sinn),它所选择的感知内容只是对身体之可能的态势具有重要性的东西。虽然这些“内容”因每一个体之不同而有别——哪怕是同一些对象——,但我们并不怀疑,我们在这些内容中所感知到者是同一个自然。[22]从根本上驳斥所谓心灵性的东西即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东西这一论断的是,假若这一命题的理由正确,那么这同一些理由也会支持另一论断,即自然也只发生在“一个人”身上。实际上导致这一命题者是“主观唯心论”。人们有理由反对这种唯心论,向它指出,假若其论证是正确的,那么不仅外在世界和物质的存在,而且既往意识内容的存在和他人的我之存在全都会被否定。在这里,只有唯我论者的瞬间之我的存在具有不容侵犯的确凿性!只要我们囿于自己身体之内的生活,我们便在事实上接近这种瞬间唯我论者。如果此一推论重要,彼一推论也同样重要:谁否认他人之我及其经历之可感知性,他必然也以同样的理由否认物质之可感知性。人们不无兴趣地看到,在哲学史上,一个实在的自然存在比他者之我的存在更经常遭到否定,虽然没有人否认自然之可感知性,但几乎所有的人都否认他人的心灵生活之可感知性。由此可以理解,我们关于他人的我之此在的信念比我们关于自然之此在的信念更深刻、也更早。
2.现在让我们转入对上述两种理论之“理所当然的”前提的另一部分的讨论。有人也许会问,在另一个人身上,除了他的“身体”和动作以外,我怎么可能感知到其他的东西呢?
非常简单的现象学观察足以说明,在这里至少没有什么东西是“理所当然的”。诚然,我们也许自以为直接地从微笑中看到他人的快乐,从泪眼中推知他人的哀伤和疼痛,从他人泛红的脸颊体会到他的羞赧,看到他祈求的双手便知道他有所求,从他双眼发出的温柔目光看得出他的爱,从他咬牙切齿的动作看得出他的愤怒,从他紧握的拳头看得出他的威吓,从他的语言推知他的意之所指的含义等。谁要是对我说,这并非“感知”,因为这不“可能”是感知,之所以不“可能”是感知,因为感知只是“感官感觉”的综合,因为肯定不会有对他人心理的感觉——肯定更没有刺激——,我请求他撇开如此可疑的理论,回到现象学事实上来。然后,他首先必须做的便是,将所列举的这些情况与事实上——根据他的理论——存在着的他偏爱对之作先验设想的东西的情况加以比较,即进行有根据的推论。例如,我可能会为一个不久前与我进行过交谈、我自以为已感知到其情感和意图的人的一系列行为所迫而作出推断:我要么误解了他因而自己出错,要么他对我撒谎或者装假。这时,我在事实上在对他的经历进行推断。我也可以从一开始便采取类似态度,即从其表情推断其思想与情感,例如,当我与某个我担心为精神错乱或疯癫者的人打交道的时候,或者当我担心他装假或怀有欺骗意图时,这就是说,只要我发现我对他的经历之内在感知性的体认以某种方式不正常地受到妨碍,或者我出于某些实在的而自身又有待进行(最后的)感知的“理由”而被迫设想经历与表情不相符合,或者这种象征性的联系——它并不仰赖个体性之特殊经历和经验——被(自动或者任意地)分离开来。[23]在这个时候,只有在这个时候我才开始“推论”。在这一方面且不可忽略这些推论资料上的先决条件是建立在对有关的人或者其他的人的朴素感知之上的;可以说,它是以那些直接感知为前提的。譬如,我不仅看到另一个人的“眼睛”,而且也看到“他在注视我”,甚至看到,“他在如此注视着我,似乎在避免让我看到,他在注视着我”!于是,我发觉他只是“假装”去感觉他根本不去感觉的东西,他撕断了我所熟悉的那条联结着他的经历及其“自然表情”的纽带,他在自己的经历要求某一特定表情现象的地方却做出另一些表情动作。于是,我确知他在撒谎,这不仅由于我证明他必定知道自己表里不一,事情并非如他所说的那样,而且我在某些情况下也能够直接感知到他撒谎这一事实本身,即撒谎行为本身。所以,我可以冷静地对某人说:“您心里所指的并非您所说的;您没有表达清楚”;这就是说,我把握住了他心里所指的意思的内容,这是从他的言词中绝不可能推断出来的,否则我就不可能根据事先传达给我的“意思”来更正他的话了。
人们也许会说,这些差别是存在的,但这并非感知与推论的差别,而是一种简单、原始的或者“不自觉的”推论与一种复杂、自觉的推论的差别。不过,让我将这种有利于错误理论的、人们既可以用以证明一切又不证明任何东西的异议搁置不议吧。[24]
现在让我们考察一下那种认为人们除了“最先”“感知到”他人的身体及其动作之外,不“可能”“感知到”其他任何东西的论断。
我从我们与之一起生活的其他一些人身上所感知到的,“最先”既非“他人的身体”(只要不是正在进行一次外部的医疗检查),也不是他人的我和“灵魂”,而是我们直接观察着的统一的整体状态,而这种直观内容最先没有“被分解”为“外在感知”方向与“内在感知”方向。随之,我们在这一发生阶段的基础上要么处在外在的、要么处在内在的感知方向。与“最先”“呈现于”我们这样一个个体性的身体统一状态的同时,也给予了我们一个可以接受内在感知与外在感知的可能对象,其根据在于这些直观内容的本质联系——它甚至已经成为我进行自我感知的基础——,而不是通过在我自己身上进行的观察和归纳得到的。这种联系也可以用来解释一般生命形式的本质。[25]
在这种个体性身体单元上所存在的“现象”像单元本身一样,在心理—形体上是中性的。人们可以对它继续进行分析,譬如分析为纯颜色、线条和形式单元以及交换、运动和变化单元等。现象在这个阶段上的每一个“表现单元”是一个从属于作为此一生命形式单元之个体性整体之整体的单元。在这个阶段,这样一个现象单元还完全没有象征性功能,不论是对于在外在感知中所呈现出的身体单元及其各部分,还是对属于内在感知的有关个体之我之单元与经历单元及其各部分而言。于是,这个阶段的“现象”进入完全不同的单元构成(Einheitsbildungen)和这些构成之结构,随之它们便(在外在感知行为中)获得象征性功能,即象征性个体之身体(和它与周围其他身体之变化相关联的变化系列)或者(在内在感知行为中)个体之我(和它面对周围其他的我之变化的变化系列)。沿着这些不同的感知方向——并根据正在进行者是此一种还是彼一种感知——呈现出同一刺激后果的一种单元构成,它作为另一个个体之身体借以进入我们的感知的现象(或者作为一个周围世界印象之直观后果的现象),呈现出的同一刺激后果之另一种单元构成,则是作为他人个体之我借以进入我们的感知的现象(或者作为一个为内在世界之直观表达后果的现象)。正是由于这个缘故,从本质上看便不可能将一种“表达性现象”(例如微笑、威胁性的或者善意的抑或温柔的“一瞥”)分解为如此大量的现象,这些现象的各个成分对于我们借以感知来自周围形体世界的身体或者印象单元的现象单元而言,似乎仍然是同一的统一体。如果我遵循外在感知方向考察一下在其中呈现于我的那些可能会成为对个体之身体的哪怕最细小部分的外观的现象单元,那么——,尽管这些单元存在着种种可能的联系——我绝不会看到“微笑”或者“请求”抑或“威胁性手势”的单元。所以,作为脸颊表面上的覆盖层而出现在我眼前的红色绝不是其“结果”的一种被体认到的羞赧的“红晕”单元。这同一种原初的红色现象以这种脸颊红晕的形式同样可以表示“燥热”、“愤怒”、“**”和灯的红色光亮。
我们由此也许可以更深刻地理解认为我们“只能感知他人的身体”那种假想的“理所当然性”。如果人们最初使颜色、音响、形式等变成“感觉”,而它们实际上却是在感觉伴随下出现的“质”(Qualit?ten);如果人们又将并非建立在“感觉”,而是建立在这类质的复合(Qualit?tskomplexe)之上的“感觉”当成一种“感觉”复合;如果人们随之又忘记按照这种“感知”观念(以对它的双重误解)是既不可能“感知”“我”,也同样不可能“感知”“身体的”,但又自认为完全能够——在这些前提之下——“感知”它们,那么,便产生一个奇特的结论:人们虽然能够“感知”他人的身体,但却不能够感知他人的我。部分错误的实际设想之总和——与“第四范畴”相联系——导致了这一“结论”。
因此,人们推崇哪一种感知理论,对我们并没有什么意义。谁如果认为,“感知”的内容是感觉和那些——举例说——以往感觉之被激活的记忆踪迹的复合体,他就不要妄想能够“感知”他人的身体!谁如果认为,“感知”总是包含着一种判断,他就应该明白,这样一来人们便可以作出这种(奇怪的)“直接”判断说,另一个人正经历着羞惭。如果有人说,感知包含着一种“推论”(但却是一种“不自觉的”推论),那么,他在对他人的心灵感知中也应允许使用这种不自觉的“推论”。[26]从另一个人的身体发出的物理、化学等性质的刺激必然侵袭我的身体,这并不要求在“友善表情”等类现象呈现于我以前,必然已经向我呈现出他人的一副身体,或者必然首先向我呈现出与那些刺激相应的个别感性现象,如声音、颜色、气味等。
不论何时何地,首先“呈现于”我们以及呈现于动物和原始人之前者总是整体状态结构(Ganzheitsstruktur),感性现象只是出现在它们能够作为这些结构的基础而发挥作用的时候,只是出现在它们能够承担对整体状态的符号和表现功能的时候。
[1] 里普斯甚至将既往的心灵生活——我们从其中所“被赋者”只是一种被解析为“回忆意象”的意象——以及关于外在世界之存在的设想,也归结为盲目的信仰。这极少逻辑依据。里普斯由此达到的结论是,他者之我的存在至少像既往的心灵生活和外在世界的存在那样肯定。
[2] M.W.Shinn:《儿童智力发展》,P.Univ.of Galif.Stud.,vol.1-4。
[3] B.Erdmann:《再现心理学》。
[4] 康德将他提出的知性中的十二个先天范畴分为四组,第四组即模态范畴,与此相应的是第四个原则是经验的思想公设。康德的错误在于使分析理性超出了经验范围。——译者
[5] 贝歇尔试图证明,在这里不存在Quaternio,但我觉得他没能做到。问题并不是我们怎样设定并非我们的经历之个别经历,而是如何设定他人之我的存在,这个我从根本上看就没有“我们的”经历,因为它有它自己的,即他者之我的经历。他者的我之在(Ichsein)恰恰先于他者之我的个别经历而出现于我们之前。从本己之我跨向他者之我迈出的一步,完全不同于从一个发生的他者之我跨向第二个、第三个等他者之我迈出的一步。
[6] 我想在另外的场合指出,这种与自笛卡儿以来的机械论生物学合流的“移情论”对生命事实的解释是多么错误。当前对于哲学最重要的使命是,为生命认识奠定现象学的基石,并进而在认识论的背景下给予生物学以独立的、不仰赖化学、物理学以及心理学的权利。
[7] 最终,我们必须为我们在某“一种材料”中发现的一切“理性的”思想单元(Sinneinheiten)设想某些本质上应属于它们的行为,而又为这些行为设想一个为材料加进这种“思想”的位格中心(Personzentrum)。
[8] 关于“位格”(Person)这一概念,请参见《伦理学中的形式主义与实质的价值伦理学》,第六章。
[9] “内在感知”作为行为方向有别于“外在感知”(其本质不可能使它通过感官功能,更不可能通过感官完成)。这一区别自然并不涉及从一个规定的个体看何者在内、何者在外的问题。从本质上看,“内在感知”“属于”对心理的东西的把握,不论感知者是感知“自己本身”还是另一个人。关于这些概念,参见《自我认识的偶像》一文。
[10] 是的!在发生这种情况时,“思想”也是纯然从形式上“指涉我的”,因为这是其本质所在。但这个“我”只是意识之多样形式和单一形式中的一个数位值(Stellenwert),并非经历过的事,更不是“本己的”我,后者只可能存在于对立面中,即与一个“外来的”、“另一个”我相对的对立面中。
[11] 基于这一事实,所以,最终只有那些属于一个民族或宗教共体之群体并熟悉其“传统”的人才,可能完美地理解这个民族的(或者这个宗教共体的)思想史。拉普莱希特(Lamprecht)在其《文化政治》一书中也提出了这一看法。
[12] 这种原始主义(Primitivismus)今天再次在群体心理现象研究中受到重视,由此很容易说明,群体心理现象包含着许多对个体而言为“病态”的东西。例如,人们可以在群体心灵过程中又发现一系列具有歇斯底里特征的现象。
[13] 即使在外在感知中,刺激也绝不限定被感知者之如此在,它只限定对此一而不对彼一进行感知;另外,这同样可以用来解释回忆与再现和联系的关系,——这两种情况只能在对这里作为基础的一般认识学说的总体表述中加以说明。
[14] K.Fiedlers:《艺术活动的起源》。
[15] 如果人们将这种平行论理解为每一心理的和每一形体的变化之清晰的相互依存关系,那么,人们就必须设想中介我们的视、听的光波与气流也是一种“心理的”伴生现象,当然这种现象只是为了假设的成立而虚构的。正如Sigwart所强调的,这种设想也包括关于存在着一种远距离的心理影响的设想。关于这个问题Tr.K.Osterreich在他讨论隐秘的现象的书中提出许多中肯之见。
[16] 这同样的情况对于外在的感知也是存在的。有的人认为,它的对象——自然有一种本质上不同于心灵过程的对于身体的依附关系,这是错误的。在一切自然现象中都同样存在着一种本体上依附于和独立于身体的因素。
[17] 这种“图像”自然并非特殊的、实在的“对象”,而只是对他人经历之有限的“看法”。
[18] H.Bergson:《论意识的直接材料》,Paris,1908。
[19] 姑且不说,同一性原则足以说明,现象这机械性还原(mechanische Reduktion)的设想是完全错误的——如闵斯特伯格所说,实际上,“同一种”声音可以被感知、想象、回忆,也可以为多数主体感觉到,这无须将它——只是为了认定为同一的缘故——规定为运动。关于造成对自然现象之机械性还原的实际理由,我将在另一个地方就其本质进行讨论。
[20] 所以不难理解,闵斯特伯格赋予心理学的使命是,最终将一切心理现象,包括“意愿”都“改造”成为“感觉”——这对于我却是不可理解的一句话。
[21] 最近屈尔珀(O.Külpe)也有类似表述,参见他的《实在化》。另可参见拙文《自我认识的偶象》和该文针对Husserl关于逻各斯的文章的注释。M.Geiger对此有非凡论述,见他的《论无意识》(载《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
[22] 这里所讨论者还不是特殊的“实在性之给予”,我们认为它与领域问题毫不相干,它只是作为对我们的意志行为的“抵制”而给予的。
[23] 参见Koffka:《经历与表情》,他也否认一种纯然“争取得到的”联系。
[24] 这种理论的心理学上的来源是不难证明的。从历史上看,它是特殊的启蒙理论系列(适用于国家的契约论、语言上的约定俗成论等)的分支,它们全都根据一种“人为社会”的类比——在这种社会中不信任已经成为定势——来评价原初的“共体”。参见《道德建构中的怨恨》。
应注意,我们往往以推论方式对待自己的经历;譬如当我们说“我当时如此做了,得成为怎样一个人呢”的时候;或者当我们想从自己身上解释一种按照自己的情况为我们所不理解的情绪时,等等。
[25] 这也适用于低等动物。人们可以完全“机械式地”解释一条普通蠕虫的曲身动作,并作为生理学嘲笑(如Jacques Loeb)一种说法,即蠕虫“曲身”是因为“疼痛”(因为蠕虫的各个部分在没有头的情况下同样曲身)。如果基于这种机械原因解释的可能性而得出结论说,这种动作并非同时是疼痛的表现现象(因为蠕虫在失去头的情况下感觉不到疼痛),那自然是很荒唐的。这种推论之荒唐正如说一个人的脸红并非羞惭的“表现”,因为这是一次机械上(肯定)可以解释的血流涌上脸颊的结果。诸如表情现象之类的象征性功能会与机械上的因果解释有何相干?
[26] 感觉论可能非常天真。休谟感到奇怪的是,人们只是由于外表分为“黄色的”、“黑色的”或者“白色的”而相互争斗和仇恨。他竟如此理解种族斗争和种族仇恨!相反,我们可以冒昧地设想,美国人之恨黑人并非因为其肤色“黑”——迄今并没有证明,他们也仇恨黑色的披巾和衣服——,而是因为他们从黑黝黝的肤色中嗅出了黑人的气味!(见休谟:《英国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