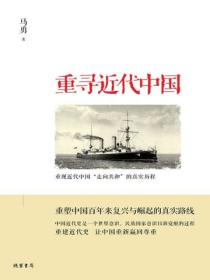现代化的真正实现有赖于能否确立稳定的秩序,而秩序的建设一方面需要政府积极协调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使各利益集团在确认现代化共识的前提下进行有秩序的竞争;另一方面,各利益集团以及全体社会公众,为了国家和民族现代化的整体利益,既要充分利用对政府的监督权力,使政府的行为不至于超越秩序,或危及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又要接受政府的指导与协调,使各利益集团及全体社会公众的行为也纳入秩序的轨道。简言之,为了现代化的根本目标,任何个人、任何利益集团、任何行为的责任者和担当者,都必须在秩序之内进行活动,而不应凌驾于秩序之上。
当然,和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秩序本身也是一种运动中的范畴。它既不可能凝固于某一点,同时,从实际运作程序看,它也不可能永远处于平衡状态。它的平衡是暂时的,不平衡是绝对的。但平衡是根本目标,不平衡是为了重新实现更高层次上的平衡的必然阶段,而不是社会成员的追求目标。
反观近代中国的全部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中国现代化的历程之所以步履维艰,裹足不前,或收效甚微,除却无数复杂的内外在因素和机遇的丧失之外,最根本的原因之一,恐怕还在于社会公众一直未能确立现代化根本目标下的秩序共识,遂使中国秩序一直处于不平衡状态。
中国秩序的失衡不始于五四,而是与中国现代化同时起步。早在19世纪中叶,中国现代化酝酿之际,中国秩序的失衡即已显露征兆。早期洋务运动思想家和传统社会的改良主义者,困惑于中国进步与发展的阻力何以如此巨大的客观事实,便已试图从传统秩序的方面寻找内在原因。如果说龚自珍“无八百年不夷之天下,天下有万亿年不夷之道。然而十年而夷,五十年而夷,则以拘一祖之法,惮千夫之议,听其自堕,以俟踵兴者之改图尔”的说法307。依然是“药方之贩古时丹”308,企求发挥传统秩序的调节功能,挽救社会危机的话,那么,魏源提出的“欲制夷患,必筹夷情”“师夷之长技之制夷”以及“款夷”的主张等,在客观上势必引发对旧秩序合理性的怀疑。他说:“天下事,人情所不便者变可复,人情所群便者变则不可复。江河百源,一趋于海,反江河之水而归之山,得乎?履不必同,期于适足;治不必同,期于利民。是以忠、质、文异尚,子、丑、寅异建,五帝不袭礼,三王不沿乐,况郡县之世而谈封建,阡陌之士而谈井田,笞杖之世而谈肉刑哉!礼,时为大,顺次之,体次之,宜次之。”309这实际上是要求改变中国旧有的社会秩序以合乎变化了的现实。
不过,魏源的这种思想倾向一直到清朝末年的新政、君主立宪等运动,虽然对旧秩序的不合时宜性提出过种种责难与建议,但他们并不是要求彻底破坏旧有的秩序,而是期望以清政府为主导自觉协调旧秩序与现实生活中的不适应的部分,促进社会秩序由不平衡达到平衡。
但是,自魏源以来的这些善良愿望毕竟统统化为泡影,于是人们便很自然地从根本上怀疑旧秩序存在的合理性、合法性,怀疑清政府以及此后名实不符的共和政府的能力、诚意,于是有了辛亥革命,有了五四运动。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对现存政府合法性的怀疑无疑是基于善的理念,也就是说,他们依据善的理念作为批判和评价现实生活和现实国家的标准。因此,他们实际上是把体制的各种政治形态的改变和道德目的等同起来。这一点诚如毛泽东后来所分析的那样:“五四运动所反对的是卖国政府,是勾结帝国主义出卖民族利益的政府,是压迫人民的政府。这样的政府要不要反对呢?假使不要反对的话,那么,五四运动就是错的。这是很明白的,这样的政府一定要反对,卖国政府应该打倒。你们看,孙中山先生远在五四运动以前,就是当时政府的叛徒,他反对了清朝政府,并且推翻了清朝政府。他做的对不对呢?我以为是很对的。因为他所反对的不是反抗帝国主义的政府,而是勾结帝国主义的政府,不是革命的政府,而是压迫革命的政府。五四运动正是做了反对卖国政府的工作,所以它是革命的运动。”310
辛亥革命不在本文的讨论范围。关于五四运动,毛泽东实际上已经讲得很清楚,它是中国人民反对卖国政府的一次革命运动。由于政府卖国,因此必须打倒,必须推翻。这里的实质性问题其实是秩序与爱国的内在关联。
无需否认,探讨这一问题的首要困难在于如何确认当时政府的法律地位,其次是如何确认五四爱国运动对政府的指控。关于第一个问题甚为复杂,它实际上是辛亥革命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1916年6月6日,袁世凯在国人的一片咒骂声中死去。不久,袁世凯政府的副总统黎元洪“依法就职”,继任总统。在孙中山等人的强烈要求下,黎元洪恢复了1912年的宪法,召回了旧国民议会的议员,重新组织了内阁,由段祺瑞任总理。对黎元洪的做法,孙中山甚为满意,于是他指示中华革命党通告国内外各支分部:“迨袁贼自毙,黎大总统依法就职,因令各省党军停止进行。今约法归复,国会定期召集。破坏既终,建设方始,革命名义,已不复存,即一切党务亦应停止。”311这就于事实上承认了黎元洪政府的合法性。
不久,黎元洪与段祺瑞闹分裂,黎将段解职。段纠集北洋系军人谴责黎,黎于是同意张勋出面调停。然而张勋又有自己的打算,他不是调停黎段的矛盾,而是借机进入北京复辟了清朝。1917年7月,段祺瑞以共和国再造者的姿态进入北京,平息了张勋的短命复辟,又逼黎元洪让位于副总统冯国璋。
冯、段之间有过短暂的合作,但由于他们分属于北洋系的两大系统,利益的驱使造成他们并不可能真正合作。1918年10月,段祺瑞安福集团控制的国会将冯挤下台,而冯所属的直系集团则以段勾结日本为借口,指责段出卖中国以换取贷款。此后北方政府在人事上还有种种变动,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实际上都是段祺瑞一系控制。五四爱国运动的主要矛头就是针对段祺瑞的所谓北洋政府。
与段祺瑞的北洋政府对峙的是南方的孙中山领导的中华民国军政府。这是中国当时的实际状况,从法理学的角度看,南北两政府都有其存在的法律依据。事实上,不论南方政府还是一般国民,都视段祺瑞的北京政府为一政治实体,否则南方政府就不会和北方政府对等谈判,五四爱国民众也就不会向段祺瑞的北京政府请愿。
就国际地位看,国际社会承认段祺瑞政府是中国的合法代表,出席巴黎和会的代表除了王正廷代表南方军政府外,其余的均应看作北方政府人士。
再看五四爱国运动对北方政府的指控。山东问题是五四运动的导火线,但此事由来已久,甚为复杂。如果站在客观、公正的立场上看,中国拒绝在巴黎和约的最后文本上签字,不仅维护了中国的主权尊严,而且将在国际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有助于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312正如福开森当年所描述的那样:“据美国人之感想,以威总统对于山东问题让步于日本,以期日本加入国际联盟,实属铸成大错。现在群情忿慨,甚为反对。欲图补救,惟有中国绝端拒绝签字之一法而已。若拒绝签字,则较诸保留为尤善,且有助于中国之国际地位甚大也。”“美国舆论及参议院对于巴黎中国代表团拒绝签署和约一事,深表赞同,情意恳至(挚)。”313因此,中国政府拒绝签字是正确的选择。
中国政府代表团最后确实这样做了,这也确实是五四运动的巨大历史功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在五四运动的巨大的革命洪流下,当时军阀政府不得不被迫向帝国主义进行交涉,巴黎和会的代表陆征祥等竟不敢签字和约。这是中国人民的胜利,这是中国革命走上新民主主义阶段的开始。”314
不过,当我们回过头来重新审视一下巴黎和会上中国代表团的全部交涉过程,我们便很容易发现北方政府虽然在是否签约上有过某些犹豫,但自始至终的主流见解差不多都是拒绝签约。先看陆征祥等人于五四运动爆发前二日即5月2日引咎辞职书中的一段话,书中写道:“我国对德宣战,原冀列席和会。乃此次和会办法,迥与历次公会不同,各国列席全权先即大分差等,我国仅得其二,抗议虚掷东流。此祥之无状者一。到会列席,原为提议商酌,冀有公道之主张,稍减利权之损失。所有希望各案,尤以胶州为先,迭次陈述理由,各国多表同意,内有政府之决心,外有国民之后盾,乃力争数月之结果,终违当日之初衷。此祥之无状者二。”315很显然,中国代表团在和会上一开始的底牌就是要收回山东主权,只是由于种种原因而未能实现。对这一结果,代表团和北方政府当然负有责任,但毕竟国势太弱,“弱国无外交”,无法争得在国际上的应有地位。
然而问题在于,既然代表团和北方政府的底牌是收回山东主权,何以称北方政府是卖国政府,何以因此又引起规模如此宏大的五四爱国运动?如欲解释此一问题,愚以为只有从秩序与爱国的内在关联入手。
爱国是一个公民最起码的责任心,如果一个人连自己的国家都不爱,那么他在中国这样文化传统的国度里便难以生存。作为中国的政治家,最大的耻辱莫过于卖国,最高的荣誉也就是看他能否在盖棺论定时获得爱国者的美谥。对于国民特别是青年学生,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情绪,他们可能有时对国内政治麻木不仁,但在涉及国家主权、民族利益的时候,我们的国民,尤其是青年学生便极容易唤起自己的良知。因此我们看到,中国聪明的政治家无不注意以爱国心调动青年的热情。就连蒋介石虽然有意贬低五四运动的启蒙价值和文化意义,但他也不能不肯定五四运动中学生们的爱国热情。316简言之,在不同的中国人那里,爱国的心态是完全不相同的。
青年的爱国**最容易被人挑拨,也最容易被人利用。不过,这种挑拨与利用的外在条件,必定是秩序失范最严重的时候。如果秩序处在最佳状态,政府可以对社会和青年进行有益的指导,社会公众和青年也比较容易以理性的态度利用自己的权力监督政府。依此反观五四运动爆发的那一年,我们看到中国的秩序是近代以来最坏的几个年头之一,不仅南北政府对峙而和谈不成,而各个政府内部利益集团也在进行无休止的明争暗斗。如北方政府,“安福系所组成的新国会,于1918年9月选举徐世昌为大总统,冯国璋遂下野。安福系认为这次选举既能倒冯,又举一个毫无军权实力的北洋元老徐世昌来作傀儡,那末段祺瑞仍居有参战督办地位,无论是出面组阁与否,实际上操纵全部军政大权。但是徐世昌并非甘心作傀儡,他这次能被选出为大总统,亦正是利用直皖二系之争,坐收渔人之利。”317在这种失范的秩序下,青年学生的爱国热情即使不被利用,也往往是一种盲目的行为。
史料表明,五四运动爆发前夕的中国,不仅青年学生不了解事情的真相,即或某些当事者对政府的秘密外交及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关系也不甚了了。“三四月间,上海报界接王正廷专使自巴黎来电云:吾辈提议于和会者,主张废除二十一款及其它秘约不遗余力,推测日本之伎俩仅有二途:曰引诱,曰用武。然皆与正谊公道相违;必不出此。但吾国人中有因私利而让步者,其事与商人违法贬卖者无异,此实卖国之徒也。所望全国舆论对于该卖国贼群起而攻之,然后我辈在此乃能有讨论取消该条件之余地。此电文既披露于各报,于是群情忿怒如触汤火,谓果有是人者,真秦桧再生于今日,李完用复乎中土矣!……时人既读此电,以为此卖国贼必指在巴黎之华人掣专使之肘者,始疑叶玉虎氏,然叶滞在美洲尚未抵欧,于是群疑梁启超氏。”318
作为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正式成员和南方政府的唯一代表,王正廷仅以“推测”之词吁请国内舆论有所表示,可见此时中国之秩序处于一种非正常的状态。而国内人民特别是青年学生当此时真有所表示不是有点儿盲目,有点儿不太负责任了吗?
再看五四亲历者匡互生1925年对五四大游行背景的回忆。他说:“北京各校全体学生本来有一种五月七日举行示威游行运动的预备。不料自五月一日起,由巴黎和会传到北京的消息一天险恶一天。到了五月三日,由几家报纸和几个外国教员宣传的消息,竟说中国的外交已完全失败,并说失败的原因完全在曹汝霖、章宗祥、陆宗舆等秘密订立的高徐、济顺两路借款合同的换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诺’四个大字上面。因为‘二十一条’的承认还可以说是由于最后通牒压迫的结果,在以谋求永久和平相标榜的和会场中可以借着各国的同情把全案推翻的,但日本的外交家却能立刻拿出中国专使所未曾知道的密约换文上所有的‘欣然承诺’四个字来作非强迫承认的反证,来作箝制中国专使的利器。这一个消息宣传以后,北京所有的学生除了那些脑筋素来麻木的人以外,没有不痛骂曹、章、陆等没有良心的,没有不想借一个机会来表示一种反抗的精神的。因空气这样紧张的缘故,大家就有提前举行示威运动的提议,于是五月四日举行游街大会的议案就由各校代表会议议决了。”319
学生的爱国热情诚然可贵,但秩序紊乱之际的任何冲动,即使收到良好实际效果,也很难说是一种理性选择,更不要说被不同派系的政治活动家所利用了。当我们冷静思索巴黎和会的消息是如何转到学生那里去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怀疑北方政府内部运作程序的紊乱、各派系之间的争斗以及他们对学生爱国热情的利用。据当时参与政府处理和会事务的叶景莘回忆说,五月一日,外交委员会决定不签约,由汪大燮、林长民将电稿亲呈总统徐世昌,徐令国务院拍发巴黎中国代表团。“但二日国务院又密电专使签约,院里电报处一个林长民的同乡当晚潜去报告他。三日侵晨,汪、林到会,汪命即刻结束会务,……林密电梁启超并请他通知巴黎中国留学生,他另又通知国民外交协会嘱发电反对。我……打了英文电与上海复旦公学李登辉校长,说‘政府主签,我们在此已尽其所能反对,请上海响应’。这个电的署名是随便写了三个英文字。……傍晚,我到汪处报告,汪问还有什么办法可想,我说:‘北大学生本要游行,何不去告蔡先生。’汪即坐马车从东单二条口赶到东堂子胡同西口蔡宅。蔡即电召北大学生代表于当晚九点在他家会议。”320叶、汪、林的爱国热情我们无需怀疑,但是我们不能不想到作为当局成员当此关头首先想到发动学生,利用学生去实现自己在正常的政治运作中无法实现的政治主张,不仅有悖于自己的政治身份,实际上也多少有点对学生真诚爱国情感的亵渎。
然而,几十年过去了,谁又想到去这样思考呢?究其原因,这正是中国人的爱国情结在起着顽强的作用。似乎只要是为了爱国,采取什么样的手段都不算过分,造成什么样的后果也都无所谓。殊不知,一个美妙的爱国名词有时会掩盖并不一定正义的行为。中国欲真正完成向现代社会的过渡与转变,恐怕在唤起国人的爱国热情的同时,也应该再提倡一点别的什么东西,比如法律、秩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