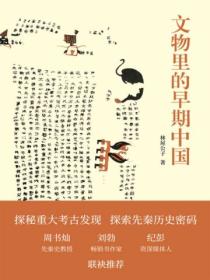34 西汉杀人祭柱铜贮贝器【滇王大墓】
《鬼吹灯》中古滇国与献王墓原型,出土了两类全世界独一无二的文物
西汉杀人祭柱铜贮贝器
《鬼吹灯》的《云南虫谷》卷,讲的是主角胡八一等人去高黎贡山,进入古滇国献王墓探险的故事,留下了一段段恐怖又刺激的经历。那么,这个古滇国是否真实存在,它存在于哪段历史时期,又有着什么样的历史文化呢?
古滇国的传说
《史记·西南夷列传》是最早记录滇国历史的一份史料。
在汉武帝时期,西南地区少数民族部落统称为“西南夷”,西南夷没有形成统一的国家政权,而是由大大小小的部族组成。
这些部族中有的比较先进,拥有君长,民众结着椎形的发髻,农业以耕地为主,其中较大的就有夜郎(在今贵州西部、云南东南部和广西西北部)、邛都(在今四川西昌、凉山及云南楚雄、丽江)和滇国(在今云南昆明一带)。在他们之外,还有一些比较落后的部族,没有君长,民众结着辫子,农业以畜牧为主,在滇国附近有嶲人(在今云南保山)和昆明人(在今云南大理,东至楚雄、滇池一带)。
在这些部族中,只有滇国的出身不平凡。原来当初在楚威王的时候,将军庄蹻带领军队顺着沅水而上,夺取了巴郡、黔中郡以西的地方。庄蹻到达了方圆三百里的滇池,征服了当地的土著。正当庄蹻想返回时,巴郡、黔中郡被秦国攻占,庄蹻无法通行。于是庄蹻只好退回滇池,为了取得土著的支持,他顺从滇人的习俗,改变楚人的服饰,称王建立滇国。庄蹻本是楚庄王的后裔,所以滇国也是楚国的分支。
在战国史料中,多次提到庄蹻这个人物。
楚怀王二十八年(前301),楚军在垂沙之战中败于齐、韩、魏三国联军,楚国统帅唐眜被杀,而楚将庄蹻趁机发动叛乱,攻打郢都,导致楚国四分五裂。大儒荀子还把庄蹻与秦国的商鞅、齐国的田单和燕国的乐毅,并称为善于用兵的名将。
秦灭六国后,派遣常頞开通五尺道,在西南夷地区都设置了郡县,纳入秦帝国的版图。但在秦朝灭亡后,汉朝又舍弃了这些地区,将巴郡和蜀郡作为与西南夷的边界。
汉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年),鄱阳县令唐蒙出使南越,得到蜀郡出产的枸酱,南越人说枸酱来自牂牁江,而住在牂牁江上游的就是夜郎国。因为蜀郡商人与夜郎贸易,枸酱这样才流入南越。南越虽然是汉的藩属,实际上却基本是割据势力。唐蒙计划从牂牁江进攻南越,于是建议武帝收服西南夷族群,设置郡县来管辖。不过因为道路开辟困难,西南夷屡屡反叛,武帝只能暂停对西南夷的经略。
前122年,张骞出使西域,在大夏国居住时见到蜀郡的布和邛都的竹杖,得知来自邛都西面两千里的身毒国。由于大夏与汉朝被匈奴隔断,武帝就派遣使者穿过西南夷去寻找身毒国。使者王然于、柏始昌、吕越人等人到达滇国,滇王尝羌留下他们,并派人帮他们找道路,但却被西边的昆明人阻拦,最终没有找到身毒。不过使者却对滇国风土人情有了了解,滇王也问使者:“汉朝和我们比谁大呢?”后来夜郎侯也这样问过使者。
虽然滇王、夜郎侯系“夜郎自大”,但在西南夷中确实也算强大。使者汇报给武帝,认为可以招徕。等到南越国反叛时,汉武帝通过犍为郡征调南夷土著,且兰君反动叛乱,杀死使者和太守。于是汉军征发部队,灭亡了且兰(今贵州都匀、黄平)。前111年,南越国也被消灭。灭亡且兰的汉军就又灭亡了汉朝和滇国之间的头兰,并且诛杀了不服的且兰、邛、筰等君长,其他部族震惊,纷纷向汉朝称臣,夜郎侯就在此时进京,被封为夜郎王。
之后,武帝就派王然于再次入滇国,劝说滇王称臣。此时滇王部众有数万人,与东北的劳浸、靡莫两国互相倚仗,不愿意投靠汉朝。劳浸、靡莫两国甚至还多次冒犯汉朝使者和士卒。前109年,武帝发兵灭亡了劳浸、靡莫,面对压境的大军,滇王终于知道自己是“滇国自大”,举国投降了汉朝。所幸滇王对汉朝使者一直较为友善,而且本身也具有实力,所以武帝虽然将滇国设置为益州郡,但仍然赐给滇王王印,让他与夜郎王一样,继续统治部族。
《史记·西南夷列传》对滇国的记录到此结束,《汉书·西南夷列传》《后汉书·西南夷列传》也有记载滇国,内容与《史记》大同小异。前109年,武帝设置益州郡,将滇国并入汉朝国土,之后史料不再有滇国的明确记录。在后来汉昭帝、王莽、汉光武帝时期,益州郡夷人多次发动叛乱,但也均被中央政府平定。滇人作为西南夷的一支,慢慢融入了华夏之中,这个神秘古国的历史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的一部分。
古滇国的发现
《史记》中这枚所谓的“滇王之印”,在20世纪还真的被考古工作者发现。
在第二次考古发掘中,在石寨山六号墓出土了一枚金质的“滇王之印”。滇王金印为蛇钮方印,印文为篆书“滇王之印”四个字,边长二点四厘米、高两厘米,现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经鉴定,这批墓葬的年代在战国至西汉时期。
这种金印在考古中也有发现,比如1784年日本就曾出土一枚“汉委奴国王”金印,也系蛇钮;1981年江苏扬州也发现了一枚“广陵王玺”金印,2008年长沙市公安机关又追回两枚“长沙王玺”“长沙王印”金印,均系龟钮。可见,石寨山墓葬就是滇国墓葬,滇国的存在得到了印证,汉武帝赐滇王金印也是信史。
除了金印外,在石寨山六号滇王墓中还出土了一件玉衣,其中包括札片六十九片、坯片九十七片,玉质为和田玉,来自中原。这种玉衣在其他地方汉代诸侯王墓也有发现,最有名的就是1968年河北满城中山靖王墓第一次发现完整的金缕玉衣,滇王墓玉衣的特征与刘胜墓金缕玉衣相似,但穿孔内却没有金属丝或丝线的痕迹,或许这件玉衣并非成品,只是玉衣的一种象征。
石寨山一号墓出土一件正方形钮座铜镜,座外有篆书铭文“畜思君王,心思不忘”八字,四角有草叶纹图案,边缘为内向连弧纹。这样的铜镜,应当也是从中原传入。
整体来说,考古发现能够印证文献记录,古滇国存在于滇池区域和滇东南一带。《云南虫谷》说滇王墓在高黎贡山,但高黎贡山在青藏高原南部,相对于历史上的古滇国有较大差距。
另外,考古也能印证古滇国于汉武帝时受封而消亡,但“庄蹻入滇”的传说却无法印证,因为古滇国的青铜器具从春秋时期就已经具备,直到西汉中期受封前后才开始进入铁器时代。总之,战国时期其文化面貌并没有较大改变,仍然是一支独立发展的古文明。
古滇人的生活
当然,滇王金印、玉衣和铜镜都是中原文物,而更能体现滇文化的特色的,还是古滇国给自己铸造的青铜器。
出土于石寨山十二号墓的一件“杀人祭柱铜贮贝器”,表现的是杀人祭柱的祭祀场面,是目前已出土贮贝器中人物最多的一件。其中共有一百二十七个人物,每个人高三至六厘米。又有一长方形楼房,高十七点五厘米,无墙壁,以两圆木支撑,有两架梯子上下,类似后世壮族巫师祭祀的祠。楼上正中坐着一位妇女,比身边人体型大,旁边有八个人进食,还有一个人手捧食物上楼。楼下有待宰杀的猪、马,还有用蛇喂孔雀和饲养老虎的人。
在老虎与房屋之间又鼓架,悬挂着一面鼓和一件鋍,一人在敲打。房屋对面是村社中心,有一个柱子,柱子上盘有两条蛇,一条蛇吞入一个人的下半身,上半身仍在蛇口外。柱子旁边的木牌上还绑缚一人,另有一个戴枷锁的人,都应当是祭品。还有一些人抱着鱼、头顶箩筐、坐着交谈、骑马赶来,应当都是参与祭祀的人,此外还有身穿异族服装的外来人。在要杀的人牲旁边有两个与人同高的巨大铜鼓,在器盖两边,也各有一个大铜鼓。
柱、蛇和鼓应该都是被祭的对象,蛇在南方少数民族中地位很高,柱代表国家社稷,而铜鼓也是南方少数民族常用的打击乐器。
除了祭祀场面外,石寨山出土的贮贝器还涉及了滇人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六号墓出土了一件战争场面的铜贮贝器,该器身高五十三点九厘米、直径三十三厘米,盖上铸二十二人(现存十八人)与五匹马,滇人将领头戴兜鍪,身穿铠甲,腰束佩剑,赤足骑马,作冲杀状。其他的战士有的拿着矛、剑进攻,有的拿着盾牌防御。战败者为辫发之民,应该就是《史记》中提到的“昆明人”。他们有的被打倒,有的被刺杀,有的跪地求饶,将一场恶战描绘得淋漓尽致。
还有十二号墓出土的一件上仓图像贮贝器盖,盖直径五十厘米,中央有一投贝的圆孔,孔周装饰牧猪、羊图,盖周装饰上仓图,人们把临时粮堆的粮食,用头顶筐运送到木仓房中。木仓房顶呈人字形,身呈井字形。比较有特色的还有出土于十号墓的一件鎏金骑士铜贮贝器,器高五十厘米,盖径二十六厘米,盖中央置一小铜鼓为座,上立一柱,柱端平台上矗立着一位鎏金的骑马执缰骑士。周边环绕着四牛,鼓耳呈虎作攀登状,张开大嘴欲吞噬。
除此之外,青铜贮贝器还有表现畜牧活动、纺织活动、赶集(或进贡)活动、行船活动、误导活动、狩猎活动以及各类图案和动物,生动表现了滇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石寨山十三号墓出土了一件双人舞盘鎏金铜扣饰,高十八点五厘米,宽十二厘米,背面有矩形齿扣。正面鎏金,有两男子双手各执一圆钹,腰佩常见,展臂屈腰,双膝弯曲,作跳跃状。两人均赤足,左脚与后跟相抵,脚下共踏一蛇,蛇张口咬住右边人的右小腿。值得一提的是,这样的钹舞,在山东沂南画像墓和四川画像砖也曾出现。此外,还有六号墓出土的一件四人缚牛铜扣饰,高九点六厘米,宽十六厘米,表现四个人将一头牛绑在柱子上即将宰杀。
除了这类表现社会生活的扣饰外,也有不少表示动物图案的,最具特色的是一种动物搏斗扣饰,比如七十一号墓出土了一件鎏金二豹噬猪铜扣饰,长十六厘米,宽十厘米。其中一豹扑于猪背,后爪抓住猪后腿,前爪抓住猪肩腹,张口咬住猪背,另一豹钻到猪腹下,抓咬猪腹。造型生动,栩栩如生。还有十三号墓出土的一件长方形狐边铜扣饰,高五点七厘米,宽九点二厘米,正面镶嵌白绿色玛瑙管珠及绿松石,边缘一周雕刻首尾相接的狐狸,也非常有特色。
除了贮贝器和扣饰外,其他青铜器虽然并非滇人独有的种类,但也具有自己的风格特色。比如兵器就比较喜欢以人物或动物装饰。
1972年,征集到一件李家山墓葬中出土的猎首纹铜剑,剑长二十八点二厘米,剑刃后部铸人像,发髻高耸,举手箕坐,是典型的滇人打扮;柄部铸有一阔口利齿人像,左手提人头,右手持短剑,反映了滇文化中的“猎头”习俗。石寨山六号墓出土了一件吊人铜矛,长四十一点五厘米,刃部后端两侧各吊一**男子,双手反缚,头发下垂,表情痛苦,大概是奴隶。石寨山十三号墓出土了一件三熊铜戈,长二十三点五厘米,銎背雕刻着三熊,似乎只是仪仗用品。
除了蔚为大观的青铜器外,滇人墓葬还出土了陶、漆木、金、银、玉石、锡、铁等器具,有些也有自己的特色。比如石寨山七号墓出土的一件长方形银错金带扣,前端有弧形空槽,槽上横装一齿,与现代裤带扣非常形似。中央有一只飞虎,右前爪持树枝状物,虎眼用橙黄色玛瑙镶嵌,全身镶有薄金片和绿松石珠,身后为山石云气缭绕状。整个带扣制作非常精美,也是一件非常难得的宝物。
可惜的是,滇国人并没有自己的文字。在石寨山十三号墓出土了一块刻有图形符号的铜片,似乎蕴藏着一些信息,有学者认为这可能是古滇国的图形文字,但这样的符号发现太少,也难以作更多的解读。不过,目前石寨山的发掘尚未结束,神秘的古滇国还有不少秘密,等待我们进一步去探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