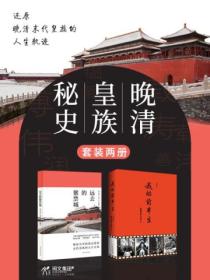第四篇 长春时代
第九章
一、百鬼昼行的所谓“新京”
自从这个长春被污染了“新京”的臭名衔以来,果然它真不愧是个鬼子和汉奸的荟萃之处,立即现出了新殖民地首府的千奇百怪景象来。在街头巷尾到处都可以看到趾高气扬、横冲直撞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兵士;耀武扬威的腰挎日本军刀,足穿长筒皮靴的关东军军官;高插着有关东军特权标志的小旗,坐在汽车内不可一世的日寇法西斯将领;狐假虎威地抱着鸡犬皆仙的优越感而挺胸叠肚的日本人,满身东洋气息,嘴留仁丹胡满口日本式名词的鬼子特务和日本翻译;志得意满,官僚架子十足的傀儡政权中的卖国“新贵”;鸭步鹅行,满口诗云子曰,好像是惊蛰出土的昆虫似的封建残余古董;解开腰间皮带打人,随便开口骂人,扛着轻机枪逛窑子的伪军兵士;见了日本人点头哈腰,满脸堆笑,见了自己同胞便横眉立目,盛气凌人的伪警察;斜挎皮盒子六轮手枪,臂缠特务符号,昂头阔步,虎视眈眈的日寇宪兵,等等。在当时的长春,从整个表面上看,简直可以说是已经到了“有人皆魑魅,无处不肮脏”的幻灭地步。我举当时的几个实例来介绍一下在沦陷当时的悲惨龌龊的情况。
(1)女扮男装的川岛芳子
从来就以和日本帝国主义分子特别是和日本法西斯军官有紧密联系而臭名昭彰的前清肃亲王女儿金璧辉——川岛芳子,这时便也以日寇女特务的姿态在东北大肆活动起来。她在一起初,是以身穿马褂长袍,头戴镶有珍珠宝石瓜皮小帽的男装,以奇形怪状来大出风头,后来索性改成肩列伪将级军官的满金肩章,身穿伪满军服的男装女将了。并且还自称为司令。所到之处,总是照例要带着一群青年鬼子和汉奸以及流氓特务之类,作为她的保驾打手,而神气十足地出入于饭店、舞场之类的公众场所,真是达到了路人侧目的地步。而当时的日伪报纸、杂志以及电影、广播等,更都把她捧得上了天,不是称她为男装的美人,便是把她描绘成为一个“巾帼英雄”的形象,致使在当时一些不知道她究竟底细的人,也盲目地认为她是一个了不起的人物,甚至还有人竟自给她加上了“谜的女杰”的绰号。因此,她也就更加得意忘形起来。因为她完全是凭借着日寇的势力,对于日寇军部方面,尤其是因为她和当时的日本宪兵特务,经常保持紧密的联系,所以当时一般人即使受到她的欺侮和敲诈,也是敢怒而不敢言。所以她也就越发肆行无忌起来。至于一般汉奸,则更是不敢对她稍有一些违逆的了。
在当时的这种百鬼昼行的时代中,特别是这个女怪物闹得更是厉害,因而颇有一些“耳食之流”的人物,认为她确是一个神出鬼没、不可捉摸的神秘存在,其实,说破本是不值半文钱的。只是因为她不但经常乱搞男女关系,并且还善于吹牛说谎。例如,她说曾用跳伞落到海拉尔去诱说抗日的苏炳文将军,致遭其部下枪击而弹头尚留在体内,以及教给日本某师团长骑马等的无稽之谈,来作为哗众取宠的材料,所以她的行动就越发神秘了起来。其实她只不过是一个被日寇军阀尽情玩弄的、堕落到了不可救药程度的卖国女贼而已。
据说,她的结果是在一九四五年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投降以后,便被国民党军队从北京捉到南京去,在惩治卖国女间谍的罪名下,结束了她的龌龊丑恶的一生。
(2)“翊卫军”的兵士
在伪满十四年中,一直担任保护伪宫的这支武装部队,在一起初是被叫作“翊卫军”的(后来改编为伪“禁卫队”和伪“禁卫步兵团”)。名义上虽然是个军,其实在当时,也只不过是拥有约一个营内外步兵的兵力,并且还是由熙洽从吉林各伪部队内拼凑而成。据说,在乍一开到长春时,因为其中的伪军官和伪士兵都是东拉西凑而来,名符其实的乌合之众,所以军官既不认得兵,兵也认不得他们的所谓官长。因此到了长春在正式整编时,有些士兵的阶级,则完全由于自己的委派而成为当时的正规编制的。例如有些比较狡黠的伪军士,便在自己的肩头上,安上一对上士的肩章,那么他就成为一个正式的上士,而那些比较鬼头些的伪兵,也同样是用这种自我任命的方式,得到了二级跳或是连升三级的拔擢。在站岗时,因为各排各班都同样处在杂乱无章的状态中,既没有名册,也没有工作制度和规定,所以就专靠个人的高兴和个人间的互相通融,去执行对我保卫的任务。有些狡黠的兵,为要安然做一夜的好梦,便钻到木板床下去睡大觉,或是藏在不易被人发现的好隐蔽场所,于是到了换岗的时候,便得由他们的上级硬逼那些比较老实的人去替他们打补子。有的还以一顿饺子或是一碗面作为代替站岗的公平交易。于是,一些既无钱又窝囊些的人,有时就得在风雪交加的深夜里,或是在炎日当空的盛暑下,连站两三个小时的岗,也没有人前往替换,有时便不得不抛弃了所担任的岗位,回到兵房来大吵大骂。至于酗酒、赌博和打架、溜号等事,更是司空见惯的家常便饭,甚至还有一些兵士手持步枪或是扛着轻机枪时常到妓馆去寻欢取乐。有一次就有一个兵士因为受到了妓女的慢待,便开枪打死、打伤了五个人,然后就脱下军服塞在水沟内,而把武器背起一跑完事。
诸如此类的情形,在一九三二年伪组织乍一成立的当时,是很多的。等到日本人当了伪军官之后,逐渐掌握了伪军实权,就变成准奴隶兵营了。
(3)刘准尉的企图
在担任守卫伪宫的上记部队中,有个姓刘的准尉,因为他平日吸食鸦片,钱不够花,日本宪兵队内的特务腿子,就想利用他这一弱点,发现一些什么问题来邀功。于是便特意寻找机会和刘接近,不料他俩结识之后,明侦暗访了多少日子,也没有发现出一些什么征候来,但这个为了自己向鬼子邀功不择手段的特务,便在寻找把柄不到的情急之下,想出了一个栽赃陷害的毒计来。
有一天,他故意做出同情刘的样子说:“老弟,现在你既有这样的一口累——指吸鸦片而言——每月队里的那点薪饷是不会够的吧?不想个法子可不行啊……”
刘听了叹了一口气说:“这可又有什么法子可想?”那个特务见刘已上了钩,便更进一步做出想替他设法的样子说:“发财并不难,这就看你的胆量如何了!”
刘认为他在开玩笑,便也笑着说:“你别捣乱了,难道叫我持枪做强盗吗?”
那特务却一本正经地说:“我还能调理你,叫你去干那冒险的蠢事?我对你说实话,我有一个朋友,想要寻找一张宫内府的房舍位置图样,如果你能把它弄到手,我敢保你能发一笔大财。”
刘听了吐了吐舌头说:“这样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并且那样的详图,可叫我从哪里入手啊?”
特务见他心已似乎有些动摇,于是又说:“这样的事,是神不知鬼不晓,又有什么危险可言,我敢保不让你暴露出来就是了。接着又说:你不是成天际在那里服勤务吗?只要你能画出一张可靠的草图就行,我保你能够得到一大笔外财就是了!”
于是这个求财心盛的刘准尉,便煞费苦心地画了一张伪宫概略位置的草图。那特务更同他约好,叫他在某月某日某时,把这张图秘密送到某处,交到一个届时在那里等候接图的人。并保证钱图两交,万无一失。于是这个刘准尉便如约前往,结果是在人赃俱全的事实下,被捉送到伪法院,被判了一个无期徒刑。当然这个特务,因为破案有功,受到了相当的褒赏。
二、卖国密约——伪执政的代价
日本帝国主义对待汉奸,是一贯使用放高利贷的方法来劫持他们的。首先是有效地采取了欲取先予的偷鸡撒米方针,上赶着先把钱给你送到面前,等到你要伸手去拿时,他便又会另换一副面孔,不但是毫不留情地先从其中扣去几成的所谓“利息”,还用惊人的盘剥方法去进行无止境的剥削。而这个借钱的人更是无法摆脱这种利上加利,利中滚利的反复剥削的了。于是只得干脆落到他的债务圈子内,永远也不得翻身。日寇就是用这种阴狠毒辣办法来对待我的。
当我在一九三二年三月到了长春,当上了所谓伪执政后,当时的日寇关东军司令官本庄繁便立即摆出债主的架子来,经过郑孝胥之手,把一张彻头彻尾的卖国密约拿到我的眼前,不但是把东北所有的矿山、港湾、航运、陆运(铁路交通)等一切的权利,罄其所有地断送到日寇之手,更从广义的方面来看,真可以说是上自天空,下至地底,完完全全都由我全盘托出,双手奉献了。同时,在其中也包括了日本帝国主义移民政策,以及日伪之间的所谓经济同盟。此外,如用日本人来充当伪满的最高顾问,等等。像是这种包罗万象的卖国密约,如果拿它来和袁世凯的“二十一条”卖国条约相比,那么,那个曾经引起全国人民的无比愤怒和遭到世界各国人民舆论斥责的“二十一条”,和我无条件承认的这个卖国密约有着天地之别呢!
本庄繁所提出的这个要求,也就是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以正式承认我当伪满洲国执政,来提出这一带有要账式的交换条件的。而我呢,也就在患得患失、卖国求荣心理下,丧心病狂地整个答应下这一罪恶要求,以致在以后连续而来的一步紧似一步的种种卖国殃民协定,全都是从这里脱胎而出,只不过是把其中的内容从密约变成正式公约,从笼统的章句,变成为更具体的条项,从非正式的东西,变成合法化的证契而已。
像是后来在同年(一九三二年)日寇关东军司令官兼驻伪满特命全权大使武藤信义和伪国务总理郑孝胥之间所签订的所谓“日满议定书”,则是把上记卖国密约做了合法化的正式手续,并把它添枝加叶地具体实现了。再加上所谓的“日满共同防卫”,那更是由我首先点头承认了日寇在东北的永远驻兵权利。因此,这不仅出卖了东北人民的一切利益,而且更由于我的甘心情愿,才把这块祖国的神圣领土,双手拱献于日本法西斯强盗,任其把它当作从事疯狂侵略的军事基地,不独我东北人民在过去十四年长期呻吟在日寇的皮鞭和刺刀之下,并且还使日寇充分利用了这块军事基地,而更进一步地侵略我们整个祖国的大片国土,大量屠杀了我国的父老兄弟姐妹,终于使自己的祖国受到了一千万以上的宝贵人命牺牲和五百亿美元的严重物质损害。还不止于此,就连日寇的侵略越南、缅甸、菲律宾、爪哇以及威胁苏联的罪恶活动,也都是因为它充分利用了这块军事基地上的人力、物力、财力所造成的。足见这个出卖祖国全东北人民利益的罪恶协定,真可以说是伪满十四年来一切罪恶的总出发点,而这个总出发点上的罪恶者本人就是我!
三、到长春以来的生活一斑
明明采用的是伪执政的制度,可是偏偏又有了什么伪大同的所谓年号;明明绝对不是“复辟”,可是偏偏在当时的敌伪之间,却有很多人把我称为“皇上”。诸如此类,真是一种荒诞离奇的现象。因此,就连我在当时长春伪执政府内的生活,也当然不能出乎上述的矛盾情况之外,总是有着两重或是三重的性格。
固然,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在当时是承认我是个伪执政的了,可是除了公式,在那些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当中的某些人,也还是公然地对我以“皇上”相称。至于在那帮封建残余者之间以及在我家庭之内的小圈子里,那更是一切都要率由旧章的了。请想一想:就连当我狼狈遁入北京日本公使馆的时候,以及在天津做“租界寓公”的时候,尚且没有一天丢下过“皇帝”的臭架子,何况是到了长春,当上了伪执政,尽管当时的我是一个纯粹的大傀儡,但总算是又登上了政治舞台,在某种程度上,又可以公然地摆出统治者的臭架子来,并且在那时拿我当作求差混饭对象的寄生虫豸,也比过去繁殖了不知有多少,当然在拍捧齐下的生活中,也就使我身上的“皇帝”气息越发浓厚起来。像是那些向我称臣跪拜、歌功颂德、献功邀宠以及卖身投靠等应运而生的人物,真如麻蝇聚粪一样,都纷纷围绕着我乱乱哄哄地闹着。不用说,在我那称孤道寡的生活中,是会越发增添了不少活气的。同时,也使我那以帝王自任的雄心同吹肥皂泡一般越发胀大了起来。不过是,我在当时的所谓“君主”威风仍然是被局限于在我那家庭的小范围内,只能是袍笏登场地饱尝那身为傀儡的滋味,而未能达到真正专制魔王的独裁野心。不论当傀儡汉奸,或是当专制魔王,总之,这都是背叛祖国人民和危害祖国人民的罪恶行为。
(1)我钻进新鸟笼子
在我爬上了头号汉奸——伪执政的交椅后,有一天,我忽然逸兴遄飞地想要到当时长春的唯一公园(西公园)——即现在的胜利公园去散步,于是便同我的妻子和两个妹妹坐上汽车逛公园去了。不料,我这种不告而出的举动,却惊动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宪兵和警察等,他们便立刻大惊小怪地慌作一团,就在刹那之间,把这个公园完全包在严密的警戒网中。成群结队的汽车,一批一批的敌伪当地官吏,都一齐由四面八方向这个公园“杀”来。我看到形势不对,便急忙坐汽车回伪执政府。从此以后,便在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善意”的压力下,我重又收入到长春的“新鸟笼”内,除了所谓必要的正式出门,一直到八·一五为止,我从未自由地出过这只“鸟笼”一步。
(2)不揣其本地制造党羽野心
我为了蓄养我的实力,曾想出了不少“不揣其本,而齐其末”的方法,想要替自己培植出一批专为我个人效死的武装心膂股肱来,于是就干出了不少件既卑鄙可恨又愚蠢的事情来。我想先从比较远些的事例说起。
例如,在九一八事变后,我便想起了曾经在一九一七年到北京亲身参加过张勋叛变的所谓复辟事件的张海鹏来。这时张正带兵驻扎在东北洮辽一带。恰巧这时,我的本家侄子宪原、宪基刚从日本士官学院毕业回国到天津来见我,并说他们将要往东北去投奔张海鹏。我听了认为良机莫失,便用黄绢写了一封所谓的信,信中大意是勉励他要好好地静俟时机的到来,俾能帮助我进行复辟的罪恶活动。并找出一些行贿的所谓礼品一齐交到宪原等之手,使其面交张海鹏。后来宪氏兄弟见到了张海鹏之后,便都被留在他的部队里,当上了军官。
在一九三一年,日寇甲级战犯土肥原和我做了勾搭后,又有在天津日本驻屯军通译官吉田忠太郎向我建议,说现在有几个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毕业的军官留学生都在东北,我可以给他们写一封信鼓励鼓励他们,在将来能给“新国家”效劳,并说现有一个叫森赳的日本军官将赴东北,可以托他给他们带去。
我听了这种实获我心的“高见”,当然是高兴异常,便又拿出黄绢来,本着下诏书的心情,给宪原、连组、郭文林(连为善耆之孙,郭为蒙族)等写了信,叫他们伺机帮助我,并“封给他们以上校的空头军衔,还送了他们和当时蒙古贵族凌升以一些礼物,都交森赳给带去了”。
除了我在当时曾极力拉拢想拼凑一些能给自己卖命的打手,以后在伪满更想进一步培育一批自己的嫡系炮手,于是,便利用了伪执政的地位,从自己的亲属和亲信之中选出了十名自认为可靠的“可造之才”来,而把他们送入了日本士官学校里去留学。
我现在先介绍一下这些位所谓可造之才与我的关系。
我的弟弟溥杰,我的内弟兼妹夫郭布罗·润麒,我的叔伯兄弟溥佳(即金智元,伪执政府侍卫官),我的堂侄毓峻(伪执政府侍卫官),我的使用人祁继忠,熙洽的外甥马骥良(伪执政府侍卫官),张彪的儿子张梃(伪执政府侍卫官),我的族侄裕哲(伪执政府侍卫官),赵国圻(伪执政府侍卫官),还有所谓非“嫡系”的“杂牌”留学生庞永澄、孙经纶和孙文思(孙其昌的儿子)共十二个人。
不过是,这些位在当时所谓的陆军将校候补生,因为不是所谓皇亲国戚,就是官僚子弟的缘故,都是纨绔积习熏染甚深的人物,所以到了毕业的时候,只能剩下九员“大将”了。后来这帮人在毕业回来后,都被当时的伪军政部给吸收了过去,都被正式编入在伪军之中,然后并把他们分散开来调到伪军的各部队去,结果是并未能达到以我为中心从事工作的预期目的。
此外,除了我由天津原来带来的十几名“保镖”,我还在当时从蒙古、北京等处陆续共招来了三百来名青年,编成一支分三个队的所谓护军。不过这种编制是和过去在北京清宫里的护军不同,并不是皇宫警察的性质,而是一种变相的陆军,不但拥有步枪、轻机枪之类的武器装备,就是教育训练等,也都是按照正规陆军的方式去施行。当时任该伪统领的是伪上校郭文林和三个伪少校队长,其中的两个队长都是拿我的亲信来充当,并且还使我那心腹喽啰头目——伪执政警卫处处长佟济煦亲自管辖着这支伪部队。当时,对这个队的士兵所灌输的思想教育,都是以我为中心的绝对奴化教育,同时还时常使佟济煦到队里进行所谓精神讲话,对他们进行尽忠于一人的封建反动教育。一方面我还经常用赏赐的名义给他们以野猪、鳇鱼、酒肉之类的东西,作为邀买人心的钩饵。还把其中认为成绩优秀的人,选送到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去进行所谓军事上的深造。固然日本帝国主义者,很快就发现了这个“漏洞”而把它堵死,但是我也送去了两批一共四五个人到了日寇的“军阀育成所”——陆军士官学校。
不过是日本法西斯强盗们是绝对不会让它的傀儡——我,能够制造自己势力的。
恰巧有一个星期日,当这批变相的陆军放假出营的时候,在长春的公园内,因为游船的关系,起初是和一个拒不卖票的朝鲜人发生了争端,后来园中的日本人群起干涉并围打这二十几个人的“护军”。后来日本鬼子越聚越多,于是发生了团体的斗殴。日本鬼子放出的警犬,也被“护军”踢死了。因为这些“护军”都多多少少会一些我国的拳脚之类的武术,所以便以绝对劣势的少数人把他们打得落花流水。这时,日本人当中还有两个横行无忌的日寇关东军参谋也受了轻伤。因此,就给日寇关东军提供了寻衅的借口。后来,日本宪兵队用汽车从伪宫内府里逮捕了很多的护军,都给关押在宪兵队内,进行了惨无人道的严刑酷讯,如灌凉水,用皮鞭抽打,并迫令他们**跳舞等等,而日寇则围观取笑。并且还打算把这件事扩大到“反满抗日”的方面去。所以当日寇一把这顶“大帽子”祭了起来,我这个“畏日如虎”的伪皇帝便沉不住气了,只好一再向吉冈安直(关东军参谋、伪帝室御用挂)哀求,乞其转圜了。结果是由吉冈代表着日寇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向我提出了几项要求:①撤换负责人;②驱逐肇事人出伪满“国境”;③派人向关东军两个参谋道歉和慰问;④保证今后永远不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当时我只有一一照办,速求了事的了。
结果是,日寇对我尚算“开面”,把关在日本宪兵队的伪“护军”放了出来,于是我就抱着斩马谡的心情,以行政处分的形式处分了佟济煦,撤换了一个伪队长并把那些“肇事”的人全部驱逐出“境”,才算是把这件事勉强平息下去。
事件固然在表面上,总算是以我这方面的屈服而告终,但日本帝国主义分子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是一步紧似一步把对于我这个唯一的基本武装小团体做了再接再厉的进攻。结果是不但把队里的步枪之类的武器全部收缴了去,而换上了仅够支撑门面的为数有限的手枪,并把这个陆军式的部队编制也给改变为纯伪宫中警察的组织,最后索性把伪宫内府警卫处长也给换上了日本人长尾吉五郎。不仅如此,连士兵也逐步替换了新人——他们认为可靠的人。
(3)我当时的日常生活
在我乍一尝到当傀儡头子的滋味以后,固然还认为不如当专制皇帝过瘾,但由于饥者易为食的心理上的关系,也还觉得“慰情聊胜于无”而有些勃勃的兴致。同时在伪满初期,还有许多溜须捧盛的汉奸伪官吏能够随时地来见我。因此,我尚能每天从早晨九时起,便由我所住的缉熙楼到勤民楼去勤勉一次。可是后来,情况变了,我受日寇、特别是吉冈安直的限制,所以后来除了每周定期的伪总理和伪参议府议长向我做报告,那些溜须捧盛的伪官吏便不能随便来见我了。所以除了在每次所谓正式接见和“特任式”,并关于一切所谓典礼上的重要事情,我对于勤民楼的兴趣,也就一天不如一天了。因而也就以歪就歪地大倦其勤,同时也逐渐对于睡早觉就相对地感到了兴趣。后来索性不每天到勤民楼去“尽勤”了,反正是到那里去,根本也就是一种形式,什么办公不办公,只要能按照日本关东军所决定的事项,由它所派来的高级腿子——吉冈安直,把他写在纸条上的话照方抓药似的念一遍,就算尽到了头号汉奸的职责。此外,对于“火曜会”(详见后篇)所给内定的,更由伪国务院和伪参议府所通过的伪政策法令等,只要是它们认为应该叫我签名的,我给签上,应该需要我“裁可”的我就给写上一个“可”字,就算是我百分之百地完成了自己的义务!
我因为既然无须乎到勤民楼去走形式,那么,在我的寝室内,甚至有时我坐在恭桶上,又何尝不能尽自己的“职责”?本来要我签可的东西,只要在上面涂一个“可”字就行,差不多连内容都可以不必去看,并且也无须去看,因为看也等于白费工夫和徒劳自己的眼睛。所以我有时候,就坐在便桶上,从用人的手中,把一沓一沓的“裁可”文件接过来,便用他给蘸好了的墨笔,写个“可”字,就算是完事大吉,负责处理完毕。
不但是我积极地卖国投敌曾给我祖国人民招来了不可估计的灾害;就是我在消极尸位的时候,也不知由于我的大笔一挥,曾给我们祖国东北人民造成无限灾祸。不论积极也罢,消极也罢,我的罪恶是百死不能赎的。因为灾难是事实,是铁一般的无情事实!
自从我开始“倦勤”以后,我的迟眠晏起习惯便逐渐有了发展。最后则竟自到了非至深夜一两点,甚至三点不睡,早晨则是除了有事情,非到十时或是十一时前后不起,每天两顿饭的时刻也没有一定,“早饭”大约是十二时至下午一二时都不一定。并且到了四五点钟的时候,还得睡一个“中觉”,不到晚上七八点钟是不肯离床的。因此,我当时的所谓“晚饭”差不多早者九时或十时,晚者非至十一十二时,一般人在好梦正浓的时候,我才能吃。
所以,在当时甚至还有人误会我吸食鸦片。我认为这种误会,并不是无因的,因为这种俾昼作夜的生活,就是在旧社会中也确是除了鸦片瘾者,是太少见的。
此外,我在当时,还沉湎于佛学之中。因此,我就经常吃起斋来了。而后由于我对于佛学的造诣逐渐加深,我的吃素次数也就相对地有了增加,到了最后,简直是到了见肉便皱眉的程度。那时我所爱诵的有关“轮回思想”的诗,如:
“人吃死猪肉,猪吃死人肠,猪不嫌人臭,人反道猪香,彼此莫相啖,莲肉生沸汤”等之类。
总之,一句话,在当时,我几乎认为吃肉,简直就是一种罪孽,甚至迷信地认为自己所吃的猪肉,就可能是自己死去的亲人今世托生为猪的肉。所以在当时,在我的食桌上,差不多嗅不到荤腥的气味。
我那时对于厨房的工作员也是极端苛刻的。经常是像防贼一般防范他们赚我的钱,除了使用比较亲信的仆从,对于上市买菜的人,做特务式的秘密跟踪,有时还用间接补助的方法,向我的弟弟妹妹们打听:你们买一只鸡是多少钱哪?或是你们买一斤鸡蛋得多少钱哪?等等,并且给予这些厨房工作人员的工钱,也是限定在很低很低的框子内,特别是在伪满末期物价飞涨的时期,我所付出的工资简直还在一般普通工资之下。不但如此,除了在给我做饭做菜时,经常派人去监视他们的清洁状态如何和严稽其有无轨外行动,每当我认为所做的菜不很可口,或是有什么不洁之物混在菜里时,便一声令下:罚某人某人几块钱。当然在这种罚款的数目来说,既没有明文的规定,也没有什么法的根据,只不过是随心所欲地冲口说出几个数目字而已。由于这种凭我喜怒的罚款,是时常有的,虽然也有时因为某某做的菜很不错,而得到奖金若干的时候,不过是,遗憾得很,总是奖的时候少,罚的时候多,结果仍是固定在罚不敷奖的状态之中。但是过去的那些位大师傅,也差不多摸着了我的脾气,他们并不以受罚为意,也不以每月挣钱少为忧,因为他们是自有弥补这一漏卮的比较有效方法的,那就是,他们可以时常利用“请愿”的方法,通过在我身旁的使用人的嘴,编出一些理由来,向我请求补助,在当时把这种“请愿”叫作“求恩”,我对于这一点,倒是差不多有求必应的。这也就是工钱既少,罚款又多,规矩又严,监视又紧,而他们尚能勉强和我相安无事的原因之一。
除了我当时的饮食起居确是处处与常人殊,还有一样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我的嗜药成癖了。这种所谓嗜癖,并不专专限于服用一方面,而是更兼有聚集收藏之癖的。在长春虽然已经没有像北京清宫那样的御药房以及太医院之类,但也有我自用的汉药柜和西药库以及儒而兼医的老侍医和一呼即到的所谓西医给我做着日常的伴侣。在我的那个汉药柜内,不但是把差不多的药材都准备得齐全,几乎每次抓药时,都可以用不着出门到汉药铺去买,就可以供我随时的受用,甚至在伪满末期,普通药铺的缺货如犀角等等,我都是绰有余裕,无须担心。至于西药,不论是内服、外用,或是注射等等,也是应有尽有,丰富异常。特别是德国“拜耳”的药和日本的药。我就是这样以兼收并蓄死藏为乐的。
在我服汉药时,不但是自己经常擅于改窜大夫所开的药方,甚至还有自开自饮和给别人硬开药方的时候。对于西药则主要是专靠德国拜耳药厂所出的小册子,来作为掌握西药的最主要根据,对于医生的意见,反倒把它列在聊资参考的地位。并且我还打破了一般人所常爱说的恨病吃药的范围,而是进入了无病吃药的特殊范例之中,光是注射荷尔蒙就是一天一针地注射了不计其数。至于帮助消化,健体卫身的药,更是几乎无日或离的了。
总之,在当时药类对于我,就几乎同我每天不能不吃饭、不喝水差不多,它已成为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不能离开的必需品之一。
此外,我还想把我在当时的生活之中,最为愚蠢得可恨同时又奇怪得可怜的一个突出的实际例子作为本项的最后介绍吧!
有一个时期,我因为迷信于坐禅的方法,便时常关起房门静坐,因此,便最怕在附近发生一些什么杂音。不过是在那时,我在庭院附近养有一只仙鹤,一般服侍我的人,当然是在“楚王好细腰,宫中多饿死”的当时环境下,人人都屏声息气地连咳嗽一声都怕惊了我的“入定”。可是仙鹤却不然了,它不但不懂得保持极端的肃静,反倒时常地以“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的高鸣,毫不客气地来惊动我。我于是就派几个专人,轮流地去监视仙鹤的“轨外行动”。我并且还给他们定出严厉的罚则来:如果鹤鸣一声便罚他们五角钱。因此,这几位“控鹤专员”都吃了苦了。想要用布条缠上仙鹤的长嘴,又怕受到“谋杀仙鹤”的罪,不缠上吧,仙鹤是有随时引吭长鸣的“天赋自由权利”的。不过是,他们却有“穷思通”的好窍门的,他们终于在几次受罚之后,掌握住鹤鸣的生理惯态,于是就在长期的积累经验之下,得到了一伸颈就用小棒敲的科学方法。从此这只仙鹤则是饱受了缩颈哑子之苦,而我则是得到了万籁无声的参禅妙谛。
四、国际联盟调查团
在一九三二年三月,伪满傀儡政权刚一成立之后不久,便由当时的国际联盟派来了以李顿为首的调查团到东北来做调查。
固然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操纵下的这个调查团到东北来是别有用心的,并且尽管在西方国家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是存在有某种程度讨价还价的隐蔽意图在内,但不论怎样说,在当时到东北来做实际调查的这个国联调查团,则是以调查日寇侵略罪行为任务而来到东北从事实地调查的一个国际团体。可是当时的我却完全和日本鬼子走上了一条道路,简直是不顾一切地给日寇当上了传声筒和宣传工具,竟自甘心在日寇的辔勒之下,厚颜无耻地向调查团说出了弥天大谎:硬把手执武器侵入自己祖国东北神圣领土的狗强盗说成不是侵略,而是仗义执言,并死也不肯放口地说日本军队纯粹是为了替东北三千万人民来扫除张氏父子的秕政而兴的“义师”。所以东北人民才如“拨云雾而见青天”地建立了满洲国这块“独立自主”的新“王道乐土”。同时那帮汉奸大官也都和我一样,也都是各如其分地在“一德一心”的鬼名词尚未出现在伪国字典以前,就把“一德一心”的实际行动,活灵活现地表示出来了!
在当以英国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调查团来见我以及到伪满各处调查时,都有日寇关东军将校跟在一起,寸步不离。这说明日寇是一面利用汉奸,一面是贼人胆虚,防范极严,恐怕走漏了日伪的罪恶秘密。而我更是一意仰日本主子的鼻息,而欺骗了国际联盟调查团。
这只能说以我为首的这帮汉奸,难道不是为了要去舔一舔日本鬼子杀害自己同胞的鲜血残渣,才这样丧心病狂地拼命给民族敌人打掩护?这不是完全成了日寇的忠实走狗,甘心和全国人民以及全世界爱好和平的、正义的人民为敌吗?
当然,凡是帝国主义国家,都是一丘之貉的坏东西。日寇想要独占我国的东北,把它变成为它的殖民地;而西方帝国主义国家也是满心里不愿意日寇独吞这块肥肉,但又在扶日反苏的一贯阴谋方针下,更不甘心替那腐朽无能的当时南京政府去过分得罪那另有妙用的日本帝国主义;并想能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酝酿出一种两下让步的缓和空气来,好形成它们牺牲中国利益,给日本一些便宜,因而另外制造出一个在它们操纵之下的“国际共管”新局面来。而达到既可抑制日本愈闹愈甚的疯狂野心,又可把东北这块所谓的肥肉用分赃的办法,借以维持一下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均衡状态。
话虽如此,但是我这种帮助日寇来共同欺骗国际联盟调查团的态度,则确确实实是一种利敌卖国的严重罪恶行为!
不但如此,而后我还更进一步地忠实执行了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罪恶侵略政策,更卑鄙无耻地用我的名义派丁士源到日内瓦去替日寇的侵略行为做颠倒黑白的辩护,硬把日寇将东北攫为己有、变成为纯粹殖民地这种铁一般的事实,说成是“日本并没有干涉满洲国的内政”,还把傀儡的汉奸政权说成为“独立自主的新国家”。并且要求他们承认伪满。像是这种丧尽民族气节、背叛祖国人民到底,蓄意欺骗世界人民的滔天罪恶行为,除了拿甘心卖国求荣,不择手段来做解释,是绝对不能再有其他的话可说的。
特别是日寇为什么要在国际联盟调查团到来以前,就手忙脚乱地要把伪傀儡政权快快地组织起来?因为不如此,等到这个国际联盟调查团来到之后,日寇的这次侵略行为便会完全站不住脚,日寇便没有在世界舆论面前做狡展的余地。这样,即使西方帝国主义国家并不是对于中国有什么“仗义”的好心肠,那么最小限度,也不会让日寇从那时起就从心所欲地把这块殖民统治地盘**达十四年之久,至不济也能使我东北的父老兄弟姐妹少受多少地狱般的痛苦。同时也不至于使日寇安安稳稳地把全东北利用为它的有力军事侵略基地,那么,对于我国的全盘侵略行动,也不会竟自到了那样严重的地步。回想起来,汉奸的帮凶罪恶,特别是我的助桀为虐的罪恶,真是百死莫赎的滔天大罪!
我常想只要把我前半生中的无数罪恶,挑出其中一件来,就充分够得上被处极刑,可是现在的我,却在祖国人民政府的父母般的人道主义待遇下,过着学习改造的认罪自新生活,真使我不能不痛定思痛地来恨我自己的过去,痛悔我过去的前半生。也使我不能不想到这里,有时就忍不住地要流下那惭感悔恨交并的泪!
祖国人民,我真是万万分对不起你们!
我真是万万分没有向你们抬起头来的勇气!
真是欲报之德,除非是“春蚕到死丝方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