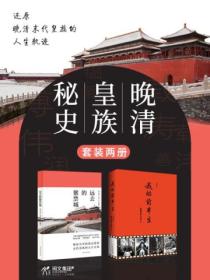第四章 开始正式走上了犯罪的道路
一、张勋[14]复辟
是的,当张勋背叛中华民国实行复辟罪恶勾当的时候,是在一九一七年七月一日,正当我十二岁的时候。
固然在当时,我还是个小孩子,并且也确是被那个臭名千载的“辫子兵统帅”——张勋,重把我抱上了皇帝的宝座;固然是在那场见不得人的丑剧之后,也曾听到陈宝琛对我说:“段祺瑞认为这次的复辟,都是由张勋一个人给制造出来的。是他来逼迫‘清室’的孤儿寡妇,并非出自‘清室’的本意。因此对‘清室’的‘优待条件’,仍可一仍其旧。”但是平心来说,我这个小孩子,虽然不是自己要往“宝座”上去爬,但在当时,我对张勋那次所制造出来的既成事实,却并不是无动于衷,更不是未曾欣然色喜,总之,在当时的我,早已经成为一个“半拉子”的封建统治者了。
张勋
大约是在张勋叛国的前一年吧?年月日我现在虽然已记不清,但是我还记得,当他那次到北京来时,曾到清宫见了我一次。那时我因为要接见陌生人,不知应该说些什么话才好,于是我那陈宝琛老业师便教导我在见他的时候,应该说什么样的话。当张勋见我时,仍然是跪拜称臣,我也就按照老师的传授,一五一十地向他说了几句慰劳的寒暄语。果然张勋听了很觉高兴,并对我的这种慰劳表示了感激之意。为什么张勋会如此呢?因为他自从到了民国之后,依然没有把他的那条辫发剪掉,借以表示他始终忠于一姓的决心。不过是,当袁世凯在世的时候,他确曾一贯忠心耿耿地替袁来效力,自从袁死之后,他才毫无顾忌地要拉下脸皮阴谋复辟的。
关于复辟的阴谋这件事,张勋曾在过去的所谓“督军团代表会议”上就已经秘密做出了决定。到了一九一七年,因为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在政治势力上的尖锐摩擦,冲突已形成表面化,张勋遂趁此机会以调停黎、段之间的纷争为借口,别有用心地率领着他部下的一部分军队来到北京。过了几天之后,他便出人意料地宣布了清朝的复辟。于是那些自命为前清遗老、专门梦想开倒车的封建余孽,如康有为、刘廷琛之辈,都纷纷麇集到张勋的周围,打算浑水摸鱼地讨个重要职位,重温一下尚未过足的封建官瘾。当时给张勋当参谋长的万绳 ,也是主张复辟最有力的一个,这就更给这帮猎官的“遗老”,打开了一个“方便之门”。
在七月一日那天,张勋突然气势汹汹地带兵进入清宫,并纠合了很多“逐臭之夫”声言要见我。我这时正在毓庆宫读书,不过陈宝琛却是早已与闻其事,便胸有成竹地告诉我说,张勋的来意,就是打算实行清朝复辟,并且还反复地嘱咐我,须立即应允他的要求。我在当时虽然还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但听到这样的话,心里也觉得很高兴。因为我从小时起,一直在受着封建统治的专制毒素教育,再加上宫中的一切生活环境和物质条件的影响,所以我一向就是把国家看成是爱新觉罗氏祖祖代代传留下来的一姓私有物。何况那反动阶级本质的烙印,在当时已经深深在我头脑中起了相当的作用,所以尽管我在当时还是个小孩子,但对“清朝复辟”这四个字的意义,已能从心里感到有一种不由自主的欢欣激动。
于是我就回到了“养心殿”,见到了张勋。他见了我之后,便像是逢场作戏似的伏地向我叩头,并大言不惭地对我说明了来意。大意是,由于中国近几年来的政局混乱,民不聊生久矣,所以人心现已倾向于恢复大清,实行帝制。并说:“只有这样,才能重拯斯民于水火之中,而使之重登于衽席之上。”并着重表示:他代表各省官民一致拥护我重登“大宝”。又说:当他在徐州召开会议时,各省督军都已表示赞成复辟。于是我也就表示答应了这一要求。据说,张勋还见了宫中的四位太妃,对她们也曾重复了这一篇话,当然,那四位太妃更都是求之不得地表示了认可。
然后便由张勋和他的羽翼以及那群苍蝇般的遗老,就像分赃一般,用超快速度决定了伪内阁的名单。经我草草过目之后便公布出去了。我记得其大致内容是:张勋任伪内阁首席议政大臣兼领北洋大臣。其他如王士珍、袁大化、陈宝琛、雷震春、张镇芳、刘廷琛和梁敦彦等人,也都当上了伪议政大臣等职位。不料正在那短短十一天的开倒车迷梦方酣之际,段祺瑞就在马厂誓师进兵讨逆。而这出复辟的历史丑剧,也就在讨逆的几声炮响中匆匆地闭了幕。
张勋虽然也曾调兵遣将地做了一连串的困兽之斗,但在那邪正相争大势所趋之下,只能是节节败退,缩入到北京城内。
这时在南苑的空军,也起来协力于对张勋的讨伐,并且还先声夺人地在清宫投下了三颗炸弹。一颗落在御花园内水池中,将池子炸毁了一小部分;一颗落在西长安街的“隆福寺”外——“储秀宫”东墙附近,未炸裂;一颗落在“乾清门”外,炸伤轿夫一名。
尽管在这次轰炸时,据说是因受到段祺瑞的劝阻,未继续大肆轰炸,但是,对于当时的清室,以及所谓的王公大臣,确是给予了精神上的一个大打击。
当听到炸弹声时,我正在书房和老师谈话,我当时心中非常害怕,太监们便簇拥着我急忙回到“养心殿”寝室内隐蔽。在当时,既没有防空的设备可言,更没有关于防空的起码知识,只是把窗外遮太阳用的长竹帘(宫中叫作“雨搭”)放了下来,以防炸碎玻璃伤人而已。那四位太妃,也都在各自的宫殿里,被太监扶掖着藏在寝室深处。据说荣惠太妃竟躲匿在桌子底下。至于所谓的各王公大臣,也都在事后变颜变色地陆续跑到宫中,向我和太妃遥致问候之后,便又都一筹莫展地各自回家。
不到几天之后,段祺瑞指挥下的讨伐军便乘胜攻入北京。当那些叛军缩到南池子张逆住宅附近,做最后挣扎的巷战时,我和四位太妃也都在各自寝室中,为拂晓攻击的枪炮声所惊醒。于是我们便又各自在太监或宫女等乱作一团的情况下,再把挂在窗外堪称唯一“防御武器”的“雨搭”放了下来,据说这次是为了防御流弹。这时,宫中的内外各门都紧紧关闭,以至外面的消息也一概杜绝。只仗着当时的“护军统领”毓逖,经常通过“奏事处”太监,把一些赝造战况传了进来。其实,当时的真正情况,毓逖也同样无从得知,只是为了“安定人心以防意外”起见,特意诌出一些迎合当时反动心理的假消息而已。例如,他报告说:“张勋获得全胜,段祺瑞的军队全被歼灭。”果然我和太妃听到这样“喜讯”之后,便都高兴异常。于是那帮见缝就钻的太监,便又造出一些应运而生的“神话”来。例如说:“怪不得在今天早晨枪炮还没响以前,就听到有两只乌鸦在养心殿房脊上,一问一答地叫唤着。原来它们是给‘报喜’来的。”又说:“今天早晨,听到在‘养心殿’的‘西暖阁’后面,有叮叮当当盔甲的声音。”接着更自圆其说地继续自加注释道:“这就是‘关老爷’(在‘西暖阁’内供有关羽像和‘青龙偃月刀’)出来‘显圣’,是为了要保护‘万岁爷’和四位‘老主子’的!”等到下午外面枪声渐次平息下来之后,太监们便又传出了新的谣言说:“在御花园钦安殿内所供的‘关帝’和‘赤兔马’身上都出了汗,这也是出来‘显圣’,四处奔驰保护累出来的。”当然我和四位太妃,是不会相信这种暗合心意的神话的了,于是就在惊魂甫定之下,又从各自的“避难掩蔽”下钻了出来,都不约而同地先后到钦安殿去叩头致谢。到了第二天,我们才正式得到了“内务府”的报告,说张勋业已一败涂地,逃到荷兰公使馆去了。这时大家才都如梦初醒地把脑袋耷拉下来默不作声。
还有当叛军的败相日益浓厚时,那些乌合麇聚到伪内阁当上伪阁僚的各位“大臣”等,便如同“树倒猢狲散”一般,纷纷狼狈辞职鼠窜而去。最后只剩下罪魁祸首的张勋和三朝元老的王士珍以及我那老师陈宝琛等尚未辞职。有一天,陈宝琛急急忙忙来见我,要求赶紧拿出皇帝办事的小印来捺用,为的是要把一张公文交张勋转交张海鹏(当时东北军阀中的冯德麟、张海鹏、汤玉麟等都参加了这次的叛变),使其悄悄脱出急归东北,任命张作霖为东三省总督,好求援于他协助复辟,以挽救当前的危局。而这颗小印,照例是放在一个方形木匣内。匣子尽管在我身边,但开匣的钥匙,则一向是归我父亲载沣掌管,每次开匣取印捺用时,都得由宫中“奏事处”的太监从我这里拿去木匣交我父亲开匣用印,用完之后,仍由我父亲亲自把匣锁好,再经过“奏事处”太监之手,送回我这里保存。但在这垂死挣扎之际,已再没有工夫做那种烦琐的手续,于是我那位陈老夫子便“情急智生”,采取了“通权达变”的“非常手段”,砸毁了木匣子的锁,在张勋所拟定的那张所谓“谕旨”上盖了印,便由陈宝琛把这张“病急乱投医”的阴谋文件,匆匆交到张勋手中去了。不过后来张作霖对此始终并未做出什么表示来,总之,这件事又是以枉费心机而告终。
几天之后,就以张勋的逃入荷兰公使馆,而使这段复辟的罪恶迷梦结束了。但是我在这出丑剧的尾声中,还串演了一场丑剧中的丑剧哩。
那就是当张勋彻底失败之后,我的父亲和陈宝琛等,把预先早就准备停当的再度退位“诏书”拿了出来,做了一个关上宫门自欺欺人的颁布手续。在我听了那篇老着脸皮哓哓分辩言辞中所着重表明的如“……这完全罪在张勋而与清室无关。现在自己仍愿还政于中华民国……”等无耻谎言时,我居然被那句“还政于中华民国”的话给刺激得哭了出来。于是在我身旁的太监们,也有人随声附和地哭了起来。这就是我在十二岁时所干出来的事情。足见在当时,我的年岁虽小,可是我那与人民为敌的反动阶级罪恶本质,却是不能和我的年龄做相对比较的!
二、盗窃了人民的宝贵文化遗产
在一九二二到一九二三年之间,我因为受了庄士敦的影响,以及我对于当时宫中生活方式的不满,又加上我对于“小朝廷”尔后命运的不安,所以便产生了要到欧洲去留学的念头。当我把这种心情和希望向当时有关人士透露出来时,不料却遭到我老师以及家属中“权威人士”的极力反对。对此表示赞同的,只有庄士敦一人。
他们反对的主要理由是:
中华民国对于“清室”的“优待条件”,早为国际上所公认,中华民国又怎能单方擅自废止?
其实,他们反对的本意却不在此。
请想一想,为什么在张勋复辟时,他们却谁都没有想到“优待条件”的事?再者,在那“优待条件”中,有没有“许可背叛中华民国”的一项条款?为什么在复辟时,早把“优待条件”中明文规定的义务,完全忘个干干净净,而到了现在的时候,却又把中华民国无权从片面加以废止为唯一理由?并且还满怀信心,厚颜无耻地拿这种不值一驳的歪理来,作为反对我自动辞去这种优待而出国留学的有力借口?
他们也不想一想“优待条件”和我出国留学,可又有什么关系?更不想一想,既是发生了像张勋复辟那样的事件,明明是先从受优待的“清室”这一方面,违背了人家之所以要“优待”的本意。在复辟失败之后,之所以尚未废止“优待条件”,只是因为当时的北洋军阀政权,根本就不是真能给人民办事、对人民负责的革命政府,并且那些位政治“巨头”,也是和过去的清朝有过相当瓜葛的旧历史人物,所以才让“清室”钻了这个空子而捡了几年的“优待便宜”。按正理说,能继续受着“优待”,已经是一件意外的奇事了,怎么还能居然自觉满有理地公然扬言中华民国没有取消“优待条件”的权力呢?足见这帮寄生于当时“小朝廷”内的大人先生,是善于睁着眼睛说梦话,并且是只知依赖着外国——所谓国际上的力量,认为外国可以,并且应该干涉自己国家的内政,同时他们也确是在希望着帝国主义列强来干涉自己国家的内政。这种丧失民族气节、只知自顾自的反动丑恶奴才嘴脸,这种封建余孽的反动阶级本质,真可以说是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程度。所以我认为,他们之所以竭力反对我的出国留学,并不是真个地在重视着这一项类似空文的“优待条件”,而只是要拿“优待条件万万岁”来安我的心。尤其是对于我打算在出国同时,自动辞退“优待条件”这件事,感到了十分惊慌,所以才拿这样的话来作为借口。总之,他们最害怕的,就是有关他们的吃饭问题。因为像我这样的“饭东”一走,他们的祖传“铁饭碗”,就有立时被打破之虞,所以才会做出这种“齐心戮力,众谋佥同”的反对。
至于在我这方面呢,也有我自己的一个如意算盘。因为,我在当时曾认为到外国去留学,不但可以避免日后可能发生的生命危险;自动辞退那篇逐渐名存实亡的“优待条件”纸面文章,还可以博得一个“开明”的美名;并且到了外国,多多少少总能得到一些“新知识”;还可以在将来学成回国之后,拿这种“留学外国”的新政治资本,来做“伺机观变”之用;同时,到了所谓必要之际,也可以依靠外国——帝国主义国家的“奥援”,一方面再纠合那帮所谓遗老之类,来恢复过去自己的“祖业”。
他们的内心实话既不能对我做公开的阐述;我的潜在私图当然也不便对他们做无保留的倾叙,所以,在我和他们之间,是有一段无形的墙壁在隔着,只能在同床异梦的心情下,各自怀着不可告人的鬼胎,而各自做着自家的打算。
双方的意见既不能合拍,我那有利于我而不利于他们的留学计划,当然就得搁浅。但是我却没有甘心于这次的碰壁,于是就想起了一个“做好准备,徐为后图”的办法来。
我的同母弟溥杰是非常赞成我出国留学的。因为他自幼也是一个彻头彻尾具备了封建统治反动思想的野心家。他不但无条件地赞同了我的那种如意算盘,并且还变本加厉地向我提出了“须要立即积极进行”的具体建议,并自告奋勇,表示愿意负责这一窃运的实际罪恶行动,同时还表示了要和我一同出国留学的决心。
于是,盗窃祖国人民宝贵文化遗产的罪行便开始了。
我们兄弟二人就狼狈为奸地首先求我叔父载涛,在天津旧英国租界戈登路,为我购买一幢楼房。然后就由溥杰利用他每天在上午陪我读书的机会,每天一包袱、一包袱地把宫中由明、清两代不断从人民手中掠取来的我国民族艺术文化结晶,都择尤地陆续盗运出去,一直这样地干了半年之久。
在那次所窃运出去的宝贵人民遗产中,现在想起来最使我觉得痛心和不胜内疚的,都是些出类拔萃、精中取精的唯一珍品。现在所列举的,只不过是其中的九牛一毛程度。例如,在墨迹方面,有晋代王羲之的《曹娥碑》和《二谢帖》的手卷;有他儿子王献之的真迹;钟繇的字;僧怀素的草书;唐欧阳询的墨迹;宋赵构(高宗)的字;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亲笔原稿;米芾和董其昌的字等。至于元代赵孟 的字,那就更多了。在绘画方面,有唐王维的人物;阎立本的真迹;宋徽宗的画;宋马远和夏珪以及马麟各自画的《长江万里图》;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等等。手卷、册页和挂轴等共计起来,达千几百件之多。在古版书籍方面,则是把“乾清宫”西侧“昭仁殿”内所藏的宋版、明版的珍贵书籍全部盗运出去。至于书籍的名称,早已记不清楚。现在抄录一下潘际坰先生所引用的《故宫已佚书籍书画目录四种》——“一九三四年国立北平故宫博物院印行”——中的一段便可知其概略:
“这本只为少数人所留意的书,原是由‘清室善后委员会’在一九二六年第一次出版的。‘弁言’的全文如下:
“民国十四年三月十九日,点查毓庆宫至‘余字九六四号分号五十四’时,发现题名‘诸位大人借去书籍字画玩物等糙账’一册,内有‘宣统庚申年三日记’等字样。当时颇讶其可随意借取,继又于是年七月三十一日点查养心殿至‘吕字五二四号’,更发现‘赏溥杰单’一束,又‘收到单’一束。二者大致符合。内计宋、元、明版书籍二百余种,唐、宋、元、明、清五朝字画一千余件,皆属琳琅秘籍,缥湘精品,天禄书目所载,宝笈三编所收,择其精华,大都移运宫外。国宝散失,至堪痛惜。兹将三种目录印行,用告海内关心国粹文化者。”
潘先生更继续记述说:“从‘赏溥杰书画目’看来,自‘宣统十四年’(一九二二年)七月十三日‘赏’起,一直‘赏’到同年十二月十二日,足有五个月之久,这与溥仪所说的‘大约有半年’是符合的。
“第一天‘赏’的是十种宋版书:
宋版毛诗 四册
宋版韵语阳秋 一套
宋版玉台新咏 一套
宋版卢户部诗集 一套
宋版五经 一匣四套
宋版纂图互注南华真经 一套
宋版和靖先生文集 一套
御题宋版尚书详节(解) 一套
宋版帝学 一套
宋版孙可之文集 一套
最后一天‘赏’的是三十卷画,这里面有:
唐寅野航雨景。周之冕花卉真迹。赵孟 乐志论书画合璧。
马远山居秋爽图。赵伯驹蓬瀛仙馆。文徵明赤壁赋图。
宋人摹顾恺之听琴图。仇英画五百罗汉。
黄公望溪山无尽图……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共‘赏’掉了两卷:一在一九二二年农历十一月十八日;一在十二月初八日。
“从这份目录还可以发现‘赏赐’的单位大多用十,最常见的是三十,偶尔也用五做单位,如十一月初九日就‘心硬’了一点,只让溥杰开了一份共收到二十五件的清单。仅仅‘赏’一部书的时候也不是没有,但那不是十几套,就是四匣、八匣,而且是极其珍贵的善本。如九月二十八日,溥杰收到宋版《资治通鉴》一部,十八套……”
总之,被我们偷窃出去的这些无价可估的祖国人民宝贵文化遗产,就是这样一批批地到了天津的,目的是为了在将来如果离开了北京就可以依靠出卖这些东西过活;并可靠它充作赴帝国主义国家留学的费用,同时还可借之做依靠外敌力量,好再骑在祖国人民头上。我现在痛切感觉到,盗窃祖国的珍贵民族文化遗产,当然是一件无可补赎的严重罪行,但是想以此来达成自己的一姓尊荣野望,那更是罪大恶极无可宽宥的。
至于那些人民宝贵遗产的最后命运是,在天津的时候,我曾从其中拿出几十件将它们变卖。其余的全部,则是当我在伪满时,有一天负责监视和支配我的日本关东军司令部中将参谋吉冈安直忽然对我讲:“务希把那一大批书画文物从天津运到新京(长春)的‘宫内府’来。否则将会有人这样想:‘满洲国皇帝为什么不把他的东西存放在满洲国内,而偏偏要放在满洲国土之外的天津?’这很可能使人怀疑你仍想要回天津去住!”我听了他这语中带刺的说法,只得托他设法把这些东西从天津运到长春来。后来在日寇将要垮台时,我曾把其中的一部分带到通化大栗子沟,这些东西的下落,我就不知道了。
这便是我盗窃人民宝贵文化遗产的经过,也是我的反动思想在过去的行动中,又一罪恶的事实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