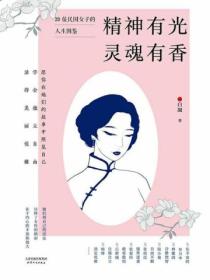巾帼从不让须眉
1925年,陈香梅出生于北京。她的家族,是真正的书香门第。父亲陈应荣十三岁就留洋,先是在英国牛津大学获得法学博士,之后又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回国后,陈应荣在北京师范大学当教务长兼英文系主任。
陈香梅的母亲廖香词与陈应荣是指腹为婚,同样来自真正的大户人家。陈香梅的外祖父廖凤舒,曾担任中国驻古巴公使。廖家“住的是轩门巨宅,用的是进口欧美家具,踏的是厚厚的中国地毯,起居室玻璃柜中陈列着中国的古玩。家规很严,吃晚饭时都需穿戴整齐如赴宴一般”。廖香词曾在英国、法国和意大利读音乐和绘画。在陈香梅的记忆中,母亲就是一位淑女。
陈香梅的童年,也有着优渥的生活条件。她在北京住的是中西合璧的四合院,家里有用人、车夫、门房、厨子、听差,以及专门负责打扫和洗熨衣服的老妈子。
她的名字,是外祖父取的。陈家一共有六个女儿,陈香梅排行第二。姐妹六人,她的性格受母亲影响最大。学识渊博的母亲常常告诉陈香梅:“淑女应该居心仁厚。”母亲还说:“一个人的出身和成就,都是次要,要紧的是能把握人生的真谛。”只不过,那时的陈香梅还太小,不能体会这句话的含义。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日军全面侵华,陈廖两家的家产几乎**然无存,陈香梅跟随家人从北平流亡到香港避难。在北平时,一家人的生活还能勉强应付。陡然搬到高消费的香港,生活很快就变得捉襟见肘。
父亲此时去了美国作外交官,母女七人留在香港铜锣湾居住。没过多久,廖香词罹患子宫癌,很快便病故了。那时的陈香梅还不到十四岁,大姐还不到二十岁,最小的妹妹才六岁。失去了母亲,父亲又不在身边,六姐妹在生活上十分无助。陈香梅是姐妹中最有见解和最有能力的,自然就成了姐妹中的主心骨。
香港沦陷时,姐妹六人正在圣保罗女书院寄读。日寇的铁蹄四处践踏,香港变得日无安宁,最糟糕的是,她们与父亲失去了联系。为了避免遭受日本人的摧残,陈香梅决定带着姐妹们离开香港,逃回内地。
这注定是波折坎坷的一路。出发之前,陈香梅把母亲留下来的珠宝一部分缝在棉衣里,另一部分藏进挖有洞的书里,作为日后的经济来源。她们先从香港坐船到了澳门,过海关时,面对日本海关的搜身,纵然早熟镇定,陈香梅还是吓出一身冷汗。好在,她从容应对,成功地保住了母亲留下的遗物。
船上挤满了逃难的人,六姐妹好不容易在甲板上找到容身之处,却不敢移动分毫。因为只要一走开,位置立刻就会被人抢走。原本三个钟头的行程,邮船竟然开了三天三夜。好不容易到了澳门,接下来的路越发难走。
从澳门到广州湾,陈香梅不敢再走水路,因为害怕遭到日本人的拦截。她只能带着姐妹,跟随众多逃亡的人一同步行。沿途时常遇到轰炸,还要躲避趁火打劫的土匪。一路上,她们随处都能看到草草建起的新坟,躺在里面的都是没能成功穿越封锁线的难民。
十五天的路程,她们觉得仿佛漫长得如同一个世纪。到达广州湾的赤坎市,陈香梅发现,那里处处挤满了难民。客栈家家住满,几番周折,陈香梅才和姐姐在赤坎西关楼附近租下一间简易的平房。
她从未住过如此恶劣的环境,空气里充斥着垃圾的腐烂气味,让她联想到死亡。虽然住宿环境奇差,但好歹算是一处容身之地。如何活下去,才更考验人心的韧性。
因为物资短缺,当时物价奇高。六姐妹身边并没有太多现金,陈香梅不得不变卖母亲留下的珠宝。她和大姐拿着一套钻石项链和戒指、一对玉镯去变卖,遇到了一位外地商人。对方坚持必须验货,确认是真货后才付款。年轻的两姐妹轻信了他人,将带来的珠宝全部交给对方。当第二天陈香梅找到对方居住的旅馆时,才发现早已人去楼空。
这次受骗,令六姐妹的生活雪上加霜。没过多久,广州湾也变得兵荒马乱。继续等待父亲的消息,已经希望渺茫。陈香梅决定离开,带着姐妹继续逃亡。
她联系了一所桂林的学校,决定先去那里安顿下来,等待父亲的消息。
从广州湾到桂林,沿途都是荒凉的小村落,根本找不到住宿的地方。她们只能和难民挤在一起,姐妹六人只能挤在两张木板**。虱子、臭虫、老鼠强占了难民居住的地方,姐妹六人身上被咬出大片大片的红肿,陈香梅在如此恶劣的条件下,染上了疟疾。
即便生病,她依然不敢耽误行程,强行带病走了两天,病情不断加重,又染上了痢疾。六姐妹不得不停下来,好不容易找到一个铁皮仓库,姐姐又找来当地的郎中给陈香梅看病。药喝下去后,陈香梅依然不见好转,反而开始高烧,人事不省,昏死过去。
姐妹们守在陈香梅身边大哭,她们知道,如果陈香梅死了,她们可能便要一同死在这里。熬到第三天,奇迹出现了,陈香梅醒了。她们简单地休整之后,将身上的首饰贱卖掉,重新出发。
辗转一个半月,六姐妹才终于到达桂林。一路上,她们没有食物,就吃蝗虫、蚱蜢。偶尔买到一点食物,陈香梅全部分给妹妹,自己躲在角落里吃豆子。那段地狱般的逃难岁月,真正让陈香梅的意志受到了磨炼。
到了桂林,她们终于联系上父亲。父亲想带六姐妹去美国留学,陈香梅却拒绝了。她说:“我不能在祖国受难时离开她。我要工作,要尽我对祖国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