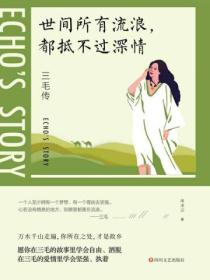翩翩似是故人来
这份家的安全,解除了我一切对外及对己的防卫。有时候,人生不要那么多情反倒没有牵绊,没有苦痛,可是对着我的亲人,我却是情不自禁啊!
——三毛《回娘家》
休息一天后,三毛前往小沙镇陈家村的老宅祭祖。实际上,三毛哪里懂得那么多祭礼风俗?除了从书上看来一些传统礼法,便是在台湾一些寺庙里所学。尽管如此,当她跪在爷爷坟前痛哭时,围观的许多人也都流下了眼泪。
人们都说:“小沙女回来了!”他们要看看这个从未进过祖宅、不入家谱、从海峡对岸回来的女人怎样祭奠她的先祖。三毛接过亲人递上的毛巾,擦去脸上的妆容和漂泊的风尘,本应更安心,却忽然又晕了过去,过了一刻钟才醒来。
尽管是进步乡绅,为家乡建设付出很多,但在那场浩劫中,爷爷陈宗绪的墓地却被毁坏得很严重,老宅也未能幸免。时过境迁,也因为三毛即将回来探亲,当地政府出资修缮了老宅,亲戚在陈宗绪原坟墓处又修建了新坟,还建了一条通往墓地的水泥路。
了解到这些的三毛心中自是忿忿的,却又无法表达什么。她在家里的旧书箱底翻出过家谱,也看过爷爷的自传,认为陈宗绪受得起这样的排场和待遇,这次上坟和祭祖,她要“衣锦还乡”,要让九泉之下的爷爷扬眉吐气。
三毛举着点燃的香,拜了拜天地,又跪倒在坟前早已预备好的红毯上,在心里与祖先对话,三跪九叩,情绪激动之下又晕了过去。醒来后,三毛便要求去爷爷的坟上看看。因为刚刚下过雨,到处都是泥泞。三毛煞有介事地看了坟地的风水,检查了墓碑上的铭文雕花,这才扑向墓碑,痛哭着高呼:“阿爷——阿爷——,魂——兮——归——来——”
围观的小孩子嘻嘻地笑起来,他们哪里懂得三毛心里的悲哀。在场的上了年纪、多少知道一点其中故事的人却都红了眼睛。
徐静波一直陪在三毛身边,早就按照她的要求准备好了装坟头土的盒子与装水的瓶子。三毛装了一把坟上的土,这是故土,也是爷爷的魂魄所在,需要给父母带回去的。
倪竹青与亲戚们陆陆续续上前跪拜,三毛跪在泥地里答礼。有些老人流着泪感慨,若不是当年陈宗绪创办免费小学,恐怕现在的自己也不会过上今天的好日子。三毛心里暗暗地想,终于,陈家的人平了当年的冤屈,祖父在天有灵,应当安息了吧。
老宅有口水井,三毛并没有忘记。亲戚帮她打了一桶水上来,但三毛执意自己打水,不仅装在瓶子里,还喝了一口。临走时还带上了老宅的提篮和一只当年陈家用来盛饭的粗碗——这都是家里的东西啊。
一向迷信神秘力量的三毛,回到宾馆后还是不放心,取出一点土,掺着一点井水,饮了下去,在心里告诉自己,从今以后自己就是有了根的人,再不会水土不服。
在离别的船上,三毛再也忍不住,哭着伏倒在栏杆上,对自己说:“死也瞑目。”
喝了故乡的水,沾染了故乡的风尘,拥抱了故乡的亲人,人生从此有了来处,再不会有颠沛流离。
三毛第一次回到大陆,许多陪在她身边的人不约而同地提到,她的身体状况非常不好,有时候一天要晕倒三四次。三毛从不在自己的作品中写自己患了什么病,她的父母也一向低调,并不以三毛的身体状况博人同情。在徐静波的回忆文章中,或可侧面了解到一些情况。
在见面之前,三毛就整理好自己的病历单寄给了徐静波,委托他在杭州帮自己寻访名医。徐静波联系到著名的内科医生,并组织成立了专家小组,可三毛并不相信西医能够治好她。她的确早已病入膏肓,勉力支撑——西方医学一直没有让她痊愈,病痛的魔鬼不时折磨着她。
在张乐平家里的时候,三毛的肩颈痛和胃病就让老人十分担忧,可见情况之严重。三毛让徐静波找一些气功大师为她治疗,虽然自己并不相信气功的疗效,但徐静波还是非常尊重三毛的诉求,为她找来了三位大师。三毛最后“拉下衣领,露出脖子上周围红红点点,告诉我们她患有淋巴癌,一直没有治好”(1)。
在去世前两天给倪竹青的信中,三毛提到自己的“喉内、胸、子宫都有癌已查出来了”,还让倪竹青夫妇不要担心,是“腺癌”。但是这件事她的父母和媒体都不知道,治疗耗资不菲,又耽误工作,三毛感到极度痛苦,也只能无奈地接受现状。
关于三毛的真实病情,并没有太多资料可供考证。早在撒哈拉沙漠时,因为当地卫生条件极差,她患有妇科病,久未得治;在大加纳利岛上,这病还没有痊愈,又遭遇了车祸,回到台湾被中药治好过,但是荷西去世后,她工作劳累,神经紧绷,是否积郁成疾,亦未可知。
此番回到故土,三毛自觉今生无憾。人生百年,匆匆已过四十载,仿佛飘在半空中的风筝,终于知道线的那头握在谁的手中。对于与三毛的见面和离别,张乐平认为作家白桦的说法甚妙:“我不讲欢迎,因为你本来就是这里的人;我也不说再见,因为你还会再来……”(2)
大陆的第一次行程,其实十分匆忙。三毛并没有回到南京,她的父亲陈嗣庆也很奇怪,为什么没有去南京看看呢?对于出生于重庆但生活印象都是南京的三毛来说,那或许才应该是故土吧?
生在重庆,当时正赶上轰炸时期结束,常理来讲,婴儿能了解什么、记得什么呢?但三毛却对父亲说,一睁眼就看到了兵荒马乱,向着巨大的铁鸟行进。她和姐姐被带进了窄窄的空间,在铁盒子上紧张地坐好。四周充斥着尖锐的蜂鸣,头顶上是网球一样的吊袋。母亲的脸色并不好,她也感到恐惧。
他们的确由重庆起飞,回到了祖父创业的城市——南京。离开大陆的时候,三毛还不到四岁,却对很多事情记忆深刻。她知道,她的家在南京鼓楼头条巷四号。没有人教过她地址怎么说,因为当时她实在太小,不被允许单独出门。当哥哥姐姐们和别人谈起自己的家庭地址时,一旁的三毛便记了下来。虽然并没有什么用处,但她还是记住了,记了四十年——那是她的家。
南京的这栋房子里曾住着二十多口人,伯父一家、陈嗣庆一家、倪竹青以及一些帮佣。三毛以为这样的大家庭,开支巨大,应该是承蒙祖上余荫才过得来那样惬意的日子。但是父亲告诉她,房子是租来的。陈嗣庆兄弟俩没有分过家,一直在一起生活,祖父在三毛回到南京之前就回舟山养老去了,他几乎将所有的积蓄都捐给了家乡的慈善事业。
房子的一层是父亲和伯父办公的地方,他们在这里开设了一家法律事务所,业务往来频繁,因而收入尚可。倪竹青是非常重要的工作人员,他那手好字在当时起到了打字机的作用,若是没有他,很多事情都做不来。
房子是回字形的独栋,四周是并不算高的围墙。但是对于刚刚脱离婴儿期、步入幼儿时代的三毛来说,攀越还是颇为困难。她经常爬上假山,偷着玩弄三堂哥饲养的蚕宝宝,或者望着院子外面发呆——各种建筑的屋顶和各种颜色式样的国旗,沉淀着古旧,也飞扬着无奈。
前院种着梧桐树,桑树和花花草草,后院的篱笆有一面墙的爬墙玫瑰。三毛实在太小,孩子们的游戏总是与她无关,年轻人窃窃私语时也总是叫她走开。父母忙忙碌碌,没有时间理会她,她便安静地观察着后院的生态:烟火弥漫的灶间,纳鞋底、熨烫衣物的女佣,挨打的马蹄子,垂死的门房婆婆。
三毛一直笃定地说自己看到门房婆婆死去之前,从口中飞出了一串白蛾,原来那就是人的灵魂,最后要告别躯体,回归纯粹自由。三毛在这里第一次听见英文,那来推销地毯的可怜的流亡俄国人或者犹太人,拿到父亲递过去的钱,交给父亲一块地毯,握手的时候说上一句:“OK,you get it !”
这些都是非常新奇的事情,足够让她铭记一生。
对于院子外面的世界,三毛熟悉的不过是信教的母亲带着孩子去做礼拜的场景罢了。三毛不懂神的意味,只是单纯地认为那是母亲崇拜的大人物,于是便将“耶稣”挂在嘴边。但是神好像也并不能带来什么。抗战胜利后,在原本以为到来了的和平年代,他们还是去了台湾。
物是人非,故土不堪回首,月明依旧。通邮以后,三毛陆续得知了大陆亲人的情况。儿时的回忆有多深刻、多美好,失去故人就有多令人心碎。
她想把那永恒的记忆都留在当年。
(1)引自张乐平《我的“女儿”三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两岸情”征文)。
(2)引自张乐平《我的“女儿”三毛》(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海峡两岸情”征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