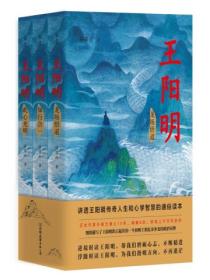(一)
这一夜,王守仁在无意之间洞破玄机,悟到了“良知”这个人世间最大的道理。
第二天早上,守仁走出山洞,已经是一个新人了。看天天蓝,看水水绿,只觉得天地之间再没有一丝阴霾之气。
现在的王守仁在为他自己活着,在整理内心的良知,寻找快乐的真理。从内心深处觉得人不管在什么地方,过什么日子,只要活着,就应该活得有乐趣,有追求,多做有意义的事。而今天要做的第一件有意义的事,就是跟老何交朋友。
刚到驿站,就看见老何正在菜园子里侍弄那几棵青菜。守仁见了朋友觉得喜悦,老远就冲他打个招呼:“老何,昨晚睡得好吗?”
老何停了手,抬头看着王守仁,半天才答一声:“好。”接着低头忙自己的事。
王守仁走过来看着老何忙碌,忍不住说了句:“你这菜园子种得真好。”
这是一句真心话。
老何虽木讷,种地倒是把好手,把这个菜园子着实侍弄得不错。只是守仁自到龙场以来整天心烦意乱,满脑子都是杂七杂八的想头儿,根本就没正经往菜园子里看过一眼。可今天也不知怎么,他的心气儿平了,再看这一园碧绿的蔬菜,觉得又可喜又可爱。就在老何身边蹲下,看着他除草、松土、捉虫子,越看越觉得有趣。忍不住说:“老何,你教我种菜吧。”
想不到驿丞大人忽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老何打了个愣,不知怎么回话。守仁呵呵地笑着说:“我这个人呀,真正是四体不勤、五谷不分,什么活儿也不会干,你可别嫌我笨哦。”一句话把老何也说乐了。
这是守仁到龙场半年来,第一次看见老何的笑脸。
以前的王守仁是状元公的大公子,名满天下的大才子,做过大官,办过大事,当过大英雄,是个非同一般的大人物。虽然他心里并没有看不起老何的意思,但在这个大字不识的驿卒面前,无形之中还是端着一副好大的架子。守仁端着这么一副架子,不肯真心与老何亲近,老何又哪敢和这个京城出来的公子哥儿亲近?今天守仁忽然把一切“架子”都丢开,自己蹲在地头上要跟老何学种菜,老何当然没有二话,就手把手地教起他来。
守仁是个公子哥儿出身,果然手笨,一招一式都不像样,老何不厌其烦,教得耐心。两个人在土坷垃里刨弄了一上午,不自觉地就亲近起来了。守仁问老何:“你家在四川什么地方?”
“灌县。”
四川守仁虽没去过,可这个灌县大大有名。“那地方离青城山不远吧,都说夔门天下雄,剑阁天下险,峨眉天下秀,青城天下幽,好地方!”
听守仁称赞自己的家乡,老何的话立时多起来了,把青城山里的上清宫、建福宫、祖师殿、天师洞、天桥,还有什么圣母洞、白云洞、金壁天仓、山泉雾潭……说个不停。
“相传东汉年间中原一带出了六部魔王、八大鬼帅,带着无数鬼兵鬼卒为患人间,正一天师张道陵在青城山设坛作法,收服八大鬼帅,又把六部魔王镇在山下,后人专门在青城山上修了一座上清宫,供奉张天师神位。这上清宫里有一个圣灯亭,每到晚上,从山下就可以看到圣灯亭里有灯火点起,少的三五盏,多到几百几千盏,都说这是张天师驾临上清宫,各路神仙来朝贺点起的神灯,我们当地人都到上清宫里求签许愿,请下神符去邪除怪,保佑平安,那真是有求必应,最灵验不过的。”
以前和这个无知无识闷头闷脑的老何说话总觉得索然无味。可今天不知怎么了,老何说他家乡的山水,讲这些神异故事,守仁听得悠然神往:“家乡这么好,怎么到贵州来做驿卒了?”
“家里没亲人了,也没有地,活不下去了。在这儿当个驿卒,好歹有口饭吃。”老何叹了口气,不想再说这些事,“王大人家在哪里?”
“浙江余姚。”
老何不知道余姚在什么地方,只说:“我听说浙江地肥水多,富裕。”
每个人都喜欢听别人夸赞他的家乡,守仁也是一样,被老何一夸,顿时喜笑颜开:“是啊,余姚城里就有一条姚江,水大得很,江边上有座龙泉山,山上有座龙泉寺,好大的,足足占了半座山……”
其实余姚龙泉山只是一座小山头儿,和灌县青城山比起来,就像一颗核桃比一个西瓜,差得远了。可老何想不到这些,还以为龙泉山也是绵延几百里的大山。听说龙泉寺“占了半座山”,惊得把眼睛都瞪圆了:“好厉害!这么大的庙我一辈子也没见过。”
守仁听出老何误会了,就笑着补了一句:“不是庙大,是龙泉山小。爬到山顶用不了一个时辰。”
听守仁这么一解释,老何也呵呵地笑了起来:“怪不得哟,我就说哪个庙要修得那么大……我们老家水也多,有个都江堰,大人晓得吧?”
“知道知道!那是战国时候修的,距今一千几百年了,引来岷江之水,半个成都平原都靠它灌溉,古人在那里建有分水鱼嘴、离堆、宝瓶口、飞沙堰,枯水不旱,丰水不涝,鬼斧神工,天下奇绝!”
老何竖起大拇指:“王大人不愧是读书人,知道的东西真多。”
老何这句夸奖是真心实意。可守仁却知道自己这只不过是照搬书本上看来的东西,算不得真本事。嘿嘿一笑,故意学着老何的四川腔说了一句:“我懂得啥子嘛,连煮个稀饭儿都不会。”一句话把老何逗得哈哈大笑,守仁也笑了一场。
这天守仁跟老何整整收拾了半天菜园子,也说了半天话。到中午老何煮饭的时候,守仁就帮着到菜园里拔菜,又洗又切,又帮忙添柴煮粥。到饭熟的时候,他的肚子也饿得咕咕叫了,这一顿饭吃得格外香甜。
吃着饭,看着倒了半边的驿站,守仁心思一动,又想起一件事来:“老何,你会不会打土坯?”
“打土坯干什么?”
“你看驿站的房子倒了,咱两个现在住得都不像样,反正一天里有大半天闲着没事,不如自己打些土坯,把房子修起来,有没有公事还是其次,咱们自己先有个地方住。不然总住在窝棚里,又冷又潮的,时间长了身子受不了。”
想不到这位驿丞大人忽然想出这么个主意来。老何半天没琢磨过来。可再往下想,越想越觉得有理。贵州山里潮湿多雨,整天住窝棚,早晚要落下病,到老来就受罪了。他就说:“要得,大人说干,咱们就干起来。”
打土坯盖房子,修好驿站,公事方便,自己也有个住处,这是守仁的“良知发动”。第二天早起,俩人就和泥割草准备打土坯,这就叫个“知行合一”。由此可知:“知行合一”确实都在日常生活中体现出来,简单朴素,没有“神奇”之处。只要依此做去,效验显著。
当然,打土坯这个活儿王守仁根本不会干。
好在这事不难,挖来有黏性的土掺上些草,拌和起来用脚使劲踩,等泥和好了,放在一个长方形的木模子里夯打个几十下儿,取出来就是一块土坯,把打好的坯盖上稻草放几天,晾干了就能用了。
可和泥、打坯都是力气活儿。老何身强力壮,一天下来能打两三百块,守仁身体瘦弱,又没干过这个活儿,打夯的手法不对路,只知道在两条胳膊上用力气,结果打不了几块就累得肩酸背痛,汗落如雨。
见守仁打不动坯了,老何就在边上“嘿哟,哦哟”地喊起号子来。
守仁知道这是老何在给他鼓劲儿呢!自己如今攥着夯把子在这儿打土坯,就得先学会怎么出力气。就照着老何的样子学,可学来学去,老觉得哪里不太对劲儿?低头往身上一看,明白了!敢情到现在自己还一直穿着那件儒生的长衫子,只是把袍角撩起来掖在腰里了。这副样子哪能干得了活儿?
把这一点想明白,王守仁就把身上的长衫脱了,帽子也摘了,连那副“儒生”的架子都彻底丢在一旁,挽起袖口,卷高裤脚,一眼一眼看着老何的样子,放开喉咙喊着号子,腰腿肩膀一起使劲,一夯一夯尽力去打。
这一天守仁勉勉强强也打了五六十块坯,累得腰都直不起来了。到晚上脚步蹒跚地回到山洞往草堆上一倒,顿时睡得昏天黑地,哪还想得起什么犯愁?
简直连咳嗽都忘了。
就这么搞了一两个月,守仁练得臂膀也粗了,腰杆也壮了,一天下来也能打一百多块土坯了。和老何商商量量,有说有笑,一天一天地忙活着。那座已经垮在地上的龙场驿站慢慢立起三面围墙,眼瞅着有点儿模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