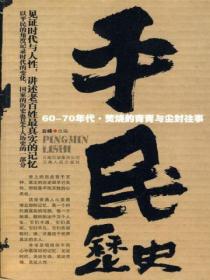文 / 一景
“文革”时,我刚上小学二年级。从扬州来了位“百科全书”式的表哥,一石激起千层浪。既是扬州表兄,当属“旧文化”的遗少,特爱怀旧,号称看过几百部电影。睡觉前,哥儿俩四只脚参差不齐地伸入洗脚盆,片名由此推出:从拉美影片《中锋在黎明前死亡》到国产片《李双双》,每晚一部。兴致高时,“连映两场”(当然没“新闻简报”。)表兄记忆过人,才气横溢,就像我们洗脚盆里的热水,一个劲向外泼。听他娓娓道来:赵丹演《林则徐》,初出场,抬轿停,赵丹出。只走出三步,便听得电影院内观众席间爆发出雷鸣般掌声:那三步走得好!(后来看徐进导的《红楼梦》,方知那名演员步态之讲究:徐玉兰饰贾宝玉,“挣脱了那不离不弃的黄金锁”,斜眼瞥了一下通灵宝玉,嘴角露出一丝不屑的淡淡微笑,随手一撇,然后转身开步而走,那几步,雍容洒脱,不紧不慢,再配上“群情激昂”的众女声伴唱:“抛弃了……”相形之下,迈克尔·杰克逊的“太空步”简直是残废人重获新生的乱摆动!)表哥又讲王丹凤演女理发师,琢磨着丈夫搭乘的火车进站是个啥样,不觉之中将剃头推子模拟缓缓进站的火车,在手下胖顾客的头顶深深开出一条“铁道”(如今看来像哈佛广场的“朋克头”),我便咧着缺牙的嘴大笑。
电影故事讲多了,脑子里构出了一个世界:想象中,“文革”前,五六十年代的“黄金时代”。而我听故事的年代又如噩梦一般,一长队颤巍巍的老人或执铁锅或拎铁炉,一路走,一路敲:“我有罪”,胸前挂着牌。城内的三个疯子,一日忽聚一起,挽臂横行于街头,曰:“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害得我常做噩梦,梦见那个疯老太婆,穿一身紫红追我,我怎么也跑不快……相比,表哥的故事,便成了冬日被窝中的温暖。即便是那阿根廷中锋须在黎明前死亡,也死得动人。况且,还有那个美丽的芭蕾舞女子恋人,着白天鹅服,掬一把天鹅之死的温馨泪。由此,我更羡慕表哥:偏偏让他赶上那个“温暖”的年代,而我只有画饼充饥想象的份儿。
更恼人的是,“文革”初尚有一些“内部批判”影片却没眼福。一日得票两张,表哥与我同去,结果在影院门口我被挡驾,说是儿童不宜。只好悻悻离开,将票转手“倒卖”了。换得的钱恰好够买一盒“飞行棋”,回家海陆空大战一场方才消解心头之恨。
“文革”后开禁,饱赏了五六十年代的“旧片”,像封窖百年的贵州茅台,一开封,醇香浓郁,三日不知肉味。究竟是片子真好,还是因为其中凝聚了童年幻想的缘故,说不清楚。现在,一想起那些片子,就神思飞越:许云峰冷看重庆夜;李向阳大智金蝉脱壳;刘三姐**舟歌满两岸;苦妹子倒影姑苏池塘;小嘎子悄然轮胎放气;阿黑哥飞马搭救恋人……美则美矣,可哪知一幅银幕遮住了“肃反”的滥杀,“反右”的无情,和连年的饥馑!同是五六十年代截然相反的两幅图景:前者温情脉脉,歌舞升平;后者杀气腾腾,全无诗意可言。不幸的是我们这一代人因有后者,而将前者的虚幻就此抹去。正因为伴着无法做到的那些虚幻长大,那虚幻便成了真实的过去——该怎样称它呢?真实的虚幻?虚幻的真实?由此,构成了一个矛盾:我们所怀旧的对象是不值得去留恋的,但那毕竟又是我们仅有的无法选择的过去。回想起来,酸甜苦辣,却一样滋滋有味。我仍然执著地相信那个银幕世界是个确实的存在:心灵的世界,感觉的世界。对那个世界的追缅,其实是对自己心路历程的追溯。说来也真是个悖论:对精神贫乏的年代的回忆,现在竟成了丰富的内心世界的内容……将来准有一天,我们白发苍苍地坐在镭射录像机前,独自看《枯木逢春》之类老片子,遥想那时候心潮起伏,老泪纵横。旁边玩电子游戏的孙子辈们一定会瞥一眼屏幕,再大惑不解地盯着咱们看半晌,然后嘟囔道:“多奇怪的老家伙!”言毕,又埋头去玩他们的“二十一世纪星球大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