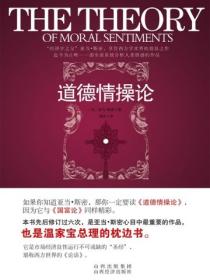第二篇 论优点和缺点;或奖惩的对象
第一章:论对于优缺点的感觉
引言
人类的行为还有另外一种品质。这种品质既不用来评价行为举止是否合宜,也不用来评价一个的行为是礼貌的还是粗鄙的,这种品质反映的是我们对一件事物鲜明而直接的态度,即优点和缺点。
前面已经提到,我们可以从两个不同的方面去思考各种行为产生的依据,全部善恶所系的内心情感。第一个,可以从激发它的原因和对象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第二,可以从它可能产生的结果和往往产生的结果之间的关系来研究。一种感情相对于激发它的原因或者对象来说是否恰当,是否相称,决定了两者关系是否相适宜,是有礼还是粗俗。这种感情可能产生或往往产生有利或有害的结果,进而决定了这种感情所引起的行为的优点和缺点。接下来我们要探讨的是究竟哪些方面构成了我们关于行为优缺点的评判。
第一节 任何值得感激的行为都应受到奖赏 任何遭致怨恨的行为都应受到惩罚
任何优秀的表现,显然都应该得到报答;同样的,任何恶意的表现,也应该受到惩罚。
那种直接促使我们去报答的感情,就是感激;而那种直接促使我们去惩罚的感情,就是愤恨。
报答和惩罚两者虽然以不同方式进行,但其实它们都是一种回报方式,只是报答回报以好处,而惩罚则是以恶报恶。
除了感激和愤恨之情外,还有一些情绪,它们会引起我们对他人幸福和痛苦的关心。但是,没有任何感情可以直接引起我们对他人幸福和痛苦的操劳。由于长期的相识和彼此之间的融洽关系而产生的爱和尊敬,必然会让我们对其幸福表示高兴,因为他是一个令人感到愉快的对象。正是如此,我们才会情愿为促成这种幸福而助一臂之力。即使他没有我们的帮助就取得了这种幸福,我们自己内心也会有极大的满足。这种感情所渴望的一切就是看到他的幸福,而不必去考虑他幸福的缔造者。但是,感激并不能以这种方式得到满足。如果一个带给了我们许多宝贵财富的人,在没有得到自己帮助的情况下就获得了幸福,我们的爱或许会得到满足,但较之他在之前对自己所做的贡献来说,我们内心还是感到会亏欠他一些东西。
同样,我们内心的不满所产生的憎恨和厌恶,常常会导致我们对他人的不幸抱以幸灾乐祸的态度。他们的行为和品质曾经激发了我们内心痛苦不快的感觉。但即使这样,即使厌恶和不快压抑了我们的同情心,并且有时甚至会对别人的痛苦幸灾乐祸,但这种情况下并不存在愤恨。如果我们和自己的朋友都没有受到严重的人身攻击,那么这些感情自然不会希望给他人带来不幸。虽然我们并不害怕插手他人的不幸而受到惩罚,但是我们情愿以其他方式去发生。对于一个被强烈仇恨感支配的人来说,听见他所憎恶和痛恨的人死于一场意外,或许会让他高兴。但是,哪怕他仍然有一点点正义感的话,那么这种兴奋的情绪就会与自身道德品质相悖,从而在他心中产生一定的悲伤情绪。正是这种自动作用于他人不幸的念头会异乎寻常地拷打着自己的内心,当他们想到自己可能也会做出这样一件穷凶极恶的事情来,就会开始用对待他所厌恶的人的可憎眼光来看待自己。
但是愤恨与此完全相反:一个人极大地伤害了我们,无论从肉体或者精神也好,比如他跟我们有杀父之仇,不久后他又死于严重的疾病或者因为别的罪名丢了性命,我们或许会平息自己的愤怒,但是不会完全消除我们的愤恨。愤恨不仅仅让我们希望他受到应有的惩罚,而且因为他作为加害者,我们希望亲手处置他来平息他对我们造成的特殊的伤害。除非这个犯人不仅为自己而难过,而且他也表现出对自己曾经在我们身上犯下的罪行的悔恨与懊恼,不然我们心中的愤恨是不可能消除的。这个罪人也理应去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感到后悔,那样,其他人由于害怕受到相同的惩罚就会不敢再去犯下同样的罪行。这种感情的自然满足就会自动产生惩罚的一切政治结果:惩罚罪人,告诫世人。
所以,对我们来说,表现良好的人就值得报答,而那些引起人们愤恨的人,理应接受惩罚。
第二节 论合宜的感激或愤恨的对象
只有大家都认为理所应当得到感激或愤恨的行为,才是合宜的对象。但是,这些感情如同人类本性的其他感情一样,只有在得到一个公正的旁观者的充分同情和一个没有利害关系的旁观者的认可的情况下,才显得为大众所认可。
作为某些人发自内心感激的对象,显然应该得到应有的报答,这种感激由于与大众的心思相同而为人所赞同。而作为被某些人所愤恨的对象时,就理应受到惩罚,这种愤恨是每个有理智和有道德的人所能接受和表示同情的。在我们看来,当一种行为显然应该得到报答,那么每个了解它的人也必定都希望他得到回报,我们也乐于见到这样的报答。当然,某种行为显然应该得到惩罚,每个人又都会对此显示出自己的愤怒。因此,我们也乐于见到这种惩罚。我们羡慕同伴交好运时的快乐,无论我们的朋友把什么看成是这种好运的原因,我们也都会同他们一起对此抱有喜悦和满足之情。我们理解他们对此怀揣的热爱,并且同样也对他们产生爱意。如果这创造快乐的东西遭到破坏,或者被搁置于一个他们无法触及关心到的位置,搁置于一个他们所不能保护的范围,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虽然我们除了再次见到他们失去了原有的愉快之外并没有失去什么,但是我们心里还是会因为他们的原因而产生遗憾。如果为自己同伴带来幸福的是一个人的话,那么这种感觉就更能深深地体会到。当我们见到他人受到帮助和关怀之时,我们产生的对受益者幸福的同情也仅仅是有助于激起我们对行善者所怀有的感激而已。如果我们想象受益者必定用看待行善者的眼光来看待他,行善者的形象就会以非常善良和亲切的形象出现在我们面前。因此,我们乐于对这种能让我们感到愉快的感情表示同情,这种感情是受益者对行善者所特别怀有的。从各个方面来看,这些回报都是与他们的对象相称的。
同样,当我们看见自己的同伴悲伤失望,我们自己内心也会产生深深的遗憾。因为我们的心与他的悲伤时刻紧密相连着,就很容易被他那竭力挣扎、力图摆脱痛苦的精神所打动。怠惰而又消极的同情会使我们同他一起处于痛苦之中,我们乐于用另一种更为活跃而又积极的情感来代替它,由此我们赞同他为消除这种悲伤所作的努力,也同情他对引起这种悲伤的事情表示厌恶。同上文描述的一样,当引起这些痛苦的是一个人时,情况更是如此。当我们看见一个人受到别人的欺压和伤害时,我们对受难者的痛苦所感到的同情,好像仅仅有助于激发我们对受难者的同情和对侵犯者的愤恨。我们乐于见到受难者还击自己的仇敌,而且无论什么时候,当他在一定程度上实行自卫或报复时,我们也会迫切并情愿地帮助他。如果受难者在争斗中竟然死去,我们不仅对死者的朋友和亲戚们的愤恨表示同情,而且会换位到受难者的角度去思考他的愤怒并且表示同情,虽然死者已不再具有感觉或其他任何一种人类感情。但是,由于设想自己成为了他身体的一部分,并在想象中使这个倒下的躯体重新复活,所以,当我们以这种方式在内心深切体会他的处境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当事人不可能感到的情绪,然而这是通过对他的一种想象而感受到的。我们在想象中为他蒙受的那种巨大而无可挽回的代价流出了我们的同情之泪,似乎只是我们心理上对他负有的一点儿责任。我们认为,他遭到的伤害还需要我们更多的关注。我们感觉到那种在自己想象中认为他应该感觉到的那种愤恨,并感觉到假如他那冰冷而无生命的躯体尚未失去意识,他也会感到的那种愤恨。我们想象他还在高呼以血还血。一想到他受到的伤害尚未得到公正的裁决,就感觉到死者似乎也为之不安。人们想象经常出现在凶手床边的恐怖形象,按照迷信想象的,从坟墓中跑出来要求对过早结束他们生命的那些人进行惩罚的鬼魂,都来自于这种对死者的想象和我们的愤恨所产生的同情。对于这种最可怕的罪恶,至少在我们充分考虑惩罚的效用之前,上帝就以这种方式将神圣而又必然的复仇法则,强有力地铭刻在了人们心中。
不认可施恩者的行为,就不可能同情受益者的感激;或者,对损人的动机感到赞许,就不会对受难者的愤愤不平产生同情。
而且要看到,人们的行动或者意识不论对其受影响者——如果我们能这么讲的话——如何有利或者有害,在前一种情况下,如果行动者的动机显得不那么合宜,而且我们也不能理解他产生这种行为的感情,我们就不可能对受益者产生感激;相反,在后一种情况中,如果行为者的动机并不是那么的不合适宜,影响他行动的感情就跟我们所必须理解的一样,我们也不会对受难者的愤愤不平感到同情。在前一种情况下,些许的感激貌似是应当的;在后一种情况中,满腔的愤恨貌似也是不应该的。前一种行为好像是应该得到报答,而后一种行为又好像不应该受到惩戒。
1.最开始我要声明,如果我们无法体会行善者的感情,如果他这样做的动机显得不合情理,我们就很难对受益者所抱有的感激之心表示同情。出于最普通的动机却给予别人最大的恩惠,并不仅仅是因为谁的族姓或者爵位恰好与赠与者的族姓和爵位相同,而把一笔财富赠与该人,这是一种愚蠢而过分的慷慨,根本就只配得到轻微的报答。此类帮助好像不需要被给予什么报答。我们对行动者的愚蠢行径的蔑视妨碍了自己对那位得到帮助的人的感激产生同感。他的恩人貌似并不值得感激,由于我们置身于感激者的境遇时,感到对一个恩人不可能怀有高度的尊敬,所以在很大程度上打消了对他谦恭的尊敬和尊重(我们通常认为这种尊敬和尊重应当给予更加适合的人);但是如果他一直仁慈而又人道地对待自己懦弱的朋友,我们就不可能对其表示出更多的尊重和尊敬——我们会将这种敬意给予更加值得的人。那些对自己的意中人无所顾忌的滥施财富、荣誉和权力的君主,鲜能获得那种程度的对他们自身的依恋。而这种依恋只对那些对于自己的善行有节制的人才能产生。大不列颠的詹姆斯一世非常好心而且慷慨,但是却几乎没有得到任何人的喜爱;尽管他拥有温和友善的性情,但是在他生前死后都没有一个朋友。可是英格兰全部的贵族和绅士都为他那个卓越却节俭的儿子舍弃了自己的财产乃至生命,尽管他生性冷酷无情。
2.接下来我要说,无论一个人给别人造成了多大的不行,只要它的动机和情绪完全能够得到我们的同情和认可,我们就根本不会去同情受害者的怨恨。当两个人在争吵的时候,我们一旦偏袒向其中一个,并且完全赞同他的愤怒,自然就不可能体谅另外一个人的愤怒。我们同情那个被自己赞成动机的人,所以认为他是正确的;并且肯定会无情地去反对另外一个——我们认为他是错误的——不可能对他表现同情。所以,不论后者将要受到什么样的痛苦和磨难,当它小于我们希望他受到的痛苦时,它既不会让我们感到恼火也不会让我们感到不快。当一个冷酷无情的凶手被推上断头台的时候,我们也许会有些怜悯他的不幸,但是如果他狂妄的对检举他的人或者法官表现出不满和抗争,那么我们不可能对他的不满产生同情。人们总是对如此可恶的的罪犯有一个愤怒的自然倾向,对罪犯来说这确实是致命和具有毁灭性的。而我们不会对这种感情倾向感到不快,因为一旦我们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下,我们难免会赞同这种感情倾向,且不会有任何困难。
第三节 对前几章内容的简要回顾
当一个人因为别人给他的恩惠而心存感激时,我们对这种感激并不完全表示同情,除非后者是出于某些我们完全赞许的动机。我们必须从心底接受行动者的原则并且赞同影响他行动的所有感情,才可能完全同情因这种行动而受益的人的感激之情并和它一致。一旦施恩者的行动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合宜,无论结果会有多少好处,也不一定要给对方同等的报答。
但是,当这种善意的举动和导致它的合宜感情结合为一体的时候,当我们全然赞许行动者的动机时,我们由此会产生对他的敬意,对那些感激涕零的人的同情心也会大增。于是,他的行动看起来需要或者极力要求——如果允许我这么说的话——一个相适应的报答,我们自然也能够体谅那种引起了报答之心的感激之情。如果说我们这样全然赞许产生这种行动的感情的话,那么我们必然会同样赞许这类报答行为,并且会把被报答的人看作是一个适当并且合适的对象。
同样的,仅仅由于一个人给某人带来了不幸,我们就对后者对前者产生的愤怒几乎不能表示赞同,除非前者造成的不幸是出于我们不可理解的动机。在我们能够全然体谅受难者的愤恨时,必然是我们不赞同行动者的动机,并从心底决绝对影响他行动的全部感情表示同情。如果这些动机及感情不是那么的不符合事宜的话,那么不管他们对那些受难者会产生多么严峻的后果,这些行动看起来都不是那么地应该得到惩罚或者成为众人愤恨的对象。
然而,当这种行为所产生的伤害和由此产生的不适宜的感情合为一体的时候,当我们带着愤愤不平的心情去拒绝为行动者的动机付出同情时,我们自然会真诚地同情受难者的愤恨。于是,这些行动看起来应该得到和极力要求——如果允许我这么说的话——理所应当的惩罚;而且我们全然了解并且赞同要求惩戒这种行动的那种强烈的愤怒。当我们如此全然同情并且赞同要求给予惩罚的那种感情时,这个罪人必然是看起来要成为适合的惩罚对象。在这种情景中,当我们同情和赞成因为这种行动产生的感情时,我们自然也赞成这种行为,并且把受到惩罚的人看做是理所应当的对象。
第四节 对优点和缺点判断力的分析
判断一个行为是否适度,取决于行动者的感情和动机是否让我们产生同情。当然,如果允许我这么说的话,我们对优点的感觉源于对接受行为者的感激之心的间接同情。除非我们事先就赞同施恩者的动机,要不然不可能全然体谅受益者的感激,所以,对忧点的感觉应该也是一种混合的感情。它是由两个完全不同的部分组成的:一种是对受益者感激之心的间接同情;一种是对行动者感情的直接同情。
当我们觉得某种品质或行为值得被给予报答的时候,我们往往能够清晰地分辨这两种掺杂在一起的感情。当我们在阅读史书的时候,那些仁慈高尚、大义凛然的行为,常常让我们激动万分,迫切地想要了解其目的。这些行动背后那种过于慷慨的精神常常让我们感慨万分,为他们的成功激动,为他们的失意伤感。在我们的幻想中,我们早已把自己当成是哪个对我们做出行动的人了;在想象中,我们还把自己置身于那个久远的甚至被人遗弃的冒险经历中,并幻想自己是阿或卡米卢斯、提莫莱昂或阿里斯提得斯式的角色。我们的情感其实一直建立在同情行动者的基础上,对从这种行动中获得好处的那些人的间接同情也很明显地表现出来。每当我们设身处地地去思考这些受益者的处境时,我们是带着非常强烈的真挚的同情去体会、去思考他们对那些真诚为他们服务过的人怀有的充满谢意的感情。我们会像他们一样去拥抱恩人。我们从心底里对他们最强烈的感激产生同感。我们认为,对他们来说怎样的感激和报答都是不为过的。当他们对所得到的帮助给予这种合适的报答时,我们会由衷地赞许这种做法;而如果他们的行为使他们看起来似乎对这样的帮助无动于衷的时候,我们会感到万分震惊。简单的说,我们关于这些行动及其奖励的整体感觉,关于这种恰当合适的行动的报答和能使其行动者感受到愉悦的整体感觉,都来源于感激和热爱的富有同情的感情。当带着这种情感去切身体会当事人身处的环境时,我们必然会因为那个人能够做出这么崇高而恰当的善行而充满激动的心情。
一样的,我们觉得某人的行为不合时宜,是因为我们对他的感情和动机缺乏同情,甚至有可能是直接带着反感情绪的。所以,我们对缺点的感觉源自我们对愤怒者的间接同情。
由于我们除非在心里本身就不赞同行动者的动机,然后拒绝对它们产生任何同情,确实不可能同情受难者的愤恨,所以,和对优点的感觉是一样的,对缺点的感觉也是一种复杂的感情。它也是由对行动者的感情表示直接反感和对受难者的愤恨表示间接同情两种感情组成的。
很多时候,当我们觉得某种品质或行为应该得到惩罚时,我们也能清楚地区分这两种混杂在一起的感情。我们在阅读有关博尔吉亚或尼禄寡廉鲜耻和残酷暴虐史料的时候,会从心底表示一种对于影响他们行动的可憎感和反感,而且怀着恶心和恐怖的心情拒绝对这种恶劣的动机表示什么同情。我们的情感其实就是建立在对行动者的直接反感上的。与此同时,对受难者的愤愤不平产生的同情也更加明显。如果我们能够设身处地地去想象一下被人侮辱、被人出卖或者被人谋杀的那些人的不幸,难道我们会对时间的残忍和蛮横的压迫者无动于衷吗?我们对无辜的受害者所承受的痛苦产生同情,和我们对他们正当自然的愤怒产生强烈的同感是一样自然而然的。前一种感情实际上只是增进了后一种感情,而一想到他们的痛苦,就会增强并且激起我们对那些导致这些结果的行动者的憎恨。如果我们能够想象受难者的全部痛苦,就必然会更加真诚地同他们一起去反对欺压他们的行动者;就会更加迫切地赞成他们所有的报仇意图,那种惩戒是因为他们的罪行而导致的。对于这些骇人听闻的暴行得到应有的惩罚会产生兴奋,还有对于他逃脱了这种惩戒时表现的愤恨,总之,我们对这种恶有恶报和惩罚恰当合适地落在一个应得的人身上,以及能够使之感到痛苦的所有东西,都来自一个旁观者心中自然而然的愤慨。——无论什么时候,旁观者都对受难者的境遇了如指掌。
而对于大多数人来讲,以这种方法把我们对恶有恶报的自然情感归于对受难者的愤恨所产生的同情,看起来可能是对人类情感的贬低。愤恨一般会被认为是一种不可爱的**,以至于人们常常认为,对于恶有恶报这类如此值得称许的情感是不会全然建立在愤恨上的。也许人们更愿意这么说:我们对善有善报的感情是建立在对从善行中得到好处的人的感激之情抱有同情的基础上的;因为如同其他的善良**一样,感激被认为是一种仁爱的原则,它必然不可能建立在有损任何感激的情感和精神价值上。但是很明显,愤恨和感激在所有方面都是互相对立的。
让我们来想想以下的情况吧。虽然我们经常会看到不同程度的愤愤不平,它是所有感情中最难以控制的一种,但是如果它能够适当地压低或者降到和旁观者怀有的愤恨一样程度的话,就不会受到什么责难了。如果我们身为一个旁观者,感到自己的愤恨和受难者的愤恨完全是一样的;如果后者的愤恨在哪个方面也没有超过我们的愤恨;如果他的每个手势甚至每句话都没有表现出比我们更加强烈的情绪的话;如果他并不想给对方什么超越了我们想要看到的惩戒,或者我们为此更加想要惩戒对方,我们就一定会完全赞同他的情感。按照我们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情绪必然是证明了他的情绪是正确的。而且,经验也证明,绝大部分人都不怎么能控制这种情绪,更何况要把缺乏修养、情不自禁、压抑强烈的愤恨变成合宜的情绪,需要做出很大的努力。因此,对那个看来可以努力自我驾驭天性中最难以控制的**的人,我们自然会产生相当的钦佩和尊敬。当受难者的愤恨和往常一样超过了我们所能赞同的最大限制时,我们当然不能对此表示赞同也不可能对此谅解。我们不赞成那种程度的憎恨,甚至超过了我们不赞成其他在想象中出现过的同样过分的**。我们不光是不赞成这种过分强烈的愤恨,甚至把它当作是我们憎恨和愤愤的对象。当这种感情在公众里通常以这样一种方式——过分百次而只节制一次——显现出来的时候,由于它最最普遍的表现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很容易把它当作可恨可恶的感情。但是,就算是拿眼前人们的堕落来说,上帝也没有这么无情地对待我们,赋予我们以罪恶的天性,无论是从不同的方面还是从整体;无论是从赞同还是期许的合宜对象来说。在某些情况下,我们感到这种平时是过分强烈的感情可能也是很微弱的。我们有时候会抱怨谁显得勇气不足或者过分不在乎自己所受的伤害;和我们由于他的这种感情过分强烈而表示对他厌恶一样,我们由于他的情绪过低也会对其产生轻视。
如果那些有灵感的作家们觉得,像人类这种软弱与不完整的生灵,所有程度的情绪也是罪过或者邪恶的话,那么,他们也一定不会那么经常地、激烈地讨论上帝的暴怒和愤慨了。
让我们再来思考这样一个问题:目前的研究不仅仅是一个涉及正确与否的问题——如果允许我这样说的话——而是一个有关事实的问题。我们现在并不是在思考:在何种原则下一个完美的人会赞成对恶劣行为的惩罚;而是思考:在什么样的原则下一个像人这样如此软弱和不完整的生灵会真正赞成对恶劣行为的惩戒。显而易见,我现在提到的原则对于他的情感具有很大的影响;并且,“恶劣行为应该得到惩罚”似乎是理所应当的。正是社会的存在需要用恰当的惩罚去限制不应该和不正当的愤恨。于是,对那些怨恨加以惩戒会被看成是一种合适的和值得赞扬的做法。因此,即使人类自然地被赋予一种追求社会幸福和保护社会的欲望,那上帝也并没有委托人类的理性去发现运用一定的惩戒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手段;取而代之的是赋予了人类一种直觉和本能,赞同运用一定的惩戒是达到这个目的的最佳方法。上帝在这一方面的精细和他在其它很多情况下的精细确实是一致的。至于所有那些目的,由于它们特殊的重要性可以说是上帝所中意的目的——如果可以这样表达的话。上帝不仅这样始终如一地使得人们对于他所中意的目的具有一种强烈的欲望,而且为了人们自身的原因,相同的使他们具有对一些手段的欲望——只有依靠这种手段才能达到这些目的,而这同人们产生它的倾向是没有关系的。因而,自卫、种的繁衍就必然成为上帝在构造一切动物的过程中已经确定的重要目的。人类被赋予一种对那两个目的的强烈欲望和一种对同二者相反的东西的厌恶;被赋予对死亡的惧怕和对生活的热爱;被赋予一种对种的延续和永存的欲望和一种对种族灭绝的想法的惧怕。然而,虽然上帝这样地赋予我们一种对这些目的非常强烈的欲望,并没有把发现、达到这些目的的合适手段寄托于我们的理性中缓慢而不确定的判断。上帝通过直接和原始的本能引导我们去发现、达到这些目的的绝大部分手段,口渴、饥饿、两性结合的**、害怕痛苦、快乐幸福,都促使我们为了自己去使用这些手段,丝毫不去考虑这些手段是否真的会导致那些有益的目的,就是伟大的上帝想通过这些手段达到的目的。
在结束这段注解之前,我必须说行为合宜性的赞同和对善行或者优点所表示的赞同之间的差异。当我们赞同任何人的适宜的感情之前,不仅必须要像他一样被感动,而且还要察觉我们和他在感情上的一致。这样,就算听到落在朋友身上的什么不幸时,我们会正确地想象出来他过度忧虑的心情;但是在知道他的行动方式之前,在发现他和我的情绪是协调一致之前,我不可能说我赞同那些影响他行为的情感。所以,合适的赞同需要的是感情的一致和对行动人的完全同情。相反的是,当我们听到另一个人获得恩惠,让他按自己所喜欢的方式受到感动时,如果我清楚地知道他的情况,感觉到他的感激之情是来自心底的,那么我们必然会赞同他的恩人的所作所为,而且还会觉得他的行动是值得赞扬和报答的。不难看出,受惠者是否怀有感激之情丝毫不会影响我们对施恩者所持的感情。所以,这里不需要感情上的完全一致。这足以证明:如果他怀有感激,那么它们必然是一致的;而且我们对有点的感觉常常是建立在虚幻的同情上。所以,当我们明了地知道别人的情况时,才会常常为某些当事人不会感动的方法受到感动。在我们对缺点所产生不赞同和对不合时宜的行动所产生的不赞同之间是有那么一些类似的差异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