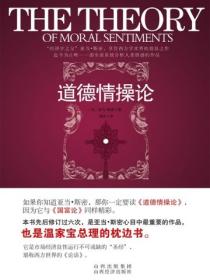第三章 论自我克制
依照完美的谨慎、严格的正义与恰如其分的仁慈等准则来要求自己行为的人,可以被称为具有完善美德的人。但是,仅仅只是正确地了解这些准则,并不能确保人们会以这种方式行事。人们内心的**与冲动总能引诱人们背弃冷静清醒时拥戴的一切准则而轻易地将他们引入歧途。如果没有完善的自制力,即使对那些高尚的准则有着最充分的了解,也无法使人们成为具有完善美德的人。
古代一些优秀的道德学家曾经把这些**与冲动分成两种不同的类型来进行研究。第一,强烈而短暂的**——有时甚至是一时的冲动——需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来抑制;第二,微弱却持久的**——可以轻松加以抑制,但它的连续而频繁出现却更容易将人们引入万劫不复的深渊。
恐惧和愤怒连同其它与它们相关的情绪,构成了第一种类型;对安逸、享乐、赞美等能够满足个人欲念的事物的喜爱,构成了第二种类型。强烈的恐惧和愤怒,通常难以在片刻间加以抑制。对安逸、享乐、赞美等能够满足个人欲念的事物的喜爱,虽然可以做到片刻的抑制——甚至一段时期——但是,它们对人们的的引诱是无休无止的,因而常常将我们带入歧途,**我们做出为之悔恨终生的事情。前一种**促使我们背离自己的职责,而后者则是引诱我们背离自己的职责。那些古代道德学家将对前一种**的控制称作意志坚定、坚毅和刚强,而将对后一种感情的控制称为取予有节、庄重和谨慎。
对上述这两种冲动**的克制就是一种美,这种自我克制的行为本身就应该得到一定程度的尊敬和赞美。这种美与从自我克制中得到的好处,以及在这种克制下我们谨慎、正义和合宜的仁慈的行为本身之美无关。在一种情况下,这种努力所表现出来的力量和高尚激起了某种程度的尊敬和称颂。人们的自我克制之所以能够得到某种程度的尊敬和赞美,是因为作出这种努力所表现出来的可贵的人格力量、坚忍不拔与长久的一致性。
坚忍之人——面对危险、困苦,甚至濒临死亡之时,能够保持如同平日的镇定,泰然处之,并且能够不违背自己的良心,不说不公正的话,不做不公正的事——这样的人,必然能够得到高度的赞美与钦佩。如果他出于对人类以及自己国家的热爱,在争取自由和正义的事业中罹难,那么人们对他受到的苦难最深切的同情,对迫害他的不义之人最强烈的义愤,对他高尚的志愿最由衷的感激,对他的品质的最深刻的理解,都与对他高尚行为的钦佩融为一体,并且常常激起这种情感,使其转化为最狂烈的崇拜。从古至今,深受人们喜爱和怀念的伟大英雄往往都是这样——他们为了争取真理、自由和正义的事业而牺牲在断头台上,并且至死不曾丢弃自己的身份与尊严。如果苏格拉底的敌人容许平静地死在他自己的**,那么这个伟大的哲学家便不可能受到如此由衷的赞誉,获得如此令人眩目的光环。这样的光彩在后世的仁人志士中时常可见。当我们欣赏弗图和霍布雷肯雕刻的杰出历史人物头像时,很难有人不感到,那些雕刻在一些最杰出的人物——托马斯·莫尔、雷利、罗素、西德尼等——头像下面那把作为砍头标记的斧子,更显示出了他们真正的尊贵和情趣,这远比人们自己佩带的纹章等无用的装饰物优越得多。
这种高尚的行为不只能给清白有德之人的品质增添光辉,它甚至使拥有它的囚犯也能受到亲切的敬意。当一个窃贼或拦路强盗庄重和坚定地出现在断头台上时,虽然我们完全赞成对他的惩罚,但我们难免会感到惋惜:一个具有优异和卓越才能的人,竟然会犯下这样卑劣的罪行。
战争是人们获得和锻炼这种高尚品质最好的学校。正如我们所说,世间最可怕的事情莫过于死亡,而克服了对死亡恐惧的人,在面对任何其它的自然灾难时都能临危不乱,泰然自若。战争让人们逐渐熟悉了死亡,从而消除了意志薄弱和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对死亡迷信的恐惧。他们只把死亡看作是生命的终结——仅仅是一种厌恶的对象——正如生命是人们所追求向往的对象一样。他们也从经验中了解到:许多表面看来很可怕的危险,并不像它们所显现的那么恐怖。如果我们鼓起勇气、开动脑筋和沉着应对,就很有可能从最初看来毫无希望的危险处境中获得生机。因此,他们对死亡的恐惧便可大为减轻,而从中逃脱的信心或希望则得到了相应的增强。当他们处在危险之中时,他们学会了顺应与轻松面对,不会慌不择路地急于逃避。正是这种对危险和死亡习惯性的蔑视,使得军人的形象格外高大,军人的职业格外高尚,并且在人们的意识中,这种职业同其它职业相比显得更为可敬可贵。在为自己的国家服役期间,成功地履行军人的职责,英勇地为国效力,似乎在每个时代都是人们所喜爱的英雄的显著特征。
战场上建立的丰功伟业,虽然不符合一切正义的原则与信念,并且丝毫没有人性,但却往往能够引起人们浓厚的兴趣,甚至原本可能毫无可取之处的指挥者也会因此博得一定程度的尊敬。我们甚至对海盗们的冒险也有着不凡的兴致,我们会怀着某种尊敬和钦佩的心情来读那些卑猥而毫不足取的人们的历史,因为他们在追逐那些罪恶的目标时,忍受并克服了历史课本中难以描述的危险、艰辛与困苦。
通常情况下,对愤怒的克制似乎没有对恐惧的克制那样崇高。从古至今的著名辩论中,往往是对正义愤慨的恰如其分的表达构成了最精彩最令人叹服的段落。雅典的狄摩西尼痛骂马其顿国王的演说,西塞罗控诉喀提林党徒的演说,都是因为对这种愤慨的恰当表达而得以流传千古。但是,这种合宜的愤怒都是经过抑制并缓和到公正的旁观者能够给予理解与同情的范畴。超过这个界限的过激的愤怒与吵嚷的冲动,总是令人不快和厌恶的。使我们更感兴趣的,是愤怒的对象而非这个发怒的人。通常情况下,宽恕这种高尚的品质比最合宜的忿恨更为合理。无论引起愤怒的一方是否做出了合宜的道歉,为了公众的利益需要与最可恨的敌人联合起来以便履行某项最崇高的职责时,那个能够抛去心中一切敌意,对那些曾经做过最激烈斗争的人们**真诚、相互协作的人,似乎应当得到我们高度的钦佩与赞扬。
然而,对愤怒的克制,并不总是显得如此慷慨壮烈。恐惧出现在愤怒的对立面,常常也是抑制愤怒的动机。若恐惧压抑了愤怒,我们无法将这种卑微怯懦当作一种高尚。愤怒使人好斗,而纵容愤怒有时似乎显示出某种大胆无畏的品质。虚荣的人往往纵容愤怒,却从不纵容恐惧。那些爱好虚荣却外强中干的人,在他们的下属或不敢反对他们的人面前,常常摆出一副昂扬激奋的样子,自以为这样便显示出了所谓气魄。无赖混混总是喜欢编造许多谎言,将自己描述得凶狠残暴,他认为这样一来,在听众的心中自己就算不是一个可亲可敬的人,起码也是一个可怕的人。现代的风气鼓动人们去决斗,在一定程度上甚至可以说是鼓励私人复仇,这种风气在很大程度上是因恐惧而抑制愤怒的行为变得更为可鄙。不管以什么动机为依据,在对于恐惧的抑制之中,总存在着某些高尚之处,而对于愤怒的抑制则不然。对愤怒的抑制除非是基于体面、尊严与合宜的意识为基础,否则很难得到一致的赞同。
在没有面对什么特别**的时候,按照谨慎、正义和仁慈的准则行事,似乎并不显得十分高尚。然而,处于巨大的危险和困境之中小心谨慎地冷静行动;诚挚地遵循神圣的正义准则;不受那些会将我们带上歧途的利益的**;不理会企图激怒我们去违反这些准则的重大伤害;不因为那些忘恩负义的小人而妨害我们的仁慈之心——这些都属于最高贵的智慧与最完善的美德。自我克制不仅本身是一种重要的美德,而且,所有其它美德的主要光辉大都也源于自制。
对恐惧与愤怒的抑制,都是伟大而高尚的自制力量。当我们为正义与仁慈所驱使而这样做时,不仅表现出伟大的美德,而且为其他美德也增添了光辉。然而,它们有时也会被截然不同的动机所驱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自我控制本身仍然被看作是伟大而值得尊敬的,但它们很可能会是极端危险和可怕的力量。不避斧钺的勇猛可能会被用来犯下滔天恶行;表面上的平静和开朗有时可能隐匿着坚定而残忍的复仇决心。虽然卑鄙的念头玷污了这种压抑的力量,但是不持卑劣看法的旁观者常常会对此表示出高度的钦佩。学识渊博的历史学家达维拉常常称颂美第奇家族中的凯瑟琳的巧伪趋利;严肃认真的克拉伦敦勋爵颇为赞赏迪格比勋爵及其后布里斯托尔伯爵的虚伪掩饰;很有见地的洛克先生十分欣赏沙夫茨伯里伯爵的虚伪隐忍。甚至西塞罗似乎也认为这种欺骗虽不算崇高,但也并非不适用于灵活机动的斗争方式,从总体来看,还是值得赞同和尊敬的。当山河动**,国家大乱,出现激烈的党争和内战之时,这种隐秘的掩饰和工于心计的欺骗就会悄然生长。当法律变成了一纸空文,清白无辜者的安危不能得到保证之时,为求自保,大部分人面对占上风的政党不得不采取表面上的顺从,阳奉阴违、见风使舵。这种虚伪的品质,常常与冷静坚毅的态度和毅然决然的勇气为伴。运用这种伪诈需要极大的勇气,正如确认死亡需要经过某种鉴定一样。它通常可以用来加强或减弱对立党派之间的深切敌意,而正是这种敌意滋长了伪诈的品质。虽然它有时会派上用场,但是它的危害也是显而易见的。
对那些不很强烈和狂暴的**的抑制似乎更有益处,因为它们不易被危险的动机所利用。节制、庄重、谨慎和适宜,都被认为是是无害而可爱的。受人喜爱的单纯质朴,令人敬重的勤奋节俭,都来自和缓而不懈地自我克制,并且伴随着它们与生俱来的朴实的光彩。那些行走在幽静的生活之路上的人们,因为缓而不懈地自我克制而显得优美和典雅;这种优美和典雅,虽然没有绚烂夺目的光彩,但其令人喜爱的程度却并不逊于英雄、政治家和议员彪炳千古的丰功伟绩。
在从几个不同的方面对自我克制的性质做了说明之后,我认为再没有必要进一步详述这种美德了。现在我只打算探讨合宜的程度:即公正的旁观者所感受与赞成的**程度,这种合宜的程度因不同**而改变。对于某些**,其过分比不足更让人觉得舒适,即这种**达到的合宜程度比较高,或者说它更接近于过分而不是不足。对于另一些**,人们持有相反的意见,其不足比过分更令人觉得舒适,即这种**达到的合宜程度比较低,或者说它更接近于不足而不是过分。前者是旁观者最乐于接受和同情的**,而后者则恰恰相反。前者是当事人即时的感受合乎心意而表达出的一种**,容易被旁观者所接受;后者则是当事人即时的感受不合心意而表达出的一种**,不易被旁观者所接受,有时甚至会被厌烦。这可以被看作一条普遍准则,目前为止,在我的考察之中尚未出现一个例外。不用很多例子便马上就能充分地说明并证实这条准则。
那些有助于人类团结的感情,即仁爱、慈悲、天伦之情、友爱、尊敬等情绪,即使有时会显得过分,也不会被人讨厌。虽然我们有时会抱怨这种过分的感情,但仍然会以同情甚至是亲切的方式看待它,而不会厌恶它。人们对它的过分更多感到的是遗憾而非愤怒。通常情况下,对于这种感情的发出者来说,放纵这种过分的感情是愉快而且令人兴奋的。然而在很多时候,尤其当这种过分的感情被施加在忘恩负义者身上之时,常常使这种感情的发出者感到深切的苦恼。不过即便如此,善良的人也会对此报以极大的同情,同时对那些忘恩负义麻木不仁的人表示出极大的愤慨。与此相反,那些对别人的痛苦麻木不仁无动于衷的铁石心肠——被我们归为感情不足的一类人,当他们陷入困境,也会受到相同的对待;而且,由于他不会获得任何的友谊与亲情,也就无法享受到世上一切最好的情谊。
使人们产生隔阂,阻碍人们团结的感情,即愤怒、憎恨、妒忌、怨恨等情绪,其过分比不足更易使人不快。过分地具有这类感情的人,自己也会感到卑劣可耻,更会使其成为他人所厌恶甚至憎恨的对象。缺乏这种感情虽然也是一种缺陷,但往往不会受到人们的责难。对一个男人来说,缺乏正当的义愤是其品质中致命的缺陷,这使他没有能力保护自己或他的朋友免受侮辱和侵犯。作为人类的本能,愤怒和憎恨也是有缺陷的。过分和没来由的愤怒和憎恨便是令人厌恶的妒忌。妒忌是这样一种**,它让人们怀着恶意用厌恶心情来看待正人君子身上所体现出的一切与之相称的优势。然而,那些在重大选择上软弱退缩,毫无原则地容忍鄙陋之人凌驾于自己之上的人,被斥责为没有骨气的软弱的人。这种软弱,通常表现为慈悲、圆滑、逃避争斗、惧怕混乱和求饶,有时也出现在不合理的宽宏大量之中。具有这种宽宏大量的人幻想自己可以藐视一时的利益,于是在面对纷争时,十分轻易地放弃了它。然而,伴随在这种软弱之后的常常是强烈的懊丧和悔恨;最后常常演变为对那些合理获得自己利益者的最恶毒的妒忌与憎恨。为了能够在世界上舒适惬意地生活,在任何情况下都有必要像维护自己的生命和财产那样,去维护自己的尊严和地位。
对我们个人的挑衅所带来的感受,与我们对危险和痛苦的感受一样,它的过分比不足更令人感到厌恶。在人类所有品质中,懦夫的品质最为可鄙,而在最可怕的危难中平静而无畏地面对死亡的品质最为可敬。我们由衷地尊敬那些以昂然自若的气概和坚忍沉着的态度来忍受痛苦甚至折磨的人;反之,我们很难尊重那些在痛苦和折磨面前意志消沉,只会像妇人那样哀号痛哭的人。那些对每个微小的不幸都过于敏感而烦躁不安的人,是多么地可怜和令人厌倦。一个坚定沉着的人从不允许日常生活进程中的微小伤害或微不足道的挫折打扰自己内心的平静;然而面对侵扰世界的自然与道德的邪恶之时,他会期待并甘于忍受来自它们的痛苦,因为这样对他本身来说是一件幸事,也给他的所有伙伴带来安宁与舒适。
我们对自己所受到的伤害和不幸的感受,有时会非常强烈,有时也可能非常微弱。面对自己的不幸如同槁木死灰般无动于衷的人,对他人的不幸必然也不会有所感触,更不用说去帮助他们解除不幸了。对自己蒙受的伤害没有什么感触的人,必然会对他人蒙受的伤害视而不见,并且更不愿意去保护他人或为他人复仇。对人类现实生活中的各种变故视而不见、麻木不仁,必然会消减对自己行为合宜性的一切热诚的关注。恰恰是这种关注,构成了美德的真正精髓。如果我们对自己的行为的后果漠不关心,我们也不会关心自己这些行为的合宜性。能够感受到降临在自己身上的灾难所带来的全部痛苦,能够感受到自己蒙受的伤害所具有的一切卑劣品性,能够更强烈地感受到自己的品格所应具备的尊严,能够不被自己本能的**所摆布,而是按照自己内心中那个上帝的使者所指定和赞许的情绪来支配自己的全部行为举止——这样的一个人,才是真正具有美德的人,才是值得热爱、尊敬和钦佩的对象。麻木不仁与那种以尊严和合宜的意识为基础的高贵的自我克制——即高尚的坚定,绝不相同,过度的麻木不仁会使高尚的自我克制具有的价值全然丧失。
虽然对于个人所遭到的伤害、危险和不幸的麻木不仁会使自我克制的价值化为乌有,但是,上述感受却却往往得到过分的表现。当合宜感——人类内心的高尚法官能够克制这种对痛苦、伤害的过分的感受时,这种行为必然会显得非常的高尚和伟大。但是,这种克制所要付出的努力是巨大的,并非人人都能做到。一个人,通过付出坚韧不拔的巨大努力很可能在行为上表现得完美无缺,但是,在内心之中,两种本性之间的争执、思想的冲突,有可能过于激烈,以至于难以获得平静。上帝已经赋予明智的人强烈而敏锐的感受,而且这种感受并没有因早期的教育和锻炼而减弱,但他会在职责和合宜性所许可的范围内回避可能对自己带来伤害的境况。对于精神和肉体的痛苦都过于敏感的人,不应从事军人的职业,也不能轻率地投身于派系的争斗。虽然合宜感会努力克制那些冲动与**,但内心的平静却总是在斗争中首先遭到破坏。当这样的感情骚扰频繁出现时,理性的判断也并不总能保持平常的那种敏锐与精确。虽然他起初总是打算采取合宜的行动,但最终往往还是会轻率地采取行动,以至于使他在自己今后的生活中将永远感到羞耻。刚毅、坚强的性格,无论是先天的还是后天的,对自我克制这种高尚的努力来说,无疑是十分必要的。
战争和派系争斗虽然是塑造人们坚强果敢性格的最好学校,是医治人们懦弱卑猥的最佳药物。然而,如果在课程完全结束之前,在药效完全发挥之前,激烈斗争的考验就不期而至的话,其结果就很难令人满意。
我们对人类生活中的欢娱与享受的感受,同样会因其过分或不足而带来种种不快。然而,相较两者,过分的快乐似乎并不像不足那样使人感到不快。无论是旁观者还是当事人,对欢娱与享受的强烈癖好,必然比麻木不仁更令人愉快。人们往往迷恋于年青人的欢乐,甚至是孩童的嬉戏,而且对老年人的那种单调乏味的庄重守旧感到厌烦。确实,若这种对快乐的追求没有被合宜感所抑制,尤其是当它同周围环境、同当事人的年龄或地位不相称,并且沉迷其中以致忽略自己的利益和职责时,这种追求就会被认为是过分的,并且是对个人和社会都有害的。然而,在通常情况下,备受指责的并不是对欢乐的强烈癖好,而是合宜感和责任感的缺乏。如果一个年轻人对适合他年龄的消遣和娱乐毫无兴致,只会谈论书本教条和功业,人们并不会因他的清心寡欲而称赞他,即使他从不沾染那些不合宜的纵情享乐,相反,他往往会因为迂腐古板而受到人们的厌弃。
自我评价有可能会太高,也有可能会太低。对于大部分人来说,高估自己总是令人愉快的,反之则不然。然而公正的旁观者也许会持有截然相反的看法,在他们看来,低估自己恐怕要比高估自己更令人感到舒适。就我们身边的同伴而言,他们对自己评价过高总是比过低更容易受到我们的反感。当他们在我们面前摆出一副盛气凌人高高在上的姿态时,我们的自尊心往往会受到伤害。我们的自尊和自负会促使我们去指责他们的自尊和自负,此时,我们便不能再作为他们公正的旁观者了。然而,如果我们的同伴能够容忍他人在自己面前趾高气扬装模作样,我们就会责备他,甚至认为那是可鄙的。相反,如果他们努力在人群中脱颖而出,甚至爬到和他所具有的优点不相称的高位,那么,虽然我们可能不完全赞成他们的行为,但仍旧会替他感到高兴。而且,在内心中没有妒忌的情况下,我们对他到达高位而产生的不快,总是大大少于他们容忍自己被贬低时产生的不快。
在评判我们的品行的优劣上,有两种不同但都很常用的标准。一种是金科玉律般尽善尽美的标准,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认可的;另一种标准在其之下,通常只要付出努力,最平凡的人也能够达到,是我们自己、同伴和对手——我们生活中的大多数人都能符合的标准。在我们试图评价自己时,或多或少地都会注意到这两种不同的标准。然而,不同的人,甚至相同的人处在不同的环境中总是产生不同的注意力,有时倾向于前一种标准,有时倾向于后一种标准。
当我们采取前一种标准进行评判时,即使是我们中间最有智慧和最优秀的人,在自己品性中也只能看到缺点和不足。除了能找到表示谦逊、遗憾和悔改理由之外,我们再也没有什么理由来自命不凡和自以为是。而当我们采取后一种标准进行评判时,我们会感到自己真正达到或者达不到我们用来衡量的那个标准。
具有智慧和美德的人往往将注意力集中于完美无缺的标准。在每一个人的心中都存在着这种标准,它是人们在对自己和他人的品行的长期观察中逐渐形成的,是良心这个判断行为好坏的伟大的法官和仲裁者日积月累,循序渐进、逐步加工而成的标准。每个人都会持有这种观念。根据为此付出的那些观察的细致程度和精确程度,以及进行那些观察的专心程度的不同,每个人对这种标准的掌握程度也不相同,但整体的色调都是协调的,所勾画出来的轮廓也是逼真的。具有智慧和美德的人,天生就具有细致和精确的感受能力,他为了进行这种观察时而倾尽全力。在他的不懈努力之下,色彩和轮廓上的特征每天都有所改进。由于他比其他人为此付出的努力更多,所以他的理解更加深入,并在自己的心中塑造了更接近于准确的模型,从而更加深切地沉溺于它那高雅而神妙的美。他竭尽所能地临摹那位非凡的大师所创作出的完美作品,但却难以做到尽善尽美。他面对永远无法达到上帝作品之完美精确的复制品,感到自己一切努力都存在着缺陷,并因此怀抱忧伤和羞愧的忏悔:自己是多么地缺乏注意力和判断力,从而在行为和谈吐上都无法达到那完美合宜的法则,并且就这样偏离了那个他想要用来塑造自己品性和行为的模型。然而,当他把自己的注意力转向第二条标准,即他身边的人通常能达到的那种标准时,他就会意识到自己的长处了。可是他主要的注意力总是集中在前一条标准上,因此他从中所受到的打击远比从他处得到的补偿要高得多。他从不会因此自视甚高以致傲慢地看不起品质不如他的那些人,因为它对自身的不足了如指掌,也十分清楚在追求完善品质的路上所要遇到的困难,所以他不会抱着不屑与轻蔑的态度来看待他人更加明显的缺陷。他决不会因其卑猥而侮辱他们,而总是怀着宽厚的同情去看待他们,并且乐意以自己的劝告和体会来督促他们进步提高。没有一个凡人能真正做到完美无缺,以致不会有人在一切方面都胜过他人。所以如果有人一时在某个方面胜过了他,他决不因此妒忌他们的优点,因为他明白,要超过自己是多么地不易,所以他对他们的优点总是抱以真诚的敬意,并且必然给予他们应得的高度赞许。总之,真正的谦虚、客观地评估自己和他人的优点的良好品质,会烙印在他的心中并且体现在他一切行为和举止上。
在所有具有自由和有独创性的艺术形式中,如绘画、诗歌、音乐、辩论和哲学中,最伟大的艺术家总是最谦逊的,因为他比任何人更清楚地认识到,即使是自己最优秀的作品,同他观念中形成的完美作品相比,还会存在着很大的差距。对于这种完美作品他在心中已经形成了某种观念,他竭尽全力地模拟它,但也无法指望自己能模仿得一模一样。只有低等的艺术家才为自己的成就沾沾自喜,因为他们几乎没有形成尽善尽美的概念,甚至从不加以考虑,而且他们更愿意和其他的艺术家相比,甚至是不如他们的。伟大的法国诗人布瓦洛常常说:没有一个伟大的艺术家曾经对自己的作品感到十分满意,尽管他的某些作品或许并不比从古至今的同类诗歌差。他的老朋友桑托伊尔,只创作过一些中学生水平的拉丁诗作品却喜欢幻想自己是一个诗人,而且是作出对自己的作品十分满意的样子。布瓦洛用可能是狡黠的双关语来回答他:他当然是这方面有史以来唯一一个伟大的人。布瓦洛总是用他在诗歌领域里最完美的标准来考量自己的作品。我相信布瓦洛已经尽了一个人所能作出的最大努力,去深入地探求这个标准并力图精确地把它表现出来;而桑特维尔主要是用同时期其他一些拉丁诗人的作品来考量自己的作品,如此比较,他的水平当然是不低的。这样看来,倾其一生去进行努力,而使自己的言谈举止始终符合那完美的标准是十分困难的,相比之下,制作一个精美的艺术品要容易得多。艺术家总是投入其全部技能、经验和知识,从容不迫地从事他那宁静的创作工作。聪明人在任何时候——健康时或者患病时、成功时或者失意时、劳累或者清闲时——都必定保持自己行为的合宜性。他从不会因突如其来的困难和不幸而惊惶失措,不会因他人的不义之举而采取不择手段的行动,不会因激烈的派系斗争惶恐万状,也不会因残忍的战争而亡魂丧胆。
当人们更关注于第二条标准——人们通常能够达到的那种平常程度的优良品质,并以其来评价自己的优缺点,判断自己的品质和行为时,很多人都会真切地感到自己的所作所为已然大大超过了这条标准,这是正确的,也被公正的旁观者所承认。然而,若这些人的主要注意力总是指向一般的标准而不是观念上的完美标准,他们就难以意识到自己的缺点和不足,所以他们常常是狂妄自大盛气凌人的。他们还热衷于赞美自己和轻视别人,虽然他们的品质并不十分端正,更不具备真正谦虚有德之人所具备的那种优点,但是,他们那极端的自我赏识与自以为是还是能迷惑民众,甚至常常使高明的人也受到欺骗。民间那些冒充内行的骗子不学无术却往往获得惊人的成功,这足以说明民众是多么容易被走花溜水的自我吹嘘所欺骗,从而成为他们的崇拜者。而且特别是当这些吹嘘被某种高度真实的优点所维护时,当它们被夸夸其谈的卖弄渲染的金碧辉煌时,当它们得到位高权重者的支持时,当它们偶尔成功并且为此博得民众的高声喝采时,即使清醒的聪明人也难免失去主见,和愚民一起沉湎于崇拜迷信之中。正是这种愚蠢的喝采与膜拜常常将理智的人心搅乱。而且当远远的注视那些伟大人物时,人们往往会怀着某种真诚和钦佩心情去敬仰他们,有时会更甚于骗子的自我吹嘘。当内心没有妒忌的时候,人们都乐于钦佩甚至崇拜别人,并且自然而然地在自己的心意中将那些高高在上的家伙塑造成圣人的样子。或许这些所谓的伟大人物过分的自我赞美是很容易理解的,不熟悉他们的人常常怀着尊重甚至几乎是崇敬的心情去听信那些夸耀,而能够洞悉真相、了解情况的聪明人只会对这种无耻的夸耀嗤之以鼻。几乎在所有时代中都有这种情况:大部分声名显赫、威风八面的人物,在相隔多年的后世中变得一文不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