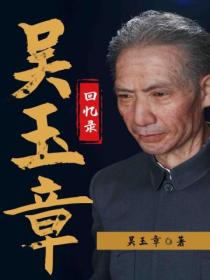汪精卫刚到武汉,仍伪装革命的样子。“四·一二”惨案发生后,汪也跟着别人拍桌子,大骂蒋介石,但是他骨子里却无时无刻不想反共。他住在谭延阆家里。谭的家里有一个四川名厨师,做得一手好菜。谭延阊家是个地主阶级的大本营。、湖南许多地主遭到了当地农民的清算,都跑到谭延闾那里去造谣诽谤。汪精卫不仅吃了许多四川菜,同时也喝了许多地主的迷魂汤,于是就显出了他的反革命面目。他一见我们,就叫喊说农民运动搞的太过火。陈独秀也跟着帮腔。有一次,不知哪个地主造谣,说某某司令的母亲因为是小脚就被农民解去脚布,用箩筐抬着游街;又说某地农民协会扣留了政府的粮米,不让运出去。汪精卫借题发挥,暴跳如雷地说:“这不是造反吗?岂有此理!是政府管农会?还是农会管政府?”陈独秀也在一边应声:“是谁在湖南搞的?简直是乱搞!”
汪、陈到武汉之前,我们本来想建立一支完全由我党所掌握的军队,因此决定把共产党员连某所指挥的一个营扩充为一个师。人员、粮饷、军械都已经筹划好了。当时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政府中占优势,工农革命情绪又很高,所以干起什么事来都很顺手。可是陈独秀来了,附和谭延阊的意见,说什么计划中配备的枪槭比別的军队都好,怕引人妒忌;他又说自己建立军队,太惹人注目等等。就这样前怕狼、后怕虎,这一师军队始终没有建立起来。
1927年4月下旬,我党在武汉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但这次大会实际上并未解决任何问题。陈独秀只是表面上承认了一下错误,而大会竟仍然选他作党的总书记,这样就使他的机会主义路线得以继续执行和发展。我虽是四川省的代表,但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因为怕暴露了共产党员的身份不好在国民党内工作。可是大会开完后不久,陈独秀却故意地给我暴露了。他在《响导》上转载了高一涵的一篇文章,说在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中只有某某几个人是共产党员,决不可能操纵国民党,想以此来表白对国民党的忠心。这简直等于告密,给我以后在国民党内的工作增加了极大的困难。我见了这篇文章很生气,立刻跑去质问他。但他却厚颜无耻地说:“为了这件事,我一夜没有睡,想来想去觉得还是把你们几个人公开了好。”原来陈独秀反复考虑的结果是不惜牺牲一切以讨好国民党,他的机会主义毛病实已深入膏肓,无可救药了。
那时武汉政府派出继续北伐的军队,在河南受阻。1927年4、5月间,战事相持于遂平一带。随着战争的停滞,促使军队进一步分化。5月17日,驻在宜昌的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蒋介石的挑唆下发动了叛变。我们正在开会,听到夏斗寅部已经到了武昌附近的纸坊,立即要进城。大家忙着找叶挺去抵抗。一时之间,又找不到。徐谦、顾孟余这些投机政客一见大势不好,都悄悄地溜走了。后来通过电话找到了叶挺,才知道夏军已经被叶的部队打垮了。当时叶挺领导着他的部队和黄埔军校武汉分校学生组成的队伍把叛军打得一败涂地。如果叶军一直把叛军追到岳州,完全可能把它一鼓歼灭。可是汪精卫主张调解,唐生智这时也说他可以招呼夏斗寅。于是派了陈公博等进行调解。反革命打我们,没有人出来调解;我们打反革命,“和事佬”就这样多。武汉政府中的那些反动分子的反共意图,已昭然若揭,可是陈独秀还在那里跟他们无原则地大讲“团结”,对农民运动泼冷水,说农民运动搞得“过火”。
夏斗寅叛变后,湖南的反革命势力起而呼应。5月21日,第三十五军许克祥团在长沙发动叛变,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大肆屠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这就是血腥的“马日事变”。当时长沙附近各县的工人和农民义愤填膺,集合十数万人准备于5月30日进攻长沙。长沙只有许克样一个团的兵力,只要我们领导上坚决一点,消灭这支叛军,可以说是瓮中捉鳖。汪精卫听到消息,大发脾气,指责我们不该打许克祥。陈独秀就赶快下命令取消进攻长沙的计划。大多数部队接到命令后停止了行动,只有其中一支工农部队没有接到停止进攻的命令。5月30日,这支工农部队单独攻扑长沙,由于没有其他方面的配合,结果失败了。这次失败完全是陈独秀机会主义的错误。事后汪精卫还讥笑陈独秀:“你们十万大军怎么连许克祥的一个团也打不赢。”反动派就是这样可恶,你越让步,他就越嚣张。象这种让步完全是软弱的表现,怎能达到团结的目的呢?
5月30日,武汉政府的北伐军打下了郑州,与冯玉祥在西北的国民军取得了联络。这是一个喜讯,但喜讯中也包含着噩兆。因为在机会主义的领导下,党在政治上不能振作起来,那末军事上的每一步进展就只能成为革命阵营内部进一步分化的契机。6月10日,汪精卫、唐生智、谭延阊、徐谦、邓演达等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会议是秘密进行的,我身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和政治委员,对会议内容也一无所知,可见汪精卫是如何处心积虑地来对付我们。他们从郑州回来后,我只见邓演达垂头丧气,情绪消沉。6月19日,蒋介石又和冯玉祥举行徐州会议,决定分共与宁汉合作。冯玉祥给汪精卫打来一个电报,说已在徐州与蒋介石开会商谈。那时我是国民党中央常委兼秘书,一切重要文电都由我经管,我看到这个电报十分惊异,就问汪精卫:“冯玉祥为什么跑到徐州去跟蒋介石开会?他们商谈些什么问题7”汪精卫含糊其辞,先说不知道,后来又说电报弄错了。我把这种可疑的情形告诉了陈独秀,但陈独秀仍是若无其事,泰然置之。
形势一天天地恶化。唐生智的军队从前线开回了武汉,名义上是拱卫政府,实际上是要控制局势,以便先发制人。不久军事委员会下令收缴工人纠察队的枪支,陈独秀竟同意了这项命令。于是我们手中仅存的一部分武装也被解除了。事后军事委员会开会时,武汉卫戍司令李品仙还说:“只收到一千支坏枪。”意思是说还有更多的好枪藏起来了,还要逼我们交枪。其实我们手上已根本没有什么武装了。
财政方面的情况也很糟。蒋介石叛变后,身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不辞而去,跑到上海去投靠蒋介石。他丢下了一笔糊涂账,后来由湖北的两个反动商人来接管财政。那时前线的开支很大,政府收入不多,再加上管财政的人贪污中饱,弄的国库空,空如也,十分困难。
针对这种非常危急的情况,共产国际在5月发出了紧急指示,内容是实行土地革命,发展工农运动;加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中的左派力量;动员党员和工农群众,编练五万军队;组织革命军事法庭,肃清反革命分子。这是当时挽救革命的唯一方法,陈独秀却扣留了这个指示,不让全党知道。直到6月23日,在党中央的一次扩大会议上,任弼时同志要求陈独秀把共产国际的指示在党内公布出来,陈独秀拒不接受,还大发脾气。我问坐在旁边的张太雷同志是怎么回事,张太雷同志把指示内容告诉了我。我说:“这样重要的指示,怎么我一点也不知道。”张太雷同志说.·“我也是刚刚知道的,许多人都不知道这回事。”在革命十分危急的关头,陈独秀仍然用家长作风来坚持他的机会主义路线,革命的失败怎能避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