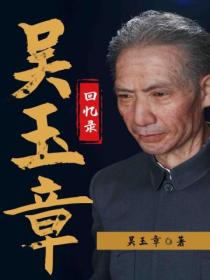1935年,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国际上,德、意、日法西斯联盟已开始形成,并在世界许多地区加紧了它们的侵略行动;世界各国人民,也采取了各种形式来抵御法西斯的侵略,一个广泛的世界人民反法西斯阵线正开始形成起来。在国内,日寇继占领我国东北四省以后,又不断对我发动新的侵略,妄图囊括平津、席卷华北,进而占领全中国。日本帝国主义在1935年制造的所谓“华北事件”其目的即在于此。中国的民族危机至此空前严重。国民党反动政府对于日寇的新进攻,仍采取臭名昭著的不抵抗政策,节节退让。1935年夏,它与日寇订立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接着,在日寇新的压迫下,它又准备成立半傀儡性的所谓“冀察政务委员会”,想牺牲冀察两省的主权,来满足日本侵略者的胃口。但是,中国人民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和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决不答应,他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坚决展开了抗日救亡的斗争。一个新的爱国运动的**即将到来。
与此同时,红军在突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后,中国共产党于长征途中召开了著名的遵义会议,改变了“左”倾机会主义错误的领导,确立了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党中央的新领导,然后在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下,完成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于1935年10月,胜利地到达了陕北革命根据地。红军到达接近抗日前线的陕北,对华北人民的抗日斗争,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由于日寇侵略所引起的太平洋国际关系和中国内部阶级关系的变化,中日民族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这种形势,要求我党采取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联合一切抗日人民和军队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35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八一宣言”)。这个宣言,号召全国人民在亡国灭种迫在眉睫的关头,“无论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政见和利害不同,无论各界同胞间有任何意见上或利益上的差异,无论各军队间过去和现在有任何敌对行动,大家都应当有‘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真诚觉悟,首先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宣言并号召组织全中国统一的国防政府和组织全中国统一的抗日联军。“八一宣言”传到国民党统治区以后,得到了各阶层人民广泛的同情,促进了抗日运动的发展。
1935年7月一8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季米特洛夫在会上作了一个著名的报告。这次大会根据当时的国际形势,提出了在资本主义各国建立工人阶级反法西斯的统一战浅和各民主阶层反法西斯的人民阵线,以及在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国家建立反帝国主义侵略的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中国共产党的“八一宣言”,就是根据这一新的方针发表的。
我在莫斯科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以后,党决定派我到法国巴黎去扩大正在那里出版的《救国报》,以加强反法西斯和建立抗日民族统……战线的宣传。1935年10月,我由苏联动身去法国。
11月初,我秘密地到达巴黎。一到巴黎,我就按着原来的规定,到一家咖啡馆去和约定的同志(曾同过路,彼此认识)接头。外国的啡咖馆和中国的茶馆差不多,只要买点东西,呆上半天,主人也不干涉。这天我到咖啡馆的时候,里面人来人往,十分热闹,我也要了些咖啡、点心,又时而看看书报,以消磨时间,避人耳目。由于我的行动自然,并没有引起旁人的注意。但是—直等了四个多钟头,还不见接头的人来。这时咖啡馆里来去的人已变更多次,如果再呆下去,就会引起别人的怀疑。我非常着急。当时我想,来接头的同志怕引人注意也许在门外等候,便慢步出门寻视。不久,远远望见他走来了。在他的示意下,我便跟他走去。我们就这样又接上了关系。接着,我们便开展了工作。但这时,法国政府在中国南京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忽令《救国报》停刊。为了反抗法国政府这道命令,使报纸继续出版,我去找法国共产党的同志们商量,问他们是否可以通过起诉,争取复刊。那时法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领导下,很有国际主义精神,对中国革命极力帮助。他们对我说:这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政治问题,这次令《救国报》停刊,是法国政府为了外交关系由内阁决定的。起诉无用,抗议也无济于事。并说:好在法国政府自来标榜言论、出版自由,如果把报头的汶字和法文稍加修改(保持大意相同),仍可继续出版。这时,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在开展,国内人民和国外华侨纷纷来函订报,各方需要很急,而且报纸的纸版要从莫斯科航空寄来,如不赶快设法,很容易使报纸脱期,从而会引起各方面的疑惧。因此,我急电领导请示,建议改称《救国时报》。在得到回示同意后,我们赶忙把莫斯科寄来的纸版改了报头,使报纸一期也不脱,《救国时报》居然在“一二·九”那天,又继《救国报》而出版了。把汉字报头增加一个“时”字,并不大引起人们的注意;而在法文报头上,却如同新出一家报纸似的,法国政府因此也就不再追问。
就在《救国时报》出版那一天,1935年12月9日,国内爆发了伟大的一二·九爱国运动。北平学生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华北,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半傀儡政权的建立,以挽救中国的危亡,他们突破了反动军警的封锁,不顾大刀水龙的袭击,英勇地走上街头,举行了激昂悲壮的示威游行。由北平学生掀起的抗日**,迅速席卷全国,打破了国民党统治区多年来白色恐怖的反动局面,使蒋介石经常夸耀的所谓“安内攘外”的卖国政策一天天地趋于破产。我们在国外听到这个消息,当时兴奋之情,真非言语所能形容。我们决心加紧工作,办好《救国时报》,希望它能在日益高涨的抗日运动中发挥积极的作用。
还在我从莫斯科赴巴黎之前,为了扩大报纸的规模,我们就决定要在巴黎创办印刷所。那时陈云同志也在莫斯科。由于他和商务印书馆有长期的关系,他特为我给上海商务印书馆写了一封托买汉字铜模的介绍信。我到巴黎后即把信发出。“一二九”运动发生后,我们是多么盼望这套铜模赶快到来啊!1936年3月,铜模果然运到了巴黎。经过大家紧张的筹备,印刷所建立起来了。印刷所的建立,不仅避免了由莫斯科航运纸版常因气候关系致使报纸有脱期的危险,而且从此扩大了报纸印刷的规模,解决了国内外所需要的发行数量。
《救国时报》是我党在国外从事抗日宣传的机关报。它从1935年12月9日创刊到1938年2月10日终刊,历时二年余,共出版了152期。它的主要任务是宣传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从创刊号起,就明确地栺出,在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条件下,中国的唯一出路,就是全民族一致对外,建立全民救国的联合战线。它发表了许多论文;刊载了许多中共中央的文件和—毛泽东同志的著作;不断地报导国内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情况,特别是东北抗日联军的斗争情况;并经常揭露蒋介石进行反革命内战和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投降的阴谋活动。它为推动中国抗战,作了不少工作。此外,它还经常发表斯大林、季米特洛夫等同志的论文、演讲词,不断报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以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情况。这些,对于当时正处在苦难中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的中国人民说来,是很大的鼓舞。
因为《救国时报》的言论代表了广大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在国内外拥有广泛的读者,成为当时国内外同胞特别是进步青年很喜读的报刊之一。它的发行数量增长很快,在创刊时仅销行五千份;不到一年,就增至两万份,而且还远不能满足读者的需要。在销行的两万份中,国内约一万余份,不仅北京、上海、广州、重庆等大城市,就是西康、新疆等边远地区和若干小县城内也有它的读者,而且几乎是每份报纸都是许多读者传阅;它在国外的发行范围,遍及四十三个国家,拥有九千六百余订户,欧洲华侨中有它的读者,美洲华侨也很喜欢它,南洋一带和澳洲、非洲、印度等地也都有它的读者。
也正因为《救国时报》反映了人民的要求,所以它得到国内外广大群众的支持。1936年2月11日,一个新加坡的读者来信说:“这边——马来亚的华侨对于贵报的态度表示很拥护,凡是读过贵报的人,都愤恨日本和一切卖国贼汉奸,而且争先恐后地要先读贵报。记得有一友人带《救国时报》—张往马六甲,该报由侨胞互相传递,直至破烂不堪,字迹模糊,还是不肯放手。这个事实,正是说明贵报的态度正确。”1936年8月12日,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总司令杨靖宇同志来信说:“贵报之内容精彩,议论正确,固不必说,而所标出宗旨为‘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团结全民,抗日救国’正与敝军之宗旨相合。我们的口号也是不分党派,不问信仰,只要是抗日救国的,都一致联合起来。正因为如此,故贵报甚得敝军全体士兵的欢迎。我们应该更感谢贵报的,就是你们关于东北义勇军抗日的消息登载独多,使我们全体士兵看到,抗日杀贼的意志愈益坚决兴奋。”1958年我到哈尔滨参观革命博物馆时,就看到东北抗日联军保存下来的《救国时报有些还是烈士们的遗物。据说明员同志说:该报在当时东北抗日联军中广为流传,深受广大官兵热爱,对于他们坚持东北游击战争,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各地读者不仅在精神上支持我们,而且在经济上也援助我们,例如在有一段时期内,我们收到读者自动汇来的捐款即达六千余法朗,其中有杨靖宇同志和全体将士捐输的,也有国内外同胞捐输的。这些,都给了我们《救国时报》的同志们以很大的鼓舞。
《救国时报》在它的发展过程中,也曾邁到过许多困难,其中最主要的是经济上和发行上的困难。它虽然有《救国报》的资金作基础,也得到各地同胞解囊支援,但因它并非营业组织,收入有限,而各种费用支出颇巨,两者相较,常常不足。虽然同志们节衣缩食,甚至继以典质,即使“罗掘俱穷”,也还是难以为继。因此后来有时不能按期出版,或出版后又无钱付邮。在发行上,由于国内外反动派的检查,报纸常被扣留,订户及代派处往往收不到。那时国民党反动政府对报刊入口检查最严,我们的报纸往国内发行极不容易。为此,我们不得不想更多的办法。记得1936年初,上海生活书店的一位同志到了巴黎,他手头上有《新生周刊》的订户名单及住址,那时《新生周刊》已被查封,我们便利用它的订户名单及住址来寄《救国时报》,使我们的报纸得以在国内广为流传。总之,《救国时报》虽然遭遇到许多困难,但由于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援,再加上报社全体人员同心同德地艰苦奋斗,终于克服了一切困难,坚持了两年多的斗争,完成了它所负的光荣的历史使命。
我在巴黎办《救国时报》的时候,为了加强在欧洲各国的中共党员的联系,交换情况和交流工作经验,于1936年1月,在巴黎召开了一次旅欧党员代表会议,到有在英国、德国、比利时、荷兰、法国等国工作的党员代表十余人。我在会上作了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党的新政策的报告。会议讨论了组织各国华侨抗日救国联合会的问题,并制订了筹备计划。这些长期散居在国外的同志,由于客观环境很难与党的领导组织联系,而各兄弟党领导他们也有困难,因此,他们的工作不能很好地开展,情绪也有些沉闷。于是,大家建议成立一个统一的领导机构来加强对旅欧各国党员的领导和联系。这个问题虽然未能得到解决,但通过这次会议,大家听了我的报告和讨论了今后的工作,觉得有了党的新政策可以遵循,都非常高兴地返回了各自的工作岗位,生气勃勃地展开了工作,比起从前来总算进了一步。
我在巴黎除了办《救国时报》以外,为了宣传抗日和争取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还作了一些其他的工作。1936年春,听说胡汉民到了法国,住在宜斯海边休养,我想他在国难当头的时期,思想或许有所转变,便派我的儿子(震寰)持函往见,想约他见面,对他谈谈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谁知这位在大革命时代就著名的右派分子,这时仍然顽固不化,见我的信后竟不敢作答。我知其行将就木,已经不可救药了,便没有再去理他。后来胡愈之等来巴黎,我和他们畅谈,颇为投契。他们要求到苏联,我为他们联系,并代办了入境手续。
1936年3月,世界学生联合会为援助中国学生的抗日救国运动在伦敦召开大会。在这以前不久,曾在比利时首都开过一次国际青年代表大会。在会上,我们的代表为了扩大统一战线,把表面看来似乎左倾一点和比较与我们接近一点的国民党分子王海镜推入大会主席团,谁知这位王海镜后来竟反对我们的代表在会上讲话。鉴于这一教训,我想这次伦敦大会,再不能蹈覆辙,便写信给德国我党支部负责人王炳南同志,力说我们一方面要顾到统一战线方面要保持我党的独立性、斗争性,断不能因为统一战线而把自己的手足束缚起来,并要我们的代表去伦敦后找侯雨民同志好好筹商办法。因时间紧迫,稍缓即要误事,我们又没有预定秘密通讯方法,怎么办呢?考虑到以前几封信都没有失误过,想来这一次也不一定会出问题,便大胆地写了一封指示信,急忙挂号寄出。谁知这时王炳南同志已另调工作,新接任的刘光德(刘咸一)同志又搬了家,他两天后到旧房东那里取得我的信,已被人拆过了。后来,当大会开始的时候,出乎我们代表的意料,国民党特务忽在会场上散发以“民族先锋社”名义影印的我那封信,并大嚷什么大会是共产党所召集和操纵的。他们还以“留德中国学生会”名义致电大会,反对我们的代表出席会议。我们的代表都很惊讶。但是国民党特务这一无理取闹,在我党代表的有力驳斥下,并没有得到多少同情。大会执行主席柯乐满当场驳斥了他们,大会筹备委员会也回信驳斥了他们的来电。这次大会并没有被他们所破坏,终于获得了成功。我们的代表返巴黎后,说起这件事,并把影印的信给我看,果然是我用假名“平洋”写的那封信。我这时深深地感到:自己的警惕性还不够高,考虑问题还不够周密,在反动统治下做革命工作,必须随时警惕啊!后来查明,这件事原来是国民党政府驻德国大使馆的人干的。他们经常派出特务跟踪共产党人,窃取机密。就是他们把我那封信秘密偷去影印后又送回了原处。他们不仅把影印的信在大会会场上散发,而且遍寄国内外,企图以此来挑拨离间,破坏我们进行的统一战线工作。接着,国民党政府驻德大使程天放,就串通德国法西斯组织“冲锋队”对我们施加迫害,逮捕了刘光德同志和反帝同盟的许德瑗等人。为了反抗反动派的迫害,我们发动了许多团体向德国政府抗议,并要求国民党大使馆将人保出。程天放自然是不会答应的,我们对他也并不存在什么幻想,这样做只不过是为了更加暴露他的嘴脸而已。由于许多团体的抗议,加上德国和国际舆论的谴责,德国政府不得不将许德瑗等释放,但刘光德同志却被无理驱逐出境。这一消息传出后,党组织惟恐我也发生危险,便急电要我返回莫斯科,并派人来接替我的工作。
原来我到法国去是非法居住的,没有居留证,是经不得检查的。刚到巴黎时,报社又被查封,同志们怕有危险,不要我到报馆去,但我每天总要设法去一次。我还常约同志们到咖啡馆商量工作,有时风声很紧,大家都为我担心。当时法共的同志们给了我根大的帮助,极力设法掩护我。我一到巴黎,他们就把我送到一个同情分子开的旅馆里,住约十月之久,未出问题。这固然是由于法共同志们和旅馆主人的掩护,同时也由于我自己小心谨慎,举止大方,和自己装扮的身分相称,并注意保守秘密。主人一家因此都很喜欢我。1937年,我再到巴黎进行抗日战争的国际宣传工作时,曾去看他们,并告以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形成,抗战胜利有望,他们一家人都非常高兴。直到如今,对于法共同志们和法国朋友们的帮助,我仍感激不忘。正是由于他们的国际主义的援助,才使《救国时报》胜利出版,并使我胜利地完成了党所交给我的任务。
1936年7月,我把报社的工作交代以后,返回莫斯科,又走上了新的工作岗位。
(196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