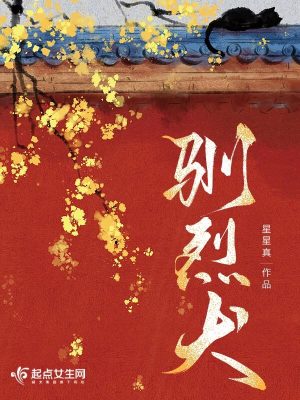河道人真的很多,沈宜亭被江寺一把拦在身边,硬是没让她挤到半点,便把人带了进去。
沈宜亭花十个铜板买了两只花灯,上面还有签,求亲人安康,亦或者求夫妻和睦。
江寺要了个白首如新,瞥见一边沈宜亭要了个亲人安康,有些吃味。
“你为沈夫人放的么?”
他语气实在是太阴阳怪气,让沈宜亭难以忽视,特别是目光还瞥过那花灯,眼底有些针对意味。
沈宜亭本欲给阿姐祈福,被他拉过来看花灯,便顺道放给阿姐。
哪知道江寺竟然这样吃味。
她摇了摇头,走去售卖纸条的那边,花一个铜板又买了一张‘情深不渝’的纸条,然后放在江寺那只花船中。
“阿姐有孕,我担忧他,并非为此不愿与你长久”,说完,她看江寺仍垂着情绪,便大胆伸手,捏了捏他还带着热意的耳朵,“你竟然连这也要挑我的不是。”
江寺被她顺毛安抚,又见那‘情深不渝’四个大字,只觉得又是一个饴糖,甜到心底,其余什么散了。
“我并非挑错。”
他紧跟着沈宜亭,一只手拿着花船,另一只手还要同她牵着,“沈夫人可是有孕,我今日瞧见她肚子略显,为此将我爹好生骂了一顿。”
江寺黏糊糊的倚在她耳边。
“你骂侯爷?骂他做何?”
说完,沈宜亭反应过来,自己先笑了:“你觉得那是侯爷的孩子?”
她挑眉,只觉得江寺也有糊涂时。
江寺不愿承认自己脑子晕的这回事。
只在她颈窝蹭着。
沈宜亭弯下身子,混迹在人群中,将花船放在水面,才起身,手指贴着江寺的后颈。
她身体一向有些凉,手脚到了冬日便容易冷,一只手被江寺握着,不见寒凉,另一只手却冰得吓人。
江寺反手到冷意,身体颤了一下,却没将她的手拿下来,而是皱了皱眉头:“你怎么这样冷?”
沈宜亭继续用手去冰他,便还笑到:“出门受风吹,哪有不冷的,你以为人人像你,火炉一样。”
江寺这才将她手拿下,快速把手上花灯放出去,然后将她两只手都牵过来,放在手心好生暖着。
他眉眼有些不好,似是怕沈宜亭冻到。
“你可还有什么想看的,不若回府?”沈宜亭手确实寒凉,江寺摸着便担忧。
但她也只有手脚凉,身上都是暖和的,倒也不至于就这样生了病,也想着出来一趟,看看再走。
因此回去路上,在沿路买了不少小吃食,有特意给沈相静带的冰糖葫芦和蜜饯。
江寺看她去买时,那笑容灿烂无比,还以为是给自己的。
谁知道沈宜亭买回来便收好,甚至都没问他要还是不要。
“沈宜亭”,江寺又勾勾的看她,“原来你不是为我买的。”
沈宜亭才看了眼被油纸袋包好的吃食,有些失笑:“这是为阿姐带的。”
江寺脸色更黑了几分。
他当然知道是给沈相静带的,但沈宜亭满脑子都是阿姐,竟然问也不问他。
江寺咬着牙,“我、也、要!”
他眼神略带几分强势,但身体没动,好像虚张声势的大狗,眼神再凶狠,也只晃着尾巴委屈巴巴看着主人。
沈宜亭没想到他竟然这样较真,于是抽出一只冰糖葫芦递过去。
冰糖葫芦外层包裹糯米纸,内里先是一层琉璃一样的糖衣,然后才是里面的山楂。
盛京的水果不管什么,都有个特点。
够酸。
江寺一口便咬下一颗山楂,整个吞入口中,沈宜亭看着他脸色,果然没多久,便见他微扯了扯眉。
沈宜亭抬手捂着嘴,似藏着笑意。
江寺忍着酸意咽下山楂,唇齿间还带着一股泛酸的气息,让他隐隐感觉有些牙疼。
“沈夫人竟然爱吃这样的东西,真的不会嫌酸么。”
江寺不解摇了摇头,将那根糖葫芦又返回一只油纸袋中。
沈宜亭看他方才巴巴的同她讨要,现在又不肯吃,便有些好笑。
“阿姐有身孕,怀着孩子的妇人爱吃酸不是很正常么,我早说了,并不是不愿为你买,是知道你不爱吃。”
江寺被她哄顺毛,继续跟着她做她挡开人群的一堵墙。
只是沈宜亭的话多少还在心里留下印子。
趁着人流涌过去一波,他便俯首,贴在沈宜亭耳边。
“沈宜亭,以后你怀了宝宝,我也给你买这个,让你天天都能吃上”,说完他顿了顿,觉得实在不好。
万一那日这买冰糖葫芦的老汉不来了怎么办。
于是,江寺又改口:“不如我学一学这是如何做的,每日做给你?”
沈宜亭不知道他是怎么一下子想到这里,但仍旧觉得好笑。
“你今日才同我表明心意,便想让我为你生儿育女?”
她转头瞥了眼江寺,那眼神有些倨傲,隐隐拿乔。
江寺嘴角笑容更灿烂,紧贴在她肩窝,黏糊糊蹭她:“还不许人想想了?”
沈宜亭回:“哪知道你想的这样美。”
“那不是,今日实在太美了,所想便更美。”江寺黑曜石样的眼睛盯着她,五官满是惬意神采,确实能看出他今日实在高兴。
新年的灯会尚且不是最热闹,眼下街上只有舞狮和戏台,等到了元宵,一整条街张灯结彩,满天花灯升空,还有许多张彩的节目都要拿出来,皇城周围也要盛放烟火,以示祥瑞。
因而沈宜亭也并没有在外久待。
临到回府时,江寺还有些念念不舍,非要她允诺,元宵也一起出来,才愿意将她放回院子。
次日除夕,候府也开始挂上红锦,红联也陆续张贴。
檐上悬挂的灯笼被换上一层吉祥的新衣,灯烛也加了油进去,变得比原来更亮。
一早起,沈宜亭就遇见出来领新衣的翟墨。
府中的绣娘在临近年节时便开始准备了,眼下缝制了不少衣服,翟墨领的真是江寺的那份。
沈宜亭思虑一秒,便叫停他,同他一起走了一趟。
“夫人让我往在摘星院送新年需要的红锦和喜联,摘星院可是还未张贴?”
翟墨愣了一下,自先夫人过世后,候府便许久不曾这样重年节了,加之世子也少有尚在京中过年的日子,摘星院仔细算来,也有许久不曾贴红锦和红联。
“姑娘说的是,我家世子不曾战意这些,劳姑娘费心。”
沈宜亭点头,从院子里挑了红锦和喜联,外加江寺出征后,她时常见到的新衣,一并和翟墨去了摘星院。
比起候府其余地方,摘星院要显得冷清许多。
沈宜亭到时,江寺只穿了-单衣,手握雁翎刀,挥舞生风,惊起院中落叶,硬是斩断呼啸寒风。
那开了刃的刀锋冷光看上去颇为锐利,被他挥动起来宛如白练漂浮。
“你怎么来了?”
江寺瞥到沈宜亭的娉婷身姿,手上招式一停,凌空一挥,将雁翎刀插入旁边放着的刀鞘中。
沈宜亭四面看了眼他的院子,摘星院被洒扫打理过,眼下已经十分干净,出去几片被江寺练剑时惊下的落叶,看不见什么突兀。
但也太冷清。
他院子里本就没有什么装饰,上过几层台阶便走到院中,院中除了一棵大树和一座石桌,再无其他,然后便是闭上黑沉木门的房屋。
沈宜亭叹了口气:“今日除夕,便要将院子重新装点,想到你恐怕不记得拿这些,我便给你送来了。”
沈宜亭点了点托盘上的东西。
那些红锦江寺不曾在意,只有一对春联,上面蘸着浓墨挥毫,字体大气凛然,铁画银钩,笔锋流转间颇有几分熟悉的感觉。
“这是你亲手写的?”
江寺将它拿起来看了看,确定是沈宜亭的字迹。
平日她传信写在纸条上的字迹要收敛一些,虽不是盛京女子所学的簪花小楷,却也并不张狂。
眼下这副题字,笔墨挥毫,笔走龙蛇,十分有意气。
沈宜亭自己院中和沈相静那里的联,都是她自己写就。
后院的喜联多是她的字迹,前院便不能如此,而是请了书法大家,特意买了墨宝。
“后院几副都是我写就,如何?”沈宜亭含笑看他。
江寺见那字迹心喜,越看越珍爱,“自然是极好。”
他凑近沈宜亭耳边,微吹嘘她:“我看沈姑娘这一手好字,可不得留下做传家宝?”
沈宜亭听出打趣,伸手揪起他的耳朵,将他朝后拉开。
翟墨原是没有注意他们做什么,可中途听到世子小声叫了句痛,便下意识看过去。
便见到沈姑娘两只手揪住世子的两侧耳朵,她分明没用力,那指尖之间都是松的,说是揪住,更像抚摸。
偏偏世子叫痛。
翟墨心下觉得不对,仔细定睛,好好看了一眼。
他那里是痛,那脸上笑容灿烂得比当空日曜都晃眼,分明心里乐得止不住。
于是翟墨便将目光收回来。
心说世子和沈姑娘感情深笃,打闹一番也无所不可。
沈宜亭也听见江寺叫痛,可她知道是他故意这样说,那人分明笑得可欢,甚至微低下身子,还叫她更能够到他耳朵,巴不得她揪住这几下。
“净说这些不正经的话,小心我放下东西便走了。”
沈宜亭松开他,江寺这才直起身,听了这话,神色一变,忙伸出长臂将她朝自己怀中揽过来:“你想这就走?那可不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