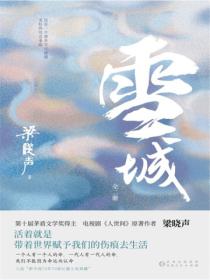6
从第二天开始,她每天晚上都引导小俊“阅读”这座城市。如同一只城市的麻雀引导一只乡下的麻雀参观城市所有的屋檐。她毫不吝惜地花掉她多年的积蓄,仿佛那些钱原本就是为小俊积蓄的。
她自己也是第一次领略这座城市的种种娱乐,也是第一次获得娱乐的愉快。没有小俊,她不会去光顾那些场所;没有小俊,在那些场所她也不会获得愉快;没有小俊,她不会出现在大饭店里点名菜。因为是和小俊一起,这样的事则显得意义非同一般了。在她的逻辑中,甚至不明确小俊和她自己,究竟谁更应该感激谁了。
城市对连偏僻小镇的风貌都没有领略过的北大荒姑娘小俊,像专门善于撩拨和**情窦初开的少女情欲的西方舞男。她是完全被“他”迷住了,被“他”迷得心旌飘摇,她整个儿的心几天之后便彻底被“他”俘虏了去。城市这本“书”她一旦翻开就不能再放下了,她的心思已进入了这本“书”。她恍恍然觉得自己不再是读者,而是角色,一位女主角,一位年轻的待嫁的女主角。她想象着哪一天在城市中遇到一位心上人,而姚玉慧这位“大姐”是她的保护人。她迷住了城市这个风流倜傥精力充沛的“舞男”,好比小猫一口叼住了一个大发腥味的鱼头,谁若企图抢下来她就会挠谁,哪怕是主人。
“大姐,明天晚上你带我到哪儿玩去?”
“大姐,今天晚上路过的那个咖啡厅你哪天带我去呀?那里边的灯光真神秘啊!在那里边唱歌儿的一个晚上能挣不少钱吧?”
“大姐,要不明天咱们参观时装展销会吧?”
“大姐,后天歌舞团招考演员,你一定带我去,啊?我不是想考。像我这样的,哪考得上?我是听人家说,考演员的,都是漂亮的人……大姐,那么多漂亮的人聚到一块儿,多热闹啊……大姐,咱们就去看看热闹开开眼界呗!”
每天晚上,临睡前,这北大荒姑娘一定要获得“大姐”明确的回答,明天晚上“读”哪一“章”哪一“节”,否则,她像固执的小女孩儿似的纠缠不休,或者噘起嘴显出不高兴的样子。
在小俊所说的那个咖啡厅,女流行歌手边唱边舞,将北大荒姑娘唱得如醉如痴,即使在如醉如痴的情况下,她仍牢记着服务员还欠她们钱。
临走时,她崇拜地望着那女流行歌手,提醒道:“大姐,欠咱们一元多没找给咱们呢!”
女流行歌手的演唱服是本着节约得无法再节约的精神做的,看着就使人感到那么的凉快。然而咖啡厅里却依然浪费地放着冷气。小俊这么认为。
“大姐”在她手上掐了一下,低声制止道:“别说!”把她拉扯走了。
走到外面,她百思不得其解地问:“大姐,明明欠咱们一元多钱嘛!为什么不要?”
“不能要。那是小费。”
“小费?什么是小费呀?”
“小费……就是人家为咱们服务了,人家为咱们付出了微笑,咱们就得给人家点儿钱。”
“可……她们是挣工资的呀!”
“微笑挣另份儿,不包括在工资里。”
“可……她们微笑是应该的呀!咱们不是还对她们说‘谢谢’了吗?”
“她们为咱们微笑着服务是应该的,咱们对她们说句‘谢谢’也是应该的。可她们反过来说‘谢谢’咱们,那两个字是用小费买到的。否则她们会对咱们说‘谢谢’吗?”
“那我宁肯不需要她们说那两个字!”
“那我们走了就会被她们瞧不起。那里是中外合资,新加坡来的老板,本市第一家实行收小费的娱乐地方。许多人正是因为这一点才到那里去的。”
“因为那里的微笑得付钱。”
“就算这么回事儿吧。不过别处可没笑脸相迎啊!”
“早知道这样,大姐我不求你带我来了!”
“你不求我,我也会带你来的,我也没来过。那据说是代表着一种城市文明呢!”
“大姐你觉得给小费也值?”
“值。”
“你若觉得值,我就更觉得值了!”小俊笑了。
从时装展销会上回来那天晚上,小俊坐卧不安,显得又兴奋又诡秘。
终于,她吞吞吐吐地说:“大姐,我不敢瞒你……”
“什么事?”
“我福星高照,发横财了。”
“发横财了?”
“嗯……我……兴许会成大富翁!”她两眼闪闪发光。
“噢?”姚玉慧糊涂之至。
“大姐你看!”她将手探入怀里,取出的是一个条状塑料袋,内中装的是十几枚黄澄澄的崭新的金币。
姚玉慧生平第一次见到金币,而且是那么大的金币。比邮局发行的生日纪念币小不了多少,且十几枚。在这黄金大涨价的时代,姚玉慧一时估计不出它们的价值,然而它们足以使一个人富起来是无疑的。
她望着托在小俊双手中的那一塑料袋金币,愣了。它们在塑料袋中一枚压一枚地排列着。
“你?……你偷谁的?在哪儿偷的?!”她震惊同时震怒。
“大姐,不是偷的。真不是我偷的啊!在展销会上捡的。”因为金币被怀疑是偷的,小俊快急哭了。
“捡的你也不该带回来!你当时为什么不交给展销会的工作人员?!”姚玉慧的怒气并不因金币是捡的而平息。
“我不交!有丢有捡。我一人做事一人当!”小俊退开一步,防范金币被她这位“大姐”一把夺去。
“给我!”
“不……”
“给我!”
“不……”小俊又退开一步,将金币背到身后。
“你……小俊,我真没想到你会这样……”
“大姐,你别生气,你先坐下,你听我慢慢说嘛!大姐,你对我好。我心里有数,我感激你,我愿意报答你。我小俊是个仁义的姑娘!这么着大姐,你想办法把它卖了,钱咱俩平分。不管卖多少钱,咱俩都平分!行不行?”
她向前走一步,小俊向后退两步。
她终于说:“行。”想先将金币骗到手。
“拿去吧。”小俊终于将金币扔在**。灯光的照耀之下,它们在**发着黄澄澄的金辉。
她默默从**拿起了那袋金币。奇怪于它们的分量竟很轻很轻,也开始奇怪金币怎么会装在一个连半分钱都不值的透明的塑料袋里。每一块金币的正面,都凸压着“2000$”的字样。她知道“$”代表美元。十四块,那么它们价值两万八千美元。她也听说如今黑市上人民币兑换美元的比率是1:6。那么它们价值近二十万人民币。
拥有了这些金币,如今是足以使一个中国人变成为阔佬的。
她翻过塑料袋看,每一块金币的背面又都凹压着“恭喜发财”四个中国字。
姚玉慧将这些金币在手里掂了又掂。她终于怀疑起它们的真伪了。
“大姐,你一定能想出稳妥的办法倒手是不是?大姐我不回北大荒了!有了它们傻瓜才回北大荒呢!大姐我要在城里买住房,买两间像你这样的单元楼房。然后我要起个执照做个体户。我从此要当一个城市人,嫁给一个城市人。大姐今后我还是少不了得求你帮我什么忙。大姐今后我要把你看作是我的亲姐姐,一辈子不忘你对我的大恩大德。”小俊轻轻走到她身边,欣赏着金币,以充满憧憬的语调,絮絮地娓娓动听地尽说尽说,这北大荒的姑娘陶醉在某种向往之中了。
“不是金币。金币不可能这么轻。”姚玉慧断然地说,然后将它们抛到了**。
“不是金币?不是金币是什么?明明是金币!”小俊迅速地将它们抓了起来,眼里闪出精明的目光,狡猾地望着她。那意思是:大姐,你别跟我来这一套,你骗不了我的,我不是三岁小孩儿!
“我绝不逼你交到任何地方了,完全属于你。”她脱衣服,预备睡觉。
小俊则扯开了塑料袋,将那些金币抖落**,拿起一枚,像旧时代金银铺的老板似的,放一半在嘴里使劲儿咬,结果一口咬下半个金币。她吐在手心,瞅着呆住了。
姚玉慧见状,从她手心拿起看看,又放在她手心,笑道:“吃了吧,是巧克力。”
“巧……克力?怎么是巧克力呢?怎么是巧克力呢?”小俊也呆笑了。
突然这姑娘一头扎在**,大哭,边哭边嚷:“不吃!不吃不吃!”抓起那些“金币”,歇斯底里地扔向四面八方……
就在那一时刻,好“大姐”厌倦了自己所扮演的角色……
第二天小俊“病”了。
小俊似病非病地在**整整躺了一天。不吃,不喝,不说话。
小俊病好了之后,变得无精打采,沉默寡言了,却矢口不提打算什么时候回家。
小俊不提,好“大姐”姚玉慧也不提。她认为自己不该提,因为她已经说过那样的话——“这里就是你的家一样,你愿意住多久便住多久。”
她依旧提议带小俊去什么什么地方开开眼界,玩玩。但她已经没有了最初那种兴致勃勃的好情绪。
小俊也没有了初来乍到时那种希望能在一天内就逛遍这一座城市的好情绪。
所里要派一个人到南京参加律师事务经验交流会议,她第一次为自己争取了一次出差机会。
她要摆脱自己已经厌倦了的好“大姐”的角色,起码希望摆脱一个时期。她觉得自己如果要将好“大姐”的角色成功地饰演到底,有始有终,非得超出目前的“规定情节”,重新体验角色,重新进入角色不可。她唯恐在没有来得及重新进入角色之前,不但已经厌倦了自己的角色,而且厌倦了小俊这个配角。
配角?究竟小俊是配角?或我自己是配角?她得不出一个肯定的结论。而这件事不过是生活中的戏剧?小戏一场?
不,不,不……
小俊,我发誓,管理员,我发誓,我姚玉慧本不是在演戏啊!我是真心实意欢迎你们的呀!我从内心里想要亲近你们,亲近一些人,或者仅仅哪一个人。
她怀着一颗对别人感到无比内疚的心到南京去了。
她没有委托家人照顾小俊这位远方客人。
母亲根本不会将小俊当作客人,在母亲眼里,小俊不过就是一个土里土气的北大荒姑娘而已。和家里曾经频繁雇用频繁辞退的那些来自安徽、四川、江西、江苏农村的小“阿姨”们是一类姑娘。与其说母亲很难容忍她们,毋宁说她们很难容忍母亲。母亲的令人难以容忍,不惟是因为进入了更年期,更是因为曾经管理过许多男人和女人,而现在连儿女们也压根儿不服她管了。
父亲是能够将小俊当作客人的,但父亲自己仿佛也变成家里的一位客人了。父亲是那么害怕终于有一天也会像母亲一样,被时代的大潮毫不留情地彻底逼退到家中,所以像一个老孤儿,一往情深不知疲倦地留恋在社会上,出席各种各样的会议,包括一些无关紧要的,政协主席到场既没有什么意义也不见得很受欢迎的会议。
弟弟是不堪信任的,并且绝对不能够礼貌地平等地对待小俊。因为他是一个“出色”的城市人。
妹妹对这位来自北大荒的姑娘那种被自己的想象夸张了的好奇心,在与小俊进一步接触之后,很快便会索然的。索然了,便不肯履行任何义务了。何况,在玩乐方面,妹妹一向喜欢“天马行空,独往独来”。连小赵也常常寻找不到她的芳踪,对之无可奈何,敢怒而不敢言。
好“大姐”将小俊“移交”给了电脑以“优选”的方式替她选择的那一个男人——英语教师田非。当初,在婚姻介绍所,她就是通过电脑“红娘”才结识他的。除了夏律师,他是最值得她信任的人。她虽然至今仍爱不起他来,但却信任着他。别人说他本分,业务型,是个老成持重的知识分子。电脑也是将他这么归类的。她认为在这一点上,别人和电脑并没错。尽管她至今仍爱不起他来,努力想爱也无济于事,但她准备嫁给他。甚至可以说,其实她已经下了决心嫁给他,下了决心要结束老姑娘的生活。只不过因为仍爱不起他来,希望再往后些做他的老婆。婚姻介绍所的人曾含蓄地告诉过她,即或电脑,也是很难再为她选择一个对于她那么理想的男人了。电脑尚且很难,她自己还能存什么非分之想呢?在这科学的大时代,不相信科学无疑是不明智的。
7
她从南京回来,到家已经夜里十点多了。
小俊不在,也没有发现小俊那个小包袱在。
她以为他已经替她将小俊送上火车了。这本是自己应该做到的,却没做到。怀着更深的内疚,拥抱着旅途的疲乏,她酣睡了。
早晨醒来,却一眼发现小俊睡在席梦思**。
“小俊,你没走?”
“大姐,不最后见你一面,我怎么会走呢?”
“猫呢?”
“大姐,真对不住你,猫饿跑了,好几天没回来了!”
“跑就跑吧,我早讨厌它了。”
“大姐,你看下手表,几点了?”
“七点半了。”
小俊哎呀一声,撩开被子,匆匆忙忙穿衣服。
“这么早哪儿去呀?”
“他约我到太阳岛去!”
“谁?”
“田老师啊。”
小俊仿佛对她问“谁”感到很奇怪。
“你穿这件旗袍裙显得更漂亮了,好像不是我送给你的呀。”
“田老师给我买的。”
小俊穿好,就去洗脸。洗完脸,走入卧室,对着大衣柜镜子描眉,抹口红,小俊居然还染了鲜红的指甲!
十几天不见,小俊学会化妆自己了。
“大姐,我走了!”
“嗯。”
有了那么时髦的挎包,难怪不见了她的包袱皮儿。
…………
小俊又是很晚很晚才回来。
“小俊,你打算哪一天走啊?大姐得预先给你订票,保证让你坐卧铺回家。”
“大姐,我决定不回家了!我给你当阿姨吧!”
“给我当阿姨?开玩笑!我又不是小孩子!”
“我说的阿姨就是用人啊!大姐,你不是早晚要结婚的吗?结了婚不是早晚要生孩子的吗?将来雇别人,莫如现在雇下我啊!”
“那你自己就不结婚了?你不是订婚了吗?不是准备今年结婚的吗?”
“什么订婚不订婚的,那是北大荒那一套,不受法律保护!”
小俊不但善于打扮和化妆自己了,而且增长了法律常识,不用问必定归功于他。
“不行!你得回北大荒去,我要对你父亲负责任!”
“我绝不回北大荒去!田老师他喜欢我!他也不会让我回去的!”
“他喜欢你那是因为我喜欢你!”
“因为你喜欢我?”小俊笑了,“是不是因为你喜欢我,我才不管,反正我已经是他的人了!”
那语气,那神气,如同在说,反正他已经板上钉钉是我小俊的人了!
“什……么?”
“大姐,当着真人不说假话,他和我睡过了!那么他就得和我结婚,那么我就是一个城市女人了,那么我将来生下的孩子也是城市人了。我可不是好让人白白占便宜的姑娘!他若敢说一个‘不’字,我告他。那么他今后的前程就完蛋了!他这人把前程看得比什么都重,谅他也不敢说一个‘不’字!我现在犯愁的,倒是怎么在城里找到工作,将来我们不能光靠他那点儿工资过日子啊!大姐你帮帮我吧,帮人帮到底啊!”
“他……他是我的!”
“你的?”
小俊默默地瞧着她,继而瞧镜子。她们站在大衣柜镜前。在她们之间,一个男人究竟愿意选择谁?小俊似乎有点儿不相信自己的判断力了,因而才瞧镜子,镜子是客观的,镜子使小俊恢复了自信。
小俊又瞧着她,摇摇头笑了:“大姐,你怎么这么说话呢?”潜台词是,大姐你太缺少自知之明了啊!
那语气,那神气,那借助镜子向她证明什么暗示什么的做法将她激怒了,令她感到受了极大的羞辱。她劈面给了小俊一耳光!
“他是我的!他是婚姻介绍所用电脑介绍给我的!他就要和我结婚了!你被他玩弄了!”她叫嚷。
小俊捂脸退后,凝眸注视她。
那姑娘的目光使她感到身上发冷。
小俊说:“活该!”
结果又挨了她一耳光。
“活该!”小俊跺脚,“谁叫你不预先告诉我?我小俊要是知道,也不费心思勾引他!你不预先告诉我,怨得着我吗?”那语气,那神气,仿佛哪一个城市里的男人,都已经是她想勾引便注定会勾引上的了。
她又举起了手臂。
小俊却没再往后退,反而往前走了一步,平静地冷冰冰地说:“大姐,随你打吧。”
她的手臂缓缓垂下了。
她坐在折叠**,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羞耻感**着她的自尊心,她无声地哭了,泪水从她指缝间落下:“小俊,小俊,我……我不是因为……我怎么向你父亲交代啊!”
“大姐,你别哭,你犯不着哭,犯不着觉得对不起我……和我父亲,算我自讨的。既然他是你的,我不告他了。我小俊看在你的分儿上,放他一马,我不告他,他还是你的。你对我不错,我小俊有良心。我认了。算我报答你。”小俊语气平静,冷冰冰,包含有大大“开恩”的意味和对弱者的怜悯意味。
她的自尊心更加感到被无情地**。然而她无话可说,也觉得没有任何理由再发怒。应该乞求宽恕的,分明已不是小俊,而是她了。
她羞耻得没勇气抬一下头。
“大姐,咱们相处这些日子,小俊我太搅扰你了。几次你希望和我谈谈心里话,我不痴,我看出来了,但我没把心里话掏给你。今天,咱们好到头了,我把心里话掏给你。你听明白了,我恨你!我在第一天曾想把你这里偷个一干二净!但你一见面就对我那么好,让我不忍。我恨你们!恨你们当年那些知青!你们呼呼啦啦一大队一大队地去到北大荒了,喊着‘扎根边疆,建设边疆’‘屯垦戍边’‘战天斗地’‘改天换地’什么什么的,可你们自己说,你们给北大荒究竟带去了多少变化?河里鱼少了,草甸子里黄花少了,林子里蘑菇少了,木耳成了宝贝了!你们受过的苦,我们也受了!等我们刚刚从内心里觉得,你们的的确确是给我们带去从前没有过的东西的时候,你们呼呼啦啦,诅天咒地,骂爹怨娘地几天工夫就全走光了!还在北大荒‘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是谁?是我们!永远永远只该是我们吗?村子里哪一户生了一个小孩,我去看看,觉得好像认识了那皱巴巴的小脸儿一百年!因为那是我们北大荒人!难道北大荒永远只该有我们北大荒人吗!大姐,我告诉你,你轻易不要再回北大荒去!更不要以什么‘探家’代表团的身份回北大荒去。没谁真正欢迎你们,鬼才信你们回去是‘探家’!你们当年从北大荒回城市那才是真的‘探家’!你们永远忘不掉你们是城市人,和我们不一样的。怨恨你们的不光我小俊一个人!你知道你们走后我们有些北大荒人怎么讲?他们讲:老毛子坑过北大荒一次,知识青年又坑了北大荒一次,比老毛子坑得厉害多了!如果我们北大荒人还接待你们回去的人,那不过是礼貌。大姐,我小俊说的可都是真话!你仔细想想我这些话你就能明白我小俊了!你可要记住我的话!至于田老师,我绝不恨他。相反,我感激他!因为我被他喜欢过!你说他那是假装的?是玩弄我?假装的就假装吧!玩弄就玩弄!我不在乎!反正他让我真正高兴过,真正快活过,真正胡思乱想过!……大姐,要说的,都说了。最后一句话,我小俊对不起你了,我给你鞠躬谢罪了!”
她没有勇气抬起头。
小俊的话对于她无异于一片冰雹。
而当她终于抬起头时,小俊已不在了。
地上,是她送给小俊那双鞋。**,是她送给小俊那些衣物裙子,一件不少,包括他给小俊买的那件旗袍裙,和那只时髦的手提包。
“小俊!”她冲到走廊大喊。
“小俊!”她冲回房间,伏在窗口大喊。
“小俊!”她又迅速地离开房间,一边往楼下跑,一边大喊。
“小俊!”
“小俊!”
“小俊!”
她在楼外东跑一阵,西跑一阵,寻找着,呼唤着。
“小俊!”
“小俊!”
“小俊!”
她的声音在一幢幢高楼之间回**,如同有数以百计的姚玉慧在呼唤。
小俊一声不应。
她不相信小俊这么快就走得很远了,更不相信小俊是躲藏在什么地方了。她觉得小俊是消失了,彻底消失在城市的黑夜中了。
夜深沉。城市死寂一片如公墓。在这一个仲夏之夜,她周身寒冷得瑟瑟发抖。
“小俊!”她用尽力气呼唤了最后一声。然而那只不过是低低的一声咽唤,连微小的回声也没有造成。
三层楼的一扇窗子骤然推开,被惊醒好梦的一个男人吼:“半夜三更的穷喊什么?叫魂啊!”
夜深沉。城市死寂一片如公墓。温风拂面,她似觉北风扫来!满天星斗,她看成是大雪纷飞!在这一个仲夏之夜,姚玉慧她快要被冻僵了!连天接地仿佛冰川耸立!她“最后的停泊地”冻结在冰川之中。那山,那树,那河,那狗,那些曾非常熟悉又变得非常陌生了的人冻结在冰川之中。以及她内心里存留至今的那点儿温馨,那点儿被她的回忆一次次过滤了的诗化了的大不真实的温馨。
隔着透明的冰川,一座冰山载着她那被冻结的“最后的停泊地”在城市的深沉的死寂一片如公墓的黑夜漂浮远去……月光将那被冻结了的一切都照耀得清清楚楚,反射着水晶般的冽辉……她仿佛觉得她自己也被冻结在连天接地的耸立的冰川之中了,无法随同她的“最后的停泊地”漂浮远去……
“喵……”近处一声猫叫。
不知是不是她那只波斯猫……
8
第二天晚上,姚玉慧又用电话将她的未婚夫召了来。
他进门时,她正在厨房里洗几只玻璃杯。她知道他走近,甚至能想象出他有些鬼鬼祟祟的神情。她没有回过头去,仍然洗着玻璃杯,仔仔细细地擦拭着。
“小俊呢?”他装出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
“走了!”
“走了?”他语气中分明透出了怀疑,却仍然装出不相干的样子,他轻轻踱进了卧室,游移不定的目光东瞅西看,仿佛认为小俊被她藏了起来。
“什么时候走的?”
“昨天。”
“那……预先怎么不告诉我?”
“她是我的客人,又不是你的客人。”
“那……从礼貌上讲,我也该送送她嘛!”
“你对她够礼貌的了。”
“她……临走也没向你提我一句?让你给我带好什么的?”他那双目光老成厚道的眼睛,在近视眼镜后心虚地眨了几眨。
“提了。她说一辈子忘不了你!”
她往两只杯里倒满啤酒。
桌上,摆着几盘买的熟食和现炒的菜。
“请入座吧!”她说,摘下围裙,团成一团,扔向墙角,首先在一把椅子上坐下。
他这才走出卧室,在另一把椅子上坐下。
“我不会炒,将就点儿。”
“好主妇也是后天在生活中培养的嘛!”
两人默默注视着,举起各自的杯,都笑着。
他说:“第一次吃你炒的菜。”
她说:“我也是第一次炒菜。”
“为此干一杯?”
“奉陪。”
于是他们轻轻碰杯。
她盯视着他,慢慢倾斜酒杯,从容不迫地一饮而尽。
他却只饮半杯。
“我甘拜下风。”
“随便。”
他觉得她今天情绪真好。
她觉得他今天情绪真好。
两人喝酒,吃菜,东一句西一句聊。
他说:“听听音乐吧?”
她便起身将一盘舞曲塞入录音机。
优美的舞曲助长着良好的气氛。
“想跳吗?”
“想。”
“那咱们跳。”
“不会。”
“我教你……”
他饮尽那杯酒,站起来。
她又往他杯里倒满酒,也站起来。
他跨近她,揽她腰,握她手。
在他带动下,她机械地呆板地旋转。
“第一次?”
“第一次。”
“从来没跟别的男人跳过?”
“从来没跟别的男人跳过。”
“不信。”
“信不信由你。”
“真是第一次,证明你很有节奏感。”
“谢谢你的鼓励。”
优美的舞曲将他们从客厅送入卧室,又将他们从卧室扯到客厅。
“知道这是什么舞曲吗?”
“不知道。”
“华尔兹。高雅的华尔兹。”
“记住了。高雅的华尔兹。”
舞曲停止,两人各自归座,继续喝酒,吃菜,东一句西一句漫无边际地聊。
气氛良好。
他心里这么认为。
她心里也这么认为。
然而没有**。
优美的舞曲和刚才的双人舞,并没能将良好的气氛更推向情感热烈的**。
他想营造出一个**。
她也想。
然而两人之间的气氛始终驻在良好的状态停滞不前,他做出种种煞费苦心的尝试却无法营造**。
她也是。
他暗暗觉得遗憾。
他认为这个晚上她是多多少少像点儿女人了。
应该有**。
她同样暗暗觉得遗憾。
她往他杯里预先放了几片安眠药的齑粉。
应该有**。
因为这个晚上她企图杀了他。
她要在**过后杀了他。
要在他认为她也是一个值得他爱的女人后杀了他。
要在她得到他一次后,更进一步说,要在她得到了一次那一种满足后杀了他。
因为他是电脑通过优选之法“分配”给她的一个男人。一个科学认为对于她非常之理想的男人。她有权通过这一个男人得到一次那一种满足。
而后杀了他。
为小俊。为她自己。更为她的“最后的停泊地”——是他毁灭了它。
彻底毁灭了它。
她再也找不到赖以从城市退却的营盘了。
她觉得她已没了为将来所保留的归宿……
当她和他都离开桌子时,她又往录音机里塞入一盒磁带。迪斯科。
他坐在沙发欣赏,十指按膝点拍节。
他说:“迪斯科挺好听嘛,看来欣赏完全是观念问题。”
她说:“我同意。”
她不慌不忙收拾桌子,耐心期待安眠药发生效力。
“今天我不走吧?”
“今天你别想走。”
“我头晕了。”
“你醉了。”
“我真是个没酒量的男人……那我先到**躺着去了……”
“那你先到**躺着去。”
他摇摇晃晃走入卧室,在卧室内他转过身,用流露情欲的目光望着她,笑道:“今天你受看了点儿。”
她说:“是吗?”
她心不在焉地做这做那,有意磨蹭了些时候,然后走入洗漱间洗手,洗脸,刷牙。
为什么刷牙?有什么必要?
她暗问自己,却回答不了自己。
当她脱了衣服,上了床,安眠药已在他身上很见效了。
他酣睡得像那只饿跑了的波斯猫被她喂过安眠药片的样子,而且打着很响的鼾。
她推他,掐他胳膊,擂他那完全没有胸肌的胸脯,揪住他的耳朵往起拎他的头,将他的身体拥过来,掀过去,任她如何摆布,也无法将**的男人弄醒。
他好像不用她杀,已然死了。
这使她对他的报复心理陡增百倍!
她拉开床头柜,操起预先放入的一把削果刀。用那样的一把刀杀死一个男人,尽管是一个酣睡的不健壮的男人,也未免显得太短小了。
她想往他心口扎一刀。
想割断他腕动脉。
然而一旦操刀在手,她丝毫没了胆量。
她连杀死一条鱼的胆量也没有。
她根本不敢下手,哪怕是在他**的身体的某一部位划一道浅浅的伤口。
她对血有种特殊的恐惧。
报复心理却烧灼着她。
不知为什么,她朝大衣柜镜子瞥了一眼。
镜中那个操刀想要杀人的自己,更加令她感到恐惧。
甚于她对别人的身体流出的血的恐惧。
她操刀的手抖了。
继而她全身抖了。
那把很难用以杀死一个人的削果刀掉在**。
她怯懦地心慈手软地扑在**哭。
但她的报复心理不允许她不对他实行任何报复。
她哭着下了床,寻找到一把剪刀。
她又上了床,跪在**,将枕巾铺展在自己膝上,将他的头抱起来放在自己膝上,剪那个男人由于谢顶剩得不多的头发。
她眼里凝聚仇恨。
一边哭,一边剪。
剪下一撮,随手扔在地上一撮,仿佛那是极其肮脏的东西……
那情形并不像一个被报复心理所燃烧的女人在对一个毁灭了她最重要也最宝贵的精神依托的男人实行报复。
像圣母在哀怜死亡的耶稣……
夜里,他醒了,**着身体蹦下床,也不开灯,到客厅里来找水喝,发现她和衣睡在沙发上。
“你……你怎么还是睡在沙发上?”
她没有睡,立刻坐起。
“现在该我睡到**去了。”
“又让我睡沙发?”
“不。你走。”
她走入卧室,将他的衣物一件件从卧室内抛在他脚下。
她堵立在卧室门口,冥冥黑暗中,她枯瘦的身影也是黑的,像站在修道院门洞里的夜游的修女。
“走?……为什么?”
“你应该明白。”
他有几分明白了,默默地,一件件地,慢腾腾地穿上他的衣服。
他连鞋也穿好了之后,却不走,望着她枯瘦的黑影,期待她打消赶走他的念头。
她却说:“从今天起,我们之间的关系完结了。”
他向门口走去。
“我不会散布那件事。”
他站住了。
她又说:“这扇门从今以后再也不对你敞开了。”
他转过身,艰难地咽了口唾沫,声音滞涩地问:“你……真不散布?”
“我保证。”
“别人问起来……我……如何解释?”
“随便。比如可以说我毫无女人味儿,令任何一个男人都难以忍受。”
“那么……玉慧……再见了。”
枯瘦的“修女”身影在冥冥的黑暗中岿然不动。
马路对面一幢兴建中的大楼,电焊的弧光一闪一闪,给她的影子镶着闪烁的银边。
她倔傲地沉默着。
“你真像你装的那么坚强吗?”他低声问。
她倔傲地沉默着……
破碎从正中观察,大抵是而且起码是双向的射裂现象。
9
一星期后,当年生产建设兵团的营后勤管理员出现在姚玉慧面前。不是首先找到她那老姑娘的心理设防壁垒森严的“城堡”,而是首先找到了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办公室。
“教导员,我可被骗惨了!”
他一开口便说了这么一句话。像许多当年的北大荒知青见了当年的“顶头上司”叫“连长”“指导员”“营长”一样,他也仍叫她“教导员”,尽管他的年纪比她大。
一种沉淀了的习惯。如同获得了博士学位的人或者当了教授的人见了自己的小学老师仍毕恭毕敬一样。何况当年的教导员如今仍是个官儿,而当年的营后勤管理员如今却只不过是一个北大荒的个体农场职工了。他对她那种恭敬尤胜当年几分。
“老姜,我求求你别在这儿说,到我家去我再向你解释吧!”她唯恐他再多说一句话,几乎是拉扯着心里有些不明不白的北大荒人离开了办公室。办公室里的两位年轻姑娘在他们走后猜疑了半天。
她一路不开口,匆匆地领他走,仿佛领一位陌生人赶火车。
她不开口,他便也谨慎地沉默着。
她带他一进入房间,关上门,将拎包往沙发上一扔,站在他面前说:“老姜,在这儿,你可以往我脸上吐唾沫。可以骂我。可以扇我耳光。”
“教导员……你……什么意思啊?……他们骗我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他们?……谁们?”
“还能是谁们?当年我手底下那几个知青呗!我托运来了十几麻袋黄豆,还带来了六百多元钱。想把黄豆卖了,钱凑一起,办一批服装倒腾回去,赚笔钱。我得找他们帮忙啊!除了他们,在这城里我也没个熟人可找啊!找到了一个,就是营部开‘嘎斯六九’的那个关耀文,结果找到了一串儿七八个,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都是当年的北大荒知青。他们说这种事儿找到他们算找对了,不难办成。教导员你说我要是连他们都信不过的话,在这城里还有我老姜信得过的人吗?我把黄豆和钱都交给了他们。结果……嗨!”那北大荒人蹲了下去。
“结果怎样?”
“结果他们是串通一气儿,合伙坑骗我!钱,没了。黄豆,没了。再找他们,找不到了!好容易找到一个,一推六二五。说后来就没插手,找另外几个去!还说……”
“还说什么?”
“还说……‘不就是几麻袋黄豆,几百元钱嘛,就算意思我们哥儿几个了吧!当年你管理我们管理得够孙子的,如今孝敬孝敬我们也是应该的!’教导员,我收那十几麻袋黄豆不容易啊!那是我和小俊她们姐儿几个的血汗啊!那六百元钱,是小俊准备结婚用的钱哇!”北大荒人伤心得孩子似的哭起来。
“混……蛋!老姜,你别哭。你找我,是想告他们?我姚玉慧能给你讨回个公平的!”
“不,我不告他们!”他右手擤了一把鼻涕,左手掏手绢,掏遍几个兜儿,没掏出条手绢来,只好将鼻涕抹在鞋上,接着说,“教导员,我不告他们。当年我常对他们进行‘再教育’,如今想起也觉得挺对不起他们的。在一块儿十多年,山不亲了,水还亲不是?闹到法院,他们更恨我一辈子不是?我找你要向你借点儿钱,我保证还你!住旅馆都没钱了,被撵出来了!我总得买张火车票才回得去呀!教导员我不说假话,我在火车站蹲了一夜,从昨天中午到现在一口东西都没吃。”说到伤心处,他双手直拍自己两腿,好像鸡扇翅膀一般。
“老姜,别急,别急。今天住我这儿,我回家住去。钱我借给你,还不还无所谓。”她将他扶起,推向沙发。待他坐下,给他沏了杯茶,翻出半盒烟递给他。
那北大荒人便不再说话,勾着头,一口紧接一口贪婪地吸烟——样子真是够可怜的。大概几天没吸一口烟了。
“老姜,小俊……她……回去了吧?”她站立在他面前,心头压着负罪感,低声问。
“回哪儿?”他抬起头,很奇怪地仰望着她。
“没回去?”她的心不但被负罪感所沉重地压迫着,而且被一种极大的不安所压迫着了。
“她根本就没离家呀!这次想随我一块来,因为家里活全靠她操持,没来……”
“可是……她来过我这里呀!在我这儿住了二十多天呢!”
“不可能!绝对的不可能!”
“那……那在我这里住过的……不是小俊?”
“当然不是!教导员……什么样个姑娘啊?”
于是她向他描述了一番那个曾口口声声叫她“大姐”的“小俊”。
“她拿着我写给你的信来的呀!”
“她说她就是小俊?”
“对啊!我又怎么能怀疑她不是小俊呢?”
她找出“小俊”带来的那封信给他看。
“这……这信怎么会落在别人手里呢?哎呀!八成是李驼背的姑娘吧?她常向小俊打听你的情况,准是那姑娘!教导员……你也被骗得够惨的啊!”
“我也被骗得够惨的……”与其说回答,莫如说自言自语。
一种本能的,平素游弋在潜意识中的对人的恐惧,渐渐从她心底浮出到她那张毫无女性光彩的脸上。
他们互相望着,一时无话可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