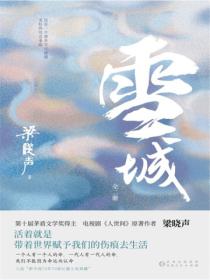3
第二天,当她来到厂房里,但见一排排组装好的桌椅,已将偌大的厂房占领得只剩一小块余地。
他却不在了。
有他的床在,有他的录音机在,她觉得他仍在身边似的。
她不复觉得这个地方阴森可怖、鬼气森森了。
她开了录音机,在节奏强烈的摇滚乐中,开始了她又一天的孤单单的工作……
那些最后从这里散去的女人们重新回到了这里。不知是被台湾女歌星的歌声和摇滚乐所吸引,还是被夜晚的灯光所吸引。她们对徐淑芳说,按照惯例,有了活儿,是要大家伙儿干的。她们提醒她,卖掉那几台破旧车床获得的钱,她不是也有份儿吗?她们的话听来振振有词,她找不到任何理由拒绝她们十分正当的劳动愿望和劳动热情。于是这个城市中的最低贱的角落,又有了紧张劳动的新气象,而郭立伟每天晚上依旧住在这里加夜班,年轻的细木工不仅仅是在帮自己的嫂子干活儿了,也是在帮她们“大家伙儿”干活儿了。那些老的或丑的女人们却并不这么认为,她们认为他完完全全是冲着他嫂子才甘心情愿地住在这么个寂寥的地方并且每天晚上加夜班到一点钟的,因此她们也就没什么必要对他表示感激。当嫂子的自然替小叔子觉得不公,她谴责她们,甚至请求她们对自己的小叔子哪怕表示出一点点感激也好。而她们偏不,她们回答她——“感激的话留给你对你小叔子说呗”或者“你们俩之间,还用得着谁感激谁不成吗?”
她们真是又老又丑。
而每当她坐在那张“床”上休息一会儿的时候,她们总是互相传递诡秘的眼色。她们是从不沾那张“床”的边儿的,她好心请她们坐,她们也不坐,宁肯就地坐块破麻袋片什么的。
有时她真想骂她们一顿。
她常常发现她们暗中窥视她,她们更用暧昧的目光看待她的小叔子;她每每替她的小叔子感到受了奇耻大辱。他却根本不注意那些老的或丑的女人用什么样的目光观察自己。他只是干活儿,吸烟,和自己年轻的嫂子并坐在“床”上,舒服地将背靠着挂了毯子的墙,说些意义不大的话,或者聚精会神地欣赏音乐。每当他和她说话的时候,她们一个个分明地是在竖耳聆听,就好像他和她说的那些意义不大的话,每一句全都包含着无数句潜台词或暗语似的。
这种时候她最想骂她们。
而这种时候她看得出来他的心情最好。
仅仅为了不破坏他的好心情,她才一次次忍住不骂她们。
令她奇怪的是他非常尊敬她们每一位。她们若组装得马虎,他常常是一声不响地拆散了重新组装而已。不得不批评她们只图组装得快,忽略了质量,他的话也讲得很礼貌,很客气,很有分寸,绝不至于使她们难堪。
一次休息时,他和她又并坐在“床”上。既然有张“床”,别人不坐,他和她何苦也不坐呢?他用火柴棍儿掏耳朵。
她说:“我替你掏。”
于是他将火柴棍儿给了她。
“转过头,冲着光。”她就跪在“床”上,伏在他肩上,替他掏起耳朵来。
而他非常惬意地闭着眼睛。
忽然她觉得厂房如同真空一样静。
她意识到了什么,立刻坐好,将火柴棍儿还到他手上,说:“还是你自己掏吧!”
那些老的或丑的女人们,一个个坐着破麻袋片什么的,像观看一对儿互相捉虱子的亲密的猴子似的,从各个角度用又有兴趣又怀有某种恶意的目光望着她和她的小叔子。
她的脸顿时充血般红。
而他,就用那根火柴吸着了一支烟,还冲她们笑。
“郭师傅,今年多大啦?”她们中的一个,不算十分老但脸盘巨大,身躯胖得像河马的一个,搭讪地问他。
“三十。”他简明地回答。
“结婚了?”
“没结。”
“有对象了?”
“没有。”
“和你嫂子同岁吧?”
“对。”
“噢……”
巨大的脸盘往前倾倒了一下,算是点了一下头。
其他的那些女人,也纷纷点头,也纷纷“噢”。
噢——老或丑的女人们失去了圆润的喉音。
她忍受不了这个。
“你们……你们无聊!无耻!”
她叫嚷着,从“床”上蹦下来跑出了厂房,气得站在两垛木料之间喘息,落泪。
他跟了出来,站在她身旁,责备地说:“嫂子,你怎么能骂她们?”
“她们……老不正经!老不要脸!”
“别骂了!”他厉声道。
她猛地转过身来,见他的神色变得那么愤怒,和他哥哥愤怒时的神色几乎一模一样。
“她们的年龄都和咱妈差不多!”
他对她提到他的母亲的时候,一向说“咱妈”,尽管她连他们兄弟的母亲的照片也没见到过,但确信他们兄弟的母亲必定是一位可敬的女人。
“她们家里生活若不困难,会让她们这种年纪的女人出来干杂活挣钱?她们对我们胡猜乱想,那也不证明她们坏!她们的脑袋又不是煤球,你总得允许她们猜想点儿什么吧?她们问的话,哪一句是无耻的话?哪一句是不正经的话?无聊是真的。我们和她们在一起,我们觉得无聊;就不许她们和我们在一起也觉得无聊?她们觉得无聊就不许她们问几句无聊的话?”
他竟对令她气愤到这种地步的事,解释得那么简单,那么平静,那么无所谓,听起竟好像根本不值得进行解释。
“你得向她们赔礼道歉。”
“我不!”
“真不?”
“就不。”
他一转身走了。
她却仍站在那里生气。
那些女人们又开始干活了,她们默默地从她身旁往厂房里搬取木料,仿佛她们习惯于受了伤害之后忍气吞声。
她擦尽了泪,也搬取木料进厂房。
“他呢?”
她们似乎都聋了,都不抬头,都一心一意地干活。
“他人呢?!”
“可不,他人呢?”
那张巨大的脸挺沉重地仰起来,河马般凸而小的一双眼睛环视着……
第二天晚上,他没来。
第三天晚上,他也没来。
第四天晚上,她到厂里去找他。
见了面,她说:“我已经向她们赔礼了。”又说,“你跟我赌气,你也得向我赔礼。”
“嫂子,我再也不跟你赌气了……”
他孩子似的笑了。
有他的帮助,加上那些女人们的“帮助”,她本需干三个月才能完的活儿,不到一个月便干完了。她和那些女人们共同得到了二千五百五十元钱。这个数目,对于钱路宽广的某些人,得来全不费工夫。一天内就可以打水漂儿似的花在餐桌上,赌桌上,或女人们的身上。而对于她,那乃是活了三十岁,第一次拿在自己手中的一笔巨款。二千五百五十元啊!然而分成十三等份的话,每人所得还不足二百元。本来这一笔巨款完全应该属于她和她的小叔子!现在却有另外十二双手等着抓取了!干活的时候她还能容忍那些女人,见了钱她竟有些憎恨她们了!她们非老即笨,她们组装的桌椅还不及总数的一半,包括她的小叔子替她们返工的;可她们现在都理所当然地等着分钱,围住她坐着破麻袋片儿什么的,都那么有耐性,目光都那么贪婪,那么兴奋。
“床”没了。她先是蹲在她们中间,一笔笔算账给她们听:每组装一套桌椅,一元五角整。一千套,一千五百元。七百套,五七三十五,一七得七……
她须得使她们每一个人心里都十分清楚,十分明白。做到这一点要有耐性。而她们那样子,似乎都在警惕她可能故意把她们算糊涂了。
“什么五七三十五,一七得七的!这账能是这么个算法吗?”
“那,依你们怎么算?”
“你这么算吧!二千套,一千五。五百套是多少?”
“五百套是七百五。”
“一百套是多少?”
“一百五。”
“二百套呢?”
“三百。”
“这不挺明白个账吗?还五七三十五,一七得七的,照你那么算,越算俺们心里越不明白了!……总共是多少?”
二千五百五十元,收据上写着。收据上写着她们也要求她算一遍给她们听。她第一次跟这么一些脑筋迟钝了的老太婆们算账,她们没费什么事儿就把她给弄糊涂了,弄到了脑筋和她们一样迟钝的地步。她们自有她们算账时的一套数学逻辑,她得运用她们那套数学逻辑算给她们听。
组装一套一元五,一千七百套应是二千五百五十元——终于使她们相信这是正确的了。而使她们进一步相信每人均得一百九十六元……余两元也是正确的,她的耐性受到了一次更大的考验。
刚开始分钱,她们中的一个忽然提出疑问:“你小叔子怎么没来?”
“他不来了。”
“为什么不来?”
“没他什么事儿啊!”
“怎么就没他什么事儿?他得了多少?活是他揽的,多得可以。但总得告诉我们个详数吧?他若是半道截去了一大笔,那可就不行!那可得找个地方摆摆理……”
“对!”
“对,对!”
她们一个个都显出非常不好惹的样子。
她说:“他一分钱也没得,他白干。不信你们可以到他厂里去问!”
她恨不得把那些钱摔在她们脸上。
“要是真的,我们也犯不上到他厂里去查问。不是余两元钱吗?你给你小叔子买几盒烟吧!”
她说:“那倒不必。我有个想法,跟你们商议商议。这一大笔钱咱们不分好不好?咱们共同存上,用来做基金,把这个小厂维持下去……”尽管她厌恶她们,她还是愿意和她们共谋一番前途。
“不好!”
她们七言八语地说不好。
她们说还是分了好,分了心里踏实。钱,无论如何是要分的。她们说她们的家里都等着花这笔钱呢!儿媳妇要买呢大衣,儿子要买录音机,孙子要买电动火车,等等,等等。
“怎么维持下去啊?”
“这我没想到个出路呢!”
“你小叔子又替你揽到活儿干了?”
“没有。我也不能总依赖着他。”
“那就分吧!”
“快分,快分!”
从这些上了年纪的,生命宛如烛之将尽的老太婆们身上,她看到了中国当代社会最底层某些家庭内部的畸形关系。她们这些老人恐怕只有用钱,才能在这种关系中收买到一点点可悲的尊敬。老人是不值钱的,晚辈们在拮据之中膨胀着享受的种种欲望,而老人们在变相地向社会行乞;倘连一分钱都不能挣了,在家庭中可能就被视为完完全全多余的东西了。
她怜悯起她们来。
分了钱,她们走了。那多余的两元钱,也不知分到她们谁手里了。她们走了后,她觉得心里轻松多了。她不愿再见到她们中的任何一个,她已经不厌恶她们了。她已经在心里宽恕了她们的卑琐,自私,对好人的罪过的猜疑和对几乎所有年轻女人的亵渎的思想;她心里只剩下了对她们的怜悯,唯其怜悯她们才不愿再见到她们。在生活中,我们最不愿见到的人,不是也往往包括那些我们最怜悯的人吗?她和她们在一起时,感到胸口仿佛特别窒闷。也许正因为她们老了,行将就木了,她们似乎需要从空间吸收比她多得多的空气……
她将一百九十六元钱用手绢包好,稳妥地揣起来。放了一段音乐静静地听,听了一会儿,关上录音机,拎在手中,环视着又变得空空****的这个厂房,不知为什么,心中竟产生了一种眷眷的依恋之情。
她正要离开,那些女人中的一个,就是在她看来哪儿哪儿都像河马的那一个又回来了,对她说:“小徐子,我信得过你!我这份儿钱今天交你了!咱俩拧成一股绳儿,把这个小厂好歹维持下去吧!总算有这么个院子,有这么个厂房,空闲在这儿怪可惜的。啊?”
她顾虑重重地审视着对方那张巨大的脸盘儿,没立刻接对方的钱。
“你别小瞧我。我能‘忽悠’!‘忽悠’是什么你懂不?”
她摇了摇头。
“‘忽悠’……就是上上下下的,方方面面的,单靠一张嘴把事儿办成!这是能耐。我有这能耐!我看你有点儿帅才。我是个好将才!你当厂长,我当副厂长!你只管出谋划策,我到处替你‘忽悠’他个天昏地暗!咱俩的钱加在一起四百来块,也不算少。如今光夹着个空皮包到处做大买卖的能人多啦,咱俩女的还不顶一个男的吗?”
“你……真那么能‘忽悠’?”她犹豫,怀疑。
“当然,你可以打听,凡认识我的,谁不知道我能‘忽悠’!”
“好!”她接过了钱。
“大娘……你姓啥呀?”
“姓马。别叫我大娘,我还没那么老。往后你叫我婶儿吧!”
“马婶儿,咱俩……同舟共济了?”
她觉得马婶儿姓马之后,倒不那么像河马了。
“同舟共济!”
4
晚上,她打电话将小叔子“请”回到家里。叔嫂一块儿包饺子时,她向他讲述分钱的情形,她以为他听了准会取笑那些女人们一番,不料他没有。
他叹口气说:“咱妈活着的时候也那样啊!为了一斤石棉线被定成一等的还是二等的,跟人家脸红脖子粗地吵。为了几毛钱的工钱,扯住人家,跟人家掰着指头算过来算过去……嫂子你不能要求每一个穷人对钱都那么大度……尤其不能要求这些老太太……”
她觉得她小叔子的那颗心善良得令她感动。
她想到了自己返城后的种种经历……
想到了自己为挣钱怎样给别人下跪……
想到了自己为挣钱在大雨中怎样奔到卸煤厂怎样对那些男劳改们喊叫:“谁要我?你们谁要我?”
想到了自己是怎样被乖戾的命运推进了这个家……
她低声说:“可也是……”
饺子包好了,她让他在屋子中间支起小圆桌,安静地坐在桌旁吸支烟,不许他再插手帮她煮。火很旺,锅开得快。她心情愉悦,暂时忘记了自己明天又是一个待业者。她轻轻哼着歌儿,忙得相当利索。一边看着锅,一边剥好了一小盘蒜,还和他一问一答地说着话儿。
“立伟,马婶儿要和我把那个小厂维持下去!我俩的钱合在一块儿了,做基金。你看我们能成不?”
“哪个马婶儿?”
“就是最胖的那一个呀!她主张的。”
“怎么不成?嫂子,现在饿不死人。我还能帮你揽到活呢!”
“真的?那太好啦!嫂子就一点儿也不愁了!马婶告诉我她能‘忽悠’……立伟你知道‘忽悠’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如今‘忽悠’也是本事啊!”
“那你怎么不学?”
“我学也学不会啊,那得靠点儿天才!”
他在里屋笑了。
她在小厨房里也笑了。
她将饺子一盘盘端上桌子,压住炉火,进了屋,安安心心地坐在他对面,和他一块儿吃起来。
“香吗?”
“香。”
“淡不?”
“不淡。”
她不由得回想起,去年郭立强参加一中考试那天,她也曾早早起来给他包了顿饺子。她转脸朝迎门的墙上望去——她和郭立强的结婚照挂在墙正中,照片上的他有点儿腼腆地微笑着。当时摄影师让他笑一笑,他就那样微笑了一下。如今那微笑成了他最后的微笑。按说最后的美好的东西,总该是极有价值的。可他那最后的微笑,除了造成她的一段感伤的回忆,还另外有些什么价值呢?一年,仅仅一年,由于他的死被强烈激怒过的当年的返城知青们,有几个还谈起“一中事件”?有几个还谈起一九八〇年“五一”国际劳动节那一天举行的震惊全市的大示威?有几个还谈起郭立强这个死者的名字?此时此刻,有谁还在怀念他?除了她,除了他的弟弟。生活就是这样,生活的本质就是这样。对于生活,一切过去了的事情,都终将是被人忘却的事情。在人心里最不能久驻的恐怕还是人。一年,仅仅一年,她每每怀念起他时的那种感伤,不是已经一天天从她心间消散了吗?就像峡谷之中的浓雾,在太阳升起后会渐渐消散一样。对于她,他已不过是她曾爱过的一个男人。如此而已,仅此而已。她又想起,为了宁宁,她和吴茵在江畔会面的时候,吴茵曾对她说应该忘掉之类的话。当时她认为吴茵是个心灵冷漠的女人,甚至对吴茵的话有些反感。而事实上,她已经差不多忘掉了他。此刻她注视着照片上的他,心灵竟是平静的。她暗暗吃惊于自己此刻心灵的平静,却也只是吃惊而已,并不能再引起更使她激动的感情波澜了。她不得不承认,无论谁忘掉一个死去的人,那本是很正常的事,绝不证明人的心灵怎样。人忘掉一个爱过的人,应该如同忘掉一个恨过的人。人不应该生活在怀念之中,人不应该靠回忆生活,不管那种回忆多么影响人。也许只有对生活绝望了的人,才靠某种怀念某种回忆过日子吧?
吴茵的话是有道理的吗?
还是我也变得心灵冷漠了?
不……我的心灵并未变得冷漠。恰恰相反啊,它分明是比原先更能蓄藏情感了啊!
摄影师当时也让她笑一笑,她似乎微笑了一下,从照片上却看不出来,照片上的她满面笼罩着愁苦。而此时此刻的她在吃饺子,心情愉悦,毫无感伤。即使想要强迫自己感伤起来也不能够。她暗暗吃惊于自己怎么会是这样一个女人?暗暗怀疑自己是不是已经不知不觉地变成一个坏女人了?
“嫂子,想什么呢?”
“我……在想你哥……”
郭立伟也朝墙上的照片望了一眼,轻轻放下筷子,盯着她说:“嫂子,该忘的,就不该再想了。”
“包括你哥哥?”
“……包括我哥哥。”
她万万料不到他会这么回答!回答得这么平静!她也轻轻放下筷子,双手捧着脸颊,两肘支在桌上,迎着他的目光,低声问:“立伟,你已经把你哥哥忘掉了吗?”
“怎么可能呢?”他垂下了目光,“只是不再想他了。”
“原先你想他的时候,想哭过吗?”
“想哭过。”
“我也是。”
“有时候我觉得哥哥是到外地去了,说不定哪天就会突然回来,突然站在我面前。”
“我也是。”
“以后我想起他的时候,就好像有一个人在旁边劝我,对我说,死是解脱,他解脱了,你还没有。他从来没有轻松地活过,你该活得比他轻松。一个人只有一条命,你得珍惜你自己的命,你得让你的生活中幸福多一点儿,快乐多一点儿……”
他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她坦白地说:“我也是。”
“有时候,我总觉得,那个劝我的人好像就是……”
“是谁?”
“是你……”他又抬起头看了她一眼,随即低下。
“我……也是……”
“我就学会了劝自己,我常常对自己说,郭立伟,你哥哥死了,你还有个好嫂子呢。你也得尽力,使你嫂子的生活中幸福多一点儿,快乐多一点儿……”
我也是——她说。没说出口,在心里说。她始终注视着他,她想:立强,我们如果不是有一个弟弟,而是有一个妹妹,那我的命会是怎样的呢?
她受一种深厚而隐秘的柔情的驱使,缓缓站了起来,镇定地走到他身边,毫无顾忌地捧起了他的脸,俯视着,端详着。她觉得那张脸真是年轻!显示着几分男人的成熟,又显示着几分孩子的天真,成熟和天真在那张脸上交融得很和谐。她心中鼓**起一阵爱意。就在那一时刻她忽然明白了自己,明白了她除去需要工作之外尤其需要什么。她丝毫也不为自己的举动感到羞耻,更不感到罪过。她任凭那一种深厚而隐秘的柔情驾驭着她,她任凭那一阵爱意鼓**着她的心。她的脸红艳艳的,那乃是因为柔情和爱意一下子从她心里溢了出来。她觉得自己就好像是一棵笋,不是从土地下,而是从塘底的淤泥中,一下子就生长了出来,瞬间冲破了一片死水,嫩绿嫩绿的,清清新新地挺立在水面之上,并且继续勃勃地生长,一节一节地向上拔。
他也是镇定的,仿佛他早就习惯了她对他如此亲爱似的。他笑了,说:“其实饺子有点儿淡,我口太重。”
她说:“不,是我口太轻了。”
她就将他的头搂抱在自己怀里,抚摸着他的脸,问:“小伟,你生活得快乐吗?”
很自然的,她竟叫起他“小伟”来了。
“就算快乐吧。”他一动不动,像孩子似的接受她的柔情和爱意,平平静静地说,“工作挺累的,又实行劳动定额,下了班,洗过澡,唯一的愿望是轻松轻松。听音乐,看小说,下棋,看电视,有时候也到俱乐部去看录像,去跳舞……”
“你还跳舞?”
“跳。干吗不跳?腿瘸也要跳。跳舞的时候我会忘了自己腿瘸,人家都说我跳得不错。”
“姑娘们愿意跟你跳?”
“认识我的就愿意,我也不请陌生的姑娘跳。”
“星期天呢?星期天你怎么打发?”
“星期天到松花江去游泳,划船。有时候一个人逛公园儿,安安静静地在那儿坐上半天,看人……”
“看人?”
“嗯。看那些男人女人,愉愉快快地从身边走过,我就觉得自己的心情也愉快起来……还坐碰碰车玩……”
“碰碰车?碰碰车是什么车?”
“你碰我,我碰你,碰来碰去的一种车。大人小孩儿都喜欢坐着玩……”
“难怪你星期天也不回家,你就没想想我一个人在家里怎么打发星期天吗?”
“想过……怎么能不想呢?嫂子,录音机我不拿回去了,留给你。如今一个人的生活里不能没有音乐啊!下个月我奖金能发挺多,我还有点儿存款,先给你买个电视机吧。买彩色的钱不够,只能买黑白的。从电视机里,你能了解到别人如今怎么生活,还能了解到外国人如今怎么生活……”
“我不要你给我买电视机,我以后挣了钱自己买。”
“那不是得以后吗?就算我先借给你钱。”
“你也活得很幸福?”
“不。不幸福……”他的头在她怀中摇了摇。
“我听你说都觉得你活得很幸福。”
“那是活得快乐。幸福靠命,快乐靠自己。我觉得不幸福,我才要多给自己寻找快乐……”
她又将他的脸捧了起来,凝视着他的眼睛,耳语似的说:“我也是……可我没处给自己寻找快乐……”
“嫂子,明天我们一块儿到公园去好吗?”
“好……”
“没工作也要高兴地活。还是我那句话,如今挣钱不是件难事了。用不着愁眉苦脸,留心看看,你就会知道。信吗?”
“信……”
她突然离开他,从食品柜中取出瓶酒,有些激动地说:“你看。我还买了一瓶酒呢,洋河大曲。售货员说是好酒,我也不知道究竟好不好,是好酒吗?”
他从她手中接过酒瓶,看了看商标,点头道:“老百姓喝,也算是好酒了。”
“嫂子陪你喝吧?”她又从食品柜中取出了两个酒盅,一个摆在他面前,一个自己拿着,复坐下去。
他却站了起来,说:“我想回厂了。”
“不行!”她也站了起来,预备阻拦他。
他说:“嫂子你别拦我,我回厂看电视,今晚有足球赛。”
她说:“你连饺子也没吃几个。”
他说:“吃饺子就那么回事儿,兴趣全在包的时候。”
她说:“那我酒白买了?特意为你买的!嫂子陪你喝一盅你再走。我去拌点儿白菜心……对了,还有一只烧鸡我都给忘了……”说着要往厨房走。
“什么都不用。”他拧开瓶盖,斟满了一盅酒,擎起来说,“我就喝一盅再走。今天嫂子高兴,我心里也高兴!”
她制止道:“别喝!”探身从他面前拿过酒瓶,给自己斟满了一盅酒,也擎起来,庄重地说:“嫂子有言在先,陪你喝一盅。”
他说:“嫂子,这酒度数高,你象征性的吧!”
她坚决地说:“不,我来真的!”言罢,两眼瞧着他,徐徐地就将那满满一盅酒饮尽了,她的脸顿时更加艳红了。她辣得吐出了舌头,赶紧夹起个饺子塞入口中。
“那我再喝两盅谢嫂子今天一番心意。”他又从她面前拿过了酒瓶,为自己连斟两次,眉都不蹙一下,连饮连尽。
她也为他夹起个饺子,走到他面前,送到他口边。
他一笑,说:“三盅酒,哪儿到哪儿!还多吃个饺子干什么?”
她说:“你吃下这个饺子压压酒,要不你走了我也这么举着……”
他耸耸肩膀,顺从地一口吞下了那个饺子,迈步往外便走。走到门口,他转过身,环视着屋里的家具,说:“这套家具是我一年前为嫂子和我哥做的,现在式样又过时了!我已经备下了料,嫂子,等你结婚时我再为你打一套式样更新的!”
她望着他,喃喃地说:“小伟,你别走……”
他问:“嫂子,你还有什么事儿闷在心里吧?”
她低下了头去,默然良久,抬起头说:“明天就是星期天,你……真带我到公园去?”
“真的。”
“我也要坐碰碰车玩!”
“那有什么不可以呢?我陪嫂子高高兴兴地玩上一整天就是了。嫂子你可要打扮得漂亮点儿,现在哪儿有穿你那种蓝涤卡的?涤卡过时了……”
“嗯……”
“明天我不回家找你了,我直接在公园门口等你。九点!”
“那,你得答应我,玩够了陪我回家,咱俩一块儿在家吃晚饭!”
“我听嫂子的。”
她望着他推开门走出去,一时觉得他从家中带走了许多对于她是不可缺少的东西,还带走了她内心那种柔情和那种爱意。一年多了,一年零五个月了,她似乎已经忘记了自己是一个女人。在愁苦的待业时期,她很少走出这个院子,走出这条街。而明天他要带她到公园里去,高高兴兴地玩上一整天!没有工作的人也是可以高高兴兴地玩上一整天的吗?为什么不可以?他不是还跳舞并且被公认跳得不错吗?他不是告诉她如今饿不死人,如今不难找到活儿干吗?她竟很迫切地想要知道,一九八一年,除了台湾女歌星邓丽君的录音磁带,周围的生活中到底还多了些什么?在这个院子,在这条街以外的年轻女人们,都开始穿些什么服装了?涤卡过时了?连涤卡都过时了,那么还有什么没过时呢?她不太信……
她还想彻底抛掉忧愁,彻底抛掉锈一般的回忆。她还想要一个人的快乐,要一个三十岁的女人的快乐。他说得对,幸福靠命,快乐靠人自己去寻找。他说得对,一个人只有一个命……他说得对,一个人应该对自己负起热情的责任……
他说得对,吃饺子就那么回事儿,兴趣全在包的时候。饺子,她也不想吃了。
她忽然很想听音乐,于是她从他留下的几盒磁带中挑选出了“邓丽君”放入录音机,音量拨到刚好能听清,悠悠然地坐在桌边听起来。
她觉得那台湾女人唱得真是悦耳动听,尽管唱得娇滴滴的,但娇得并不令人讨厌。她想,女人的本性总是娇滴滴的,自己不是就常常产生想向谁撒娇的心态吗?而那个“谁”说穿了不是一个男人吗?而没有这个“谁”确实地存在着她不是才常常觉得活得很累,很乏味儿,委屈上加委屈吗?不是正因为无处撒娇,她才常常无缘无故地在小叔子面前作嗔状吗?如果女人们无处撒娇,女人们很快就会老的吧?如果女人们无处撒娇,男人们会变得娇滴滴的吧?人原本并不是很复杂的吧?人先虚伪了其后才复杂了吧?那么人有什么正当的理由非虚伪地活着不可呢?我虚伪吗?我从前是虚伪的吗?我现在变得虚伪了吗?虚伪的女人能对自己负起热情的责任吗?徐淑芳,没谁要求你监视你怎样活着啊!谁又凭什么要求你怎样活着监视你怎样活着呢?如果他们是虚伪的,他们更凭什么呢?如果他们自以为是有权要求你监视你的,那他们便也必定受着别人的要求受着别人的监视!那人人都活得很累活得很乏味儿活得很委屈不就是很活该的事儿了吗?那么谁还能对自己有着热情的责任?
轻轻的一个吻
叫我思念到如今……
吻……
活到今天,她只被两个男人吻过。一个是王志松,在北大荒,在僻静的小河旁,他笨拙地吻了她一下,她却吓哭了。当年她十九岁。除了他的笨拙和她的恐惧,记忆中没再留下任何别的印象。可从此以后他便认定了她是属于他的,她也这么认定了。一个笨拙的吻就占有了一个十九岁的姑娘,如果这还不算荒唐可笑,那么吻对于女人就真是太可怕的事儿,男人们也太混蛋了……那也能叫作吻吗?另一个是郭立强。他是那类绝不吻一个还不是自己妻子的女人的男人,可能也是为了这一点他才决定和她结婚。他简直视女人为神圣之物,他自己也想力争做一个神圣的男人。她和他都如圣男圣女一般在这个家里共同生活了不短的时日,而别人们,包括善良的邻居们都不相信他们真的就是圣男圣女。即或人人相信,其意义又何在呢?后来她将自己的肉体在他绝望至极的时候主动奉献给了他。用自己的一个平凡女人的活生生的肉体,验证了他不过是一个平凡的男人。那个夜里他们尽吻尽吻,没有什么“轻轻的”那一说;同时也验证了他们对彼此亲爱饥渴到了何等程度。那是一个蓝色的夜。一个迷醉的、满足的、血液燃烧的、冲动之中跌宕着冲动的夜。结果第二天早晨那个“神圣”的男人就变成了一个单纯而天真的大孩子,喋喋不休地对她说,他有了她就什么都不怕了,连死都不怕了。并且分明地开始有些向她撒起娇来。结果那天早晨他连一架破扬琴也没来得及修好,就被公安人员带走了,就再也没回来,永远……
那个蓝色的夜晚!
她回想起他的时候也更是回想起它。一次次的回想,使那个夜晚竟变得像宗教日一样神圣起来,使这个家也变得神圣起来,使这张床也变得神圣起来,使每天晚上都睡在这张**的她,也于近乎神圣的回想之中变得近乎神圣起来。这个家竟渐渐地具有了教堂的色彩。正因为如此,她的小叔子不回来。正因为如此,她每次对他的挽留,哪怕是最真心实意的挽留,也不可避免地包含着虚伪的成分,以及生怕触犯了某种神圣的东西,心灵颤巍巍地恐惧……
那一个蓝色的夜晚!
那一个迷醉的、满足的、血液燃烧的、冲动之中跌宕着冲动的夜晚!
一年多了,整整一年零五个月了,女人的心在寂寞之中老化着,女人在寂寞之中渐渐忘却着自己是女人。柔情像呼吸一样,吐出去又吸进来。爱意像炉火一样,旺起来立刻又被一铲煤压下去,在心怀内进行悄悄的势将更旺的燃烧,煤压不住火。她天生是一个靠爱的自觉才能进一步自觉到自己是一个女人的女人。如果说她从前不是,那乃是因为这样的女人的成熟大抵是迟缓的。而她现在已经成熟这样一个女人了,已经是这样一个女人了。像一颗成熟得无比饱满的果子,悬挂在被折断的枯枝上。
生命的最生动的最任性的活泼,早已从这个小小的空间消散尽净了。一年多的时间,足以从封闭不严密的空间消散更多的东西。
她不禁又望着墙上的结婚照。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的合影。“上帝”和“圣女贞德”的合影。“上帝”到天国去了,“圣女贞德”仍在人世间。因为她常常觉得他仿佛是上帝,无时无刻不在俯视着她,所以她不敢以为自己是夏娃,只能难以胜任地充当“圣女贞德”。同时充当嫂子。夏娃怕上帝。而他到天国去之前,却又并没有把她那颗女人的原本极容易充满柔情极容易嚣**起爱意的心收回去带走。上帝也有疏忽的时候吗?她忽然起身,将椅子搬向那面墙,踏着椅子将相框从墙上摘了下来。连看也不看,翻出块花布包好,放进了柜子里。刚刚坐下,又觉得放在柜里并不妥。于是拿出来,一会儿塞到这里,一会儿塞到那里,尽往目光所不及的角落塞,无论塞到哪儿还是觉得不妥。她手持着它,咬着嘴唇沉思了片刻,猛转身走到厨房去,挑开几圈炉盖,将它放在炉膛中了。她蹲在炉旁,用炉钩子从炉口擞火。擞着擞着,呼地一片红光耀眼,炉火熊熊地燃烧起来了。她听到炉中发出了轻微的玻璃的碎裂声。
不知收藏在何处才好的东西,烧掉是最妥的收藏。她觉得她自己掌握了一个生活小常识。
她很想再喝点儿酒,她觉得喝了一盅酒之后那种头脑稍许有点儿发晕的感觉挺新鲜,也挺好玩。墙上没有了那照片,她才认为真正不被约束不被监视了,并且觉得这是良好的自我感觉。
她细细地切了一盘菜心儿,拍了蒜放上,浇香油浇醋拌糖。尝了尝,挺有滋味儿,挺爽口,挺满意。她又片下了一盘鸡肉,加了该加的作料,一手端一只盘子,独自笑盈盈地进得屋来,摆在桌上,就拧开酒瓶盖儿,款款落座,自斟自饮。太辛辣。她想,既然算是好酒,太辛辣也值得一醉方休啊!今宵不醉,更待何时呢?
录音机停了。
那个台湾女人……她叫什么来的?……邓……丽……君……好个娇滴滴的邓丽君!你也唱得够累的了!女人向女人撒娇作嗲……忒没意思!……对酒当歌……不行,没歌不行……
于是她从录音机中“请”出邓丽君,换了一盘磁带。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
她大声问,习惯地朝那面神圣的墙瞥了一眼。
墙上一片空白。
“几何?”
是李白的诗吗?好像中学老师讲过是李白的诗?李白作这么俗的诗吗?还诗仙呢……看来也是一个……大俗人啊!
“把酒问青天……明月几时有?”
也是李白那个大俗男人的诗吗?……初几学的呢?初二,还是初三?
她朝窗外看了看。
明月哪儿去了呢?……连星也没有……
“把酒泪(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这又是什么人的诗呢?……可惜只记住两句……
没有歌不行!这么高兴的夜晚……
录音机仍不唱,她便站起来,自唱:
我失骄杨君失柳
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
问讯吴刚何所有
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
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
唱罢,又斟一盅,壮丽地一饮而尽。她的身子摇晃了一下,本能地用一只手撑住了桌子。她觉得自己似乎变成了一根羽毛,只要那只手一离开桌子,就会飘起来。她觉得这种感觉真是奇妙极了啊!唱到“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其情不能自禁,离开桌子,摇摇晃晃做舞蹈状,脚下无根,险些倾倒,扑于**。她顺势将床单扯下,披在肩头,双臂担之,似袅袅广袖,左舒右展,前飘后敛,且旋且舞……
她醉了。